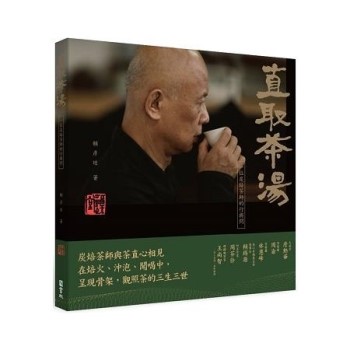身入茶流.初驗茶氣
喝著茶,茶也喝著我。茶氣、茶性由體入心,去垢洗淨一整個人生的歷程作用,我算是領教徹底了。
隨著年紀大,茶也越喝越重。尤其是高發酵、重焙火的「紅水烏龍」,厚重的深迴之韻深深吸引著我,在茶湯各種酸澀苦甘的轉圜中慰藉著我,彷彿特別懂得我那特別想穿越中年尷尬與迷惘的心。當時還沒到中年,我卻已經無預期的進入現在所謂的「中年危機」。
從小對於生命就有一種莫名的迷惘。小學四年級,我在國語課本上塗鴉式的寫著「人生在世無幾何」,這個句子惹來老師與父母當年詫異不解的眼光。沒想到三十五、六歲當逢事業略略有點成就時,馬上發現名利完全不能換取相對等的快樂幸福,隨之湧來的往往是更多的空虛與迷惘。一旦期待落空後,又找不到生命的重新定義,我就陷落了。
童年未知的懞懂如同山霧繚繞,轉成中年的具體迷惘就成了風雨雷電。事業結束後我一心想尋求生命的出口、越想越困惑。在偶然機緣下沒頭沒腦就跑到一個寺廟,含糊的跟著打了一個佛七。雖然沒有得到什麼答案,但那次經歷卻讓自己身心在茫散中第一次進入並體會了未曾有過的敏感細膩,於此也深深改變了我後來對於茶的許多認知。
…
那是1990年夏天,我開車到大坑山區散心,閒逛著剛好碰到一座寺廟,聽到禪堂裡有些人在大聲唸經。門口站著位小沙彌,他童言童語的趨前問我要不要一起唸經?我點頭說好。其實那時我連「阿彌陀佛」都不曉得,進去之後他把經本直接打開、隨手一指,說「嗯!從這裡開始。」我眼忙手亂跟著唸誦的同時,心想這小沙彌應該才四、五歲,大字不認得幾個,怎麼會一翻就知道從哪裡開始?後來幾次進出這座寺廟,卻再也沒見過他。
回家以後這段遭遇一直在心裡懸著,約隔一、二個星期我又再跑去寺裡,看見門口貼了打佛七的訊息,心想沒事就報了名。二星期後報到,等我進去以後才發覺慘了!當時對於佛法完全陌生,更何況佛七有許多儀軌及念誦。那時佛七除了一天要念佛九支香,還要拜一千拜!這一千拜並不是固定排時間一起拜,而是自己必須犧牲休息睡眠找空檔完成。後來才聽說,這裡的佛七是當時全台灣最嚴格的佛七。進來佛七後因為對人生的苦惱無處發洩,也有點急於尋求生命的答案,就沒管那麼多,很努力的跟著大家高聲誦念佛號、繞佛、拜佛。到了第三天開始感覺頭有點暈,一摸自己後頸部,突然發現竟然凸起乒乓球大的圓球,鼓漲的球肉頗為難受。然仍心想,先不管它了繼續努力吧!
隔天在繞佛時,突然從球肉上方抽出了一絲難以形容的清涼,並且往頭頂徐徐射去。頓時只感覺自己頭腦清涼,身體也變得輕柔,幾天下來所有的憂煩全消,本來快撐不下去的體力,竟然也感覺拜佛上下跪拜毫不費力,甚至不用拜墊。即使整身的力量把膝蓋直接釘到大理石地面,也沒有一絲痛感。
原本每天晚上來到最後一支跑香,幾乎會耗盡一整天最後剩餘的力氣。此刻發覺自己竟然絲毫不費任何氣力,幾圈跑下來大氣也不喘一個,而且呼吸變得異常深細、念頭變得越來越少。這時甚至進一步驚訝的發現,身體內有些暖暖的氣流,緩緩的在流竄。心裡對此有種陌生恐懼,趕緊去請教主七和尚,法師笑笑也說不上來。
解七出寺之後,碰觸到外界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這才發現自己七天竟然瘦了將近十公斤!身體從此變得敏銳,對事情原本既有的從感覺到定義都在晃動,內心更渴望找尋一種全新認知;尤其沒法待在人多味雜的地方了,口味變淡到連鹽也不吃,只好關在家與世隔絕。
…
佛七結束第二天,我上台北找詹勳華老師,他看我整個人怪怪的,就問要不要喝點「不一樣的茶」?
當時詹老師泡了一杯陳味濃郁、黑不見底的老茶,說了聲「喝」!才一入聞,當時整個人、心、氣就靜下來。再細細喝上幾口,發現茶裡頭深沈的那股熱流與我身體內的暖流,巧妙穩定的結合在一起。才喝了幾口禁不住就閉上眼,不自覺的陶醉茶湯在體內的種種流動,奇妙與驚訝徹底覆蓋過陌生與恐懼。
詹老師這才跟我說:「這就是氣。」這即是我對於「茶氣」的初入門。從此以後我深深愛上這份氣感,甚至一度迷戀不已。中年的無明迷惘時期,可以說就靠著茶氣以及紅水烏龍賦予的振奮、老茶給予的撫慰中,孤獨、自戀又顛簸的繼續的向前尋求。
…
開啟了身體對於「覺受」之門,不禁好奇更想往未知新鮮處探索,迷戀著身體覺受的各種作用,也開始因過於敏感而開始逃離現實、躲避人群。
在這一段避世的孤獨中,我更深刻努力的去面對這份「迷戀」。那時覺得世界好像什麼都沒有了,就只剩下茶願意彼此相伴。經常兀自泡著、靜默的喝著;心裡沮喪時就會奮力的泡出去、再狠狠的嚥進來。
不斷心想讓茶氣在體內衝擊出無窮力道,甚至衝破自己的孤悶,乃至將自己的自閉,用茶氣在體內逼出所有的驚異與舒坦。茶,變成是孤獨時唯一貼心的陪伴,在「泡出去、喝回來」的深刻相對中,整個世界只剩下茶是比人更值得託付的一切。因為只要虔誠以對,茶就會回饋你相對的真誠,且從不背叛。
…
那時有一位好友恰逢情傷,我跟一向不喝茶的他說:「喝茶吧!」於是他開始認真喝。才沒多久,某天的那一道茶湯真的觸碰內心,他也不禁感動到痛哭出聲,釋放了他積存難出的情苦。事後他問我,為什麼會這樣?我說:「朋友會騙你,但茶不會騙你!你給它什麼,它就回你什麼。只要真誠以待、有時它回給你的,甚至遠遠超過你所想要的。」
茶就是如此,擁有大地如母般的療癒力量。但後來我也發現,一旦這種喝茶情緒成為某種自憐自艾,加上錯用了感官撫慰,一切的作用僅在生命表層,對於生命本質與現實生活都是沒有助益的。
因為那不是茶的療癒,嚴格來說是人性的自我催眠,只是暫時逃避,並且在躲避的同時,又掩蓋了原本需要真實面對的確切與必然。生命往往會因為過度的躲避、錯誤的撫慰,而在無形間慢慢枯萎。而茶的存在,並不是基於陪伴走向枯萎。若要深知茶的芳香透淨,讓生命還原出一種深沈的釐清與安慰,不能就再耽溺於此。
喝著茶,茶也喝著我。茶氣、茶性由體入心,去垢洗淨一整個人生的歷程作用,我算是領教徹底了。
隨著年紀大,茶也越喝越重。尤其是高發酵、重焙火的「紅水烏龍」,厚重的深迴之韻深深吸引著我,在茶湯各種酸澀苦甘的轉圜中慰藉著我,彷彿特別懂得我那特別想穿越中年尷尬與迷惘的心。當時還沒到中年,我卻已經無預期的進入現在所謂的「中年危機」。
從小對於生命就有一種莫名的迷惘。小學四年級,我在國語課本上塗鴉式的寫著「人生在世無幾何」,這個句子惹來老師與父母當年詫異不解的眼光。沒想到三十五、六歲當逢事業略略有點成就時,馬上發現名利完全不能換取相對等的快樂幸福,隨之湧來的往往是更多的空虛與迷惘。一旦期待落空後,又找不到生命的重新定義,我就陷落了。
童年未知的懞懂如同山霧繚繞,轉成中年的具體迷惘就成了風雨雷電。事業結束後我一心想尋求生命的出口、越想越困惑。在偶然機緣下沒頭沒腦就跑到一個寺廟,含糊的跟著打了一個佛七。雖然沒有得到什麼答案,但那次經歷卻讓自己身心在茫散中第一次進入並體會了未曾有過的敏感細膩,於此也深深改變了我後來對於茶的許多認知。
…
那是1990年夏天,我開車到大坑山區散心,閒逛著剛好碰到一座寺廟,聽到禪堂裡有些人在大聲唸經。門口站著位小沙彌,他童言童語的趨前問我要不要一起唸經?我點頭說好。其實那時我連「阿彌陀佛」都不曉得,進去之後他把經本直接打開、隨手一指,說「嗯!從這裡開始。」我眼忙手亂跟著唸誦的同時,心想這小沙彌應該才四、五歲,大字不認得幾個,怎麼會一翻就知道從哪裡開始?後來幾次進出這座寺廟,卻再也沒見過他。
回家以後這段遭遇一直在心裡懸著,約隔一、二個星期我又再跑去寺裡,看見門口貼了打佛七的訊息,心想沒事就報了名。二星期後報到,等我進去以後才發覺慘了!當時對於佛法完全陌生,更何況佛七有許多儀軌及念誦。那時佛七除了一天要念佛九支香,還要拜一千拜!這一千拜並不是固定排時間一起拜,而是自己必須犧牲休息睡眠找空檔完成。後來才聽說,這裡的佛七是當時全台灣最嚴格的佛七。進來佛七後因為對人生的苦惱無處發洩,也有點急於尋求生命的答案,就沒管那麼多,很努力的跟著大家高聲誦念佛號、繞佛、拜佛。到了第三天開始感覺頭有點暈,一摸自己後頸部,突然發現竟然凸起乒乓球大的圓球,鼓漲的球肉頗為難受。然仍心想,先不管它了繼續努力吧!
隔天在繞佛時,突然從球肉上方抽出了一絲難以形容的清涼,並且往頭頂徐徐射去。頓時只感覺自己頭腦清涼,身體也變得輕柔,幾天下來所有的憂煩全消,本來快撐不下去的體力,竟然也感覺拜佛上下跪拜毫不費力,甚至不用拜墊。即使整身的力量把膝蓋直接釘到大理石地面,也沒有一絲痛感。
原本每天晚上來到最後一支跑香,幾乎會耗盡一整天最後剩餘的力氣。此刻發覺自己竟然絲毫不費任何氣力,幾圈跑下來大氣也不喘一個,而且呼吸變得異常深細、念頭變得越來越少。這時甚至進一步驚訝的發現,身體內有些暖暖的氣流,緩緩的在流竄。心裡對此有種陌生恐懼,趕緊去請教主七和尚,法師笑笑也說不上來。
解七出寺之後,碰觸到外界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這才發現自己七天竟然瘦了將近十公斤!身體從此變得敏銳,對事情原本既有的從感覺到定義都在晃動,內心更渴望找尋一種全新認知;尤其沒法待在人多味雜的地方了,口味變淡到連鹽也不吃,只好關在家與世隔絕。
…
佛七結束第二天,我上台北找詹勳華老師,他看我整個人怪怪的,就問要不要喝點「不一樣的茶」?
當時詹老師泡了一杯陳味濃郁、黑不見底的老茶,說了聲「喝」!才一入聞,當時整個人、心、氣就靜下來。再細細喝上幾口,發現茶裡頭深沈的那股熱流與我身體內的暖流,巧妙穩定的結合在一起。才喝了幾口禁不住就閉上眼,不自覺的陶醉茶湯在體內的種種流動,奇妙與驚訝徹底覆蓋過陌生與恐懼。
詹老師這才跟我說:「這就是氣。」這即是我對於「茶氣」的初入門。從此以後我深深愛上這份氣感,甚至一度迷戀不已。中年的無明迷惘時期,可以說就靠著茶氣以及紅水烏龍賦予的振奮、老茶給予的撫慰中,孤獨、自戀又顛簸的繼續的向前尋求。
…
開啟了身體對於「覺受」之門,不禁好奇更想往未知新鮮處探索,迷戀著身體覺受的各種作用,也開始因過於敏感而開始逃離現實、躲避人群。
在這一段避世的孤獨中,我更深刻努力的去面對這份「迷戀」。那時覺得世界好像什麼都沒有了,就只剩下茶願意彼此相伴。經常兀自泡著、靜默的喝著;心裡沮喪時就會奮力的泡出去、再狠狠的嚥進來。
不斷心想讓茶氣在體內衝擊出無窮力道,甚至衝破自己的孤悶,乃至將自己的自閉,用茶氣在體內逼出所有的驚異與舒坦。茶,變成是孤獨時唯一貼心的陪伴,在「泡出去、喝回來」的深刻相對中,整個世界只剩下茶是比人更值得託付的一切。因為只要虔誠以對,茶就會回饋你相對的真誠,且從不背叛。
…
那時有一位好友恰逢情傷,我跟一向不喝茶的他說:「喝茶吧!」於是他開始認真喝。才沒多久,某天的那一道茶湯真的觸碰內心,他也不禁感動到痛哭出聲,釋放了他積存難出的情苦。事後他問我,為什麼會這樣?我說:「朋友會騙你,但茶不會騙你!你給它什麼,它就回你什麼。只要真誠以待、有時它回給你的,甚至遠遠超過你所想要的。」
茶就是如此,擁有大地如母般的療癒力量。但後來我也發現,一旦這種喝茶情緒成為某種自憐自艾,加上錯用了感官撫慰,一切的作用僅在生命表層,對於生命本質與現實生活都是沒有助益的。
因為那不是茶的療癒,嚴格來說是人性的自我催眠,只是暫時逃避,並且在躲避的同時,又掩蓋了原本需要真實面對的確切與必然。生命往往會因為過度的躲避、錯誤的撫慰,而在無形間慢慢枯萎。而茶的存在,並不是基於陪伴走向枯萎。若要深知茶的芳香透淨,讓生命還原出一種深沈的釐清與安慰,不能就再耽溺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