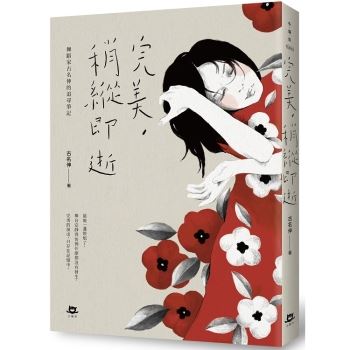〈修了三輩子的福氣〉
多年前就有個體悟,這輩子能夠當導演或是編舞家的人,一定是修了三輩子的福。怎麼說呢?你不過有了個想法希望達成,就有人資助你,又有人身體力行的投入執行,還有一幫子人打點大小的事,小至訂個便當,大至設計燈光或是執行宣傳等,最後還得有觀眾進來欣賞,而且他們還得買票啊!當然你可以說這是各憑本事,或每個人都在其中各得其所,但是別忘了,你就是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為什麼是你?就因為你的起心動念,於是在不同時刻都有需要別人幫助才能達成的期望。這難道不是命好嗎?
話又說回來,的確從每個人的角度來看,參與表演藝術的每個人真是各得其所。會表演的人,無法自己想演就可以演;做燈光的人,必須要有作品讓他發揮。表演藝術原本就是集體合作才能完成的使命,然而,冤有頭債
有主,總是要有人開個頭,可是為什麼是你?這是我每次做演出的過程中必定會經過的心路歷程。
特別是在最後關頭,大家都得聚精會神地投入時,我總會心存感激地欣賞著這一切。每個人都是全體呈現的一環,環環相扣,每個人都很重要,都不能出錯。對於能夠讓這種機緣再度發生,我總是感動莫名。
雖然各行各業也需要人與人的配合,但是藝術劇場的狀況就是不一樣。通常各種行業的存在,都有其賴以營生的理由,就算公益事業也有其必要持續操作的內容和架構。相較之下,藝術劇場明顯脆弱得多,沒有人有把握是否一定會成功,每一個製作有沒有未來性,似乎是一種奢侈的想像。但想做的人還是要做,儘管它的結果再好,到頭來還是如曇花一現,充其量可以自我安慰「凡走過的必留痕跡」。且就先從我自己的角度說起。當作品的念頭升起,在腦子裡形成了各種自有理由的想像,於是就要開始找到各方可以共同達成這個想望的人馬。找人討論音樂的協助或合作,仔細推敲舞者角色的適用性、確認尋覓經費的管道、爭取理想場地的使用機會、找到各種相關人脈資源來幫助製作的進行,接著還有服裝、舞臺、燈光、宣傳等的討論。這些都還只是紙上談兵,一個個方面布署妥當就得照進度表依序推進。從藝術面到製作面、從前期的籌備到中期的實際操作、從進劇場前密鑼緊鼓的排練,到製作群瘋狂地推票。最後當技術單位推著一箱箱的器材進入劇場,第一顆燈光被開啟後,接著各組人馬相繼進駐。前臺忙前臺的、後臺忙後臺的,編導和表演者時時刻刻在調整自己,面對每一個時刻的精力和態度。最後關頭,時間像退潮的海岸,不知不覺,回頭已無岸。然後大門開啟,觀眾進場。觀眾席燈暗,舞臺燈亮;舞臺燈暗,觀眾席燈亮。結束!一箱箱器材被推了出去,最後一個人關掉最後一盞燈。靜靜的舞臺回復到先前的樣子,一切就像不曾發生過任何事的樣子。只有經歷過的人在記憶中相信這一切真的發生過。
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發這種事件的人,要不就是有某種程度的妄想性格,要不就是著魔成癮了。但不管怎麼說,他的想望還真的能夠達成,絕對是修了三輩子才有的福氣。
對於這修了三輩子才有的福氣,我認為能在好人家當寵物貓或寵物狗,也是需要修三輩子才能擁有的。你看自以為是主人的人,如何在寵物身邊忙得團團轉地伺候寵物就知道了。有時當我身為那個始作俑者,頂著三輩子修來的福氣,為了自己的想望,忙累到像落魄的狗一樣時,我還真不介意拿我那三輩子修來的福氣去做哪個好人家的寵物狗呢。
〈我們可不可以不怕輸〉
「不要讓你的孩子輸在起跑點上」,廣告臺詞是這麼說的,說得振振有詞,說到父母的心坎裡了,於是孩子們奔波於各種確保他們從學習之初就不會遺漏的能力準備中。孩子從小被動地學會如何把時間排滿,可憐的父母也費盡所有力氣地玩接龍遊戲,一家人繞著小孩的日程表團團轉,只為努力地證明孩子是優秀的。「不要浪費時間」是生活的座右銘,孩子的忙碌絕對不亞於成人,一家人要出門,需要配合的往往是孩子的時間,而非大人的時間。這年頭在臺灣,起碼在我身邊,那種喝茶看報紙的公務員,和手背在身後澆花的教授,已經差不多絕種了。取而代之的是數不清的加班,和有假沒得放的現實。所有事情都有機制,機制提供做事依循的管道,也建立了稽查的方法和準則。
為了確認每一件事都有被妥善地做好,於是我們花了一份力氣做事,再花一份相對的力氣檢核過去所做的事。可怕的是,在檢核的過程中怕有偏頗之嫌,於是必須要由裡到外、由外到裡,轉換切入的視角,看細節、看整體,翻了再翻,只怕檢查不夠周全。說得好聽是健全制度應該配備全套措施,但稽核制度難免涉及人性,於是負責的專家為了表示責任感與專業度,再怎麼樣也要提出一些改善建議。再者,由於稽核制度的嚴謹落實,一些沒有骨氣的人索性因為不敢承擔可能被質疑的責任,而放棄任何有突破性的決定。稽核制度是社會進步的助力或是阻力?
多年前我還在文建會扶植團隊之列時,就耳聞友團對製作量要求「要五毛給一塊」的作法。我們被要求一年一個新製作,他們一年做三個,說好聽是積極進取,一方面可以提拔新人,另一方面則是交出豐富成績單的好學生。政治正確,不是嗎?但背後工作人員簡直哀聲連連,因為工作量壓死人不打緊,每一個新製作的預算都不是「拮据」兩個字足以形容的。所以連鎖反應地,每個人都學會了如何用最少的錢做最多的事。光看這種景象就讓我對表演藝術界能否進步存疑。
創作需要的自在與空間一再地被壓縮,大家為了生存已經耗費掉所有的力氣。這個環境裡存在著各種不安與焦慮,怕輸掉的不安,以及總想要做得更好的焦慮。
主流社會裡充斥著集儒家道統和資本主義之大成的觀點,對論成敗與英雄都有一致性的標準。質的考量不容易有評斷,索性就取決於看得懂的量吧。所以總希望愈來愈多、愈來愈快、愈來愈好、愈來愈周全、愈來愈清楚,起跑的槍聲一響,大多數的人都不疑有他地往同一方向衝鋒。雖然我們都祝福人家:「放輕鬆!」但是也都知道不能真的「放輕鬆」,因為﹁放輕鬆﹂會輸掉。我們都怕輸,輸了,就會被淘汰。朋友把女兒由城市轉學到鄉下,因為城市的功課太多做都做不完,沒有時間玩耍。我為這種另類媽媽拍手,但也會為她的小孩捏一把冷汗。不是因為她的想法有什麼不對,而是因為其他的人,包括製造遊戲規則的人,都不是這麼想的。螳臂擋車不容易,看來這隻螳螂最好也別費力擋車,乾脆就自己到旁邊的草地上玩耍曬太陽好不愜意。
試問我們可不可以跳開來看看通盤的畫面,那些不安與焦慮真的有必要嗎?還是只因為身陷在單一思維而生出的無明。重點在我們對自己有沒有信心,對別人有沒有信任。只要排除不信任,我們是有可能讓孩子快樂地玩耍長大,讓工作充分的授權,事情做得少而美,不怕輸,不怕錯!
多年前就有個體悟,這輩子能夠當導演或是編舞家的人,一定是修了三輩子的福。怎麼說呢?你不過有了個想法希望達成,就有人資助你,又有人身體力行的投入執行,還有一幫子人打點大小的事,小至訂個便當,大至設計燈光或是執行宣傳等,最後還得有觀眾進來欣賞,而且他們還得買票啊!當然你可以說這是各憑本事,或每個人都在其中各得其所,但是別忘了,你就是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為什麼是你?就因為你的起心動念,於是在不同時刻都有需要別人幫助才能達成的期望。這難道不是命好嗎?
話又說回來,的確從每個人的角度來看,參與表演藝術的每個人真是各得其所。會表演的人,無法自己想演就可以演;做燈光的人,必須要有作品讓他發揮。表演藝術原本就是集體合作才能完成的使命,然而,冤有頭債
有主,總是要有人開個頭,可是為什麼是你?這是我每次做演出的過程中必定會經過的心路歷程。
特別是在最後關頭,大家都得聚精會神地投入時,我總會心存感激地欣賞著這一切。每個人都是全體呈現的一環,環環相扣,每個人都很重要,都不能出錯。對於能夠讓這種機緣再度發生,我總是感動莫名。
雖然各行各業也需要人與人的配合,但是藝術劇場的狀況就是不一樣。通常各種行業的存在,都有其賴以營生的理由,就算公益事業也有其必要持續操作的內容和架構。相較之下,藝術劇場明顯脆弱得多,沒有人有把握是否一定會成功,每一個製作有沒有未來性,似乎是一種奢侈的想像。但想做的人還是要做,儘管它的結果再好,到頭來還是如曇花一現,充其量可以自我安慰「凡走過的必留痕跡」。且就先從我自己的角度說起。當作品的念頭升起,在腦子裡形成了各種自有理由的想像,於是就要開始找到各方可以共同達成這個想望的人馬。找人討論音樂的協助或合作,仔細推敲舞者角色的適用性、確認尋覓經費的管道、爭取理想場地的使用機會、找到各種相關人脈資源來幫助製作的進行,接著還有服裝、舞臺、燈光、宣傳等的討論。這些都還只是紙上談兵,一個個方面布署妥當就得照進度表依序推進。從藝術面到製作面、從前期的籌備到中期的實際操作、從進劇場前密鑼緊鼓的排練,到製作群瘋狂地推票。最後當技術單位推著一箱箱的器材進入劇場,第一顆燈光被開啟後,接著各組人馬相繼進駐。前臺忙前臺的、後臺忙後臺的,編導和表演者時時刻刻在調整自己,面對每一個時刻的精力和態度。最後關頭,時間像退潮的海岸,不知不覺,回頭已無岸。然後大門開啟,觀眾進場。觀眾席燈暗,舞臺燈亮;舞臺燈暗,觀眾席燈亮。結束!一箱箱器材被推了出去,最後一個人關掉最後一盞燈。靜靜的舞臺回復到先前的樣子,一切就像不曾發生過任何事的樣子。只有經歷過的人在記憶中相信這一切真的發生過。
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發這種事件的人,要不就是有某種程度的妄想性格,要不就是著魔成癮了。但不管怎麼說,他的想望還真的能夠達成,絕對是修了三輩子才有的福氣。
對於這修了三輩子才有的福氣,我認為能在好人家當寵物貓或寵物狗,也是需要修三輩子才能擁有的。你看自以為是主人的人,如何在寵物身邊忙得團團轉地伺候寵物就知道了。有時當我身為那個始作俑者,頂著三輩子修來的福氣,為了自己的想望,忙累到像落魄的狗一樣時,我還真不介意拿我那三輩子修來的福氣去做哪個好人家的寵物狗呢。
〈我們可不可以不怕輸〉
「不要讓你的孩子輸在起跑點上」,廣告臺詞是這麼說的,說得振振有詞,說到父母的心坎裡了,於是孩子們奔波於各種確保他們從學習之初就不會遺漏的能力準備中。孩子從小被動地學會如何把時間排滿,可憐的父母也費盡所有力氣地玩接龍遊戲,一家人繞著小孩的日程表團團轉,只為努力地證明孩子是優秀的。「不要浪費時間」是生活的座右銘,孩子的忙碌絕對不亞於成人,一家人要出門,需要配合的往往是孩子的時間,而非大人的時間。這年頭在臺灣,起碼在我身邊,那種喝茶看報紙的公務員,和手背在身後澆花的教授,已經差不多絕種了。取而代之的是數不清的加班,和有假沒得放的現實。所有事情都有機制,機制提供做事依循的管道,也建立了稽查的方法和準則。
為了確認每一件事都有被妥善地做好,於是我們花了一份力氣做事,再花一份相對的力氣檢核過去所做的事。可怕的是,在檢核的過程中怕有偏頗之嫌,於是必須要由裡到外、由外到裡,轉換切入的視角,看細節、看整體,翻了再翻,只怕檢查不夠周全。說得好聽是健全制度應該配備全套措施,但稽核制度難免涉及人性,於是負責的專家為了表示責任感與專業度,再怎麼樣也要提出一些改善建議。再者,由於稽核制度的嚴謹落實,一些沒有骨氣的人索性因為不敢承擔可能被質疑的責任,而放棄任何有突破性的決定。稽核制度是社會進步的助力或是阻力?
多年前我還在文建會扶植團隊之列時,就耳聞友團對製作量要求「要五毛給一塊」的作法。我們被要求一年一個新製作,他們一年做三個,說好聽是積極進取,一方面可以提拔新人,另一方面則是交出豐富成績單的好學生。政治正確,不是嗎?但背後工作人員簡直哀聲連連,因為工作量壓死人不打緊,每一個新製作的預算都不是「拮据」兩個字足以形容的。所以連鎖反應地,每個人都學會了如何用最少的錢做最多的事。光看這種景象就讓我對表演藝術界能否進步存疑。
創作需要的自在與空間一再地被壓縮,大家為了生存已經耗費掉所有的力氣。這個環境裡存在著各種不安與焦慮,怕輸掉的不安,以及總想要做得更好的焦慮。
主流社會裡充斥著集儒家道統和資本主義之大成的觀點,對論成敗與英雄都有一致性的標準。質的考量不容易有評斷,索性就取決於看得懂的量吧。所以總希望愈來愈多、愈來愈快、愈來愈好、愈來愈周全、愈來愈清楚,起跑的槍聲一響,大多數的人都不疑有他地往同一方向衝鋒。雖然我們都祝福人家:「放輕鬆!」但是也都知道不能真的「放輕鬆」,因為﹁放輕鬆﹂會輸掉。我們都怕輸,輸了,就會被淘汰。朋友把女兒由城市轉學到鄉下,因為城市的功課太多做都做不完,沒有時間玩耍。我為這種另類媽媽拍手,但也會為她的小孩捏一把冷汗。不是因為她的想法有什麼不對,而是因為其他的人,包括製造遊戲規則的人,都不是這麼想的。螳臂擋車不容易,看來這隻螳螂最好也別費力擋車,乾脆就自己到旁邊的草地上玩耍曬太陽好不愜意。
試問我們可不可以跳開來看看通盤的畫面,那些不安與焦慮真的有必要嗎?還是只因為身陷在單一思維而生出的無明。重點在我們對自己有沒有信心,對別人有沒有信任。只要排除不信任,我們是有可能讓孩子快樂地玩耍長大,讓工作充分的授權,事情做得少而美,不怕輸,不怕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