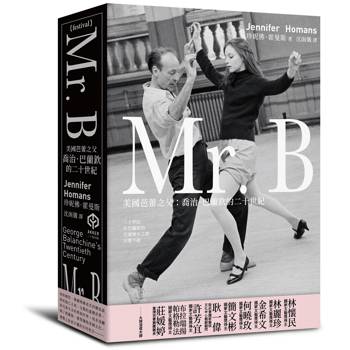〈第三章 戰爭與和平〉
(選摘)
一九一三年八月的某個暖日,年僅九歲的喬治抵達皇家劇院學校,他的第一個童年就此結束。第二個「像狗一樣」的童年緊接著開始了。這個形容詞不僅道出男孩無力對抗母親的憤怒,更貼切地描述了他不甘於從天堂般的生活跌入地獄般的生活。一切發生得太快,新生活又離家太遠,男孩的世界瞬間天翻地覆。學校看守人取代母親的角色;爐灶換成學校;俄國鄉村生活則變成歐洲化的宮廷藝術訓練,講求紀錄和常規。急遽的變化讓喬治的生活經驗斷裂成不相干的兩部分,而他只能自己默默嘗試理出一絲頭緒。
在當時,有兩個現實因素左右著喬治所處的世界局勢,並對芭蕾舞者的職涯發展影響深遠。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他逐漸發現這兩個因素的真面目,亦即皇朝和戰爭。皇朝奠定了俄羅斯芭蕾舞發展的基礎藍圖,而所有在宮廷中長大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參與到這段奇特的歷史。一切始於彼得大帝雄心勃勃的歐洲化計畫,該計畫率先將法國和義大利的芭蕾舞引入俄羅斯。這不僅是文化借鑒,更是一項規模宏大、極具野心的大規模人性工程,直到布爾什維克革命(又稱十月革命)才被推翻,終結把俄羅斯人變成歐洲人的行動。在彼得大帝及其繼任者的統治下,制服、軍階、聖彼得堡的建築風格、食物、手勢、禮儀和語言皆來自異國的歐洲文化。從那時起,沙皇開始有迎娶外國公主的慣例,例如尼古拉二世的妻子既是德國人,同時也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女。此外,直到革命前夕,宮廷的通用語言一直是法語。芭蕾舞屬於這項歐洲化計畫的一環,其根源於義大利和法國,長期用於訓練歐洲貴族的禮儀、儀態和手勢。
然而,俄羅斯人的內在本質並未消失。在最奢華的歐式住宅中,即便屋裡擺滿進口大理石、精美的藝術品和水晶吊燈,往往還會設置一個充滿俄式風情的小天地,有著溫暖的爐火、茶炊和舒適的地毯。和他們的房子一樣,有人說俄羅斯人的精神世界也是分裂的,「真正的」內在俄羅斯靈魂隱藏在歐洲人的外表之下。因此,若想成為歐洲人,勢必得歷經一場精心策畫的戲劇排演。在排練場上,所有角色皆須反覆排練、練習背誦臺詞,並熟記舞步和走位。精彩的芭蕾舞劇和各式表演就建立在這種「成為歐洲人」的意識上,成為奠定俄羅斯宮廷生活的基石。芭蕾舞於是成為一種儀式性的工具。俄羅斯人透過反覆排演,實現對異國文化的追求與幻想,企圖讓歐洲文化淩駕於自身傳統,最終達到支配眾人生活的目的。
在宮廷的背後,或者說在其核心中,還隱藏著一個更深層、冷酷的事實。喬治也被迫學著接受這件事,亦即農奴制和「農奴芭蕾舞者」的特殊制度。十八世紀末,凱瑟琳大帝解除了貴族在宮廷中的職責,許多貴族於是返回奢華的鄉間莊園,開始在莊園中複製這個戲劇性的宮廷階級制,還玩起假扮歐洲人的遊戲。莊園的主人扮演沙皇,農奴則飾演朝臣。主人不遺餘力地訓練這些農奴,讓他們適應陌生的新角色,甚至引入歐洲芭蕾舞大師、歌唱指導員、音樂家和詩人來教導年輕的農奴女孩扮演國王的朝臣。經訓練後,這些農奴芭蕾舞者得以參加各種舞會和儀式活動,猶如主人佩戴的飾品。
藝術與性之間的界限薄如蟬翼,農奴芭蕾舞者(其中許多是訓練有素、多愁善感的藝術家)往往還充當情婦或私人後宮的一員,不僅要在裸身或衣著暴露的狀態下表演,偶爾還會用皮鞭當道具。接受羞辱和抹殺自我都是成為舞者的必備技能。時至十九世紀中葉,支撐這種放縱行為的封建財政結構已崩潰,許多農奴舞者因此被賣給皇家劇院。她們在那裡重獲自由,但也付出新的代價,這次是為沙皇本人提供服務。宮廷負責決定她們的職業(這位去演戲,那位去跳舞),且服務年資須達十年,以補償培訓支出。若未經許可,她們無法擅自離開城市或結婚,性剝削仍司空見慣。在喬治來到劇院學校的數年前,農奴制和這些殘餘陋習已正式畫下句點,但劇院學校的許多學生和教職員仍出身低微或曾為農奴,而皇家劇院的管理者則為地位較高的前農奴主人及其後代。當時芭蕾舞團的領舞瑪蒂達.克謝辛斯卡婭(Matilda Kschessinskaya)便是延續前朝惡習最臭名昭彰的例子。人們都稱呼她為「金色瑪蒂達」(Golden Matilda)。其父為波蘭人物舞蹈的舞者,雖然她出身卑微,但卻長期受皇位繼承人尼古拉的供養,享受充滿豪宅、珠寶、藝術品和濱海假期的奢華生活方式。當尼古拉成婚並登基為沙皇後,瑪蒂達就轉為跟著公爵。
這一切都悄悄發生在皇家劇院學校厚厚的石牆內。此學校在這段歷史中也扮演了某種角色,其起源可追溯至宮廷建立的初期。當時安娜皇后邀請一位法國的芭蕾舞大師前來教授宮廷侍者的子女們儀態和舉止,因為這他們能否勝任這個角色的關鍵。同時,安娜也請芭蕾舞大師為皇家軍校的少年們授課,這正是拒喬治於門外的精英軍事訓練學校。軍校與芭蕾訓練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芭蕾最早源於法國和義大利,而從那時起,芭蕾就與軍事藝術並肩發展,這種搭配也成為宮廷生活的核心特徵。十九世紀初,當沙皇的建築師在設計羅西街時,也試圖將以石頭為建材的宮殿蓋在城市中,因此他們決定將皇家劇院學校設立在沃龍佐夫宮(Vorontsov Palace)的正對面,那裡正是沙皇精英軍事學院的所在地。軍事與舞蹈分別代表戰爭與和平的藝術,兩者為歷史上的近親,踏著相同的步伐並採用共同的訓練方法,從不同的面向致力打造帝國的紀律、階級和專制體制。這就是喬治的新家。
喬治恰好在艱難的時刻來到這所學校。此時,賦予芭蕾舞生命的皇室正身陷重重危機,沙皇和他的手下忙著在宮殿周圍築起越來越厚的高牆,以保護搖搖欲墜的帝制。冬宮透過國家暴力無情鎮壓來自四面八方的罷工、暗殺、爆炸、飢荒和農民起義。尼古拉二世越來越無法勝任歷史賦予他的角色,顯得十分無能。儘管尼古拉二世曾在慶祝羅曼諾夫(Romanov)家族統治三百年的奢華慶典上正式露過面,包括一場精彩的芭蕾舞表演,但除此之外,人們輕易發現沙皇與他聲稱並熱衷於代表的「人民」日漸疏遠。他退居幕後,成日享受妻子主持的維多利亞式家庭生活,屋內有塞得鼓起的舒適傢俱、綠色花環、粉紅色絲帶、丁香花、典雅的英式印花布,以及掛滿閃閃發光聖像的牆壁。費奧多羅夫(Feodorov)村位於沙皇村,是沙皇在亞歷山大宮附近所建、一個如玩具般的俄羅斯小鎮。這個村落是他最喜歡的家庭住所,裡頭有一座特別設計的新民族主義風格大教堂和一個處於地底的私人「洞穴教堂。」這裡完全體現了對俄羅斯輝煌過往的戲劇性幻想,不僅駐守的士兵個個身著十七世紀風格的服裝,連火車站也是舞臺布景,其莫斯科式的帳篷屋頂讓人聯想到早期的俄羅斯宮殿。更甚者,尼古拉和皇室成員如鴕鳥般埋首於皇家劇院和芭蕾舞劇中。正如一位老副官在沙俄政權崩潰前夕對困惑的法國大使所說,在許多俄羅斯人看來,觀賞表演代表「俄國社會過去的真實寫照,不僅過去如此,現在、未來也都該如此,充滿秩序、嚴謹、對稱的社會,處處細節都照顧到。」
在尼古拉步步退縮時,他也在不經意間削弱了自己的神聖光環。該光環以兩項名義為基礎,包含他錯誤的民族主義,以及宣稱自己為子民的代表。從一些小事上就可以觀察到這一點。舉例來說,沙皇的面孔首度印製在全國通行的郵票上,不過也會遭例行註銷。他甚至允許自己的形像出現在托盤、瓷器、糖果盒和圍巾等俗氣的紀念品上(不過手帕則被嚴格禁止),這讓一眾審查員十分不滿。尼古拉也向農奴芭蕾舞者的傳統借鏡,允許男演員在舞臺上扮演自己,以他們卑微的舞者形象呈現沙皇的威嚴。
一九一三年八月的某個暖日,喬治剛剪了頭髮並穿上制服,焦急地等候如何開始新生活的指示。而僅僅一年後,沙皇就站在冬宮的陽臺上,低頭看著跪在地上舉著聖像和宗教旗幟的人民,宣布俄國開戰。四年後,列寧就站在另一個陽臺上,這次是在芭蕾舞女演員克謝辛斯卡婭的家裡。他在憤怒的民眾面前宣布革命揭開序幕。列寧將臭名昭著、當時已遭洗劫一空的金色瑪蒂達宅邸做為其總部。此舉無疑撼動了宮廷的權威,同時深深影響小喬治.巴蘭欽瓦澤現在所屬的宮廷世界。
學校裡的生活似乎變動不大。喬治多年來每天都穿同樣的制服,甚至在開戰後的壓抑生活中也是如此著裝:褶皺整齊的軍裝式黑褲、修身白襯衫、領子上有里拉琴徽的淺藍色夾克,配上一頂圓形、硬邊、軍校生式樣的帽子。這種制服設計是為了讓男孩能夠站得筆直、走得穩且到位。上述是日常生活的服裝,而跳舞的服裝則不同。他們會穿一種極簡且暴露的短褲,長度至膝蓋以上,再配上統一的純色合身襯衫、襪子和白色芭蕾舞鞋。這一身是男舞者的標準配備。女生則住在一樓,她們穿著矢車菊藍長裙、端莊的白色披肩和黑色圍裙,而熨燙過的白色圍裙會留到週日才穿。走讀生則身著雜棕色的衣服。年紀較小的女孩會在背上紮一條辮子,並稱學姊為「女神」;年紀較大的女孩可以紮兩條辮子,並將披肩疊成大三角形後,不慌不忙地披在背上,以特別彰顯自己的身分。低年級的女孩在跳舞時會穿著有襯裙的灰色及膝連衣裙,高年級的女孩則穿著粉紅色連衣裙,只有少數班上表現最傑出的女孩,才能穿上夢寐以求的純白連衣裙。顏色越純代表達到美德標準越高。女孩們都統一穿著乾淨的粉紅色棉質長襪,在臀部處用鬆緊帶束起,秀髮整齊地向後紮成低髮髻,芭蕾舞鞋上的絲帶在腳踝處繞二或三圈,然後整齊地塞進鞋裡,有點像希臘涼鞋。
正如同對年輕舞者的嚴謹規範,對朝臣的規範同樣嚴格和詳細。每個人在宮廷裡都必須身著制服,或至少須根據位階治裝。舉凡刺繡圖案、裙子和裙襬的長度、剪裁、布料、顏色都有嚴格的規定。位階的變化意味著更換制服,就像劇院街那些模仿朝臣的孩子們一樣,朝臣會透過不同顏色表示位階的晉升:從白褲變成黑褲,紅絲帶則變成藍絲帶,而銀線會變成金線。尼古拉二世甚至下令將男子的軍裝和舞會制服分開,且跳舞時須卸下武器以免顯得格格不入。不僅是服裝,姿態、語言、座位,連在官方場合的席位都經過精心規劃和安排。
喬治以一系列的紀律為一天的行程揭開序幕。天剛濛濛亮時,學校管理員在敲響了鐘後,一陣響亮的鐘聲會傳遍學校,他們接著在宿舍裡走來走去。孩子們會先在一個巨大的公用黃銅水槽中用冷水洗漱,再快速穿好衣服。緊接著第二次鐘聲響起,示意孩子們檢查時間到了,這時他們會排成兩列、抬著頭並讓雙手垂落在身側。男孩會微微低頭敬禮,女孩則行屈膝禮並互道「早安」,然後一起禱告。早餐上午八點開始,通常是茶和麵包外加一顆雞蛋(奶油配給可減半換成每週兩次的糕點),接著上午九點開始上課,十到十二點則為芭蕾舞課。午餐提供肉類、義大利麵和蔬菜,結束後他們會在成人管理員的嚴格監督下,在花園或小區周圍散步。管理員會特別注意年齡較大的女孩,以免她們遭興致盎然的紳士窺視。
教學課程在小教室裡進行,教室裡擺放著傾斜的木桌和黑板。喬治的課程包括法文(為了和沙皇溝通)、歷史、地理、算術、俄語和俄國文學、美學、劇場化妝技巧、幾何學,以及他最擅長的東正教教義問答。當時的教育體系已升級為以德國學制為榜樣的實用專科中學,課程十分嚴謹。晚餐和甜點時間在下午四點半開始。學生們在鋪著白色桌巾的長桌上用餐,每張長桌的首位都坐著一位學校職員。學長姐像啄木鳥一樣,以猶如宗教儀式般正式且嚇人的方式逐一糾正年幼孩子的禮儀。抬首望去,只見一尊聖像高高立在靠近天花板的角落,身旁的玻璃後襯著一支鮮紅的蠟燭。這漫長的一天似乎沒有句點,他們接著上了第二堂舞蹈課,包含默劇和擊劍。對於大男孩來說,還有交誼舞課,這是他們難得能與女孩們見面的機會。最後,他們會練習樂器(喬治練習鋼琴)、做回家作業,簡單地吃完普通的棕色卡莎後就上床睡覺。晚上九點,精疲力盡的他們終於得以就寢。不過,喬治竟能設法找到微弱的燈光並藉此讀著他最喜歡的《馬克斯與莫里茨》(Max and Moritz)、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的作品或《福爾摩斯探案集》,並忘我地一路讀到深夜。澡堂每週提供一次蒸氣浴,若有孩子剛從外面骯髒的城市歸來,也可以在澡堂中擦洗身體。
學生的生活受到嚴格管制。他們不能從事其他運動,例如溜冰、騎腳踏車或打球等等,因為可能傷害到寶貴的肢體。訪客只能在有人觀察的情況下,於規定時間進入單獨的房間內會面。孩子們連回家一趟都要經過精心安排和監控。男孩們喜歡玩羅賓漢或戰爭遊戲,但嚴禁使用刀劍。實際上孩子們幾乎不須走出院子到石牆外,因其所需的一切皆唾手可得,包括一間醫務室和一座小巧優雅的教堂,教堂內裝飾華麗、璀璨炫目的聖幛被置於教堂大廳的右側,高度直達天花板。瓦西里.福斯托維奇.皮古列夫斯基(Wassily Faustovich Pigulevsky)是一位神父,他與妻子和九個孩子住在學校裡,愛打牌和喝酒的程度就像他愛上帝一樣。他從一八八○年代起就在這所學校工作,負責設計教義問答的課程,內容包括新舊約的《聖經》、斯拉夫異教和西方宗教。他對此接受懺悔。當學生列舉自己的罪過時,他會斥責學生為「小傻瓜」或「白癡。」某次四旬期輪到喬治端聖餐酒時,瓦西里對一個臉色蒼白、神情萎靡的新生低聲道:「你可以喝這酒,味道不錯。別擔心,我可以幫你多倒一點。」
就像農奴芭蕾舞者的歷史一樣,學生的背景十分多元,包含孤兒,以及前農奴、舞者、引座員、服裝師、裁縫和作曲家的子女,其中許多人都沒有父親,只有少數人來自軍人家庭,而來自特權階級者更是鳳毛麟角。這些孩子都受到皇家管理員的嚴格看管,管理員有男有女,如女督察瓦爾瓦拉.伊凡諾夫娜.利霍舍斯托娃(Varvara Ivanovna Likhosherstova)。當喬治入學時,她已在學校工作很久了。她是一位貧困貴族的遺孀,也是少將的女兒,曾住在莊嚴的斯莫爾尼修女院。孩子們大多不知道她的悲慘身:她曾嫁給一位軍官,後來軍官死後獨留她一人照顧兩個兒子,因此她迫切需要收入。瓦爾瓦拉脾氣執拗、以刻薄著稱,不僅難以相處,外表還貌似神父,身著一襲垂地的黑長袍,下巴方正得像個男人,白色的高領上扣著胸針,一頭花白的頭髮顯得格外嚴肅。她還隨身攜帶一副長柄眼鏡,以方便檢查年輕學生的全面生活細節。
違反規則的孩子會受到明確的懲罰,例如獨自站在走廊的大鐘下,遭受其他路過的孩子鄙夷地指指點點或竊竊私語,有時則是不給糖或週六不能回家,更嚴重的是週日禁足。喬治也曾受過這些懲罰,紀錄本上詳盡記錄著他童年時犯過的錯,包含大喊大叫、打人、撒謊,以及找藉口逃避工作和職責。在許多週末,他會去附近阿姨的公寓以逃離這種被管束的生活,有時也會搭火車回盧納喬基(Lounatjoki)。在他入讀的第一年聖誕節,其父甚至為所有男孩舉辦了一場派對,這意味著一群教職員、教師、學生與喬治,一起在某個週末擠上火車前往芬蘭的鄉村參與盛會。梅利頓最喜歡這種形式的派對,但喬治卻躲在角落裡害羞地看著大家。
其實喬治經常留在學校,獨自在音樂教室裡度過空蕩蕩的週日午後。音樂教室是一間大舞蹈室,掛滿沙皇和其他政要的厚重鍍金畫像。喬治似乎不在意這個房間會鬧鬼,裡頭住著一位老修士,或名叫魯奇或里奇的歌唱老師,據說後者曾在這裡上吊自殺。膽小的孩子們卻就地玩起尋找靈魂的遊戲。在靠近芭蕾舞臺的角落裡,擺放著一架精美華麗的三角鋼琴(有時是兩架),喬治可以獨自在沙皇和修士幽靈散發的憂傷氣氛下,數小時不間斷地練習和進行即興創作。有時,他也會在另一間練習室裡,凝視著陰鬱神祕的伊斯托米娜(Istomina)肖像。近一個世紀前,文豪普希金愛上這位楚楚可憐的舞者,不僅向她求愛,還寫下關於她的文字。普希金的同僚作家亞歷山大.格里博耶多夫(Alexander Griboyedov)也認識並仰慕著伊斯托米娜。她是一場雙重決鬥的導火線,這場決鬥不僅奪去一位仰慕者的性命,也讓格里博耶多夫失去了左手。普希金原本打算寫下這些戲劇性的事件,但還沒來得及寫,他自己就在另一場決鬥中不幸身亡。在校園與歷史緊密結合的氛圍中,上述一切好似都近在咫尺,尤其對於一個能背誦普希金和格里博耶多夫作品的男孩來說,更是再熟悉不過。
(選摘)
一九一三年八月的某個暖日,年僅九歲的喬治抵達皇家劇院學校,他的第一個童年就此結束。第二個「像狗一樣」的童年緊接著開始了。這個形容詞不僅道出男孩無力對抗母親的憤怒,更貼切地描述了他不甘於從天堂般的生活跌入地獄般的生活。一切發生得太快,新生活又離家太遠,男孩的世界瞬間天翻地覆。學校看守人取代母親的角色;爐灶換成學校;俄國鄉村生活則變成歐洲化的宮廷藝術訓練,講求紀錄和常規。急遽的變化讓喬治的生活經驗斷裂成不相干的兩部分,而他只能自己默默嘗試理出一絲頭緒。
在當時,有兩個現實因素左右著喬治所處的世界局勢,並對芭蕾舞者的職涯發展影響深遠。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他逐漸發現這兩個因素的真面目,亦即皇朝和戰爭。皇朝奠定了俄羅斯芭蕾舞發展的基礎藍圖,而所有在宮廷中長大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參與到這段奇特的歷史。一切始於彼得大帝雄心勃勃的歐洲化計畫,該計畫率先將法國和義大利的芭蕾舞引入俄羅斯。這不僅是文化借鑒,更是一項規模宏大、極具野心的大規模人性工程,直到布爾什維克革命(又稱十月革命)才被推翻,終結把俄羅斯人變成歐洲人的行動。在彼得大帝及其繼任者的統治下,制服、軍階、聖彼得堡的建築風格、食物、手勢、禮儀和語言皆來自異國的歐洲文化。從那時起,沙皇開始有迎娶外國公主的慣例,例如尼古拉二世的妻子既是德國人,同時也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女。此外,直到革命前夕,宮廷的通用語言一直是法語。芭蕾舞屬於這項歐洲化計畫的一環,其根源於義大利和法國,長期用於訓練歐洲貴族的禮儀、儀態和手勢。
然而,俄羅斯人的內在本質並未消失。在最奢華的歐式住宅中,即便屋裡擺滿進口大理石、精美的藝術品和水晶吊燈,往往還會設置一個充滿俄式風情的小天地,有著溫暖的爐火、茶炊和舒適的地毯。和他們的房子一樣,有人說俄羅斯人的精神世界也是分裂的,「真正的」內在俄羅斯靈魂隱藏在歐洲人的外表之下。因此,若想成為歐洲人,勢必得歷經一場精心策畫的戲劇排演。在排練場上,所有角色皆須反覆排練、練習背誦臺詞,並熟記舞步和走位。精彩的芭蕾舞劇和各式表演就建立在這種「成為歐洲人」的意識上,成為奠定俄羅斯宮廷生活的基石。芭蕾舞於是成為一種儀式性的工具。俄羅斯人透過反覆排演,實現對異國文化的追求與幻想,企圖讓歐洲文化淩駕於自身傳統,最終達到支配眾人生活的目的。
在宮廷的背後,或者說在其核心中,還隱藏著一個更深層、冷酷的事實。喬治也被迫學著接受這件事,亦即農奴制和「農奴芭蕾舞者」的特殊制度。十八世紀末,凱瑟琳大帝解除了貴族在宮廷中的職責,許多貴族於是返回奢華的鄉間莊園,開始在莊園中複製這個戲劇性的宮廷階級制,還玩起假扮歐洲人的遊戲。莊園的主人扮演沙皇,農奴則飾演朝臣。主人不遺餘力地訓練這些農奴,讓他們適應陌生的新角色,甚至引入歐洲芭蕾舞大師、歌唱指導員、音樂家和詩人來教導年輕的農奴女孩扮演國王的朝臣。經訓練後,這些農奴芭蕾舞者得以參加各種舞會和儀式活動,猶如主人佩戴的飾品。
藝術與性之間的界限薄如蟬翼,農奴芭蕾舞者(其中許多是訓練有素、多愁善感的藝術家)往往還充當情婦或私人後宮的一員,不僅要在裸身或衣著暴露的狀態下表演,偶爾還會用皮鞭當道具。接受羞辱和抹殺自我都是成為舞者的必備技能。時至十九世紀中葉,支撐這種放縱行為的封建財政結構已崩潰,許多農奴舞者因此被賣給皇家劇院。她們在那裡重獲自由,但也付出新的代價,這次是為沙皇本人提供服務。宮廷負責決定她們的職業(這位去演戲,那位去跳舞),且服務年資須達十年,以補償培訓支出。若未經許可,她們無法擅自離開城市或結婚,性剝削仍司空見慣。在喬治來到劇院學校的數年前,農奴制和這些殘餘陋習已正式畫下句點,但劇院學校的許多學生和教職員仍出身低微或曾為農奴,而皇家劇院的管理者則為地位較高的前農奴主人及其後代。當時芭蕾舞團的領舞瑪蒂達.克謝辛斯卡婭(Matilda Kschessinskaya)便是延續前朝惡習最臭名昭彰的例子。人們都稱呼她為「金色瑪蒂達」(Golden Matilda)。其父為波蘭人物舞蹈的舞者,雖然她出身卑微,但卻長期受皇位繼承人尼古拉的供養,享受充滿豪宅、珠寶、藝術品和濱海假期的奢華生活方式。當尼古拉成婚並登基為沙皇後,瑪蒂達就轉為跟著公爵。
這一切都悄悄發生在皇家劇院學校厚厚的石牆內。此學校在這段歷史中也扮演了某種角色,其起源可追溯至宮廷建立的初期。當時安娜皇后邀請一位法國的芭蕾舞大師前來教授宮廷侍者的子女們儀態和舉止,因為這他們能否勝任這個角色的關鍵。同時,安娜也請芭蕾舞大師為皇家軍校的少年們授課,這正是拒喬治於門外的精英軍事訓練學校。軍校與芭蕾訓練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芭蕾最早源於法國和義大利,而從那時起,芭蕾就與軍事藝術並肩發展,這種搭配也成為宮廷生活的核心特徵。十九世紀初,當沙皇的建築師在設計羅西街時,也試圖將以石頭為建材的宮殿蓋在城市中,因此他們決定將皇家劇院學校設立在沃龍佐夫宮(Vorontsov Palace)的正對面,那裡正是沙皇精英軍事學院的所在地。軍事與舞蹈分別代表戰爭與和平的藝術,兩者為歷史上的近親,踏著相同的步伐並採用共同的訓練方法,從不同的面向致力打造帝國的紀律、階級和專制體制。這就是喬治的新家。
喬治恰好在艱難的時刻來到這所學校。此時,賦予芭蕾舞生命的皇室正身陷重重危機,沙皇和他的手下忙著在宮殿周圍築起越來越厚的高牆,以保護搖搖欲墜的帝制。冬宮透過國家暴力無情鎮壓來自四面八方的罷工、暗殺、爆炸、飢荒和農民起義。尼古拉二世越來越無法勝任歷史賦予他的角色,顯得十分無能。儘管尼古拉二世曾在慶祝羅曼諾夫(Romanov)家族統治三百年的奢華慶典上正式露過面,包括一場精彩的芭蕾舞表演,但除此之外,人們輕易發現沙皇與他聲稱並熱衷於代表的「人民」日漸疏遠。他退居幕後,成日享受妻子主持的維多利亞式家庭生活,屋內有塞得鼓起的舒適傢俱、綠色花環、粉紅色絲帶、丁香花、典雅的英式印花布,以及掛滿閃閃發光聖像的牆壁。費奧多羅夫(Feodorov)村位於沙皇村,是沙皇在亞歷山大宮附近所建、一個如玩具般的俄羅斯小鎮。這個村落是他最喜歡的家庭住所,裡頭有一座特別設計的新民族主義風格大教堂和一個處於地底的私人「洞穴教堂。」這裡完全體現了對俄羅斯輝煌過往的戲劇性幻想,不僅駐守的士兵個個身著十七世紀風格的服裝,連火車站也是舞臺布景,其莫斯科式的帳篷屋頂讓人聯想到早期的俄羅斯宮殿。更甚者,尼古拉和皇室成員如鴕鳥般埋首於皇家劇院和芭蕾舞劇中。正如一位老副官在沙俄政權崩潰前夕對困惑的法國大使所說,在許多俄羅斯人看來,觀賞表演代表「俄國社會過去的真實寫照,不僅過去如此,現在、未來也都該如此,充滿秩序、嚴謹、對稱的社會,處處細節都照顧到。」
在尼古拉步步退縮時,他也在不經意間削弱了自己的神聖光環。該光環以兩項名義為基礎,包含他錯誤的民族主義,以及宣稱自己為子民的代表。從一些小事上就可以觀察到這一點。舉例來說,沙皇的面孔首度印製在全國通行的郵票上,不過也會遭例行註銷。他甚至允許自己的形像出現在托盤、瓷器、糖果盒和圍巾等俗氣的紀念品上(不過手帕則被嚴格禁止),這讓一眾審查員十分不滿。尼古拉也向農奴芭蕾舞者的傳統借鏡,允許男演員在舞臺上扮演自己,以他們卑微的舞者形象呈現沙皇的威嚴。
一九一三年八月的某個暖日,喬治剛剪了頭髮並穿上制服,焦急地等候如何開始新生活的指示。而僅僅一年後,沙皇就站在冬宮的陽臺上,低頭看著跪在地上舉著聖像和宗教旗幟的人民,宣布俄國開戰。四年後,列寧就站在另一個陽臺上,這次是在芭蕾舞女演員克謝辛斯卡婭的家裡。他在憤怒的民眾面前宣布革命揭開序幕。列寧將臭名昭著、當時已遭洗劫一空的金色瑪蒂達宅邸做為其總部。此舉無疑撼動了宮廷的權威,同時深深影響小喬治.巴蘭欽瓦澤現在所屬的宮廷世界。
學校裡的生活似乎變動不大。喬治多年來每天都穿同樣的制服,甚至在開戰後的壓抑生活中也是如此著裝:褶皺整齊的軍裝式黑褲、修身白襯衫、領子上有里拉琴徽的淺藍色夾克,配上一頂圓形、硬邊、軍校生式樣的帽子。這種制服設計是為了讓男孩能夠站得筆直、走得穩且到位。上述是日常生活的服裝,而跳舞的服裝則不同。他們會穿一種極簡且暴露的短褲,長度至膝蓋以上,再配上統一的純色合身襯衫、襪子和白色芭蕾舞鞋。這一身是男舞者的標準配備。女生則住在一樓,她們穿著矢車菊藍長裙、端莊的白色披肩和黑色圍裙,而熨燙過的白色圍裙會留到週日才穿。走讀生則身著雜棕色的衣服。年紀較小的女孩會在背上紮一條辮子,並稱學姊為「女神」;年紀較大的女孩可以紮兩條辮子,並將披肩疊成大三角形後,不慌不忙地披在背上,以特別彰顯自己的身分。低年級的女孩在跳舞時會穿著有襯裙的灰色及膝連衣裙,高年級的女孩則穿著粉紅色連衣裙,只有少數班上表現最傑出的女孩,才能穿上夢寐以求的純白連衣裙。顏色越純代表達到美德標準越高。女孩們都統一穿著乾淨的粉紅色棉質長襪,在臀部處用鬆緊帶束起,秀髮整齊地向後紮成低髮髻,芭蕾舞鞋上的絲帶在腳踝處繞二或三圈,然後整齊地塞進鞋裡,有點像希臘涼鞋。
正如同對年輕舞者的嚴謹規範,對朝臣的規範同樣嚴格和詳細。每個人在宮廷裡都必須身著制服,或至少須根據位階治裝。舉凡刺繡圖案、裙子和裙襬的長度、剪裁、布料、顏色都有嚴格的規定。位階的變化意味著更換制服,就像劇院街那些模仿朝臣的孩子們一樣,朝臣會透過不同顏色表示位階的晉升:從白褲變成黑褲,紅絲帶則變成藍絲帶,而銀線會變成金線。尼古拉二世甚至下令將男子的軍裝和舞會制服分開,且跳舞時須卸下武器以免顯得格格不入。不僅是服裝,姿態、語言、座位,連在官方場合的席位都經過精心規劃和安排。
喬治以一系列的紀律為一天的行程揭開序幕。天剛濛濛亮時,學校管理員在敲響了鐘後,一陣響亮的鐘聲會傳遍學校,他們接著在宿舍裡走來走去。孩子們會先在一個巨大的公用黃銅水槽中用冷水洗漱,再快速穿好衣服。緊接著第二次鐘聲響起,示意孩子們檢查時間到了,這時他們會排成兩列、抬著頭並讓雙手垂落在身側。男孩會微微低頭敬禮,女孩則行屈膝禮並互道「早安」,然後一起禱告。早餐上午八點開始,通常是茶和麵包外加一顆雞蛋(奶油配給可減半換成每週兩次的糕點),接著上午九點開始上課,十到十二點則為芭蕾舞課。午餐提供肉類、義大利麵和蔬菜,結束後他們會在成人管理員的嚴格監督下,在花園或小區周圍散步。管理員會特別注意年齡較大的女孩,以免她們遭興致盎然的紳士窺視。
教學課程在小教室裡進行,教室裡擺放著傾斜的木桌和黑板。喬治的課程包括法文(為了和沙皇溝通)、歷史、地理、算術、俄語和俄國文學、美學、劇場化妝技巧、幾何學,以及他最擅長的東正教教義問答。當時的教育體系已升級為以德國學制為榜樣的實用專科中學,課程十分嚴謹。晚餐和甜點時間在下午四點半開始。學生們在鋪著白色桌巾的長桌上用餐,每張長桌的首位都坐著一位學校職員。學長姐像啄木鳥一樣,以猶如宗教儀式般正式且嚇人的方式逐一糾正年幼孩子的禮儀。抬首望去,只見一尊聖像高高立在靠近天花板的角落,身旁的玻璃後襯著一支鮮紅的蠟燭。這漫長的一天似乎沒有句點,他們接著上了第二堂舞蹈課,包含默劇和擊劍。對於大男孩來說,還有交誼舞課,這是他們難得能與女孩們見面的機會。最後,他們會練習樂器(喬治練習鋼琴)、做回家作業,簡單地吃完普通的棕色卡莎後就上床睡覺。晚上九點,精疲力盡的他們終於得以就寢。不過,喬治竟能設法找到微弱的燈光並藉此讀著他最喜歡的《馬克斯與莫里茨》(Max and Moritz)、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的作品或《福爾摩斯探案集》,並忘我地一路讀到深夜。澡堂每週提供一次蒸氣浴,若有孩子剛從外面骯髒的城市歸來,也可以在澡堂中擦洗身體。
學生的生活受到嚴格管制。他們不能從事其他運動,例如溜冰、騎腳踏車或打球等等,因為可能傷害到寶貴的肢體。訪客只能在有人觀察的情況下,於規定時間進入單獨的房間內會面。孩子們連回家一趟都要經過精心安排和監控。男孩們喜歡玩羅賓漢或戰爭遊戲,但嚴禁使用刀劍。實際上孩子們幾乎不須走出院子到石牆外,因其所需的一切皆唾手可得,包括一間醫務室和一座小巧優雅的教堂,教堂內裝飾華麗、璀璨炫目的聖幛被置於教堂大廳的右側,高度直達天花板。瓦西里.福斯托維奇.皮古列夫斯基(Wassily Faustovich Pigulevsky)是一位神父,他與妻子和九個孩子住在學校裡,愛打牌和喝酒的程度就像他愛上帝一樣。他從一八八○年代起就在這所學校工作,負責設計教義問答的課程,內容包括新舊約的《聖經》、斯拉夫異教和西方宗教。他對此接受懺悔。當學生列舉自己的罪過時,他會斥責學生為「小傻瓜」或「白癡。」某次四旬期輪到喬治端聖餐酒時,瓦西里對一個臉色蒼白、神情萎靡的新生低聲道:「你可以喝這酒,味道不錯。別擔心,我可以幫你多倒一點。」
就像農奴芭蕾舞者的歷史一樣,學生的背景十分多元,包含孤兒,以及前農奴、舞者、引座員、服裝師、裁縫和作曲家的子女,其中許多人都沒有父親,只有少數人來自軍人家庭,而來自特權階級者更是鳳毛麟角。這些孩子都受到皇家管理員的嚴格看管,管理員有男有女,如女督察瓦爾瓦拉.伊凡諾夫娜.利霍舍斯托娃(Varvara Ivanovna Likhosherstova)。當喬治入學時,她已在學校工作很久了。她是一位貧困貴族的遺孀,也是少將的女兒,曾住在莊嚴的斯莫爾尼修女院。孩子們大多不知道她的悲慘身:她曾嫁給一位軍官,後來軍官死後獨留她一人照顧兩個兒子,因此她迫切需要收入。瓦爾瓦拉脾氣執拗、以刻薄著稱,不僅難以相處,外表還貌似神父,身著一襲垂地的黑長袍,下巴方正得像個男人,白色的高領上扣著胸針,一頭花白的頭髮顯得格外嚴肅。她還隨身攜帶一副長柄眼鏡,以方便檢查年輕學生的全面生活細節。
違反規則的孩子會受到明確的懲罰,例如獨自站在走廊的大鐘下,遭受其他路過的孩子鄙夷地指指點點或竊竊私語,有時則是不給糖或週六不能回家,更嚴重的是週日禁足。喬治也曾受過這些懲罰,紀錄本上詳盡記錄著他童年時犯過的錯,包含大喊大叫、打人、撒謊,以及找藉口逃避工作和職責。在許多週末,他會去附近阿姨的公寓以逃離這種被管束的生活,有時也會搭火車回盧納喬基(Lounatjoki)。在他入讀的第一年聖誕節,其父甚至為所有男孩舉辦了一場派對,這意味著一群教職員、教師、學生與喬治,一起在某個週末擠上火車前往芬蘭的鄉村參與盛會。梅利頓最喜歡這種形式的派對,但喬治卻躲在角落裡害羞地看著大家。
其實喬治經常留在學校,獨自在音樂教室裡度過空蕩蕩的週日午後。音樂教室是一間大舞蹈室,掛滿沙皇和其他政要的厚重鍍金畫像。喬治似乎不在意這個房間會鬧鬼,裡頭住著一位老修士,或名叫魯奇或里奇的歌唱老師,據說後者曾在這裡上吊自殺。膽小的孩子們卻就地玩起尋找靈魂的遊戲。在靠近芭蕾舞臺的角落裡,擺放著一架精美華麗的三角鋼琴(有時是兩架),喬治可以獨自在沙皇和修士幽靈散發的憂傷氣氛下,數小時不間斷地練習和進行即興創作。有時,他也會在另一間練習室裡,凝視著陰鬱神祕的伊斯托米娜(Istomina)肖像。近一個世紀前,文豪普希金愛上這位楚楚可憐的舞者,不僅向她求愛,還寫下關於她的文字。普希金的同僚作家亞歷山大.格里博耶多夫(Alexander Griboyedov)也認識並仰慕著伊斯托米娜。她是一場雙重決鬥的導火線,這場決鬥不僅奪去一位仰慕者的性命,也讓格里博耶多夫失去了左手。普希金原本打算寫下這些戲劇性的事件,但還沒來得及寫,他自己就在另一場決鬥中不幸身亡。在校園與歷史緊密結合的氛圍中,上述一切好似都近在咫尺,尤其對於一個能背誦普希金和格里博耶多夫作品的男孩來說,更是再熟悉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