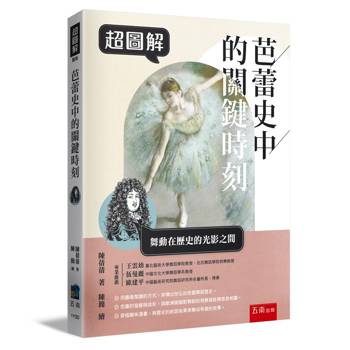Chapter 4 俄羅斯人的古典芭蕾(節錄)
4-7柴可夫斯基與佩蒂帕共創舞劇《睡美人》(1890)
1881年,自詡「真正俄羅斯人」的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1845-1894) 即位,俄羅斯推行西化改革的沙皇至此後繼無人。在對帝國劇院施行的一系列變革中,尋找「更具備俄羅斯意識」的藝術理念再次被推崇,伊凡.弗謝沃洛依斯基(Ivan Vsevolozhsky,1835-1909) 受命負責劇院的管理,越來越多的俄羅斯本土藝術家受到了帝國劇院的合作邀請,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1840-1893) 便是其中之一。在聖彼得堡的舞台積累了30 多年經驗,已逾花甲之年的佩蒂帕就是在這樣的機遇下,於1890 年完成了《睡美人》(The Sleeping Beauty) 的創作。
童話芭蕾《睡美人》是佩蒂帕與柴可夫斯基合作的第一個舞劇,在此之前,俄羅斯恢宏壯麗的音樂風格,一直是歌劇與交響樂的專屬,鮮少有「輕盈飄逸」的芭蕾編導會去考慮柴可夫斯基的作曲。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一次的精誠合作,《睡美人》的音樂對舞蹈的身體與精神發揮了作用,舞者們在壯闊、艱深的柴可夫斯基音樂中,會被「逼得」要將動作推到飽滿、細膩之至,不然就會淪為音樂的「伴舞」。《睡美人》不再展現浪漫芭蕾那種異域的情調,沒有農村多情的男孩,也沒有林中舞蹈的幽魂,劇中的「戲」與「舞」之間沒有明顯的段落分別,手勢和舞蹈流瀉一氣,銜接得無縫而不尷尬,使芭蕾重歸其源頭—「宮廷禮儀」之上。
它與俄羅斯宮廷禮儀息息相關,並且以路易十四(古代法國,而不是浪漫芭蕾時期的法國)時期的景象,滿懷情感地再現出對宮廷原則的尊崇。不僅有撼人心魄的音樂、氣勢恢宏的舞蹈,還用了大約270 套服裝、奢華誇張的布景,以及壓倒一切的「人海戰術」,創造了空前絕後的劇場奇觀,單單是《睡美人》一劇,就用掉了皇家劇院年度製作預算的四分之一不止。
佩蒂帕在劇中並不排斥「義大利絕技」,反而更加細緻地打磨技術,使其與劇情、音樂和角色的意志融合,讓炫技轉變為詩一般的隱喻。在傾向法國文化或自身文化的多次擺盪後,俄羅斯芭蕾終於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俄羅斯古典芭蕾舞劇」。《睡美人》保存了斯拉夫民族的內在氣質,也消化了來自義大利和法蘭西文化的舞蹈形式,從此刻起,俄羅斯的芭蕾舞不再只是模仿法國,而是成為了舉世公認的「俄羅斯芭蕾」。
關聯人物:伊凡.弗謝沃洛依斯基、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馬里于斯.佩蒂帕
關聯事件:俄羅斯的芭蕾不再模仿法國,而是成為了真正的「俄羅斯芭蕾」
4-8「僅止童話」卻流芳百年的《胡桃鉗》上演(1892)
1891 年,弗謝沃洛依斯基、柴可夫斯基、佩蒂帕再度攜手另一部童話芭蕾《胡桃鉗》,只是才剛開始排練,佩蒂帕便告病臥床,無奈只能將工作轉交由副手—列夫.伊凡諾夫(Lev Ivanov, 1834-1901) 完成。1892 年《胡桃鉗》的首演慘遭炮轟:劇情太簡單,情節缺乏衝突感,舞段之間沒有明顯的承繼關係,上升不到舞劇的「高度」。評論家認為:「伊凡諾夫做出了一個七拼八湊的大雜燴」,稱其為帝國劇院的「奇恥大辱」,並斥以「全劇僅止童話而已」,且宣判「該團已死」等嚴厲控訴。彼時《胡桃鉗》很快便被排除在劇院的上演名單之外,但如今它卻以傲視群倫的地位在芭蕾舞史上成為了百年經典,這一對比顯得無比諷刺,功過難評。
《胡桃鉗》的編舞家伊凡諾夫是與眾不同的,他是帝國劇院培養出來的第一位俄羅斯本土編舞家,沒有精英階層自視甚高的傲氣。他18 歲便投入佩蒂帕的羽翼之下,1877 年曾出演《舞姬》中的勇士索羅爾一角,20 年後升任為舞台總監和(在佩蒂帕之下的)第二芭蕾舞編導,終身未踏出俄羅斯國門一步。其嫻熟於西歐芭蕾的風格與技法,卻又獨具俄羅斯哀愁幽思的時代底蘊。
《胡桃鉗》於彼時招徠的觀眾雖然不多,但其中的〈雪花圓舞曲〉卻備受讚譽:伊凡諾夫先是讓成群的舞者聚在一起,排列出複雜、精巧的隊形,之後如漫天雪片一樣打散、化開、聚合,重新組成的隊形如雪花結晶般玲瓏幻化,有星星、有俄羅斯圓環舞、有鋸齒狀、有不停旋轉的巨型十字架,放射狀圖形的交叉點是個中空的圓圈,像是晶瑩剔透的寶石在舞台上發出璀璨的光芒⋯⋯這種舞蹈隊形的變化設計,保留了古典芭蕾講究的對稱構圖,但是組織的形式又偏向輕盈、空靈透澈,雖然削弱了古典芭蕾的儀式感,但卻帶有印象派美術靈動、隨性的情調。
柴可夫斯基爐火純青的音樂才華也為《胡桃鉗》助益不少,他精確巧妙地使用弦樂,其樂音彷彿透過聽覺的傳遞感染到了視覺,讓台上的舞蹈背景不時地透出一種閃耀的光彩。如〈雪花圓舞曲〉中童聲的加入,和第一幕樂曲中的兒童樂器,展現出一般舞劇音樂少見的寫實與親和。
關聯人物:列夫.伊凡諾夫、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關聯事件:俄羅斯本土藝術家盡顯其才,聯手鑄造百年經典《胡桃鉗》
4-9《天鵝湖》重獲新生,俄羅斯芭蕾就是古典芭蕾(1895/1877)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天鵝湖》版本,是佩蒂帕與伊凡諾夫合力創作/改編,搭配柴可夫斯基的音樂,1895 年於聖彼得堡首演/重新上演的版本。然而實際上,之前負責統籌波修瓦劇院(Bolshoi Theatre) 演出的劇作家別吉切夫(Vladimir Begichev, 1828-1891),就曾委約柴可夫斯基譜寫此劇的配樂,並於1877 年在莫斯科公演。莫斯科版本的《天鵝湖》情節較為複雜,邪惡、暴力又淒慘,最後王子沒有機會贖罪,而是一對戀人以身相殉,徒留月光散落在湖面的天鵝之上。柴可夫斯基所作的配樂對當時的觀眾來說雖稍顯華美,但也確實獲得了不少好評,而編舞卻慘遭各方嚴厲抨擊,修改過好幾種版本皆反響平平,最後終因預算縮減而退出了莫斯科大劇院的演出名單。一直到1893 年柴可夫斯基驟然身故,都無緣親眼看到《天鵝湖》重登舞台並大獲成功。
1894 年,弗謝沃洛依斯基在聖彼得堡為柴可夫斯基舉辦了一場紀念音樂會,伊凡諾夫將《天鵝湖》第二幕的湖畔舞蹈重新編排,由此契機,《天鵝湖》艱鉅的「翻新」工程再次推動了起來:柴可夫斯基的弟弟莫德斯特(Modest Ilyich Tchaikovsky, 1850-1916) 受邀撰寫新的腳本,德里戈 (Riccardo Drigo, 1846-1930) 則將柴可夫斯基的音樂略作調整修改,佩蒂帕負責宮廷場景的舞蹈,而那些幽思滿溢的抒情舞段,則由伊凡諾夫來刻畫。
佩蒂帕此時的編舞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他在《天鵝湖》第一幕和第三幕中為宮廷場景所編的舞段,如建築結構一般穩固完善,不僅以精緻細膩的舞姿表現出法國芭蕾的溫潤文雅,同時又在秩序井然的規儀中炫耀著義大利芭蕾的華麗技巧。黑天鵝便是在這樣的場景中,完成了她舉世矚目的32 圈揮鞭轉(Fouetté)。而由伊凡諾夫執導的《天鵝湖》第二幕可以稱得上是全劇的縮影,當中的「白色場景」與佩蒂帕在第一、第三幕富麗堂皇的異彩紛呈形成強烈對比,為觀眾帶來了一種清麗冷冽、冰清玉潔的美感轉變。《天鵝湖》的創作歷程雖支離破碎,但卻也是獨一無二的,它不僅跨越了1870 和1890兩個年代,更是集結了莫斯科與聖彼得堡這俄羅斯東西方兩大都市的文化薈萃。俄羅斯人固執的秉性與嶄新的蛻變皆深烙其中,以此明證「俄羅斯芭蕾」之積澱成型,絕非一人、一時或一地的機遇可偶然鑄就。
關聯人物:馬里于斯.佩蒂帕、列夫.伊凡諾夫、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關聯事件:俄羅斯芭蕾成為集大成者,自《天鵝湖》起,古典芭蕾便等於俄羅斯芭蕾
4-7柴可夫斯基與佩蒂帕共創舞劇《睡美人》(1890)
1881年,自詡「真正俄羅斯人」的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1845-1894) 即位,俄羅斯推行西化改革的沙皇至此後繼無人。在對帝國劇院施行的一系列變革中,尋找「更具備俄羅斯意識」的藝術理念再次被推崇,伊凡.弗謝沃洛依斯基(Ivan Vsevolozhsky,1835-1909) 受命負責劇院的管理,越來越多的俄羅斯本土藝術家受到了帝國劇院的合作邀請,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1840-1893) 便是其中之一。在聖彼得堡的舞台積累了30 多年經驗,已逾花甲之年的佩蒂帕就是在這樣的機遇下,於1890 年完成了《睡美人》(The Sleeping Beauty) 的創作。
童話芭蕾《睡美人》是佩蒂帕與柴可夫斯基合作的第一個舞劇,在此之前,俄羅斯恢宏壯麗的音樂風格,一直是歌劇與交響樂的專屬,鮮少有「輕盈飄逸」的芭蕾編導會去考慮柴可夫斯基的作曲。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一次的精誠合作,《睡美人》的音樂對舞蹈的身體與精神發揮了作用,舞者們在壯闊、艱深的柴可夫斯基音樂中,會被「逼得」要將動作推到飽滿、細膩之至,不然就會淪為音樂的「伴舞」。《睡美人》不再展現浪漫芭蕾那種異域的情調,沒有農村多情的男孩,也沒有林中舞蹈的幽魂,劇中的「戲」與「舞」之間沒有明顯的段落分別,手勢和舞蹈流瀉一氣,銜接得無縫而不尷尬,使芭蕾重歸其源頭—「宮廷禮儀」之上。
它與俄羅斯宮廷禮儀息息相關,並且以路易十四(古代法國,而不是浪漫芭蕾時期的法國)時期的景象,滿懷情感地再現出對宮廷原則的尊崇。不僅有撼人心魄的音樂、氣勢恢宏的舞蹈,還用了大約270 套服裝、奢華誇張的布景,以及壓倒一切的「人海戰術」,創造了空前絕後的劇場奇觀,單單是《睡美人》一劇,就用掉了皇家劇院年度製作預算的四分之一不止。
佩蒂帕在劇中並不排斥「義大利絕技」,反而更加細緻地打磨技術,使其與劇情、音樂和角色的意志融合,讓炫技轉變為詩一般的隱喻。在傾向法國文化或自身文化的多次擺盪後,俄羅斯芭蕾終於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俄羅斯古典芭蕾舞劇」。《睡美人》保存了斯拉夫民族的內在氣質,也消化了來自義大利和法蘭西文化的舞蹈形式,從此刻起,俄羅斯的芭蕾舞不再只是模仿法國,而是成為了舉世公認的「俄羅斯芭蕾」。
關聯人物:伊凡.弗謝沃洛依斯基、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馬里于斯.佩蒂帕
關聯事件:俄羅斯的芭蕾不再模仿法國,而是成為了真正的「俄羅斯芭蕾」
4-8「僅止童話」卻流芳百年的《胡桃鉗》上演(1892)
1891 年,弗謝沃洛依斯基、柴可夫斯基、佩蒂帕再度攜手另一部童話芭蕾《胡桃鉗》,只是才剛開始排練,佩蒂帕便告病臥床,無奈只能將工作轉交由副手—列夫.伊凡諾夫(Lev Ivanov, 1834-1901) 完成。1892 年《胡桃鉗》的首演慘遭炮轟:劇情太簡單,情節缺乏衝突感,舞段之間沒有明顯的承繼關係,上升不到舞劇的「高度」。評論家認為:「伊凡諾夫做出了一個七拼八湊的大雜燴」,稱其為帝國劇院的「奇恥大辱」,並斥以「全劇僅止童話而已」,且宣判「該團已死」等嚴厲控訴。彼時《胡桃鉗》很快便被排除在劇院的上演名單之外,但如今它卻以傲視群倫的地位在芭蕾舞史上成為了百年經典,這一對比顯得無比諷刺,功過難評。
《胡桃鉗》的編舞家伊凡諾夫是與眾不同的,他是帝國劇院培養出來的第一位俄羅斯本土編舞家,沒有精英階層自視甚高的傲氣。他18 歲便投入佩蒂帕的羽翼之下,1877 年曾出演《舞姬》中的勇士索羅爾一角,20 年後升任為舞台總監和(在佩蒂帕之下的)第二芭蕾舞編導,終身未踏出俄羅斯國門一步。其嫻熟於西歐芭蕾的風格與技法,卻又獨具俄羅斯哀愁幽思的時代底蘊。
《胡桃鉗》於彼時招徠的觀眾雖然不多,但其中的〈雪花圓舞曲〉卻備受讚譽:伊凡諾夫先是讓成群的舞者聚在一起,排列出複雜、精巧的隊形,之後如漫天雪片一樣打散、化開、聚合,重新組成的隊形如雪花結晶般玲瓏幻化,有星星、有俄羅斯圓環舞、有鋸齒狀、有不停旋轉的巨型十字架,放射狀圖形的交叉點是個中空的圓圈,像是晶瑩剔透的寶石在舞台上發出璀璨的光芒⋯⋯這種舞蹈隊形的變化設計,保留了古典芭蕾講究的對稱構圖,但是組織的形式又偏向輕盈、空靈透澈,雖然削弱了古典芭蕾的儀式感,但卻帶有印象派美術靈動、隨性的情調。
柴可夫斯基爐火純青的音樂才華也為《胡桃鉗》助益不少,他精確巧妙地使用弦樂,其樂音彷彿透過聽覺的傳遞感染到了視覺,讓台上的舞蹈背景不時地透出一種閃耀的光彩。如〈雪花圓舞曲〉中童聲的加入,和第一幕樂曲中的兒童樂器,展現出一般舞劇音樂少見的寫實與親和。
關聯人物:列夫.伊凡諾夫、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關聯事件:俄羅斯本土藝術家盡顯其才,聯手鑄造百年經典《胡桃鉗》
4-9《天鵝湖》重獲新生,俄羅斯芭蕾就是古典芭蕾(1895/1877)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天鵝湖》版本,是佩蒂帕與伊凡諾夫合力創作/改編,搭配柴可夫斯基的音樂,1895 年於聖彼得堡首演/重新上演的版本。然而實際上,之前負責統籌波修瓦劇院(Bolshoi Theatre) 演出的劇作家別吉切夫(Vladimir Begichev, 1828-1891),就曾委約柴可夫斯基譜寫此劇的配樂,並於1877 年在莫斯科公演。莫斯科版本的《天鵝湖》情節較為複雜,邪惡、暴力又淒慘,最後王子沒有機會贖罪,而是一對戀人以身相殉,徒留月光散落在湖面的天鵝之上。柴可夫斯基所作的配樂對當時的觀眾來說雖稍顯華美,但也確實獲得了不少好評,而編舞卻慘遭各方嚴厲抨擊,修改過好幾種版本皆反響平平,最後終因預算縮減而退出了莫斯科大劇院的演出名單。一直到1893 年柴可夫斯基驟然身故,都無緣親眼看到《天鵝湖》重登舞台並大獲成功。
1894 年,弗謝沃洛依斯基在聖彼得堡為柴可夫斯基舉辦了一場紀念音樂會,伊凡諾夫將《天鵝湖》第二幕的湖畔舞蹈重新編排,由此契機,《天鵝湖》艱鉅的「翻新」工程再次推動了起來:柴可夫斯基的弟弟莫德斯特(Modest Ilyich Tchaikovsky, 1850-1916) 受邀撰寫新的腳本,德里戈 (Riccardo Drigo, 1846-1930) 則將柴可夫斯基的音樂略作調整修改,佩蒂帕負責宮廷場景的舞蹈,而那些幽思滿溢的抒情舞段,則由伊凡諾夫來刻畫。
佩蒂帕此時的編舞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他在《天鵝湖》第一幕和第三幕中為宮廷場景所編的舞段,如建築結構一般穩固完善,不僅以精緻細膩的舞姿表現出法國芭蕾的溫潤文雅,同時又在秩序井然的規儀中炫耀著義大利芭蕾的華麗技巧。黑天鵝便是在這樣的場景中,完成了她舉世矚目的32 圈揮鞭轉(Fouetté)。而由伊凡諾夫執導的《天鵝湖》第二幕可以稱得上是全劇的縮影,當中的「白色場景」與佩蒂帕在第一、第三幕富麗堂皇的異彩紛呈形成強烈對比,為觀眾帶來了一種清麗冷冽、冰清玉潔的美感轉變。《天鵝湖》的創作歷程雖支離破碎,但卻也是獨一無二的,它不僅跨越了1870 和1890兩個年代,更是集結了莫斯科與聖彼得堡這俄羅斯東西方兩大都市的文化薈萃。俄羅斯人固執的秉性與嶄新的蛻變皆深烙其中,以此明證「俄羅斯芭蕾」之積澱成型,絕非一人、一時或一地的機遇可偶然鑄就。
關聯人物:馬里于斯.佩蒂帕、列夫.伊凡諾夫、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關聯事件:俄羅斯芭蕾成為集大成者,自《天鵝湖》起,古典芭蕾便等於俄羅斯芭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