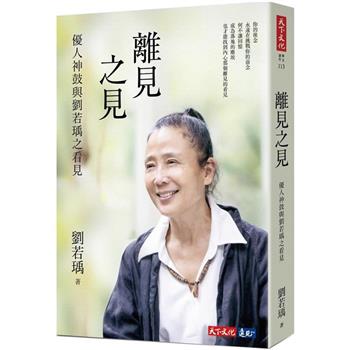去找他在找的事情,而不是去做他在做的事情
「Medea 在山上」演出呈現之後,表演藝術圈開始對葛托夫斯基具體且系統化的演員訓練方法感到好奇,想知道他到底教了我什麼。幾位想要研究這個方法的劇場老師們,策劃了一系列課程,請我示範帶領一些年輕人。我也興致勃勃、躍躍欲試。但做了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年輕人跟著做,幾位老師就在旁邊看。下課後,開始分析討論。但因為沒有親身做,看法跟我的感受一直有些差異。上了一段時間之後,對這個示範計畫,漸漸感到自己只是個工具,而不想再合作。當時在加州,是每日超過十到十五小時以上的實地訓練。西方人稱葛托夫斯基這時期的工作方式是魔鬼訓練,身體的勞累可想而知,但身體內在的領受也只有自己了解。
葛托夫斯基經常說「去做」(to do)。所以要了解葛托夫斯基,就必須親身做。正好要進行「第一種身體的行動」了,我便決定不再做示範教課。
「第一種身體的行動」結束之後,我隨即就要跟桂士達一起前往義大利,再去見葛托夫斯基。當時,我已離開加州兩年了,但還是心心念念想再去找他。桂士達告知,大師正好要開一個給舊生的工作坊,我們當然不願錯過。
同年十一月,終於在義大利佛羅倫斯附近的小鎮龐德黛拉(Pontedera)見到大師。我很緊張,但也自認有備而來,就跟桂士達一起做「運行」的動作給他看。
沒想到,他看完之後的回應是:“No, No, No. We don’t do it like this.”(不不不,我們不是這樣做。)並請湯瑪士.理查茲(Thomas Richards)示範。看見湯瑪士的動作,我當下愣住──在加州時,並不是這樣教的啊!這個舉腳的動作,以前他說要放鬆,現在卻是要繃得很緊。當下我很困惑:他到底是在找什麼?
但也立即明白他教做的動作,重點不在於姿勢,也不是技術,而是與自身內在的連結。尤其,「運行」的動作是古老瑜伽的轉化,要在山頂上凌晨日出和黃昏日落的時候做。究竟他的身體觀是什麼?身體內在跟文化、跟天地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他到底在尋找什麼?他改來改去,不斷在變化,我卻還一味地抓著他過去的東西不放?
就在重見大師的第一天,我心中卻冒出了要放下大師的念頭:我要去找到他在找的事情,而不是做他在做的事情。而且,是從我自己生長的文化源頭去尋找。
兩星期後,從義大利要返回台灣,途中經過巴黎,遇到正在寫戲劇論文的作家陳玉慧。她說:「你要回台灣做劇場,要有個團名。」她翻開《戲曲辭典》第一頁:「就叫『優』劇場吧!」「優伶」的簡稱,我覺得這個字是在形容「古老的表演者」,就說:「好喔!」
(摘自〈第一種身體的行動〉)
放下抗拒,仔細聆聽,生命可能從此不同
《海潮音》在國家戲劇院兩天的演出看似圓滿結束。幾天後,《民生報》藝文新聞版出現了一篇〈假仙扮戲演繹東方神祕?〉劇評,周慧玲在文中指出,服飾的荒謬感、擊鼓者「健美先生般竭力擠出糾結的肌肉塊」等,更直言整部作品是「假仙扮戲的做作與矯情」!
其實,就在半年前,周慧玲也曾上老泉山觀看《種花》的演出,並以「完全劇場」稱讚優,給了《種花》極高的評價。《海潮音》卻讓她受不了,從頭批判到尾。看到這劇評,我心裡好像被重重一擊──優第一次進國家戲劇院,竟然就砸鍋了。
到底哪裡不對?我一定要找出答案。於是,我一讀再讀,認真研讀周慧玲文章裡的每一句話;從服裝、動作,到舞台上呈現方式,我要知道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專業劇評者的眼睛果然銳利。事實上,我穿著那件長長戲服在台上,自己就感覺很累贅,頭上又包了一大包,的確很假仙。而周慧玲所說健美先生般的肌肉塊,我立刻意識到,應該是指〈沖岩〉段落──為了讓鼓聲清楚傳出,舞台上的鼓是斜放,鼓面朝向觀眾,所以鼓手是背對著觀眾擊鼓;當鼓手跳起來,奮力將鼓棒敲下時,觀眾看不到鼓手表情,看不見他們內在力量的呈現,只看到鼓手背部賁張的肌肉,真會覺得只是在秀肌肉。
被專業劇評者如此分析,我想,顯然這作品的呈現方式一定有問題,必須有所調整,而且費荷.達西就要來了。但如何在短短一個多月修改我們練了半年的作品呢?突然,靈機一動,何不將鼓轉過來?台下觀眾就能看到鼓手擊鼓的眼神和表情;就像短跑選手比賽時,看見選手最後衝刺時,凝聚所有能量奮力一搏的神情。
於是,我將〈沖岩〉在舞台上的鼓換了方向,而服裝的部分,就改穿平常在山上的工作服,簡單舒適。改變不多,可是,將多餘的東西拿掉後,不但團員們覺得「爽!」觀眾也能看到鼓手的呼吸、頂著一口氣往前衝上去的專注神情。當然,劇名也改了。一個多月後,再度來台的費荷.達西看到的是從《海潮音》調整後的《聽海之心》。
隔年(一九九八年)七月,我們就在法國亞維儂藝術節,以《聽海之心》在戶外演出,不僅如雷掌聲久久不絕,更被法國《世界報》(Le Monde)劇評人評為當年亞維儂上百節目中的「最佳節目」(“the best performance of the festival”)!
從此,《聽海之心》帶著我們走遍全世界,從法國到巴西、荷蘭、比利時、德國、西班牙、瑞士、義大利、挪威、英國、美國、塞內加爾、莫斯科、委內瑞拉……《紐約時報》盛讚《聽海之心》:「偉大而繁複的擊鼓、聲響,和寂靜之美。」倫敦《金融時報》則推崇:「一段綿延不絕的敲擊詩篇。」(“A prolonged percussive tone poem... ”)
周慧玲真的幫了我們一個大忙。如果沒有她那篇評論,我不會調整這作品。費荷.達西看到的,仍將是周慧玲在國家戲劇院所感受,一齣搞神祕的《海潮音》,也就不會有《聽海之心》在亞維儂藝術節帶給觀眾的直接感受,優人更不會從此站上國際舞台;可以說,沒有周慧玲那篇文章,就沒有現今的優人神鼓。
有時候批評不只是批評,放下抗拒,仔細聆聽,生命可能從此不相同。周慧玲的直言,幫助我面對內心不敢面對的問題,看見原來沒看見的問題。感謝周慧玲,我常說她是將優送去亞維儂藝術節的天使!
(摘自〈將優人神鼓送去亞維儂藝術節的天使〉)
舞台不是成就自己的地方,而是看見自己的機會
這階段李泰祥老師的指導對優而言,大大提升了我們對音感、節奏的準確度。他每星期都會上山好幾次,和我們一起排練。持續了十四個月,直到山上首演。
在山上演出的《太虛吟》,也打開了我們對山林中各種樂音的敏感度。因為在山上的自然環境中,不只是石頭,竹片、樹枝、風聲、鐵片,木頭、大鼓、小鼓……任何可以敲打、抖弄出聲音的器物,都可以成為李老師手中的樂器。我還記得有段時間,我們就在舞台上推著石頭滾過來滾過去,因為在他耳中,只要有聲音,就可以是音樂,宛如沉浸於大自然音聲的大地之子。
透過這次合作,西方樂理的訓練,補強了我們五年以來幾乎是土法煉鋼式的擊鼓傳授。除了音準、節奏的敏銳度,對優的整體音樂性而言,更是一次很大的躍進。而李老師吟詠二十年的《太虛吟》,也在優人的老泉山上進一步昇華,傳唱為更遼闊深遠的《曠野之歌》。
一九九九年底,優與李老師攜手合作的《曠野之歌──太虛吟Ⅲ》在老泉山上劇場首演,呈現來自大地的古老聲音、李泰祥的生命謳歌。而在這一年,台灣遭逢了世紀劇變──九二一大地震。當時,我們整團先到災區協助當地偏遠山區物資發送,也認識了埔里的鄉親。同年十二月《曠野之歌》在老泉山上公演之後,隨即跟李老師一起到重災區埔里,以《曠野之歌》跟在地朋友分享從大自然譜出的生命關懷。
阿襌學彈鋼琴之後,內在本具的旋律樂音也被喚醒了,開始嘗試旋律的音樂。也在創作中,他發現了音樂與動作之間的密切關係:從聲音當中看到了動作,也從動作當中聽到了音樂。對阿襌而言,動作即聲音,聲音即動作,也因而鋪陳了二○○六年使用鋼琴、大提琴、小提琴、笛、笙、洋琴等樂器的《與你共舞》,以及二○○七年的《入夜山嵐》兩部作品。
在舞台上,其實是看不見自己的,尤其在掌聲之中。感謝樊曼儂老師的一句話,讓我們看到自己的不足,也在尋求修正中,得到音樂大師李泰祥的專業與耐心指導。這一切過程,不只是學習,更是了解──了解自己、了解舞台不是成就自己的地方,而是看見自己的機會。
(摘自〈《太虛吟》聽見曠野的歌聲〉)
「Medea 在山上」演出呈現之後,表演藝術圈開始對葛托夫斯基具體且系統化的演員訓練方法感到好奇,想知道他到底教了我什麼。幾位想要研究這個方法的劇場老師們,策劃了一系列課程,請我示範帶領一些年輕人。我也興致勃勃、躍躍欲試。但做了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年輕人跟著做,幾位老師就在旁邊看。下課後,開始分析討論。但因為沒有親身做,看法跟我的感受一直有些差異。上了一段時間之後,對這個示範計畫,漸漸感到自己只是個工具,而不想再合作。當時在加州,是每日超過十到十五小時以上的實地訓練。西方人稱葛托夫斯基這時期的工作方式是魔鬼訓練,身體的勞累可想而知,但身體內在的領受也只有自己了解。
葛托夫斯基經常說「去做」(to do)。所以要了解葛托夫斯基,就必須親身做。正好要進行「第一種身體的行動」了,我便決定不再做示範教課。
「第一種身體的行動」結束之後,我隨即就要跟桂士達一起前往義大利,再去見葛托夫斯基。當時,我已離開加州兩年了,但還是心心念念想再去找他。桂士達告知,大師正好要開一個給舊生的工作坊,我們當然不願錯過。
同年十一月,終於在義大利佛羅倫斯附近的小鎮龐德黛拉(Pontedera)見到大師。我很緊張,但也自認有備而來,就跟桂士達一起做「運行」的動作給他看。
沒想到,他看完之後的回應是:“No, No, No. We don’t do it like this.”(不不不,我們不是這樣做。)並請湯瑪士.理查茲(Thomas Richards)示範。看見湯瑪士的動作,我當下愣住──在加州時,並不是這樣教的啊!這個舉腳的動作,以前他說要放鬆,現在卻是要繃得很緊。當下我很困惑:他到底是在找什麼?
但也立即明白他教做的動作,重點不在於姿勢,也不是技術,而是與自身內在的連結。尤其,「運行」的動作是古老瑜伽的轉化,要在山頂上凌晨日出和黃昏日落的時候做。究竟他的身體觀是什麼?身體內在跟文化、跟天地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他到底在尋找什麼?他改來改去,不斷在變化,我卻還一味地抓著他過去的東西不放?
就在重見大師的第一天,我心中卻冒出了要放下大師的念頭:我要去找到他在找的事情,而不是做他在做的事情。而且,是從我自己生長的文化源頭去尋找。
兩星期後,從義大利要返回台灣,途中經過巴黎,遇到正在寫戲劇論文的作家陳玉慧。她說:「你要回台灣做劇場,要有個團名。」她翻開《戲曲辭典》第一頁:「就叫『優』劇場吧!」「優伶」的簡稱,我覺得這個字是在形容「古老的表演者」,就說:「好喔!」
(摘自〈第一種身體的行動〉)
放下抗拒,仔細聆聽,生命可能從此不同
《海潮音》在國家戲劇院兩天的演出看似圓滿結束。幾天後,《民生報》藝文新聞版出現了一篇〈假仙扮戲演繹東方神祕?〉劇評,周慧玲在文中指出,服飾的荒謬感、擊鼓者「健美先生般竭力擠出糾結的肌肉塊」等,更直言整部作品是「假仙扮戲的做作與矯情」!
其實,就在半年前,周慧玲也曾上老泉山觀看《種花》的演出,並以「完全劇場」稱讚優,給了《種花》極高的評價。《海潮音》卻讓她受不了,從頭批判到尾。看到這劇評,我心裡好像被重重一擊──優第一次進國家戲劇院,竟然就砸鍋了。
到底哪裡不對?我一定要找出答案。於是,我一讀再讀,認真研讀周慧玲文章裡的每一句話;從服裝、動作,到舞台上呈現方式,我要知道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專業劇評者的眼睛果然銳利。事實上,我穿著那件長長戲服在台上,自己就感覺很累贅,頭上又包了一大包,的確很假仙。而周慧玲所說健美先生般的肌肉塊,我立刻意識到,應該是指〈沖岩〉段落──為了讓鼓聲清楚傳出,舞台上的鼓是斜放,鼓面朝向觀眾,所以鼓手是背對著觀眾擊鼓;當鼓手跳起來,奮力將鼓棒敲下時,觀眾看不到鼓手表情,看不見他們內在力量的呈現,只看到鼓手背部賁張的肌肉,真會覺得只是在秀肌肉。
被專業劇評者如此分析,我想,顯然這作品的呈現方式一定有問題,必須有所調整,而且費荷.達西就要來了。但如何在短短一個多月修改我們練了半年的作品呢?突然,靈機一動,何不將鼓轉過來?台下觀眾就能看到鼓手擊鼓的眼神和表情;就像短跑選手比賽時,看見選手最後衝刺時,凝聚所有能量奮力一搏的神情。
於是,我將〈沖岩〉在舞台上的鼓換了方向,而服裝的部分,就改穿平常在山上的工作服,簡單舒適。改變不多,可是,將多餘的東西拿掉後,不但團員們覺得「爽!」觀眾也能看到鼓手的呼吸、頂著一口氣往前衝上去的專注神情。當然,劇名也改了。一個多月後,再度來台的費荷.達西看到的是從《海潮音》調整後的《聽海之心》。
隔年(一九九八年)七月,我們就在法國亞維儂藝術節,以《聽海之心》在戶外演出,不僅如雷掌聲久久不絕,更被法國《世界報》(Le Monde)劇評人評為當年亞維儂上百節目中的「最佳節目」(“the best performance of the festival”)!
從此,《聽海之心》帶著我們走遍全世界,從法國到巴西、荷蘭、比利時、德國、西班牙、瑞士、義大利、挪威、英國、美國、塞內加爾、莫斯科、委內瑞拉……《紐約時報》盛讚《聽海之心》:「偉大而繁複的擊鼓、聲響,和寂靜之美。」倫敦《金融時報》則推崇:「一段綿延不絕的敲擊詩篇。」(“A prolonged percussive tone poem... ”)
周慧玲真的幫了我們一個大忙。如果沒有她那篇評論,我不會調整這作品。費荷.達西看到的,仍將是周慧玲在國家戲劇院所感受,一齣搞神祕的《海潮音》,也就不會有《聽海之心》在亞維儂藝術節帶給觀眾的直接感受,優人更不會從此站上國際舞台;可以說,沒有周慧玲那篇文章,就沒有現今的優人神鼓。
有時候批評不只是批評,放下抗拒,仔細聆聽,生命可能從此不相同。周慧玲的直言,幫助我面對內心不敢面對的問題,看見原來沒看見的問題。感謝周慧玲,我常說她是將優送去亞維儂藝術節的天使!
(摘自〈將優人神鼓送去亞維儂藝術節的天使〉)
舞台不是成就自己的地方,而是看見自己的機會
這階段李泰祥老師的指導對優而言,大大提升了我們對音感、節奏的準確度。他每星期都會上山好幾次,和我們一起排練。持續了十四個月,直到山上首演。
在山上演出的《太虛吟》,也打開了我們對山林中各種樂音的敏感度。因為在山上的自然環境中,不只是石頭,竹片、樹枝、風聲、鐵片,木頭、大鼓、小鼓……任何可以敲打、抖弄出聲音的器物,都可以成為李老師手中的樂器。我還記得有段時間,我們就在舞台上推著石頭滾過來滾過去,因為在他耳中,只要有聲音,就可以是音樂,宛如沉浸於大自然音聲的大地之子。
透過這次合作,西方樂理的訓練,補強了我們五年以來幾乎是土法煉鋼式的擊鼓傳授。除了音準、節奏的敏銳度,對優的整體音樂性而言,更是一次很大的躍進。而李老師吟詠二十年的《太虛吟》,也在優人的老泉山上進一步昇華,傳唱為更遼闊深遠的《曠野之歌》。
一九九九年底,優與李老師攜手合作的《曠野之歌──太虛吟Ⅲ》在老泉山上劇場首演,呈現來自大地的古老聲音、李泰祥的生命謳歌。而在這一年,台灣遭逢了世紀劇變──九二一大地震。當時,我們整團先到災區協助當地偏遠山區物資發送,也認識了埔里的鄉親。同年十二月《曠野之歌》在老泉山上公演之後,隨即跟李老師一起到重災區埔里,以《曠野之歌》跟在地朋友分享從大自然譜出的生命關懷。
阿襌學彈鋼琴之後,內在本具的旋律樂音也被喚醒了,開始嘗試旋律的音樂。也在創作中,他發現了音樂與動作之間的密切關係:從聲音當中看到了動作,也從動作當中聽到了音樂。對阿襌而言,動作即聲音,聲音即動作,也因而鋪陳了二○○六年使用鋼琴、大提琴、小提琴、笛、笙、洋琴等樂器的《與你共舞》,以及二○○七年的《入夜山嵐》兩部作品。
在舞台上,其實是看不見自己的,尤其在掌聲之中。感謝樊曼儂老師的一句話,讓我們看到自己的不足,也在尋求修正中,得到音樂大師李泰祥的專業與耐心指導。這一切過程,不只是學習,更是了解──了解自己、了解舞台不是成就自己的地方,而是看見自己的機會。
(摘自〈《太虛吟》聽見曠野的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