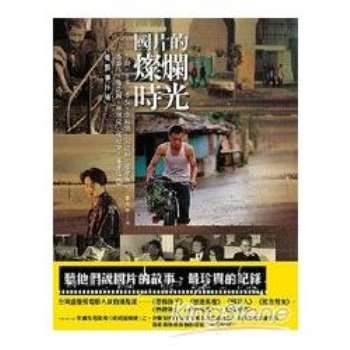故事的緣起,就是故事
(吳念真/編劇,本文整理自中影訪談)
侯孝賢的《童年往事》和楊德昌的《恐怖分子》,是我眼中最好的兩部台灣電影。《童年往事》是他的自述,記得他要跟中影報這個拍攝題材時,故事亂寫一通,當時我在中影當企劃和編劇,幫他整理了一個電影大綱交上去。
片子出來後,我非常震撼,因為那部電影讓作為台灣人的我,頭一次知道外省人的悲哀。他在裡面提到爸爸買家具都不敢買太好的,因為以後還要回去故鄉,完全不曾料到日後自己會埋骨在南方的小島上……我從《童年往事》中看到那個族群的惆悵,那已經不是個人自述了,而是整個時代動盪的集體命運。
至於《戀戀風塵》,我們是從聊天開始,大家丟自己的生命經驗,講自己的故事。其實說的時候也沒想到會拿出來拍成電影,但我對民國五十幾年年輕人島內移民、到台北尋找機會的事一直覺得很有意思,也有太多經驗可說,包括工作的待遇、和同村朋友怎樣在城市中互相支持、安慰……我把這些都講給侯孝賢聽,當時還提了另一個改編洪醒夫小說《散戲》的題材,後來孝賢去找詹宏志聊天,把幾個想拍的點子都說給他聽,宏志就建議,拍《戀戀風塵》吧。
當時孝賢和朱天文和我一起工作,因為故事是我的,他們可以用比較客觀的角度看,於是一起討論出故事大綱後,我就把劇本完成。
在這之前我已經幫中影寫了很多劇本,以前每次寫都覺得過程很痛苦,但完成《戀戀風塵》的第一版時,我印象很深,是清晨四五點,那個當下頭一次感到「啊,只有這樣唷?」那種若有所失的感覺。
是電影,還是生命經驗?
侯孝賢剪完第一版後,在中影的地下室試片,看到一些我認為很有情感的部分被剪掉,我很可惜。比如說,阿遠當兵前和女友熬夜寫信封的段落就被刪掉,那一段就是我的親身經驗。那時我女友要我帶著一千多個信封去金門,連閏年多一天她都算進去了,每一個信封都已貼好郵票,當時一張郵票兩元,花了兩千多塊,而她的月薪才六百多塊。當晚,我們兩個熬夜寫信封的地址寫到睡著,因為隔天我就要回老家準備入伍了……
但電影也有些部分很深刻地留在我腦海中,像是辛樹芬和李天祿。我第一眼看到辛樹芬的時候嚇一跳,因為她真的跟當年那個女生很像。李天祿在九份拍阿公的戲分時,我有鄰居去現場看,看到哭著出去,因為好像看到我阿公復活。
總之,從我的角度看這部電影,情感上是複雜的,但看了幾次之後,我已經感覺,這是侯孝賢的電影,不能當成我的生命經驗去看待。不過,後來我遇到天文,她很好玩,跟我念說:「ㄏㄡ!越商業他(侯孝賢)就越要剪掉!」
回想起來,當年有這樣一群人湊在一起,真的是很開心的事。大家的想法都很單純,就是怎樣讓台灣電影站起來。當年我和小野在中影工作,但整個中影唯一支持我們搞新電影的,只有總經理明驥。他是我至今遇過唯一一個會跟屬下說「這個你們是專業,我不懂,交給你們弄,我來負責」的老闆,你想想看,一個老闆能說出這種話……
現在的電影環境當然不太一樣了。老實講,現在環境比從前可能更糟。所以我也不知道能以過去的經驗給現在想做電影的人什麼影響,大概,就是保有一顆單純的心吧。
李屏賓談《戀戀風塵》——光影和鏡頭的魅力
(李屏賓/攝影指導,本文整理自中影訪談)
知道中影要把從前的電影拿出來作數位修復,我最希望的就是《戀戀風塵》和《童年往事》這兩部電影能獲得修復,因為這是我年少時期的創作,當時想法飛躍、包袱較少,因此有很多的冒險和嘗試,不像現在,經驗多了,技術也成熟了,反而難找到突破空間。
《戀戀風塵》是吳念真的年少記憶,所以在拍攝前,我跟侯導一直在想如何呈現出吳念真山上家居的環境和背景。侯導在文字創作的過程中已經有些想像,我是在看故事時感覺到,它在傳達一種時光的流逝,而這樣的感覺,經常出現在人生不同的片刻中。
這部電影有個特殊之處,就是由非專業演員擔任要角。其實從《童年往事》就開始拍非專業演員了,在這之前我們都是拍明星的,和非專業演員合作後,發現真的很難拍,你對他做出的要求、機器和光影的使用都可能對他造成影響,所以就把空間留出來,盡量不驚擾他們,讓他們能夠在那空間中隨心舒服地表演。
不過這樣一來就牽涉到光的問題,因為不容易照顧到演員的臉部、膚色、線條,但同時我也選擇放棄這樣的拍攝方式,因為片中的山野光影就足以呈現出人物的情感和遭遇了,對這群年輕的演員來說,能真誠表達情感也就夠了。
那緩緩移過山頭的雲層光影
這也是我常說想重看《戀戀風塵》最後一個(雲層光影緩緩移過山頭)畫面的原因。那個鏡頭,有著我對整部電影的觀感。
我記得拍那個畫面那天,颱風快來了,我們提前收工。攝影組先撤,到了停車場時,我看到老遠的遠山有這麼一個光,我想:整個故事講的是景物依舊、人事全非、時光流逝,就覺得這個鏡頭有意思,於是趕快把鏡頭安排好,但侯導還沒來;後來,光快要進畫面前我就開機,期待它進到好位子,因為它是雲層移動造成的,又從很遠的地方過來,很怕它不見。幸好,我們的運氣真的很好。
後來侯導來了,我跟他說可能拍到片尾可以用的鏡頭了,他一看之後,原先預計要拍的其他空鏡就都沒拍了。那個畫面,我一共拍了四百呎,以那時候來說是很多的了。
片子完成後,聽念真說日本有好多文章在談這個鏡頭,覺得這鏡頭在傳達一種訊息,好像在說話。也是從這裡,我開始發現透過鏡頭說話的可能,以及有些東西是天給你的,就像光線。常有很多很好的光線在你身邊,但你不注意,它們就不會存在。
有時候我想,儘管《戀戀風塵》是二十幾年前拍的,時代環境已經變遷,但,人生中還是有許多片刻,就像那個鏡頭──景物依舊、人事已非、時光流逝,但,生命還是有一點光劃過山際,也就有了一點希望。
廖慶松談《戀戀風塵》——侯導與楊導
(廖慶松/剪接,本文整理自中影訪談)
剪《戀戀風塵》時我也在剪《恐怖分子》,而這兩部電影都是讓我非常有成就感的作品,標記了我自己在剪接技巧和觀念上的分水嶺。
在跟侯導開始密切合作那段期間,大約是拍《風櫃來的人》時,我已對正常的剪接方式有點疲憊,想轉型,但好像又不能只是在形式上變,剛好那時在國家電影資料館看了高達、雷奈的作品,我突然發現,剪接是可以隨角色的情緒變化改變剪法的。發現這個之後,我很興奮,也就有了《恐怖分子》、《戀戀風塵》乃至於《悲情城市》,不同風格的試驗。
現在回顧,我感覺《戀戀風塵》像是我在《悲情城市》之前的練習之作,為什麼這麼說?比如《戀戀》ENDING那個山的鏡頭,就是用風景的語言描述情感,那種感覺就像古時候的詩人以景喻情,我從這裡抓到了文學性的語言,到了《悲情城市》時,就大量以杜甫律詩的結構去剪接,比如倒裝、直跳、突轉等,用詩詞的句法去營造抒情,而不是一般敘述事件、強調邏輯線性的方式。因此,對我來說,《戀戀》是《悲情》的前傳,也是我個人的成長。
侯孝賢的柔軟堅持
至於當時和兩個導演工作的經驗,也是很有趣。在剪接室和侯導跟楊導工作,表面上差異很大,但他們骨子裡對作品的控制和要求完美是一樣的。楊德昌比較低調、嚴厲,講話雖然小聲,但非常在意剪片子的方式;侯導就比較大剌剌,如果你聽到他講:「青菜,都可以!」你千萬不要相信他!
他在剪接室裡常跟我說:「你就按照我說的做,我的要是錯了,你就把我的頭斬下來當椅子坐。」但他這樣說只是用比較柔軟、不強制的方式要求你,那個堅持還是在的。
新電影那段時期,能在中影和小野、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萬仁、張毅、曾壯祥這群戰後出生的菁英一起工作,真的是一大樂事。眼看這些具文學性的新電影取代三廳電影,從我手中剪過去,現在又重新從數位修復技術再現影像的魅力,我引以為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