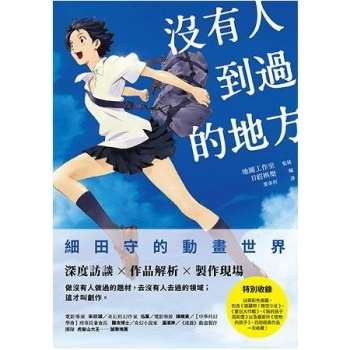從成為動畫電影導演,到成立「地圖工作室」
細田導演初次深度專訪報導──細田守導演究竟是因為什麼原因才立志製作動畫、成為動畫電影導演、成立「地圖工作室」呢?
*引用(日經娛樂!)二○一三年四月號報導的採訪內容
雖然立志成為畫家,仍難敵影像的吸引力
小學六年級畢業時不是都要在畢業紀念冊寫下將來的夢想嗎?很多人都寫在日本地圖那一頁。當時我的夢想已經很具體了,我寫「我要當動畫電影的導演」。為什麼呢?我出生於一九六七年,小學畢業剛好是一九八○,在前年,也就是一九七九,是動畫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夏季有《銀河鐵道999(THE GALLAXY EXPRESS 999)》(林重行導演作品),冬季有《魯邦三世 卡里奧斯特羅之城》(宮崎駿導演作品),雖然我還只是個小學生,看完這兩部電影卻大受感動。
此外,電影的介紹冊上還刊登了電影的設計圖――也就是分鏡。看到後我終於了解:「原來動畫電影是這樣做出來的!」同時心想「分鏡圖感覺好酷喔!」於是立志「想成為做這種電影的人」!
我本來就很喜歡畫畫,當然也喜歡動畫。一般來說,喜歡畫畫的人多半「想當漫畫家」。不過,不知為何我不怎麼想當漫畫家,而想拍動畫電影。我猜大概是因為「影像」的緣故吧。圖像會動,這對我來說是非常特別的,看到也令我興奮不已。
不過,就算想成為動畫導演,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如果是畫家,身邊至少還有美術老師或是類似背景的大人,比較懂得該怎麼入門。因此,當我升大學時選擇報考美術大學,基本上也是希望成為畫家,感覺好像比較實際。
雖然立志成為畫家,但影像對我來說仍有著難以抵擋的吸引力。大學在電影社也嘗試自行製作拍片,非常好玩喔。影像製作是沒辦法靠一個人完成的,大夥兒從分工合作開始就開心得不得了。畫家呢,基本上不就是一個人埋頭創作嗎?這種事情我從小就經歷過了。我其實不太善於跟別人互動,而在分工合作的影像製作過程中……該怎麼說呢,就是有種一個人創作時感受不到的「樂趣」。大家朝著共同的目標努力,對我來說這也有著難以抗拒的吸引力。我就讀的是金澤美術工藝大學。在這類美術大學裡,有許許多多很有個性的人。雖然美術系多半都是些自我中心的傢伙,但該怎麼把這些人才整合在一起,是非常有意思也令人期待不已的。再說,美術大學的學生雖然都習慣單打獨鬥,但團隊合作的樂趣倒是有種新鮮的感覺,參與者多半也願意接受。
我們學校規模比較小,當時整個學院只有一百四十四人,所以跟同屆的都很熟。其他像是學長姐、學弟妹,也大概都知道是哪些人。因此很容易知道誰比較有趣、誰比較漂亮、誰比較好商量。如果是規模大的大學,或許只能在社團裡活動,但小學校就是有這種好處。
進入東映動畫,跟著許多導演,學到很多
進入大學後念到一半,我還想成為畫家,但在獲得拍電影的經驗後,就開始考慮「我想當導演」。於是,後來我就進了東映動畫(現在的東映Animation),來到動畫製作第一線。但因為我好歹也是美術大學畢業,一開始被分配到繪圖的工作,擔任動畫師,工作內容就是在其他動畫師畫好原畫後製作中割(填補原畫與原畫之間的工作)。
此外,我還有機會去協助很多導演的作品。在東映有個好處,就是這裡有非常多位導演。對於這樣形形色色的導演,光看作品或許無法完全認識,但實際接觸後就會知道他們的優點和有趣之處;反過來也會知道缺點,例如工作步調太快或太慢等等這些負面教材,都讓人非常受用。尤其,自己擔任過動畫師就知道動畫師的工作有多辛苦,會想盡可能當個優秀的導演。想把自己的勞力貢獻給一個打從心底覺得值得為他付出的人。在那樣的環境下工作自然會這麼想。
那段時間,有拍攝《聖鬥士星矢》(一九八八)、《七龍珠Z》(一九九三)劇場版的山內重保導演,還有《美少女戰士》(一九九二)、《少女革命》(一九九七)的導演幾原邦彥等幾位前輩。在他們手下工作學到很多。其他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導演,每個導演的風格都不同,各有差異。去了解每一位導演構思故事背景和世界觀的方式,又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東映動畫對我而言是個很好的學校。當年的東映少說也有五十位導演,能夠看到每個人各自的風格,真的學了不少,會有很多老師告訴你導演這個工作要做些什麼,電影又是什麼。當然,我並不是要說有人會主動教你,但身邊就有這麼多能學習的對象,真是慶幸。直到現在我都還常懷念那個地方,因為那裡真的是個好環境。
一般有心想學習的年輕人一定會想要拜業界優秀或知名的人才為師,希望獲得傳授。過去我也曾這麼想,畢竟這也是一種學習方法。不過,如果只在單一位大師門下擔任助理,不就只能學到一種方式嗎?就我個人來說,在一個能見識到各種不同風格與實踐方式的地方比較好,如果有五十個人,就會有五十種不同的呈現方式,由於每種都不同,會比較容易了解、掌握所謂的呈現是什麼,藝術又該如何表現。
更重要的是,即使跟在偉大的藝術家身邊,跟他做著同樣的事,也未必能達到同樣的效果。反之,既然沒辦法做出一樣的事,不如就學習各種類型的做法,用自己能理解的方式達到可以表現的程度,以及想要表達的內容。我認為這樣是比較正確的。
第一部電影有種「總算走到這裡了」的感覺
當然,我進入東映動畫最終的目的並不只是想學習。前面提到的《銀河鐵道999》也是東映動畫的作品,我還很喜歡《穿靴子的貓》這部東映的長篇動畫。不過,嚴格說來,《銀河鐵道999》並不是東映長篇。
在東映動畫的歷史上,從一九五八年在戲院上映的第一部電影作品《白蛇傳》,到《神龍之子太郎》(一九七九),這段時間主要都是以民間傳說為題材,片長八十到九十分鐘的電影稱為「東映長篇」。《銀河鐵道999》雖然是片長超過兩小時的長篇作品,卻不稱為「長篇」,而叫「電視劇場版」。公司裡有不少人對東映動畫的劇場版作品有一分憧憬,很多做漫畫原著改編的電視動畫的人,當初進公司的夢想也是有朝一日能做到像東映長篇那樣的作品。一邊聽有參與的前輩講解東映長篇是怎麼拍出來,還看到很多資料,真是非常好玩。當時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時代,「過去是這麼費心製作,現在真的沒辦法了。」也是有人這麼說吧。《神龍之子太郎》之後,就沒有東映長篇了,但還是常聽前輩或是身邊的人說「就算現在沒辦法,總有一天還是要做出像『東映長篇』的作品。」於是,自己也不知不覺也像其他前輩一樣以拍攝東映長篇為目標。或許未來自己也有機會來到那個境界,所以要先儲備好實力,等待那一天到來。於是,我在一九九六年參加考試,成為導演。
第一次獲得拍電影的機會,就是一九九九年的《數碼寶貝大冒險》。我從擔任動畫師的時期就參與東映劇場電影「東映動畫博覽會」的片子。當我表明了對電視沒有意願,而是想拍電影後,製作部長問我:「要不要試著做一部在動畫博覽會上放映的短篇作?」我聽了高興得不得了。整個博覽會也不過只有三、四部作品,其中一部竟然是我的,這對我而言便是我電影的處女作。當時的心情是:我終於也來到這裡了!過去學習的一切成果終於有機會發揮。我產生一股強烈的意志,對自己說:「我一定要拍得很有趣,做出一部很棒的電影。」
《數碼寶貝大冒險》的幸運之處在於:它不是已經在電視上播映了好長一段時間,然後才交給劇場版的導演來負責。博覽會上的公開播放其實是在電視系列之前。一般而言,東映劇場版的中心目標是要讓長期在電視機前收看的觀眾,有機會在劇場這樣豪華的場地欣賞動畫。不過,在電視動畫系列還沒問世時,創作的自由度也相對較高。也沒有所謂的「試映版(Pilot)」,因為當時仍在討論要不要製作電視版本。我不太清楚電視臺的組織架構,總之,得在三個月前才能決定播放與否。然而,由於是跨媒體,必須在電視系列開始播出時,劇場版配合其時機上映。因此,即使不確定電視版要不要播出,還是非開始進行劇場版不可。搞不好到時就不播放電視版了,但劇場版一上映,就不能後悔。因為這樣,就只做了二十分鐘的短篇。但我總算能拍攝第一部電影了。我在東映長篇的歷史上能有一部電影作品,實在非常光榮。之後,那股「想拍長篇」的情緒越來越強烈。當然,擔任過電視版導演對於在動畫業界的資歷也很重要,同樣是值得驕傲的。不過我卻沒有這段經歷,或許我曾有過機會,但我還是比較想拍電影。後來,我因為種種狀況離開了惠我良多的東映,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搞不好會走到死巷子裡。但我還是「想拍電影」,這股信念孕育出《跳躍吧!時空少女》以及之後的作品。一路走來,我一直堅持「想拍電影」這個信念。
第四個位子坐著「電影之神」
要拍《跳躍吧!時空少女》時,我說是要拍動畫電影,有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到這時還想改編成動畫?」因為包括大林宣彥導演在內,這本原著已經多次改編成影視作品。然而,我認為每一個時代都應該有能反應出該時代的作品,隨時隨地都要為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創作出給他們欣賞的片子。因此,我是以要讓這個世代的人也感到新鮮的宗旨下創作,沒想到竟然那麼暢銷,還大受歡迎那麼久,至今富士電視臺的黃金時段仍會播放。這部電影以一種前所未有、難以想像的方式讓更多人看到。
是因為有《跳躍吧!時空少女》,才有「那部片」嗎?就是我忍不住自問「過去影史上有『一大家子拯救世界』的電影嗎?我想沒有吧。」而就是因為這樣,我才拍了《夏日大作戰》(二○○九)。
拍電影時有部分真的是要等到最後結果揭曉才會知道的。觀眾喜不喜歡也得等觀眾看了才知道呀。如果先有電視版才拍成電影,心裡多少會有個底,但原創作品真的無從得知。我認為,既然是這樣,要是不是稍微具挑戰性的內容,觀眾可能連看都不想看呢。必須要讓觀眾看了之後揮手大喊著說:「這跟其他的電影都不一樣!」或是「這部片好有趣喔!」要是不能做出這種水準的作品,沒有人會多看一眼的。打安全牌換句話說就是隨處可見。所以我認為必須隨時保持挑戰的心。
當初因為對東映長篇懷有憧憬,因此想拍電影,後來也真的拍了,但這條路越走越覺得電影真是好難,深切感受到它的難度簡直沒有極限。另一方面,獲得許多意想不到的支持,也是電影的有趣之處。所以每次我都會這麼想,在導演、製作人和編劇討論內容的會議上共識三個座位,但其實「還有另一個座位」。如果問我另一個座位上是誰,我想就是「電影之神」。電影的命運就看電影之神的心情好壞來決定。即使做好萬全準備,盡了人事、做了各式各樣的宣傳、並且認為「這下絕對沒問題!」但最後的決定權還是在電影之神手上。從這個角度來看,第四個座位上的電影之神似乎很喜歡《狼的孩子雨和雪》(二○一二)。這真的非常幸運。無論是《夏日大作戰》或是《跳躍吧!時空少女》,過程中都有很多不安與擔憂,但我想必受到了電影之神的眷顧,最後都能順利完成,而且還獲得下一次機會。
當然,拍電影未必每次都這麼順遂,票房失敗的機率也很高。我覺得既然是這樣,就該拍出會讓觀眾覺得「來看這部片是對的!」的電影。約會時看的電影絕對不能失敗呀!一定要拍出「邀人一起去看,接下來去吃飯的時光也變得更愉快」的電影才對。
希望能在地圖工作室創作出能一同思考人生的電影
因為《跳躍吧!時空少女》這部片,我獲得參加國外的影展的機會,開始更常思考日本的環境。如果電影是一種吸收了當地人情緒的產物,那麼,看到各國導演以各自國家的狀況為題材來創作電影時,我都會思考:日本的狀況又是怎麼樣的呢?我們意識到這樣的問題了嗎?每次出國,我都特別會反思日本的情況。
因此,我就會想:會不會有些東西在日本因為太貼近生活,因此沒被注意到,搞不好那其實是全球共通的題材?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對此有共鳴,不就應該拍成電影嗎?例如,不管是哪個國家的人,一定都有親戚吧?親子關係與孩子的成長也是全世界的人共同的體驗。我們經常會說「大眾題材」,也就是只要身而為人都會面對到的相同問題。有時候,身在日本會很難客觀地去看日本的狀況,但若是到了國外看電影,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夏日大作戰》或是《狼的孩子雨和雪》的主題在日本而言,會被認為是非常具挑戰性的嘗試,但若是強調出來到海外仍能引起共鳴的因素,家庭問題就會是個很重要的題材,也非常吸引人――而且到最後反而會覺得「只有這個主題了吧」。其實在國外也能看到非常多這樣的作品。
在拍攝《狼的孩子雨和雪》時,我成立了「地圖工作室」。這是個非常小的地方,也可能隨時會消失,但我們的將來會怎麼發展,或許就像我前面提到,得看另一個座位上的電影之神的臉色。成立一間公司並不代表從此就能獲得自由,或保證創作的主體性不受動搖。因為所謂主體性從一開始就已存在,就算開了公司,預算也不會是無上限,最終結果還是會跟過去一樣。只不過,即使有重重限制,但能和一群夥伴一同創作電影,還有更重要的是:我想做出能讓更多人看到、而且看過的觀眾都會覺得「這部電影真不賴!」的作品。又或是做出能讓大家共同思考人生的電影。
透過電影,未來還能認識更多人,一起去分享這個世界上各種有趣的東西,我覺得這樣真好。
細田導演初次深度專訪報導──細田守導演究竟是因為什麼原因才立志製作動畫、成為動畫電影導演、成立「地圖工作室」呢?
*引用(日經娛樂!)二○一三年四月號報導的採訪內容
雖然立志成為畫家,仍難敵影像的吸引力
小學六年級畢業時不是都要在畢業紀念冊寫下將來的夢想嗎?很多人都寫在日本地圖那一頁。當時我的夢想已經很具體了,我寫「我要當動畫電影的導演」。為什麼呢?我出生於一九六七年,小學畢業剛好是一九八○,在前年,也就是一九七九,是動畫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夏季有《銀河鐵道999(THE GALLAXY EXPRESS 999)》(林重行導演作品),冬季有《魯邦三世 卡里奧斯特羅之城》(宮崎駿導演作品),雖然我還只是個小學生,看完這兩部電影卻大受感動。
此外,電影的介紹冊上還刊登了電影的設計圖――也就是分鏡。看到後我終於了解:「原來動畫電影是這樣做出來的!」同時心想「分鏡圖感覺好酷喔!」於是立志「想成為做這種電影的人」!
我本來就很喜歡畫畫,當然也喜歡動畫。一般來說,喜歡畫畫的人多半「想當漫畫家」。不過,不知為何我不怎麼想當漫畫家,而想拍動畫電影。我猜大概是因為「影像」的緣故吧。圖像會動,這對我來說是非常特別的,看到也令我興奮不已。
不過,就算想成為動畫導演,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如果是畫家,身邊至少還有美術老師或是類似背景的大人,比較懂得該怎麼入門。因此,當我升大學時選擇報考美術大學,基本上也是希望成為畫家,感覺好像比較實際。
雖然立志成為畫家,但影像對我來說仍有著難以抵擋的吸引力。大學在電影社也嘗試自行製作拍片,非常好玩喔。影像製作是沒辦法靠一個人完成的,大夥兒從分工合作開始就開心得不得了。畫家呢,基本上不就是一個人埋頭創作嗎?這種事情我從小就經歷過了。我其實不太善於跟別人互動,而在分工合作的影像製作過程中……該怎麼說呢,就是有種一個人創作時感受不到的「樂趣」。大家朝著共同的目標努力,對我來說這也有著難以抗拒的吸引力。我就讀的是金澤美術工藝大學。在這類美術大學裡,有許許多多很有個性的人。雖然美術系多半都是些自我中心的傢伙,但該怎麼把這些人才整合在一起,是非常有意思也令人期待不已的。再說,美術大學的學生雖然都習慣單打獨鬥,但團隊合作的樂趣倒是有種新鮮的感覺,參與者多半也願意接受。
我們學校規模比較小,當時整個學院只有一百四十四人,所以跟同屆的都很熟。其他像是學長姐、學弟妹,也大概都知道是哪些人。因此很容易知道誰比較有趣、誰比較漂亮、誰比較好商量。如果是規模大的大學,或許只能在社團裡活動,但小學校就是有這種好處。
進入東映動畫,跟著許多導演,學到很多
進入大學後念到一半,我還想成為畫家,但在獲得拍電影的經驗後,就開始考慮「我想當導演」。於是,後來我就進了東映動畫(現在的東映Animation),來到動畫製作第一線。但因為我好歹也是美術大學畢業,一開始被分配到繪圖的工作,擔任動畫師,工作內容就是在其他動畫師畫好原畫後製作中割(填補原畫與原畫之間的工作)。
此外,我還有機會去協助很多導演的作品。在東映有個好處,就是這裡有非常多位導演。對於這樣形形色色的導演,光看作品或許無法完全認識,但實際接觸後就會知道他們的優點和有趣之處;反過來也會知道缺點,例如工作步調太快或太慢等等這些負面教材,都讓人非常受用。尤其,自己擔任過動畫師就知道動畫師的工作有多辛苦,會想盡可能當個優秀的導演。想把自己的勞力貢獻給一個打從心底覺得值得為他付出的人。在那樣的環境下工作自然會這麼想。
那段時間,有拍攝《聖鬥士星矢》(一九八八)、《七龍珠Z》(一九九三)劇場版的山內重保導演,還有《美少女戰士》(一九九二)、《少女革命》(一九九七)的導演幾原邦彥等幾位前輩。在他們手下工作學到很多。其他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導演,每個導演的風格都不同,各有差異。去了解每一位導演構思故事背景和世界觀的方式,又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東映動畫對我而言是個很好的學校。當年的東映少說也有五十位導演,能夠看到每個人各自的風格,真的學了不少,會有很多老師告訴你導演這個工作要做些什麼,電影又是什麼。當然,我並不是要說有人會主動教你,但身邊就有這麼多能學習的對象,真是慶幸。直到現在我都還常懷念那個地方,因為那裡真的是個好環境。
一般有心想學習的年輕人一定會想要拜業界優秀或知名的人才為師,希望獲得傳授。過去我也曾這麼想,畢竟這也是一種學習方法。不過,如果只在單一位大師門下擔任助理,不就只能學到一種方式嗎?就我個人來說,在一個能見識到各種不同風格與實踐方式的地方比較好,如果有五十個人,就會有五十種不同的呈現方式,由於每種都不同,會比較容易了解、掌握所謂的呈現是什麼,藝術又該如何表現。
更重要的是,即使跟在偉大的藝術家身邊,跟他做著同樣的事,也未必能達到同樣的效果。反之,既然沒辦法做出一樣的事,不如就學習各種類型的做法,用自己能理解的方式達到可以表現的程度,以及想要表達的內容。我認為這樣是比較正確的。
第一部電影有種「總算走到這裡了」的感覺
當然,我進入東映動畫最終的目的並不只是想學習。前面提到的《銀河鐵道999》也是東映動畫的作品,我還很喜歡《穿靴子的貓》這部東映的長篇動畫。不過,嚴格說來,《銀河鐵道999》並不是東映長篇。
在東映動畫的歷史上,從一九五八年在戲院上映的第一部電影作品《白蛇傳》,到《神龍之子太郎》(一九七九),這段時間主要都是以民間傳說為題材,片長八十到九十分鐘的電影稱為「東映長篇」。《銀河鐵道999》雖然是片長超過兩小時的長篇作品,卻不稱為「長篇」,而叫「電視劇場版」。公司裡有不少人對東映動畫的劇場版作品有一分憧憬,很多做漫畫原著改編的電視動畫的人,當初進公司的夢想也是有朝一日能做到像東映長篇那樣的作品。一邊聽有參與的前輩講解東映長篇是怎麼拍出來,還看到很多資料,真是非常好玩。當時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時代,「過去是這麼費心製作,現在真的沒辦法了。」也是有人這麼說吧。《神龍之子太郎》之後,就沒有東映長篇了,但還是常聽前輩或是身邊的人說「就算現在沒辦法,總有一天還是要做出像『東映長篇』的作品。」於是,自己也不知不覺也像其他前輩一樣以拍攝東映長篇為目標。或許未來自己也有機會來到那個境界,所以要先儲備好實力,等待那一天到來。於是,我在一九九六年參加考試,成為導演。
第一次獲得拍電影的機會,就是一九九九年的《數碼寶貝大冒險》。我從擔任動畫師的時期就參與東映劇場電影「東映動畫博覽會」的片子。當我表明了對電視沒有意願,而是想拍電影後,製作部長問我:「要不要試著做一部在動畫博覽會上放映的短篇作?」我聽了高興得不得了。整個博覽會也不過只有三、四部作品,其中一部竟然是我的,這對我而言便是我電影的處女作。當時的心情是:我終於也來到這裡了!過去學習的一切成果終於有機會發揮。我產生一股強烈的意志,對自己說:「我一定要拍得很有趣,做出一部很棒的電影。」
《數碼寶貝大冒險》的幸運之處在於:它不是已經在電視上播映了好長一段時間,然後才交給劇場版的導演來負責。博覽會上的公開播放其實是在電視系列之前。一般而言,東映劇場版的中心目標是要讓長期在電視機前收看的觀眾,有機會在劇場這樣豪華的場地欣賞動畫。不過,在電視動畫系列還沒問世時,創作的自由度也相對較高。也沒有所謂的「試映版(Pilot)」,因為當時仍在討論要不要製作電視版本。我不太清楚電視臺的組織架構,總之,得在三個月前才能決定播放與否。然而,由於是跨媒體,必須在電視系列開始播出時,劇場版配合其時機上映。因此,即使不確定電視版要不要播出,還是非開始進行劇場版不可。搞不好到時就不播放電視版了,但劇場版一上映,就不能後悔。因為這樣,就只做了二十分鐘的短篇。但我總算能拍攝第一部電影了。我在東映長篇的歷史上能有一部電影作品,實在非常光榮。之後,那股「想拍長篇」的情緒越來越強烈。當然,擔任過電視版導演對於在動畫業界的資歷也很重要,同樣是值得驕傲的。不過我卻沒有這段經歷,或許我曾有過機會,但我還是比較想拍電影。後來,我因為種種狀況離開了惠我良多的東映,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搞不好會走到死巷子裡。但我還是「想拍電影」,這股信念孕育出《跳躍吧!時空少女》以及之後的作品。一路走來,我一直堅持「想拍電影」這個信念。
第四個位子坐著「電影之神」
要拍《跳躍吧!時空少女》時,我說是要拍動畫電影,有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到這時還想改編成動畫?」因為包括大林宣彥導演在內,這本原著已經多次改編成影視作品。然而,我認為每一個時代都應該有能反應出該時代的作品,隨時隨地都要為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創作出給他們欣賞的片子。因此,我是以要讓這個世代的人也感到新鮮的宗旨下創作,沒想到竟然那麼暢銷,還大受歡迎那麼久,至今富士電視臺的黃金時段仍會播放。這部電影以一種前所未有、難以想像的方式讓更多人看到。
是因為有《跳躍吧!時空少女》,才有「那部片」嗎?就是我忍不住自問「過去影史上有『一大家子拯救世界』的電影嗎?我想沒有吧。」而就是因為這樣,我才拍了《夏日大作戰》(二○○九)。
拍電影時有部分真的是要等到最後結果揭曉才會知道的。觀眾喜不喜歡也得等觀眾看了才知道呀。如果先有電視版才拍成電影,心裡多少會有個底,但原創作品真的無從得知。我認為,既然是這樣,要是不是稍微具挑戰性的內容,觀眾可能連看都不想看呢。必須要讓觀眾看了之後揮手大喊著說:「這跟其他的電影都不一樣!」或是「這部片好有趣喔!」要是不能做出這種水準的作品,沒有人會多看一眼的。打安全牌換句話說就是隨處可見。所以我認為必須隨時保持挑戰的心。
當初因為對東映長篇懷有憧憬,因此想拍電影,後來也真的拍了,但這條路越走越覺得電影真是好難,深切感受到它的難度簡直沒有極限。另一方面,獲得許多意想不到的支持,也是電影的有趣之處。所以每次我都會這麼想,在導演、製作人和編劇討論內容的會議上共識三個座位,但其實「還有另一個座位」。如果問我另一個座位上是誰,我想就是「電影之神」。電影的命運就看電影之神的心情好壞來決定。即使做好萬全準備,盡了人事、做了各式各樣的宣傳、並且認為「這下絕對沒問題!」但最後的決定權還是在電影之神手上。從這個角度來看,第四個座位上的電影之神似乎很喜歡《狼的孩子雨和雪》(二○一二)。這真的非常幸運。無論是《夏日大作戰》或是《跳躍吧!時空少女》,過程中都有很多不安與擔憂,但我想必受到了電影之神的眷顧,最後都能順利完成,而且還獲得下一次機會。
當然,拍電影未必每次都這麼順遂,票房失敗的機率也很高。我覺得既然是這樣,就該拍出會讓觀眾覺得「來看這部片是對的!」的電影。約會時看的電影絕對不能失敗呀!一定要拍出「邀人一起去看,接下來去吃飯的時光也變得更愉快」的電影才對。
希望能在地圖工作室創作出能一同思考人生的電影
因為《跳躍吧!時空少女》這部片,我獲得參加國外的影展的機會,開始更常思考日本的環境。如果電影是一種吸收了當地人情緒的產物,那麼,看到各國導演以各自國家的狀況為題材來創作電影時,我都會思考:日本的狀況又是怎麼樣的呢?我們意識到這樣的問題了嗎?每次出國,我都特別會反思日本的情況。
因此,我就會想:會不會有些東西在日本因為太貼近生活,因此沒被注意到,搞不好那其實是全球共通的題材?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對此有共鳴,不就應該拍成電影嗎?例如,不管是哪個國家的人,一定都有親戚吧?親子關係與孩子的成長也是全世界的人共同的體驗。我們經常會說「大眾題材」,也就是只要身而為人都會面對到的相同問題。有時候,身在日本會很難客觀地去看日本的狀況,但若是到了國外看電影,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夏日大作戰》或是《狼的孩子雨和雪》的主題在日本而言,會被認為是非常具挑戰性的嘗試,但若是強調出來到海外仍能引起共鳴的因素,家庭問題就會是個很重要的題材,也非常吸引人――而且到最後反而會覺得「只有這個主題了吧」。其實在國外也能看到非常多這樣的作品。
在拍攝《狼的孩子雨和雪》時,我成立了「地圖工作室」。這是個非常小的地方,也可能隨時會消失,但我們的將來會怎麼發展,或許就像我前面提到,得看另一個座位上的電影之神的臉色。成立一間公司並不代表從此就能獲得自由,或保證創作的主體性不受動搖。因為所謂主體性從一開始就已存在,就算開了公司,預算也不會是無上限,最終結果還是會跟過去一樣。只不過,即使有重重限制,但能和一群夥伴一同創作電影,還有更重要的是:我想做出能讓更多人看到、而且看過的觀眾都會覺得「這部電影真不賴!」的作品。又或是做出能讓大家共同思考人生的電影。
透過電影,未來還能認識更多人,一起去分享這個世界上各種有趣的東西,我覺得這樣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