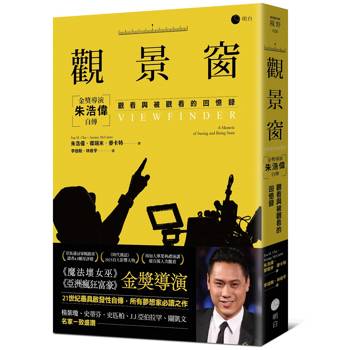第一章
在我的學校裡,籃球隊員就像神一樣,他們高大挺拔,充滿自信和勇氣。我哥賴瑞不是隊上最高的球員──他自稱身高六呎二(約一百八十八公分),比較科學的說法是六呎一(約一百八十五公分)但他絕對是球隊的領袖人物。我五年級時,正值賴瑞和隊友稱霸聯盟。有些朋友向我承認,他們和我混在一起,只是為了能跟賴瑞玩 (這些朋友現在還是這樣講)。
我不怪他們。賴瑞不僅是明星運動員,他還有第二個特點,此一特點對他弟弟後來的人生和職涯影響深遠:他是「電影明星」。
在大賽之前,全校都會湧進體育館觀賞球隊的精采集錦影片:關鍵投籃,防守爭搶,超強球技,再配上炫目標題和超炸配樂。今天,任何擁有智慧型手機的人都可以製作出更精緻的影片。但在一九九○年,學校周遭只有少數人擁有創造這些奇觀所需的工具和技能,就連籃球隊員都對這些人敬畏有加,給予他們電影製作最高讚譽:下一個史蒂芬.史匹柏。
歸功於籃球活動的人氣,拍攝電影的熱潮席捲了松林預校(Pinewood School)的校園,有些老師甚至允許我們以「製作影片」代替「撰寫讀書報告」。賴瑞非常熱中「影片代替作業」的形式,像他這種善於交際的人,拍影片遠比寫論文來得有趣。但相較於寫論文,拍電影有個缺點,你必須扛著沉重的攝影機。在錄影帶年代,光是電池的尺寸和重量就相當於一塊磚頭。但賴瑞找到了解決方案:他老弟。
有一天,他正製作英語課影片作業,內容應該是《坎特伯里故事集》,這可以解釋為何我記憶中賴瑞和他的朋友會打扮成中世紀鄉紳在洛沙托斯閒晃。一如往常,我拿著攝影機跟在後面,經過閒晃、隨興拍攝的一整天後,賴瑞宣布停機。他和搭檔回到「基地營」,也就是我家客廳。接下來,事情才開始變得有趣。
賴瑞霸占了電視和錄放影機,從爸媽房間搬來另一台錄放影機。他的一個朋友──少數清楚影片來源的聰明人──在咖啡桌上放一台我後來才知道叫「混音器」的機器。混音器裝好後,又把其他器材散布在地板上,黃紅白三色線材被連結拼湊成蜘蛛網一般。
這時我才明白,這些設備是用來「剪輯」。當時我不知道這個專有名詞是什麼意思,但我不想因為發問而引人注意,尤其是在金童酷大哥允許我和他一起混的時候。
終於我發現「剪輯」是指把我們錄下來的影像和聲音切割開來,再重新拼接回去。聽起來很簡單,但事實上就算是最基本的修改也複雜得難以置信,一定要依照正確順序按下正確按鈕:暫停、錄製、快轉、錄製、倒退、錄製。慢慢地,一段一段剪,一段一段接,影片才慢慢變好,獲得節奏與張力,帶出一些充滿情感的片刻。一兩個小時後,整天胡鬧的屁孩們開始像稱職的表演者,像是真正在乎自己所做的事。
然而賴瑞還不滿意。他有一個願景,他想藉由加入英國喜劇電影《聖杯傳奇》的片段來增強影片效果:上帝撥開雲層與下方的人對話,但音源換成賴瑞的聲音。在那笨拙的老類比時代,這種混合音訊與影像效果的進行方式,會讓剪接過程複雜到嚇人。這意味著要同時按下一堆按鈕,旋轉一堆轉盤,並調整一堆推桿。賴瑞想達到夠大的效果,就需要每個人幫忙,甚至包括我。
我坐在音響前方的指定位置,指尖懸停在播放按鈕上。
三……二……一 ……錄!
手指按下,轉盤旋轉,磁帶開始滾動。
沒成功。我們的時間點必須抓得更完美,但它總是不完美,我們必須再試一次,然後又再試一次。每次失敗,都會增加壓力。當你用錄影帶或任何類比技術作業時,每次重錄都會讓畫面品質下降。
最後,我們以為已經搞定。但是回放重播時,全都笑到東倒西歪。這超可笑的,有夠天才啦!
三十五年後,我仍記得那一刻感受到的驚嘆──在我腦海中閃過改變一生的頓悟。
喔!我想,電影就是這樣拍出來的。
────
松林預校雖然允許我們以拍影片代替寫作業,但這不代表學校採取無拘無束、隨心所欲的教育方針。儘管校方宣稱該校並無教派,但它是由摩門教家庭所創辦,並受到摩門教價值觀影響。先不說在校園裡喝酒、抽菸或吸毒,我們甚至不能攝取咖啡因。有些孩子可能會對這些規定感到窒悶,但我感覺受到保護。
所有人在松林預校都被妥善照顧,但我比多數人受到更多庇護。我和賴瑞相差六歲,在這六年間,父母又多添了三個孩子:克莉絲汀娜、霍華和珍妮佛。到我夠大到能穿上松林制服時,兄姊已為我在學校鋪好路。老師們在見到我之前,就已先知道我了。
接送朱家小孩上下學和參加課外活動,對我父母來說是持續性的挑戰。無奈我父親工作時間長得令人難以置信,例如,在餐廳他總是「最先到」和「最後走」,總是錯過家庭假期(他常說,中餐館的管理就是「微觀管理」,要事必躬親),因此,管理我們這團騷亂的責任就落在我媽身上。我知道她要面對的挑戰,所以當她偶爾忘記在放學時來接我,我不會當成是針對我個人。為了掩飾尷尬,我會讓老師以為我正朝我媽的廂型車走去,然後躲進灌木叢裡,等所有人都離開後,再走到幾個街區外的阿姨家。
不過,童年時的許多星期天,我們並沒有分頭行動,而是集體移動。我媽會開車載五個孩子到舊金山,我們購買所有演出的季票:歌劇、芭蕾舞、交響樂。因為我們年年都去,所以總能拿到很棒的位子。中場休息時,我會晃到樂池裡檢查樂器。久而久之,連舊金山芭蕾管弦樂團的指揮丹尼斯.德.科托都認識我了。
「總有一天你會成為我們的首席小提琴手,對吧?」
「其實,我比較想要你的工作。」
他大笑之後,把指揮棒遞給我,還要我保管好。我超愛那根指揮棒,並且確實一直保管著,直到被我的狗咬爛。
我媽誠心渴望我們能認識貝多芬和布拉姆斯。但當我回想那些外出時光,總覺得它們像是一種「說故事」的行動。那是她為我們家庭「編織敘事」的機會,而觀眾是恰巧在場的旁人。
我媽殷切期盼我們家就是典型的「美國夢家庭」。我們和其他人一樣聰明,一樣有教養,我們做得到,我們夠資格。我們不會在週日下午無精打采地穿過飯店大廳,她會確保我們穿著稱頭的西裝,看起來帥氣。
這個「故事」不只是由我們講述,也不只是關於我們,而是為了我們而存在的,我媽希望我們能在陌生環境的規範和儀式中感到自在。她以自身為榜樣,教我們如何自信應對任何狀況(我母親平時親切又笑容滿面,除非你惹到她。我們家幾乎都是天蠍座,這就說得通了)。她希望我們感到自己屬於這裡,屬於任何地方。
一切都照計畫進行。大概啦!
你可能以為朱家孩子參加音樂會的那些年,會讓他們稍微像全神貫注的小樂迷,但不幸坐在我們旁邊的觀眾會告訴你事實並非如此。我媽可以堅持讓我們去看表演,但面對五個盛裝打扮的小孩,父母所能施加的控制都很有限。有時我們會專注欣賞,但多數時間都很失控。
我們難免會惹來鄰座的白眼,也聽過不少難聽的耳語。你大概可以想像,這會帶來一些麻煩──甚至可能是一場危機,這和我們原本應該向所有人展示的家庭形象與優雅教養背道而馳。母親完全清楚這些騷亂,她該如何讓她的「故事」保持完美無瑕呢?
她的解方充滿啟示性,真的足智多謀。她無視那些責難、噓聲、輕蔑、怒目,任由它們從身邊掠過。當我和兄姊們看到那些狀況對她無關緊要時,我們也決定不去在意。她從未告訴我們她在做什麼,她構築出一個氣泡般的屏障,一道能量場,我們可以在裡面培養自我意識,與外界射來的箭矢隔絕。
有時,那些被冒犯的鄰座或許有點道理。也許我們本可以少開幾個關於穿緊身褲男士走光的玩笑。但多年來,我們常在自己並無過錯卻仍遭受到傷害性言行時,想起母親的教誨。這等同於一種家訓,從未宣示卻始終恪遵:當別人惡待你時,絕對不要抱怨。
絕對不要抱怨。
────
在我們非凡家庭的「故事」中,每個人都應該是與眾不同的個體。也正因如此,從小開始,媽媽就給我們機會培養各種天賦、才華、技能與興趣。
我們上過各式各樣的課程:學習如何演奏小步舞曲,如何在上網時打出吊球,如何切球上果嶺。甚至上禮儀課,由一位正經八百的英國女士教導如何正確喝完一碗湯(完全不是粗魯的美式喝法)。這像是社交十項全能訓練計畫,媽媽精心準備,為的是讓我們能昂首闊步走進任何場合,贏得別人的尊重。
最後,我們各自找到不同的定位。例如,克莉絲汀娜發現並培養了非凡的芭蕾舞天賦,在我看來,她盡可以在那條路上大展身手。舞蹈從來不是我的強項,即使上了十二年踢踏舞課之後也不是(對小孩幫助不大,但對後來拍音樂劇電影的導演來說,真是大有用處)。珍妮佛在籃球和舞蹈方面都表現出色,我則是被貼上「創意者」的標籤。在混亂的家庭中,我用想像力為自己創造一個安全的世界,尤其是手裡拿著色鉛筆時。
我愛畫畫,我一直在畫畫。我會虛構出異世界的生物,然後將它們勾勒在紙上。我不是班上繪畫最好的人,但我從中得到的快樂無人能及。更廣義來說,「創意者」只是「怪咖」的委婉說法。在學校裡有兄姊保護,我可以隨心所欲表現。今天,一個像我這樣活力旺盛的小孩,可能會得到一個臨床病理診斷,但這種事不會發生在我成長時期的松林預校。例如,當我把臉塗成像世界摔角聯盟(WWF)的職業摔角手終極戰士( Ultimate Warrior)一樣,然後在籃球比賽裡表現得很瘋狂,他們會說:「喬恩(Jon,朱浩偉的英文名字)就是這樣,才像喬恩。」
我媽不僅容忍這些搞怪,還備加鼓勵。
「喔,天哪,你好有趣喔!」在欣賞完愚蠢的歌曲或舞蹈後,她會這樣講。例如我試
著做出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在《外星戰將》(Moonwalker)錄影帶上看到的月球漫步動作時(我反覆看,看到帶子磨壞掉)。「你太有才華了!」
我讓她吹捧讚美我。為什麼不?
因此,六年級,當松林預校決定打造一個鬼屋來嚇唬並娛樂學生時,包括家長在內的每個人都不知道它該如何運作,我卻立即提出偉大創意。我做了平面圖、計畫書、設計畫稿,讓我驚喜的是,孩子和大人們都對我把創意變成現實感到興奮。
當一位朋友告訴我,聖荷西市立輕歌劇院正為下一部作品徵選一位十一歲演員時,我覺得自己有機會得到角色,特別是我發現這部作品要找亞裔演員。即便在那麼小的年紀,我也知道符合條件的人並不多。
在我的學校裡,籃球隊員就像神一樣,他們高大挺拔,充滿自信和勇氣。我哥賴瑞不是隊上最高的球員──他自稱身高六呎二(約一百八十八公分),比較科學的說法是六呎一(約一百八十五公分)但他絕對是球隊的領袖人物。我五年級時,正值賴瑞和隊友稱霸聯盟。有些朋友向我承認,他們和我混在一起,只是為了能跟賴瑞玩 (這些朋友現在還是這樣講)。
我不怪他們。賴瑞不僅是明星運動員,他還有第二個特點,此一特點對他弟弟後來的人生和職涯影響深遠:他是「電影明星」。
在大賽之前,全校都會湧進體育館觀賞球隊的精采集錦影片:關鍵投籃,防守爭搶,超強球技,再配上炫目標題和超炸配樂。今天,任何擁有智慧型手機的人都可以製作出更精緻的影片。但在一九九○年,學校周遭只有少數人擁有創造這些奇觀所需的工具和技能,就連籃球隊員都對這些人敬畏有加,給予他們電影製作最高讚譽:下一個史蒂芬.史匹柏。
歸功於籃球活動的人氣,拍攝電影的熱潮席捲了松林預校(Pinewood School)的校園,有些老師甚至允許我們以「製作影片」代替「撰寫讀書報告」。賴瑞非常熱中「影片代替作業」的形式,像他這種善於交際的人,拍影片遠比寫論文來得有趣。但相較於寫論文,拍電影有個缺點,你必須扛著沉重的攝影機。在錄影帶年代,光是電池的尺寸和重量就相當於一塊磚頭。但賴瑞找到了解決方案:他老弟。
有一天,他正製作英語課影片作業,內容應該是《坎特伯里故事集》,這可以解釋為何我記憶中賴瑞和他的朋友會打扮成中世紀鄉紳在洛沙托斯閒晃。一如往常,我拿著攝影機跟在後面,經過閒晃、隨興拍攝的一整天後,賴瑞宣布停機。他和搭檔回到「基地營」,也就是我家客廳。接下來,事情才開始變得有趣。
賴瑞霸占了電視和錄放影機,從爸媽房間搬來另一台錄放影機。他的一個朋友──少數清楚影片來源的聰明人──在咖啡桌上放一台我後來才知道叫「混音器」的機器。混音器裝好後,又把其他器材散布在地板上,黃紅白三色線材被連結拼湊成蜘蛛網一般。
這時我才明白,這些設備是用來「剪輯」。當時我不知道這個專有名詞是什麼意思,但我不想因為發問而引人注意,尤其是在金童酷大哥允許我和他一起混的時候。
終於我發現「剪輯」是指把我們錄下來的影像和聲音切割開來,再重新拼接回去。聽起來很簡單,但事實上就算是最基本的修改也複雜得難以置信,一定要依照正確順序按下正確按鈕:暫停、錄製、快轉、錄製、倒退、錄製。慢慢地,一段一段剪,一段一段接,影片才慢慢變好,獲得節奏與張力,帶出一些充滿情感的片刻。一兩個小時後,整天胡鬧的屁孩們開始像稱職的表演者,像是真正在乎自己所做的事。
然而賴瑞還不滿意。他有一個願景,他想藉由加入英國喜劇電影《聖杯傳奇》的片段來增強影片效果:上帝撥開雲層與下方的人對話,但音源換成賴瑞的聲音。在那笨拙的老類比時代,這種混合音訊與影像效果的進行方式,會讓剪接過程複雜到嚇人。這意味著要同時按下一堆按鈕,旋轉一堆轉盤,並調整一堆推桿。賴瑞想達到夠大的效果,就需要每個人幫忙,甚至包括我。
我坐在音響前方的指定位置,指尖懸停在播放按鈕上。
三……二……一 ……錄!
手指按下,轉盤旋轉,磁帶開始滾動。
沒成功。我們的時間點必須抓得更完美,但它總是不完美,我們必須再試一次,然後又再試一次。每次失敗,都會增加壓力。當你用錄影帶或任何類比技術作業時,每次重錄都會讓畫面品質下降。
最後,我們以為已經搞定。但是回放重播時,全都笑到東倒西歪。這超可笑的,有夠天才啦!
三十五年後,我仍記得那一刻感受到的驚嘆──在我腦海中閃過改變一生的頓悟。
喔!我想,電影就是這樣拍出來的。
────
松林預校雖然允許我們以拍影片代替寫作業,但這不代表學校採取無拘無束、隨心所欲的教育方針。儘管校方宣稱該校並無教派,但它是由摩門教家庭所創辦,並受到摩門教價值觀影響。先不說在校園裡喝酒、抽菸或吸毒,我們甚至不能攝取咖啡因。有些孩子可能會對這些規定感到窒悶,但我感覺受到保護。
所有人在松林預校都被妥善照顧,但我比多數人受到更多庇護。我和賴瑞相差六歲,在這六年間,父母又多添了三個孩子:克莉絲汀娜、霍華和珍妮佛。到我夠大到能穿上松林制服時,兄姊已為我在學校鋪好路。老師們在見到我之前,就已先知道我了。
接送朱家小孩上下學和參加課外活動,對我父母來說是持續性的挑戰。無奈我父親工作時間長得令人難以置信,例如,在餐廳他總是「最先到」和「最後走」,總是錯過家庭假期(他常說,中餐館的管理就是「微觀管理」,要事必躬親),因此,管理我們這團騷亂的責任就落在我媽身上。我知道她要面對的挑戰,所以當她偶爾忘記在放學時來接我,我不會當成是針對我個人。為了掩飾尷尬,我會讓老師以為我正朝我媽的廂型車走去,然後躲進灌木叢裡,等所有人都離開後,再走到幾個街區外的阿姨家。
不過,童年時的許多星期天,我們並沒有分頭行動,而是集體移動。我媽會開車載五個孩子到舊金山,我們購買所有演出的季票:歌劇、芭蕾舞、交響樂。因為我們年年都去,所以總能拿到很棒的位子。中場休息時,我會晃到樂池裡檢查樂器。久而久之,連舊金山芭蕾管弦樂團的指揮丹尼斯.德.科托都認識我了。
「總有一天你會成為我們的首席小提琴手,對吧?」
「其實,我比較想要你的工作。」
他大笑之後,把指揮棒遞給我,還要我保管好。我超愛那根指揮棒,並且確實一直保管著,直到被我的狗咬爛。
我媽誠心渴望我們能認識貝多芬和布拉姆斯。但當我回想那些外出時光,總覺得它們像是一種「說故事」的行動。那是她為我們家庭「編織敘事」的機會,而觀眾是恰巧在場的旁人。
我媽殷切期盼我們家就是典型的「美國夢家庭」。我們和其他人一樣聰明,一樣有教養,我們做得到,我們夠資格。我們不會在週日下午無精打采地穿過飯店大廳,她會確保我們穿著稱頭的西裝,看起來帥氣。
這個「故事」不只是由我們講述,也不只是關於我們,而是為了我們而存在的,我媽希望我們能在陌生環境的規範和儀式中感到自在。她以自身為榜樣,教我們如何自信應對任何狀況(我母親平時親切又笑容滿面,除非你惹到她。我們家幾乎都是天蠍座,這就說得通了)。她希望我們感到自己屬於這裡,屬於任何地方。
一切都照計畫進行。大概啦!
你可能以為朱家孩子參加音樂會的那些年,會讓他們稍微像全神貫注的小樂迷,但不幸坐在我們旁邊的觀眾會告訴你事實並非如此。我媽可以堅持讓我們去看表演,但面對五個盛裝打扮的小孩,父母所能施加的控制都很有限。有時我們會專注欣賞,但多數時間都很失控。
我們難免會惹來鄰座的白眼,也聽過不少難聽的耳語。你大概可以想像,這會帶來一些麻煩──甚至可能是一場危機,這和我們原本應該向所有人展示的家庭形象與優雅教養背道而馳。母親完全清楚這些騷亂,她該如何讓她的「故事」保持完美無瑕呢?
她的解方充滿啟示性,真的足智多謀。她無視那些責難、噓聲、輕蔑、怒目,任由它們從身邊掠過。當我和兄姊們看到那些狀況對她無關緊要時,我們也決定不去在意。她從未告訴我們她在做什麼,她構築出一個氣泡般的屏障,一道能量場,我們可以在裡面培養自我意識,與外界射來的箭矢隔絕。
有時,那些被冒犯的鄰座或許有點道理。也許我們本可以少開幾個關於穿緊身褲男士走光的玩笑。但多年來,我們常在自己並無過錯卻仍遭受到傷害性言行時,想起母親的教誨。這等同於一種家訓,從未宣示卻始終恪遵:當別人惡待你時,絕對不要抱怨。
絕對不要抱怨。
────
在我們非凡家庭的「故事」中,每個人都應該是與眾不同的個體。也正因如此,從小開始,媽媽就給我們機會培養各種天賦、才華、技能與興趣。
我們上過各式各樣的課程:學習如何演奏小步舞曲,如何在上網時打出吊球,如何切球上果嶺。甚至上禮儀課,由一位正經八百的英國女士教導如何正確喝完一碗湯(完全不是粗魯的美式喝法)。這像是社交十項全能訓練計畫,媽媽精心準備,為的是讓我們能昂首闊步走進任何場合,贏得別人的尊重。
最後,我們各自找到不同的定位。例如,克莉絲汀娜發現並培養了非凡的芭蕾舞天賦,在我看來,她盡可以在那條路上大展身手。舞蹈從來不是我的強項,即使上了十二年踢踏舞課之後也不是(對小孩幫助不大,但對後來拍音樂劇電影的導演來說,真是大有用處)。珍妮佛在籃球和舞蹈方面都表現出色,我則是被貼上「創意者」的標籤。在混亂的家庭中,我用想像力為自己創造一個安全的世界,尤其是手裡拿著色鉛筆時。
我愛畫畫,我一直在畫畫。我會虛構出異世界的生物,然後將它們勾勒在紙上。我不是班上繪畫最好的人,但我從中得到的快樂無人能及。更廣義來說,「創意者」只是「怪咖」的委婉說法。在學校裡有兄姊保護,我可以隨心所欲表現。今天,一個像我這樣活力旺盛的小孩,可能會得到一個臨床病理診斷,但這種事不會發生在我成長時期的松林預校。例如,當我把臉塗成像世界摔角聯盟(WWF)的職業摔角手終極戰士( Ultimate Warrior)一樣,然後在籃球比賽裡表現得很瘋狂,他們會說:「喬恩(Jon,朱浩偉的英文名字)就是這樣,才像喬恩。」
我媽不僅容忍這些搞怪,還備加鼓勵。
「喔,天哪,你好有趣喔!」在欣賞完愚蠢的歌曲或舞蹈後,她會這樣講。例如我試
著做出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在《外星戰將》(Moonwalker)錄影帶上看到的月球漫步動作時(我反覆看,看到帶子磨壞掉)。「你太有才華了!」
我讓她吹捧讚美我。為什麼不?
因此,六年級,當松林預校決定打造一個鬼屋來嚇唬並娛樂學生時,包括家長在內的每個人都不知道它該如何運作,我卻立即提出偉大創意。我做了平面圖、計畫書、設計畫稿,讓我驚喜的是,孩子和大人們都對我把創意變成現實感到興奮。
當一位朋友告訴我,聖荷西市立輕歌劇院正為下一部作品徵選一位十一歲演員時,我覺得自己有機會得到角色,特別是我發現這部作品要找亞裔演員。即便在那麼小的年紀,我也知道符合條件的人並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