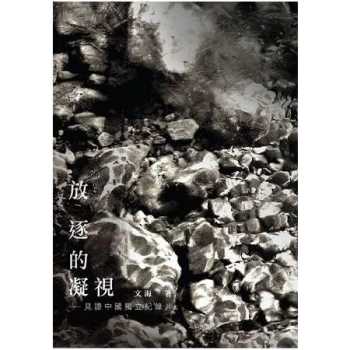導讀
當我們談論獨立電影時我們談論什麼曾金燕
獨立就是不接受審查,也不接受具有官方性質的資金援助。總而言之,就是對官方採取一種強硬的決絕態度。──張獻民教授(北京電影學院)
拒絕來自任何方面的電影審查……拒絕因為發行或其他商業目的而對影片進行刪改。──黃牛田電影宣言(2007年)
我可能會死吧。以前是被錢困擾,現在為身體所累。無論如何,我絕對不會去做那些低俗下作的東西。我們就是為了反對那些東西才成為獨立導演,如今卻要加入那個行列,我辦不到。──王兵(獨立導演)
緣起
2010年9月16日,導演文海從威尼斯影展一回中國就被國保帶走,四個硬碟被查扣至今。事件導火線是兩年前文海製作的《我們》這部刻畫當代老、中、青三代獨立知識分子精神面貌的作品,和他匿名拍攝的《劉曉波被捕前的最後訪談》。釋放後,他搬離北京,一度隱遁於寺廟,最後移居香港。2013年,在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劃為期一年的資助下,他採訪了中國當代幾位重要的獨立紀錄片導演,並完成《放逐的凝視》一書。此書刻畫了一群遊離於政治體制和資本市場之外的中國獨立紀錄片電影人。文海一方面試圖通過對受訪者的呈現,確立一套新的價值體系來評價當代中國獨立電影創作,另一方面也試圖尋找精神資源解答他內心的困惑:為何我們這些不過是用不成熟的電影藝術表達想法的人,最後卻都成了國家的敵人?
2010年前後,以地下狀態發展十餘年的獨立電影節,已經在北京、南京、雲南等地連接起一個鬆散的網絡。新、老、本土及海外獨立電影創作者、研究者和觀眾,不定期聚在一起觀看年度新作,討論中不乏爭吵、分歧。作品通過中國廣電總局審查的導演們,自然是正統體制的寵兒,獲得官方認可以及市場空間。而地下創作者和評論者,也在體制外逐漸形成了一個自如的「亞體制」,規模雖遠不能與官方體制相比,但自有它的製片、導演、評論和觀眾體系。然而,為了確保電影節得以開幕,獨立電影節的籌辦者們,陸陸續續接受了當局對播放片單不同程度的干預、審查和限制。它們的生存空間近年突然急劇萎縮,政治打壓由針對單個具體片目,擴展到不加區分、對獨立電影節的群體打壓,使得獨立電影創作、討論和播放處境,甚至不如2000年以前。2011年以後,多個核心獨立電影網站一度被關閉,執行任務的警察對獨立電影節採取更強硬並直接終止的行動,包含斷電、衝入現場檢查觀眾身分證、驅散人群、毆打、限制人身自由等。2014年,警方甚至將栗憲庭電影基金資料庫裡的一千五百五十二部館藏影片直接拉走,至今未歸還。
幾乎與此同時,「獨立電影」在中國、香港、臺灣,瞬間變成一個流行名詞,它似乎意味著:道德上的優越──大量呈現底層和邊緣人的生活;藝術上的超越──不進入廣電總局審查系統的創作;政治正確上的飛躍──對抗商業和政治強權。於是,國家資金開始大量挹注中央電視臺紀錄片頻道,專門拍攝、剪輯紀錄片的商業公司也隨之興起。臺灣CNEX則以強勁之勢,在兩岸三地吸收資金、整合文化、投資紀錄片創作、組織放映、討論和發行,在主流化「獨立」紀錄片之時,很難說沒有致使具強烈社會批判性的獨立紀錄片製作更加邊緣化。不少中國導演以通過獨立電影創作獲得專業認可,然後進入體制或亞體制籌資創作,選題上,他們迴避政治敏感可能遭致嚴重懲罰的議題──輕微懲罰是一種可承受後果並可帶來榮耀的象徵資本;作品處理上,先行自我過濾政治敏感點,以力求發行時能「抵達」最廣泛的觀眾,以及為燒錢的下一部創作尋找資金、資源。
徹底不和審查系統玩的導演,則免除了等待審查機構隨意決定作品命運時的提心吊膽,他們一般有兩種選擇方向──要麼在資金、放映和發行上放棄中國乃至大中華地區;要麼將影片完全開放到網路上。表面上,導演們在中國各取所需,各有活法,相互串演角色,倒也能相安無事。自我審查也可以被視作是一種對抗壓制言論自由的積極策略,使完全不可能流通的作品,獲得一定程度的能見度。但自我審查對創作力的扼殺,並不那麼容易被創作者察覺。遊走於各種體制、亞體制和各種圈子者,不乏自認為玩弄審查,最後卻被審查玩弄,進入自我過濾模式創作,將思想和藝術表現局限於隱形的禁錮圈中而不自知。例如,把張藝謀近年的影片《歸來》,和他早期的《活著》加以比照,失色又失魂。賈樟柯試圖衝撞審查機制的劇情片《天注定》,取材於當代中國的社會事件,技術和內容深度上,足以冷眼傲視電影院裡所播放的中國當代各色作品。不過,即使是出色的劇情片,一旦放在覆蓋著饑荒、上訪、文革等題材的獨立紀錄片語境中加以對照,問題便直接指向:這些具有能見度的創作者群體,他們的作品迴避了當下中國哪些關鍵議題,他們的作品,又是如何依舊單薄,難以接近那咫尺天涯的社會真實。
以知識階層之名
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曾經對十九世紀在沙皇暗黑統治下的俄國如此評價:它對於世界的重大貢獻,是使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誕生。知識階層與知識分子(intellectual)不同,受過高等教育並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者,並非就是知識階層。知識分子掌握信息並且對社會現實有較好的理解,但未必願意身體力行。而哪怕只是識得一文半字,卻深刻理解社會運作的底層人士,採取推動社會福祉並形成公共影響的行動者,就算是知識階層的一分子,因為他們堅決反對舊體制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為躲避審查和避免直言帶來的殘酷後果,如流放、死刑,知識階層將社會政治批評轉向文學形式,而催生了十九世紀輝煌的俄羅斯文學,以及獨具特色的「別林斯基」式的文學批評──模糊小說人物與現實的區別,批評小說中的人與事,如同批評現實一般。
在學術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職業知識分子、技術知識分子、世界公民層面的知識分子、從政的知識分子等範疇裡,已經有不少厚學之士,探討過當代知識分子的職責、現狀和局限。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政府將子彈射向學生與平民,使得知識分子與公眾從改革開放的寬鬆氣氛裡,突然回到專制統治的強烈恐懼中,這種無處不在的恐懼,成為思維工作者求真的首要障礙。六四鎮壓留給知識分子的「遺產」,是結束學院知識分子西化的、激進的社會啟蒙進程。在這裡,激進是一個相對意義上的名詞。在日常實踐中,它暗含著在無處不在的審查高壓下為了存活的算計。在高等教育和高科技運用普及的今天,知識分子一詞在中國產生歧義的關鍵在於,現代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具有通過公開批評進行公共參與的含義,而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只能在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範圍內說話,批判空間受到限制,政府與知識分子處於相互疑忌的狀態。
當我們談論獨立電影時我們談論什麼曾金燕
獨立就是不接受審查,也不接受具有官方性質的資金援助。總而言之,就是對官方採取一種強硬的決絕態度。──張獻民教授(北京電影學院)
拒絕來自任何方面的電影審查……拒絕因為發行或其他商業目的而對影片進行刪改。──黃牛田電影宣言(2007年)
我可能會死吧。以前是被錢困擾,現在為身體所累。無論如何,我絕對不會去做那些低俗下作的東西。我們就是為了反對那些東西才成為獨立導演,如今卻要加入那個行列,我辦不到。──王兵(獨立導演)
緣起
2010年9月16日,導演文海從威尼斯影展一回中國就被國保帶走,四個硬碟被查扣至今。事件導火線是兩年前文海製作的《我們》這部刻畫當代老、中、青三代獨立知識分子精神面貌的作品,和他匿名拍攝的《劉曉波被捕前的最後訪談》。釋放後,他搬離北京,一度隱遁於寺廟,最後移居香港。2013年,在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劃為期一年的資助下,他採訪了中國當代幾位重要的獨立紀錄片導演,並完成《放逐的凝視》一書。此書刻畫了一群遊離於政治體制和資本市場之外的中國獨立紀錄片電影人。文海一方面試圖通過對受訪者的呈現,確立一套新的價值體系來評價當代中國獨立電影創作,另一方面也試圖尋找精神資源解答他內心的困惑:為何我們這些不過是用不成熟的電影藝術表達想法的人,最後卻都成了國家的敵人?
2010年前後,以地下狀態發展十餘年的獨立電影節,已經在北京、南京、雲南等地連接起一個鬆散的網絡。新、老、本土及海外獨立電影創作者、研究者和觀眾,不定期聚在一起觀看年度新作,討論中不乏爭吵、分歧。作品通過中國廣電總局審查的導演們,自然是正統體制的寵兒,獲得官方認可以及市場空間。而地下創作者和評論者,也在體制外逐漸形成了一個自如的「亞體制」,規模雖遠不能與官方體制相比,但自有它的製片、導演、評論和觀眾體系。然而,為了確保電影節得以開幕,獨立電影節的籌辦者們,陸陸續續接受了當局對播放片單不同程度的干預、審查和限制。它們的生存空間近年突然急劇萎縮,政治打壓由針對單個具體片目,擴展到不加區分、對獨立電影節的群體打壓,使得獨立電影創作、討論和播放處境,甚至不如2000年以前。2011年以後,多個核心獨立電影網站一度被關閉,執行任務的警察對獨立電影節採取更強硬並直接終止的行動,包含斷電、衝入現場檢查觀眾身分證、驅散人群、毆打、限制人身自由等。2014年,警方甚至將栗憲庭電影基金資料庫裡的一千五百五十二部館藏影片直接拉走,至今未歸還。
幾乎與此同時,「獨立電影」在中國、香港、臺灣,瞬間變成一個流行名詞,它似乎意味著:道德上的優越──大量呈現底層和邊緣人的生活;藝術上的超越──不進入廣電總局審查系統的創作;政治正確上的飛躍──對抗商業和政治強權。於是,國家資金開始大量挹注中央電視臺紀錄片頻道,專門拍攝、剪輯紀錄片的商業公司也隨之興起。臺灣CNEX則以強勁之勢,在兩岸三地吸收資金、整合文化、投資紀錄片創作、組織放映、討論和發行,在主流化「獨立」紀錄片之時,很難說沒有致使具強烈社會批判性的獨立紀錄片製作更加邊緣化。不少中國導演以通過獨立電影創作獲得專業認可,然後進入體制或亞體制籌資創作,選題上,他們迴避政治敏感可能遭致嚴重懲罰的議題──輕微懲罰是一種可承受後果並可帶來榮耀的象徵資本;作品處理上,先行自我過濾政治敏感點,以力求發行時能「抵達」最廣泛的觀眾,以及為燒錢的下一部創作尋找資金、資源。
徹底不和審查系統玩的導演,則免除了等待審查機構隨意決定作品命運時的提心吊膽,他們一般有兩種選擇方向──要麼在資金、放映和發行上放棄中國乃至大中華地區;要麼將影片完全開放到網路上。表面上,導演們在中國各取所需,各有活法,相互串演角色,倒也能相安無事。自我審查也可以被視作是一種對抗壓制言論自由的積極策略,使完全不可能流通的作品,獲得一定程度的能見度。但自我審查對創作力的扼殺,並不那麼容易被創作者察覺。遊走於各種體制、亞體制和各種圈子者,不乏自認為玩弄審查,最後卻被審查玩弄,進入自我過濾模式創作,將思想和藝術表現局限於隱形的禁錮圈中而不自知。例如,把張藝謀近年的影片《歸來》,和他早期的《活著》加以比照,失色又失魂。賈樟柯試圖衝撞審查機制的劇情片《天注定》,取材於當代中國的社會事件,技術和內容深度上,足以冷眼傲視電影院裡所播放的中國當代各色作品。不過,即使是出色的劇情片,一旦放在覆蓋著饑荒、上訪、文革等題材的獨立紀錄片語境中加以對照,問題便直接指向:這些具有能見度的創作者群體,他們的作品迴避了當下中國哪些關鍵議題,他們的作品,又是如何依舊單薄,難以接近那咫尺天涯的社會真實。
以知識階層之名
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曾經對十九世紀在沙皇暗黑統治下的俄國如此評價:它對於世界的重大貢獻,是使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誕生。知識階層與知識分子(intellectual)不同,受過高等教育並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者,並非就是知識階層。知識分子掌握信息並且對社會現實有較好的理解,但未必願意身體力行。而哪怕只是識得一文半字,卻深刻理解社會運作的底層人士,採取推動社會福祉並形成公共影響的行動者,就算是知識階層的一分子,因為他們堅決反對舊體制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為躲避審查和避免直言帶來的殘酷後果,如流放、死刑,知識階層將社會政治批評轉向文學形式,而催生了十九世紀輝煌的俄羅斯文學,以及獨具特色的「別林斯基」式的文學批評──模糊小說人物與現實的區別,批評小說中的人與事,如同批評現實一般。
在學術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職業知識分子、技術知識分子、世界公民層面的知識分子、從政的知識分子等範疇裡,已經有不少厚學之士,探討過當代知識分子的職責、現狀和局限。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政府將子彈射向學生與平民,使得知識分子與公眾從改革開放的寬鬆氣氛裡,突然回到專制統治的強烈恐懼中,這種無處不在的恐懼,成為思維工作者求真的首要障礙。六四鎮壓留給知識分子的「遺產」,是結束學院知識分子西化的、激進的社會啟蒙進程。在這裡,激進是一個相對意義上的名詞。在日常實踐中,它暗含著在無處不在的審查高壓下為了存活的算計。在高等教育和高科技運用普及的今天,知識分子一詞在中國產生歧義的關鍵在於,現代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具有通過公開批評進行公共參與的含義,而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只能在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範圍內說話,批判空間受到限制,政府與知識分子處於相互疑忌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