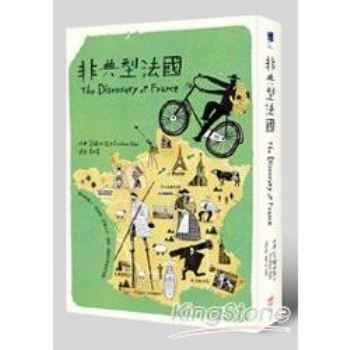第十四章 法國的奇觀
高地居民正發掘平原和山谷時,有種新的遷徙族已在往山區前進。第一批就出現在十八世紀中葉。到了紹丹村成為鬼城時,他們已散播到法國其他地方。那時在法國,他們被叫做「touriste」(觀光客)。這字眼來自英語,用以指稱從事「壯遊」(Grand Tour)的旅人,其中大部分人前往佛羅倫斯、威尼斯、羅馬、那不勒斯。
早期的觀光客幾乎全是英國人,且主要出現於阿爾卑斯山、庇里牛斯山,以及從巴黎往南到里昂、義大利那三條路線上的過夜休息點。觀光客為了享樂、陶冶心靈或健康而旅行,顯然無視於常識和體力極限。與探險家不同的,他們不想只是發現。他們並未只是觀察和記錄,反倒是改造他們所好奇的東西,使其改頭換面。他們重建過去,按照他們所偏愛的色彩打扮當地人,最後建構了他們自己的城鎮和景觀。
這類新式旅人幾乎是一出現就開始繁殖、分化,個體愈來愈弱,而群體愈來愈強。但一八五八年哲學家暨史學家泰訥,為這類觀光客的原型下定義時,這類原型觀光客仍相當普遍:
腿長,體瘦,頭前俯,腳板寬大,雙手有力,特別適於抓握。帶著手杖、雨傘、斗篷、橡膠外套……以令人欣賞的方式行走大地……在歐博訥(Eaux-Bonnes),他們有人掉了旅行日誌,被我撿到。日誌標題是「我的感想」:
八月三號。穿越冰川。右鞋裂開。抵達馬拉戴塔(Maladetta)山頂。見到先前觀光客留下的三只瓶子……回程時,嚮導盛宴款待。晚上,有人在我門口吹奏風笛,獻上綁了絲帶的大花束。全部花費一百六十八法朗。
八月十五號。離開庇里牛斯山。一個月內以徒步、騎馬、搭馬車的方式走了三百九十一里格;十一次登高,十八趟短途旅行。用掉兩根手杖,一件外套,三條長褲,五雙鞋子。充實的一年。
附註:絕美的國家,叫人感動不已。
這種仿英雄體寫成的法國觀光記述,在那一百年前的一七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就已問世,就在薩瓦的邊界上。那天下午,夏莫尼村的小隱修院院長和村民,聽到槍聲和啪啪的馬鞭聲迴蕩於山間,大為驚訝。幾小時後,他們注意到古怪的一行人,不知所為何來,循著阿爾沃(Arve)河谷跌跌撞撞吃力往上爬。八名英格蘭紳士和五名配備重武器的僕人,正騎著非常疲累的馬在與急流搏鬥,其中有些人已掉了鞋子。
這支探險隊的領隊,綽號「拳擊」的溫德姆(William ‘Boxing’ Windham)原住在日內瓦,對遙遠的白色高山上據說有叫冰川的廣大冰原深深著迷。他找不怕死的人跟他一起去探索那座所謂的受咀咒山(Montagnes Maudites),可想而知未能如願。但就在這時,探險家波卡克(Richard Pococke)在從埃及、黎凡特返國途中,來到日內瓦。六月十九日,他們和其他六個在日內瓦無所事事的紳士啟程。三天後他們抵達蒙唐韋(Montenvers)冰川腳下的夏莫尼。(待續)在這之前,來夏莫尼的外地人,就只有膽子大的收稅員、巡迴主教、薩瓦公爵的地圖繪製員,但夏莫尼村民倒是常出遠門。他們到日內瓦賣岩羚羊皮、水晶、蜂蜜;他們的牧羊人靠著製作乳酪的本事,在這整個地區炙手可熱。許多村民從事巡迴推銷工作,會經由第戎和朗格勒(Langres)去巴黎,並聲稱曾在巴黎遠遠見到他們家鄉的山。當時,隨時都有約三分之一夏莫尼村民住在巴黎。
村民主動表示願讓這一行英格蘭人住進家裡,但他們拒絕,選擇在村外紮營。他們派人看守,火整夜沒熄。幾十年後,夏莫尼的老人家仍拿這些英格蘭紳士一心提防走失綿羊和好奇孩童的故事以饗外來客。夏莫尼人善於模仿他人,無疑誇大了溫德姆一行人的防備心態。但溫德姆本人也誇大了夏莫尼村民的無知。他不辭艱險來到荒山野嶺,想看到的東西裡,就包括「原始」人。隔天早上,他問當地人冰川的事,聽到有女巫在冰上守安息日的「荒謬」傳說,滿意但不驚訝。
募得嚮導和挑夫,記下他所認為村民對他這支勇敢隊伍的欽佩之情後,溫德姆一行人爬過雪崩肆虐過的「悲慘災區」,微顫顫走過懸崖邊緣,循著路痕鮮明的獵徑抵達蒙唐韋山頂(六十年後,遜位皇后約瑟芬帶著六十八名嚮導和女侍,也走過這條路線)。在山頂,他們見到「無法形容的景致」:「叫人不得不想像那是(日內瓦)湖水被暴風翻攪騰空,然後一下子結成冰所形成。」後來,有人將這一類似格陵蘭的景致,取名(或許幾乎可以說是冠上圖說)「冰海」(Mer de Glace)。
溫德姆對觀光業發展的重大貢獻,不是他發現了冰川,而在引進了浪漫主義的感性。他為這趟遠征所寫的遊記,在日內瓦的沙龍裡大為流傳。一七四四年,該遊記於全歐各地刊物刊出,蔚為轟動。山突然間成為時髦新寵。對當時大部分人來說,冰崖就差不多和骯髒村落或破敗哥德式教堂一樣迷人。狄索爾(Jean Dusaulx)於一七八八年來到庇里牛斯山時,有位女士問他,「你對這些可怕東西有何看法?」她指的是後來被叫做美景的東西。山只是碰巧陡直的荒地。在今人眼中,旺圖山稱雄、統合周遭群山,但在十八世紀末期之前,提到該山的普羅旺斯遊記少之又少,更別提詳細介紹該山。當時瞭解山者不多。一七九二年,有位逃離「恐怖統治」的神父,發現成群的巨大岩體要花上半天時間才能勉強爬完,大為驚愕:「我一直以為山是龐大但孤立的凸出物。」
對於那些想過這問題的人來說,山和住在山上的人,乃是原始世界的殘餘。地球一如人類,正緩緩步向完美狀態,屆時,「地勢將平緩到不可能出現山崩,而草木將安穩立在山的遺骸上」(拉蒙〔Louis Ramond〕,《庇里牛斯山觀察》〔Observations faites dans le Pyrenees,1789〕)。英國作家沃爾浦爾(Horace Walpole)在花了四天穿越阿爾卑斯山,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小寵物狗大白天被狼抓走後,寫道,「真荒涼的岩石,真難看的居民!」「希望這輩子不要再見到。」
溫德姆探險之行後,觀光客紛紛入侵薩瓦的阿爾卑斯山。蘇格蘭醫生摩爾(John Moore)在一七七九年抱怨道,「只要提到什麼新奇或特別的東西,幾乎都會引來別人告訴你……這位先生,那的確不錯;但相信我,根本和薩瓦的冰川不能比。」該世紀結束時,「冰海」騎馬可到,觀光客可在名叫「自然之殿」的山中避難小屋過夜。若非拿破崙拒絕夏莫尼人的要求,甚至會有條道地的公路通達「冰海」。拿破崙說道:「這些人不知道怎樣才是對他們有利。如果人可以搭馬車上『冰海』,那些名媛貴婦還有什麼驚險故事可拿來說?」詩人雪萊走訪那個「只住有暴風雨的荒涼地方」(〈寫於夏莫尼山谷詩〉〔Lines written in the Vale of Chamouni,1816〕)時,那個「荒涼地方」的旅館已足夠容納當地人口數倍的遊客。形形色色的商人、教師、畫家、植物學家、無所事事的領主、人稱「adventuress」(用不正當手段謀取名利或地位的女人)的有趣女人,在靜得叫人難以忍受的氣氛中,一起圍著餐桌而坐。當時有半數以上觀光客來自英格蘭,因此英格蘭作風大行其道。其中有些人來看「冰海」,有些人來攻頂不久前已被認定為歐洲最高峰的白朗峰。一七八六年,一名當地牧羊人和一名醫生首度登頂白朗峰。一個世紀後,阿爾卑斯山、庇里牛斯山的主要山頭,幾乎全都給征服過幾次。拜圓滑的嚮導之賜,許多人離去時,都自得地以為自己是第一個登頂所爬山峰的人。(待續)溫德姆從事那趟探險之行時,在法國較平坦的地區,觀光客幾乎不存在。當時,能讓旅人擬出法國觀光行程的資訊太少,而鼓勵人待在家裡的東西則太多。自十二世紀的聖地牙哥.德.坎波斯泰拉朝聖指南問世以迄這時,指南書籍幾乎是一成不變。這本出自克呂尼(Cluny)修道院僧侶之手的朝聖指南,描述了主要路線和聖地、食宿、每段驛站之間可能花費的時間、朝聖者大概會受到的接待。貫穿全書的主張,乃是離文明開化的北部愈遠,情況就愈糟。越過加龍河,語言就是鴨子聽雷的「土話」;朗德(徒步三天行程)是個有巨蠅和流沙的地區,吃不到肉、魚、麵包,喝不到葡萄酒和水;加斯科涅居民嗜酒、好色、多話、愛挖苦人、好客,最後一點無疑未必是十足的好事。
七百年後,指南書仍循著類似的思路撰寫。此類書的作者認定其讀者是巴黎人,或至少是已在巴黎展開旅程的人,因為據一七四○年《法蘭西新旅行》(Le Nouveau voyage de France)一書,「要打造個人品味,要充分瞭解普羅旺斯的習俗和政府,首先應研究首都和宮廷。」基於顯而易見的理由,大部分書把內容局限在驛道沿途可見到的東西。奧熱(Jean Ogee)於一七六九年所寫的布列塔尼指南,就取了很典型的副書名:「包含此路左右兩側半里格(一.六公里多一點)內出現的所有特別事物。」景物本身不被視為旅行的目的。為紓解漫長旅程的無聊,指南書會提供詳細歷史知識,供旅人排解煩悶,煩擾同車乘客之用。布里瓦爾(John Breval)一七三八年針對「歐洲幾個地區」所寫的指南,鎖定能從「最荒涼平原或最杳無人煙之村落」(即使只知它們的年代和名字)得到樂趣的「那群讀者」。
由於當時地理資訊缺乏,大部分作者借用先前著作的內容,而這些先前著作又是抄襲自更早的著作。因此,作者寫起明明早已不存在的古蹟,仍寫得像是親眼見過一般。許多作者顯然認為不會有人照著他們書中的指示去遊歷,於是鉅細靡遺描述了一些憑空杜撰的地方城鎮。馬爾蘭旅行時,帶著德.埃瑟恩(Robert de Hesseln)的小巧《法國萬有辭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la France,1771),乃是因為「將介紹整個國家的六冊書,放在馬車的口袋裡隨行,很有用」。遺憾的,提供資訊給埃瑟恩的在地人,有時叫他失望,一如馬爾蘭一七九○年抵達洛澤爾省首府時所發現的。「埃瑟恩先生很用心把芒德(Mende)擺在山上,說它呈三角形,住了許多人。這句話只錯了三個地方。」
甚至在十九世紀結束時,仍有許多指南書描寫旺圖山頭「永不融化的雪」(那「雪」其實是白岩石)。其中有一本出版於一八八八年,還提到熱比耶德容克山頂「荒涼的沼澤中,長了數叢濃密的藨草」,但其實該山山頂十足乾燥(此山名來自意指「岩石」和「山」的兩個字,但在現代法語裡,此名意指一束燈心草)。這些作者大部分除了搭火車,從未去到巴黎外大街以外的地方。(待續)法國境內為新式開明觀光客出版的第一本旅行指南,乃是當時史上最充滿感情、最煞費苦心、卻也最不實用的指南之一。拉瓦列(Joseph Lavallee)的《法國諸省遊歷》(Voyages dans les departements de la France),一七九二年開始以分期出版的分冊形式問世。這時,拉瓦列投入革命陣營不久,狂熱支持革命理念,想讓那些目中無人的巴黎人知道,巴黎以外的各省其實和他們高高在上的首都一樣有趣。他和志同道合者啟程走遍全國,循一條毫無中斷的路線,穿過所有省分,且每個省都只通過一次。
除了那條古怪但理論上合理的路線,這本書還有幾個地方不同於一般指南。首先,拉瓦列和其工作團隊似乎真的親自走完這趟旅程(描繪瓦朗謝訥的那張圖,從遠距離呈現該鎮,因為繪者擔心遭被視作間諜射殺。談羅亞爾河下游省那一章,略去該省大部分地區,因為道路不通,且船因風阻而無法在基伯龍上岸)。其次,這本書打算賣到全國各地,賣到每個設有驛站長的鎮。最後,該書重新界定了愛國觀光客所不想遺漏的景點。它揚棄陰暗古老的大教堂,而推崇工廠、公共散步場所、新住宅區。論南錫的段落,就很典型:
兵營宏偉,醫院美觀……其他建築,例如教堂,則可鄙。過去,主教住得比他所佯稱尊崇的上帝還要好。
這本指南最特別之處,乃是讚揚巴黎以外的各省居民,但即使如此,布列塔尼人仍給單單排除在外:那些受貴族壓迫的愚昧無知之人,據說喝酒喝到不要命的狂暴狀態,「空氣中偶爾迴蕩著發酒瘋者拿頭猛撞冷冰冰牆壁的聲音」。
雖有這段譫妄性的囈語,拉瓦列的《法國諸省遊歷》一書,協助建立了一個如今幾可說和文明同義的觀念:深信自然美景和歷史名勝乃是國家財富的一部分。在某些任職於新省分的官員,將風景優美之地列入省內資源調查標的時,這仍是個新奇的觀念。梅卡迪耶(Jean-Baptiste Mercadier)一八○○年對阿列日省的描述,乃是最早描述觀光景點之經濟潛力的官方文件之一。他提到化石層、礦物泉、布滿鐘乳石的岩洞、差點被鋸木廠老闆改成工業時代醜東西的貝列斯塔(Belesta)泉。他還提到矗立於阿列日省山丘頂上已成廢墟的要塞,特別是蒙塞居爾(Montsegur)的要塞。蒙塞居爾「是擊敗、屠殺阿爾比派(Albigensian,卡特里異端教派〔Cathar heretics〕)的地方,以此著稱於世」。如今,「卡特里教派景點觀光」是該地區主要的收入來源之一,而梅卡迪耶的描述,為這一觀光業留下最早的記載。(待續)在巴黎以外省分花了那麼多時間之後,在無數次清醒躺在死氣沉沉的城鎮裡苦苦想著巴黎之後,若要梅里美針對新興的觀光業和發展觀光業的主要障礙寫份報告(指低劣的旅館和地方食物),出來的很可能是同樣叫人洩氣的報告。
從大革命後以迄這時,的確已有大幅改善:驛馬車服務更為可靠,原本沒有公路、橋梁的地方,有了較便捷的公路和橋梁。潛伏於森林裡的強盜變少,路邊的示眾架上,不再掛有塗了焦油、不怕日曬雨淋的強盜屍體,使受過活強盜威脅的旅人,不必於強盜死後再受他們的驚嚇。在這只一個世代前,甚至有位王族成員覺得巡遊法國是苦不堪言的事。一七八八年,十三歲的蒙龐西耶公爵(Duc de Montpensier)被派去佩爾什(Perche)省的特拉普派隱修院見學。雖有一名藝術家、一名植物學家、負責提供歷史知識的老師讓利斯夫人奉派與他同行,他這趟觀光卻不開心:
我們於九點半離開凡爾賽,六點抵達這裡(摩爾塔涅)。當天傍晚,我們見到這整個鎮,很可怕的鎮。鎮上有個叫人很不舒服的古井,有人問我們對那井有何看法,據說那是鎮上最值得一看的東西之一。我們在非常糟糕的客棧裡過夜,但床和被單很乾淨。
根據讓利斯夫人在其常用語一書中有關客棧的章節,蒙龐西耶公爵能有乾淨床單可用,大概得歸功於她:
這裡面氣味很難聞。
房間得清掃,並燒些糖或醋除味。只要進入客棧房間,就應如此預為防備。
給我們拿些被單來,潔白、像樣的被單。話先說在前頭,我會很仔細檢查被單。
我自己帶了被單,但一向會叫客棧準備被單,以便把客棧被單鋪在床墊上,再把我自備的被單鋪在上面。
在外國觀光客帶著錢、滿懷期待到來之前,大部分旅館都只是位在驛站的簡陋客棧。所有房客圍著一張大餐桌一起用餐,客房簡陋,有時只是設於廚房或餐室裡的雙層床。圍著餐桌用餐者,通常是四處行走的推銷員,他們不等女士享用,就自行去取用蔬菜燉肉湯,且似乎只需短暫的睡眠。
單人房通常只有大旅館有提供。許多旅人上床時,發現自己要與客棧老闆的家人或驛馬車的乘客同床。一七二八年出版的一本禮儀書,以幾個段落說明身處這一微妙情況時,該怎麼做才不會失禮:「如果迫於低劣的住宿設施,得與自己所尊敬的人同房」,讓那人先寬衣,然後自己再鑽進被子裡,「睡覺時不發出一絲聲音」。隔天早上,絕不可光著身子讓對方見到,不要用鏡子,不要梳頭髮,特別是如果床設在廚房裡,「頭髮可能飄進盤子裡」的話。
除了位在大道旁的客棧,其他的「客棧」可能只是常碰到旅人前來要求投宿的農人,在附屬建築裡擺上幾張跳蚤充斥的床充當的簡陋住所。進入十九世紀許久以後,仍常有旅人被迫接受免費食宿,如果想付錢,還會惹得主人老大不高興。來到較荒涼地區的觀光客,特別是法國觀光客,似乎認為自己的冒險行徑理當受到獎勵,因而對於想牟利的客棧老闆大為不滿。一八三五年出版了庇里牛斯山區「藝術」指南的「兩名友人」,提醒旅人千萬要提防「愛探聽隱私、貪婪、自私、粗魯、無知的一般山區居民」。聖瑪麗德康龐(Sainte-Marie-de-Campan)的居民稱家裡太窮,無法讓他們投宿,令他們大為反感。好心讓他們在店裡打地鋪的那位補鞋匠,想必很驚訝於那「兩位友人」造訪後,愈來愈多人前來敲他的屋門。因為那本指南在旅館一覽表中,列出他的名字和地址。法洛先生(Don Farlo)住在緊鄰法國、西班牙邊界的西班牙城鎮潘蒂科薩(Panticosa),名字和地址也被列出。法洛「並沒有經營客棧,但人大方又好客,只要求投宿者支付膳宿成本」。(待續)拿破崙垮臺後,貿易與觀光復甦,差強人意的旅館變多。盟國旅館(Hotel des Allies)、英國人旅館(Hotel des Anglais)、美國人旅館(Hotel des Americains)之類名稱,通常表示舒適的旅館。在較大的城鎮,旅館老闆會派員工去接驛馬車。喬治.德平和同行乘客於一八一二年抵達歐塞爾,立即遭到旅館員工的包圍,那些員工個個在唱著自己旅館多好多好:
美麗拔得頭籌。所有旅客未經人指點,就自發性站到長得最漂亮那位拉客者旁邊,令其他還在試圖拉走落後旅客的同業大為惱火;但前者像個高明的女牧羊人,小心提防,不讓其他同業靠近她的客人,成功將客人全帶到萊奧帕爾客棧。
客棧老闆可能身兼驛站站長、木頭商人、菸草商、村鎮長等身分。雖然這些是壟斷性生意,但全國各地價格很快就穩定到令所用錢幣的幣值大大低於英鎊或美元的法國旅人大為惱火的程度。雨果在《悲慘世界》裡如此界定客棧老闆的角色:「吸男人的血,剪女人的毛,剝小孩的皮」;「懂得影子能對鏡子造成多大磨損,藉此訂定照鏡子的價錢。」一頓飯通常要價三法朗,如果旅館位在種釀酒葡萄的地區,這價錢包含葡萄酒;若住宿和三餐由旅館全包,一天要價六至八法朗,而在這同時,工人的平均日工資是一塊半法朗。
英、美觀光客鮮少抱怨價格,但往往驚駭於缺乏衛生設施。默瑞的指南建議讀者,「不要忘了帶塊香皂」,因為「個人盥洗用的東西,供應極不完善」。房客通常在臥室裡用餐,臥房的牆和地板可能「積了數年的髒汙,黑得不得了」,且到處是跳蚤。克拉多克(Cradock)夫人的女僕,在一間房間裡就殺了四百八十隻跳蚤。有人曾在廚房裡見到狗使勁扯咬腸子。在里昂附近某客棧的院子裡,英國作家席克內斯(Philip Thicknesse)看到菠菜擺在扁籃子裡,似乎要給狗吃,大為吃驚。結果,同一天更晚,他看見年輕女僕把那些菠菜端到他餐桌。(「我端起盤子,把那盤菜全倒在她頭上。」)
對許多觀光客來說,旅行中最苦的事,不是翻越阿爾卑斯山山口或搭夜間馬車走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而是非得上cabinet d’aisance(廁所)不可。為迎合英國人的期盼,法國旅館漸漸變成有效率且客觀的處所,雖然法國人覺得這沒有人味且嚇人,不過這樣的結果不見得總是合外國人的意。一七六三年在尼姆,英國作家史摩萊特發現「克洛亞辛娜神殿」(Temple of Cloacina,「廁所」別稱)的「情況叫人震驚」:
年輕女僕告訴我,為服務英國旅客,她主人已特別命人做了那個東西;但她為自己已做的事感到很抱歉,因為常來她房子的法國人,全不坐在那上面,而是大在地板上,她為此不得不一天清理三、四次。
後來的觀光客會為坐浴盆而感到困惑,會被小黑洞兩側的瓷造腳踏墊嚇到,但即使在較單純的年代,仍有些不解的謎團。一八一二年,在貝阿恩境內,有人睡在四層式上下鋪的第三層,夜裡被一股氣味和拉繩操作滑輪的聲音驚醒。漆黑中有人低聲說,「沒事,先生,只是教區牧師(vicar)在上去。」後來「vicaire」一詞成為當地「夜壺」的代稱。在如今仍認為人若有必要、可以在公共場所大小便的國家,這種事沒什麼好大驚小怪。過去,農家歡迎任何人在其指定的農家場院角落解放。在村落,橋梁和遮頂小巷之類有遮蔽的地方,乃是「沿用數代的廁所,把戶外的空氣當作消毒劑」(《萬有大辭典》的大便槽〔Fosse d’aisances〕詞條)。
過去,在城鎮,公共設施的舒服,有時叫人吃驚。理察的一八二八年巴黎指南,特別提到「最時髦的廁所」。這些廁所有的比私人住家的廁所還要乾淨,收費只十五分錢,羅浮宮博物館門口的廁所就是一例。在巴黎市神殿市郊路(Rue du Faubourg du Temple)上,有間很出色的廁所,值得「從技術角度去看看」。築門遮住如廁者的廁所,變得愈來愈普遍,且這樣的廁所往往標示有「一○○」(來自cent〔分錢〕和sent〔氣味〕這個不甚高明的雙關語)。在普羅旺斯,城鎮居民有時在屋子一隅開個供人方便的小房間,將便溺物賣給收糞肥者。到了一八六○年代,這一互蒙其利的安排已擴及到尼斯、昂蒂布(Antibes)、聖拉斐爾(Saint-Raphael)三地周邊的石子路沿線。原本得躲到灌木叢後面方便的驛馬車旅客,這時有了裝飾有攀緣植物的小木屋可用。爭奪肥料的農民,以法語或尼斯語(Nissard),以漂亮工整的字體,寫了布告,貼在這類廁所上:Ici on est bien(這裡很棒),Ici on est mieux(這裡更棒),或Ma questo e necessario。(待續)另一項民生大事,涵蓋的內容太廣,恐怕要一部百科全書才能勉強道盡。但那部百科全書會把大部分篇幅著墨於罕見、例外的事物上。標準餐飲太泛泛,沒有人提,除非實在難吃得可以。十九世紀初的小說,為何通常將大餐和(往往與大餐同時出現的)狂歡之類特殊活動等量齊觀,原因在此。
少有人料到法國有朝一日會成為美食觀光客的聖地。過去,除了有錢人家和一些餐廳,食譜很罕見。法文的recette(食譜)一詞起初指的是藥物的調製方法。大部分流傳的「食譜」是巫術療法——「將鴿子從中間剖開;取出心臟;將心臟放在小孩頭上」,諸如此類——或農民智慧的片斷。在魯西永,有人認為鴨子會說「Naps! Naps!」,因為鴨子搭配蕪菁(加泰羅尼語稱之nap)最美味。那些把吃得飽飽視為飲食最高享受的人,似乎未把心思放在有趣的食物組合上。有個故事說到四名來自布列塔尼地區聖布里厄(Saint-Brieuc)的年輕男子,各逞天馬行空的想像,討論各自想吃的東西。第一個想吃特別長的臘腸,第二個想像用「腳趾般大的豆子」和培根一起烹煮,第三個挑的是如海洋那般大片的脂肪,用巨杓舀起最精華的部分享用,第四人則抱怨他們「把世上最好的東西都挑走」。
如今許多法國城鎮以「傳統」地方美食來推銷自己,而那些美食大多只是安肚香腸(andouilee,「是種熟食,把豬或野豬腸子切碎,加上大量香料,再灌進另一個腸子裡」)的一種。現代各式大同小異的安肚香腸,一如蘇格蘭的肉餡羊肚,都只是裝模作樣地將過去的香腸做精緻改良。在過去,氣味辛辣的安肚香腸絕對是難得吃到的東西。對於過去冒險闖入巴黎以外地方的觀光客來說,真正道地的法國味是已走味的麵包。走味的程度,反映燃料可取得的難易。一八二○年在圖魯茲出版的一本鄉村建築手冊,提到公共爐子應大到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烘焙出一星期所需的麵包。在阿爾卑斯山區,會一次烘焙出足供一年食用、有時兩或三年食用的麵包。至少會有一次,把烘焙出的麵包吊在冒煙的火上烘乾,或在太陽下曬乾。有時,所謂的「長條形麵包」只是用大麥和豆粉製成的薄餅乾。為便於入口,改善其顏色,居民會用白脫牛奶或乳清軟化麵包。有錢人用的則是白葡萄酒。
這就是烘製麵包者吃上一整年的麵包,硬如石頭,不受天候影響,能帶著遠行。較硬的麵包從貯藏處拿出來時,硬如化石,得用榔頭敲碎,跟著一些馬鈴薯,或許也加牛奶調味,煮上五次。大部分旅人一想到吃當地麵包就怕,於是改吃自備的餅乾。在奧佛涅地區,居民用黑麥粉加麥麩,製成濃黑的黏稠食物,食用時配水和乳清好入口。在玉米漸漸取代小米的西南部,麵團切片,然後油炸,或放在灰燼下面燜熟。配上鹽醃沙丁魚或蕁麻湯,它曾被視為是人間美味,但只有每天吃的人這麼認為。
在美食貧乏的省分,當觀光客狼吞虎嚥當地兔肉和雞肉時,或許會覺得自己受剝削,但他們所享用的食物,通常已經遠比當地人豐富了。在法國許多地區,過去只在特殊場合吃肉。一八四四年官方派往的調查團就發現,儘管安茹運送數噸的肉到巴黎,但當地人幾乎吃素。正餐吃的是麵包、湯(甘藍、馬鈴薯或洋蔥)、一份蔬菜、一顆煮熟的蛋。一年的菜單裡,可能還包括偶爾才吃上的一塊乳酪、冬天時的一些堅果、禮拜日會用點加鹽豬油改變一下麵包的味道。
地方上吃的肉不必然來自農家院子或牧場。唯一不會被吃掉的大型動物,就是惹人反感的狼,但饑荒時例外。在勃艮第地區,有些人認為狐狸是美味佳餚,「前提是在結霜時,掛在園子裡的梅樹上兩星期。」莫爾旺山區和朗德省的居民則會吃紅松鼠,這種松鼠性情溫馴,老人家用棍子就能將其捕殺。土撥鼠有冬眠前清光腸裡穢物的習慣,在阿爾卑斯山區,居民會將牠們扯出地洞煮熟,有時泡在水裡二十四小時以去除麝香氣味。土撥鼠肉質油膩,嚐起來微微帶有煤煙的味道。其脂肪可以用來抹在患風濕的手腳上,以及用做油燈燃料。在庇里牛斯山區,熊有時候會吃人,但要到觀光客開始嗜吃珍奇山產之後,才有人吃熊。一八三四年一本介紹圖魯茲和其周圍的指南建議,「偶爾有熊被殺,可吃到用熊肉做成的牛排(原文如此),味道甚佳。」
最初,很難理解過去的人如何靠傳統日常食物活命。在貝桑松度過童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分子普魯東聲稱,他家平常吃烤過的玉米粉(gaude)、馬鈴薯、蔬菜湯,吃得「又高又壯」,但以這些食物為主食,大概會長不高且體弱多病。在回憶錄或遺囑「撫養費」(pensions alimentaires)裡提及的許多日常飲食,缺乏維生素和蛋白質的攝取,久而久之會要人命。在某些例子裡,熱量幾乎全來自做成麵包的穀類食物。但研究證實,普魯東也和他所照料的乳牛一樣,一天裡有許多時間在嚼食植物,用玉米、嬰粟籽、豌豆、匍匐風鈴草、波羅門參、櫻桃、葡萄、玫瑰果、黑刺莓、黑刺李祭五臟廟。在法國境內較溫暖的地區,拿來打牙祭的食物營養成分可能比較高。在亞維儂附近,佩迪吉耶大啖梨子、葡萄、杏子、無花果,還有許多種他已無法用法語講出名字的野生水果。一八六二年全法國有超過三百萬個蜂巢(每十三個居民有一蜂巢),表示當時的日常食物並非總是如今人印象中那麼貧乏。在菜色單調的地區,將?桲裹上蜂蜜,再放在餘燼裡烤過,可能就是令人難忘的美食。(待續)在工業式農業使穀類席捲全國之前,可食植物和動物的種類和數量都較多。伊拉提森林那位健壯的野人,似乎一直是個素食者。在聖塞爾南(Saint-Sernin)附近被捕的「阿韋龍的維克托」,可能吃過雞肉、鴨肉、淡水螫蝦,但大概沒吃過如今聖塞爾南旅館「野小孩菜單」(Menu de l’Enfant Sauvage)上所列的其他菜(羅克福爾乳酪、舒芙蕾凍糕、胡桃酒)。一七三一年在香檳地區松吉(Songy)附近被人發現的野女童蔓米(Memmie),靠生吃兔肉、青蛙過活,她也吃樹葉與根莖,會用結實的拇指、食指到處挖。
如今,觀光客到富饒的農業地區旅遊,吃到的卻是牛排薯條和淋上點油的乾枯萵苣,店家也絲毫不覺有對不起的意思。這種現象其實是百年來所造成的結果。隨著鐵路將觀光客快速送到鄉間,將農產品送往城市,法國的美食地圖似乎頓時生機勃勃。在巴黎雜誌上撰寫地理文章的作家,對各地區的特色美食猛流口水:來自伊錫尼(Isigny)的奶油、科佩伊的蘋果、蒙莫朗西(Montmorency)的櫻桃、拉翁的朝鮮薊、第戎的芥茉和黑醋栗甜酒(cassis)、佩里戈爾的松露、圖爾和阿讓(Agen)的李子乾、巴約訥的巧克力。這些特產裡,有一些名產並不能代表一個地區的精神,只是反映了某食品雜貨店的宣傳技倆。過去,它們鮮少出現於觀光客的餐盤上,且未必可在該地區吃到。第戎地區原本並不盛產黑醋栗,直到一八四一年,當地有位富創業心的咖啡店老闆到巴黎考察市場,注意到黑醋栗甜酒很受歡迎,開始把他自產的黑醋栗甜酒當該地特產推銷,第戎才開始盛產。在種葡萄兼釀葡萄酒的地區,好葡萄酒往往反而難尋。法國葡萄酒的鑑賞家,在倫敦、巴黎或圖爾(因有大量英格蘭僑民),比在法國鄉間收入更好。在法國鄉間,喝得起葡萄酒的人,用餐時較喜歡搭配渣釀白蘭地(eau de marc,用釀製葡萄酒過程中留下的糊狀葡萄渣提餾出的烈酒)。
被餐飲業者和雜貨商運到巴黎銷售的食物,創造出鄉間虛幻不實的形象。在帕莉塞夫人(Mme Pariset)《家庭主婦新完全持家手冊》(Nouveau manuel complet de la maitresse de maison,1852)的食譜一節中,主要材料顯然在巴黎的一般家庭裡就有,頂多請女僕到中央市場去採買。她的食譜要人用來自艾克斯的橄欖油、勃艮第的玉米粉、布列塔尼的去殼燕麥,史特拉斯堡培根和格呂耶爾(Gruyere)乳酪,不過食譜裡的菜——相當樸實的蔬菜燉肉和用大量甘藍菜煮的湯——不是發源自法國鄉間,而是來自「最上等的餐桌」。
最上等的餐桌幾乎全在巴黎。據說,一八八九年,巴黎市內每一百家餐廳才有一家書店。「巴黎的牙祭之旅,在過去大概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如今卻幾乎和環遊世界一樣久。」許多「地方」美食是從巴黎傳到地方。農民小說家紀堯曼(Emile Guillaumin)筆下的波旁內一家人,看到來訪的巴黎親戚蹲在池塘邊,抓起青蛙丟進袋子裡,大為驚駭(一八八○年):「沒人知道怎麼料理青蛙,侄子只好自己煮煮看。」
外國觀光客入境百年之後,才有大批法國男女開始親自去發掘法國。但即便如此,大部分的饕客仍偏愛到巴黎餐廳探索各地美食。有個法國人當時就做了一趟最啟發人心的發現之旅,就是大仲馬一八六九年在布列塔尼北海岸羅斯科夫的旅行。當時羅斯科夫是法國西部商品蔬菜栽培業的龍頭城市。一八六○年代,每年有數百艘船載著洋蔥和朝鮮薊離開這小港到英國,顯然是因為曾經有個大膽的傢伙在倫敦拿著「英格蘭洋蔥不好」的板子,結果成功將洋蔥銷售出去。不過當大仲馬定居羅斯科夫寫《菜餚大辭典》(Le Grand Dictionnaire de Cuisine)時,靈感多得自想像力,而不是食物:「盛產魚,但此外沒什麼東西:硬如子彈的朝鮮薊、水水的菜豆、不新鮮的奶油。」他的廚師瑪麗事前就斷言,這次遠行只會空手而回。她忿忿離開,回去可發現並享用到法國所有奇特美食的巴黎。
高地居民正發掘平原和山谷時,有種新的遷徙族已在往山區前進。第一批就出現在十八世紀中葉。到了紹丹村成為鬼城時,他們已散播到法國其他地方。那時在法國,他們被叫做「touriste」(觀光客)。這字眼來自英語,用以指稱從事「壯遊」(Grand Tour)的旅人,其中大部分人前往佛羅倫斯、威尼斯、羅馬、那不勒斯。
早期的觀光客幾乎全是英國人,且主要出現於阿爾卑斯山、庇里牛斯山,以及從巴黎往南到里昂、義大利那三條路線上的過夜休息點。觀光客為了享樂、陶冶心靈或健康而旅行,顯然無視於常識和體力極限。與探險家不同的,他們不想只是發現。他們並未只是觀察和記錄,反倒是改造他們所好奇的東西,使其改頭換面。他們重建過去,按照他們所偏愛的色彩打扮當地人,最後建構了他們自己的城鎮和景觀。
這類新式旅人幾乎是一出現就開始繁殖、分化,個體愈來愈弱,而群體愈來愈強。但一八五八年哲學家暨史學家泰訥,為這類觀光客的原型下定義時,這類原型觀光客仍相當普遍:
腿長,體瘦,頭前俯,腳板寬大,雙手有力,特別適於抓握。帶著手杖、雨傘、斗篷、橡膠外套……以令人欣賞的方式行走大地……在歐博訥(Eaux-Bonnes),他們有人掉了旅行日誌,被我撿到。日誌標題是「我的感想」:
八月三號。穿越冰川。右鞋裂開。抵達馬拉戴塔(Maladetta)山頂。見到先前觀光客留下的三只瓶子……回程時,嚮導盛宴款待。晚上,有人在我門口吹奏風笛,獻上綁了絲帶的大花束。全部花費一百六十八法朗。
八月十五號。離開庇里牛斯山。一個月內以徒步、騎馬、搭馬車的方式走了三百九十一里格;十一次登高,十八趟短途旅行。用掉兩根手杖,一件外套,三條長褲,五雙鞋子。充實的一年。
附註:絕美的國家,叫人感動不已。
這種仿英雄體寫成的法國觀光記述,在那一百年前的一七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就已問世,就在薩瓦的邊界上。那天下午,夏莫尼村的小隱修院院長和村民,聽到槍聲和啪啪的馬鞭聲迴蕩於山間,大為驚訝。幾小時後,他們注意到古怪的一行人,不知所為何來,循著阿爾沃(Arve)河谷跌跌撞撞吃力往上爬。八名英格蘭紳士和五名配備重武器的僕人,正騎著非常疲累的馬在與急流搏鬥,其中有些人已掉了鞋子。
這支探險隊的領隊,綽號「拳擊」的溫德姆(William ‘Boxing’ Windham)原住在日內瓦,對遙遠的白色高山上據說有叫冰川的廣大冰原深深著迷。他找不怕死的人跟他一起去探索那座所謂的受咀咒山(Montagnes Maudites),可想而知未能如願。但就在這時,探險家波卡克(Richard Pococke)在從埃及、黎凡特返國途中,來到日內瓦。六月十九日,他們和其他六個在日內瓦無所事事的紳士啟程。三天後他們抵達蒙唐韋(Montenvers)冰川腳下的夏莫尼。(待續)在這之前,來夏莫尼的外地人,就只有膽子大的收稅員、巡迴主教、薩瓦公爵的地圖繪製員,但夏莫尼村民倒是常出遠門。他們到日內瓦賣岩羚羊皮、水晶、蜂蜜;他們的牧羊人靠著製作乳酪的本事,在這整個地區炙手可熱。許多村民從事巡迴推銷工作,會經由第戎和朗格勒(Langres)去巴黎,並聲稱曾在巴黎遠遠見到他們家鄉的山。當時,隨時都有約三分之一夏莫尼村民住在巴黎。
村民主動表示願讓這一行英格蘭人住進家裡,但他們拒絕,選擇在村外紮營。他們派人看守,火整夜沒熄。幾十年後,夏莫尼的老人家仍拿這些英格蘭紳士一心提防走失綿羊和好奇孩童的故事以饗外來客。夏莫尼人善於模仿他人,無疑誇大了溫德姆一行人的防備心態。但溫德姆本人也誇大了夏莫尼村民的無知。他不辭艱險來到荒山野嶺,想看到的東西裡,就包括「原始」人。隔天早上,他問當地人冰川的事,聽到有女巫在冰上守安息日的「荒謬」傳說,滿意但不驚訝。
募得嚮導和挑夫,記下他所認為村民對他這支勇敢隊伍的欽佩之情後,溫德姆一行人爬過雪崩肆虐過的「悲慘災區」,微顫顫走過懸崖邊緣,循著路痕鮮明的獵徑抵達蒙唐韋山頂(六十年後,遜位皇后約瑟芬帶著六十八名嚮導和女侍,也走過這條路線)。在山頂,他們見到「無法形容的景致」:「叫人不得不想像那是(日內瓦)湖水被暴風翻攪騰空,然後一下子結成冰所形成。」後來,有人將這一類似格陵蘭的景致,取名(或許幾乎可以說是冠上圖說)「冰海」(Mer de Glace)。
溫德姆對觀光業發展的重大貢獻,不是他發現了冰川,而在引進了浪漫主義的感性。他為這趟遠征所寫的遊記,在日內瓦的沙龍裡大為流傳。一七四四年,該遊記於全歐各地刊物刊出,蔚為轟動。山突然間成為時髦新寵。對當時大部分人來說,冰崖就差不多和骯髒村落或破敗哥德式教堂一樣迷人。狄索爾(Jean Dusaulx)於一七八八年來到庇里牛斯山時,有位女士問他,「你對這些可怕東西有何看法?」她指的是後來被叫做美景的東西。山只是碰巧陡直的荒地。在今人眼中,旺圖山稱雄、統合周遭群山,但在十八世紀末期之前,提到該山的普羅旺斯遊記少之又少,更別提詳細介紹該山。當時瞭解山者不多。一七九二年,有位逃離「恐怖統治」的神父,發現成群的巨大岩體要花上半天時間才能勉強爬完,大為驚愕:「我一直以為山是龐大但孤立的凸出物。」
對於那些想過這問題的人來說,山和住在山上的人,乃是原始世界的殘餘。地球一如人類,正緩緩步向完美狀態,屆時,「地勢將平緩到不可能出現山崩,而草木將安穩立在山的遺骸上」(拉蒙〔Louis Ramond〕,《庇里牛斯山觀察》〔Observations faites dans le Pyrenees,1789〕)。英國作家沃爾浦爾(Horace Walpole)在花了四天穿越阿爾卑斯山,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小寵物狗大白天被狼抓走後,寫道,「真荒涼的岩石,真難看的居民!」「希望這輩子不要再見到。」
溫德姆探險之行後,觀光客紛紛入侵薩瓦的阿爾卑斯山。蘇格蘭醫生摩爾(John Moore)在一七七九年抱怨道,「只要提到什麼新奇或特別的東西,幾乎都會引來別人告訴你……這位先生,那的確不錯;但相信我,根本和薩瓦的冰川不能比。」該世紀結束時,「冰海」騎馬可到,觀光客可在名叫「自然之殿」的山中避難小屋過夜。若非拿破崙拒絕夏莫尼人的要求,甚至會有條道地的公路通達「冰海」。拿破崙說道:「這些人不知道怎樣才是對他們有利。如果人可以搭馬車上『冰海』,那些名媛貴婦還有什麼驚險故事可拿來說?」詩人雪萊走訪那個「只住有暴風雨的荒涼地方」(〈寫於夏莫尼山谷詩〉〔Lines written in the Vale of Chamouni,1816〕)時,那個「荒涼地方」的旅館已足夠容納當地人口數倍的遊客。形形色色的商人、教師、畫家、植物學家、無所事事的領主、人稱「adventuress」(用不正當手段謀取名利或地位的女人)的有趣女人,在靜得叫人難以忍受的氣氛中,一起圍著餐桌而坐。當時有半數以上觀光客來自英格蘭,因此英格蘭作風大行其道。其中有些人來看「冰海」,有些人來攻頂不久前已被認定為歐洲最高峰的白朗峰。一七八六年,一名當地牧羊人和一名醫生首度登頂白朗峰。一個世紀後,阿爾卑斯山、庇里牛斯山的主要山頭,幾乎全都給征服過幾次。拜圓滑的嚮導之賜,許多人離去時,都自得地以為自己是第一個登頂所爬山峰的人。(待續)溫德姆從事那趟探險之行時,在法國較平坦的地區,觀光客幾乎不存在。當時,能讓旅人擬出法國觀光行程的資訊太少,而鼓勵人待在家裡的東西則太多。自十二世紀的聖地牙哥.德.坎波斯泰拉朝聖指南問世以迄這時,指南書籍幾乎是一成不變。這本出自克呂尼(Cluny)修道院僧侶之手的朝聖指南,描述了主要路線和聖地、食宿、每段驛站之間可能花費的時間、朝聖者大概會受到的接待。貫穿全書的主張,乃是離文明開化的北部愈遠,情況就愈糟。越過加龍河,語言就是鴨子聽雷的「土話」;朗德(徒步三天行程)是個有巨蠅和流沙的地區,吃不到肉、魚、麵包,喝不到葡萄酒和水;加斯科涅居民嗜酒、好色、多話、愛挖苦人、好客,最後一點無疑未必是十足的好事。
七百年後,指南書仍循著類似的思路撰寫。此類書的作者認定其讀者是巴黎人,或至少是已在巴黎展開旅程的人,因為據一七四○年《法蘭西新旅行》(Le Nouveau voyage de France)一書,「要打造個人品味,要充分瞭解普羅旺斯的習俗和政府,首先應研究首都和宮廷。」基於顯而易見的理由,大部分書把內容局限在驛道沿途可見到的東西。奧熱(Jean Ogee)於一七六九年所寫的布列塔尼指南,就取了很典型的副書名:「包含此路左右兩側半里格(一.六公里多一點)內出現的所有特別事物。」景物本身不被視為旅行的目的。為紓解漫長旅程的無聊,指南書會提供詳細歷史知識,供旅人排解煩悶,煩擾同車乘客之用。布里瓦爾(John Breval)一七三八年針對「歐洲幾個地區」所寫的指南,鎖定能從「最荒涼平原或最杳無人煙之村落」(即使只知它們的年代和名字)得到樂趣的「那群讀者」。
由於當時地理資訊缺乏,大部分作者借用先前著作的內容,而這些先前著作又是抄襲自更早的著作。因此,作者寫起明明早已不存在的古蹟,仍寫得像是親眼見過一般。許多作者顯然認為不會有人照著他們書中的指示去遊歷,於是鉅細靡遺描述了一些憑空杜撰的地方城鎮。馬爾蘭旅行時,帶著德.埃瑟恩(Robert de Hesseln)的小巧《法國萬有辭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la France,1771),乃是因為「將介紹整個國家的六冊書,放在馬車的口袋裡隨行,很有用」。遺憾的,提供資訊給埃瑟恩的在地人,有時叫他失望,一如馬爾蘭一七九○年抵達洛澤爾省首府時所發現的。「埃瑟恩先生很用心把芒德(Mende)擺在山上,說它呈三角形,住了許多人。這句話只錯了三個地方。」
甚至在十九世紀結束時,仍有許多指南書描寫旺圖山頭「永不融化的雪」(那「雪」其實是白岩石)。其中有一本出版於一八八八年,還提到熱比耶德容克山頂「荒涼的沼澤中,長了數叢濃密的藨草」,但其實該山山頂十足乾燥(此山名來自意指「岩石」和「山」的兩個字,但在現代法語裡,此名意指一束燈心草)。這些作者大部分除了搭火車,從未去到巴黎外大街以外的地方。(待續)法國境內為新式開明觀光客出版的第一本旅行指南,乃是當時史上最充滿感情、最煞費苦心、卻也最不實用的指南之一。拉瓦列(Joseph Lavallee)的《法國諸省遊歷》(Voyages dans les departements de la France),一七九二年開始以分期出版的分冊形式問世。這時,拉瓦列投入革命陣營不久,狂熱支持革命理念,想讓那些目中無人的巴黎人知道,巴黎以外的各省其實和他們高高在上的首都一樣有趣。他和志同道合者啟程走遍全國,循一條毫無中斷的路線,穿過所有省分,且每個省都只通過一次。
除了那條古怪但理論上合理的路線,這本書還有幾個地方不同於一般指南。首先,拉瓦列和其工作團隊似乎真的親自走完這趟旅程(描繪瓦朗謝訥的那張圖,從遠距離呈現該鎮,因為繪者擔心遭被視作間諜射殺。談羅亞爾河下游省那一章,略去該省大部分地區,因為道路不通,且船因風阻而無法在基伯龍上岸)。其次,這本書打算賣到全國各地,賣到每個設有驛站長的鎮。最後,該書重新界定了愛國觀光客所不想遺漏的景點。它揚棄陰暗古老的大教堂,而推崇工廠、公共散步場所、新住宅區。論南錫的段落,就很典型:
兵營宏偉,醫院美觀……其他建築,例如教堂,則可鄙。過去,主教住得比他所佯稱尊崇的上帝還要好。
這本指南最特別之處,乃是讚揚巴黎以外的各省居民,但即使如此,布列塔尼人仍給單單排除在外:那些受貴族壓迫的愚昧無知之人,據說喝酒喝到不要命的狂暴狀態,「空氣中偶爾迴蕩著發酒瘋者拿頭猛撞冷冰冰牆壁的聲音」。
雖有這段譫妄性的囈語,拉瓦列的《法國諸省遊歷》一書,協助建立了一個如今幾可說和文明同義的觀念:深信自然美景和歷史名勝乃是國家財富的一部分。在某些任職於新省分的官員,將風景優美之地列入省內資源調查標的時,這仍是個新奇的觀念。梅卡迪耶(Jean-Baptiste Mercadier)一八○○年對阿列日省的描述,乃是最早描述觀光景點之經濟潛力的官方文件之一。他提到化石層、礦物泉、布滿鐘乳石的岩洞、差點被鋸木廠老闆改成工業時代醜東西的貝列斯塔(Belesta)泉。他還提到矗立於阿列日省山丘頂上已成廢墟的要塞,特別是蒙塞居爾(Montsegur)的要塞。蒙塞居爾「是擊敗、屠殺阿爾比派(Albigensian,卡特里異端教派〔Cathar heretics〕)的地方,以此著稱於世」。如今,「卡特里教派景點觀光」是該地區主要的收入來源之一,而梅卡迪耶的描述,為這一觀光業留下最早的記載。(待續)在巴黎以外省分花了那麼多時間之後,在無數次清醒躺在死氣沉沉的城鎮裡苦苦想著巴黎之後,若要梅里美針對新興的觀光業和發展觀光業的主要障礙寫份報告(指低劣的旅館和地方食物),出來的很可能是同樣叫人洩氣的報告。
從大革命後以迄這時,的確已有大幅改善:驛馬車服務更為可靠,原本沒有公路、橋梁的地方,有了較便捷的公路和橋梁。潛伏於森林裡的強盜變少,路邊的示眾架上,不再掛有塗了焦油、不怕日曬雨淋的強盜屍體,使受過活強盜威脅的旅人,不必於強盜死後再受他們的驚嚇。在這只一個世代前,甚至有位王族成員覺得巡遊法國是苦不堪言的事。一七八八年,十三歲的蒙龐西耶公爵(Duc de Montpensier)被派去佩爾什(Perche)省的特拉普派隱修院見學。雖有一名藝術家、一名植物學家、負責提供歷史知識的老師讓利斯夫人奉派與他同行,他這趟觀光卻不開心:
我們於九點半離開凡爾賽,六點抵達這裡(摩爾塔涅)。當天傍晚,我們見到這整個鎮,很可怕的鎮。鎮上有個叫人很不舒服的古井,有人問我們對那井有何看法,據說那是鎮上最值得一看的東西之一。我們在非常糟糕的客棧裡過夜,但床和被單很乾淨。
根據讓利斯夫人在其常用語一書中有關客棧的章節,蒙龐西耶公爵能有乾淨床單可用,大概得歸功於她:
這裡面氣味很難聞。
房間得清掃,並燒些糖或醋除味。只要進入客棧房間,就應如此預為防備。
給我們拿些被單來,潔白、像樣的被單。話先說在前頭,我會很仔細檢查被單。
我自己帶了被單,但一向會叫客棧準備被單,以便把客棧被單鋪在床墊上,再把我自備的被單鋪在上面。
在外國觀光客帶著錢、滿懷期待到來之前,大部分旅館都只是位在驛站的簡陋客棧。所有房客圍著一張大餐桌一起用餐,客房簡陋,有時只是設於廚房或餐室裡的雙層床。圍著餐桌用餐者,通常是四處行走的推銷員,他們不等女士享用,就自行去取用蔬菜燉肉湯,且似乎只需短暫的睡眠。
單人房通常只有大旅館有提供。許多旅人上床時,發現自己要與客棧老闆的家人或驛馬車的乘客同床。一七二八年出版的一本禮儀書,以幾個段落說明身處這一微妙情況時,該怎麼做才不會失禮:「如果迫於低劣的住宿設施,得與自己所尊敬的人同房」,讓那人先寬衣,然後自己再鑽進被子裡,「睡覺時不發出一絲聲音」。隔天早上,絕不可光著身子讓對方見到,不要用鏡子,不要梳頭髮,特別是如果床設在廚房裡,「頭髮可能飄進盤子裡」的話。
除了位在大道旁的客棧,其他的「客棧」可能只是常碰到旅人前來要求投宿的農人,在附屬建築裡擺上幾張跳蚤充斥的床充當的簡陋住所。進入十九世紀許久以後,仍常有旅人被迫接受免費食宿,如果想付錢,還會惹得主人老大不高興。來到較荒涼地區的觀光客,特別是法國觀光客,似乎認為自己的冒險行徑理當受到獎勵,因而對於想牟利的客棧老闆大為不滿。一八三五年出版了庇里牛斯山區「藝術」指南的「兩名友人」,提醒旅人千萬要提防「愛探聽隱私、貪婪、自私、粗魯、無知的一般山區居民」。聖瑪麗德康龐(Sainte-Marie-de-Campan)的居民稱家裡太窮,無法讓他們投宿,令他們大為反感。好心讓他們在店裡打地鋪的那位補鞋匠,想必很驚訝於那「兩位友人」造訪後,愈來愈多人前來敲他的屋門。因為那本指南在旅館一覽表中,列出他的名字和地址。法洛先生(Don Farlo)住在緊鄰法國、西班牙邊界的西班牙城鎮潘蒂科薩(Panticosa),名字和地址也被列出。法洛「並沒有經營客棧,但人大方又好客,只要求投宿者支付膳宿成本」。(待續)拿破崙垮臺後,貿易與觀光復甦,差強人意的旅館變多。盟國旅館(Hotel des Allies)、英國人旅館(Hotel des Anglais)、美國人旅館(Hotel des Americains)之類名稱,通常表示舒適的旅館。在較大的城鎮,旅館老闆會派員工去接驛馬車。喬治.德平和同行乘客於一八一二年抵達歐塞爾,立即遭到旅館員工的包圍,那些員工個個在唱著自己旅館多好多好:
美麗拔得頭籌。所有旅客未經人指點,就自發性站到長得最漂亮那位拉客者旁邊,令其他還在試圖拉走落後旅客的同業大為惱火;但前者像個高明的女牧羊人,小心提防,不讓其他同業靠近她的客人,成功將客人全帶到萊奧帕爾客棧。
客棧老闆可能身兼驛站站長、木頭商人、菸草商、村鎮長等身分。雖然這些是壟斷性生意,但全國各地價格很快就穩定到令所用錢幣的幣值大大低於英鎊或美元的法國旅人大為惱火的程度。雨果在《悲慘世界》裡如此界定客棧老闆的角色:「吸男人的血,剪女人的毛,剝小孩的皮」;「懂得影子能對鏡子造成多大磨損,藉此訂定照鏡子的價錢。」一頓飯通常要價三法朗,如果旅館位在種釀酒葡萄的地區,這價錢包含葡萄酒;若住宿和三餐由旅館全包,一天要價六至八法朗,而在這同時,工人的平均日工資是一塊半法朗。
英、美觀光客鮮少抱怨價格,但往往驚駭於缺乏衛生設施。默瑞的指南建議讀者,「不要忘了帶塊香皂」,因為「個人盥洗用的東西,供應極不完善」。房客通常在臥室裡用餐,臥房的牆和地板可能「積了數年的髒汙,黑得不得了」,且到處是跳蚤。克拉多克(Cradock)夫人的女僕,在一間房間裡就殺了四百八十隻跳蚤。有人曾在廚房裡見到狗使勁扯咬腸子。在里昂附近某客棧的院子裡,英國作家席克內斯(Philip Thicknesse)看到菠菜擺在扁籃子裡,似乎要給狗吃,大為吃驚。結果,同一天更晚,他看見年輕女僕把那些菠菜端到他餐桌。(「我端起盤子,把那盤菜全倒在她頭上。」)
對許多觀光客來說,旅行中最苦的事,不是翻越阿爾卑斯山山口或搭夜間馬車走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而是非得上cabinet d’aisance(廁所)不可。為迎合英國人的期盼,法國旅館漸漸變成有效率且客觀的處所,雖然法國人覺得這沒有人味且嚇人,不過這樣的結果不見得總是合外國人的意。一七六三年在尼姆,英國作家史摩萊特發現「克洛亞辛娜神殿」(Temple of Cloacina,「廁所」別稱)的「情況叫人震驚」:
年輕女僕告訴我,為服務英國旅客,她主人已特別命人做了那個東西;但她為自己已做的事感到很抱歉,因為常來她房子的法國人,全不坐在那上面,而是大在地板上,她為此不得不一天清理三、四次。
後來的觀光客會為坐浴盆而感到困惑,會被小黑洞兩側的瓷造腳踏墊嚇到,但即使在較單純的年代,仍有些不解的謎團。一八一二年,在貝阿恩境內,有人睡在四層式上下鋪的第三層,夜裡被一股氣味和拉繩操作滑輪的聲音驚醒。漆黑中有人低聲說,「沒事,先生,只是教區牧師(vicar)在上去。」後來「vicaire」一詞成為當地「夜壺」的代稱。在如今仍認為人若有必要、可以在公共場所大小便的國家,這種事沒什麼好大驚小怪。過去,農家歡迎任何人在其指定的農家場院角落解放。在村落,橋梁和遮頂小巷之類有遮蔽的地方,乃是「沿用數代的廁所,把戶外的空氣當作消毒劑」(《萬有大辭典》的大便槽〔Fosse d’aisances〕詞條)。
過去,在城鎮,公共設施的舒服,有時叫人吃驚。理察的一八二八年巴黎指南,特別提到「最時髦的廁所」。這些廁所有的比私人住家的廁所還要乾淨,收費只十五分錢,羅浮宮博物館門口的廁所就是一例。在巴黎市神殿市郊路(Rue du Faubourg du Temple)上,有間很出色的廁所,值得「從技術角度去看看」。築門遮住如廁者的廁所,變得愈來愈普遍,且這樣的廁所往往標示有「一○○」(來自cent〔分錢〕和sent〔氣味〕這個不甚高明的雙關語)。在普羅旺斯,城鎮居民有時在屋子一隅開個供人方便的小房間,將便溺物賣給收糞肥者。到了一八六○年代,這一互蒙其利的安排已擴及到尼斯、昂蒂布(Antibes)、聖拉斐爾(Saint-Raphael)三地周邊的石子路沿線。原本得躲到灌木叢後面方便的驛馬車旅客,這時有了裝飾有攀緣植物的小木屋可用。爭奪肥料的農民,以法語或尼斯語(Nissard),以漂亮工整的字體,寫了布告,貼在這類廁所上:Ici on est bien(這裡很棒),Ici on est mieux(這裡更棒),或Ma questo e necessario。(待續)另一項民生大事,涵蓋的內容太廣,恐怕要一部百科全書才能勉強道盡。但那部百科全書會把大部分篇幅著墨於罕見、例外的事物上。標準餐飲太泛泛,沒有人提,除非實在難吃得可以。十九世紀初的小說,為何通常將大餐和(往往與大餐同時出現的)狂歡之類特殊活動等量齊觀,原因在此。
少有人料到法國有朝一日會成為美食觀光客的聖地。過去,除了有錢人家和一些餐廳,食譜很罕見。法文的recette(食譜)一詞起初指的是藥物的調製方法。大部分流傳的「食譜」是巫術療法——「將鴿子從中間剖開;取出心臟;將心臟放在小孩頭上」,諸如此類——或農民智慧的片斷。在魯西永,有人認為鴨子會說「Naps! Naps!」,因為鴨子搭配蕪菁(加泰羅尼語稱之nap)最美味。那些把吃得飽飽視為飲食最高享受的人,似乎未把心思放在有趣的食物組合上。有個故事說到四名來自布列塔尼地區聖布里厄(Saint-Brieuc)的年輕男子,各逞天馬行空的想像,討論各自想吃的東西。第一個想吃特別長的臘腸,第二個想像用「腳趾般大的豆子」和培根一起烹煮,第三個挑的是如海洋那般大片的脂肪,用巨杓舀起最精華的部分享用,第四人則抱怨他們「把世上最好的東西都挑走」。
如今許多法國城鎮以「傳統」地方美食來推銷自己,而那些美食大多只是安肚香腸(andouilee,「是種熟食,把豬或野豬腸子切碎,加上大量香料,再灌進另一個腸子裡」)的一種。現代各式大同小異的安肚香腸,一如蘇格蘭的肉餡羊肚,都只是裝模作樣地將過去的香腸做精緻改良。在過去,氣味辛辣的安肚香腸絕對是難得吃到的東西。對於過去冒險闖入巴黎以外地方的觀光客來說,真正道地的法國味是已走味的麵包。走味的程度,反映燃料可取得的難易。一八二○年在圖魯茲出版的一本鄉村建築手冊,提到公共爐子應大到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烘焙出一星期所需的麵包。在阿爾卑斯山區,會一次烘焙出足供一年食用、有時兩或三年食用的麵包。至少會有一次,把烘焙出的麵包吊在冒煙的火上烘乾,或在太陽下曬乾。有時,所謂的「長條形麵包」只是用大麥和豆粉製成的薄餅乾。為便於入口,改善其顏色,居民會用白脫牛奶或乳清軟化麵包。有錢人用的則是白葡萄酒。
這就是烘製麵包者吃上一整年的麵包,硬如石頭,不受天候影響,能帶著遠行。較硬的麵包從貯藏處拿出來時,硬如化石,得用榔頭敲碎,跟著一些馬鈴薯,或許也加牛奶調味,煮上五次。大部分旅人一想到吃當地麵包就怕,於是改吃自備的餅乾。在奧佛涅地區,居民用黑麥粉加麥麩,製成濃黑的黏稠食物,食用時配水和乳清好入口。在玉米漸漸取代小米的西南部,麵團切片,然後油炸,或放在灰燼下面燜熟。配上鹽醃沙丁魚或蕁麻湯,它曾被視為是人間美味,但只有每天吃的人這麼認為。
在美食貧乏的省分,當觀光客狼吞虎嚥當地兔肉和雞肉時,或許會覺得自己受剝削,但他們所享用的食物,通常已經遠比當地人豐富了。在法國許多地區,過去只在特殊場合吃肉。一八四四年官方派往的調查團就發現,儘管安茹運送數噸的肉到巴黎,但當地人幾乎吃素。正餐吃的是麵包、湯(甘藍、馬鈴薯或洋蔥)、一份蔬菜、一顆煮熟的蛋。一年的菜單裡,可能還包括偶爾才吃上的一塊乳酪、冬天時的一些堅果、禮拜日會用點加鹽豬油改變一下麵包的味道。
地方上吃的肉不必然來自農家院子或牧場。唯一不會被吃掉的大型動物,就是惹人反感的狼,但饑荒時例外。在勃艮第地區,有些人認為狐狸是美味佳餚,「前提是在結霜時,掛在園子裡的梅樹上兩星期。」莫爾旺山區和朗德省的居民則會吃紅松鼠,這種松鼠性情溫馴,老人家用棍子就能將其捕殺。土撥鼠有冬眠前清光腸裡穢物的習慣,在阿爾卑斯山區,居民會將牠們扯出地洞煮熟,有時泡在水裡二十四小時以去除麝香氣味。土撥鼠肉質油膩,嚐起來微微帶有煤煙的味道。其脂肪可以用來抹在患風濕的手腳上,以及用做油燈燃料。在庇里牛斯山區,熊有時候會吃人,但要到觀光客開始嗜吃珍奇山產之後,才有人吃熊。一八三四年一本介紹圖魯茲和其周圍的指南建議,「偶爾有熊被殺,可吃到用熊肉做成的牛排(原文如此),味道甚佳。」
最初,很難理解過去的人如何靠傳統日常食物活命。在貝桑松度過童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分子普魯東聲稱,他家平常吃烤過的玉米粉(gaude)、馬鈴薯、蔬菜湯,吃得「又高又壯」,但以這些食物為主食,大概會長不高且體弱多病。在回憶錄或遺囑「撫養費」(pensions alimentaires)裡提及的許多日常飲食,缺乏維生素和蛋白質的攝取,久而久之會要人命。在某些例子裡,熱量幾乎全來自做成麵包的穀類食物。但研究證實,普魯東也和他所照料的乳牛一樣,一天裡有許多時間在嚼食植物,用玉米、嬰粟籽、豌豆、匍匐風鈴草、波羅門參、櫻桃、葡萄、玫瑰果、黑刺莓、黑刺李祭五臟廟。在法國境內較溫暖的地區,拿來打牙祭的食物營養成分可能比較高。在亞維儂附近,佩迪吉耶大啖梨子、葡萄、杏子、無花果,還有許多種他已無法用法語講出名字的野生水果。一八六二年全法國有超過三百萬個蜂巢(每十三個居民有一蜂巢),表示當時的日常食物並非總是如今人印象中那麼貧乏。在菜色單調的地區,將?桲裹上蜂蜜,再放在餘燼裡烤過,可能就是令人難忘的美食。(待續)在工業式農業使穀類席捲全國之前,可食植物和動物的種類和數量都較多。伊拉提森林那位健壯的野人,似乎一直是個素食者。在聖塞爾南(Saint-Sernin)附近被捕的「阿韋龍的維克托」,可能吃過雞肉、鴨肉、淡水螫蝦,但大概沒吃過如今聖塞爾南旅館「野小孩菜單」(Menu de l’Enfant Sauvage)上所列的其他菜(羅克福爾乳酪、舒芙蕾凍糕、胡桃酒)。一七三一年在香檳地區松吉(Songy)附近被人發現的野女童蔓米(Memmie),靠生吃兔肉、青蛙過活,她也吃樹葉與根莖,會用結實的拇指、食指到處挖。
如今,觀光客到富饒的農業地區旅遊,吃到的卻是牛排薯條和淋上點油的乾枯萵苣,店家也絲毫不覺有對不起的意思。這種現象其實是百年來所造成的結果。隨著鐵路將觀光客快速送到鄉間,將農產品送往城市,法國的美食地圖似乎頓時生機勃勃。在巴黎雜誌上撰寫地理文章的作家,對各地區的特色美食猛流口水:來自伊錫尼(Isigny)的奶油、科佩伊的蘋果、蒙莫朗西(Montmorency)的櫻桃、拉翁的朝鮮薊、第戎的芥茉和黑醋栗甜酒(cassis)、佩里戈爾的松露、圖爾和阿讓(Agen)的李子乾、巴約訥的巧克力。這些特產裡,有一些名產並不能代表一個地區的精神,只是反映了某食品雜貨店的宣傳技倆。過去,它們鮮少出現於觀光客的餐盤上,且未必可在該地區吃到。第戎地區原本並不盛產黑醋栗,直到一八四一年,當地有位富創業心的咖啡店老闆到巴黎考察市場,注意到黑醋栗甜酒很受歡迎,開始把他自產的黑醋栗甜酒當該地特產推銷,第戎才開始盛產。在種葡萄兼釀葡萄酒的地區,好葡萄酒往往反而難尋。法國葡萄酒的鑑賞家,在倫敦、巴黎或圖爾(因有大量英格蘭僑民),比在法國鄉間收入更好。在法國鄉間,喝得起葡萄酒的人,用餐時較喜歡搭配渣釀白蘭地(eau de marc,用釀製葡萄酒過程中留下的糊狀葡萄渣提餾出的烈酒)。
被餐飲業者和雜貨商運到巴黎銷售的食物,創造出鄉間虛幻不實的形象。在帕莉塞夫人(Mme Pariset)《家庭主婦新完全持家手冊》(Nouveau manuel complet de la maitresse de maison,1852)的食譜一節中,主要材料顯然在巴黎的一般家庭裡就有,頂多請女僕到中央市場去採買。她的食譜要人用來自艾克斯的橄欖油、勃艮第的玉米粉、布列塔尼的去殼燕麥,史特拉斯堡培根和格呂耶爾(Gruyere)乳酪,不過食譜裡的菜——相當樸實的蔬菜燉肉和用大量甘藍菜煮的湯——不是發源自法國鄉間,而是來自「最上等的餐桌」。
最上等的餐桌幾乎全在巴黎。據說,一八八九年,巴黎市內每一百家餐廳才有一家書店。「巴黎的牙祭之旅,在過去大概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如今卻幾乎和環遊世界一樣久。」許多「地方」美食是從巴黎傳到地方。農民小說家紀堯曼(Emile Guillaumin)筆下的波旁內一家人,看到來訪的巴黎親戚蹲在池塘邊,抓起青蛙丟進袋子裡,大為驚駭(一八八○年):「沒人知道怎麼料理青蛙,侄子只好自己煮煮看。」
外國觀光客入境百年之後,才有大批法國男女開始親自去發掘法國。但即便如此,大部分的饕客仍偏愛到巴黎餐廳探索各地美食。有個法國人當時就做了一趟最啟發人心的發現之旅,就是大仲馬一八六九年在布列塔尼北海岸羅斯科夫的旅行。當時羅斯科夫是法國西部商品蔬菜栽培業的龍頭城市。一八六○年代,每年有數百艘船載著洋蔥和朝鮮薊離開這小港到英國,顯然是因為曾經有個大膽的傢伙在倫敦拿著「英格蘭洋蔥不好」的板子,結果成功將洋蔥銷售出去。不過當大仲馬定居羅斯科夫寫《菜餚大辭典》(Le Grand Dictionnaire de Cuisine)時,靈感多得自想像力,而不是食物:「盛產魚,但此外沒什麼東西:硬如子彈的朝鮮薊、水水的菜豆、不新鮮的奶油。」他的廚師瑪麗事前就斷言,這次遠行只會空手而回。她忿忿離開,回去可發現並享用到法國所有奇特美食的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