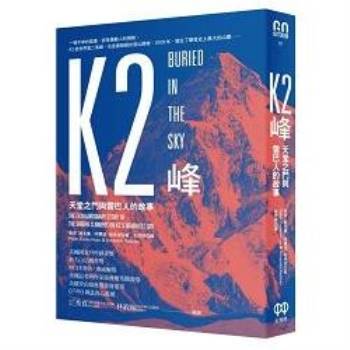【前言】
死亡地帶THE DEATH ZONE
巴基斯坦K2峰瓶頸路段
死亡地帶:海拔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度
懸掛在峭壁上,與死亡之間只有一把冰斧,一位名叫麒麟.多杰(Chhiring Dorje)的雪巴人往左盪去。從上方山壁脫落的巨大冰塊,快速朝他衝來。
和冰箱一樣大的冰塊。
冰塊的一側撞上山壁。這個龐然大物像車輪一樣滾下來,擦過麒麟的身邊,幾乎掃過他的肩膀,在下方消失了蹤影。
砰。它撞上下方某個東西,四分五裂。
衝擊震動了山峰,冰塵直衝上來。
那時大約是2008年8月1日的午夜,麒麟只模糊地知道自己的大略位置:他在K2的瓶頸路段(Bottleneck)之上或附近。瓶頸路段是世界上最危險山峰上、最致命的一段路。它位於接近波音七三七飛翔的高度,從麒麟身處的地點往下方的暗夜延伸。星光下,瓶頸散發出一縷縷往深淵處滲去的霧氣,這通道似乎沒有終點。它上方的冰捲曲得像是壓人的浪。
麒麟的大腦因為缺氧而呆滯,飢餓和疲勞幾乎摧毀他的身體,只要張開嘴,舌頭就結凍;他喘著氣,任由乾燥的空氣刷搓喉嚨、鞭打雙眼。
麒麟的動作很遲緩,他覺得寒冷又疲倦,已經沒有力氣回想自己為了攀登K2而犧牲了什麼。這位已經登頂聖母峰十次的雪巴登山者,數十年來心中揮之不去的,就是攀登K2的念頭。K2遠比聖母峰更困難,它是高海拔登山領域中最神聖的獎品。麒麟來到這裡了,儘管他的妻子流著眼淚,儘管登山的花費超過父親四十年的收入,儘管喇嘛警告他:K2之神不會容忍這次的攀登。
麒麟在那天傍晚站上K2峰頂,他沒有使用氧氣。無氧登頂K2足以讓他躋身世界最成功的精英登山者行列,但是下山時卻出現計畫外的狀況。他曾經夢想過這份成就、英雄式的歡迎,甚至名氣,但現在什麼都不重要了。麒麟有妻子、兩個女兒、蒸蒸日上的生意,以及十幾個倚賴他維生的親戚。他現在只想回家,活著回家。
一般來說,下山應該要比現在的情況還要安全些。攀登者通常在午後不久,趁著氣溫較暖,尚有日光可以看路的時候下撤。他們利用固定繩垂降,控制下降的速度,越過大片的冰。攀登者會儘快通過瓶頸附近容易發生雪崩的路段,減少暴露時間,降低被雪掩埋的機率。快速下降是麒麟原本的計畫。現在四周闇黑,早先的落冰切斷了繩索。固定繩不見了,他不可能回頭。他只能仰賴冰斧來制動。這還牽涉到另外一條人命:繫在麒麟吊帶上的另一個攀登者。
位於麒麟下方的男人名叫巴桑.喇嘛(Pasang Lama)。三個小時之前,巴桑為了幫助更無助的攀登者,放棄了自己的冰斧。因為他和麒麟一樣,原本打算使用固定繩垂降下山。
當巴桑發現瓶頸路段上的繩索消失了,他認為自己的死期到了。如果沒有他人的幫助,困在這裡的巴桑哪裡也去不了。但他想不出誰會試圖拯救他。任何願意和巴桑繫在一起的攀登者,將面對極大的滑墜風險。要獨自使用一隻冰斧滑下瓶頸,都已經是件不可能的任務,何況再加上另一個人的重量。巴桑想著,對他展開救援行動無異是自殺,任何務實的人都會坐視他的死亡。
如他所料,已經有個雪巴略過他下山了。巴桑假設麒麟也會略過他自行下山。麒麟和巴桑隸屬不同的團隊,沒有義務對巴桑伸出援手。現在,巴桑懸在麒麟下方不到三公尺的地方,兩人之間用條小繩連接著。
躲過冰塊之後,兩人都低下頭,默默與山神協商。幾秒鐘之後,山神回應了,發出電子音效般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是彈撥橡皮筋的聲音被失真效果器放大了。咻。聲音持續不斷,回音則愈來愈大、愈長、愈快、愈低沉,聲音從左邊來,又從右邊來。攀登者知道這聲音背後的意義:他們周圍的冰正在碎裂。每一道咻咻聲,就是冰川上一道曲折的裂痕,冰川準備要釋放冰塊了。
當感到冰塊接近時,這兩個人可以稍稍移到旁邊,或是扭曲一下身體來閃躲。若是沒躲過,砸一下也忍得過去。只是冰川遲早會放出像巴士一樣大的冰塊,屆時除了祈禱,恐怕也沒有其他的辦法。麒麟和巴桑必須在冰塊砸死他們之前,下撤到安全的地方。
喳一聲,麒麟將冰斧劈進冰裡。他接著往前踢,嗤的一聲,縛在登山靴下的冰爪刺入冰中。他這樣下降了一、兩公尺—喳、嗤、嗤、喳、嗤、嗤—將自己卡在斜坡上,讓與他繫在一起的人可以用一樣的韻律來移動。巴桑用拳頭擊打堅硬的冰,試圖做出可以抓的手點。但是這個點又淺又光滑,幾乎承受不了他的體重。每當巴桑的腿往下伸展,他與麒麟間的小繩便會被拉緊,直到踢進冰爪,才會解除小繩上的壓力。安全小繩上的受力幾乎把麒麟帶離山壁,但他成功地讓自己牢牢掛在山壁上,小心翼翼地繞過冰壁的外突處、裂隙地帶、凹陷處,以及突出的小冰塊。有時候他和巴桑必須肩並肩,手牽手,協調彼此的動作。有時候巴桑先走,麒麟會用冰斧將自己固定在冰壁上的一個好位置,控制連接兩人的安全小繩。
石頭、冰塊落在他們的身上,砸向他們的頭盔,但是他們已經下降了一半的路段,也認為自己會活下來。那天晚上沒有風,氣溫為攝氏零下二十度,以K2的標準來看,算是溫和的天氣。他們看到下方最高營地熠熠生輝的燈光。麒麟和巴桑沒料到接下來要發生的事。
不知道是冰還是落石敲中巴桑的頭,他開始搖晃。
他的身體重重拉扯兩人之間的小繩,將麒麟拉離冰壁。
兩人往下墜落。
麒麟用兩手抓住冰斧,猛力朝山壁揮動。但冰斧的利刃怎麼也抓不住山壁。它像把手術刀從雪上切過。
下滑得更快了,麒麟提起胸膛抵住冰斧的扁頭,往斜坡的方向鑿去。沒有用,麒麟又滑墜了七公尺,之後是十公尺。
巴桑用拳頭擊打斜坡,試圖抓住東西,卻只是徒勞地讓手指滑過冰粒。
兩人朝黑暗滑墜得更遠。
他們的尖叫聲必定通過瓶頸的集聲地形,傳到山峰的東南面,但是在那兒的倖存者什麼都沒有聽到,他們對人體墜落的轟隆聲已經無感,他們全都迷路了。他們感到茫然,開始產生幻覺。有的人偏離了路線,有的人則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以便在兩個都不怎麼樣的選項中,仔細挑出一個:冒險在黑夜下攀通過瓶頸路段,還是在死亡地帶露宿等待天明。
幾個小時前,第一個登頂K2的愛爾蘭人杰爾.麥克唐納(Ger McDonnell)在斜坡上砍出一個能供他坐下的小平台。耐心等待是無法抵抗雪崩的,但至少今晚他有個棲息之所。
擠在他身邊的是義大利籍攀登者馬可.孔福爾托拉(Marco Confortola)。兩人強迫自己唱歌來保持清醒:他們用沙啞的聲音,低聲吟唱記得的歌曲,任何可以防範他們因沉睡而死亡的歌曲。再早些,一位法國的攀登者在山頂上對女友許下諾言。「我再也不會離開妳,」休斯.迪奧巴雷德(Hughes D’Aubarede)在衛星電話上對女友說,「現在,我完成了。明年此時,我們都會在沙灘上。」那天晚上,他從瓶頸滑落,喪失了生命。休斯雇用的巴基斯坦籍高海拔協作員卡里姆.馬赫本走偏了路線,到達籠罩在瓶頸之上的冰冠,他在那兒倒下來等著凍死。
再往下走,幾噸冰塊帶走了一位挪威籍新婚女子的丈夫。這次攀登是他們的蜜月旅行,現在,只剩她獨自下山。
這裡許多人自認是世界級的攀登者。他們從法國、荷蘭、義大利、愛爾蘭、尼泊爾、挪威、巴基斯坦、塞爾維亞、南韓、西班牙、瑞典和美國來到這裡。有些人已經為攀登K2犧牲了一切。他們這次的攀登演變成災難,最後的結果甚是慘淡:在二十七小時之內,有十一位攀登者罹難。是K2攀登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山難。
哪裡出了錯?為什麼攀登者明知道來不及在夜幕降臨前下撤,還是繼續往上走?為什麼他們犯下一個個看似簡單的錯誤,包括沒有帶夠繩索?
這個故事成為國際媒體寵兒,登上《紐約時報》、《國家地理探險》雜誌、《戶外》雜誌的頭版,以及其他數以千計的刊物。眾多部落客輪番上陣談論這個故事,帶起眾人的揣測,然後是紀錄片、舞台劇、回憶錄和電視脫口秀。
有人認為這個故事是傲慢的範例,自視過高加上瘋狂,導致的生命浪費:追求刺激者用盡全力,就為了得到贊助商的注意;瘋子把攀登當作逃避現實的最後一招;漠視他人的西方人為了自身的榮耀,利用貧困的尼泊爾人和巴基斯坦人;贊助商以及媒體利用死者,增加報紙和產品的銷量;等著看好戲的人把觀察這景象當作娛樂。
「你想要冒生命危險?」有則《紐約時報》的讀者回覆這樣寫著,「那麼你應該為國家、家庭或是社區冒這個險。攀登K2或是聖母峰只是自私的行為,對什麼都無益處的行為。」
「英雄,我的屁英雄,」另一個人語帶不屑,「……這些自大狂應該離山遠遠的。」
有些人看到了勇氣:探險者與大自然的不可測對立;迷失的靈魂冒著巨大風險,在這個空虛的世界裡尋找意義。
「攀登能夠擴展我們看待人類潛能的眼光,」美國登山協會(American Alpine Club)執行董事菲爾.鮑爾斯(Phil Powers)寫給媒體的信上這麼說著。另一封信改寫老羅斯福總統(Teddy Roosevelt)曾說過的話,「去挑戰強大的目標,嘗試贏得光輝的勝利,就算最後被人視作失敗者,依舊遠比與那些不知享受、或是受苦的可憐靈魂為伍來得好,因為那些人不過就是生活在既不懂勝利、也不懂挫敗的灰暗裡。」
有人則提出了基本問題:在山上等死的那些人,究竟在做什麼?這些人受了什麼驅動,才會冒這樣的風險?在他們受困於山頂之前;在死亡與喪禮之前;在搜救與重聚之前;在格鬥與友誼之前;在相互指責與和解之前—一切看似完美。裝備,檢查又檢查;路線,建立了;天氣,很合作;團隊,一致且完整。那個讓他們花費無數時間訓練以及金錢的日子終於來臨。他們準備登上K2,站在地球上最險惡的山頂上,勝利吶喊,展開旗幟,打電話給所愛的人。
麒麟和巴桑,在他們墜入暗夜的時候,必定在想著: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
死亡地帶THE DEATH ZONE
巴基斯坦K2峰瓶頸路段
死亡地帶:海拔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度
懸掛在峭壁上,與死亡之間只有一把冰斧,一位名叫麒麟.多杰(Chhiring Dorje)的雪巴人往左盪去。從上方山壁脫落的巨大冰塊,快速朝他衝來。
和冰箱一樣大的冰塊。
冰塊的一側撞上山壁。這個龐然大物像車輪一樣滾下來,擦過麒麟的身邊,幾乎掃過他的肩膀,在下方消失了蹤影。
砰。它撞上下方某個東西,四分五裂。
衝擊震動了山峰,冰塵直衝上來。
那時大約是2008年8月1日的午夜,麒麟只模糊地知道自己的大略位置:他在K2的瓶頸路段(Bottleneck)之上或附近。瓶頸路段是世界上最危險山峰上、最致命的一段路。它位於接近波音七三七飛翔的高度,從麒麟身處的地點往下方的暗夜延伸。星光下,瓶頸散發出一縷縷往深淵處滲去的霧氣,這通道似乎沒有終點。它上方的冰捲曲得像是壓人的浪。
麒麟的大腦因為缺氧而呆滯,飢餓和疲勞幾乎摧毀他的身體,只要張開嘴,舌頭就結凍;他喘著氣,任由乾燥的空氣刷搓喉嚨、鞭打雙眼。
麒麟的動作很遲緩,他覺得寒冷又疲倦,已經沒有力氣回想自己為了攀登K2而犧牲了什麼。這位已經登頂聖母峰十次的雪巴登山者,數十年來心中揮之不去的,就是攀登K2的念頭。K2遠比聖母峰更困難,它是高海拔登山領域中最神聖的獎品。麒麟來到這裡了,儘管他的妻子流著眼淚,儘管登山的花費超過父親四十年的收入,儘管喇嘛警告他:K2之神不會容忍這次的攀登。
麒麟在那天傍晚站上K2峰頂,他沒有使用氧氣。無氧登頂K2足以讓他躋身世界最成功的精英登山者行列,但是下山時卻出現計畫外的狀況。他曾經夢想過這份成就、英雄式的歡迎,甚至名氣,但現在什麼都不重要了。麒麟有妻子、兩個女兒、蒸蒸日上的生意,以及十幾個倚賴他維生的親戚。他現在只想回家,活著回家。
一般來說,下山應該要比現在的情況還要安全些。攀登者通常在午後不久,趁著氣溫較暖,尚有日光可以看路的時候下撤。他們利用固定繩垂降,控制下降的速度,越過大片的冰。攀登者會儘快通過瓶頸附近容易發生雪崩的路段,減少暴露時間,降低被雪掩埋的機率。快速下降是麒麟原本的計畫。現在四周闇黑,早先的落冰切斷了繩索。固定繩不見了,他不可能回頭。他只能仰賴冰斧來制動。這還牽涉到另外一條人命:繫在麒麟吊帶上的另一個攀登者。
位於麒麟下方的男人名叫巴桑.喇嘛(Pasang Lama)。三個小時之前,巴桑為了幫助更無助的攀登者,放棄了自己的冰斧。因為他和麒麟一樣,原本打算使用固定繩垂降下山。
當巴桑發現瓶頸路段上的繩索消失了,他認為自己的死期到了。如果沒有他人的幫助,困在這裡的巴桑哪裡也去不了。但他想不出誰會試圖拯救他。任何願意和巴桑繫在一起的攀登者,將面對極大的滑墜風險。要獨自使用一隻冰斧滑下瓶頸,都已經是件不可能的任務,何況再加上另一個人的重量。巴桑想著,對他展開救援行動無異是自殺,任何務實的人都會坐視他的死亡。
如他所料,已經有個雪巴略過他下山了。巴桑假設麒麟也會略過他自行下山。麒麟和巴桑隸屬不同的團隊,沒有義務對巴桑伸出援手。現在,巴桑懸在麒麟下方不到三公尺的地方,兩人之間用條小繩連接著。
躲過冰塊之後,兩人都低下頭,默默與山神協商。幾秒鐘之後,山神回應了,發出電子音效般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是彈撥橡皮筋的聲音被失真效果器放大了。咻。聲音持續不斷,回音則愈來愈大、愈長、愈快、愈低沉,聲音從左邊來,又從右邊來。攀登者知道這聲音背後的意義:他們周圍的冰正在碎裂。每一道咻咻聲,就是冰川上一道曲折的裂痕,冰川準備要釋放冰塊了。
當感到冰塊接近時,這兩個人可以稍稍移到旁邊,或是扭曲一下身體來閃躲。若是沒躲過,砸一下也忍得過去。只是冰川遲早會放出像巴士一樣大的冰塊,屆時除了祈禱,恐怕也沒有其他的辦法。麒麟和巴桑必須在冰塊砸死他們之前,下撤到安全的地方。
喳一聲,麒麟將冰斧劈進冰裡。他接著往前踢,嗤的一聲,縛在登山靴下的冰爪刺入冰中。他這樣下降了一、兩公尺—喳、嗤、嗤、喳、嗤、嗤—將自己卡在斜坡上,讓與他繫在一起的人可以用一樣的韻律來移動。巴桑用拳頭擊打堅硬的冰,試圖做出可以抓的手點。但是這個點又淺又光滑,幾乎承受不了他的體重。每當巴桑的腿往下伸展,他與麒麟間的小繩便會被拉緊,直到踢進冰爪,才會解除小繩上的壓力。安全小繩上的受力幾乎把麒麟帶離山壁,但他成功地讓自己牢牢掛在山壁上,小心翼翼地繞過冰壁的外突處、裂隙地帶、凹陷處,以及突出的小冰塊。有時候他和巴桑必須肩並肩,手牽手,協調彼此的動作。有時候巴桑先走,麒麟會用冰斧將自己固定在冰壁上的一個好位置,控制連接兩人的安全小繩。
石頭、冰塊落在他們的身上,砸向他們的頭盔,但是他們已經下降了一半的路段,也認為自己會活下來。那天晚上沒有風,氣溫為攝氏零下二十度,以K2的標準來看,算是溫和的天氣。他們看到下方最高營地熠熠生輝的燈光。麒麟和巴桑沒料到接下來要發生的事。
不知道是冰還是落石敲中巴桑的頭,他開始搖晃。
他的身體重重拉扯兩人之間的小繩,將麒麟拉離冰壁。
兩人往下墜落。
麒麟用兩手抓住冰斧,猛力朝山壁揮動。但冰斧的利刃怎麼也抓不住山壁。它像把手術刀從雪上切過。
下滑得更快了,麒麟提起胸膛抵住冰斧的扁頭,往斜坡的方向鑿去。沒有用,麒麟又滑墜了七公尺,之後是十公尺。
巴桑用拳頭擊打斜坡,試圖抓住東西,卻只是徒勞地讓手指滑過冰粒。
兩人朝黑暗滑墜得更遠。
他們的尖叫聲必定通過瓶頸的集聲地形,傳到山峰的東南面,但是在那兒的倖存者什麼都沒有聽到,他們對人體墜落的轟隆聲已經無感,他們全都迷路了。他們感到茫然,開始產生幻覺。有的人偏離了路線,有的人則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以便在兩個都不怎麼樣的選項中,仔細挑出一個:冒險在黑夜下攀通過瓶頸路段,還是在死亡地帶露宿等待天明。
幾個小時前,第一個登頂K2的愛爾蘭人杰爾.麥克唐納(Ger McDonnell)在斜坡上砍出一個能供他坐下的小平台。耐心等待是無法抵抗雪崩的,但至少今晚他有個棲息之所。
擠在他身邊的是義大利籍攀登者馬可.孔福爾托拉(Marco Confortola)。兩人強迫自己唱歌來保持清醒:他們用沙啞的聲音,低聲吟唱記得的歌曲,任何可以防範他們因沉睡而死亡的歌曲。再早些,一位法國的攀登者在山頂上對女友許下諾言。「我再也不會離開妳,」休斯.迪奧巴雷德(Hughes D’Aubarede)在衛星電話上對女友說,「現在,我完成了。明年此時,我們都會在沙灘上。」那天晚上,他從瓶頸滑落,喪失了生命。休斯雇用的巴基斯坦籍高海拔協作員卡里姆.馬赫本走偏了路線,到達籠罩在瓶頸之上的冰冠,他在那兒倒下來等著凍死。
再往下走,幾噸冰塊帶走了一位挪威籍新婚女子的丈夫。這次攀登是他們的蜜月旅行,現在,只剩她獨自下山。
這裡許多人自認是世界級的攀登者。他們從法國、荷蘭、義大利、愛爾蘭、尼泊爾、挪威、巴基斯坦、塞爾維亞、南韓、西班牙、瑞典和美國來到這裡。有些人已經為攀登K2犧牲了一切。他們這次的攀登演變成災難,最後的結果甚是慘淡:在二十七小時之內,有十一位攀登者罹難。是K2攀登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山難。
哪裡出了錯?為什麼攀登者明知道來不及在夜幕降臨前下撤,還是繼續往上走?為什麼他們犯下一個個看似簡單的錯誤,包括沒有帶夠繩索?
這個故事成為國際媒體寵兒,登上《紐約時報》、《國家地理探險》雜誌、《戶外》雜誌的頭版,以及其他數以千計的刊物。眾多部落客輪番上陣談論這個故事,帶起眾人的揣測,然後是紀錄片、舞台劇、回憶錄和電視脫口秀。
有人認為這個故事是傲慢的範例,自視過高加上瘋狂,導致的生命浪費:追求刺激者用盡全力,就為了得到贊助商的注意;瘋子把攀登當作逃避現實的最後一招;漠視他人的西方人為了自身的榮耀,利用貧困的尼泊爾人和巴基斯坦人;贊助商以及媒體利用死者,增加報紙和產品的銷量;等著看好戲的人把觀察這景象當作娛樂。
「你想要冒生命危險?」有則《紐約時報》的讀者回覆這樣寫著,「那麼你應該為國家、家庭或是社區冒這個險。攀登K2或是聖母峰只是自私的行為,對什麼都無益處的行為。」
「英雄,我的屁英雄,」另一個人語帶不屑,「……這些自大狂應該離山遠遠的。」
有些人看到了勇氣:探險者與大自然的不可測對立;迷失的靈魂冒著巨大風險,在這個空虛的世界裡尋找意義。
「攀登能夠擴展我們看待人類潛能的眼光,」美國登山協會(American Alpine Club)執行董事菲爾.鮑爾斯(Phil Powers)寫給媒體的信上這麼說著。另一封信改寫老羅斯福總統(Teddy Roosevelt)曾說過的話,「去挑戰強大的目標,嘗試贏得光輝的勝利,就算最後被人視作失敗者,依舊遠比與那些不知享受、或是受苦的可憐靈魂為伍來得好,因為那些人不過就是生活在既不懂勝利、也不懂挫敗的灰暗裡。」
有人則提出了基本問題:在山上等死的那些人,究竟在做什麼?這些人受了什麼驅動,才會冒這樣的風險?在他們受困於山頂之前;在死亡與喪禮之前;在搜救與重聚之前;在格鬥與友誼之前;在相互指責與和解之前—一切看似完美。裝備,檢查又檢查;路線,建立了;天氣,很合作;團隊,一致且完整。那個讓他們花費無數時間訓練以及金錢的日子終於來臨。他們準備登上K2,站在地球上最險惡的山頂上,勝利吶喊,展開旗幟,打電話給所愛的人。
麒麟和巴桑,在他們墜入暗夜的時候,必定在想著: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