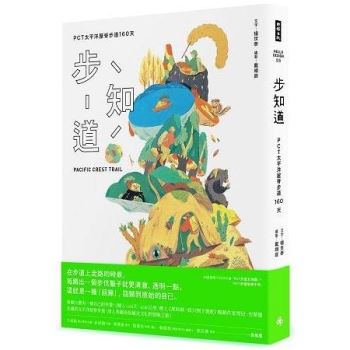第1章、站上起點之前
在決定挑戰太平洋屋脊步道的當下,也就是我興奮地坐在辦公室跟呆呆訊息熱線的時候,其實就有意識到該做的準備一定非常繁雜,畢竟據我們所知,在全球華人之中,也只有一位來自中國目前在德州求學的年輕女孩張諾婭在二O一四年走完全程。這還是我從維基百科查到的資訊,否則剛開始,我甚至以為這條熱門的路線肯定已有很多台灣人走過。
也就是說,我們無法像在台灣登山一樣,上網輸入幾個關鍵字,馬上就能找到一堆網友分享的遊記或是參考價值很高的行程規劃。沒有,完全沒有,只有幾篇零星的文章提到這條路線,而且大多是電影《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的影評心得。雖然熱心的張諾婭已在網路提供了很多實用資訊,但做計劃一向謹慎又龜毛的我其實還是非常焦慮。
我自認是個態度悠哉的人,但每次跟呆呆出國旅行,總習慣在手機上標注幾點幾分到哪個餐廳吃飯?要逛哪間戶外用品店?巨細靡遺地規劃好所有細節,即使時間還很充裕,也會不自覺地想要按表操課,下場當然就是把兩個人都累垮。這種強迫症的個性可能來自家人的影響。記得小時候每次家庭旅遊,在出發前一個星期,就看到他們老早把所有行李都打包完畢,逼得我不做點什麼也不行。還好婚後呆呆的步調比較緩慢,讓我急躁的個性緩和許多。
但太平洋屋脊步道畢竟是全然陌生的環境,況且還得走上那麼久的時間,現有的資訊根本不足以解答我對步道的疑惑。一天要走幾公里?走幾天後要到哪個城鎮補給?吃什麼?穿什麼?用什麼?當地的溫差有多少?海拔多高?天黑的時間是幾點?類似這樣的問題不斷在腦海裡打轉,完全沒辦法靜下來計劃細節。於是我買下所有可以到手的英文指南和地圖,一頁一頁慢慢地讀,用標籤貼紙記下重點,在書頁上劃上記號,同時在網路瘋狂搜尋各種相關資訊。結果弄巧成拙,各種陌生名詞和地名反而讓人更無所適從。
一直到走上步道一段時間後,才瞭解這種周全的計劃並不適用這麼長時間的旅行。突發的大雪或森林火災導致道路封閉,經過有毒植物和動物保護區需要另外繞道,還有各種無法預期的狀況,像是體力衰退、運動傷害⋯⋯等等,每個變數都有可能導致旅行的延宕,甚至中斷。
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徒步計劃準備時間可長可短,有人三天內就決定出發,也有人花了數年的評估才付諸行動,但一般來說平均需要四到五個月的時間。準備事項包含擬定徒步計劃、設定補給點、採買合適的裝備和服飾、申請各式許可證和美國觀光簽證,以及一連串的體能訓練或戶外技能訓練。
按照常理,為了專心準備而辭掉工作的我,絕對有充足的時間應付這些瑣事。我甚至想像自己一天的行程會是早上出去晨跑,接著做重量訓練,然後在家裡專心地研究步道的資料。等到出發的那一天,我會是一個強壯、精神奕奕又滿腹求生知識的真男人,隨時都能幫呆呆扛起她負荷不了的裝備,大步大步地往山裡走去。結果現實並非如我想像得那麼美好,大部份時間我都是坐在電腦前打字,為第一本書《山知道》日夜趕稿,甚至連瘦身的目標也悄悄放棄,率性地把自己吃胖到人生體重的巔峰。
寫書這件事從來沒有出現在我的生涯規劃裡,如同走上太平洋屋脊步道這個決定,兩者都開啟了另一扇窗,讓原本平淡的生活多了一點刺激和改變。而其中一個意外收穫是,為了宣傳《山知道》而設立的臉書專頁,竟然讓我們找到計劃在同一年出發的台灣人。這感覺就像美國太空總署發射的旅行者號(Voyager)太空船,在漫長航行後與光年之遙的外星人接觸,那張錄下「地球之聲」的鍍金唱片終於被聽見了。
「原來我們並不孤單!」我興奮地跟呆呆分享這個好消息。
透過臉書我們跟Alex搭上線,很快就約好在咖啡廳碰面,聊天後才曉得他也是半年前就計劃要走太平洋屋脊步道,只是礙於工作的關係,遲遲沒有真的下定決心,連機票跟簽證都尚未辦妥。相較另外兩位常常一起登山露營的好朋友——吉米跟小又,很早就決定跟我和呆呆組隊,從起點出發徒步約一千兩百公里,直到登上美國本土最高峰的惠特尼山頂(Mt. Whitney)後才各自解散,他們兩人會飛回台灣,而我跟呆呆則繼續往加拿大前進。吉米跟小又只走某一路段的方式,在美國有個術語叫「分段徒步」(Section-Hike),而打算從頭走到尾的人則稱為「全程徒步」(Thru-Hike)。每年有上千人挑戰全程徒步,但順利走到終點的人可能不到三成。
從決心要走太平洋屋脊步道以來,一直以為我們這對夫妻檔是台灣唯二的挑戰者,老實說心裡其實是有一點驕傲和興奮的。即使連名義上的第一步都尚未踏出,但我們已經把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付諸行動,當然會想要為自己喝彩;但同時,我們也會擔心、害怕,對自己沒有信心,對未知充滿恐懼。雖然有很多前輩建議,長程徒步最好是單獨出發,那些成群結隊的,通常不到半途就會四分五裂。步伐不同,理念也會不同,即使跟最親密的人結伴同行也不見得能相處融洽。但可能潛意識裡我是個膽小鬼吧,就像走進烏漆抹黑的地方會想張開雙手尋找任何可以碰觸的東西,不確定能夠抓到什麼,但至少心裡會覺得踏實許多。不管如何,在人生地不熟的環境,有個夥伴能夠互相照應總是讓人比較心安。
大概是我跟呆呆的極力慫恿成功,Alex最後還是決定出發了。他在搞定機票、簽證和工作後就先飛到美國的叔叔家,位於洛杉磯市區東邊約二十公里,總人口數近六萬,是一座很多亞洲人移民定居的中型城市「阿凱迪亞」(Arcadia),距離南邊的步道起點還有三個小時車程。呆呆的老同學子敏也住在那邊,她二話不說,很早就義氣地答應幫我們寄送包裹和補給裝備,擔任我們此行最重要的補給人角色。我跟呆呆、吉米和小又一行四人跟Alex約好在阿凱迪亞碰面,在出發日前幾天利用空檔採購食物跟裝備,也順便調整時差並適應當地的氣候。
飛到美國的前一晚,我們跟家裡的貓咪還有家人道別。兩隻已屆歐巴桑年齡的小貓,跟往常一樣窩在習慣的位置,牠們不會明白我們即將要踏上的旅程有多麽艱辛,只是瞪大眼睛站得遠遠地看呆呆把門關上。貓真是個奇怪的生物,對愛的需求很獨裁,也許這就是牠們總是姿態優雅的緣故。相較之下,父母親對我們遠行的態度可就不像貓咪那麼平淡,特別是我的母親,可以感受到她壓抑著自己對兒子和媳婦的憂心,知道我出發前很煩躁,都半夜了還在整理去美國的資料和文件,所以把嘮叨的話都藏在心裡,只簡單說了幾句。
「出門在外,自己要注意安全跟健康。要把翊庭顧好,她是你老婆,照顧她是你身為丈夫的責任。」停頓一下,又補了一句。「如果覺得很累就找地方多休息幾天,不要勉強自己。」
「我知道啦,如果真的累了不想走,我們會去搭計程車的,妳放心啦!」我用開玩笑的語氣安撫她,告訴她這條步道很安全,請不用為兒子擔心。但其實我把路上會遇到的最糟狀況都過濾掉了,而且事實上,在偏僻的步道周圍根本沒有像樣的大眾運輸系統,身為徒步旅行者,唯一可以搭乘的交通工具是路人的便車。
當機場接送的廂型車開進家裡的院子,時間是半夜兩點,母親和二姊幫我們把行李搬到車上。小時候她常跟我說,每次回娘家,老遠就看到外婆站在巷口等著大夥團聚,那殷切盼望一家團聚的身影深深烙印在她的腦海裡。後來外婆走了,我媽也老了,她扮演起一樣的角色,每當我要離開家裡,不管去的地方距離多遠,她一定堅持站在門口和我說再見。那天晚上,因為忙到幾乎沒有睡覺所以記憶非常模糊,所以不記得有沒有抱著和她道別,但我永遠都不會介意再給她一次緊緊的擁抱。
四月十八日,在我生日隔天,我們抵達加州的洛杉磯國際機場。上一次入境美國是大學剛畢業那年,跟朋友到東岸的紐約體驗一個月的背包客生活。接下來的十二年間,我再也沒去過那麼遠的地方,也沒有離開台灣那麼久的時間。如今再度踏上美國的土地,除了親切,還多了一股懷念。
「到美國這麼久的時間要做什麼?觀光需要這麼久的時間嗎?」入境的時候,一位亞裔海關人員一邊檢查證件一邊試著了解此行的目的。畢竟我們持有的B2觀光簽證,跟一般入境使用的電子簽證不一樣,所以他花了比較多時間「盤查」我們的底細。
「我們是來健行的。」我指著我身後的大背包,「我們要去走太平洋屋脊步道,PCT,你知道嗎?電影有演,我們要花六個月時間從墨西哥走到加拿大。」我預期他會瞪大眼睛,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二六五O英哩,這就是我們要走的距離。」通常說出這條步道的總長度時,總會聽到幾聲讚嘆和崇拜,這時心裡就會有一種輕飄飄的虛榮感。但明明連一英哩都還沒完成。
「不,我沒聽過。」他的神情帶有幾分歉意,但隨即又露出挖苦的表情笑著說:「這世界上步道這麼多,為什麼偏偏要選這條?我們加州山上有很多響尾蛇,很危險的。」
其實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一直以來這個問題我都不曉得正確答案是什麼。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會這麼毅然辭掉穩定的工作,挑戰這樣一條又長又困難,需要花上半年時間準備,然後再用另外半年光陰才能走完的步道?這問題在腦子裡縈繞好多回,隨著出發的時間慢慢逼近,一直沒有可以說服自己和其他人的滿意答案。當然不是「因為它在那裡」,也不是「想要找回自己」,或許有更複雜、更難以解釋的念頭隱藏在那層薄霧後面。又或許想做一件事情其實不需要什麼理由,心裡就是突然有什麼東西被觸碰了、被揪起了、被點燃了,驅使我跟呆呆踏上這條命中註定的道路,過往經歷的一切,彷彿都是為了此刻而準備。
「大概是因為美國比較安全吧,而且聽說這是全世界最美的步道!」我試著拍點馬屁,希望他快點讓我們入境。這一切都太難解釋了,我沒有時間跟心情用生硬的英文和他溝通深度話題。加上轉機時間,將近一整天的飛行其實把我們都累垮了,但我還是擠出一臉笑容,畢竟能不能順利在美國停留足夠讓我們完成旅行的時間,其實是得看他的臉色來決定。
他挑了一下眉毛,似乎不是很滿意這個答案,但也沒再多說什麼。
「歡迎來到美國。」他大章一蓋,護照上頭標示必須在二O一六年十月十七日前離境,一百八十天的停留時間到手,我們的旅程終於正式展開。
在決定挑戰太平洋屋脊步道的當下,也就是我興奮地坐在辦公室跟呆呆訊息熱線的時候,其實就有意識到該做的準備一定非常繁雜,畢竟據我們所知,在全球華人之中,也只有一位來自中國目前在德州求學的年輕女孩張諾婭在二O一四年走完全程。這還是我從維基百科查到的資訊,否則剛開始,我甚至以為這條熱門的路線肯定已有很多台灣人走過。
也就是說,我們無法像在台灣登山一樣,上網輸入幾個關鍵字,馬上就能找到一堆網友分享的遊記或是參考價值很高的行程規劃。沒有,完全沒有,只有幾篇零星的文章提到這條路線,而且大多是電影《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的影評心得。雖然熱心的張諾婭已在網路提供了很多實用資訊,但做計劃一向謹慎又龜毛的我其實還是非常焦慮。
我自認是個態度悠哉的人,但每次跟呆呆出國旅行,總習慣在手機上標注幾點幾分到哪個餐廳吃飯?要逛哪間戶外用品店?巨細靡遺地規劃好所有細節,即使時間還很充裕,也會不自覺地想要按表操課,下場當然就是把兩個人都累垮。這種強迫症的個性可能來自家人的影響。記得小時候每次家庭旅遊,在出發前一個星期,就看到他們老早把所有行李都打包完畢,逼得我不做點什麼也不行。還好婚後呆呆的步調比較緩慢,讓我急躁的個性緩和許多。
但太平洋屋脊步道畢竟是全然陌生的環境,況且還得走上那麼久的時間,現有的資訊根本不足以解答我對步道的疑惑。一天要走幾公里?走幾天後要到哪個城鎮補給?吃什麼?穿什麼?用什麼?當地的溫差有多少?海拔多高?天黑的時間是幾點?類似這樣的問題不斷在腦海裡打轉,完全沒辦法靜下來計劃細節。於是我買下所有可以到手的英文指南和地圖,一頁一頁慢慢地讀,用標籤貼紙記下重點,在書頁上劃上記號,同時在網路瘋狂搜尋各種相關資訊。結果弄巧成拙,各種陌生名詞和地名反而讓人更無所適從。
一直到走上步道一段時間後,才瞭解這種周全的計劃並不適用這麼長時間的旅行。突發的大雪或森林火災導致道路封閉,經過有毒植物和動物保護區需要另外繞道,還有各種無法預期的狀況,像是體力衰退、運動傷害⋯⋯等等,每個變數都有可能導致旅行的延宕,甚至中斷。
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徒步計劃準備時間可長可短,有人三天內就決定出發,也有人花了數年的評估才付諸行動,但一般來說平均需要四到五個月的時間。準備事項包含擬定徒步計劃、設定補給點、採買合適的裝備和服飾、申請各式許可證和美國觀光簽證,以及一連串的體能訓練或戶外技能訓練。
按照常理,為了專心準備而辭掉工作的我,絕對有充足的時間應付這些瑣事。我甚至想像自己一天的行程會是早上出去晨跑,接著做重量訓練,然後在家裡專心地研究步道的資料。等到出發的那一天,我會是一個強壯、精神奕奕又滿腹求生知識的真男人,隨時都能幫呆呆扛起她負荷不了的裝備,大步大步地往山裡走去。結果現實並非如我想像得那麼美好,大部份時間我都是坐在電腦前打字,為第一本書《山知道》日夜趕稿,甚至連瘦身的目標也悄悄放棄,率性地把自己吃胖到人生體重的巔峰。
寫書這件事從來沒有出現在我的生涯規劃裡,如同走上太平洋屋脊步道這個決定,兩者都開啟了另一扇窗,讓原本平淡的生活多了一點刺激和改變。而其中一個意外收穫是,為了宣傳《山知道》而設立的臉書專頁,竟然讓我們找到計劃在同一年出發的台灣人。這感覺就像美國太空總署發射的旅行者號(Voyager)太空船,在漫長航行後與光年之遙的外星人接觸,那張錄下「地球之聲」的鍍金唱片終於被聽見了。
「原來我們並不孤單!」我興奮地跟呆呆分享這個好消息。
透過臉書我們跟Alex搭上線,很快就約好在咖啡廳碰面,聊天後才曉得他也是半年前就計劃要走太平洋屋脊步道,只是礙於工作的關係,遲遲沒有真的下定決心,連機票跟簽證都尚未辦妥。相較另外兩位常常一起登山露營的好朋友——吉米跟小又,很早就決定跟我和呆呆組隊,從起點出發徒步約一千兩百公里,直到登上美國本土最高峰的惠特尼山頂(Mt. Whitney)後才各自解散,他們兩人會飛回台灣,而我跟呆呆則繼續往加拿大前進。吉米跟小又只走某一路段的方式,在美國有個術語叫「分段徒步」(Section-Hike),而打算從頭走到尾的人則稱為「全程徒步」(Thru-Hike)。每年有上千人挑戰全程徒步,但順利走到終點的人可能不到三成。
從決心要走太平洋屋脊步道以來,一直以為我們這對夫妻檔是台灣唯二的挑戰者,老實說心裡其實是有一點驕傲和興奮的。即使連名義上的第一步都尚未踏出,但我們已經把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付諸行動,當然會想要為自己喝彩;但同時,我們也會擔心、害怕,對自己沒有信心,對未知充滿恐懼。雖然有很多前輩建議,長程徒步最好是單獨出發,那些成群結隊的,通常不到半途就會四分五裂。步伐不同,理念也會不同,即使跟最親密的人結伴同行也不見得能相處融洽。但可能潛意識裡我是個膽小鬼吧,就像走進烏漆抹黑的地方會想張開雙手尋找任何可以碰觸的東西,不確定能夠抓到什麼,但至少心裡會覺得踏實許多。不管如何,在人生地不熟的環境,有個夥伴能夠互相照應總是讓人比較心安。
大概是我跟呆呆的極力慫恿成功,Alex最後還是決定出發了。他在搞定機票、簽證和工作後就先飛到美國的叔叔家,位於洛杉磯市區東邊約二十公里,總人口數近六萬,是一座很多亞洲人移民定居的中型城市「阿凱迪亞」(Arcadia),距離南邊的步道起點還有三個小時車程。呆呆的老同學子敏也住在那邊,她二話不說,很早就義氣地答應幫我們寄送包裹和補給裝備,擔任我們此行最重要的補給人角色。我跟呆呆、吉米和小又一行四人跟Alex約好在阿凱迪亞碰面,在出發日前幾天利用空檔採購食物跟裝備,也順便調整時差並適應當地的氣候。
飛到美國的前一晚,我們跟家裡的貓咪還有家人道別。兩隻已屆歐巴桑年齡的小貓,跟往常一樣窩在習慣的位置,牠們不會明白我們即將要踏上的旅程有多麽艱辛,只是瞪大眼睛站得遠遠地看呆呆把門關上。貓真是個奇怪的生物,對愛的需求很獨裁,也許這就是牠們總是姿態優雅的緣故。相較之下,父母親對我們遠行的態度可就不像貓咪那麼平淡,特別是我的母親,可以感受到她壓抑著自己對兒子和媳婦的憂心,知道我出發前很煩躁,都半夜了還在整理去美國的資料和文件,所以把嘮叨的話都藏在心裡,只簡單說了幾句。
「出門在外,自己要注意安全跟健康。要把翊庭顧好,她是你老婆,照顧她是你身為丈夫的責任。」停頓一下,又補了一句。「如果覺得很累就找地方多休息幾天,不要勉強自己。」
「我知道啦,如果真的累了不想走,我們會去搭計程車的,妳放心啦!」我用開玩笑的語氣安撫她,告訴她這條步道很安全,請不用為兒子擔心。但其實我把路上會遇到的最糟狀況都過濾掉了,而且事實上,在偏僻的步道周圍根本沒有像樣的大眾運輸系統,身為徒步旅行者,唯一可以搭乘的交通工具是路人的便車。
當機場接送的廂型車開進家裡的院子,時間是半夜兩點,母親和二姊幫我們把行李搬到車上。小時候她常跟我說,每次回娘家,老遠就看到外婆站在巷口等著大夥團聚,那殷切盼望一家團聚的身影深深烙印在她的腦海裡。後來外婆走了,我媽也老了,她扮演起一樣的角色,每當我要離開家裡,不管去的地方距離多遠,她一定堅持站在門口和我說再見。那天晚上,因為忙到幾乎沒有睡覺所以記憶非常模糊,所以不記得有沒有抱著和她道別,但我永遠都不會介意再給她一次緊緊的擁抱。
四月十八日,在我生日隔天,我們抵達加州的洛杉磯國際機場。上一次入境美國是大學剛畢業那年,跟朋友到東岸的紐約體驗一個月的背包客生活。接下來的十二年間,我再也沒去過那麼遠的地方,也沒有離開台灣那麼久的時間。如今再度踏上美國的土地,除了親切,還多了一股懷念。
「到美國這麼久的時間要做什麼?觀光需要這麼久的時間嗎?」入境的時候,一位亞裔海關人員一邊檢查證件一邊試著了解此行的目的。畢竟我們持有的B2觀光簽證,跟一般入境使用的電子簽證不一樣,所以他花了比較多時間「盤查」我們的底細。
「我們是來健行的。」我指著我身後的大背包,「我們要去走太平洋屋脊步道,PCT,你知道嗎?電影有演,我們要花六個月時間從墨西哥走到加拿大。」我預期他會瞪大眼睛,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二六五O英哩,這就是我們要走的距離。」通常說出這條步道的總長度時,總會聽到幾聲讚嘆和崇拜,這時心裡就會有一種輕飄飄的虛榮感。但明明連一英哩都還沒完成。
「不,我沒聽過。」他的神情帶有幾分歉意,但隨即又露出挖苦的表情笑著說:「這世界上步道這麼多,為什麼偏偏要選這條?我們加州山上有很多響尾蛇,很危險的。」
其實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一直以來這個問題我都不曉得正確答案是什麼。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會這麼毅然辭掉穩定的工作,挑戰這樣一條又長又困難,需要花上半年時間準備,然後再用另外半年光陰才能走完的步道?這問題在腦子裡縈繞好多回,隨著出發的時間慢慢逼近,一直沒有可以說服自己和其他人的滿意答案。當然不是「因為它在那裡」,也不是「想要找回自己」,或許有更複雜、更難以解釋的念頭隱藏在那層薄霧後面。又或許想做一件事情其實不需要什麼理由,心裡就是突然有什麼東西被觸碰了、被揪起了、被點燃了,驅使我跟呆呆踏上這條命中註定的道路,過往經歷的一切,彷彿都是為了此刻而準備。
「大概是因為美國比較安全吧,而且聽說這是全世界最美的步道!」我試著拍點馬屁,希望他快點讓我們入境。這一切都太難解釋了,我沒有時間跟心情用生硬的英文和他溝通深度話題。加上轉機時間,將近一整天的飛行其實把我們都累垮了,但我還是擠出一臉笑容,畢竟能不能順利在美國停留足夠讓我們完成旅行的時間,其實是得看他的臉色來決定。
他挑了一下眉毛,似乎不是很滿意這個答案,但也沒再多說什麼。
「歡迎來到美國。」他大章一蓋,護照上頭標示必須在二O一六年十月十七日前離境,一百八十天的停留時間到手,我們的旅程終於正式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