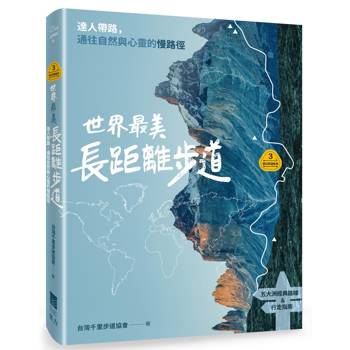紐西蘭.蒂阿拉羅瓦步道
——邁向遙遠那端的長路
文、攝影/許斐倩
小碎石不斷地向下滾落,我踩在由一顆顆火山石礫堆疊而成的山,像是隻逆流而上的鮭魚,試圖前往頂峰──那個似乎能直通地球心臟的火山口。每跨出一步、漆黑的小石頭就跟著我一起向下滑動兩步,彷彿無論怎麼努力,都無法到達山頂。
這是我踏上「蒂阿拉羅瓦步道」(Te Araroa Trail,簡稱 TA)的第四十九天。Te Araroa 在紐西蘭毛利人語中,意指「邁向遙遠那端的一條長路」,而此刻的我已經從紐西蘭北島的最北端,用雙腳緩慢移動了 1120 公里,來到北島的肚擠位置,走上 TA 官方認定的最精彩路段之一 ──通加里羅越嶺(Tongariro Crossing),這條路線穿越了絕美而獨特的火山地形,與過去四十八天走過的風景迥然不同。
也許是過於興奮,使我冒然決定離開 TA 路線,加碼爬上這座在《魔戒》電影中的末日火山──瑙魯荷埃峰(Mt. Ngauruhoe),企圖把我對未知的徬徨拋入,願其摧毀。
直到坐在火山口邊緣品嚐午餐,一面回望來時路,才發現自己已經走了這麼一段不容易的路。
同舟共濟:用雙手前行的日子
〔前略〕TA起步的第一天仍歷歷在目,在逐漸逼近的黑夜與潮水中,獨自開啟我的第一公里,內心依舊掙扎不安:「我會不會太高估自己了?」「我,確定要踏上這條路嗎?」
在紐西蘭工作了半年、參加了一場皇后鎮馬拉松、又將四天三夜人生第一趟的過夜健行作為TA暖身之後,我就站在這裡了,一心想用剩下的簽證時間,把雙腳當作交通方式,踏遍紐西蘭。
我以打工度假簽證的身份來到紐西蘭,起初在一間荒僻的公路咖啡廳工作,儲蓄旅費,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某天,咖啡廳老闆告訴我有位騎單車前來借宿的法國女孩,希望我去跟她打個招呼。這段十五分鐘的談話,卻徹底改變了我的未來半年、甚至可能一輩子的視野。
這位法國女孩名叫 Laura,她告訴我,她正從紐西蘭的南島最南端,以單車旅行的方式回到北島最北端,此時已完成路程的四分之三。就在我對她的壯舉感到佩服時,她又告訴我,前一年她曾以徒步方式走完了從最北端到最南端的 3000 公里長途路線。而那條路,就是TA。更讓我驚訝的是,她在開始之前毫無戶外活動經驗,「上路後肌肉就會慢慢長出來了,你也做得到。」眼前的她是個身高沒有高我多少、目測不超過160公分的女孩,帶著燦爛自信的笑容,與我分享她的故事。
從那天開始,我每晚都在咖啡廳後的小木屋裡,一面刷著牙,一邊眼睛緊盯著牆上的紐西蘭地圖,地圖上有一條我之前沒有留意過的紅色虛線,原來那就是 TA 的路線。TA 穿越了我一直想去的地方,還有一些我從未聽過的地方,這讓我對未知充滿了期待,低頭看著曾支撐我完成42公里馬拉松的兩條腿,徒步旅行紐西蘭的想法逐漸成形。
我相信自己的雙腳,能帶我遍覽山海四季。
然而這個浪漫的夢想,就在踏上TA的第一天、在每一個步伐的掙扎中幻滅。肩上背負了衣物、相機行動電源、帳篷睡眠系統、烹煮器具、飲用水、和接下來六天的糧食...等,總共將近15公斤的重量,將43公斤的我,重重地往沙灘上拓印出一個個深厚的足跡,每一次的舉步都越來越猶豫。
「我真的做得到嗎?」「這跟跑步完全不同吧...」一望無際的海平面,嘶聲吶喊也不會有人回應的廣闊沙灘,只有海鷗俯衝覓食和牠口中的戰利品,演繹著生命和死亡。未知可能是期待,也可能是恐懼。
我在毫無人跡的沙灘上拖行14公里,直到看見營地的八頂帳篷,我才有心思享受滿天星斗與海浪的包圍。隔日,我也在這遇見了同行的夥伴。
我們聊天笑鬧、手舞足蹈,打發著漫長的步行時間,每當遇到困難和內心的折磨,有人能理解、能互相分享和支持,是十足幸運的事,探索未知的膽量與興奮也一起加倍放大。這是行走於官方長距離步道上的一大優點,在熱門季節總能遇見來自不同國家、擁有各種期待和想像的徒步者,我們懷抱不同的故事出發,卻朝向同一個目標前進。
有些徒步者只在營地見過一兩次面,有些則是一同行走數週後以各自的步調分開。但每當我們連接上社群網路,關心鼓勵的話語便在空中飛梭。在我登上末日火山後的隔天,我們再次相聚在旺加努伊河(Whanganui River)──TA 的 1200 公里處,一起展開為期六天、全長227公里的渡航旅程。
旺加努伊之旅(Whanganui Journey) 原本就是紐西蘭官方十大步道(Great Walks)之一,也是唯一一條不是用「腳」來走的步道。這條步道開放於10月到4月穩定的氣候中,使用獨木舟划行在整體來說平穩但偶有激流的河流裡,欣賞河谷和懸崖景色。河道沿途設有官方妥善規劃和管理的靠岸處與簡單營地,我們可以上岸至小村落遊覽,並在岸上紮營或住進民宿中過夜。
TA步道的設置,是以既有的山徑和步道為基礎,通過公路、水路和私有土地的串接,路線不只有單純的徒步路徑,還混合河流獨木舟、建議騎乘越野單車、與搭船接駁等路段,無論採用什麼方式前進,「每一哩路都算數」。TA 將旺加努伊之旅這段仰賴雙手前行的獨木舟步道納入其中,讓它在世界其他長距離步道裡顯得豐富多元。
這是我第一次划獨木舟,加上不擅水域,更增添了對這趟旅程的恐懼;就像當初剛踏上TA的那個我,在完全沒有背負重裝經驗下進入山林,一切重新學習。我這名台灣人,竟是在同樣被海洋環繞、由板塊擠壓出層層山嶺的紐西蘭,才開始學習於自然中探索和生活。
獨木舟出租公司簡短地介紹了操作技巧,提供了一張地圖,並交代務必穿著救生衣,就留下我們這群遠征隊自行面對任務。第一天,我的背維持著 90 度的挺立坐姿,手緊握著槳,與同船的美國女孩 Sara 配合節奏一、二、一、二地喊著,眼睛直盯著每個大大小小疑似湍流的白色水花。
我們渡過了幾個激流,幾次險些翻船,我坐在前面的位置被揚起的河水濺得全身濕透,但這已經算是順利的了,其他艘的夥伴都落水了一輪。
經過一天的磨練,拿起槳,我開始能夠直覺地操控船隻,朝想去的方向前進,船彷彿成為身體的一部分,我也成為河的一部分。我們被水撐著、推著,「噗咚」一聲,有人跳入水裡、獲得一身清涼;左邊傳來《海洋奇緣》主題曲的哼唱,大家就自動和聲。歌聲環繞著,手中拿著啤酒,偶爾輕輕地划動槳,我舒服的躺下,享受著不需仰賴雙腳的移動方式。
「我知道你不會游泳,擔心你落水會害怕,所以奮力划著希望我們的船不會翻覆。」在臉部肌肉總算放鬆、恢復放聲大笑的能力後,我的夥伴美國女生 Sara 這麼告訴我,這下換我的眼眶肌肉抽動了。
徒步是很個人的事,那些堅持與抉擇,最終仍會回歸到自己。但若沒有夥伴同行,我還能走這麼遠嗎?
安全感:誰在我的帳篷外來回走動?!
紐西蘭的北島地勢相對平緩,相較受登山愛好者嚮往的南島壯闊山峰,北島TA經過的山徑類似於台灣的郊山或中級山等級,偏屬冷門步道,除了TA徒步者,幾乎很少遇到其他健行客。有時感覺自己就像地圖上一顆小到不能再小的微粒,即使在這片叢林底下消失,也不會有人察覺。
那是一片美麗而幽暗的森林,潮濕的土壤、涼冷的溫度,我與兩位結伴同行的TA徒步者都下意識地加快腳步,想在天黑前離開。但步伐還是趕不上星辰的速度,我們只能就地迫降,勉強在泥濘的軟地中找了三塊還算平坦乾燥的區域,各自拿出背包中的帳篷建置當晚的避身之處。我們散落在入夜的林子裡,連月光也無法穿透的漆黑野地中,沒人想離開自己的小屋,彼此之間的距離也遠得難以交談,空氣中留下屬於自然的聲響。
突然,一個頻率穩定又厚實的腳步聲由遠而近,朝我的帳篷靠近,近到我感覺他已經站在我的門口,隨時會扯開帳篷拉鍊。我屏住呼吸,仔細聽著這片布之外的聲響,腦中閃過好幾個可能性,會是當地居民嗎?還是路過的徒步者?又或是….?
帳篷的布,架起我與外界的距離,卻又薄到能被輕易移除,「Sara!是不是有人來了?」呼叫夥伴的句子已經準備衝過喉嚨。
突然,「噗!噗!噗!噗!」一聲聲的噴氣聲響,伴隨著腳步聲,環繞著我的帳篷,像極了有人在按壓除塵吹球。我不知所措,想著該如何防衛、我有什麼選擇?
這時,一個畫面閃過我的腦袋,雞爪般的腳、胖胖的身體、尖長的嘴喙,每當拿出 1 元紐幣就能看見牠。「該不會是奇異鳥?!牠在我的帳篷旁邊嗎?」那是紐西蘭的國鳥,當我意識到這個可能性時,我的緊繃情緒瞬間轉變成興奮,立即開啟手機的錄音功能,紀錄這獨特的聲響。接下來的幾天,每當遇到在地居民,我便會拿出音檔詢問,也終於證實了我的猜測:那晚奇異鳥就在我的身邊。此時又多麼希望帳篷的布是透明的,讓當時的我能在黑暗中一窺牠的身影。
自古有著天然海洋隔離,幸運未受到肉食動物侵擾的紐西蘭,加上多年來持續對生態與邊境進行嚴格保護,島上沒有猛獸、毒蟲、甚至連蛇都沒有,也因此成為世界上唯一留下無翼鳥這種不需飛行能力逃避的淨土。
「紐西蘭森林裡最讓人需要擔心的,就是突然出現的人吧!」我總這樣笑著說。少了一項需要留意擔心的事,對於第一次進行長距離徒步的我,有著莫大的安全感,更是很好的練習場域。
但當藉口少了一個,那麼最大的考驗,便是面對自己的內心了。
山屋:流浪徒步者的溫暖棲所
穿梭在淺山地區的北島1600公里路程,似乎在為南島的深山路線做行前體力訓練;多數時候我們背著帳篷,在山中野營、或者在城鎮的露營區中紮營,有時入住背包客棧;每日為自己設下的目標通常像是:「今天讓我來走個28公里吧!」或者是:「今天就抵達鎮上去補給、洗衣服吧!」幾乎每天都能和當地居民聊上一兩句,體驗紐西蘭的文化,感受人情。
南島的徒步日常則截然不同。
南阿爾卑斯山脈縱貫而成的山區,造就絕美的自然景色與密佈的徒步網絡,不僅是紐西蘭熱門的觀光去處,也是多數TA徒步者最期待的路段,甚至有人只願走南島。1400 公里無止境的壯麗地貌,常常讓我難以評判哪段更美了;審美疲勞,是徒步在紐西蘭南島的奢侈。
紐西蘭的環境保護部也廣設山屋,尤其是南島,並發行了山屋通行證,只要約台幣兩千元,半年內即可無限次數使用山屋(除公告排除的山屋)。TA路線上的山屋多數採先到先使用的入住方式,沒有管理員駐守,全憑山友們的自主維護、保持日常整潔,幸運的話,幾乎是標配的柴火爐旁還會堆放乾材,可能是巡山員、獵人、又或是熱心山友搬放,讓我們在一日濕冷的行走之後,得以偎著火光,烘乾濕溽的裝備。
在漫漫荒野中,山屋得以具象化此刻的自己身在地圖何處,與人描述路況時也變成:「某某山屋到某某山屋的路段真的超難走的!」像是數饅頭般,憑經過的山屋就能推估自己的前進速度,距離TA的終點又剩多遠。
TA路線在規劃時也避免與熱門的登山路線重疊,以減少長距離徒步者需要提前申請住宿的安排困難性,搭便車補給是難得與人類交談的機會,有時24小時過去,都遇不到一位徒步者。與自己對話的空間,直視內在的時間,多到奢侈,多到害怕面對自己。
南島的高山天氣更難以捉摸,隨著秋冬接近,步道開始推起白雪,河流更加難以通行,時間壓力的堆疊、在大自然面前認知自身的弱小無力、心智也在挑戰中逐漸耗盡,好幾次在安全的考量下我被迫退回登山口,卻又質疑著自己是否只是沒勇氣嘗試。
「到底為什麼要走上這條路?」我埋著頭拼了命地往終點踏去,只想結束這一切,卻受限無法掌控的天氣、和自身能力的不足,而充滿無力感。
無數天的日記被埋怨爬滿,當晚也不例外,直到三位獵人進入山屋打斷了我的書寫。「這個地方很美對嗎?我們每個月都會來至少一週,享受景色並帶回一週的食物呢!」「這個區域有很多野生的鹿,如果妳來的路上有留意,旁邊山坡上就有呢!」
我愣愣地看著他們,好些時候接不下話。「哪裡來的鹿?不過是數小時前才經過的地方,我怎麼卻記不清樣貌了?我剛剛,有抬頭看看身邊的景色嗎?」
我們都夢想旅行即是生活,但當旅行成為生活日常,我們還會對日常感到悸動嗎?
最高的坎:意料之外的光
站上TA的最高點史塔格鞍部(Stag Saddle),溫暖的陽光照亮了前陣子受天氣打亂行程的壞心情。老實說,1925 公尺不是太高,尤其相較能列出百岳的台灣。
但當乘載著近百日的里程數,踏上史塔格鞍部並看到標示TA制高點的立牌,我不顧肩頭持續受地心引力下拉的重量,以及大腿頻繁上提的酸痛感,奔跑向前,緊緊擁抱著它,心臟撲通撲通地猛烈跳動,分不清是因為激烈運動、還是過度感動,為漫長路途努力到這一刻的自己感到滿足,似乎能走到如此高處、走過如此遠的距離,剩下的五分之一路程也隨之明朗。
過了史塔格鞍部,路徑闢至稜線上,可以遠眺紐西蘭最高峰──3724公尺的庫克山(Mt. Cook),以及著名的觀光勝地提卡波湖(Tekapo)湖。微風吹來,暖陽灑落,我與旅伴決定提早放下帳篷,獨享沒有其他觀光客踏足的角度。
配著百萬美景入口的晚餐後,手機傳來當晚極光指數很高的訊息,我拉開那層薄薄的帳篷,望向湖的那一端,遠方的天空有著像雲一般迅速飄動的灰色帶狀物,在長曝光的鏡頭下,它們成了紅黃綠交錯的彩盤,那正是南極光!怎麼也沒料到,一個臨時起意,竟得以在極光下入睡。
而帳棚的另一側,是滿天的星斗。望著劃過頭頂的銀河,我想起踏上步道的第一天,在沙灘上精疲力盡地走到天黑,每個跨步都在質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繼續旅程,直到蜷縮進小小的帳篷,在滿天星空下、聽著海浪聲,緊繃的身心才逐漸放鬆,臉上不由自主地浮現微笑,入眠。我知道我享受這種生活,我開始期待著明天在哪裡醒來、又會看見什麼風景。
「感謝自己選擇這條道路」即便路上總有艱辛困難,或無法自行掌控的事,但每一步都帶領我了解自己和身體,藉由雙腳逐步丈量這個世界。
這一刻,我想起最初的樣子,心中的那個低谷,似乎也過了。
向外擴散的力量:繼續往南行
那已經是第七天沒洗澡了,雖然在南島的路線上,也不是最久的一次。
在森林裡穿梭數日的野營或居住於山中小屋,除非剛好有合適的溪水與溫度可盥洗,否則擦澡便是最低限度的清潔,但即便是在入秋的紐西蘭徒步,皮膚仍經不起挑戰地代謝出身體應有的分泌,從髮梢到髮根,沾黏著這些天的空氣與塵染。地上的小蟲繞開我而行,是否被我的氣味給嚇壞?聽到耳邊嗡嗡的聲音,擔心已經被蒼蠅給盯上了,此時走入人煙稠密的瓦納卡鎮( Wanaka )上,「五味雜陳」的我,壓低帽緣,企圖遮掩束束分明的瀏海。
停車場裡有位女士,打從駛入車格後目光就集中在我身上,下了車,表情顯示的疑惑更為醒目,她皺起眉頭注視著我,似乎在猶豫是否要與我交談。「也許她以為我是流浪漢?」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如此,「還是她嫌我手中登山杖敲擊地面的聲音吵到她?」我曾被這樣批評過。
當我慢慢走過她身旁時,她也以同樣的速度走向我,「我想問問你,你在做什麼?」她的聲音讓我停下腳步,但我無法聽出她的目的,於是小心翼翼地解釋我正在走一條稱為TA的步道,跨越紐西蘭的南北島。
「我住在這附近,看過好幾位像你一樣的人走過去,一直很好奇你們在做什麼。但今天不知道為什麼,看到你,我突然決定開口跟你聊天,也解答我一直以來的疑惑。」我們就這樣站著聊了半個小時,談論步道、談我、談她。
道別前她說:「最近我不斷思考自己該做些什麼改變,我想要出發展開旅程,但不知道要往何處去,今天遇見你,以及你所從事的事情,給了我一個方向,謝謝你。」
法國女孩 Laura 用她的生命故事開啟了我的旅程,而毛利小孩歌聲的熱情、夥伴支持的能量、路途上收到的加油打氣,都成為我持續前進的動力。如今,力量被傳遞著,從TA這條路徑向外擴散。我不知道她將朝著哪個方向前進,但我邁向極南點的腳步,更踏實了。
橫跨之後:3000公里的終點
在蒂阿拉羅瓦步道上移動的第 120 天,站在步道最南端的布拉夫(Bluff),我總算轉身向北,這一路上,每一個跨出的步伐都很小,卻足以繪出自己的緯度。
120天前那個剛出發的自己,絕沒想過真的能步行 3000 公里來到終點。每日僅僅是為了想做的事、為了一個目標,用盡全力投入自己,期待著未知的驚喜,也正面迎向未知的恐懼;不僅是為了挑戰自己,更是為了發現自己的脆弱和堅強,試圖將自己融入大自然中,感受作為一種動物的本質。
《魔戒》裡甘道夫曾對佛羅多說:「我們該做的決定,是在有限時間裡該做什麼。」(All we have to decide is what to do with the time that we are given.)我在這趟旅程中也有了如同魔戒遠征隊夥伴般的陪伴,一路上的困難和挑戰,似乎都變得微不足道。
回望我所橫跨的紐西蘭,我體會到的、學到的、感受到的,都已經裝進肩上的背包中。視線的那一頭,是我的家鄉台灣,那是最終的目的地,更是另一個旅程的起點。
——邁向遙遠那端的長路
文、攝影/許斐倩
小碎石不斷地向下滾落,我踩在由一顆顆火山石礫堆疊而成的山,像是隻逆流而上的鮭魚,試圖前往頂峰──那個似乎能直通地球心臟的火山口。每跨出一步、漆黑的小石頭就跟著我一起向下滑動兩步,彷彿無論怎麼努力,都無法到達山頂。
這是我踏上「蒂阿拉羅瓦步道」(Te Araroa Trail,簡稱 TA)的第四十九天。Te Araroa 在紐西蘭毛利人語中,意指「邁向遙遠那端的一條長路」,而此刻的我已經從紐西蘭北島的最北端,用雙腳緩慢移動了 1120 公里,來到北島的肚擠位置,走上 TA 官方認定的最精彩路段之一 ──通加里羅越嶺(Tongariro Crossing),這條路線穿越了絕美而獨特的火山地形,與過去四十八天走過的風景迥然不同。
也許是過於興奮,使我冒然決定離開 TA 路線,加碼爬上這座在《魔戒》電影中的末日火山──瑙魯荷埃峰(Mt. Ngauruhoe),企圖把我對未知的徬徨拋入,願其摧毀。
直到坐在火山口邊緣品嚐午餐,一面回望來時路,才發現自己已經走了這麼一段不容易的路。
同舟共濟:用雙手前行的日子
〔前略〕TA起步的第一天仍歷歷在目,在逐漸逼近的黑夜與潮水中,獨自開啟我的第一公里,內心依舊掙扎不安:「我會不會太高估自己了?」「我,確定要踏上這條路嗎?」
在紐西蘭工作了半年、參加了一場皇后鎮馬拉松、又將四天三夜人生第一趟的過夜健行作為TA暖身之後,我就站在這裡了,一心想用剩下的簽證時間,把雙腳當作交通方式,踏遍紐西蘭。
我以打工度假簽證的身份來到紐西蘭,起初在一間荒僻的公路咖啡廳工作,儲蓄旅費,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某天,咖啡廳老闆告訴我有位騎單車前來借宿的法國女孩,希望我去跟她打個招呼。這段十五分鐘的談話,卻徹底改變了我的未來半年、甚至可能一輩子的視野。
這位法國女孩名叫 Laura,她告訴我,她正從紐西蘭的南島最南端,以單車旅行的方式回到北島最北端,此時已完成路程的四分之三。就在我對她的壯舉感到佩服時,她又告訴我,前一年她曾以徒步方式走完了從最北端到最南端的 3000 公里長途路線。而那條路,就是TA。更讓我驚訝的是,她在開始之前毫無戶外活動經驗,「上路後肌肉就會慢慢長出來了,你也做得到。」眼前的她是個身高沒有高我多少、目測不超過160公分的女孩,帶著燦爛自信的笑容,與我分享她的故事。
從那天開始,我每晚都在咖啡廳後的小木屋裡,一面刷著牙,一邊眼睛緊盯著牆上的紐西蘭地圖,地圖上有一條我之前沒有留意過的紅色虛線,原來那就是 TA 的路線。TA 穿越了我一直想去的地方,還有一些我從未聽過的地方,這讓我對未知充滿了期待,低頭看著曾支撐我完成42公里馬拉松的兩條腿,徒步旅行紐西蘭的想法逐漸成形。
我相信自己的雙腳,能帶我遍覽山海四季。
然而這個浪漫的夢想,就在踏上TA的第一天、在每一個步伐的掙扎中幻滅。肩上背負了衣物、相機行動電源、帳篷睡眠系統、烹煮器具、飲用水、和接下來六天的糧食...等,總共將近15公斤的重量,將43公斤的我,重重地往沙灘上拓印出一個個深厚的足跡,每一次的舉步都越來越猶豫。
「我真的做得到嗎?」「這跟跑步完全不同吧...」一望無際的海平面,嘶聲吶喊也不會有人回應的廣闊沙灘,只有海鷗俯衝覓食和牠口中的戰利品,演繹著生命和死亡。未知可能是期待,也可能是恐懼。
我在毫無人跡的沙灘上拖行14公里,直到看見營地的八頂帳篷,我才有心思享受滿天星斗與海浪的包圍。隔日,我也在這遇見了同行的夥伴。
我們聊天笑鬧、手舞足蹈,打發著漫長的步行時間,每當遇到困難和內心的折磨,有人能理解、能互相分享和支持,是十足幸運的事,探索未知的膽量與興奮也一起加倍放大。這是行走於官方長距離步道上的一大優點,在熱門季節總能遇見來自不同國家、擁有各種期待和想像的徒步者,我們懷抱不同的故事出發,卻朝向同一個目標前進。
有些徒步者只在營地見過一兩次面,有些則是一同行走數週後以各自的步調分開。但每當我們連接上社群網路,關心鼓勵的話語便在空中飛梭。在我登上末日火山後的隔天,我們再次相聚在旺加努伊河(Whanganui River)──TA 的 1200 公里處,一起展開為期六天、全長227公里的渡航旅程。
旺加努伊之旅(Whanganui Journey) 原本就是紐西蘭官方十大步道(Great Walks)之一,也是唯一一條不是用「腳」來走的步道。這條步道開放於10月到4月穩定的氣候中,使用獨木舟划行在整體來說平穩但偶有激流的河流裡,欣賞河谷和懸崖景色。河道沿途設有官方妥善規劃和管理的靠岸處與簡單營地,我們可以上岸至小村落遊覽,並在岸上紮營或住進民宿中過夜。
TA步道的設置,是以既有的山徑和步道為基礎,通過公路、水路和私有土地的串接,路線不只有單純的徒步路徑,還混合河流獨木舟、建議騎乘越野單車、與搭船接駁等路段,無論採用什麼方式前進,「每一哩路都算數」。TA 將旺加努伊之旅這段仰賴雙手前行的獨木舟步道納入其中,讓它在世界其他長距離步道裡顯得豐富多元。
這是我第一次划獨木舟,加上不擅水域,更增添了對這趟旅程的恐懼;就像當初剛踏上TA的那個我,在完全沒有背負重裝經驗下進入山林,一切重新學習。我這名台灣人,竟是在同樣被海洋環繞、由板塊擠壓出層層山嶺的紐西蘭,才開始學習於自然中探索和生活。
獨木舟出租公司簡短地介紹了操作技巧,提供了一張地圖,並交代務必穿著救生衣,就留下我們這群遠征隊自行面對任務。第一天,我的背維持著 90 度的挺立坐姿,手緊握著槳,與同船的美國女孩 Sara 配合節奏一、二、一、二地喊著,眼睛直盯著每個大大小小疑似湍流的白色水花。
我們渡過了幾個激流,幾次險些翻船,我坐在前面的位置被揚起的河水濺得全身濕透,但這已經算是順利的了,其他艘的夥伴都落水了一輪。
經過一天的磨練,拿起槳,我開始能夠直覺地操控船隻,朝想去的方向前進,船彷彿成為身體的一部分,我也成為河的一部分。我們被水撐著、推著,「噗咚」一聲,有人跳入水裡、獲得一身清涼;左邊傳來《海洋奇緣》主題曲的哼唱,大家就自動和聲。歌聲環繞著,手中拿著啤酒,偶爾輕輕地划動槳,我舒服的躺下,享受著不需仰賴雙腳的移動方式。
「我知道你不會游泳,擔心你落水會害怕,所以奮力划著希望我們的船不會翻覆。」在臉部肌肉總算放鬆、恢復放聲大笑的能力後,我的夥伴美國女生 Sara 這麼告訴我,這下換我的眼眶肌肉抽動了。
徒步是很個人的事,那些堅持與抉擇,最終仍會回歸到自己。但若沒有夥伴同行,我還能走這麼遠嗎?
安全感:誰在我的帳篷外來回走動?!
紐西蘭的北島地勢相對平緩,相較受登山愛好者嚮往的南島壯闊山峰,北島TA經過的山徑類似於台灣的郊山或中級山等級,偏屬冷門步道,除了TA徒步者,幾乎很少遇到其他健行客。有時感覺自己就像地圖上一顆小到不能再小的微粒,即使在這片叢林底下消失,也不會有人察覺。
那是一片美麗而幽暗的森林,潮濕的土壤、涼冷的溫度,我與兩位結伴同行的TA徒步者都下意識地加快腳步,想在天黑前離開。但步伐還是趕不上星辰的速度,我們只能就地迫降,勉強在泥濘的軟地中找了三塊還算平坦乾燥的區域,各自拿出背包中的帳篷建置當晚的避身之處。我們散落在入夜的林子裡,連月光也無法穿透的漆黑野地中,沒人想離開自己的小屋,彼此之間的距離也遠得難以交談,空氣中留下屬於自然的聲響。
突然,一個頻率穩定又厚實的腳步聲由遠而近,朝我的帳篷靠近,近到我感覺他已經站在我的門口,隨時會扯開帳篷拉鍊。我屏住呼吸,仔細聽著這片布之外的聲響,腦中閃過好幾個可能性,會是當地居民嗎?還是路過的徒步者?又或是….?
帳篷的布,架起我與外界的距離,卻又薄到能被輕易移除,「Sara!是不是有人來了?」呼叫夥伴的句子已經準備衝過喉嚨。
突然,「噗!噗!噗!噗!」一聲聲的噴氣聲響,伴隨著腳步聲,環繞著我的帳篷,像極了有人在按壓除塵吹球。我不知所措,想著該如何防衛、我有什麼選擇?
這時,一個畫面閃過我的腦袋,雞爪般的腳、胖胖的身體、尖長的嘴喙,每當拿出 1 元紐幣就能看見牠。「該不會是奇異鳥?!牠在我的帳篷旁邊嗎?」那是紐西蘭的國鳥,當我意識到這個可能性時,我的緊繃情緒瞬間轉變成興奮,立即開啟手機的錄音功能,紀錄這獨特的聲響。接下來的幾天,每當遇到在地居民,我便會拿出音檔詢問,也終於證實了我的猜測:那晚奇異鳥就在我的身邊。此時又多麼希望帳篷的布是透明的,讓當時的我能在黑暗中一窺牠的身影。
自古有著天然海洋隔離,幸運未受到肉食動物侵擾的紐西蘭,加上多年來持續對生態與邊境進行嚴格保護,島上沒有猛獸、毒蟲、甚至連蛇都沒有,也因此成為世界上唯一留下無翼鳥這種不需飛行能力逃避的淨土。
「紐西蘭森林裡最讓人需要擔心的,就是突然出現的人吧!」我總這樣笑著說。少了一項需要留意擔心的事,對於第一次進行長距離徒步的我,有著莫大的安全感,更是很好的練習場域。
但當藉口少了一個,那麼最大的考驗,便是面對自己的內心了。
山屋:流浪徒步者的溫暖棲所
穿梭在淺山地區的北島1600公里路程,似乎在為南島的深山路線做行前體力訓練;多數時候我們背著帳篷,在山中野營、或者在城鎮的露營區中紮營,有時入住背包客棧;每日為自己設下的目標通常像是:「今天讓我來走個28公里吧!」或者是:「今天就抵達鎮上去補給、洗衣服吧!」幾乎每天都能和當地居民聊上一兩句,體驗紐西蘭的文化,感受人情。
南島的徒步日常則截然不同。
南阿爾卑斯山脈縱貫而成的山區,造就絕美的自然景色與密佈的徒步網絡,不僅是紐西蘭熱門的觀光去處,也是多數TA徒步者最期待的路段,甚至有人只願走南島。1400 公里無止境的壯麗地貌,常常讓我難以評判哪段更美了;審美疲勞,是徒步在紐西蘭南島的奢侈。
紐西蘭的環境保護部也廣設山屋,尤其是南島,並發行了山屋通行證,只要約台幣兩千元,半年內即可無限次數使用山屋(除公告排除的山屋)。TA路線上的山屋多數採先到先使用的入住方式,沒有管理員駐守,全憑山友們的自主維護、保持日常整潔,幸運的話,幾乎是標配的柴火爐旁還會堆放乾材,可能是巡山員、獵人、又或是熱心山友搬放,讓我們在一日濕冷的行走之後,得以偎著火光,烘乾濕溽的裝備。
在漫漫荒野中,山屋得以具象化此刻的自己身在地圖何處,與人描述路況時也變成:「某某山屋到某某山屋的路段真的超難走的!」像是數饅頭般,憑經過的山屋就能推估自己的前進速度,距離TA的終點又剩多遠。
TA路線在規劃時也避免與熱門的登山路線重疊,以減少長距離徒步者需要提前申請住宿的安排困難性,搭便車補給是難得與人類交談的機會,有時24小時過去,都遇不到一位徒步者。與自己對話的空間,直視內在的時間,多到奢侈,多到害怕面對自己。
南島的高山天氣更難以捉摸,隨著秋冬接近,步道開始推起白雪,河流更加難以通行,時間壓力的堆疊、在大自然面前認知自身的弱小無力、心智也在挑戰中逐漸耗盡,好幾次在安全的考量下我被迫退回登山口,卻又質疑著自己是否只是沒勇氣嘗試。
「到底為什麼要走上這條路?」我埋著頭拼了命地往終點踏去,只想結束這一切,卻受限無法掌控的天氣、和自身能力的不足,而充滿無力感。
無數天的日記被埋怨爬滿,當晚也不例外,直到三位獵人進入山屋打斷了我的書寫。「這個地方很美對嗎?我們每個月都會來至少一週,享受景色並帶回一週的食物呢!」「這個區域有很多野生的鹿,如果妳來的路上有留意,旁邊山坡上就有呢!」
我愣愣地看著他們,好些時候接不下話。「哪裡來的鹿?不過是數小時前才經過的地方,我怎麼卻記不清樣貌了?我剛剛,有抬頭看看身邊的景色嗎?」
我們都夢想旅行即是生活,但當旅行成為生活日常,我們還會對日常感到悸動嗎?
最高的坎:意料之外的光
站上TA的最高點史塔格鞍部(Stag Saddle),溫暖的陽光照亮了前陣子受天氣打亂行程的壞心情。老實說,1925 公尺不是太高,尤其相較能列出百岳的台灣。
但當乘載著近百日的里程數,踏上史塔格鞍部並看到標示TA制高點的立牌,我不顧肩頭持續受地心引力下拉的重量,以及大腿頻繁上提的酸痛感,奔跑向前,緊緊擁抱著它,心臟撲通撲通地猛烈跳動,分不清是因為激烈運動、還是過度感動,為漫長路途努力到這一刻的自己感到滿足,似乎能走到如此高處、走過如此遠的距離,剩下的五分之一路程也隨之明朗。
過了史塔格鞍部,路徑闢至稜線上,可以遠眺紐西蘭最高峰──3724公尺的庫克山(Mt. Cook),以及著名的觀光勝地提卡波湖(Tekapo)湖。微風吹來,暖陽灑落,我與旅伴決定提早放下帳篷,獨享沒有其他觀光客踏足的角度。
配著百萬美景入口的晚餐後,手機傳來當晚極光指數很高的訊息,我拉開那層薄薄的帳篷,望向湖的那一端,遠方的天空有著像雲一般迅速飄動的灰色帶狀物,在長曝光的鏡頭下,它們成了紅黃綠交錯的彩盤,那正是南極光!怎麼也沒料到,一個臨時起意,竟得以在極光下入睡。
而帳棚的另一側,是滿天的星斗。望著劃過頭頂的銀河,我想起踏上步道的第一天,在沙灘上精疲力盡地走到天黑,每個跨步都在質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繼續旅程,直到蜷縮進小小的帳篷,在滿天星空下、聽著海浪聲,緊繃的身心才逐漸放鬆,臉上不由自主地浮現微笑,入眠。我知道我享受這種生活,我開始期待著明天在哪裡醒來、又會看見什麼風景。
「感謝自己選擇這條道路」即便路上總有艱辛困難,或無法自行掌控的事,但每一步都帶領我了解自己和身體,藉由雙腳逐步丈量這個世界。
這一刻,我想起最初的樣子,心中的那個低谷,似乎也過了。
向外擴散的力量:繼續往南行
那已經是第七天沒洗澡了,雖然在南島的路線上,也不是最久的一次。
在森林裡穿梭數日的野營或居住於山中小屋,除非剛好有合適的溪水與溫度可盥洗,否則擦澡便是最低限度的清潔,但即便是在入秋的紐西蘭徒步,皮膚仍經不起挑戰地代謝出身體應有的分泌,從髮梢到髮根,沾黏著這些天的空氣與塵染。地上的小蟲繞開我而行,是否被我的氣味給嚇壞?聽到耳邊嗡嗡的聲音,擔心已經被蒼蠅給盯上了,此時走入人煙稠密的瓦納卡鎮( Wanaka )上,「五味雜陳」的我,壓低帽緣,企圖遮掩束束分明的瀏海。
停車場裡有位女士,打從駛入車格後目光就集中在我身上,下了車,表情顯示的疑惑更為醒目,她皺起眉頭注視著我,似乎在猶豫是否要與我交談。「也許她以為我是流浪漢?」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如此,「還是她嫌我手中登山杖敲擊地面的聲音吵到她?」我曾被這樣批評過。
當我慢慢走過她身旁時,她也以同樣的速度走向我,「我想問問你,你在做什麼?」她的聲音讓我停下腳步,但我無法聽出她的目的,於是小心翼翼地解釋我正在走一條稱為TA的步道,跨越紐西蘭的南北島。
「我住在這附近,看過好幾位像你一樣的人走過去,一直很好奇你們在做什麼。但今天不知道為什麼,看到你,我突然決定開口跟你聊天,也解答我一直以來的疑惑。」我們就這樣站著聊了半個小時,談論步道、談我、談她。
道別前她說:「最近我不斷思考自己該做些什麼改變,我想要出發展開旅程,但不知道要往何處去,今天遇見你,以及你所從事的事情,給了我一個方向,謝謝你。」
法國女孩 Laura 用她的生命故事開啟了我的旅程,而毛利小孩歌聲的熱情、夥伴支持的能量、路途上收到的加油打氣,都成為我持續前進的動力。如今,力量被傳遞著,從TA這條路徑向外擴散。我不知道她將朝著哪個方向前進,但我邁向極南點的腳步,更踏實了。
橫跨之後:3000公里的終點
在蒂阿拉羅瓦步道上移動的第 120 天,站在步道最南端的布拉夫(Bluff),我總算轉身向北,這一路上,每一個跨出的步伐都很小,卻足以繪出自己的緯度。
120天前那個剛出發的自己,絕沒想過真的能步行 3000 公里來到終點。每日僅僅是為了想做的事、為了一個目標,用盡全力投入自己,期待著未知的驚喜,也正面迎向未知的恐懼;不僅是為了挑戰自己,更是為了發現自己的脆弱和堅強,試圖將自己融入大自然中,感受作為一種動物的本質。
《魔戒》裡甘道夫曾對佛羅多說:「我們該做的決定,是在有限時間裡該做什麼。」(All we have to decide is what to do with the time that we are given.)我在這趟旅程中也有了如同魔戒遠征隊夥伴般的陪伴,一路上的困難和挑戰,似乎都變得微不足道。
回望我所橫跨的紐西蘭,我體會到的、學到的、感受到的,都已經裝進肩上的背包中。視線的那一頭,是我的家鄉台灣,那是最終的目的地,更是另一個旅程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