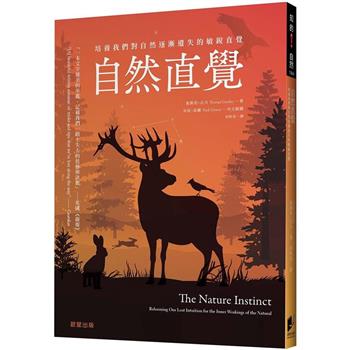我們的目標是不使用任何地圖或導航儀器,抵達克里特島(Crete)北岸的海域,然後朝南走,直到我們抵達南岸。若給烏鴉飛行,距離大約是二十六英里,但是我們不會飛也不會走太多直線路線。我猜我們得準備好步行它兩倍的距離。路途中還有大約八千英尺(譯註:一英尺為三〇・四八公分)的山脈。
但是真正的挑戰是炎熱、水和重量。那是九月天,土地焦乾。我希望我們可以在長達四天的步行中不依賴從任何額外食物或水分。但是在華氏九十九度(譯註:約為攝氏三七・二度)的高溫之下,在山區負重步行四天,代表需要大量的水;而水很重。我們出發時背的東西愈多、行囊愈重,就愈發舉步維艱、行進速度就愈緩慢,需要的水就更多。這真是個捉弄人的難題。對我來說最好的妥協方案似乎是一人背四加崙的水。為了避免陷入缺水的緊急狀況,我們打算讓自己不許使用儲備的水,除非我們認輸、打開緊急地圖和GPS,然後前往文明世界。要到終點出現在眼前時才能碰最後一加崙的水。對休閒散步而言,以上規定聽起來有點艱難,我知道有些人因為中暑而身亡,且一切可能發生得很突然。事實上,這是我唯一擔心的風險。
在一個北岸小鎮帕諾莫斯(Panormos),我的好朋友艾德(Ed)和我檢查了自己的行囊之後又替彼此檢查。我們把水瓶塞進背包,夾在背包外側,喝了滿肚子淡水,然後抵達海邊,蹣跚地走進炎熱的山丘。
自然領航最讓人沮喪的特點之一,就是很難在半野外的環境中評估路的產權。自然並不會像標示出方向和地形一樣標示出產權。不久之後,有個牧羊人從破舊不堪的建築物走出來,很快速地說了一串希臘語告誡我們。我們對他的語言一翹不通,但是身體語言流利又容易理解——他要我們按原路折返。但我們簡單的計畫並不允許回溯;因為我們時間有限,且水也不多,所以我們試了各種方法說服他讓我們通過。他開始生氣了。我們嘗試不同的策略。
我讀過一些克里特島的歷史,知道這片山脈依然充滿第二次世界大戰黑暗記憶的遺毒。在納粹佔領期間,有幾回英勇的抵抗發生,接著德國人在此屠殺一波。這裡的槍枝依然氾濫,克里特人還保有自豪、獨立的精神,尤其是在我們將經過的農村山區。
「我們來自英國倫敦。」
我不知道是這句話幫了忙,或是時機剛好恰當,總之他的情緒緩和下來,很快就揮手道別讓我們出發。之後遇到的人都非常友善。甚至有一名橄欖農夫邀請我們搭他的牽引機載我們一程——但我們有禮地拒絕了。這有違我們決定遵從的、由一岸至另一岸的奇怪遊戲規則。
我們踩著一步又一步沉重的步伐,朝上坡邁進。
「安全。」
「安全。」
我們稍早建立的一項不那麼愉悅的例行程序,是互相報告自己尿液的顏色。我們知道隨著路途愈陡峭,我們會冒著脫水的風險,尿液顏色會變深,所以我們希望保持尿液顏色為正常的琥珀色。
第一天總是最難熬。山腳下很熱,我們的背包重量達到極限,而且一路幾乎都是無情的上坡。艾德轉移我對溫度的注意力,問我能不能用溫室植物的排列來幫助我們找到方向。我不確定,但是惦記稍後要確認。原來溫室會以南北向為首選,除非夏天的日照不夠,才會是東西向較佳。所以,也許有幫助吧。
在汗流浹背的第一天結束時,在我們即將橫越的山稜線旁有一間山屋,我們在一旁攤開泡綿墊,安頓下來。我們把自己逼到極限,而我不確定在如此炎熱的氣溫之下,我們接下來幾天還能不能趕上進度,但也許我們不需要趕路。如果我們趕路,至少後面會遇到一些下坡,我們的背包大概每天可以減輕十磅(譯註:約四・五四公斤)。
我們吃了些咖哩調理包,看星星出現。我設了一些經緯儀——對照北極星排列石頭——以便早晨太陽躲在雲層後時,可作為我們正確的指引。然後我們蓋著一千顆星星躺下。
艾德開始咒罵,但是我很快就加入他的行列。蚊子對我們展開一波波的攻勢。我們在身上噴滿防蚊液之後再度躺平。過了如此疲憊的一天,可能要像老鼠那麼大的蚊子才會讓我們徹夜難眠,不過我們的確斷續地醒來,感覺到它們嗡嗡作響和叮咬我們的臉。斷續的頻率規律到我們發現一種模式。每次我們被蚊子吵醒時都是陰天;從來沒有天空清澈的時候。這個規律性如此可靠,以至於我們等待烏雲散去才閉上眼睛,心裡很清楚下一片烏雲來襲時,我們又會醒來。
我擁有過去幾十年來儲存在腦海裡的所有自然領航技巧。但毫無疑問,除非天氣有異,否則太陽都會是我們主要的羅盤。
九月上旬,太陽會在東、西方以北幾度之處升起、落下,正午時會位於正南方。重點是它如何在這段期間改變方位。這過程並不完全相同。靠近正午時的太陽方位變化程度會比日出和日落時更劇烈。每次進行認真的探險,我都會嘗試計算太陽通過東南方和西南方的時間,試圖掌握這個情況。這讓我得以測量太陽一天當中的路徑——愈靠近一日正午(而且總是與日出和日落等距離),在接近午餐時間的情況變化愈劇烈。我發現這是重新熟悉運用太陽作為羅盤的最快方式。
一開始是定時交叉確認時間與太陽的方向。我們有手錶——這是我們對現代性的讓步。現在幾點?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處於東南時間的哪一邊?早半小時——好,意思是太陽一定位於東南方的東邊幾度。我們用這項資訊選出一個目標點瞄準,最好是在中段或更遠的距離,然後在曠野重複執行這個過程,也許一天十幾次,在林地或寸步難行的山區可能要更頻繁地反覆執行。
然後有些更有趣的事開始浮現。到了某個時候,也許是第二天快結束時,正式確認變得不那麼頻繁,非正式的確認則比較普遍。聽起來可能沒太大意義,但我認為有意義。我們不再需要稍微緩慢地深思熟慮;我們能察覺太陽在空中的位置及其所指的方向。我們的大腦已經慢慢鍛造出一種新的思考模式。這就是「太陽砧」(sun anvil)。我們自太陽獲得的意義變成了一種直覺。
隔天,這種變化已經根深蒂固。很難說明我們是什麼時候開始思考的;太陽就在那裡,默默又有效地指引我們前往所選的方向。這也是許多現今的原住民及我們祖先過去運用太陽的做法。
有時太陽會受到雲層遮蔽,我們甚至遇到短暫的下雨,這正是可用彩虹領航的絕佳機會。天空中交雜著陽光和烏雲,太陽好好躲在山脊線後方,一道彩虹出現在我們眼前,幫盆谷另一側山脈的枯燥棕色增添了迷人的色彩。畫面十分奇特。我感覺到思考模式再次瓦解。
如果我們把一道彩虹想成一個完整圓圈的一部分,圓心一定總是位於太陽正對側——這就是在一日之初和一日之末的彩虹總是一枚巨大半圓的原因。要用彩虹領航,我們只需要想著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那彩虹就會在相反一八〇度的位置。不過這需要一些有意識的計算。雖然這相當簡單,但令人驚訝的是,它跟前幾個小時透過太陽位置直覺找路的感覺很不一樣。我們已經透過練習把太陽羅盤從緩慢思考拉到快速思考,而彩虹卻又把思考模式拉回去。如果彩虹持續的時間夠久,我們無疑可以學會憑直覺運用它,就像太陽一樣,但是陣雨過去了,這樣的機會一直沒出現。
第二天午休時,我們在山羊擠奶房的陰涼處休息。我在一片生鏽鐵片的影子末端放一枚硬幣,與其說是因為必要,不如說是出於我的個人消遣。午餐吃了冷的辣肉醬配香蕉脆片後,我在最新的陰影末端放了第二枚硬幣;兩個硬幣的連線就在地面上標出東西向。
幾小時後,我們經過一棟屋子,屋外曬著海灘裝備。除非我們的方向錯得離譜,不然我們所見的海洋特徵很有可能是來自南岸,而非北岸,光是這樣想就很滿足。
第二天下午很糟。我們走在山嶺(spur)上,為了試圖維持在制高點,這通常是好的策略,卻發現我們陷入相互交錯的山嶺迷宮裡。上坡和下坡都很陡峭,在陰天之下殘酷地交替走了幾個小時。我們感到疲憊不堪又意志消沉。我們根據自認往南移動的距離判斷我們的進度。山嶺迫使我們往東然後往西,導致我們費了很多力氣卻完全沒有往南前進。我們決定在天黑前一小時紮營——如果可以,我都想鋪好床和吃頓飯,不管多簡陋都沒關係,只要在太陽下山前搞定就好。
我們在樹林間找到一塊空地,看起來很完美。動物骨頭的數量比理想還多一些,但是清理起來比大部分我們考慮的紮營點無盡的岩石還輕鬆多了。附近茂密的矮樹叢中有隧道,顯然我們安頓在獸徑的網絡旁,但既然我們知道克里特島沒有我們需要擔心的動物,就沒有太在意。
晚餐後,艾德和我研究了透過星星建構的各種羅盤:天蠍座與夏季大三角(Summer Triangle,或稱領航員大三角Navigator’s Triangle)指向南方,天鵝座(Cygnus)、仙后座(Cassiopeia)與指向北極星的北斗七星(Big Dipper)。我們再次建立經緯儀,隔天早上就能看到標記在地面的指針。
接下來的夜晚都無法放鬆。當我們安頓好互道晚安後,聽到一輛汽車從山上眾多土路之一開過來。距離聽起來近到彷彿能看到車燈,不過我們都沒看到。然後我們聽到了第一聲槍響。山腰附近傳出髒話,對比起來,幾晚前對蚊子的咒罵根本不算什麼。
在克里特島這些較荒涼的地區,打獵是最受歡迎的消遣。顯然有人正在開槍,就算不是直接對我們開槍,也離我們很近。我們太累了,不小心選了打獵的黃金地段紮營。我們打開頭燈,我打開另一個備用的燈,設定成閃燈模式。接著我翻找背包底部的袋子,裡面裝有我原以為不需要的東西,我開始折斷螢光棒,掛在樹上。腎上腺素飆升。我們可能擅闖了一塊領地,即使這是個半野外區域,也不清楚我們到底該跳上跳下還是儘量壓低身體。我們選擇了後者,躺下然後聆聽。後來又有幾聲槍響,然後我們聽到汽車發動並開走的聲音。
如果是平常,這種經歷會讓我保持清醒一個小時,但是經歷了兩天非常耗體力的行程,我很快就開始昏昏欲睡。
幾分鐘後,我坐起身,再次打開我的頭燈。燈光照亮一張受驚的貓臉。距離我的臉只有六英尺之遠,牠盯著我看,體型明顯比家貓大,但是有著相似的特徵。牠停頓了一會兒,好像在打量這個狀況是誰佔上風。我保持靜止不動,回瞪牠。然後牠衝進林下植物(譯註:undergrowth,也就是森林中較矮的灌木叢或樹叢)中。
「那是什麼?」艾德問道。
「我不知道」,我回答。
「你怎麼會想要打開頭燈?」
「我一定是聽到什麼聲音了。」但是我並不確定。那隻動物撤退時幾乎無聲,而我懷疑牠是否有發出任何聲音吵醒我。我可能永遠無法得知是什麼讓我坐起身並打開頭燈。我腦中仍然會浮現那張動物的臉,那只有可能是一種物種:有時稱作克里特山貓(Cretan lynx)的一種野貓。這種貓非常罕見,多年來被認為已絕種。我現在很珍惜這段回憶,但是在當時,我只想要不受槍聲或稀有貓干擾,好好睡上一覺。
隔天早上,我們在吃早餐時尋找野貓的蹤跡。那裡有一些,不過還有數百個其他的蹤跡。整片空地是一片殺戮戰場,有成千上萬個小骨頭。我很難斷定大部分的殺戮究竟是掠食者還是人類造成的。
我們決定放棄維持制高點的策略,往下切至山谷。太陽再度露臉,我們順利抵達地面,穿越荒涼又滿布岩石的景色往南前進,抵達一片橄欖林。
到第三天午餐時,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海岸沿線的文明世界,我們欣然接受,尤其我們的水量已經探底。隨著高度下降,氣溫再度上升,我們在那天下午抵達海岸。我們蹣跚地走在沙灘上,把手伸入海中,拍照留念。接著我們研究旅館和餐廳的招牌,釐清我們到底身在何方。我們發現是在一個叫做阿吉亞加里尼(Agia Galini)的地方,意思是「神聖的和平」。我們都沒聽過這個地方。原來就在我們在起點帕諾莫斯的正南方。這說明了運氣與判斷不相上下。我的意思是,我們大腦有一部分的區域允許自己受太陽砧影響,而我們則讓它們負責困難的工作。我敢說,如果我們太過仰賴聰明又緩慢的思考,我們的處境將不會那麼順利。
但是真正的挑戰是炎熱、水和重量。那是九月天,土地焦乾。我希望我們可以在長達四天的步行中不依賴從任何額外食物或水分。但是在華氏九十九度(譯註:約為攝氏三七・二度)的高溫之下,在山區負重步行四天,代表需要大量的水;而水很重。我們出發時背的東西愈多、行囊愈重,就愈發舉步維艱、行進速度就愈緩慢,需要的水就更多。這真是個捉弄人的難題。對我來說最好的妥協方案似乎是一人背四加崙的水。為了避免陷入缺水的緊急狀況,我們打算讓自己不許使用儲備的水,除非我們認輸、打開緊急地圖和GPS,然後前往文明世界。要到終點出現在眼前時才能碰最後一加崙的水。對休閒散步而言,以上規定聽起來有點艱難,我知道有些人因為中暑而身亡,且一切可能發生得很突然。事實上,這是我唯一擔心的風險。
在一個北岸小鎮帕諾莫斯(Panormos),我的好朋友艾德(Ed)和我檢查了自己的行囊之後又替彼此檢查。我們把水瓶塞進背包,夾在背包外側,喝了滿肚子淡水,然後抵達海邊,蹣跚地走進炎熱的山丘。
自然領航最讓人沮喪的特點之一,就是很難在半野外的環境中評估路的產權。自然並不會像標示出方向和地形一樣標示出產權。不久之後,有個牧羊人從破舊不堪的建築物走出來,很快速地說了一串希臘語告誡我們。我們對他的語言一翹不通,但是身體語言流利又容易理解——他要我們按原路折返。但我們簡單的計畫並不允許回溯;因為我們時間有限,且水也不多,所以我們試了各種方法說服他讓我們通過。他開始生氣了。我們嘗試不同的策略。
我讀過一些克里特島的歷史,知道這片山脈依然充滿第二次世界大戰黑暗記憶的遺毒。在納粹佔領期間,有幾回英勇的抵抗發生,接著德國人在此屠殺一波。這裡的槍枝依然氾濫,克里特人還保有自豪、獨立的精神,尤其是在我們將經過的農村山區。
「我們來自英國倫敦。」
我不知道是這句話幫了忙,或是時機剛好恰當,總之他的情緒緩和下來,很快就揮手道別讓我們出發。之後遇到的人都非常友善。甚至有一名橄欖農夫邀請我們搭他的牽引機載我們一程——但我們有禮地拒絕了。這有違我們決定遵從的、由一岸至另一岸的奇怪遊戲規則。
我們踩著一步又一步沉重的步伐,朝上坡邁進。
「安全。」
「安全。」
我們稍早建立的一項不那麼愉悅的例行程序,是互相報告自己尿液的顏色。我們知道隨著路途愈陡峭,我們會冒著脫水的風險,尿液顏色會變深,所以我們希望保持尿液顏色為正常的琥珀色。
第一天總是最難熬。山腳下很熱,我們的背包重量達到極限,而且一路幾乎都是無情的上坡。艾德轉移我對溫度的注意力,問我能不能用溫室植物的排列來幫助我們找到方向。我不確定,但是惦記稍後要確認。原來溫室會以南北向為首選,除非夏天的日照不夠,才會是東西向較佳。所以,也許有幫助吧。
在汗流浹背的第一天結束時,在我們即將橫越的山稜線旁有一間山屋,我們在一旁攤開泡綿墊,安頓下來。我們把自己逼到極限,而我不確定在如此炎熱的氣溫之下,我們接下來幾天還能不能趕上進度,但也許我們不需要趕路。如果我們趕路,至少後面會遇到一些下坡,我們的背包大概每天可以減輕十磅(譯註:約四・五四公斤)。
我們吃了些咖哩調理包,看星星出現。我設了一些經緯儀——對照北極星排列石頭——以便早晨太陽躲在雲層後時,可作為我們正確的指引。然後我們蓋著一千顆星星躺下。
艾德開始咒罵,但是我很快就加入他的行列。蚊子對我們展開一波波的攻勢。我們在身上噴滿防蚊液之後再度躺平。過了如此疲憊的一天,可能要像老鼠那麼大的蚊子才會讓我們徹夜難眠,不過我們的確斷續地醒來,感覺到它們嗡嗡作響和叮咬我們的臉。斷續的頻率規律到我們發現一種模式。每次我們被蚊子吵醒時都是陰天;從來沒有天空清澈的時候。這個規律性如此可靠,以至於我們等待烏雲散去才閉上眼睛,心裡很清楚下一片烏雲來襲時,我們又會醒來。
我擁有過去幾十年來儲存在腦海裡的所有自然領航技巧。但毫無疑問,除非天氣有異,否則太陽都會是我們主要的羅盤。
九月上旬,太陽會在東、西方以北幾度之處升起、落下,正午時會位於正南方。重點是它如何在這段期間改變方位。這過程並不完全相同。靠近正午時的太陽方位變化程度會比日出和日落時更劇烈。每次進行認真的探險,我都會嘗試計算太陽通過東南方和西南方的時間,試圖掌握這個情況。這讓我得以測量太陽一天當中的路徑——愈靠近一日正午(而且總是與日出和日落等距離),在接近午餐時間的情況變化愈劇烈。我發現這是重新熟悉運用太陽作為羅盤的最快方式。
一開始是定時交叉確認時間與太陽的方向。我們有手錶——這是我們對現代性的讓步。現在幾點?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處於東南時間的哪一邊?早半小時——好,意思是太陽一定位於東南方的東邊幾度。我們用這項資訊選出一個目標點瞄準,最好是在中段或更遠的距離,然後在曠野重複執行這個過程,也許一天十幾次,在林地或寸步難行的山區可能要更頻繁地反覆執行。
然後有些更有趣的事開始浮現。到了某個時候,也許是第二天快結束時,正式確認變得不那麼頻繁,非正式的確認則比較普遍。聽起來可能沒太大意義,但我認為有意義。我們不再需要稍微緩慢地深思熟慮;我們能察覺太陽在空中的位置及其所指的方向。我們的大腦已經慢慢鍛造出一種新的思考模式。這就是「太陽砧」(sun anvil)。我們自太陽獲得的意義變成了一種直覺。
隔天,這種變化已經根深蒂固。很難說明我們是什麼時候開始思考的;太陽就在那裡,默默又有效地指引我們前往所選的方向。這也是許多現今的原住民及我們祖先過去運用太陽的做法。
有時太陽會受到雲層遮蔽,我們甚至遇到短暫的下雨,這正是可用彩虹領航的絕佳機會。天空中交雜著陽光和烏雲,太陽好好躲在山脊線後方,一道彩虹出現在我們眼前,幫盆谷另一側山脈的枯燥棕色增添了迷人的色彩。畫面十分奇特。我感覺到思考模式再次瓦解。
如果我們把一道彩虹想成一個完整圓圈的一部分,圓心一定總是位於太陽正對側——這就是在一日之初和一日之末的彩虹總是一枚巨大半圓的原因。要用彩虹領航,我們只需要想著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那彩虹就會在相反一八〇度的位置。不過這需要一些有意識的計算。雖然這相當簡單,但令人驚訝的是,它跟前幾個小時透過太陽位置直覺找路的感覺很不一樣。我們已經透過練習把太陽羅盤從緩慢思考拉到快速思考,而彩虹卻又把思考模式拉回去。如果彩虹持續的時間夠久,我們無疑可以學會憑直覺運用它,就像太陽一樣,但是陣雨過去了,這樣的機會一直沒出現。
第二天午休時,我們在山羊擠奶房的陰涼處休息。我在一片生鏽鐵片的影子末端放一枚硬幣,與其說是因為必要,不如說是出於我的個人消遣。午餐吃了冷的辣肉醬配香蕉脆片後,我在最新的陰影末端放了第二枚硬幣;兩個硬幣的連線就在地面上標出東西向。
幾小時後,我們經過一棟屋子,屋外曬著海灘裝備。除非我們的方向錯得離譜,不然我們所見的海洋特徵很有可能是來自南岸,而非北岸,光是這樣想就很滿足。
第二天下午很糟。我們走在山嶺(spur)上,為了試圖維持在制高點,這通常是好的策略,卻發現我們陷入相互交錯的山嶺迷宮裡。上坡和下坡都很陡峭,在陰天之下殘酷地交替走了幾個小時。我們感到疲憊不堪又意志消沉。我們根據自認往南移動的距離判斷我們的進度。山嶺迫使我們往東然後往西,導致我們費了很多力氣卻完全沒有往南前進。我們決定在天黑前一小時紮營——如果可以,我都想鋪好床和吃頓飯,不管多簡陋都沒關係,只要在太陽下山前搞定就好。
我們在樹林間找到一塊空地,看起來很完美。動物骨頭的數量比理想還多一些,但是清理起來比大部分我們考慮的紮營點無盡的岩石還輕鬆多了。附近茂密的矮樹叢中有隧道,顯然我們安頓在獸徑的網絡旁,但既然我們知道克里特島沒有我們需要擔心的動物,就沒有太在意。
晚餐後,艾德和我研究了透過星星建構的各種羅盤:天蠍座與夏季大三角(Summer Triangle,或稱領航員大三角Navigator’s Triangle)指向南方,天鵝座(Cygnus)、仙后座(Cassiopeia)與指向北極星的北斗七星(Big Dipper)。我們再次建立經緯儀,隔天早上就能看到標記在地面的指針。
接下來的夜晚都無法放鬆。當我們安頓好互道晚安後,聽到一輛汽車從山上眾多土路之一開過來。距離聽起來近到彷彿能看到車燈,不過我們都沒看到。然後我們聽到了第一聲槍響。山腰附近傳出髒話,對比起來,幾晚前對蚊子的咒罵根本不算什麼。
在克里特島這些較荒涼的地區,打獵是最受歡迎的消遣。顯然有人正在開槍,就算不是直接對我們開槍,也離我們很近。我們太累了,不小心選了打獵的黃金地段紮營。我們打開頭燈,我打開另一個備用的燈,設定成閃燈模式。接著我翻找背包底部的袋子,裡面裝有我原以為不需要的東西,我開始折斷螢光棒,掛在樹上。腎上腺素飆升。我們可能擅闖了一塊領地,即使這是個半野外區域,也不清楚我們到底該跳上跳下還是儘量壓低身體。我們選擇了後者,躺下然後聆聽。後來又有幾聲槍響,然後我們聽到汽車發動並開走的聲音。
如果是平常,這種經歷會讓我保持清醒一個小時,但是經歷了兩天非常耗體力的行程,我很快就開始昏昏欲睡。
幾分鐘後,我坐起身,再次打開我的頭燈。燈光照亮一張受驚的貓臉。距離我的臉只有六英尺之遠,牠盯著我看,體型明顯比家貓大,但是有著相似的特徵。牠停頓了一會兒,好像在打量這個狀況是誰佔上風。我保持靜止不動,回瞪牠。然後牠衝進林下植物(譯註:undergrowth,也就是森林中較矮的灌木叢或樹叢)中。
「那是什麼?」艾德問道。
「我不知道」,我回答。
「你怎麼會想要打開頭燈?」
「我一定是聽到什麼聲音了。」但是我並不確定。那隻動物撤退時幾乎無聲,而我懷疑牠是否有發出任何聲音吵醒我。我可能永遠無法得知是什麼讓我坐起身並打開頭燈。我腦中仍然會浮現那張動物的臉,那只有可能是一種物種:有時稱作克里特山貓(Cretan lynx)的一種野貓。這種貓非常罕見,多年來被認為已絕種。我現在很珍惜這段回憶,但是在當時,我只想要不受槍聲或稀有貓干擾,好好睡上一覺。
隔天早上,我們在吃早餐時尋找野貓的蹤跡。那裡有一些,不過還有數百個其他的蹤跡。整片空地是一片殺戮戰場,有成千上萬個小骨頭。我很難斷定大部分的殺戮究竟是掠食者還是人類造成的。
我們決定放棄維持制高點的策略,往下切至山谷。太陽再度露臉,我們順利抵達地面,穿越荒涼又滿布岩石的景色往南前進,抵達一片橄欖林。
到第三天午餐時,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海岸沿線的文明世界,我們欣然接受,尤其我們的水量已經探底。隨著高度下降,氣溫再度上升,我們在那天下午抵達海岸。我們蹣跚地走在沙灘上,把手伸入海中,拍照留念。接著我們研究旅館和餐廳的招牌,釐清我們到底身在何方。我們發現是在一個叫做阿吉亞加里尼(Agia Galini)的地方,意思是「神聖的和平」。我們都沒聽過這個地方。原來就在我們在起點帕諾莫斯的正南方。這說明了運氣與判斷不相上下。我的意思是,我們大腦有一部分的區域允許自己受太陽砧影響,而我們則讓它們負責困難的工作。我敢說,如果我們太過仰賴聰明又緩慢的思考,我們的處境將不會那麼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