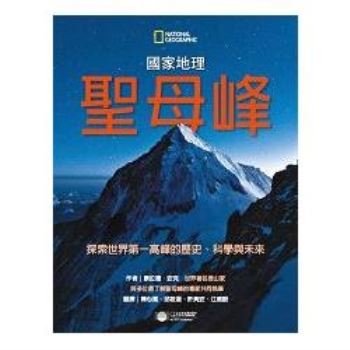聖母峰的無盡呼喚
湯瑪斯‧洪賓
2012年春季,國家地理學會和The North Face聯合贊助「聖母峰遠征紀念之旅」(Legacy Expedition to Everest)。和當時另一支由艾迪鮑爾(Eddie Bauer)公司贊助的登山隊一樣,紀念遠征隊的目標,是重訪半世紀前美國聖母峰遠征隊(AMEE)1963年的路線;成員分別從南坳和西稜兩線上山,預計在峰頂會合後,西線隊伍繼續循我和威利‧安索德(Willi Unsoeld)當年的路線,從南線下山。結果,南線隊伍遇上兩次天氣尚可的短暫空檔,趁著其中一次按計畫走完全程。不過,西稜方面因為落石太多,加上雪況惡劣,太過危險無法攀登。2012年的情況其實很常見;過去半世紀以來,約有60支隊伍嘗試走西線攻頂,成功率大約一成,途中死亡的機率和成功登頂不相上下。
《聖母峰的呼喚》這本書紀念美國遠征隊首次登頂50週年,以及艾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lary)和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登頂60週年,他們兩位是最早登上聖母峰的人。本書由國家地理學會出版,可說再適合不過;國家地理學會不僅是1963美國聖母峰遠征隊的主要贊助者,學會成員巴瑞‧畢紹普(Barry Bishop)也參加了當時的遠征,並擔任攝影。他左頁這張照片拍到的兩個小小人影,就是走在西肩(West Shoulder)稜線上的安索德和我。充滿未知魅力的聖母峰在前方巍峨聳立,顯得我們十分渺小。這個畫面在我看來,正詮釋了這趟西稜冒險的精髓:享受未知。
美國聖母峰遠征隊的成就遠遠超過我們想像。5月1日,吉姆‧惠特克(Jim Whittaker)與雪巴嚮導納旺貢布(Nawang Gombu)同行,成為第一位登頂聖母峰的美國人。三週後,另外四人也隨後登頂:路特‧傑斯塔(Lute Jerstad)和巴瑞‧畢紹普在5月22日下午3點多 ,成功從南線登頂。稍晚,威利和我在6點15分也登上頂峰。那是史上第一次有人從西稜登頂;途中經過一處,威利喜歡叫它「洪賓的雪崩陷阱」,現在通稱為洪賓雪溝(Hornbein Couloir)。我們後來從南線下山,趕上路特和巴瑞,最後四個人被迫在8500多公尺的地方,臨時露宿了一夜。我們能熬過那晚真的非常幸運,威利和我能完成橫跨喜馬拉雅主峰的創舉,也實在是老天眷顧。
人和山的關係不斷演變,我們會循新的路線攀登聖母峰,也是可以預見的發展。這種探索的本質,就是持續創造不確定性:我們首先找到夢想的目標,接著想辦法抵達山腳,最後再找出爬上山巔的途徑。一旦「征服」一座山(用個令人不悅的說法),下個挑戰就是開發新路線。到了這個階段,還會開始講究風格,或是不靠輔助氧氣攀登(特別是爬聖母峰的時候)。再演變到後來,又加入新的不確定性,例如從峰頂滑雪或跳傘下山,回去還趕得上晚餐時間。隨著人和山的關係日趨成熟,也必然會出現「商業導覽」式的登山活動,讓經驗不足但嚮往高山的人,也能體驗這種極限探險的滋味。
這些演變都不是聖母峰獨有的現象,但只有在聖母峰,數量遽增的登山客,爭相尋求嚮導公司的協助,帶領他們爬上世界最高點。聖母峰被愛死了,只是死的不是聖母峰。
我必須承認,雖然1996和之後幾年發生過大型山難,但在2012年登山季的遠征紀念活動之前,我都還能說服自己,聖母峰登山客愈來愈多,由登山業者提供輔助、嚮導帶團上山,是合理、務實,無可阻擋的趨勢,跟其他登山勝地沒什麼不同。我相信經驗不足但身體強健的登山客,在嚮導的指引下攀登聖母峰,安全至少有一定保障。我覺得聖母峰登山新手增加,死亡率卻沒有提高,這一點很了不起;我認為這要感謝嚮導和業者的專業、細心與通力合作,例如在危險地段加裝固定繩,避免遊客一失足就不幸身亡。
我也相信,現在這些聘請嚮導公司服務的顧客,登山動機可能和我相去不遠。很久以前我就發現,攻頂的決心強烈與否,和登山動機似乎並無關聯,不論背後的動力是追求名利、想體驗天險美景,或單純想進行一次心靈探索,看看自己做不做得到。
1963年和現在最鮮明的對比之一,就呈現在馬克‧詹金斯(Mark Jenkins)對2012年遠征活動的描述(本書第七章),以及相關照片中:其中一張看似有條細細的黑線 ,是數百名登山客繫在固定繩上,沿著洛子峰壁(Lhotse Face)蜿蜒而上;另一張照片中,登山客多到像擠沙丁魚,排隊等著登上希拉瑞臺階(Hillary Step)。也許現在爬聖母峰最危險的事,就是人滿為患、大排長龍,有時要等上數小時。更讓我驚恐的是,想到這麼多人等在山上,不知何時會跟大自然的詭譎力量交會──可能是猛烈的暴風、或是大規模雪崩;這是攀登高山必須下承擔的風險。跟其他自然災害一樣:問題不是會不會發生,而是什麼時候發生。
我是美國中西部長大的平地人,13歲與山邂逅便一見鍾情。這份愛定義了我的人生──不只因為我身為一名業餘登山愛好者;這份愛影響我生活許多層面,包括我擔任醫生、研究員和教育者的職業生涯,包括我與家人相處、與豐富我生命的每個人共度的時光,也幫助我在逐漸變老的時候,還能保有幾分從容(希望是這樣)。少年時期,聖母峰只存在我的想像之中,從沒想過能親眼看見,更沒想過要去攀登。回頭展望這50年,我很慶幸出生在對的時間,有機會在聖母峰還只屬於我們的時候,參與這場偉大的探險。
那樣的聖母峰已成過去。現在的聖母峰人潮擁擠,社交熱絡的基地營和高山上的氛圍,都與我所認知的山完全相反。多數時候,我和這座垂直世界一直保持寧靜共處的關係,與志同道合的夥伴一同漫步其中。不過我也能理解,聖母峰為何吸引敢於接受挑戰的人;我們都懷著相似的熱情,追求夢想。就像這本書的標題一樣,讓我們翻到下一頁,和康拉德‧安克(Conrad Anker)一起回應聖母峰的「呼喚」吧!
湯瑪斯‧洪賓Thomas Hornbein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退休教授,專長麻醉學、生理學及生物物理學,也是1963美國聖母峰遠征隊的一員。他和威利‧安索德搭檔,以阿爾卑斯式攀登策略,沿著凶險的西稜登上峰頂,為登
山史寫下新的一頁。他們在攀登途中,行經一處颳風下雪的蝕溝,後來命名為「洪賓雪溝」,以紀念他的功績。
湯瑪斯‧洪賓
2012年春季,國家地理學會和The North Face聯合贊助「聖母峰遠征紀念之旅」(Legacy Expedition to Everest)。和當時另一支由艾迪鮑爾(Eddie Bauer)公司贊助的登山隊一樣,紀念遠征隊的目標,是重訪半世紀前美國聖母峰遠征隊(AMEE)1963年的路線;成員分別從南坳和西稜兩線上山,預計在峰頂會合後,西線隊伍繼續循我和威利‧安索德(Willi Unsoeld)當年的路線,從南線下山。結果,南線隊伍遇上兩次天氣尚可的短暫空檔,趁著其中一次按計畫走完全程。不過,西稜方面因為落石太多,加上雪況惡劣,太過危險無法攀登。2012年的情況其實很常見;過去半世紀以來,約有60支隊伍嘗試走西線攻頂,成功率大約一成,途中死亡的機率和成功登頂不相上下。
《聖母峰的呼喚》這本書紀念美國遠征隊首次登頂50週年,以及艾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lary)和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登頂60週年,他們兩位是最早登上聖母峰的人。本書由國家地理學會出版,可說再適合不過;國家地理學會不僅是1963美國聖母峰遠征隊的主要贊助者,學會成員巴瑞‧畢紹普(Barry Bishop)也參加了當時的遠征,並擔任攝影。他左頁這張照片拍到的兩個小小人影,就是走在西肩(West Shoulder)稜線上的安索德和我。充滿未知魅力的聖母峰在前方巍峨聳立,顯得我們十分渺小。這個畫面在我看來,正詮釋了這趟西稜冒險的精髓:享受未知。
美國聖母峰遠征隊的成就遠遠超過我們想像。5月1日,吉姆‧惠特克(Jim Whittaker)與雪巴嚮導納旺貢布(Nawang Gombu)同行,成為第一位登頂聖母峰的美國人。三週後,另外四人也隨後登頂:路特‧傑斯塔(Lute Jerstad)和巴瑞‧畢紹普在5月22日下午3點多 ,成功從南線登頂。稍晚,威利和我在6點15分也登上頂峰。那是史上第一次有人從西稜登頂;途中經過一處,威利喜歡叫它「洪賓的雪崩陷阱」,現在通稱為洪賓雪溝(Hornbein Couloir)。我們後來從南線下山,趕上路特和巴瑞,最後四個人被迫在8500多公尺的地方,臨時露宿了一夜。我們能熬過那晚真的非常幸運,威利和我能完成橫跨喜馬拉雅主峰的創舉,也實在是老天眷顧。
人和山的關係不斷演變,我們會循新的路線攀登聖母峰,也是可以預見的發展。這種探索的本質,就是持續創造不確定性:我們首先找到夢想的目標,接著想辦法抵達山腳,最後再找出爬上山巔的途徑。一旦「征服」一座山(用個令人不悅的說法),下個挑戰就是開發新路線。到了這個階段,還會開始講究風格,或是不靠輔助氧氣攀登(特別是爬聖母峰的時候)。再演變到後來,又加入新的不確定性,例如從峰頂滑雪或跳傘下山,回去還趕得上晚餐時間。隨著人和山的關係日趨成熟,也必然會出現「商業導覽」式的登山活動,讓經驗不足但嚮往高山的人,也能體驗這種極限探險的滋味。
這些演變都不是聖母峰獨有的現象,但只有在聖母峰,數量遽增的登山客,爭相尋求嚮導公司的協助,帶領他們爬上世界最高點。聖母峰被愛死了,只是死的不是聖母峰。
我必須承認,雖然1996和之後幾年發生過大型山難,但在2012年登山季的遠征紀念活動之前,我都還能說服自己,聖母峰登山客愈來愈多,由登山業者提供輔助、嚮導帶團上山,是合理、務實,無可阻擋的趨勢,跟其他登山勝地沒什麼不同。我相信經驗不足但身體強健的登山客,在嚮導的指引下攀登聖母峰,安全至少有一定保障。我覺得聖母峰登山新手增加,死亡率卻沒有提高,這一點很了不起;我認為這要感謝嚮導和業者的專業、細心與通力合作,例如在危險地段加裝固定繩,避免遊客一失足就不幸身亡。
我也相信,現在這些聘請嚮導公司服務的顧客,登山動機可能和我相去不遠。很久以前我就發現,攻頂的決心強烈與否,和登山動機似乎並無關聯,不論背後的動力是追求名利、想體驗天險美景,或單純想進行一次心靈探索,看看自己做不做得到。
1963年和現在最鮮明的對比之一,就呈現在馬克‧詹金斯(Mark Jenkins)對2012年遠征活動的描述(本書第七章),以及相關照片中:其中一張看似有條細細的黑線 ,是數百名登山客繫在固定繩上,沿著洛子峰壁(Lhotse Face)蜿蜒而上;另一張照片中,登山客多到像擠沙丁魚,排隊等著登上希拉瑞臺階(Hillary Step)。也許現在爬聖母峰最危險的事,就是人滿為患、大排長龍,有時要等上數小時。更讓我驚恐的是,想到這麼多人等在山上,不知何時會跟大自然的詭譎力量交會──可能是猛烈的暴風、或是大規模雪崩;這是攀登高山必須下承擔的風險。跟其他自然災害一樣:問題不是會不會發生,而是什麼時候發生。
我是美國中西部長大的平地人,13歲與山邂逅便一見鍾情。這份愛定義了我的人生──不只因為我身為一名業餘登山愛好者;這份愛影響我生活許多層面,包括我擔任醫生、研究員和教育者的職業生涯,包括我與家人相處、與豐富我生命的每個人共度的時光,也幫助我在逐漸變老的時候,還能保有幾分從容(希望是這樣)。少年時期,聖母峰只存在我的想像之中,從沒想過能親眼看見,更沒想過要去攀登。回頭展望這50年,我很慶幸出生在對的時間,有機會在聖母峰還只屬於我們的時候,參與這場偉大的探險。
那樣的聖母峰已成過去。現在的聖母峰人潮擁擠,社交熱絡的基地營和高山上的氛圍,都與我所認知的山完全相反。多數時候,我和這座垂直世界一直保持寧靜共處的關係,與志同道合的夥伴一同漫步其中。不過我也能理解,聖母峰為何吸引敢於接受挑戰的人;我們都懷著相似的熱情,追求夢想。就像這本書的標題一樣,讓我們翻到下一頁,和康拉德‧安克(Conrad Anker)一起回應聖母峰的「呼喚」吧!
湯瑪斯‧洪賓Thomas Hornbein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退休教授,專長麻醉學、生理學及生物物理學,也是1963美國聖母峰遠征隊的一員。他和威利‧安索德搭檔,以阿爾卑斯式攀登策略,沿著凶險的西稜登上峰頂,為登
山史寫下新的一頁。他們在攀登途中,行經一處颳風下雪的蝕溝,後來命名為「洪賓雪溝」,以紀念他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