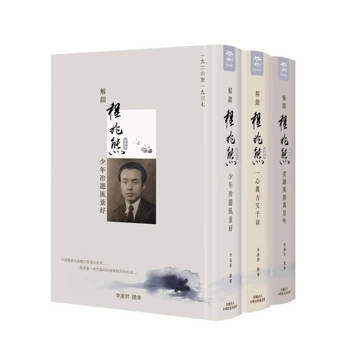程兆熊先生與許思園先生
程先生於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十一月十二日的國父誕辰紀念日作了〈從人性與人之使命悼許思園先生〉以悼念許先生,這離許先生去世的一九七四年已是六年之後,概得知訊息的時間已是晚。程先生與許思園先生之情誼從中山大學畢業後前往南京創業便已開始,難得人生得知己,在南京同遊共語,在南昌同行暢談,在巴黎同學共食。
他在大同大學畢業後,即被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請去,和宗白華、方東美先生等同事。那時我正在南京辦國際譯報。我由他的表弟楊蔭渭先生介紹,才和他相識,並常來往。(〈從人性與人之使命悼許思園先生〉)
程先生之寫舊詩乃因許先生建議,程先生之對儒學興趣亦有許先生之影響。程先生提及與許思園先生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夏天認識以後的往來樂趣,更言其性情:
我因常和許思園兄同去雞鳴寺,且住處相近,故無所不談,無所不議。有一次論到明太祖,他忽一言一發,儘讓我一人說個不休。問他亦不答,別時亦不送,而且態度冷冷然。過了一些時,我再去看他,向他請教,他方言道:這就是我的試探,看你如何?隨後,他忽勸我不要做新詩。可以做做舊詩。那時,我們正在雞鳴寺,面對紫金山,俯視玄武湖。我乃言:「天臨湖水近,地接遠山間,野堤春草綠,隔水菜花黃」,他便大笑了。他的智慧極高,學識自然更博。他能詩,而不作詩。
那時,南昌設立了一個行營,成一軍事重鎮和安內的中心,同時也由那裡發出一個中國文化學會和新生活運動的號召。我和君毅、思園二兄南昌之行,即因此故。
我們乘坐長江輪,來往都經過九江,並宿於潯陽江頭。我們無所不談,大快平生。
我們來時,在潯陽江頭一宿。我們回時,又在潯陽江上一宿。我們三人談到深夜。(《九十回憶》)
我們很清楚知道唐君毅先生是透過許思園先生介紹給程兆熊先生的,而許思園先生則是由楊蔭渭先生介紹給程先生認識,楊蔭渭先生是楊蔭鴻先生之弟(許思園先生的表兄),楊蔭鴻先生介紹其弟楊蔭渭與程先生相識。如此形成了這個朋友圈,也因此方有後來程許唐三人於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同往南昌行營謁見蔣委員長,(此南昌行及唐先生主編《小國際》二事,於後續談)及說好了許先生赴巴黎留學,由唐先生繼任其教職,而程先生則欲去巴黎籌辦國際譯報社分社。結果,最終反倒是程先生先去了巴黎,沒設成分社,倒取得了法國巴黎園藝工程師和文學博士,而許先生亦非直奔巴黎而是先至倫敦再赴巴黎,去巴黎的時間應該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年中之時了,且程先生竟成了許先生的媒人,兩人先後取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程先生憶著這段美事:
創辦自強日報社與遷移歷史
自強日報社是程先生繼創辦國際譯報社之後所創辦的第一個報社,以此切開留學巴黎之前後辦報經歷。程先生有這麼一段記述:
等博士將弄到手時,日本已佔領了我們的北平南京。………當我由歐洲回到武漢時,不久武漢又失了。我在武昌辦的一個報社,便遷到常德,後來我終於到了重慶,又到了昆明,再回到上饒,當時曾路過鵝湖,一瞥之下,印象是很淡的。(《憶鵞湖》)
關於自強日報社現今所存的訊息亦極其薄弱,蓋「報」者不若雜誌期刊,想一則老百姓們習慣用報紙包物可保溫,二則日報者是每日新聞,一天過了就是舊聞,看過也就拿來墊桌面、包殘渣,除非機關單位圖書館等刻意留存,否則較少存於後世,尤其日軍敵機轟炸軍民撤退逃難的歲月,更加難以留存於世。《自強日報》之片紙隻字大概俱毀於烽火之中,現今除了可以在幾篇文章提起《自強日報》與程兆熊先生外,只存程先生自己的記述了,而我們所看見的兩篇相關文章,則多有揣測與誤記誤評現象,但亦有值得參考的內容,我們一起於後見端詳。
程先生除了在《憶鵞湖》中提到辦了自強日報社,並於《山川草木間》、《論中國山水》及《九十回憶》三書裡多次把當時自強日報社因日軍的侵襲而輾轉的艱難行跡記錄了下來,由此可知《自強日報》對程先生一生而言概亦極具意義,方每每提起。
抗日戰爭期間,余由武漢將所辦之自強日報,搬至湖南常德。常德在長沙大火時,一度危急,余之家人遂由常德遷桃源,又遷沅陵,終於入蜀,卜居歌樂山中。自民國二十八年年初起,至民國三十年春止,凡二載有餘。(《山川草木間》)
自強日報社創設於武昌,因武漢淪陷而由程先生親自將其遷至湖南常德,結果除了敵機轟炸外又受長沙大火波及,程先生行跡便又離開常德。此長沙大火,史稱文夕大火,「文」字來自中國歷史上特有的一種電報紀日方法的韻目代日,即十二日,所以長沙大火發生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深夜,即十三日凌晨的人為失控火災。陳誠先生可說是當事人,他說:
抗戰八年,有兩件最使人痛心的事:一件就是汪兆銘甘心作漢奸,一件就是張治中長沙放火。
武漢會戰告一段落後,廣州亦已陷入敵手。此時,敵人在戰略上雖不再作速戰速決的打算,但打通粵漢路,藉以切斷我西南大後方與東南沿海的聯絡,卻是因利乘便之舉。為達成這項目的,敵人下一步的企圖就是占領長沙。(《陳誠回憶錄》)
誰創辦了《理想與文化》月刊?
且看程兆熊先生與程行敬先生
程先生說《理想與文化》前七期是在重慶出版,概這是一開始的規劃,而創刊號出版時程先生遠在昆明,或許從第三期以後《理想與文化》的編輯并不是在成都,實則已由昆明程先生所任職的川滇特別黨部宣傳科進行的了。就程兆熊先生所述種種以及《理想與文化》月刊的重慶社址設在「重慶上清寺特圍鮮宅」,可以很清楚知道,這與程先生絕對脫離不了關係,因為「上清寺」是程先生回到重慶居住的地方,「鮮宅」即是程先生好友鮮季明。我們儘是可見程先生的人脈資源之廣博的,不論其行至何處,何處便可聚攏一批有志之士行有志之事,筆者與此端又深有戚戚焉矣。
究竟是誰真正創辦且編輯發行了《理想與文化》?我們且可從以下資料獲知一些訊息:
第七期前《理想與文化》掛名社長兼發行人的廖聞天先生是重慶江津縣愛國商人,吳漢驥先生是民初著名詩人吳芳吉的二兒子(吳宓先生曾著有《吳芳吉先生傳略》),也是江津人,而程行敬先生更是江津的大地主,江津與白沙合稱津沙,在抗日戰爭時是中國大後方四大文化區之一(當時重慶尚屬四川),這大後方文化區還包括我們此前提過的中國哲學研究所成立之處的北碚。當時歐陽竟無先生的支那內學院亦遷於江津,故與程先生等眾人一起討論刊名,程行敬先生乃於其時求學於支那內學院。程先生嘗如是說:
我也想著我的鄉前輩歐陽竟無先生對我的一位本家程行敬君之言。一次是當他閉門讀《莊子》時,歐陽先生正種小菜完畢,乃過門而入,以泥手示之曰:
「是你在讀莊子,還是我在讀莊子」?
一次是他去歐陽先生房中,問《中庸》「天地位,萬物育」之義。歐陽先生即說道:
「你看我這裡,窗明几淨,人在窗前,書在架上。這就是: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要之歐陽先生一生學佛,獨創支那內學院,說這些話時,正式對日抗戰內學院西遷至四川江津之時,我那本家,是江津的大地主,求學於院中。……
我在抗日戰爭時,因留法之故,被派至滇越鐵路。乃函內學之本家來顛擔任秘書,彼向歐陽先生請是,即獲允准,並謂:
「此時,你應竭力前往相助,義不容辭。」
此時,雲南已轉為前方。義之所在,自歐陽先生視之,除敵人外,一切已無鴻溝。(《儒家思想──性情之教》)
程兆熊先生去昆明任川滇鐵路特別黨部主任委員時,請程行敬先生去做其秘書,在昆明時常同遊滇之高山流水。程行敬先生是歐陽竟無先生支那內學院的學生,與唐君毅先生父母交往甚深,一說是唐君毅先生父親唐迪風先生的及門弟子。程行敬先生因程兆熊先生邀約其赴昆明,且已得到歐陽竟無先生之允准,便在臨行前探望師母,當時唐老夫人記述:「癸未春二月程君敬晚過 我將應友人約赴昆明任某職 其悲憫之懷不容自己 鄉多求請其事者或白冤或次述紓困人 感君飢春風無纖塵勤大學讀竭誠 贈化閒泛泛」、「行敬三十一初度與法雨合影詩見示茲將南去昆明和韻戲作」(唐陳卓僊,《思復堂遺詩》,臺灣學生書局,一九七七),乃作〈贈程行敬〉一詩贈之為勉:
平時摩得熟,臨時用得著。 首在明明德,新民居其末。 思誠泣鬼神,行健撼山嶽。 如-奇花初胎,如源泉活活。 顧諟天明命,致知在格物。 汲汲魯中叟,彌縫乏其術。 我佛大慈悲,慈航空寂寞。 道德五千言,世人尚咄咄。 感君饑溺懷,展轉傷局躅。 際曉南其轍,彈冠俟心腹。 春風入庭戶,明月照華屋。 几淨無纖塵,勤攜《大學》讀。 竭誠奉贈君,未遑計辭俗。 (秦春燕,〈「詩以教何」與「詩何以教」〉,關東學刊,二〇二〇年第二期);《思復堂遺詩》箋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八年)
由上可知程行敬先生是應了程兆熊先生之約,歲後(一九四三年二月)亦去了昆明。而程行敬先生還真是為了去幫程兆熊先生方於是時(一九四三年二月)入黨,三月正式入職於川滇鐵路特別黨部,其職為宣傳科長,並於該年四月返回重慶參加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二十五期(四月十一至五月十六日),被編入第一大隊第三中隊。然程行敬先生自己所寫的「人事調查表」中,作為理想與文化月刊總編輯一職,竟是從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一月起始,這便顛覆了吾人之認知,《理想與文化》創刊號是直到這年的十二月才出刊的,依程行敬先生所載,那末,筆者戲稱是在那年的十月,眾人餞別程兆熊先生時方說起辦《理想與文化》便不成立,眾人商討的時間便往前挪到了程兆熊先生從上饒第三戰區的文化設計委員會回到重慶中訓團時即已商榷!經過一年的籌措,餞別會上或許是鮮季明先生說:設址就設在我家吧!這樣將出版的時間提上了日程也說不定。(有時候不得不有點兒天馬行空的想像,那場景便鮮活了起來)《理想與文化》第二期是程行敬先生出行昆明前出版的(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而第三期第四期合刊則是其在昆明準備回重慶受訓之前出版的(一九四三年四月),如此可斷:程行敬先生是名符其實的總編輯。
程行敬先生受完訓回到昆明,在該年(一九四三)六月提交的工作報告書則載(〈程行敬〉,《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29-060000-1253):
余於今春始奉 委到川滇鐵路特黨部工作,任職不久,即奉調來團受訓,特黨部於去冬始成立各項工作,正開始發展,現辦有川滇月刊,已出至第二期,川滇畫報,亦出至第二期,以上兩種,均為月刊,外有曙村壁報,每週一次,出至第八期。共有四區黨部,黨員六百二十五人。
所以可以得知程先生是在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秋去到昆明籌備川滇鐵路特別黨部,年末與此同時,有一位曹伯森先生,其於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五月任職川滇鐵路特別黨部宣傳科科長兼人事室主任,其直屬長官便是時任川滇特別黨部主任委員的程兆熊先生,而陳誠先生時為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往前看曹伯森先生之任職過程有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任中央軍官學校政治部政治教官,其時之長官為政治部主任陳誠先生;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一月起至隔年(一九四三)五月任五十四軍司令部秘書,其長官為黃維先生,這很容易聯想曹先生與程先生會有的交集。曹先生在川滇鐵路特別黨部任職三個月後(即同年約八月間)上呈一份給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的學員工作報告書,其「工作概況」一欄內載(〈曹伯森(曹符任)〉,《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29-210000-3643):
本人現任宣傳科科長間人事室主任,本部人員無多關核人事管理業務,較為簡單,故本人負責工作側重宣傳,而宣傳工作中尤以編辦各種刊物為主,本部所辦刊物有「川滇月刊」「曙報週刊」「理想與文化月刊」「曙報」等四種,均為本科負責編輯。
關於程行敬先生與曹伯森先生所各提到的《川滇畫報》及《川滇月刊》目前皆未能找到存刊,應許是敘昆(川滇)鐵路特別黨部當時黨內的刊物。我們在一份由中國國民黨敘昆鐵路特別黨部籌備員樓兆元先生所造,以中國國民黨敘昆鐵路黨部之名呈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的「三十二年度工作計畫大綱簡明表及支出概算表」(由敘昆川滇兩路局組成,由部補助,當時交通部部長朱家驊先生),內見將《川滇月刊》及《西南日報》、《西南交通月刊》等三份刊物的費用編入活動費中,《川滇月刊》編費為九萬元;既是「三十二年度支出概算表」,或許是程先生尚未抵達昆明之前即已做的概算,若以程行敬先生提交報告的六月時說兩份月刊皆已出第二期,那必然是在程先生就任時才出版的。而這《曙報周刊》與《曙報》應許就是程先生請吳宓先生當主編,最終沒有辦成的刊物(於後將述及)。
曹先生的報告中另有「服務機關內優良人才與事實」一欄,欣見曹先生對其長官程兆熊先生之評價,內載:「本部主任委員程兆熊學術修養甚好,有價值之著作頗多。」而程行敬先生則如此寫:「主任委員程兆熊涵養純粹,品德甚高,堪為黨人模範,書記長凌樹藩堅毅果敢,力行甚勇」。
曹伯森先生接任宣傳科科長,或許程行敬先生一開始乃任宣傳科科長,受訓回滇之後,可能調任程兆熊先生所言的「秘書」一職,而原職由曹先生補任,這個時間點(五月)是可以對上的。我們從側面來看看程先生的本家,這是極難得看見中央訓委會黨政班對一位受訓學員的評價像程行敬先生這樣高的:
第二十五期受訓川滇鐵路特黨部科長程行敬 四川江津
人:品行端正,性情寬和,志趣高尚,氣度寬大,思想靈敏,盡忠職守,學識優良,才具幹練,經驗尚豐,體格活潑,儀表恭敬,工作迅速。
事:擅長文字,並諳音樂,可謂多才多藝,對於宣傳工作,頗能勝任。
視察意見:該元素質甚佳,文字音樂均所擅長,如能以之擔任宣傳工作或可更有較優之成績表現。
程行敬先生在填寫的「現職」欄上是將川滇鐵路特別黨部宣傳科長及理想與文化月刊總編輯兩個身份同時寫上的,亦即都是現在進行式。這曹先生只小程先生三歲,從軍前當過中學校長,離開軍職擔任大學教授,這報告應不至於糊寫,那末,當時這四份刊物是由川滇鐵路特別黨部所辦,既然編辦刊物是川滇鐵路特別黨部宣傳科的主要工作,顯然已經接手編輯已出版的《理想與文化月刊》與《川滇月刊》和計劃出版的《曙報》與《曙報周刊》,然而《理想與文化》的總編輯依然是程行敬先生。
程先生於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十一月十二日的國父誕辰紀念日作了〈從人性與人之使命悼許思園先生〉以悼念許先生,這離許先生去世的一九七四年已是六年之後,概得知訊息的時間已是晚。程先生與許思園先生之情誼從中山大學畢業後前往南京創業便已開始,難得人生得知己,在南京同遊共語,在南昌同行暢談,在巴黎同學共食。
他在大同大學畢業後,即被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請去,和宗白華、方東美先生等同事。那時我正在南京辦國際譯報。我由他的表弟楊蔭渭先生介紹,才和他相識,並常來往。(〈從人性與人之使命悼許思園先生〉)
程先生之寫舊詩乃因許先生建議,程先生之對儒學興趣亦有許先生之影響。程先生提及與許思園先生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夏天認識以後的往來樂趣,更言其性情:
我因常和許思園兄同去雞鳴寺,且住處相近,故無所不談,無所不議。有一次論到明太祖,他忽一言一發,儘讓我一人說個不休。問他亦不答,別時亦不送,而且態度冷冷然。過了一些時,我再去看他,向他請教,他方言道:這就是我的試探,看你如何?隨後,他忽勸我不要做新詩。可以做做舊詩。那時,我們正在雞鳴寺,面對紫金山,俯視玄武湖。我乃言:「天臨湖水近,地接遠山間,野堤春草綠,隔水菜花黃」,他便大笑了。他的智慧極高,學識自然更博。他能詩,而不作詩。
那時,南昌設立了一個行營,成一軍事重鎮和安內的中心,同時也由那裡發出一個中國文化學會和新生活運動的號召。我和君毅、思園二兄南昌之行,即因此故。
我們乘坐長江輪,來往都經過九江,並宿於潯陽江頭。我們無所不談,大快平生。
我們來時,在潯陽江頭一宿。我們回時,又在潯陽江上一宿。我們三人談到深夜。(《九十回憶》)
我們很清楚知道唐君毅先生是透過許思園先生介紹給程兆熊先生的,而許思園先生則是由楊蔭渭先生介紹給程先生認識,楊蔭渭先生是楊蔭鴻先生之弟(許思園先生的表兄),楊蔭鴻先生介紹其弟楊蔭渭與程先生相識。如此形成了這個朋友圈,也因此方有後來程許唐三人於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同往南昌行營謁見蔣委員長,(此南昌行及唐先生主編《小國際》二事,於後續談)及說好了許先生赴巴黎留學,由唐先生繼任其教職,而程先生則欲去巴黎籌辦國際譯報社分社。結果,最終反倒是程先生先去了巴黎,沒設成分社,倒取得了法國巴黎園藝工程師和文學博士,而許先生亦非直奔巴黎而是先至倫敦再赴巴黎,去巴黎的時間應該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年中之時了,且程先生竟成了許先生的媒人,兩人先後取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程先生憶著這段美事:
創辦自強日報社與遷移歷史
自強日報社是程先生繼創辦國際譯報社之後所創辦的第一個報社,以此切開留學巴黎之前後辦報經歷。程先生有這麼一段記述:
等博士將弄到手時,日本已佔領了我們的北平南京。………當我由歐洲回到武漢時,不久武漢又失了。我在武昌辦的一個報社,便遷到常德,後來我終於到了重慶,又到了昆明,再回到上饒,當時曾路過鵝湖,一瞥之下,印象是很淡的。(《憶鵞湖》)
關於自強日報社現今所存的訊息亦極其薄弱,蓋「報」者不若雜誌期刊,想一則老百姓們習慣用報紙包物可保溫,二則日報者是每日新聞,一天過了就是舊聞,看過也就拿來墊桌面、包殘渣,除非機關單位圖書館等刻意留存,否則較少存於後世,尤其日軍敵機轟炸軍民撤退逃難的歲月,更加難以留存於世。《自強日報》之片紙隻字大概俱毀於烽火之中,現今除了可以在幾篇文章提起《自強日報》與程兆熊先生外,只存程先生自己的記述了,而我們所看見的兩篇相關文章,則多有揣測與誤記誤評現象,但亦有值得參考的內容,我們一起於後見端詳。
程先生除了在《憶鵞湖》中提到辦了自強日報社,並於《山川草木間》、《論中國山水》及《九十回憶》三書裡多次把當時自強日報社因日軍的侵襲而輾轉的艱難行跡記錄了下來,由此可知《自強日報》對程先生一生而言概亦極具意義,方每每提起。
抗日戰爭期間,余由武漢將所辦之自強日報,搬至湖南常德。常德在長沙大火時,一度危急,余之家人遂由常德遷桃源,又遷沅陵,終於入蜀,卜居歌樂山中。自民國二十八年年初起,至民國三十年春止,凡二載有餘。(《山川草木間》)
自強日報社創設於武昌,因武漢淪陷而由程先生親自將其遷至湖南常德,結果除了敵機轟炸外又受長沙大火波及,程先生行跡便又離開常德。此長沙大火,史稱文夕大火,「文」字來自中國歷史上特有的一種電報紀日方法的韻目代日,即十二日,所以長沙大火發生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深夜,即十三日凌晨的人為失控火災。陳誠先生可說是當事人,他說:
抗戰八年,有兩件最使人痛心的事:一件就是汪兆銘甘心作漢奸,一件就是張治中長沙放火。
武漢會戰告一段落後,廣州亦已陷入敵手。此時,敵人在戰略上雖不再作速戰速決的打算,但打通粵漢路,藉以切斷我西南大後方與東南沿海的聯絡,卻是因利乘便之舉。為達成這項目的,敵人下一步的企圖就是占領長沙。(《陳誠回憶錄》)
誰創辦了《理想與文化》月刊?
且看程兆熊先生與程行敬先生
程先生說《理想與文化》前七期是在重慶出版,概這是一開始的規劃,而創刊號出版時程先生遠在昆明,或許從第三期以後《理想與文化》的編輯并不是在成都,實則已由昆明程先生所任職的川滇特別黨部宣傳科進行的了。就程兆熊先生所述種種以及《理想與文化》月刊的重慶社址設在「重慶上清寺特圍鮮宅」,可以很清楚知道,這與程先生絕對脫離不了關係,因為「上清寺」是程先生回到重慶居住的地方,「鮮宅」即是程先生好友鮮季明。我們儘是可見程先生的人脈資源之廣博的,不論其行至何處,何處便可聚攏一批有志之士行有志之事,筆者與此端又深有戚戚焉矣。
究竟是誰真正創辦且編輯發行了《理想與文化》?我們且可從以下資料獲知一些訊息:
第七期前《理想與文化》掛名社長兼發行人的廖聞天先生是重慶江津縣愛國商人,吳漢驥先生是民初著名詩人吳芳吉的二兒子(吳宓先生曾著有《吳芳吉先生傳略》),也是江津人,而程行敬先生更是江津的大地主,江津與白沙合稱津沙,在抗日戰爭時是中國大後方四大文化區之一(當時重慶尚屬四川),這大後方文化區還包括我們此前提過的中國哲學研究所成立之處的北碚。當時歐陽竟無先生的支那內學院亦遷於江津,故與程先生等眾人一起討論刊名,程行敬先生乃於其時求學於支那內學院。程先生嘗如是說:
我也想著我的鄉前輩歐陽竟無先生對我的一位本家程行敬君之言。一次是當他閉門讀《莊子》時,歐陽先生正種小菜完畢,乃過門而入,以泥手示之曰:
「是你在讀莊子,還是我在讀莊子」?
一次是他去歐陽先生房中,問《中庸》「天地位,萬物育」之義。歐陽先生即說道:
「你看我這裡,窗明几淨,人在窗前,書在架上。這就是: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要之歐陽先生一生學佛,獨創支那內學院,說這些話時,正式對日抗戰內學院西遷至四川江津之時,我那本家,是江津的大地主,求學於院中。……
我在抗日戰爭時,因留法之故,被派至滇越鐵路。乃函內學之本家來顛擔任秘書,彼向歐陽先生請是,即獲允准,並謂:
「此時,你應竭力前往相助,義不容辭。」
此時,雲南已轉為前方。義之所在,自歐陽先生視之,除敵人外,一切已無鴻溝。(《儒家思想──性情之教》)
程兆熊先生去昆明任川滇鐵路特別黨部主任委員時,請程行敬先生去做其秘書,在昆明時常同遊滇之高山流水。程行敬先生是歐陽竟無先生支那內學院的學生,與唐君毅先生父母交往甚深,一說是唐君毅先生父親唐迪風先生的及門弟子。程行敬先生因程兆熊先生邀約其赴昆明,且已得到歐陽竟無先生之允准,便在臨行前探望師母,當時唐老夫人記述:「癸未春二月程君敬晚過 我將應友人約赴昆明任某職 其悲憫之懷不容自己 鄉多求請其事者或白冤或次述紓困人 感君飢春風無纖塵勤大學讀竭誠 贈化閒泛泛」、「行敬三十一初度與法雨合影詩見示茲將南去昆明和韻戲作」(唐陳卓僊,《思復堂遺詩》,臺灣學生書局,一九七七),乃作〈贈程行敬〉一詩贈之為勉:
平時摩得熟,臨時用得著。 首在明明德,新民居其末。 思誠泣鬼神,行健撼山嶽。 如-奇花初胎,如源泉活活。 顧諟天明命,致知在格物。 汲汲魯中叟,彌縫乏其術。 我佛大慈悲,慈航空寂寞。 道德五千言,世人尚咄咄。 感君饑溺懷,展轉傷局躅。 際曉南其轍,彈冠俟心腹。 春風入庭戶,明月照華屋。 几淨無纖塵,勤攜《大學》讀。 竭誠奉贈君,未遑計辭俗。 (秦春燕,〈「詩以教何」與「詩何以教」〉,關東學刊,二〇二〇年第二期);《思復堂遺詩》箋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八年)
由上可知程行敬先生是應了程兆熊先生之約,歲後(一九四三年二月)亦去了昆明。而程行敬先生還真是為了去幫程兆熊先生方於是時(一九四三年二月)入黨,三月正式入職於川滇鐵路特別黨部,其職為宣傳科長,並於該年四月返回重慶參加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二十五期(四月十一至五月十六日),被編入第一大隊第三中隊。然程行敬先生自己所寫的「人事調查表」中,作為理想與文化月刊總編輯一職,竟是從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一月起始,這便顛覆了吾人之認知,《理想與文化》創刊號是直到這年的十二月才出刊的,依程行敬先生所載,那末,筆者戲稱是在那年的十月,眾人餞別程兆熊先生時方說起辦《理想與文化》便不成立,眾人商討的時間便往前挪到了程兆熊先生從上饒第三戰區的文化設計委員會回到重慶中訓團時即已商榷!經過一年的籌措,餞別會上或許是鮮季明先生說:設址就設在我家吧!這樣將出版的時間提上了日程也說不定。(有時候不得不有點兒天馬行空的想像,那場景便鮮活了起來)《理想與文化》第二期是程行敬先生出行昆明前出版的(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而第三期第四期合刊則是其在昆明準備回重慶受訓之前出版的(一九四三年四月),如此可斷:程行敬先生是名符其實的總編輯。
程行敬先生受完訓回到昆明,在該年(一九四三)六月提交的工作報告書則載(〈程行敬〉,《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29-060000-1253):
余於今春始奉 委到川滇鐵路特黨部工作,任職不久,即奉調來團受訓,特黨部於去冬始成立各項工作,正開始發展,現辦有川滇月刊,已出至第二期,川滇畫報,亦出至第二期,以上兩種,均為月刊,外有曙村壁報,每週一次,出至第八期。共有四區黨部,黨員六百二十五人。
所以可以得知程先生是在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秋去到昆明籌備川滇鐵路特別黨部,年末與此同時,有一位曹伯森先生,其於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五月任職川滇鐵路特別黨部宣傳科科長兼人事室主任,其直屬長官便是時任川滇特別黨部主任委員的程兆熊先生,而陳誠先生時為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往前看曹伯森先生之任職過程有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任中央軍官學校政治部政治教官,其時之長官為政治部主任陳誠先生;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一月起至隔年(一九四三)五月任五十四軍司令部秘書,其長官為黃維先生,這很容易聯想曹先生與程先生會有的交集。曹先生在川滇鐵路特別黨部任職三個月後(即同年約八月間)上呈一份給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的學員工作報告書,其「工作概況」一欄內載(〈曹伯森(曹符任)〉,《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29-210000-3643):
本人現任宣傳科科長間人事室主任,本部人員無多關核人事管理業務,較為簡單,故本人負責工作側重宣傳,而宣傳工作中尤以編辦各種刊物為主,本部所辦刊物有「川滇月刊」「曙報週刊」「理想與文化月刊」「曙報」等四種,均為本科負責編輯。
關於程行敬先生與曹伯森先生所各提到的《川滇畫報》及《川滇月刊》目前皆未能找到存刊,應許是敘昆(川滇)鐵路特別黨部當時黨內的刊物。我們在一份由中國國民黨敘昆鐵路特別黨部籌備員樓兆元先生所造,以中國國民黨敘昆鐵路黨部之名呈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的「三十二年度工作計畫大綱簡明表及支出概算表」(由敘昆川滇兩路局組成,由部補助,當時交通部部長朱家驊先生),內見將《川滇月刊》及《西南日報》、《西南交通月刊》等三份刊物的費用編入活動費中,《川滇月刊》編費為九萬元;既是「三十二年度支出概算表」,或許是程先生尚未抵達昆明之前即已做的概算,若以程行敬先生提交報告的六月時說兩份月刊皆已出第二期,那必然是在程先生就任時才出版的。而這《曙報周刊》與《曙報》應許就是程先生請吳宓先生當主編,最終沒有辦成的刊物(於後將述及)。
曹先生的報告中另有「服務機關內優良人才與事實」一欄,欣見曹先生對其長官程兆熊先生之評價,內載:「本部主任委員程兆熊學術修養甚好,有價值之著作頗多。」而程行敬先生則如此寫:「主任委員程兆熊涵養純粹,品德甚高,堪為黨人模範,書記長凌樹藩堅毅果敢,力行甚勇」。
曹伯森先生接任宣傳科科長,或許程行敬先生一開始乃任宣傳科科長,受訓回滇之後,可能調任程兆熊先生所言的「秘書」一職,而原職由曹先生補任,這個時間點(五月)是可以對上的。我們從側面來看看程先生的本家,這是極難得看見中央訓委會黨政班對一位受訓學員的評價像程行敬先生這樣高的:
第二十五期受訓川滇鐵路特黨部科長程行敬 四川江津
人:品行端正,性情寬和,志趣高尚,氣度寬大,思想靈敏,盡忠職守,學識優良,才具幹練,經驗尚豐,體格活潑,儀表恭敬,工作迅速。
事:擅長文字,並諳音樂,可謂多才多藝,對於宣傳工作,頗能勝任。
視察意見:該元素質甚佳,文字音樂均所擅長,如能以之擔任宣傳工作或可更有較優之成績表現。
程行敬先生在填寫的「現職」欄上是將川滇鐵路特別黨部宣傳科長及理想與文化月刊總編輯兩個身份同時寫上的,亦即都是現在進行式。這曹先生只小程先生三歲,從軍前當過中學校長,離開軍職擔任大學教授,這報告應不至於糊寫,那末,當時這四份刊物是由川滇鐵路特別黨部所辦,既然編辦刊物是川滇鐵路特別黨部宣傳科的主要工作,顯然已經接手編輯已出版的《理想與文化月刊》與《川滇月刊》和計劃出版的《曙報》與《曙報周刊》,然而《理想與文化》的總編輯依然是程行敬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