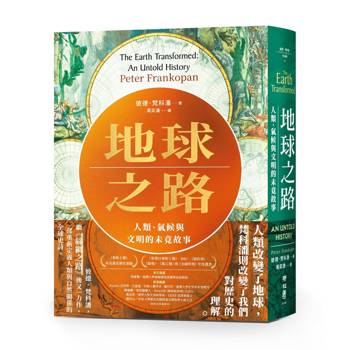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大地還是混沌空虛……
──《創世記》1:1
對於全球氣候的劇變,我們都要感恩戴德。要是沒有數十億年間劇烈的天體與太陽活動、頻繁的小行星撞擊、開天闢地的火山爆發、大氣成分的徹底轉變、壯觀的板塊漂移與不斷的生物適應生物,今天就沒有我們。天體物理學家常說,在恆星周邊有些位置剛好的地方,不會太熱也不會太冷,這就是所謂的「適居帶」(goldilocks zone)。地球就是眾多例子之一。不過,自從我們的行星在大約四十六億年前形成以來,地表的環境一直在改變,有時候堪稱是災變。地球存在的這段時間裡,大部分的時候是我們物種不可能會喜歡,甚至根本無法生存下來的。來到今日世界,我們以為人類造就了危險的環境與氣候變遷;但我們同時也是過往巨變的重要受益者。
我們在這顆行星上的角色真的微不足道。最早的人族(hominins)要到幾百萬年前才出現,而解剖結構上最早的現代人(包括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s〕)則是大約五十萬年前才出現。對於他們出現之後的這段期間,我們所知的不僅東一塊西一塊,很難詮釋,而且往往猜測成分居多。隨著時間逐漸接近現代,則有考古學能幫助我們更可靠地了解人類如何生活;但他們做了什麼、想過什麼、相信些什麼,則得等到大約五千年前,完整的書寫體系發展出來之後,我們才能了解。整體而言,我們據以細緻、縝密重建過去的那些敘述、文件與文本,只涵蓋世界歷史大約○.○○○一%的時間。人類這個物種不光是存在就很幸運,而且從歷史的大棋盤來看,我們是很晚才出現的新棋子。
人類就像最後一刻才登門的粗魯客人,大吵大鬧,簡直要把主人的家給拆了,自然環境遭受的人為衝擊不可小覷,而且衝擊的步調愈來愈快,不少科學家因此懷疑人類是否能長久存在。不過,大吵大鬧也不稀罕。首先,不是只有我們物種會改造周圍的環境,生物相(也就是植物、動物及微生物)當中的其他物種在人與自然的關係當中,既不是被動的參與者,也不是純粹的旁觀者,不只是單純的存在。每個物種都在改變、適應與演化的過程中發揮影響力,有時候也會造成毀滅性的後果。
正因為如此,部分學者對「人類世」的概念與名稱始終抱持批評態度,覺得不該把人類推上「特殊物種」的優越位置,好像是由人類界定什麼叫做「野生」、界定什麼是可以使用的「資源」(無論是否永續)。有人覺得這種作法「傲慢無比,太過高估人類的貢獻,還把其他生命形態貶到簡直是空氣的地步」。
***
自有地球以來,前半段時間的地球大氣幾乎沒有氧氣存在。我們的行星是經由漫長的聚合,經過一層又一層的累積才形成的,接著遭到火星大小的撞擊體強烈碰撞,釋放出足以融化地函的能量,岩漿海與蒸氣之間的交互作用才產生最早的、無氧的大氣層。
地球的生物地球化學循環最終造成一次徹底的轉變。雖然各界對於產氧光合作用(oxygenic photosynthesis)如何發生、何時發生以及為何發生仍未有定論,但有機生物標記、化石和基因組規模數據等證據顯示,藍菌(cyanobacteria)演化後吸收陽光,從中獲得能量,用水與二氧化碳製造出糖,同時釋出副產物──氧氣。新模型顯示,早期地球每年發生十億至五十億次閃電,這或許是前生物反應磷(prebioticreactive phosphorus)之所以如此大量的由來,而磷則是陸生生命出現的關鍵。
大約三十億年前(或者更早),已經有足夠的氧氣製造出來,在養分豐富、擾動較少的淺海棲地形成「綠洲」。大約在二十五億至二十三億年前,大氣含氧量迅速累積,原因可能是化學反應、演化發展、藍菌超大量增生、火山爆發或地球自轉減速(或上述五種因素的結合),引發所謂的「大氧化事件」(Great Oxidation Event),這是複雜生命體降生途中的重要瞬間。
氣候也因此出現劇變,迅速增加的氧氣與甲烷反映,產生水蒸氣與二氧化碳。超級大陸因陸塊碰撞形成時,地球的溫室效應也在減弱,導致整個行星完全被冰雪所覆蓋。地球繞日的軌道變化,亦即所謂的「米蘭科維奇循環」(Milankovitch cycle),可能也在這段過程中發揮影響力。巨大隕石撞擊同樣是可能因素,一來是拋飛入大氣的碎片阻擋陽光與熱,二來撞擊力也影響大陸的形成。數百萬年期間的冰河時期有強有弱,但「雪球地球」(Snowball Earth)整體效應強烈如斯,部分科學家甚至因此稱這整段時期為「氣候災難」。
不穩而複雜的雪球地球過程,是現今研究中頗有進展的主題。這次冰河期和後來的冰河期一樣,都對地球的動植物生命帶來深遠的改變。其中,小型生物往更大的體型演化,因為冷冽海水稠度更高,比較大的體型能抵銷阻力,加快移動速度。近年來,有人主張八千公里長的「超級山脈」說不定對大氣氧含量的提升有所影響,而數億年間從山脈上受到侵蝕、進入海洋的沉積物,如磷、鐵和養分也推動生物的演化。
複雜、肉眼可見的生物化石紀錄,在埃迪卡拉生物群(Ediacara Biota)時期開始出現。咸認始於五億七千萬年前的埃迪卡拉紀,已有至少四十種經辨識出的物種發展成對稱的多細胞動物──據信對稱有助於行動。埃迪卡拉紀不僅是各種海洋動物多元分化的時期,也是其演化、發展與適應的重要時期,例如三葉蟲的前肢就是在這段期間發展出呼吸器官。
奧陶紀(Ordovician)接近尾聲時(約四億四千萬年前),氣候突然冷卻(可能是引發阿帕拉契山脈〔Appalachian mountains〕造山運動的同一場板塊運動所導致的),氣溫陡降,海平面降低,並引發深海洋流的轉變,同時海平面下降,海中浮游與自游物種的棲地因此縮小。同一場寒化引發了一波滅絕;另一波滅絕則發生在溫度回正、海平面上升、洋流停滯,導致氧氣量驟降時。汞的痕跡和明顯的酸化跡象顯示,火山活動是第二階段滅絕過程的關鍵因素,最終有八五%的物種滅絕。
對於這場幾乎消滅所有活物的滅絕中,火山爆發只是一個片段。月球可能也是接下來數百萬年間變化的一環。地球在撞擊中誕生,拋入太空的碎片形成月球。月球的引力是潮汐的關鍵因素,因為有潮汐產生的海流,才能把熱從赤道帶往極區,徹底形塑地球的氣候。
月球以前距離地球更近(說不定只有今日距離的一半),潮汐力想必更強,對地球氣候與野生動植物的影響也更大:近年來的模擬顯示,大範圍的潮汐可能迫使硬骨魚類進入陸地上的淺水池,進而促成演化出可以承重的肢體與呼吸器官。
月球不僅在地球本身的轉變中軋了一腳,甚至影響這顆星球上的生命發展。月球的影響力如今依然重要。許多海洋生物的繁殖週期跟月相緊密同步,魚、蟹與浮游生物的遷徙、產卵也受到月光的觸發。珊瑚基因會根據月亮的盈虧改變其活動量。月相似乎會影響塞倫蓋蒂(Serengeti)地區牛羚的交配季節,而且跟母牛的自然分娩有關。滿月時,許多靈長類動物的夜間活動更活躍──也許是因為光線更好,讓牠們更有機會避開掠食者。據觀察,信天翁在月明夜更活躍。雖然研究還不多,但月相與月光似乎跟數十億季節性動物的年度遷徙密切相關,尤其是鳥類,因為光線對牠們的覓食機會影響極大。
人類的行為、活動力,甚至是生育力,似乎跟月相的變化有重要的關係。學者研究沒有電力供應(因此是很好的控制變因)的阿根廷原住民社區,結果顯示在滿月前的幾個晚上,也就是太陽下山後的幾個小時內仍然有月光的晚上,大家比較晚睡覺,睡眠時間也比較短。也就是說,沒有人工照明設施的前工業社群,人們的睡眠模式可能同樣受到月相的影響。女性月經週期的長期數據,表現出跟月光與月球重力有相關性,部分學者因此主張人類的生殖行為原本跟月相是同步的,是近期才受到現代生活方式的影響而改變。
流行文化經常反映出月亮會影響、干擾人的行為舉止,比方說「瘋子」(lunatic)一語就暗示精神疾病與月亮的關係,但就算其間有任何因果關係,科學家也往往會淡化之。不過,部分研究人員也強調,躁鬱病患的發作,跟三種獨特的月相有顯著的同步性。也就是說,月亮對洋流、全球氣溫與氣候、生殖週期,乃至於整個地球上的生命,都有重要的影響。
至於月潮對於電離層-增溫層天氣體系,乃至於對演化過程或滅絕事件的影響,則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滅絕事件並不罕見。情況最為慘烈的滅絕事件,發生在兩億五千兩百萬年前,人稱「大滅絕」(Great Dying)。這次事件的主因,是今日西伯利亞的位置發生前所未有的火山爆發,噴發極為大量的岩漿。很有可能是在某個關鍵的瞬間,地面上不再噴發岩漿,開始形成熔岩層,把氣體困在地表下,直到引發一連串超級猛烈的噴發才釋放出來。無論具體情況如何,總之,有大量的溫室氣體噴發進入大氣層,引發生物圈的不穩定。土壤與海水溫度一開始可能上升八至一○℃,然後又增加了六至八℃,赤道地區的溫度恐高達四○℃。結果九六%的海洋生物滅絕,四分之三的陸地動物消失,地球上的森林也全數消失了。
──《創世記》1:1
對於全球氣候的劇變,我們都要感恩戴德。要是沒有數十億年間劇烈的天體與太陽活動、頻繁的小行星撞擊、開天闢地的火山爆發、大氣成分的徹底轉變、壯觀的板塊漂移與不斷的生物適應生物,今天就沒有我們。天體物理學家常說,在恆星周邊有些位置剛好的地方,不會太熱也不會太冷,這就是所謂的「適居帶」(goldilocks zone)。地球就是眾多例子之一。不過,自從我們的行星在大約四十六億年前形成以來,地表的環境一直在改變,有時候堪稱是災變。地球存在的這段時間裡,大部分的時候是我們物種不可能會喜歡,甚至根本無法生存下來的。來到今日世界,我們以為人類造就了危險的環境與氣候變遷;但我們同時也是過往巨變的重要受益者。
我們在這顆行星上的角色真的微不足道。最早的人族(hominins)要到幾百萬年前才出現,而解剖結構上最早的現代人(包括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s〕)則是大約五十萬年前才出現。對於他們出現之後的這段期間,我們所知的不僅東一塊西一塊,很難詮釋,而且往往猜測成分居多。隨著時間逐漸接近現代,則有考古學能幫助我們更可靠地了解人類如何生活;但他們做了什麼、想過什麼、相信些什麼,則得等到大約五千年前,完整的書寫體系發展出來之後,我們才能了解。整體而言,我們據以細緻、縝密重建過去的那些敘述、文件與文本,只涵蓋世界歷史大約○.○○○一%的時間。人類這個物種不光是存在就很幸運,而且從歷史的大棋盤來看,我們是很晚才出現的新棋子。
人類就像最後一刻才登門的粗魯客人,大吵大鬧,簡直要把主人的家給拆了,自然環境遭受的人為衝擊不可小覷,而且衝擊的步調愈來愈快,不少科學家因此懷疑人類是否能長久存在。不過,大吵大鬧也不稀罕。首先,不是只有我們物種會改造周圍的環境,生物相(也就是植物、動物及微生物)當中的其他物種在人與自然的關係當中,既不是被動的參與者,也不是純粹的旁觀者,不只是單純的存在。每個物種都在改變、適應與演化的過程中發揮影響力,有時候也會造成毀滅性的後果。
正因為如此,部分學者對「人類世」的概念與名稱始終抱持批評態度,覺得不該把人類推上「特殊物種」的優越位置,好像是由人類界定什麼叫做「野生」、界定什麼是可以使用的「資源」(無論是否永續)。有人覺得這種作法「傲慢無比,太過高估人類的貢獻,還把其他生命形態貶到簡直是空氣的地步」。
***
自有地球以來,前半段時間的地球大氣幾乎沒有氧氣存在。我們的行星是經由漫長的聚合,經過一層又一層的累積才形成的,接著遭到火星大小的撞擊體強烈碰撞,釋放出足以融化地函的能量,岩漿海與蒸氣之間的交互作用才產生最早的、無氧的大氣層。
地球的生物地球化學循環最終造成一次徹底的轉變。雖然各界對於產氧光合作用(oxygenic photosynthesis)如何發生、何時發生以及為何發生仍未有定論,但有機生物標記、化石和基因組規模數據等證據顯示,藍菌(cyanobacteria)演化後吸收陽光,從中獲得能量,用水與二氧化碳製造出糖,同時釋出副產物──氧氣。新模型顯示,早期地球每年發生十億至五十億次閃電,這或許是前生物反應磷(prebioticreactive phosphorus)之所以如此大量的由來,而磷則是陸生生命出現的關鍵。
大約三十億年前(或者更早),已經有足夠的氧氣製造出來,在養分豐富、擾動較少的淺海棲地形成「綠洲」。大約在二十五億至二十三億年前,大氣含氧量迅速累積,原因可能是化學反應、演化發展、藍菌超大量增生、火山爆發或地球自轉減速(或上述五種因素的結合),引發所謂的「大氧化事件」(Great Oxidation Event),這是複雜生命體降生途中的重要瞬間。
氣候也因此出現劇變,迅速增加的氧氣與甲烷反映,產生水蒸氣與二氧化碳。超級大陸因陸塊碰撞形成時,地球的溫室效應也在減弱,導致整個行星完全被冰雪所覆蓋。地球繞日的軌道變化,亦即所謂的「米蘭科維奇循環」(Milankovitch cycle),可能也在這段過程中發揮影響力。巨大隕石撞擊同樣是可能因素,一來是拋飛入大氣的碎片阻擋陽光與熱,二來撞擊力也影響大陸的形成。數百萬年期間的冰河時期有強有弱,但「雪球地球」(Snowball Earth)整體效應強烈如斯,部分科學家甚至因此稱這整段時期為「氣候災難」。
不穩而複雜的雪球地球過程,是現今研究中頗有進展的主題。這次冰河期和後來的冰河期一樣,都對地球的動植物生命帶來深遠的改變。其中,小型生物往更大的體型演化,因為冷冽海水稠度更高,比較大的體型能抵銷阻力,加快移動速度。近年來,有人主張八千公里長的「超級山脈」說不定對大氣氧含量的提升有所影響,而數億年間從山脈上受到侵蝕、進入海洋的沉積物,如磷、鐵和養分也推動生物的演化。
複雜、肉眼可見的生物化石紀錄,在埃迪卡拉生物群(Ediacara Biota)時期開始出現。咸認始於五億七千萬年前的埃迪卡拉紀,已有至少四十種經辨識出的物種發展成對稱的多細胞動物──據信對稱有助於行動。埃迪卡拉紀不僅是各種海洋動物多元分化的時期,也是其演化、發展與適應的重要時期,例如三葉蟲的前肢就是在這段期間發展出呼吸器官。
奧陶紀(Ordovician)接近尾聲時(約四億四千萬年前),氣候突然冷卻(可能是引發阿帕拉契山脈〔Appalachian mountains〕造山運動的同一場板塊運動所導致的),氣溫陡降,海平面降低,並引發深海洋流的轉變,同時海平面下降,海中浮游與自游物種的棲地因此縮小。同一場寒化引發了一波滅絕;另一波滅絕則發生在溫度回正、海平面上升、洋流停滯,導致氧氣量驟降時。汞的痕跡和明顯的酸化跡象顯示,火山活動是第二階段滅絕過程的關鍵因素,最終有八五%的物種滅絕。
對於這場幾乎消滅所有活物的滅絕中,火山爆發只是一個片段。月球可能也是接下來數百萬年間變化的一環。地球在撞擊中誕生,拋入太空的碎片形成月球。月球的引力是潮汐的關鍵因素,因為有潮汐產生的海流,才能把熱從赤道帶往極區,徹底形塑地球的氣候。
月球以前距離地球更近(說不定只有今日距離的一半),潮汐力想必更強,對地球氣候與野生動植物的影響也更大:近年來的模擬顯示,大範圍的潮汐可能迫使硬骨魚類進入陸地上的淺水池,進而促成演化出可以承重的肢體與呼吸器官。
月球不僅在地球本身的轉變中軋了一腳,甚至影響這顆星球上的生命發展。月球的影響力如今依然重要。許多海洋生物的繁殖週期跟月相緊密同步,魚、蟹與浮游生物的遷徙、產卵也受到月光的觸發。珊瑚基因會根據月亮的盈虧改變其活動量。月相似乎會影響塞倫蓋蒂(Serengeti)地區牛羚的交配季節,而且跟母牛的自然分娩有關。滿月時,許多靈長類動物的夜間活動更活躍──也許是因為光線更好,讓牠們更有機會避開掠食者。據觀察,信天翁在月明夜更活躍。雖然研究還不多,但月相與月光似乎跟數十億季節性動物的年度遷徙密切相關,尤其是鳥類,因為光線對牠們的覓食機會影響極大。
人類的行為、活動力,甚至是生育力,似乎跟月相的變化有重要的關係。學者研究沒有電力供應(因此是很好的控制變因)的阿根廷原住民社區,結果顯示在滿月前的幾個晚上,也就是太陽下山後的幾個小時內仍然有月光的晚上,大家比較晚睡覺,睡眠時間也比較短。也就是說,沒有人工照明設施的前工業社群,人們的睡眠模式可能同樣受到月相的影響。女性月經週期的長期數據,表現出跟月光與月球重力有相關性,部分學者因此主張人類的生殖行為原本跟月相是同步的,是近期才受到現代生活方式的影響而改變。
流行文化經常反映出月亮會影響、干擾人的行為舉止,比方說「瘋子」(lunatic)一語就暗示精神疾病與月亮的關係,但就算其間有任何因果關係,科學家也往往會淡化之。不過,部分研究人員也強調,躁鬱病患的發作,跟三種獨特的月相有顯著的同步性。也就是說,月亮對洋流、全球氣溫與氣候、生殖週期,乃至於整個地球上的生命,都有重要的影響。
至於月潮對於電離層-增溫層天氣體系,乃至於對演化過程或滅絕事件的影響,則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滅絕事件並不罕見。情況最為慘烈的滅絕事件,發生在兩億五千兩百萬年前,人稱「大滅絕」(Great Dying)。這次事件的主因,是今日西伯利亞的位置發生前所未有的火山爆發,噴發極為大量的岩漿。很有可能是在某個關鍵的瞬間,地面上不再噴發岩漿,開始形成熔岩層,把氣體困在地表下,直到引發一連串超級猛烈的噴發才釋放出來。無論具體情況如何,總之,有大量的溫室氣體噴發進入大氣層,引發生物圈的不穩定。土壤與海水溫度一開始可能上升八至一○℃,然後又增加了六至八℃,赤道地區的溫度恐高達四○℃。結果九六%的海洋生物滅絕,四分之三的陸地動物消失,地球上的森林也全數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