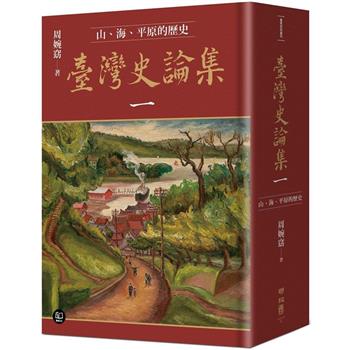(節錄)
第一章 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
引子
稱海上的島為山,是沿襲甚久的習慣。讀過中國詩詞的人,大都記得白居易〈長恨歌〉的詩句:「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這裡的仙山指海上神仙居住的島嶼。然而,不是神仙居住的島嶼才叫做山,舉凡海上諸島都可以稱山。我們或可推測,當人們搭船浮沉於茫茫大海中,遠遠望見島嶼時,不管大小,它的樣子總像是一座浮在水面上的山。
我們不知道稱海島為山,起源於何時,可以確定的是,明代海上行船人約定俗成稱島為山。例如,明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奉命出使琉球(沖繩,今屬日本),經過兩年的準備,他和隨員在嘉靖十三年五月五日(陰曆)從福建福州長樂縣廣石出海。由於逆風,船隻航行速度很慢,三天後(五月八日)出海口,「方一望汪洋矣」;他從船艙出來觀望,「四顧廓然,茫無山際,惟天光與水光相接耳。雲物變幻無窮,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雖若可樂,終不能釋然於懷。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第二天(五月十日),「南風甚速,舟行如飛」,他們「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得知明嘉靖年間,海上通稱島嶼為山,有時也稱為嶼。當船駛近島嶼,人們說「山將近矣」、「山近矣」。
陳侃出海後不久,看到的「小山」小琉球,如果按照第二天他們即經過平嘉山(彭佳嶼)、釣魚嶼等島嶼來看,他所望見的「小山」是臺灣島的一部分,從方位來看是北臺灣。這個時候的臺灣,還是「鮮為人知」,人們似乎還不清楚它是一個大島嶼,還是分成幾個小山。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了解臺灣的「身影」如何慢慢浮現在明人的視野中,由遠而近,由不熟悉而逐漸熟悉,由幾個島逐漸「合成」一個大島。然而,明朝之前,文獻上一直有讓後人爭論不休的疑似臺灣的記載。三國時代的夷洲、隋代的流求、宋朝的流求、元代的瑠求、琉球,都是難解之謎。讓我們先回顧這些說法吧。
一、夷洲與流求之謎
要談中國對臺灣的認識,一般總是從《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孫權傳)和《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談起,這是中文文獻中疑似臺灣的記載。已故的人類學家凌純聲先生甚至主張應該從《史記》〈東越列傳〉談起,認為臺灣可能是東越人所移殖的地方。這可能又太遙遠了。
關於《三國志》中的夷洲和《隋書》中的流求是否為臺灣,學者之間看法不同,說法時斷時續,算是個百年以上的爭論。我們先不去談爭論的內容,讓我們看看文獻本身的記載。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云:
〔黃龍〕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孫權「求」夷洲、亶洲的動機不清楚,或許仿秦始皇故事也未可知。其結果是,大軍無法抵達亶洲,卻到達夷洲,虜了數千人回來。亶洲傳言是秦始皇派徐福浮海求神山、仙藥最後所抵達的地方,這地方的人民常到會稽買布;會稽人出海也有遭風漂流到此地,這在在令人想起日本。我們知道後來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國是從長江口附近登陸,以此,日本人到會稽買布,也算合理。根據這份文獻,夷洲、亶洲一開始並舉,可見在人們的認知上,相距不遠。但是,實際浮海訪尋,亶洲又顯得遙不可及,大軍以抵達夷洲作結。
從以上如此簡短的文獻,要判斷夷洲是否為臺灣,其實並不具有太大的意義。倒是《三國志》其他兩個地方也提及「夷州」(此處「州」字無三點水,然根據文脈應即為上引之「夷洲」),這兩條都在列傳,與孫權想「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珠崖)」而遭到大臣勸阻有關,勸阻遣分軍遠征夷州分別為陸遜和全琮。據此,夷州和珠崖應有地理上的親近性(〈全琮傳〉云:「權將圍珠崖及夷州。」)。三國時的珠崖郡即海南島,孫權的夷州之役「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得不補失」,「權深悔之」。除了地理可能鄰近海南島之外,文獻遠不足以讓我們具體指夷州即臺灣。
如果《三國志》關於夷洲的記載過於簡略,《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所記該國情況則相當詳盡。〈流求國〉起頭云:「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以下是很長的一大段文字,描寫流求國的風土人情,包羅甚廣,不遜同書對日本的描寫,若全文迻錄,恐過於冗贅,在此僅引最後一段。文末云:
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崐崘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這是個「屢勸不聽」的故事。流求至少兩度拒絕隋的招撫,最後隋煬帝派大軍遠征,予以痛擊,帶回男女數千人。
孫權遣將浮海求夷洲、亶洲在黃龍二年(二三○),隋煬帝遣將浮海痛擊流求國,事在大業四年(六○八),前後相隔三百七十八年。三國時代的「夷洲」是不是隋代的「流求國」,本身就是個問題。在這裡我們不能不討論沈瑩《臨海水土志》中的「夷洲」。《臨海水土志》已佚,我們知道該書關於夷洲的記載,是因為《後漢書.東夷列傳》唐章懷太子注中引用該書:
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髠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鬭,摩礪青石以作(弓)矢〔鏃〕。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所日,乃啖食之,以為上肴」也。
沈瑩是三國時代吳國人,孫亮於太平二年(二五七)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今天的會稽市約當北緯三十度,從地圖上來看,琉球群島在其東南方,臺灣在其南方。雖然沈瑩是三國時代的人,這段關於「夷洲」的記載,並未被採入《三國志》。《三國志》作者陳壽(二三三—二九七)以近乎當代人的身分撰寫三國歷史,可以說「去古未遠」。陳壽在《三國志》中提到夷洲時,未採用沈瑩《臨海水土志》,原因不明,可能有以下兩種情況:一、陳壽編撰《三國志》時,未得見《臨海水土志》;二、陳壽得見此書,但不認為沈瑩的「夷洲」就是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遠征的「夷洲」,因而未予採用。總之,我們是否可以拿沈瑩筆下的「夷洲」來「實化」孫權派兵攻打的「夷洲」,還是個問題。
沈瑩的《臨海水土志》也收入北宋李昉等編纂的《太平御覽》,見於卷七八○「叙東夷」條,內容遠較《後漢書》章懷太子注詳盡。由於《太平御覽》全文較長,茲迻錄註中,以供參考(惟請注意此一版本中「夷洲」作「夷州」)。如果我們比對沈瑩《臨海水土志》的夷洲以及《隋書》〈流求國〉,可以獲致這樣一個結論:夷洲和流求國鮮少共通之處,雖然兩處居民都分別具有東南亞古文化的某些特徵。換句話說,我們很難說沈瑩的夷洲和《隋書》流求國必然是關於同一地理空間的紀錄,兩者在文化上未必具有相承的關係;至於《三國志》的夷洲,則因為記載過於簡略,無法和《隋書》作有意義的比對。
《隋書》關於流求國的記載,相對於當時關於其他「東夷」的記載,不能不說頗為詳盡,連該地動植物都有所描述。然而,如上所述,問題出在〈流求國〉似乎是個孤立的民族誌文獻,缺乏可資比對、輔證的其他材料,孤伶伶地懸在史書裡,無法進一步攷查,不像高麗、新羅、百濟,以及倭國(日本)有其他的史料可資參照。這份孤懸的文獻本身是個謎,流求國到底是臺灣、沖繩,實難獲得確論。以下幾個面向,是我們可以加以思考的。
第一章 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
引子
稱海上的島為山,是沿襲甚久的習慣。讀過中國詩詞的人,大都記得白居易〈長恨歌〉的詩句:「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這裡的仙山指海上神仙居住的島嶼。然而,不是神仙居住的島嶼才叫做山,舉凡海上諸島都可以稱山。我們或可推測,當人們搭船浮沉於茫茫大海中,遠遠望見島嶼時,不管大小,它的樣子總像是一座浮在水面上的山。
我們不知道稱海島為山,起源於何時,可以確定的是,明代海上行船人約定俗成稱島為山。例如,明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奉命出使琉球(沖繩,今屬日本),經過兩年的準備,他和隨員在嘉靖十三年五月五日(陰曆)從福建福州長樂縣廣石出海。由於逆風,船隻航行速度很慢,三天後(五月八日)出海口,「方一望汪洋矣」;他從船艙出來觀望,「四顧廓然,茫無山際,惟天光與水光相接耳。雲物變幻無窮,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雖若可樂,終不能釋然於懷。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第二天(五月十日),「南風甚速,舟行如飛」,他們「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得知明嘉靖年間,海上通稱島嶼為山,有時也稱為嶼。當船駛近島嶼,人們說「山將近矣」、「山近矣」。
陳侃出海後不久,看到的「小山」小琉球,如果按照第二天他們即經過平嘉山(彭佳嶼)、釣魚嶼等島嶼來看,他所望見的「小山」是臺灣島的一部分,從方位來看是北臺灣。這個時候的臺灣,還是「鮮為人知」,人們似乎還不清楚它是一個大島嶼,還是分成幾個小山。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了解臺灣的「身影」如何慢慢浮現在明人的視野中,由遠而近,由不熟悉而逐漸熟悉,由幾個島逐漸「合成」一個大島。然而,明朝之前,文獻上一直有讓後人爭論不休的疑似臺灣的記載。三國時代的夷洲、隋代的流求、宋朝的流求、元代的瑠求、琉球,都是難解之謎。讓我們先回顧這些說法吧。
一、夷洲與流求之謎
要談中國對臺灣的認識,一般總是從《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孫權傳)和《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談起,這是中文文獻中疑似臺灣的記載。已故的人類學家凌純聲先生甚至主張應該從《史記》〈東越列傳〉談起,認為臺灣可能是東越人所移殖的地方。這可能又太遙遠了。
關於《三國志》中的夷洲和《隋書》中的流求是否為臺灣,學者之間看法不同,說法時斷時續,算是個百年以上的爭論。我們先不去談爭論的內容,讓我們看看文獻本身的記載。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云:
〔黃龍〕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孫權「求」夷洲、亶洲的動機不清楚,或許仿秦始皇故事也未可知。其結果是,大軍無法抵達亶洲,卻到達夷洲,虜了數千人回來。亶洲傳言是秦始皇派徐福浮海求神山、仙藥最後所抵達的地方,這地方的人民常到會稽買布;會稽人出海也有遭風漂流到此地,這在在令人想起日本。我們知道後來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國是從長江口附近登陸,以此,日本人到會稽買布,也算合理。根據這份文獻,夷洲、亶洲一開始並舉,可見在人們的認知上,相距不遠。但是,實際浮海訪尋,亶洲又顯得遙不可及,大軍以抵達夷洲作結。
從以上如此簡短的文獻,要判斷夷洲是否為臺灣,其實並不具有太大的意義。倒是《三國志》其他兩個地方也提及「夷州」(此處「州」字無三點水,然根據文脈應即為上引之「夷洲」),這兩條都在列傳,與孫權想「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珠崖)」而遭到大臣勸阻有關,勸阻遣分軍遠征夷州分別為陸遜和全琮。據此,夷州和珠崖應有地理上的親近性(〈全琮傳〉云:「權將圍珠崖及夷州。」)。三國時的珠崖郡即海南島,孫權的夷州之役「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得不補失」,「權深悔之」。除了地理可能鄰近海南島之外,文獻遠不足以讓我們具體指夷州即臺灣。
如果《三國志》關於夷洲的記載過於簡略,《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所記該國情況則相當詳盡。〈流求國〉起頭云:「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以下是很長的一大段文字,描寫流求國的風土人情,包羅甚廣,不遜同書對日本的描寫,若全文迻錄,恐過於冗贅,在此僅引最後一段。文末云:
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崐崘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這是個「屢勸不聽」的故事。流求至少兩度拒絕隋的招撫,最後隋煬帝派大軍遠征,予以痛擊,帶回男女數千人。
孫權遣將浮海求夷洲、亶洲在黃龍二年(二三○),隋煬帝遣將浮海痛擊流求國,事在大業四年(六○八),前後相隔三百七十八年。三國時代的「夷洲」是不是隋代的「流求國」,本身就是個問題。在這裡我們不能不討論沈瑩《臨海水土志》中的「夷洲」。《臨海水土志》已佚,我們知道該書關於夷洲的記載,是因為《後漢書.東夷列傳》唐章懷太子注中引用該書:
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髠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鬭,摩礪青石以作(弓)矢〔鏃〕。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所日,乃啖食之,以為上肴」也。
沈瑩是三國時代吳國人,孫亮於太平二年(二五七)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今天的會稽市約當北緯三十度,從地圖上來看,琉球群島在其東南方,臺灣在其南方。雖然沈瑩是三國時代的人,這段關於「夷洲」的記載,並未被採入《三國志》。《三國志》作者陳壽(二三三—二九七)以近乎當代人的身分撰寫三國歷史,可以說「去古未遠」。陳壽在《三國志》中提到夷洲時,未採用沈瑩《臨海水土志》,原因不明,可能有以下兩種情況:一、陳壽編撰《三國志》時,未得見《臨海水土志》;二、陳壽得見此書,但不認為沈瑩的「夷洲」就是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遠征的「夷洲」,因而未予採用。總之,我們是否可以拿沈瑩筆下的「夷洲」來「實化」孫權派兵攻打的「夷洲」,還是個問題。
沈瑩的《臨海水土志》也收入北宋李昉等編纂的《太平御覽》,見於卷七八○「叙東夷」條,內容遠較《後漢書》章懷太子注詳盡。由於《太平御覽》全文較長,茲迻錄註中,以供參考(惟請注意此一版本中「夷洲」作「夷州」)。如果我們比對沈瑩《臨海水土志》的夷洲以及《隋書》〈流求國〉,可以獲致這樣一個結論:夷洲和流求國鮮少共通之處,雖然兩處居民都分別具有東南亞古文化的某些特徵。換句話說,我們很難說沈瑩的夷洲和《隋書》流求國必然是關於同一地理空間的紀錄,兩者在文化上未必具有相承的關係;至於《三國志》的夷洲,則因為記載過於簡略,無法和《隋書》作有意義的比對。
《隋書》關於流求國的記載,相對於當時關於其他「東夷」的記載,不能不說頗為詳盡,連該地動植物都有所描述。然而,如上所述,問題出在〈流求國〉似乎是個孤立的民族誌文獻,缺乏可資比對、輔證的其他材料,孤伶伶地懸在史書裡,無法進一步攷查,不像高麗、新羅、百濟,以及倭國(日本)有其他的史料可資參照。這份孤懸的文獻本身是個謎,流求國到底是臺灣、沖繩,實難獲得確論。以下幾個面向,是我們可以加以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