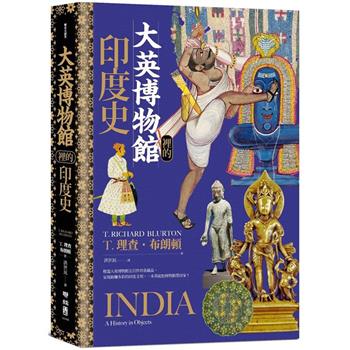佛陀的生平及《本生經》故事
今天,我們不可能確切無疑地描述佛陀在歷史上真正的生平。早期的資訊係口耳相傳,很快就被加油添醋。事實和傳說最終在文本裡結合,《大事》(Mahavastu)和《普曜經》(Lalitavistara)是早期的例子。兩者都是早期素材的彙編,後者也許在西元 3 世紀就寫成我們今天熟悉的版本。我們從這些文本得知,佛陀本名悉達多,生於今印度/尼泊爾邊界迦毘羅衛城的王室。佛陀出生有夢的預示:摩耶夫人夢到一頭白象從她的右脇而入。
他在藍毗尼園(Lumbini Garden)誕生,過程離奇:他從右脇而出(右邊在南亞傳統代表雄性和吉兆)。這個孩子年輕時過得奢侈,但有一天,他看到一個病人、一具屍體和一位流浪苦行者,感到良心不安,遂毅然決然離開王室生活,拋妻棄子,尋找理解人類存在的更佳方式。他在夜深人靜時離開宮殿,進入森林,就地剃髮,象徵徹底告別世俗生活,展開苦行。
在森林裡,他遵循多位導師的教誨,並嚴格實行捨棄我執。最後,明白苦行已無益於他的探索,他坐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樹下冥思。這裡,他遭到魔王波旬攻擊,誘惑與武力並施。他擊退這些雜念,請來大地女神見證,透過長年累積善德,他不再受到任何業力影響,如獲新生。他已悟道,而這將通往徹底解脫,即「涅槃」(他始終沒有賦予定義,而這個詞可比擬為火焰熄滅)。
離開菩提伽耶,他轉往鹿野苑(Sarnath),在此首次布道,「初轉法輪」(圖五)。他闡述他所獲得可脫離無盡輪迴轉生的知識,這便是四聖諦與八正道。四聖諦是苦(生即是苦)、集(苦為集合欲望所致)、滅(消滅欲望才可去除痛苦)、道(修正道為消滅欲望之法)。隨後他便列出八條正道。
剩餘的人生歲月,佛陀都在印度東部傳道。菩提伽耶和鹿野苑成為朝聖中心,且延續至今。死後,他的骨灰分成八個部分,分別存放在墳塚裡,成為第一批窣堵坡—─佛教建築的典型。
佛陀死後,《本生經》(前世故事)的構想開始發展,訴說佛陀成佛前的生平。故事中認知的概念是,佛陀依據一個人的「業報」來教導輪迴轉生—─即一個人行為的果,可能會在生命階梯上上下下。我們全都在這段旅程的某處,最終,當所有前世的負面因果用罄,便不再有重生的必要。因為佛陀已走完旅程,走入涅槃,我們必須假設他已經歷過多世生命,每一世都積累必要的善業,使他終能生而為人(之前有幾世為動物),終獲解脫。《本生經》的故事取用了古老的民間文學寶庫,並呈現在現存最早的佛陀雕塑中。這些故事由看似頗不近人情的道德觀所主導,由冷漠的因果律決定一切,但也從一開始就洋溢著同情憐憫。
舞王濕婆
濕婆神在火圈裡跳著極樂之舞的形象,或許是「印度教的印度」的概念中最為人熟知的濃縮。世界各地都見得到「舞王濕婆」(Shiva Nataraja)的雕塑。這位神的這尊聖像之所以受到矚目,部分應歸功於作家、思想家及藝術家阿南達.庫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1887-1947)。他的父親是斯里蘭卡泰米爾人,母親是英國人,而他的著作,以及諸如法國雕塑家奧古斯特.羅丹(Auguste Rodin)的作品,都大力促成這種形式持續受歡迎,不過現在我們知道,庫馬拉斯瓦米的解釋只是眾多可能詮釋的一種。
這個形象背後的神話與宇宙活動有關。印度傳統認為時間是循環而非線性的,舞王濕婆的形象為站在時間的盡頭與初始;他「舞出」一個循環,「舞進」另一個循環。濕婆一貫的作風就是出現在時間的極端,而非之中。他手中的標誌象徵了這個故事的毀滅與創造元素:上左臂在一個循環的盡頭持火,代表毀滅,上右臂則拿著沙漏狀的鼓,代表創造(鼓聲會使創造開始)。
這種描繪濕婆的方式在朱羅時代(9 到 13世紀)備受歡迎,尤與該王朝高韋里三角洲腹地上契當巴南(Chidambaram)的神廟關係密切。契當巴南神廟大大受惠於朱羅王朝的贊助。在這類神廟中,「奉愛」聖者如 7 世紀詩人阿帕爾的詩句,為信徒懷念吟詠。
舞王濕婆形象的淵源尚不明確。在象島—─孟買港的窟龕島—─上,有一塊這個主題的浮雕,可回溯至8世紀。不過,大致可確定的是,舞王濕婆擺出「極樂之舞」(anandatandava)姿態(有四條手臂、一腳高抬、在光環裡跳舞)的概念,是泰米爾人的想法。何時開始以青銅製作不得而知,但有件作品很可能是最早期的一例。冶金學分析顯示這件物品與我們劃歸帕拉瓦王朝(先於朱羅的統治者)的少數青銅雕塑有諸多雷同之處。另外,從圖像學的觀點,這件雕塑亦具有年代較早的條件,如火輪為橢圓形而非圓形;左側的肩帶垂下,未揚起連接火圈;頭髮也抑制在頭的周圍,沒有揚起來連接火圈。最後,被神踩在腳下、代表無知的侏儒,身體與神像垂直,後來的雕塑則大多平行。
大型的舞王濕婆青銅像,是為遊行使用而鑄造;後來被舉著穿梭大街小巷的舞王繪畫,則是印度畫家為英國觀光客製作。在還沒有攝影的年代,這些為不熟悉這項傳統的人士提供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