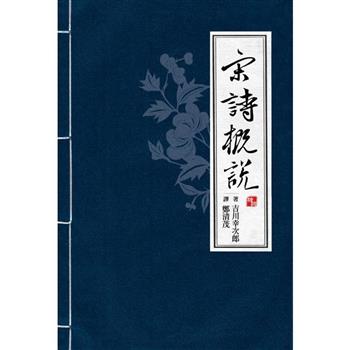序章 宋詩的性質
第一節 宋的時代
中國史過了一半之後,連續地出現了唐、宋、元、明、清五大朝代。宋朝居第二。天子姓趙。
宋史分為北宋與南宋兩個時期。
北宋以汴京(今河南省開封市)為首都,從十世紀中葉起,大致上統一了中國全土,歷一百六十年,直到十二世紀初葉為止;約略相當於日本平安朝中期至末期的院政時代。當時以滿洲為根據地的契丹族,早已建立了一個國家,國號曰遼,始終與北宋為敵;而更使北宋感到屈辱的是,遼的領土竟然囊括了所謂「燕雲十六州」,即今包含北京在內的河北省北部,以及山西省北部。到了北宋中葉,唐古特族的國家西夏,崛起西方,也構成了很大的威脅。然而,儘管如此,由於鞏固的中央集權制度,國內卻大體上平安無事,保持了一片昇平景象。根據《宋史‧地理志》,在最後一代皇帝徽宗的崇寧年間,即一一○○年前後,全國戶數達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戶;人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人。首都開封一地的人口,就有四十四萬二千九百四十人。而且這些人口數目,按照宮崎市定氏的說法,只算男人,女人並不包括在內。至於首都開封的繁榮情形,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裡有詳細的描寫。
蘇軾在下面的一首七言絕句裡,也反映了當時首都及其近郊農村富裕的情形。在一九○三年的上元節,即倒數第二代皇帝哲宗的元祐八年,舊曆正月十五夜,年輕的皇帝陪著祖母太后,從宮門上觀賞著首都熱鬧的夜景。自號東坡居士的詩人蘇軾,官拜禮部尚書(約等於現在的教育部長),也是陪宴的大臣之一。上元節就是元宵,街頭巷尾,張燈結綵,又有遊行花車穿梭其間,是一年一度最熱鬧的晚上。這首題為〈上元樓上侍飲呈同列〉的詩,寫的就是詩人當時的觀感。
薄雪初消野未耕,賣薪買酒看升平。
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有笑聲。
第一句「薄雪」云云,點出這時正是農閑季節。近郊的農民用賣薪所得的錢買了酒,成群結隊,絡繹不絕地進城來趕今夜的熱鬧,看太平的景象。「倡優」指在花車或戲棚上獻藝的演員。也許是我們的君主崇尚勤儉,務去浮華的關係,上以風化下,那些倡優所表演的雜技曲藝都實在不敢令人恭維。倒是一般人民為豐收而高興的笑聲,卻到處可聞,顯得繁華熱鬧之至。
蘇軾另外一首有名的七言絕句,題為〈春夜〉,大概也是作於那時的汴京。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
歌管樓臺聲細細,鞦韆院落夜沉沉。
「月有陰」,月色朦朧之意。不知從那一家高樓上,伴著輕細的管笛,傳來了曼靡的歌聲。外面是無風的月夜。深深的院子裡空空的,白天在那裡盪鞦韆的少女們,她們的驚叫,她們的芳蹤,如今安在?在沉沉的春夜裡,在朦朦的月光下,只見鞦韆靜靜地垂著彩色的繩子。
由於天下太平,人民豐衣足食,教育自然就普遍起來。甚至農村也不例外。蘇軾弟子輩的晁沖之,有一首絕句〈夜行〉說:
老去功名意轉疎,獨騎瘦馬適長途。
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
這時代的人不必轉戰疆場,只要參加科舉,如能及第,也一樣可獲得「功名」。詩人自己屢次應考而名落孫山,懷著不遇的牢騷,騎著瘦馬趕著夜路。忽然看到在一個偏僻的小村裡,快到天亮了,居然還有些人家點著燈光。對了,這裡一定有些年輕人,跟我以前一樣,正在為了準備科舉開著夜車吧。
當時教育的普及並不限於中原。蘇軾晚年被流放到海南島所作的詩裡,就曾經提到在那遙遠的海島上,竟然也有教育農家子弟的村塾。
不過,從滿洲背後崛起的女真族,先建立了金朝,滅了北宋宿敵遼國之後,就把侵略的箭頭轉向北宋。一一二六年,首都汴京陷落,徽宗與欽宗父子當了俘虜,被押到滿洲去。北宋一百六十年的和平就被破壞了。
徽宗的第九子高宗,繼承帝位後,逃到南方,建都於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統治了長江流域的地區。這是南宋的開始。爾後一百五十年間,領土掩有中國南半部,俗謂「半壁天下」。雖然南宋先是與金為敵,後來又與成吉思汗的蒙古對峙,但與北宋一樣,卻能長期地保持了國內的和平。那個時期的日本,先後有保元、平治、源平等戰亂,內戰頻仍,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根據南宋中葉寧宗嘉定十一年(一二一八)的統計,國內共有一千三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戶。一二七六年,忽必烈汗的元朝蒙古軍攻陷了杭州,併吞了南宋疆土,時為日本鎌倉時代的中期。吳自牧的《夢梁錄》,寫於亡國前二年,留下了以西湖為出名的首都杭州的繁榮記錄。另外威尼斯人馬哥波羅,曾訪問了淪陷後不久的杭州,對這個當時世界最大的都市,發出了由衷的驚歎。
南宋長久的和平,不但在杭州,也滲透到鄉村的角落。這在南宋詩人的代表陸游的一萬首詩裡,到處可以看得出來。如他的七言律詩〈村居書觸目〉:
雨霽郊原刈麥忙,風清門巷曬絲香。
人饒笑語豐年樂,吏省徵科化日長。
枝上花空閑蝶翅,林間葚美滑鶯吭。
飽知遊宦無多味,莫恨為農老故鄉。
「郊原」即田園。「門巷」,門前小巷。「徵科」,徵收租稅。「化日」,化國之日,即在開明政治下充滿文化的好日子。「遊宦」是在外做官的生涯。陸游當時六十歲,對於官場已知道得太多,也有點厭倦了,回到浙江東部的故鄉,看到農村豐實而和樂的情景,不免心嚮往之。
要之,南北宋共三百十年間,邊境儘管多事,國內卻相當太平。固然由於軍人受到抑制,對外武威一直不振,但也因而避免了內戰內亂。「科舉」即公務員考選制度,在地方與首都分級舉行,相當完備。文官的登用限於有文學哲學修養的讀書人。
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
這是歐陽修於北宋仁宗嘉祐二年(一○五七),在首都汴京知貢舉,即當典試委員長時,描寫考場的詩句(〈禮部貢院進士就試〉)。那些參加考試的書生,像戰士銜枚似的一聲不響,勇往直前地進行著和平的爭鬥;聽得到的只是在紙上奔馳的筆聲,沙沙沙的,彷彿春蠶正在吃著桑葉一般。那一年的及第者之一就是蘇軾。
由於實施科舉制度的結果,具有豐富學術的讀書人往往得以一舉成名,進而平步青雲,成為位居行政中樞的權臣。例如王安石,身兼詩人、學者與宰相,就是首屈一指的典型人物。其他將在本書裡介紹的詩人,如北宋的歐陽修、南宋的陳與義、范成大、文天祥,也都做過宰相。最偉大的詩人蘇軾,雖然沒有宰相的經歷,但也做到國務大臣的一員。反過來說,當時做過宰相或大臣的人物當中,不作詩不談哲學的,可說少而又少。在中國歷史上,宋朝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時代。
不過,這些書生官吏每每結成政治派系,黨同伐異,爭權奪勢,無時或已。歐陽修的流放夷陵,蘇軾的謫居海南,都是黨爭的結果。儘管如此,殺戮行為,除了少數例外,在原則上是一種禁忌。宋朝在中國史上,可以說是流血最少的時代。
就在這樣和平的基礎上,宋朝的文學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其中,詩是重要的一部分。
第二節 詩在宋文學的地位
從宋的前朝大唐帝國開始,詩在中國文學裡就確立了主要的地位。唐詩在形式上可以分成兩類。一是句數以及句中韻律皆不受拘束的形式,通稱「古體詩」。一是句數以及句中韻律均有定型的形式,稱為「今體詩」,又名「近體詩」。再者,今體詩在原則上,又有八行而以對句為主的律詩,以及只有四行的絕句。這兩種或者可以說三種詩體,基本上都屬於抒情詩的形式,雖然成立於唐代,但在南北宋期間卻更廣泛地被繼承了下來。
所以說廣泛,第一是指詩人數目的眾多。清厲鶚的《宋詩紀事》一書,蒐羅宋代詩人傳記或軼事,可說最為賅備,所提南北宋詩人共達三千八百十二家。較之清康熙皇帝勅撰的《全唐詩》作者二千三百餘人,多了一千五百人。
其次是詩人所傳詩篇的數量,往往大的驚人。越是大詩人越是如此。南宋的代表詩人陸游,現今所傳的就有九千二百首,其中絕大多數還只是他四十歲以後的作品。梅堯臣有二千八百首,王安石一千四百首,蘇軾二千四百首,范成大一千九百首,楊萬里三千多首。唐朝詩人中,最多產的要算白居易了,也不過二千八百首。杜甫有二千二百首,李白一千多首。至於王維、韓愈等其他詩人,都在千首以下,就更等而下之了。現在已有《全唐詩》,但還沒有《全宋詩》。如果《全宋詩》一旦出現,恐怕可以收錄數十萬首,《全唐詩》雖有四萬多首,但相形之下就不免要見絀了。
不過,宋人文學不像唐人那樣地集中於詩。俗謂「唐詩宋文」,可見宋文學的主流是散文。這種說法固然未免有些偏頗,但宋人與唐人不同,除了詩之外,也傾注精力於散文的創作,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唐的散文孤立於詩的洪流之中,是一種採取自由文體的隨筆與傳記文學,始於中唐韓愈等人所發起的「古文」運動。然而這種所謂「古文」的文學,到了唐末由於繼起無人,中斷很久,直到宋朝,才又有作者出現,繼往開來,加以發揚光大。宋詩大家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同時也都是「古文」的大家。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對詩有所忽略。事實上,他們依然認為有韻律的詩,才是最高的藝術表現。
在韻文的世界裡,宋人除了普通的詩之外,又有所謂「詞」的形式。這是一種根據既存的歌譜填寫而成的歌詞,句子長短不齊,與嚴格規定全部或五言或七言句子的詩體,可以說大相徑庭。詞萌芽於唐宋,盛行於宋代,作者極多。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陸游等,當時大部分的詩人,多多少少都作過「詞」,往往附錄在各家的全集裡面。譬如歐陽修的一首〈踏莎行〉:
候館梅殘
溪橋柳細
草薰風暖搖征轡
離愁漸遠漸無窮
迢迢不斷如春水
〈踏莎行〉就是既存的歌譜,通稱「詞牌」。下面再舉一首用同一詞牌填寫的「詞」:
寸寸柔腸
盈盈粉淚
樓高莫近危欄倚
平蕪盡處是春山
行人更在春山外
諸如此類,「詞」原是用來表現柔軟感情的詩歌類型,但在宋代的發展過程中,形式和內容都越變越複雜。而且也產生了像北宋柳永、周美成,以及南宋辛棄疾、吳文英那樣專門寫「詞」的詞人。
因為「詞」的流行是個新起的現象,所以頗受近時文學史家的重視。但過度的重視卻非避免不可。何則「詞」又名「詩餘」,畢竟是詩支流。儘管不能說沒有例外,如蘇軾或辛棄疾的作品,但在原則上,「詞」是一種精巧的抒情小調。宋朝韻文文學的主流,從頭至尾還是在詩。最重要的感情依然託之於詩,不託之於「詞」。這是宋代本身的意識,也是現在的客觀判斷。其實,就創作的數量而言,「詞」遠不及詩的多。為什麼《全宋詞》已被編印而《全宋詩》尚未出現,恐怕量的多少是個重要的原因。
第一節 宋的時代
中國史過了一半之後,連續地出現了唐、宋、元、明、清五大朝代。宋朝居第二。天子姓趙。
宋史分為北宋與南宋兩個時期。
北宋以汴京(今河南省開封市)為首都,從十世紀中葉起,大致上統一了中國全土,歷一百六十年,直到十二世紀初葉為止;約略相當於日本平安朝中期至末期的院政時代。當時以滿洲為根據地的契丹族,早已建立了一個國家,國號曰遼,始終與北宋為敵;而更使北宋感到屈辱的是,遼的領土竟然囊括了所謂「燕雲十六州」,即今包含北京在內的河北省北部,以及山西省北部。到了北宋中葉,唐古特族的國家西夏,崛起西方,也構成了很大的威脅。然而,儘管如此,由於鞏固的中央集權制度,國內卻大體上平安無事,保持了一片昇平景象。根據《宋史‧地理志》,在最後一代皇帝徽宗的崇寧年間,即一一○○年前後,全國戶數達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戶;人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人。首都開封一地的人口,就有四十四萬二千九百四十人。而且這些人口數目,按照宮崎市定氏的說法,只算男人,女人並不包括在內。至於首都開封的繁榮情形,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裡有詳細的描寫。
蘇軾在下面的一首七言絕句裡,也反映了當時首都及其近郊農村富裕的情形。在一九○三年的上元節,即倒數第二代皇帝哲宗的元祐八年,舊曆正月十五夜,年輕的皇帝陪著祖母太后,從宮門上觀賞著首都熱鬧的夜景。自號東坡居士的詩人蘇軾,官拜禮部尚書(約等於現在的教育部長),也是陪宴的大臣之一。上元節就是元宵,街頭巷尾,張燈結綵,又有遊行花車穿梭其間,是一年一度最熱鬧的晚上。這首題為〈上元樓上侍飲呈同列〉的詩,寫的就是詩人當時的觀感。
薄雪初消野未耕,賣薪買酒看升平。
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有笑聲。
第一句「薄雪」云云,點出這時正是農閑季節。近郊的農民用賣薪所得的錢買了酒,成群結隊,絡繹不絕地進城來趕今夜的熱鬧,看太平的景象。「倡優」指在花車或戲棚上獻藝的演員。也許是我們的君主崇尚勤儉,務去浮華的關係,上以風化下,那些倡優所表演的雜技曲藝都實在不敢令人恭維。倒是一般人民為豐收而高興的笑聲,卻到處可聞,顯得繁華熱鬧之至。
蘇軾另外一首有名的七言絕句,題為〈春夜〉,大概也是作於那時的汴京。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
歌管樓臺聲細細,鞦韆院落夜沉沉。
「月有陰」,月色朦朧之意。不知從那一家高樓上,伴著輕細的管笛,傳來了曼靡的歌聲。外面是無風的月夜。深深的院子裡空空的,白天在那裡盪鞦韆的少女們,她們的驚叫,她們的芳蹤,如今安在?在沉沉的春夜裡,在朦朦的月光下,只見鞦韆靜靜地垂著彩色的繩子。
由於天下太平,人民豐衣足食,教育自然就普遍起來。甚至農村也不例外。蘇軾弟子輩的晁沖之,有一首絕句〈夜行〉說:
老去功名意轉疎,獨騎瘦馬適長途。
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
這時代的人不必轉戰疆場,只要參加科舉,如能及第,也一樣可獲得「功名」。詩人自己屢次應考而名落孫山,懷著不遇的牢騷,騎著瘦馬趕著夜路。忽然看到在一個偏僻的小村裡,快到天亮了,居然還有些人家點著燈光。對了,這裡一定有些年輕人,跟我以前一樣,正在為了準備科舉開著夜車吧。
當時教育的普及並不限於中原。蘇軾晚年被流放到海南島所作的詩裡,就曾經提到在那遙遠的海島上,竟然也有教育農家子弟的村塾。
不過,從滿洲背後崛起的女真族,先建立了金朝,滅了北宋宿敵遼國之後,就把侵略的箭頭轉向北宋。一一二六年,首都汴京陷落,徽宗與欽宗父子當了俘虜,被押到滿洲去。北宋一百六十年的和平就被破壞了。
徽宗的第九子高宗,繼承帝位後,逃到南方,建都於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統治了長江流域的地區。這是南宋的開始。爾後一百五十年間,領土掩有中國南半部,俗謂「半壁天下」。雖然南宋先是與金為敵,後來又與成吉思汗的蒙古對峙,但與北宋一樣,卻能長期地保持了國內的和平。那個時期的日本,先後有保元、平治、源平等戰亂,內戰頻仍,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根據南宋中葉寧宗嘉定十一年(一二一八)的統計,國內共有一千三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戶。一二七六年,忽必烈汗的元朝蒙古軍攻陷了杭州,併吞了南宋疆土,時為日本鎌倉時代的中期。吳自牧的《夢梁錄》,寫於亡國前二年,留下了以西湖為出名的首都杭州的繁榮記錄。另外威尼斯人馬哥波羅,曾訪問了淪陷後不久的杭州,對這個當時世界最大的都市,發出了由衷的驚歎。
南宋長久的和平,不但在杭州,也滲透到鄉村的角落。這在南宋詩人的代表陸游的一萬首詩裡,到處可以看得出來。如他的七言律詩〈村居書觸目〉:
雨霽郊原刈麥忙,風清門巷曬絲香。
人饒笑語豐年樂,吏省徵科化日長。
枝上花空閑蝶翅,林間葚美滑鶯吭。
飽知遊宦無多味,莫恨為農老故鄉。
「郊原」即田園。「門巷」,門前小巷。「徵科」,徵收租稅。「化日」,化國之日,即在開明政治下充滿文化的好日子。「遊宦」是在外做官的生涯。陸游當時六十歲,對於官場已知道得太多,也有點厭倦了,回到浙江東部的故鄉,看到農村豐實而和樂的情景,不免心嚮往之。
要之,南北宋共三百十年間,邊境儘管多事,國內卻相當太平。固然由於軍人受到抑制,對外武威一直不振,但也因而避免了內戰內亂。「科舉」即公務員考選制度,在地方與首都分級舉行,相當完備。文官的登用限於有文學哲學修養的讀書人。
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
這是歐陽修於北宋仁宗嘉祐二年(一○五七),在首都汴京知貢舉,即當典試委員長時,描寫考場的詩句(〈禮部貢院進士就試〉)。那些參加考試的書生,像戰士銜枚似的一聲不響,勇往直前地進行著和平的爭鬥;聽得到的只是在紙上奔馳的筆聲,沙沙沙的,彷彿春蠶正在吃著桑葉一般。那一年的及第者之一就是蘇軾。
由於實施科舉制度的結果,具有豐富學術的讀書人往往得以一舉成名,進而平步青雲,成為位居行政中樞的權臣。例如王安石,身兼詩人、學者與宰相,就是首屈一指的典型人物。其他將在本書裡介紹的詩人,如北宋的歐陽修、南宋的陳與義、范成大、文天祥,也都做過宰相。最偉大的詩人蘇軾,雖然沒有宰相的經歷,但也做到國務大臣的一員。反過來說,當時做過宰相或大臣的人物當中,不作詩不談哲學的,可說少而又少。在中國歷史上,宋朝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時代。
不過,這些書生官吏每每結成政治派系,黨同伐異,爭權奪勢,無時或已。歐陽修的流放夷陵,蘇軾的謫居海南,都是黨爭的結果。儘管如此,殺戮行為,除了少數例外,在原則上是一種禁忌。宋朝在中國史上,可以說是流血最少的時代。
就在這樣和平的基礎上,宋朝的文學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其中,詩是重要的一部分。
第二節 詩在宋文學的地位
從宋的前朝大唐帝國開始,詩在中國文學裡就確立了主要的地位。唐詩在形式上可以分成兩類。一是句數以及句中韻律皆不受拘束的形式,通稱「古體詩」。一是句數以及句中韻律均有定型的形式,稱為「今體詩」,又名「近體詩」。再者,今體詩在原則上,又有八行而以對句為主的律詩,以及只有四行的絕句。這兩種或者可以說三種詩體,基本上都屬於抒情詩的形式,雖然成立於唐代,但在南北宋期間卻更廣泛地被繼承了下來。
所以說廣泛,第一是指詩人數目的眾多。清厲鶚的《宋詩紀事》一書,蒐羅宋代詩人傳記或軼事,可說最為賅備,所提南北宋詩人共達三千八百十二家。較之清康熙皇帝勅撰的《全唐詩》作者二千三百餘人,多了一千五百人。
其次是詩人所傳詩篇的數量,往往大的驚人。越是大詩人越是如此。南宋的代表詩人陸游,現今所傳的就有九千二百首,其中絕大多數還只是他四十歲以後的作品。梅堯臣有二千八百首,王安石一千四百首,蘇軾二千四百首,范成大一千九百首,楊萬里三千多首。唐朝詩人中,最多產的要算白居易了,也不過二千八百首。杜甫有二千二百首,李白一千多首。至於王維、韓愈等其他詩人,都在千首以下,就更等而下之了。現在已有《全唐詩》,但還沒有《全宋詩》。如果《全宋詩》一旦出現,恐怕可以收錄數十萬首,《全唐詩》雖有四萬多首,但相形之下就不免要見絀了。
不過,宋人文學不像唐人那樣地集中於詩。俗謂「唐詩宋文」,可見宋文學的主流是散文。這種說法固然未免有些偏頗,但宋人與唐人不同,除了詩之外,也傾注精力於散文的創作,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唐的散文孤立於詩的洪流之中,是一種採取自由文體的隨筆與傳記文學,始於中唐韓愈等人所發起的「古文」運動。然而這種所謂「古文」的文學,到了唐末由於繼起無人,中斷很久,直到宋朝,才又有作者出現,繼往開來,加以發揚光大。宋詩大家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同時也都是「古文」的大家。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對詩有所忽略。事實上,他們依然認為有韻律的詩,才是最高的藝術表現。
在韻文的世界裡,宋人除了普通的詩之外,又有所謂「詞」的形式。這是一種根據既存的歌譜填寫而成的歌詞,句子長短不齊,與嚴格規定全部或五言或七言句子的詩體,可以說大相徑庭。詞萌芽於唐宋,盛行於宋代,作者極多。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陸游等,當時大部分的詩人,多多少少都作過「詞」,往往附錄在各家的全集裡面。譬如歐陽修的一首〈踏莎行〉:
候館梅殘
溪橋柳細
草薰風暖搖征轡
離愁漸遠漸無窮
迢迢不斷如春水
〈踏莎行〉就是既存的歌譜,通稱「詞牌」。下面再舉一首用同一詞牌填寫的「詞」:
寸寸柔腸
盈盈粉淚
樓高莫近危欄倚
平蕪盡處是春山
行人更在春山外
諸如此類,「詞」原是用來表現柔軟感情的詩歌類型,但在宋代的發展過程中,形式和內容都越變越複雜。而且也產生了像北宋柳永、周美成,以及南宋辛棄疾、吳文英那樣專門寫「詞」的詞人。
因為「詞」的流行是個新起的現象,所以頗受近時文學史家的重視。但過度的重視卻非避免不可。何則「詞」又名「詩餘」,畢竟是詩支流。儘管不能說沒有例外,如蘇軾或辛棄疾的作品,但在原則上,「詞」是一種精巧的抒情小調。宋朝韻文文學的主流,從頭至尾還是在詩。最重要的感情依然託之於詩,不託之於「詞」。這是宋代本身的意識,也是現在的客觀判斷。其實,就創作的數量而言,「詞」遠不及詩的多。為什麼《全宋詞》已被編印而《全宋詩》尚未出現,恐怕量的多少是個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