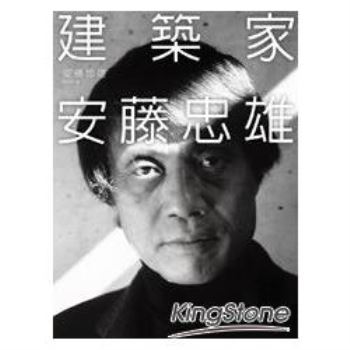雖然社會與建築的處境有很大的改變,
但我面對建築的基本態度,
依舊是﹁對抗都市的游擊隊﹂,
絲毫沒有改變。
紅磚牆的另一頭
如果說我的住宅處女作是﹁住吉長屋﹂,那麼我的第一號商業建築作品,就是在﹁住吉﹂完工後的隔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完工、坐落神戶北野町以古老洋房聞名的﹁玫瑰花園﹂︵Rose Garden︶。
這個案子的業主是二十多歲的當地人,我接受了他想蓋一棟﹁帶給街坊活力﹂的建案委託。實際上北野町當時也受到建設熱潮的衝擊,古老的街道景觀逐漸被毫無品味的大樓與公寓所破壞。這個計畫就是當地居民為了阻止毫無章法開發而展開的。
針對﹁保存街廓﹂的主題,我提出不讓建築物的量體在現有的街景中顯得突兀的配置計畫;此外,也傳承紅磚牆與山型屋頂這類西式洋房的部分風貌。
在現今的社會中,﹁維護景觀﹂一詞已相當普遍,但三十年前,當時社會對城市景觀的意識薄弱。在這個意義下,我認為考量與周遭的協調,用紅磚而不用混凝土外牆,是個正確的選擇。
但我在﹁玫瑰花園﹂中真正想打造的,並不只是紅磚牆。我傾注心力的重點,在於牆壁另一頭的﹁空間﹂。
那是位於兩棟建築之間的留白空間。當時我想在樓梯挑空的外側設置迴廊,以階梯相連,並藉由店面的排列創造出一條﹁道路﹂。這條會受到風吹雨淋的﹁道路﹂,就像一般馬路一樣,偶有不規則的彎曲,藉此在建築物中創造出﹁沉澱﹂與﹁停留﹂的空間;而爬上樓梯,便能從牆縫中看到神戶的海景——我的構想就是在建築物內打造另一個市街。
﹁玫瑰花園﹂完工後,受到委託人等愛鄉愛土的居民熱情支持,以超乎預期的想像融入當地。我認為藉由那次機會,﹁造鎮﹂的觀念便擴展到整個北野町。粗糙的再開發計畫宣告停止,取而代之的是氣氛沉穩的複合式商業建築競相成形。
在﹁玫瑰花園﹂之後,我在當地又參與了﹁北野小徑﹂︵Kitano Alley︶、﹁Rin's Gallery﹂、﹁Riran's gate﹂等,十年間大約承接了八項建案。無論是哪一棟建築,都和﹁玫瑰花園﹂一樣,主題放在與周遭環境自然的連結,以及營造場地的熱鬧氣氛。
即便一個個建築規模都不大,但只要連續興建,力量就會合而為一。最後北野町寧靜的原貌沒有受到太大破壞,古老洋房建築與現代的感性得以共存,重生為嶄新的觀光勝地。
這是藉由居民的雙手,串連起小小的點而實現的造鎮。
從建築到都市
這幾年來,東京的都市空間產生了新的變化。在泡沫經濟崩潰後,雖因為不景氣而看似停滯不前,但自九○年代後半﹁政策鬆綁﹂與﹁結構改革﹂的影響,業界又開始興建摩天大樓。過了千禧年之後,則陸續出現了大型開發案。
正好從這個時期開始,出現了︽新生代建築家設計的都心小住宅特刊︾等刊物,一般雜誌也開始大肆報導﹁建築﹂的話題。由此可看出都市的變化,與從前想在郊外購屋的人,紛紛回到市中心的現象,有著相當深刻的關連。東京都的再開發區內,吹起一陣公寓大廈的風潮,而憂心辦公大樓供過於求的﹁二○○三年問題﹂2,也鬧得沸沸揚揚,為東京的都市空間注入眾多的能量。
在高度經濟成長下的都市建設,和今日由民間資本所主導的都市建設,最大的差異在於開發策略轉向﹁重質不重量﹂。每項建案都打出文化都市或環境都市的號召,積極表明他們不像以往的開發案只重視經濟效率。而﹁表參道之丘﹂以﹁媒體旗艦﹂為名,強調其作為流行資訊發源地的特質,亦同樣置身在這股洪流中。
關於那一連串的大規模開發計畫,有正反兩面的許多意見,然而我個人認為六本木之丘雖以商業為基礎,但在地價昂貴的地段導入美術館等文化設施,對日本都市而言是極大的轉變。接連完成的國立新美術館及東京中城,這些設施如果能串連起來,六本木就能成為與上野齊名的新文化圈。但令我擔憂的是,這些設施能維持多久。只要屬於商業設施的一部分,一旦追求利潤的出資者提出要求,獲益性較低的文化設施很有可能成為第一個裁撤的目標。
但是,都市的豐裕,是從當地豐富的人文歷史,以及刻劃了歲月痕跡的空間而來。人們生活和聚集的場所,是不能當成商品拿來消費的。在建築物承受時間考驗,不斷興建之下,同潤會青山公寓在寧靜的住宅區逐漸改頭換面,成為新舊交融並充滿魅力的場所,在都市中繼續生存下去。
這種因應社會變化的包容力,以及連結時光的堅韌特質,在遭受消費文化侵蝕的現代建築中,應該是現今不可或缺的要素吧!建於青山公寓舊址的﹁表參道之丘﹂,是我對這項課題所提出的一個解答。(待續)
第二篇
在「下町唐座」的東北展正要動工的一九八七年初,一位就職於報社的朋友來找我,商量他常去的教會的改建工程。
地點在大阪府北部茨木市,是離一九七○年萬博會場不遠的閑靜住宅區一角。總樓板面積五十坪左右,是一個與社區緊密連結的小教會建築,但難題在於預算。
當時正逢現在稱為泡沫經濟的美好景氣開端,在前所未有的建設浪潮中,建材價格直飆上揚。但是,雖說是信徒們全心傾注的奉獻,從朋友口中提出的數字令人實在難以啟口。
「就算我接了設計,會有營造公司願意承包這種幾乎無法期望利潤的小案子嗎?
「打從一開始,我就很清楚這是一項艱鉅的工作,但最後還是接下了這座教會的設計委託。
最後理由只有一個:就算沒有充裕的資金,但這裡有真心希望教會能夠蓋起來的業主——也就是信徒們。
對於建築家而言,像教堂這種超越單純的功能性,而在精神上的表現倍受期待的建築,是在自我思想層面上極為重大的挑戰。
設計這座教堂時,我在神戶已經設計過一座「六甲教會」,另外在北海道的TOMAMU也正在進行「水之教會」的設計工作。同樣位於大自然的風景勝地之中,都是比較能夠自由思考的建築工作,我自信已在其中探究了所謂的「神聖的空間」。但是,上述兩者都是飯店附屬的教堂, 主要功能是做為婚禮會場,都不算真正的宗教建築——亦即人們聚會、禱告的地方。
從得知這項工作開始,我就覺得在預算上,只能蓋單純的箱型建築。但要如何從這個箱子裡,創造出讓人感到﹁別無他處﹂的神聖建築空間呢?經過了大約一年的設計,最後出來的,是在寬高同為六公尺、進深十八公尺的混凝土箱子上,斜著插入一片牆壁的配置。內部地板從後方朝著正面的祭壇以階梯狀逐漸下降。出入口等主要的開口都集中於箱子和斜牆交錯之處,刻意壓低室內的亮度。在這稀薄暗影中,光線從正面牆上穿透的十字型窗外投射進來,浮現出光線構成的十字架。
在沒有空調、四面都是清水混凝土的室內,只放著祭壇和長椅。那也是認為廉價且有粗獷質感的材料比較理想,將工地現場鷹架所用的杉木板就地取材而來。
之所以會如此徹底地緊縮物料,首先當然是因為不得不以降低成本作考量,而另一個原因,則是我本來就對於極度簡樸的禁慾生活,有一種下意識的憧憬。
我心中抱持的意象,就是中世紀歐洲的羅馬式修道院。修道士們真的是消磨著自己的生命,將粗鑿的石頭堆疊成形,打造出有如洞窟一般的禮拜堂。在那種簡樸之至的空間裡,強烈的光從沒有玻璃遮擋的開口直接射入,寧靜地照映出地上石面的表情。
那種莊嚴而美麗,直搗人心的空間,能否用混凝土箱子將它表現出來?
「光之教會」就是在這樣的想法下誕生的。(待續)
用建造的榮譽感所完成的建築
願意接下如此艱困工程的是長年往來的一家小型營造商。老闆是位非常喜歡蓋東西、不太會賺錢、比我年長三歲的男子。
因為經費不足,更希望能夠克服困境,做出讓心靈非常豐裕的建築。除了他們公司之外,再沒有人願意傾聽這種強人所難的請求了。好不容易請他們接下工作開工之後,花了許多時間在決定基礎結構的形式,但也激發了源源不絕的創意。在簡約的結構中,能選擇的要素很有限。我們在預算和時間允許的範圍內,再次徹底的探討,找尋更好的選擇。我激勵工作人員:「雖然施工開始了,設計工作還不會就這樣結束。」但是在沒有設計經費,工程費也壓到幾乎貼近原價的情況之下強行開工,照例遇到蓋房子避免不了的﹁無法預期的問題﹂而產生額外的花費,成了如假包換的赤字建案。﹁目前的金額說不定只能做到混凝土牆壁。」
當資金不足讓案子面臨無法繼續之際,我提出了一個構想,即然預算不夠,乾脆就不架屋頂,以開天窗的狀態,結束這項工程。教會並非一般的設施,而是讓人們聚集與祈禱的場所。即使沒有屋頂,雨天撐傘來做禮拜,對於心靈的溝通交流應該不構成任何的妨礙。幾年之後,等錢存夠了,再來加蓋屋頂。在那之前,當做一間沒有屋頂、晴空下的禮拜堂不也很好嗎?不過,即使設計者有這些想法,結果還是蓋了屋頂,建築物也照著計圖上的模樣完工了。
能完成這棟不符合經濟行為的建築,是因為有了身為業主的信徒們誠摯的意念,以及為了回應這意念而奮起的營造商的熱情。
一路走來,對於以身為建築業者而自豪的營造商老闆而言,無論陷入任何境界,一旦接受了委託,就絕不會選擇半途而廢。即使看不到任何經濟上的回饋,面臨著艱苦的狀況,他們也從不罷手,綑綁鋼筋、架設模板,誠心誠意地投入,為了做出最棒的混凝土而揮汗拚命。從動工開始約一年後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光之教會﹂完成了。
光與影
人的﹁信念﹂有超越經濟的力量。光之教會對於事務所起步二十餘年,當時身處在周遭環境正大幅改變的我來說,關於﹁為何而做,為誰而做﹂這個大哉問,帶來深刻的省思。
光之教會落成九年後的一九九八年五月,在旁邊開始進行為主日學而加蓋的小廳堂工程。無論規模或是結構,都承襲了老禮拜堂的混凝土箱子,用一種與老禮拜堂﹁對峙﹂的形式配置。不是單純的加量增建,我以新舊之間形成的張力為主題,進行了設計。
預算照樣吃緊,但這次負責施工的,並非當初建設光之教會的營造商。實際上,在進行光之教會的過程中發現身染重病的老闆,在建築竣工的一年後去世了。隨著他的辭世,營造商也撤下招牌,幾名有志員工組織了新公司重新出發。面對有著深厚感情的教會面臨增建,彼此都很有意願,但成立不久的新公司無力擔負這種虧本生意,結果不得不放棄同一團隊的施工。
一開始盡是一些不如人意的事情,
想嘗試些什麼,
大多以失敗告終。
儘管如此還是賭上僅存的可能性,
在陰影中一心前進,抓住一個機會,
就繼而朝向下一個目標邁進︙︙。
我的人生就是這樣,抓住微小的希望之光,
拚命地活下去。
如同﹁下町唐座﹂與﹁光之教會﹂的建設過程,建築的故事必然伴隨光和影兩種側面。人生亦然。有光明的日子,背後就必然有苦澀的陰天。
聽過我靠自學成為建築家的經歷,有人以為那是條華麗的康莊大道,這完全是誤解。在封閉保守的日本社會中,一個人毫無後盾地以成為建築家為目標,不可能一帆風順。一開始盡是不如人意的事情,無論想嘗試些什麼,大多以失敗告終。
儘管如此,我還是賭上僅存的可能性,在陰影中一心前進,抓住一個機會,就繼續朝下一個目標邁進︙︙。我的人生就是這樣,握住微小的希望之光,拚命地活下去。總是處於逆境中,從思考如何克服的過程中找到活路。
因此,在我的人生經歷中沒有卓越的藝術資質,只有與生俱來即使面對嚴酷的現實,也絕不放棄,要堅強地活下去的韌性。
要在人生中追求﹁光﹂,首先要徹底凝視眼前叫作﹁影﹂的艱苦現實,而為了要超越它,鼓起勇氣向前邁進。
在資訊進步、受到高度管理的現代社會中,人們似乎都被﹁無時無刻都要待在光芒照得到的地方﹂這種強迫意識束縛住了。
因為大人們的一廂情願,孩子從小就被教導不要去看事物的陰暗面,只要看光明面;一旦接觸外界的現實,感覺自己進入了陰影之中,就放棄一切,撒手不管了。最近新聞報導這些心靈脆弱的孩子所發生的悲慘事件,越來越頻繁。
什麼是人生的幸福?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我認為,一個人真正的幸福並不是待在光明之中。從遠處凝望光明,朝它奮力奔去,就在那拚命忘我的時間裡,才有人生真正的充實。
光與影。那是我置身建築世界四十年來,從經驗中學習到的、屬於自己的人生觀。(待續)
游擊隊的地盤
我的活動據點
我的活動據點是大阪梅田附近,佔地三十坪的小事務所。這裡原本是我的第一個設計案——小透天住宅﹁富島邸﹂︵一九七三年︶。這棟建築後來在屋主因種種緣故而轉賣之際,由我接手,並在一九八○年改成自己的工作室。之後經多次改建,在一九九○年第四次改建時完全拆除重建,以地上五樓、地下二樓的規模安定下來。
裡面從一樓到五樓是挑高的開放空間。身為老闆的我,座位在挑空空間的最底層,面對著員工進出一樓玄關之處。也就是說以挑高設計現今將縱向重疊的平面空間連成一氣,使最底層具備指揮中心的機能,如此一來,以我為首的二十五名員工帶著隨時如臨戰場的緊張感,而凝聚出強烈的一體感。
從我的座位大喊一聲,聲音可以傳到每個角落。只要爬上樓梯,每個員工在辦公桌前工作的樣子也一覽無遺。而且我就像是坐在玄關大廳一樣,員工進出事務所,必定會經過我的面前。除了海外通訊,就算是對外聯絡都禁止使用E-mail、傳真、個人電話,就連剩下的唯一聯絡方法——五台公用電話,也擺在我視線可及的範圍內,員工在跟誰談什麼、是不是出了問題等,立刻能夠掌握。
對管理者來說,這樣全體開放式的空間能隨時掌握整體狀況固然便利,但另一方面,老闆的樣子也隨時受到員工監視,有時也會覺得是個滿累人的空間。
但就是因為處在這種沒有牆的狀態,我不但能與員工時常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他們也能隨時確認彼此的狀況而一起工作。
要維持這種事務所的體制與營運,在現有規模的建築物中,目前的人數應該已是最大極限了。
如同一開始所說的,這是一棟不定期改建並依照自己的想法所築成的建築物,我大致感到滿意。唯一的缺點是,我的座位不僅在玄關旁,也面對著出入口,總之是冬冷夏熱,又最吵雜的地方。
﹁好冷﹂、﹁好熱﹂、﹁吵死了﹂等等,如此一年四季從體內湧出﹁發脾氣﹂的能量,通常都是發洩在工作上;所以要忍受我脾氣的員工想必也非常辛苦吧!
刊登於某建築雜誌訪問我的報導,下了這樣的標題:
﹁安藤忠雄——用恐懼來教育﹂我個人覺得,
因為字面上給人強烈的印象,所以還滿中意的⋯⋯(待續)
游擊隊安藤忠雄建築研究所
大約在二十年前,我接受了某建築雜誌的採訪,主題是關於員工的教育方法。因為採訪我的是建築家前輩,談起來較輕鬆,所以我就照實回答。隔月,那篇訪問報導刊登了這樣的標題:﹁安藤忠雄——用恐懼來教育﹂雖然我自己,因為標題具有震撼力而相當中意,但之後想到事務所工作或登門造訪的學生卻大量減少了。
像雕刻家、畫家等藝術家,究竟和建築家有何差異呢?我認為最大的差異之一,在於建築家為了工作必須擁有從事建築活動的團隊。從單槍匹馬闖蕩的時代,到某個程度為止,沒有團隊確實也能接案子。但是,經過十年左右,案子的規模擴大,工作數量又增加,不論是個人能力、還是社會觀點,不具備某種程度的組織能力是無法維持下去的。要成為﹁擁有社會組織的個人﹂才會被認可,並受到信賴。
組織團隊後,當然在社會與經濟面上都會出現障礙。在這當中,如何維持團隊的良好狀態,與個人藝術才能是截然不同的問題。所謂的團隊, 不加以管理就會日益肥大,等注意到這個狀況時,組織本身發展過度,只好隨著這原是為了自己而組成的團隊起舞。個人若被團隊所吞沒,那建築家也就完了。雖然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不知為何,在建築業界卻很少被當成話題來談論。
我擁有個人事務所, 是在一九六九年、二十八歲的時候。我在大阪的阪急梅田車站附近,一整排木造老房子旁的大樓中租了一間小房間,這是至今仍是我生活與工作夥伴的加藤由美子,兩人最早的出發點。剛開始可以說幾乎沒有工作、沒人上門來委託工作,唯一的工作就是參加國內外的建築設計比賽,每天都在事務所的地板上打滾,邊望著天花板邊讀書,天馬行空地幻想著不存在的計畫。幾年過後,脫離了谷底的狀態,工作漸漸增加,工作人員依然維持兩、三個人,停留在極小的規模。
找到屬於自己的組織雛型時,是在事務所邁入第十年,工作人員大約十人的時候。那是以﹁游擊隊﹂之姿而存在的設計事務所。
我們並不是一個指揮官與服從命令的士兵組成的﹁軍隊﹂,而是抱有共同理想、具備信念和職責的個人,以我為賭注而生存的﹁游擊隊﹂。這是受到切.格瓦拉︵Che Guevara︶強烈的影響:為了實現小國的自主與人類自由、平等的理想,始終以單一的個人為據點,選擇與既存社會對抗的人生。
在人口過度密集的嚴苛環境中,個人仍頑強地棲息下去——我將﹁富島邸﹂等初期興建的小型透天住宅命名為﹁都市游擊隊住宅﹂。我認為那不單是指自己所設計的建築,也是因為身為創作者的我們希望以游擊隊的方式存在。
話雖如此,要讓這些在日本安穩的社會環境中長大的年輕工作人員突然搖身一變成為游擊隊,畢竟是不可能的事。為了實現理想,在現實社會的組織當中如何落實具體的制度呢?
老闆與員工,一對一的單純關係
首先想到的方式是,所有的工作都先決定好全權負責的人,在執行過程中,我與負責的人採取一對一小團隊來進行。有五件工作就有五個負責人、十件工作就有十個負責人。如此一來,老闆和所有的工地都直接聯繫,完全不需要透過中間管理階層。
對於我個人事務所最重要的是,我與員工之間沒有認知上的差異。因為我認為如何正確地傳達並共享資訊,正是溝通問題的關鍵所在;尤其希望所有事情都單純明快。我無法忍受曖昧不明的狀況,也許是與生俱來的特質吧!
當然,即使是一對一,最高負責人的我與負責的員工之間,對於工作還是有覺悟程度的差異。沒有緊張感是無法做好工作的,就算日後會獨立開設事務所的員工,其資歷也會因為是否以認真的態度,抱持著臨場感來度過在這裡的時間,而得到差距甚大的經驗。因此,我一直是以徹底而嚴厲的態度來面對員工。這才是﹁用恐懼來教育﹂的真正含意。
我一個人參與了為數眾多的工作。而且一想到就會與各個案子的負責人確認工作進度,若有必要則加以修正。此時, 要是不小心犯錯、或是看到放棄深入思考的怠慢態度,或是忽略與工地或業主建立良好關係等,我都會毫不留情加以斥責。事務所剛創設的前幾年,我與工作人員之間的年齡相差十歲左右,正是血氣方剛之時,常常動不動就拳腳相向。但是,沒有因為設計感太差而罵過他們。
重要的是,﹁有沒有為使用建築物的人們著想?有沒有實現當初的約定?﹂我會過問的是,各案負責人有沒有﹁要完成這工作﹂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