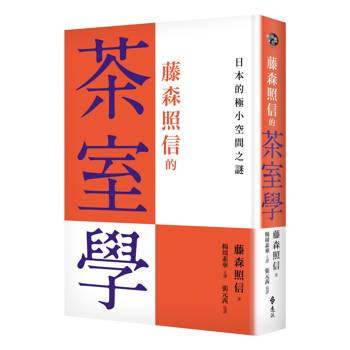改變茶室觀的兩個茶室
首次和茶室正面接觸,是在舊知秋野等先生邀請我在他任住持的京都德正寺的後院蓋一茶室時。工程途中,細川護熙先生(日本前首相)來電要我「三個月內蓋個茶室」。
兩年前就聽說他要蓋茶室。也耳聞他要以自己庭院盡頭處的樹蔭做基地,已請京都有名的數寄屋大工領班,一點一點地在搜集煤竹等的材料。
現在要做一個茶室,從設計和材料的準備到完工,需三年。
費用呢,一坪的下限是五百萬日幣,無上限。雖然很高,但絕非建築業者在揩油。我著手的茶室,是採取除業主外加上學生等很多的關係人一起參加工事的變通體制,所以正確的總工費並不淸楚,當我做〈茶室 徹〉(二○○五年)時,我想應該一次好好地計算從設計、材料到施工完成所該付的費用,付完後一坪就增為八百萬日幣。如果考量利益和風險,則一坪不到一千萬日幣應該不能接案。
三年縮短成三個月,而且三個月後要迎接貴賓,實際工期只有一個月。細川先生十七代前的祖先細川忠興,是日本戰國時代的利休七哲之一,以當時利休配合秀吉出征,數日之內完成一個茶室,迎接秀吉的故事來看,三個月也不算沒有道理。如果是利休的話,已經完成好幾個了。基地呢,也不是以前聽說的庭院的盡頭處,而是在陶藝工房的山側之斜面。從山上引來的溫泉作為中心點,由主屋和工作房三方圍成一個小廣場,如果在展開的山側置入茶室,那麼由建築圍起一個中央湧出熱泉的廣場就產生了。細川先生的願望是,做「自由的茶室」、「在爐子上放個鍋,也可以用來品嚐鍋中物」。我呢,本來就只會做自由的形式,放釜或放湯鍋對我來說是一樣的。
至今雖還沒有蓋在斜面的茶室之前例,架高的地板是山側提高一尺,谷側提高四尺,地板底部以圓木為支柱撐起,會成為一個像是從斜面上忽然浮出的有趣茶室。因工期的超短縮,就委託給劇場的舞台製作公司。其他呢,則由業主和關係人總動員。
工程途中,法國大使館的書記官來訪,依席拉克總理的身材幫我們決定躙口的尺寸後才回去。席拉克總理意外地比我們的印象個子還小。
自認的茶室第一號完成了,由於速度之快,命名為〈一夜亭〉(圖2)。
當爬上斜面的石階時,可以仰看到從地板底部突出來的爐的屁股,轉彎,則看到浮在一尺高的半空中的躙口。縮身,匍匐而入之後,上半身伸直,在正面可以看到一個橫長的大窗戶。從斜上方眺望,可以看到主屋和工作房所圍成的那個有熱湯湧出的小廣場。在主屋的日本瓦和工作房的銅板屋頂的前方,可以看到展開了一片谷間的綠意風光。雖然登上斜面看了不知幾遍已見慣的風景,但是從茶室中眺望,不論是瓦、銅板、樹林的綠意,看起來都新鮮。是不是因為從高處眺望呢?地板只離地一尺,這樣的高度不可能有眺望的效果。是不是窗框的效果呢?不怎麼樣的畫或照片裝上框後,會增加其鮮度。風景加框的話也會強調框內之景,從綿延廣闊的周圍中浮現出來。但是,為什麼從住家的窗戶眺望,就映不出這樣的新鮮感,應該不能說框緣效果是其本質,那麼,是什麼能如此地淸洗了眼球呢?
一定是躙口!
當然這不是我的創意,這是傳統茶室的定規之一,特意從狹小的入口進入。由於從小入口進入,狹小的茶室會感到寬濶的視覺效果,狹小的入口也將茶室的內與外明快的分開,產生內外是兩個別世界的心理效果,這是眾所皆知的。把狹小的內部變寬濶,內部成為別世界,換句話說,是所謂的壺中天效果。在小小壺中,由狹窄入口進入一看,在裡面展開一個不輸於外面的天地。
為了理解為什麼會引起這樣的壺中天效果,我就幾度鑽入鑽出這為席拉克總理所做比一般稍寬一點的躙口,謎解開了。縮身鑽入時,意識會一瞬間被切斷。在縮身前仍會注意到四周,身體也還是照樣在動,但到了躙口前,會吸一口氣,兩手放到地板上,頭朝下,縮身,止息,然後兩膝並排,猛然浮出上身,滑進鑽入躙口時,為了不讓身體碰觸到狹小的躙口之框,五感就收束在觸覺上,視覺消失。眼睛自然閉上。
一瞬間,意識空白化,縮身鑽入的前後是沒有連結的。從狹小洞口縮身通過時,人的身體帶給人的意識一瞬間的斷切,這可能就是壺中天效果的祕密。
到此〈一夜亭〉和傳統茶室並沒有不同,但鑽入後,就不一樣了,開了一個傳統茶室想不到的大窗,可以向外眺望。
利休規定的茶室雖有採光用的障子,但絕不允許打開向外眺望。雖然我擔心在閉鎖性為主旨的茶室中開大窗,會削弱壺中天性,不過在斜面的山側一尺,谷側四尺上所蓋的茶室,看到整體從地面浮出的效果意外的大,和一般在地上直接置入建築物所帶來的印象不同,這個印象可以補強被削弱的壺中天性。
比〈一夜亭〉稍晚,德正寺的茶室也完成,有著直角的三角定規般的平面,再加上秋野先生的畫家母親尊名秋野不矩,就取其矩字為茶室命名〈矩庵〉(圖3)。
這兩個茶室改變了我的茶室觀。
從〈矩庵〉的爐的這一件事,我知道茶室還藏有値得思考的大主題。為什麼利休在如此狹小的空間中還特地投入火呢?
從開了窗的〈一夜亭〉,可以確定即使脫離定式,所謂茶室的壺中天仍然是有可能的。若能脫離定式,茶室的自由度就可能更大。
因此,我這個對茶室甦醒的五十六歲的建築史家兼建築家,開始閱讀自從聽稻垣先生所授的《南方錄》課程後都沒有再碰過的其他茶室相關書籍,尋思「茶室是什麼?」這類的抽象思考,又聽中村昌生、熊倉功夫兩位教授的談話,從此就一腳踏進這與我不相稱的行動。
首次和茶室正面接觸,是在舊知秋野等先生邀請我在他任住持的京都德正寺的後院蓋一茶室時。工程途中,細川護熙先生(日本前首相)來電要我「三個月內蓋個茶室」。
兩年前就聽說他要蓋茶室。也耳聞他要以自己庭院盡頭處的樹蔭做基地,已請京都有名的數寄屋大工領班,一點一點地在搜集煤竹等的材料。
現在要做一個茶室,從設計和材料的準備到完工,需三年。
費用呢,一坪的下限是五百萬日幣,無上限。雖然很高,但絕非建築業者在揩油。我著手的茶室,是採取除業主外加上學生等很多的關係人一起參加工事的變通體制,所以正確的總工費並不淸楚,當我做〈茶室 徹〉(二○○五年)時,我想應該一次好好地計算從設計、材料到施工完成所該付的費用,付完後一坪就增為八百萬日幣。如果考量利益和風險,則一坪不到一千萬日幣應該不能接案。
三年縮短成三個月,而且三個月後要迎接貴賓,實際工期只有一個月。細川先生十七代前的祖先細川忠興,是日本戰國時代的利休七哲之一,以當時利休配合秀吉出征,數日之內完成一個茶室,迎接秀吉的故事來看,三個月也不算沒有道理。如果是利休的話,已經完成好幾個了。基地呢,也不是以前聽說的庭院的盡頭處,而是在陶藝工房的山側之斜面。從山上引來的溫泉作為中心點,由主屋和工作房三方圍成一個小廣場,如果在展開的山側置入茶室,那麼由建築圍起一個中央湧出熱泉的廣場就產生了。細川先生的願望是,做「自由的茶室」、「在爐子上放個鍋,也可以用來品嚐鍋中物」。我呢,本來就只會做自由的形式,放釜或放湯鍋對我來說是一樣的。
至今雖還沒有蓋在斜面的茶室之前例,架高的地板是山側提高一尺,谷側提高四尺,地板底部以圓木為支柱撐起,會成為一個像是從斜面上忽然浮出的有趣茶室。因工期的超短縮,就委託給劇場的舞台製作公司。其他呢,則由業主和關係人總動員。
工程途中,法國大使館的書記官來訪,依席拉克總理的身材幫我們決定躙口的尺寸後才回去。席拉克總理意外地比我們的印象個子還小。
自認的茶室第一號完成了,由於速度之快,命名為〈一夜亭〉(圖2)。
當爬上斜面的石階時,可以仰看到從地板底部突出來的爐的屁股,轉彎,則看到浮在一尺高的半空中的躙口。縮身,匍匐而入之後,上半身伸直,在正面可以看到一個橫長的大窗戶。從斜上方眺望,可以看到主屋和工作房所圍成的那個有熱湯湧出的小廣場。在主屋的日本瓦和工作房的銅板屋頂的前方,可以看到展開了一片谷間的綠意風光。雖然登上斜面看了不知幾遍已見慣的風景,但是從茶室中眺望,不論是瓦、銅板、樹林的綠意,看起來都新鮮。是不是因為從高處眺望呢?地板只離地一尺,這樣的高度不可能有眺望的效果。是不是窗框的效果呢?不怎麼樣的畫或照片裝上框後,會增加其鮮度。風景加框的話也會強調框內之景,從綿延廣闊的周圍中浮現出來。但是,為什麼從住家的窗戶眺望,就映不出這樣的新鮮感,應該不能說框緣效果是其本質,那麼,是什麼能如此地淸洗了眼球呢?
一定是躙口!
當然這不是我的創意,這是傳統茶室的定規之一,特意從狹小的入口進入。由於從小入口進入,狹小的茶室會感到寬濶的視覺效果,狹小的入口也將茶室的內與外明快的分開,產生內外是兩個別世界的心理效果,這是眾所皆知的。把狹小的內部變寬濶,內部成為別世界,換句話說,是所謂的壺中天效果。在小小壺中,由狹窄入口進入一看,在裡面展開一個不輸於外面的天地。
為了理解為什麼會引起這樣的壺中天效果,我就幾度鑽入鑽出這為席拉克總理所做比一般稍寬一點的躙口,謎解開了。縮身鑽入時,意識會一瞬間被切斷。在縮身前仍會注意到四周,身體也還是照樣在動,但到了躙口前,會吸一口氣,兩手放到地板上,頭朝下,縮身,止息,然後兩膝並排,猛然浮出上身,滑進鑽入躙口時,為了不讓身體碰觸到狹小的躙口之框,五感就收束在觸覺上,視覺消失。眼睛自然閉上。
一瞬間,意識空白化,縮身鑽入的前後是沒有連結的。從狹小洞口縮身通過時,人的身體帶給人的意識一瞬間的斷切,這可能就是壺中天效果的祕密。
到此〈一夜亭〉和傳統茶室並沒有不同,但鑽入後,就不一樣了,開了一個傳統茶室想不到的大窗,可以向外眺望。
利休規定的茶室雖有採光用的障子,但絕不允許打開向外眺望。雖然我擔心在閉鎖性為主旨的茶室中開大窗,會削弱壺中天性,不過在斜面的山側一尺,谷側四尺上所蓋的茶室,看到整體從地面浮出的效果意外的大,和一般在地上直接置入建築物所帶來的印象不同,這個印象可以補強被削弱的壺中天性。
比〈一夜亭〉稍晚,德正寺的茶室也完成,有著直角的三角定規般的平面,再加上秋野先生的畫家母親尊名秋野不矩,就取其矩字為茶室命名〈矩庵〉(圖3)。
這兩個茶室改變了我的茶室觀。
從〈矩庵〉的爐的這一件事,我知道茶室還藏有値得思考的大主題。為什麼利休在如此狹小的空間中還特地投入火呢?
從開了窗的〈一夜亭〉,可以確定即使脫離定式,所謂茶室的壺中天仍然是有可能的。若能脫離定式,茶室的自由度就可能更大。
因此,我這個對茶室甦醒的五十六歲的建築史家兼建築家,開始閱讀自從聽稻垣先生所授的《南方錄》課程後都沒有再碰過的其他茶室相關書籍,尋思「茶室是什麼?」這類的抽象思考,又聽中村昌生、熊倉功夫兩位教授的談話,從此就一腳踏進這與我不相稱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