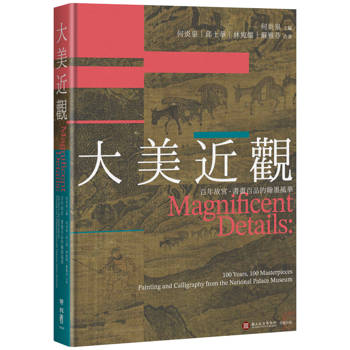書法
晉 王羲之 平安何如奉橘三帖──潮到今日的野雞體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由三件作品組成。〈平安〉、〈何如〉是兩封短信,〈奉橘〉是〈何如〉附書,為傳世書跡中最接近楷書的一件,可提供探索書聖謎樣的楷體。晚年所創之今體,點畫斜向,中心結構緊結,引起新的書寫風潮,曾被忌妒的庾翼(305-345)戲稱為「野鶩」或「野雉」體,然時至今日的標楷體仍繼承此風。
三帖皆為唐人雙鉤廓塡,複製極其逼眞精美,連墨色濃淡、行筆速度與線條質感等細節,都被精準表現出來,故有「下眞跡一等」之美譽,如「想」字。「餘」字中看似鉤摹失誤的「余」,乃由兩組正確筆順組成,一開始寫錯字,後來才補上豎鉤加一小橫來修正,珍貴地將當年誤書的過程保存下來。這些帶有修改痕跡的本子皆非寄出定本,而是階段性的稿本,王羲之傳世作品也以此為大宗。
書寫過程中充滿著驚喜與創意,達到變化神明的境界。看似無奇的「安」字,下筆後一個強而有力的折筆,直接拉至最細並完成圓轉右肩,後面三筆往中心緊靠,幾乎達到密不通風,與周圍疏可走馬的空間,產生強烈視覺對比。中間橫畫為豐潤的優美弧形,緩和中心過重的橫豎筆畫,同時牢牢地抱住整個字,將單字的重心往下移動,整體上獲得更佳的安穩感。搭配起收處的筆鋒細微變化動作,全字精神瞬間抖擻起來,收到畫龍點睛之效。
這種求新求變的書寫態度,不僅貫穿所有的作品,也出現在簽名中,傳世名款無一類同。後代書家只要學得一招半式,便足以成名,例如歐陽詢(557-641)、虞世南(558-638)、褚遂良(596-658)。儘管流傳書跡不多,卻已完整預示後世可能發展的技法與審美,幾乎無人能避開其影響力。即使最為極端的淸代碑學書家,評論的審美標準仍源自於王字系統,所大力推崇的北碑也是南方士人北漂的傑作,所展現的正是南朝流行的今體書風。看似挑戰了以王羲之為核心的傳統帖學,事實上卻更貼近帖學眞面目,完全逃離不了書聖的五指山。
人物小傳:
王羲之,字逸少,祖籍琅邪,後遷山陰(浙江紹興),官拜右軍將軍,人稱王右軍,被尊為書聖。晚年從漢魏質樸書風中,開創出妍美雄俊的今體,千變萬化,影響至今。唐太宗(598-649)親撰《晉書.王羲之傳》,給予「盡善盡美」的最高評價。
山水
宋 郭熙 早春圖──千年前的動畫
〈早春圖〉左側伸出的一對蟹爪樹,像是上下括號般地框起「早春。壬子年郭熙畫」一行小字,並鈐有「郭熙筆」一印。早期畫作留有畫家題款不多,而〈早春圖〉卻有郭熙(約1023-1085)於宋神宗(1048-1085)熙寧五年(1072),親簽並自書畫名,實是稀有珍貴,為繪畫史的重要畫例。
郭熙甚受宋神宗與蘇軾、黃庭堅等文人士大夫的喜愛與推崇,他在宮廷與官署留下頗多畫作,風靡一時。他的兒子將郭熙對繪畫的見解整理成《林泉高致》。〈早春圖〉正可與這部畫論相參看。畫中S型構成的主山,正是「大山堂堂,為眾山之主」的氣勢,其餘岡阜林壑,宛若前來朝會;前景正中巖塊上的雙松,確有「長松亭亭,為眾木之表」的風姿,其餘草木藤蘿,皆俯身相從。《林泉高致》有關「早春」的畫題就有八種:「早春雲景」、「早春雨景」、「殘雪早春」、「雪霽早春」、「雨霽早春」、「煙雨早春」、「早春晚景」、「早春煙靄」。這些畫題展現郭熙精確設定與掌握特定時間的細膩天氣型態──山水空間裡的溫度、風向、雨勢、雲煙、光線變化。〈早春圖〉又是哪一種春景呢?
畫中前景右方的漁人泊岸收網中;左方母親抱著幼兒與小童一起迎接父親回家;上方騎驢過橋的士人與僕役,與更前方持杖、挑物的行旅,或許正趕往右側建築群……,〈早春圖〉應是某個接近傍晚,煙靄漸漸襲上山巖的時刻。
煙靄的描繪令人印象深刻。乍看只是沿著山稜排列的中景林木,細看可見部分樹頂的葉子已籠在薄霧中,再看後方還有挺峭的松樹開展枝枒淺淡卻分明的形狀,左側原以為是畫絹淡淡污痕,其實是郭熙用更淡的墨色蟹爪樹枝,追蹤著同樣淺淡的墨色往下看,又發現其實還有隱約的樹冠,以及其下的主幹。光是這一小區山頭林木,就有一種可以不斷深入霧中,發現新物象浮現的感覺。這種耐人探究的迷濛,歸功自郭熙對墨色極度細膩的掌控。
郭熙描繪山石時使用的「雲頭皴」富含水分,線條粗細變化多端,經常呈現弧形扭曲的輪廓。不僅使畫面充滿濕潤的氣息,也讓山石的具體造型變得模糊難辨,增添了畫作的朦朧感與想像空間。例如小茅屋右上方的山巖肥潤的筆畫,應該以紅色還是藍色的邊緣作為那巖塊的形狀?或者整道筆畫是郭熙繪成的一塊潑辣暗面?無論作為輪廓線或內分線,雲頭皴總形成一種混融的曖昧,晃動著我們對形狀的認知。《林泉高致》提到:「筆跡不混成謂之疏,疏則無真意;墨色不滋潤謂之枯,枯則無生意。」〈早春圖〉筆跡混成、墨色滋潤,展演著屬於郭熙體會的眞意與生意。
〈早春圖〉山巒組成的「S」型或「卍」字型,從構圖上就引發動感,加上變幻無定的雲頭皴,以及墨色層次的細膩操作,讓早春煙靄隱現,在千年前的畫絹上凝結出神奇的「動畫」效果。
人物
宋人 折檻圖──戲劇張力滿分的宮廷規諫畫
這件作品取材自漢代朱雲直諫漢成帝(前51-前7)故實,屬提倡、教育君王應有納諫胸襟之規諫畫。在這幅雙拼絹本上,畫家細膩刻畫人物表情與肢體動態,藉由人物情緒與心理狀態的對照,為這個由文字記錄下的歷史場景,以圖像注入出色的戲劇性、緊張感。
在開闊而雅致之庭園中,椅上的漢成帝目光冷峻地投向其右側。其眼角微微上揚,流露出威壓之感;而其唇角下壓、雙唇緊抿,鼻翼擴張並且凸顯深刻的法令紋,顯示壓抑的怒氣。順著其視線方向,身體重心亦偏向右側,從聳起之右肩、橫倚於扶手並支撐著重心的手肘、順著手腕而垂落之袖口,一層一層將觀眾視線引導至其坐姿。皇帝的右腿盤起,而另手則以虎口反手按壓左腿,使左側胸口拉開,兩腿膝蓋朝外,形成略帶侵略性的肢體語言,展現威懾之勢。繪製雙臂衣袍所用之線條勁利多折,對照著描繪披掛到左腿衣襬所用之流暢而等距的圓弧長線條,帶出皇帝動作姿態的複雜性。在他後方,侍女交頭接耳,其中一人並伸出手指向帝師張禹。被控為佞臣的張禹(?-前5)微微側首,神情似笑非笑,眉宇之間隆起的川字紋,顯示其心中若有盤算。
另一側,被賜死的朱雲緊抱欄杆、奮力掙扎著,他張口吶喊、眼神殷切,鼻孔更因奮力抵抗而噴張,描繪衣袍的線條方向性散亂,表現出織物在拉扯之間而激烈翻飛的動態。朱雲身旁的兩名衛士則呈現穩定的壓制力量,背向畫外者張開雙腳穩固重心,表現出強行向左的拉扯力量;另一位則流露出警戒神情,他雙眼上瞟、並且因噘嘴在下巴形成一道顯著的拱形弧線,其緊扣朱雲雙肩的手指,因用力過度而關節凹折,展現出強硬壓制的力道。上前進諫的辛慶忌(?-前12)雖表情平穩,執笏彎腰姿態懇切,然衣袍末端為粗細變化顯著的Z字型曲線,顯露些微的衣帶飄揚,暗示他方才急步上前進言,身形剎地停住,衣袂因疾行的餘勢微微翻動,延續天子之怒的緊張氣氛。
畫面並未揭曉漢成帝的最終決斷,朱雲仍是命懸一線,讓此畫的圖像敍事充滿懸念與戲劇張力,使後續闡述歷史故實之勸諫寓意時,更加引人入勝。
花鳥
宋 法常 寫生──墨分五色:古代的3D 立體黑白照片
這件〈寫生〉水墨長卷共拼接了十五張長短不一的紙,依序繪製花卉、水果、蔬菜、花卉、翎毛(鳥類),將二十五種花鳥蔬果維妙維肖收於畫中,造型單純古拙。卷末款署「咸淳改元(1265)牧谿」。這種取材自日常生活的作品又被稱為「雜畫」,藉由寫生的方式,用來抒發自身內在精神,因此逐漸受到文人、禪僧的靑睞。儘管描繪的是常見的動植物,卻能藉由黑墨的單色變化生動捕捉物象的生機。畫中不相關的題材既可獨立觀看,也可以因為外型和畫法相似而被視為完整的作品,相當耐人尋味。
畫家以簡練的筆墨精準抓住動植物特徵,利用黑色水墨的濃淡、乾濕變化,呈現物象的色調,效果如同現代的黑白照片。以第十九個主題為例,畫中共繪有五種不同瓜果,分別用不同手法繪製表面的圓潤平滑或粗糙紋路。中間第三顆矮扁如南瓜的瓜果,面向觀者完整的那一片瓜瓣墨色特意由深至淺,最後在正中央留白,表現出亮到反光的蠟質表皮。儘管距今約一千年,無法完全確認是什麼品種,但仍能藉由畫家細膩繪製表皮紋路,區分五種瓜果的不同之處。
第十三個主題繪製兩株用雜草綁起的蓮蓬。畫家仔細用墨色深淺區分出蓮蓬凹凸的體積感,彷彿西洋繪畫的「明暗法」,只是底部沒有反光的亮面,只是單純的區分陰陽面。蓮莖以一淺一深的水墨平塗出光滑的表面,但也顯得較扁平無體積感,再用深墨乾筆撇出破碎的雜草。對現代人的眼睛而言,這三種畫法組合在一起的物象既平面又立體,像是超現實繪畫,也許會有點不好理解。實際上,畫家是利用不同技法強調物體的質感。這種水墨表現方式稱為「墨分五色(五彩)」或「墨具五色」。即使不上彩色顏料,觀眾也能藉由墨色的表現,為動植物「腦補」出合理的色彩及質感,可以說是古代的3D立體黑白影像。
人物小傳:
法常,號牧谿(溪)。南宋僧人畫家,擅長以簡易墨筆描繪物象,稱為「墨戲」。儘管畫風在當時被譏笑是「粗惡無古法」,然而作品被日本僧人攜回日本後,這種率性自然的風格卻深刻影響日本禪宗繪畫。
晉 王羲之 平安何如奉橘三帖──潮到今日的野雞體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由三件作品組成。〈平安〉、〈何如〉是兩封短信,〈奉橘〉是〈何如〉附書,為傳世書跡中最接近楷書的一件,可提供探索書聖謎樣的楷體。晚年所創之今體,點畫斜向,中心結構緊結,引起新的書寫風潮,曾被忌妒的庾翼(305-345)戲稱為「野鶩」或「野雉」體,然時至今日的標楷體仍繼承此風。
三帖皆為唐人雙鉤廓塡,複製極其逼眞精美,連墨色濃淡、行筆速度與線條質感等細節,都被精準表現出來,故有「下眞跡一等」之美譽,如「想」字。「餘」字中看似鉤摹失誤的「余」,乃由兩組正確筆順組成,一開始寫錯字,後來才補上豎鉤加一小橫來修正,珍貴地將當年誤書的過程保存下來。這些帶有修改痕跡的本子皆非寄出定本,而是階段性的稿本,王羲之傳世作品也以此為大宗。
書寫過程中充滿著驚喜與創意,達到變化神明的境界。看似無奇的「安」字,下筆後一個強而有力的折筆,直接拉至最細並完成圓轉右肩,後面三筆往中心緊靠,幾乎達到密不通風,與周圍疏可走馬的空間,產生強烈視覺對比。中間橫畫為豐潤的優美弧形,緩和中心過重的橫豎筆畫,同時牢牢地抱住整個字,將單字的重心往下移動,整體上獲得更佳的安穩感。搭配起收處的筆鋒細微變化動作,全字精神瞬間抖擻起來,收到畫龍點睛之效。
這種求新求變的書寫態度,不僅貫穿所有的作品,也出現在簽名中,傳世名款無一類同。後代書家只要學得一招半式,便足以成名,例如歐陽詢(557-641)、虞世南(558-638)、褚遂良(596-658)。儘管流傳書跡不多,卻已完整預示後世可能發展的技法與審美,幾乎無人能避開其影響力。即使最為極端的淸代碑學書家,評論的審美標準仍源自於王字系統,所大力推崇的北碑也是南方士人北漂的傑作,所展現的正是南朝流行的今體書風。看似挑戰了以王羲之為核心的傳統帖學,事實上卻更貼近帖學眞面目,完全逃離不了書聖的五指山。
人物小傳:
王羲之,字逸少,祖籍琅邪,後遷山陰(浙江紹興),官拜右軍將軍,人稱王右軍,被尊為書聖。晚年從漢魏質樸書風中,開創出妍美雄俊的今體,千變萬化,影響至今。唐太宗(598-649)親撰《晉書.王羲之傳》,給予「盡善盡美」的最高評價。
山水
宋 郭熙 早春圖──千年前的動畫
〈早春圖〉左側伸出的一對蟹爪樹,像是上下括號般地框起「早春。壬子年郭熙畫」一行小字,並鈐有「郭熙筆」一印。早期畫作留有畫家題款不多,而〈早春圖〉卻有郭熙(約1023-1085)於宋神宗(1048-1085)熙寧五年(1072),親簽並自書畫名,實是稀有珍貴,為繪畫史的重要畫例。
郭熙甚受宋神宗與蘇軾、黃庭堅等文人士大夫的喜愛與推崇,他在宮廷與官署留下頗多畫作,風靡一時。他的兒子將郭熙對繪畫的見解整理成《林泉高致》。〈早春圖〉正可與這部畫論相參看。畫中S型構成的主山,正是「大山堂堂,為眾山之主」的氣勢,其餘岡阜林壑,宛若前來朝會;前景正中巖塊上的雙松,確有「長松亭亭,為眾木之表」的風姿,其餘草木藤蘿,皆俯身相從。《林泉高致》有關「早春」的畫題就有八種:「早春雲景」、「早春雨景」、「殘雪早春」、「雪霽早春」、「雨霽早春」、「煙雨早春」、「早春晚景」、「早春煙靄」。這些畫題展現郭熙精確設定與掌握特定時間的細膩天氣型態──山水空間裡的溫度、風向、雨勢、雲煙、光線變化。〈早春圖〉又是哪一種春景呢?
畫中前景右方的漁人泊岸收網中;左方母親抱著幼兒與小童一起迎接父親回家;上方騎驢過橋的士人與僕役,與更前方持杖、挑物的行旅,或許正趕往右側建築群……,〈早春圖〉應是某個接近傍晚,煙靄漸漸襲上山巖的時刻。
煙靄的描繪令人印象深刻。乍看只是沿著山稜排列的中景林木,細看可見部分樹頂的葉子已籠在薄霧中,再看後方還有挺峭的松樹開展枝枒淺淡卻分明的形狀,左側原以為是畫絹淡淡污痕,其實是郭熙用更淡的墨色蟹爪樹枝,追蹤著同樣淺淡的墨色往下看,又發現其實還有隱約的樹冠,以及其下的主幹。光是這一小區山頭林木,就有一種可以不斷深入霧中,發現新物象浮現的感覺。這種耐人探究的迷濛,歸功自郭熙對墨色極度細膩的掌控。
郭熙描繪山石時使用的「雲頭皴」富含水分,線條粗細變化多端,經常呈現弧形扭曲的輪廓。不僅使畫面充滿濕潤的氣息,也讓山石的具體造型變得模糊難辨,增添了畫作的朦朧感與想像空間。例如小茅屋右上方的山巖肥潤的筆畫,應該以紅色還是藍色的邊緣作為那巖塊的形狀?或者整道筆畫是郭熙繪成的一塊潑辣暗面?無論作為輪廓線或內分線,雲頭皴總形成一種混融的曖昧,晃動著我們對形狀的認知。《林泉高致》提到:「筆跡不混成謂之疏,疏則無真意;墨色不滋潤謂之枯,枯則無生意。」〈早春圖〉筆跡混成、墨色滋潤,展演著屬於郭熙體會的眞意與生意。
〈早春圖〉山巒組成的「S」型或「卍」字型,從構圖上就引發動感,加上變幻無定的雲頭皴,以及墨色層次的細膩操作,讓早春煙靄隱現,在千年前的畫絹上凝結出神奇的「動畫」效果。
人物
宋人 折檻圖──戲劇張力滿分的宮廷規諫畫
這件作品取材自漢代朱雲直諫漢成帝(前51-前7)故實,屬提倡、教育君王應有納諫胸襟之規諫畫。在這幅雙拼絹本上,畫家細膩刻畫人物表情與肢體動態,藉由人物情緒與心理狀態的對照,為這個由文字記錄下的歷史場景,以圖像注入出色的戲劇性、緊張感。
在開闊而雅致之庭園中,椅上的漢成帝目光冷峻地投向其右側。其眼角微微上揚,流露出威壓之感;而其唇角下壓、雙唇緊抿,鼻翼擴張並且凸顯深刻的法令紋,顯示壓抑的怒氣。順著其視線方向,身體重心亦偏向右側,從聳起之右肩、橫倚於扶手並支撐著重心的手肘、順著手腕而垂落之袖口,一層一層將觀眾視線引導至其坐姿。皇帝的右腿盤起,而另手則以虎口反手按壓左腿,使左側胸口拉開,兩腿膝蓋朝外,形成略帶侵略性的肢體語言,展現威懾之勢。繪製雙臂衣袍所用之線條勁利多折,對照著描繪披掛到左腿衣襬所用之流暢而等距的圓弧長線條,帶出皇帝動作姿態的複雜性。在他後方,侍女交頭接耳,其中一人並伸出手指向帝師張禹。被控為佞臣的張禹(?-前5)微微側首,神情似笑非笑,眉宇之間隆起的川字紋,顯示其心中若有盤算。
另一側,被賜死的朱雲緊抱欄杆、奮力掙扎著,他張口吶喊、眼神殷切,鼻孔更因奮力抵抗而噴張,描繪衣袍的線條方向性散亂,表現出織物在拉扯之間而激烈翻飛的動態。朱雲身旁的兩名衛士則呈現穩定的壓制力量,背向畫外者張開雙腳穩固重心,表現出強行向左的拉扯力量;另一位則流露出警戒神情,他雙眼上瞟、並且因噘嘴在下巴形成一道顯著的拱形弧線,其緊扣朱雲雙肩的手指,因用力過度而關節凹折,展現出強硬壓制的力道。上前進諫的辛慶忌(?-前12)雖表情平穩,執笏彎腰姿態懇切,然衣袍末端為粗細變化顯著的Z字型曲線,顯露些微的衣帶飄揚,暗示他方才急步上前進言,身形剎地停住,衣袂因疾行的餘勢微微翻動,延續天子之怒的緊張氣氛。
畫面並未揭曉漢成帝的最終決斷,朱雲仍是命懸一線,讓此畫的圖像敍事充滿懸念與戲劇張力,使後續闡述歷史故實之勸諫寓意時,更加引人入勝。
花鳥
宋 法常 寫生──墨分五色:古代的3D 立體黑白照片
這件〈寫生〉水墨長卷共拼接了十五張長短不一的紙,依序繪製花卉、水果、蔬菜、花卉、翎毛(鳥類),將二十五種花鳥蔬果維妙維肖收於畫中,造型單純古拙。卷末款署「咸淳改元(1265)牧谿」。這種取材自日常生活的作品又被稱為「雜畫」,藉由寫生的方式,用來抒發自身內在精神,因此逐漸受到文人、禪僧的靑睞。儘管描繪的是常見的動植物,卻能藉由黑墨的單色變化生動捕捉物象的生機。畫中不相關的題材既可獨立觀看,也可以因為外型和畫法相似而被視為完整的作品,相當耐人尋味。
畫家以簡練的筆墨精準抓住動植物特徵,利用黑色水墨的濃淡、乾濕變化,呈現物象的色調,效果如同現代的黑白照片。以第十九個主題為例,畫中共繪有五種不同瓜果,分別用不同手法繪製表面的圓潤平滑或粗糙紋路。中間第三顆矮扁如南瓜的瓜果,面向觀者完整的那一片瓜瓣墨色特意由深至淺,最後在正中央留白,表現出亮到反光的蠟質表皮。儘管距今約一千年,無法完全確認是什麼品種,但仍能藉由畫家細膩繪製表皮紋路,區分五種瓜果的不同之處。
第十三個主題繪製兩株用雜草綁起的蓮蓬。畫家仔細用墨色深淺區分出蓮蓬凹凸的體積感,彷彿西洋繪畫的「明暗法」,只是底部沒有反光的亮面,只是單純的區分陰陽面。蓮莖以一淺一深的水墨平塗出光滑的表面,但也顯得較扁平無體積感,再用深墨乾筆撇出破碎的雜草。對現代人的眼睛而言,這三種畫法組合在一起的物象既平面又立體,像是超現實繪畫,也許會有點不好理解。實際上,畫家是利用不同技法強調物體的質感。這種水墨表現方式稱為「墨分五色(五彩)」或「墨具五色」。即使不上彩色顏料,觀眾也能藉由墨色的表現,為動植物「腦補」出合理的色彩及質感,可以說是古代的3D立體黑白影像。
人物小傳:
法常,號牧谿(溪)。南宋僧人畫家,擅長以簡易墨筆描繪物象,稱為「墨戲」。儘管畫風在當時被譏笑是「粗惡無古法」,然而作品被日本僧人攜回日本後,這種率性自然的風格卻深刻影響日本禪宗繪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