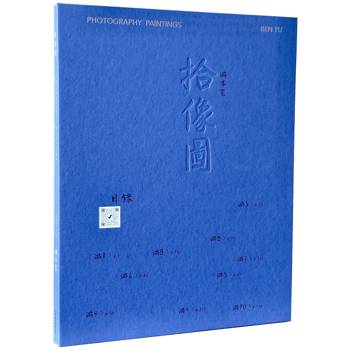◎宗教般的創作迷藥
星巴克的座椅上,靠窗的女士對一旁的男人說:藝術來自生活。心想,她一定淡化或遺漏了什麼?如果生活中的大小事都可以是藝術,那麼作品、創作者就不會是專業了。我是否過度嚴肅的把「藝術好玩」的面向排除在外?或許是吧!
拿相機創作近四十年居然還是想不通:以美術知識為本的影像藝術創作「美術攝影」,不斷質疑影像的「此曾在」是宿命?有必要全力抗拒影像真實再現的觀點嗎?拿著相機拍照是否暴露了拍攝者不善於繪畫的事實?集結眾多的作品,能否顯露出拍攝者的人格特質?
⋯⋯
⋯⋯
即使祈禱年齡跟創作沒有反向關係,倒是很清楚,作品得殘酷的面對創造力有形的考驗。大大小小的質疑,解釋了自己分秒都想要去做點什麼,無端的焦慮。
◎觀景窗後「以小觀大」的哲思
數位生活看似無遠弗屆,網路空間——忙碌、數位時間——焦慮,排隊的長龍,耳朵無法避開他人的八卦。
拍照,類比機身小小的觀景窗,雙眼篩選了當下的景物,數位的即時螢幕稍大一點,框限了現況的視野。照像的身體多了點聚焦,以小觀大的生活體驗,即使無法顯現深邃的人格特質,但多少表露了拍攝者和對象的細緻情緒反應。
拍照成像的擬真,往往加深了心智對現實「假貌」的探究,以及影像文化的悖論。攝影家拍照敘事常見的方法:(一)先看到整個(大的)世界,再從中找出個別較小的對象 ;(二)直接看到小對象,再由它擴展出去更大的世界。無論何種方法,過程中經常都修正了自己對世界的認知。
攝影人常說,攝影能力是影像的論述能力,只可惜並不是各個都能拍、說、寫。
◎減少本質以外的影像言說
有些攝影家藉由繁複的機械操作,來放慢自己直覺的反應,意圖延長對影像藝術的深思。但願如此的用心,不讓機具變成思緒的牽絆。反思,操作簡易的數位攝影對創作有害嗎?
拍攝者面對景物無意識的東拍拍西拍拍,看似嚴肅創作前的暖身,實為遮掩當下精神的焦慮。雖說邊做、邊想、邊修正,可以暫時不讓創作的困境陷在起跑點,但早晚總得在適當的時候,看清楚議題的本質,有計畫的加以表述。心想,按下快門前如果先花一點時間靜思對象的本質,不也是減少事後得花更多時間的再篩選?
語言學家說,人的耳朵必須先能聽出聲音的不同,嘴巴才能跟著發出相類似的聲音,官能跨領域的合作有其先後的次序。可見,「美術攝影家」追求內容豐富,遠離隔靴搔癢、無病呻吟的同時;還得謹記,花俏偽跨領域的美術形式淪為畫蛇添足。
星巴克的座椅上,靠窗的女士對一旁的男人說:藝術來自生活。心想,她一定淡化或遺漏了什麼?如果生活中的大小事都可以是藝術,那麼作品、創作者就不會是專業了。我是否過度嚴肅的把「藝術好玩」的面向排除在外?或許是吧!
拿相機創作近四十年居然還是想不通:以美術知識為本的影像藝術創作「美術攝影」,不斷質疑影像的「此曾在」是宿命?有必要全力抗拒影像真實再現的觀點嗎?拿著相機拍照是否暴露了拍攝者不善於繪畫的事實?集結眾多的作品,能否顯露出拍攝者的人格特質?
⋯⋯
⋯⋯
即使祈禱年齡跟創作沒有反向關係,倒是很清楚,作品得殘酷的面對創造力有形的考驗。大大小小的質疑,解釋了自己分秒都想要去做點什麼,無端的焦慮。
◎觀景窗後「以小觀大」的哲思
數位生活看似無遠弗屆,網路空間——忙碌、數位時間——焦慮,排隊的長龍,耳朵無法避開他人的八卦。
拍照,類比機身小小的觀景窗,雙眼篩選了當下的景物,數位的即時螢幕稍大一點,框限了現況的視野。照像的身體多了點聚焦,以小觀大的生活體驗,即使無法顯現深邃的人格特質,但多少表露了拍攝者和對象的細緻情緒反應。
拍照成像的擬真,往往加深了心智對現實「假貌」的探究,以及影像文化的悖論。攝影家拍照敘事常見的方法:(一)先看到整個(大的)世界,再從中找出個別較小的對象 ;(二)直接看到小對象,再由它擴展出去更大的世界。無論何種方法,過程中經常都修正了自己對世界的認知。
攝影人常說,攝影能力是影像的論述能力,只可惜並不是各個都能拍、說、寫。
◎減少本質以外的影像言說
有些攝影家藉由繁複的機械操作,來放慢自己直覺的反應,意圖延長對影像藝術的深思。但願如此的用心,不讓機具變成思緒的牽絆。反思,操作簡易的數位攝影對創作有害嗎?
拍攝者面對景物無意識的東拍拍西拍拍,看似嚴肅創作前的暖身,實為遮掩當下精神的焦慮。雖說邊做、邊想、邊修正,可以暫時不讓創作的困境陷在起跑點,但早晚總得在適當的時候,看清楚議題的本質,有計畫的加以表述。心想,按下快門前如果先花一點時間靜思對象的本質,不也是減少事後得花更多時間的再篩選?
語言學家說,人的耳朵必須先能聽出聲音的不同,嘴巴才能跟著發出相類似的聲音,官能跨領域的合作有其先後的次序。可見,「美術攝影家」追求內容豐富,遠離隔靴搔癢、無病呻吟的同時;還得謹記,花俏偽跨領域的美術形式淪為畫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