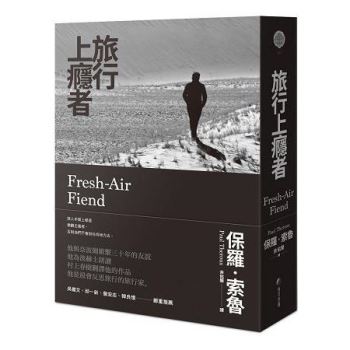我眼中的保羅‧索魯
由於有一個好像生下來就很老的奈波爾做為精神導師,保羅.索魯總是給人還很年輕的錯覺,其實這個有點瘋狂的旅人、寫作強迫症上身的筆耕者,已經七十了。 他是在你我所身處的新世界──不是指美洲,而是一個講究快速、歌頌全球化的世界中,來自舊世界──當然也不是說歐洲,而是人們仍習慣用身體丈量大地,尚未落入數位網羅的世界,一個像希羅多德或古典人類學家那樣行囊裝滿驚奇故事的漫遊者。 他親歷冷戰反戰、嬉皮運動、獨立不久還充滿殖民遺緒──包括秩序──的非洲,他那些驚人的一次性旅行路線:不管是從倫敦經歐洲、西亞、印度、東南亞、日本再從西伯利亞回到倫敦(《火車大旅行》),或是從波士頓家鄉小站一路南下巴塔哥尼亞高原(《老巴塔哥尼亞快車》)、從開羅到開普敦(《暗星薩伐旅》)、環地中海(《赫丘力士之柱》),甚至在廣袤的太平洋划獨木舟(《大洋洲的逍遙列島》)種種名副其實的壯遊,無一不是穿梭在跨度極大、異質性極強的時空,讓他猶如一個越界的巫、傳話者、通靈人。 他常常置身荒涼甚至荒謬(正是極少被主流媒體眷顧遑論注視、這世界許多土地和人的處境之寫照),但他自有定見、自得其樂,他的眼界與幽默使得他的招牌嘲諷辛辣但不帶酸腐味。他和魯西迪、馬赫富茲(!)、波赫士(I)、奈波爾的交誼(和交惡),堪稱當代傳奇。 今天的世界訊息如雲而真相如煙,行者移動更快、選擇益多卻看到更少,沒有保羅.索魯的手眼,我們真的不知道還要失去多少。
──吳繼文(知名作家)
旅人日已遠,典型在保羅‧索魯
如果要我只能介紹一個還活著的旅行作家,那我一定推薦保羅.索魯。他是個具有穿透能力的旅行作家,雖然世界上已經沒有未知的地方可以探險,但他仍懷抱著冒險情懷,穿透更難突破的政治疆界、族群藩籬和人們的心房,因而產生一種獨特的旅行文學──不媚俗,不矯揉,不隨波逐流,但也毫不留情,讀起來令人拍案叫絕、心有戚戚焉,只有真正的旅行人(Traveler)才懂得鑑賞。
──邱一新(旅行作家)
雖然我有時一邊讀保羅.索魯的旅遊書,心裡會忍不住一邊嘀咕:你這麼討厭那裡,幹嘛還要去呀?可是嘀咕完了,照樣津津有味地讀下去。沒辦法,這傢伙實在太會寫了,他那支偶爾憤世嫉俗卻也常有敏銳觀察與清澈洞見的筆,使得我這個讀者讀上了癮。
──韓良憶(知名作家)
他博學強記,又疑有自虐狂傾向,苦行僧似的完成一趟趟不可思議的大旅行,隨後出版一冊冊厚厚的遊記。他遇人遇事,態度厭煩,落筆為文,尖酸譏誚,一邊走一邊嫌,我心想:「幹嘛,有誰拿刀抵住脖子強押你旅行嗎?」 但我又一本本找來讀,有的反覆讀,有的跳著讀,有的無法終篇。大抵也是一邊讀一邊嫌,難免自嘲:「幹嘛,有誰拿刀抵住脖子強押妳讀嗎?」雷同的是自虐狂傾向。
──胡慧玲(讀者)
我非常喜歡讀保羅.索魯。我曾有一段時間生命的黑暗期,書架上的書沒一本能給我慰藉,然在無意間我買了《老巴塔哥尼亞快車》來讀,於是那段黑暗期變得稍可承受了,作者每一段的描寫我都喜歡,尤其第二十章他到達布宜諾斯艾利斯與波赫士交往的那一段,和波赫士的談話、為波赫士朗讀,不知為何,那段描述在往後常常撫慰了我的心。於是保羅.索魯的所有中文版我都買來讀了,我每本都喜歡,包括《維迪亞爵士的影子》,還翹首企盼新書。《旅行上癮者》很使我滿意,作者直陳他早年經驗(我很感興趣)、對小說、旅遊書的獨到看法,還有許多篇幅較小的、好看的旅遊經歷,書裡不時出現使我想重複閱讀之處。真好,等了好久,終於等到這本好看的書了。
──安石榴(讀者)
保羅.索魯的旅行文學最大特色是嘲諷,他喜歡顛覆既有印象,用挖苦的方式告訴讀者他的獨到觀察,譬如他描寫希臘時就是這種典型風格。 保羅.索魯評論希臘,並沒有沉醉於碧海藍天,他說,希臘人不學無術,只是一群無知的人管理自己也不了解的大理石古蹟。更糟糕的是不事生產,但由於加入歐盟,很幸運的,「已經獲得救贖」。因為,「會員的身份即意味送上門的錢」,「可以靠類似社會福利的方式存活了」。 這段文字出版於一九九五年,而二○一○年的二月,希臘爆發了債務危機,原因就是希臘政府長期借貸來支付國內的高福利體系,歐盟各國雖然痛批希臘生活方式揮霍,但最終還是不得不乖乖借出千億歐元幫他們度過難關,以免金融危機蔓延而拖垮歐盟。保羅.索魯的觀察獲得了驗證。 這種一針見血的判斷是來自他的博學,牙尖嘴利靠的是知識儲備,而不是情緒。讀保羅.索魯雖然可以感受尖酸刻薄的樂趣,但是他的遊記由於雜揉各種歷史考察、政經評論以及文學引用,事實上讀起來並不輕鬆。他像是個作家、記者、國際政治學家的混合,而且一下筆就滔滔不絕,有人說保羅.索魯的諷刺讓人厭煩,我覺得他這些民族誌式的喃喃自語才讓人厭煩──這是炫學?書一定要寫這麼厚嗎? 保羅.索魯的博學還表現在他會的語言上,從書裡看來,他除了母語英文外,至少還會西班牙文、法文、義大利文,以及一兩種非洲土語。他學會這麼多種語言,為的是旅途時與當地人對話,他非常喜歡對話,而且還常常挑釁對方,結果這些交談往往是書裡最有張力、最好看的部分。 保羅.索魯的書總是充滿了對話,除了和當地人交談之外,他還會隨身攜帶文學作品閱讀並記錄感想,這些感想是屬於心靈的對話。有時候他把兩種形式的對話結合起來──他會去拜訪當地的作家:譬如在阿根廷拜訪波赫士,在英國拜訪珍.莫里斯,在摩洛哥拜訪鮑爾斯。保羅.索魯在旅途中閱讀文學作品,是不要讓自己寂寞,那去拜訪作家,大概也是為了同樣的理由,他希望在文學的道路上感受一下溫暖與堅定。 大多數人的旅行,總是想脫離跟世界的聯繫,換得片刻寧靜。但保羅.索魯看不起觀光客,而他是旅人,挑釁的旅人,他最喜歡嘲諷的事物之一就是觀光客,他認為這些人只能獲得浮光掠影。而保羅.索魯是用打擾世界的方式在旅行,享受自虐的樂趣。他精心計畫路線,花費許多時間,掉了許多書袋,用激怒對方的方式對話,這一切只為求得一個新視野而已。而我們坐在家裡,捧讀他的著作的同時,很容易就想到:我何時也出去走走,尋求自己的視野?
──yuner(讀者)
由於有一個好像生下來就很老的奈波爾做為精神導師,保羅.索魯總是給人還很年輕的錯覺,其實這個有點瘋狂的旅人、寫作強迫症上身的筆耕者,已經七十了。 他是在你我所身處的新世界──不是指美洲,而是一個講究快速、歌頌全球化的世界中,來自舊世界──當然也不是說歐洲,而是人們仍習慣用身體丈量大地,尚未落入數位網羅的世界,一個像希羅多德或古典人類學家那樣行囊裝滿驚奇故事的漫遊者。 他親歷冷戰反戰、嬉皮運動、獨立不久還充滿殖民遺緒──包括秩序──的非洲,他那些驚人的一次性旅行路線:不管是從倫敦經歐洲、西亞、印度、東南亞、日本再從西伯利亞回到倫敦(《火車大旅行》),或是從波士頓家鄉小站一路南下巴塔哥尼亞高原(《老巴塔哥尼亞快車》)、從開羅到開普敦(《暗星薩伐旅》)、環地中海(《赫丘力士之柱》),甚至在廣袤的太平洋划獨木舟(《大洋洲的逍遙列島》)種種名副其實的壯遊,無一不是穿梭在跨度極大、異質性極強的時空,讓他猶如一個越界的巫、傳話者、通靈人。 他常常置身荒涼甚至荒謬(正是極少被主流媒體眷顧遑論注視、這世界許多土地和人的處境之寫照),但他自有定見、自得其樂,他的眼界與幽默使得他的招牌嘲諷辛辣但不帶酸腐味。他和魯西迪、馬赫富茲(!)、波赫士(I)、奈波爾的交誼(和交惡),堪稱當代傳奇。 今天的世界訊息如雲而真相如煙,行者移動更快、選擇益多卻看到更少,沒有保羅.索魯的手眼,我們真的不知道還要失去多少。
──吳繼文(知名作家)
旅人日已遠,典型在保羅‧索魯
如果要我只能介紹一個還活著的旅行作家,那我一定推薦保羅.索魯。他是個具有穿透能力的旅行作家,雖然世界上已經沒有未知的地方可以探險,但他仍懷抱著冒險情懷,穿透更難突破的政治疆界、族群藩籬和人們的心房,因而產生一種獨特的旅行文學──不媚俗,不矯揉,不隨波逐流,但也毫不留情,讀起來令人拍案叫絕、心有戚戚焉,只有真正的旅行人(Traveler)才懂得鑑賞。
──邱一新(旅行作家)
雖然我有時一邊讀保羅.索魯的旅遊書,心裡會忍不住一邊嘀咕:你這麼討厭那裡,幹嘛還要去呀?可是嘀咕完了,照樣津津有味地讀下去。沒辦法,這傢伙實在太會寫了,他那支偶爾憤世嫉俗卻也常有敏銳觀察與清澈洞見的筆,使得我這個讀者讀上了癮。
──韓良憶(知名作家)
他博學強記,又疑有自虐狂傾向,苦行僧似的完成一趟趟不可思議的大旅行,隨後出版一冊冊厚厚的遊記。他遇人遇事,態度厭煩,落筆為文,尖酸譏誚,一邊走一邊嫌,我心想:「幹嘛,有誰拿刀抵住脖子強押你旅行嗎?」 但我又一本本找來讀,有的反覆讀,有的跳著讀,有的無法終篇。大抵也是一邊讀一邊嫌,難免自嘲:「幹嘛,有誰拿刀抵住脖子強押妳讀嗎?」雷同的是自虐狂傾向。
──胡慧玲(讀者)
我非常喜歡讀保羅.索魯。我曾有一段時間生命的黑暗期,書架上的書沒一本能給我慰藉,然在無意間我買了《老巴塔哥尼亞快車》來讀,於是那段黑暗期變得稍可承受了,作者每一段的描寫我都喜歡,尤其第二十章他到達布宜諾斯艾利斯與波赫士交往的那一段,和波赫士的談話、為波赫士朗讀,不知為何,那段描述在往後常常撫慰了我的心。於是保羅.索魯的所有中文版我都買來讀了,我每本都喜歡,包括《維迪亞爵士的影子》,還翹首企盼新書。《旅行上癮者》很使我滿意,作者直陳他早年經驗(我很感興趣)、對小說、旅遊書的獨到看法,還有許多篇幅較小的、好看的旅遊經歷,書裡不時出現使我想重複閱讀之處。真好,等了好久,終於等到這本好看的書了。
──安石榴(讀者)
保羅.索魯的旅行文學最大特色是嘲諷,他喜歡顛覆既有印象,用挖苦的方式告訴讀者他的獨到觀察,譬如他描寫希臘時就是這種典型風格。 保羅.索魯評論希臘,並沒有沉醉於碧海藍天,他說,希臘人不學無術,只是一群無知的人管理自己也不了解的大理石古蹟。更糟糕的是不事生產,但由於加入歐盟,很幸運的,「已經獲得救贖」。因為,「會員的身份即意味送上門的錢」,「可以靠類似社會福利的方式存活了」。 這段文字出版於一九九五年,而二○一○年的二月,希臘爆發了債務危機,原因就是希臘政府長期借貸來支付國內的高福利體系,歐盟各國雖然痛批希臘生活方式揮霍,但最終還是不得不乖乖借出千億歐元幫他們度過難關,以免金融危機蔓延而拖垮歐盟。保羅.索魯的觀察獲得了驗證。 這種一針見血的判斷是來自他的博學,牙尖嘴利靠的是知識儲備,而不是情緒。讀保羅.索魯雖然可以感受尖酸刻薄的樂趣,但是他的遊記由於雜揉各種歷史考察、政經評論以及文學引用,事實上讀起來並不輕鬆。他像是個作家、記者、國際政治學家的混合,而且一下筆就滔滔不絕,有人說保羅.索魯的諷刺讓人厭煩,我覺得他這些民族誌式的喃喃自語才讓人厭煩──這是炫學?書一定要寫這麼厚嗎? 保羅.索魯的博學還表現在他會的語言上,從書裡看來,他除了母語英文外,至少還會西班牙文、法文、義大利文,以及一兩種非洲土語。他學會這麼多種語言,為的是旅途時與當地人對話,他非常喜歡對話,而且還常常挑釁對方,結果這些交談往往是書裡最有張力、最好看的部分。 保羅.索魯的書總是充滿了對話,除了和當地人交談之外,他還會隨身攜帶文學作品閱讀並記錄感想,這些感想是屬於心靈的對話。有時候他把兩種形式的對話結合起來──他會去拜訪當地的作家:譬如在阿根廷拜訪波赫士,在英國拜訪珍.莫里斯,在摩洛哥拜訪鮑爾斯。保羅.索魯在旅途中閱讀文學作品,是不要讓自己寂寞,那去拜訪作家,大概也是為了同樣的理由,他希望在文學的道路上感受一下溫暖與堅定。 大多數人的旅行,總是想脫離跟世界的聯繫,換得片刻寧靜。但保羅.索魯看不起觀光客,而他是旅人,挑釁的旅人,他最喜歡嘲諷的事物之一就是觀光客,他認為這些人只能獲得浮光掠影。而保羅.索魯是用打擾世界的方式在旅行,享受自虐的樂趣。他精心計畫路線,花費許多時間,掉了許多書袋,用激怒對方的方式對話,這一切只為求得一個新視野而已。而我們坐在家裡,捧讀他的著作的同時,很容易就想到:我何時也出去走走,尋求自己的視野?
──yuner(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