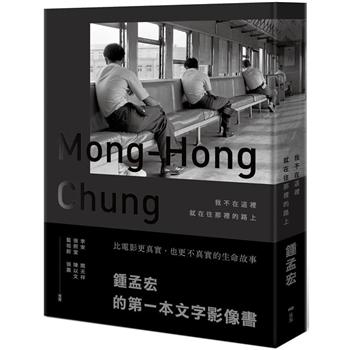相機(節錄)
安東尼奧尼的電影《春光乍現》裡面,相機不再只是一個記錄的工具,原始的影像藉由暗房不斷地放大,最後成為一個模糊、抽象的影像,進而揭發了一樁謀殺案。真實到底在哪哩?是眼睛所看到的嗎?還是隱藏在內心裡一塊不自知的角落?電影的男主角是一位憤世嫉俗的攝影家,他可以偽裝成工人的身分到工廠去拍紀實的照片,然後高價賣給媒體。他也可以化身為萬人迷般的時尚攝影家,像個巨星一樣擁有無限的魅力。在一次意外中,他拍到了一張照片,經過暗房的處理,他無意間在那張照片的角落發現某種東西,這種事情也只有在底片時代才那麼具有魅力,現在數位時代,電腦直接推進放大,那種曲折的感覺一下就沒了。男主角在暗房來來回回進出,濕淋淋的照片一張張掛起來,懸疑就這樣出來了。
當然懸疑不是這部片的重點,在我看來,安東尼奧尼想藉由這部影片,從影像中的真與假來說出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失落。其中一段男主角跑到一個演唱會現場,在舞台上演出的是六零年代英國走紅的庭中鳥樂團,一位跟吉他有仇、不斷攻擊手中樂器的那位吉他手就是Jeff¬ Beck,最後吉他被摔在地上,斷成了兩截,Je¬ff Beck 把其中一截丟到舞台下面,台下所有人搶成一團,最後還是被男主角搶到手,男主角搶到這把吉他柄之後衝到戶外,冷靜下來後看到自己手上拿了半把的爛吉他,想都沒想就把它丟在街角。
擁有第一台相機時,我還沒看過安東尼奧尼的《春光乍現》,但是我相信能拿一台相機到處拍照應該是很酷的事情。
大學二年級暑假前,在台北看了一位知名攝影前輩的攝影展,那時候看到他展出巨幅照片的震撼力,看完當下久久無法忘懷。後來得知他在暑假期間開了攝影工作坊就毅然決然報名了,很快地我就投入了他的暑假課程。
每個人都拍攝自己設定的主題,有些人拍天橋下的魔術師,有些人拍隔壁的老太太,他們不是只去拍個一天兩天,而是持續不斷地天天拍,不斷地追蹤拍攝。我一直不是很了解這些東西,心裡覺得他們記錄的那些不就是我們鄉下叔叔伯伯們的爛故事嗎?生活的貧困,工作或家庭的不美滿,不就是我從小看著長大的那些鳥事?但是在我的同學跟前輩的對談裡面,好像每一篇都是感人肺腑的故事,也許就是在那時候,內心生起對這些感人故事的排斥。可能是自己的想法太偏頗了,事情不全都是這樣子,很多人對城鄉的差異、文化的階級還是抱有很高的熱誠去探索。我想真正會排斥的原因,最主要是自己完全沒有能力去做論述。
上課幾次後,我就不太想去了,因為我都沒有什麼感動的故事可以說,拍的東西很零散,沒有歸納出一個明顯的主題。每次前輩看到我的作品時,就搖頭或發出一個很簡單的聲音:「嗯。」
似乎搖頭或嗯對我是種不忍苛責的美德,整個暑假就這樣被搖頭搖過去了。
回到學校攝影社,由於我參加過前輩的工作坊,社團大老對我另眼相看,總覺得我將會成為交大的傳奇人物,心裡那塊心虛的程度就像戈壁沙漠一樣,無邊無際。
當初在攝影營隊裡面認識了一個朋友,人胖胖的,就讀電子物理系,嘴唇永遠呈一個S狀,一副似笑非笑的樣子,他姓于,是新竹當地人。在營隊沒多久我們很快就熟起來了,原因是他也是一個不愛唸書常為功課所困的人。他一直很喜歡我拍的照片,我從來沒有把他的喜歡當客氣,反而認為是真性情的流露。
暑假完,我把在工作坊完成的照片給于同學看,他非常睥睨地看著這些照片。
「你幹嘛去找那種鄉土攝影家學攝影?你應該走自己的路,不要再去拍那些老人小孩,那些東西讓他們去拍就好了。」他說。
頓時心裡面好像被戳了個洞一樣,整個氣一洩而光。直到後來,我不小心看到羅伯.法蘭克的《美國人》,他讓我對攝影開啟了悠悠的一扇窗,他那些晃動、失焦、灰灰濛濛的反差,跟攝影前輩所講授的內容背道而馳。我不了解《美國人》的拍攝背景,但是好像喝了一杯很濃很苦的咖啡,精神為之一振。
美國朋友(節錄)
我是很意外地申請到芝加哥藝術學院的,當初陪我去吳先生那裡買唱片的女朋友已經在美國唸書了,她告訴我這所學校還不錯,鼓勵我申請看看,申請表寄過去以後,學校給我的回函是希望我從大學二年級或三年級開始讀起,主要是因為我沒有唸過電影的課程。開玩笑!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從大學開始唸起再到研究所,五六年的時光都耗盡了。學校的態度非常強硬,似乎完全沒有轉圜之地,後來也沒辦法,死馬當活馬醫,我寫了一封信給學校。
當然這封信不是我寫的,是女友幫我捉刀的。內容大概如下:
我覺得唸電影所憑藉的應該是概念或一個創作的想法,
絕對不是根據技術能力,
我很遺憾你們學校竟然是一個這麼保守、不知變通的地方……
很意外地,學校火速寄了一封信給我,他們竟然接受我的研究所申請,但是唯一的條件,就是要求我選修一堂大學部的基礎製作課程,叫做Production One。後來我聽系主任說,我是他們系上那麼多年以來,第一個研究所學生還去修Production One 的。
很快地,我行囊收一收,並提著一個很醜的大同電鍋赴美深造。
當初離開台灣的時候,爸爸把所有藏起來、埋起來的錢全部給我了,本來想用這筆錢唸到畢業,但是在第一學期結束的時候差不多快用光了,完全不解錢怎麼會用得那麼快。
我是從春季班開始唸,秋季班開課前,我算一算所有的存款連學費都付不了,那時候只有兩個選擇,死皮賴臉地回去跟家人要錢,我想爸爸可能也會死皮賴臉地跟我說沒錢,不然就是辦休學留在芝加哥伺機而動。暑假我還繼續留在學校做片子,有一次在系辦公室無意間遇到指導老師,我把情況講給她聽,她聳聳肩膀一副愛莫能助的樣子,記得要離開時,我跟她講了一句很不要臉的話。
「過了這個暑假,你可能再也看不到我這個優秀的學生了。」
不知道是我的可憐樣刺激了她,還是她真的覺得我是優秀的學生,開學前,我突然接到教務處的通知,叫我去學校找一位教務主管,教務主管是一位和藹的女士,她循循善誘地問了我很多問題,包括學校的學習、異地生活、還有關心家裡的狀況,大概的意思就是問我唸書的錢是不是家裡供應的,我把家裡的狀況稍微往慘的方向修正了百分之三十,也把父母親靠務農教育子女的苦處講給她聽,在我那有限的英文程度裡,她默默地聽著,後來她離開辦公室,把一個文件給我,她說,我的指導老師跟她講到我的狀況,她用很快的速度在學校裡面找到一筆錢,這筆錢應該可以供我一直唸到畢業。
當時我差點連媽都喊出來了,雖然我倆年紀相差沒多少。
安東尼奧尼的電影《春光乍現》裡面,相機不再只是一個記錄的工具,原始的影像藉由暗房不斷地放大,最後成為一個模糊、抽象的影像,進而揭發了一樁謀殺案。真實到底在哪哩?是眼睛所看到的嗎?還是隱藏在內心裡一塊不自知的角落?電影的男主角是一位憤世嫉俗的攝影家,他可以偽裝成工人的身分到工廠去拍紀實的照片,然後高價賣給媒體。他也可以化身為萬人迷般的時尚攝影家,像個巨星一樣擁有無限的魅力。在一次意外中,他拍到了一張照片,經過暗房的處理,他無意間在那張照片的角落發現某種東西,這種事情也只有在底片時代才那麼具有魅力,現在數位時代,電腦直接推進放大,那種曲折的感覺一下就沒了。男主角在暗房來來回回進出,濕淋淋的照片一張張掛起來,懸疑就這樣出來了。
當然懸疑不是這部片的重點,在我看來,安東尼奧尼想藉由這部影片,從影像中的真與假來說出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失落。其中一段男主角跑到一個演唱會現場,在舞台上演出的是六零年代英國走紅的庭中鳥樂團,一位跟吉他有仇、不斷攻擊手中樂器的那位吉他手就是Jeff¬ Beck,最後吉他被摔在地上,斷成了兩截,Je¬ff Beck 把其中一截丟到舞台下面,台下所有人搶成一團,最後還是被男主角搶到手,男主角搶到這把吉他柄之後衝到戶外,冷靜下來後看到自己手上拿了半把的爛吉他,想都沒想就把它丟在街角。
擁有第一台相機時,我還沒看過安東尼奧尼的《春光乍現》,但是我相信能拿一台相機到處拍照應該是很酷的事情。
大學二年級暑假前,在台北看了一位知名攝影前輩的攝影展,那時候看到他展出巨幅照片的震撼力,看完當下久久無法忘懷。後來得知他在暑假期間開了攝影工作坊就毅然決然報名了,很快地我就投入了他的暑假課程。
每個人都拍攝自己設定的主題,有些人拍天橋下的魔術師,有些人拍隔壁的老太太,他們不是只去拍個一天兩天,而是持續不斷地天天拍,不斷地追蹤拍攝。我一直不是很了解這些東西,心裡覺得他們記錄的那些不就是我們鄉下叔叔伯伯們的爛故事嗎?生活的貧困,工作或家庭的不美滿,不就是我從小看著長大的那些鳥事?但是在我的同學跟前輩的對談裡面,好像每一篇都是感人肺腑的故事,也許就是在那時候,內心生起對這些感人故事的排斥。可能是自己的想法太偏頗了,事情不全都是這樣子,很多人對城鄉的差異、文化的階級還是抱有很高的熱誠去探索。我想真正會排斥的原因,最主要是自己完全沒有能力去做論述。
上課幾次後,我就不太想去了,因為我都沒有什麼感動的故事可以說,拍的東西很零散,沒有歸納出一個明顯的主題。每次前輩看到我的作品時,就搖頭或發出一個很簡單的聲音:「嗯。」
似乎搖頭或嗯對我是種不忍苛責的美德,整個暑假就這樣被搖頭搖過去了。
回到學校攝影社,由於我參加過前輩的工作坊,社團大老對我另眼相看,總覺得我將會成為交大的傳奇人物,心裡那塊心虛的程度就像戈壁沙漠一樣,無邊無際。
當初在攝影營隊裡面認識了一個朋友,人胖胖的,就讀電子物理系,嘴唇永遠呈一個S狀,一副似笑非笑的樣子,他姓于,是新竹當地人。在營隊沒多久我們很快就熟起來了,原因是他也是一個不愛唸書常為功課所困的人。他一直很喜歡我拍的照片,我從來沒有把他的喜歡當客氣,反而認為是真性情的流露。
暑假完,我把在工作坊完成的照片給于同學看,他非常睥睨地看著這些照片。
「你幹嘛去找那種鄉土攝影家學攝影?你應該走自己的路,不要再去拍那些老人小孩,那些東西讓他們去拍就好了。」他說。
頓時心裡面好像被戳了個洞一樣,整個氣一洩而光。直到後來,我不小心看到羅伯.法蘭克的《美國人》,他讓我對攝影開啟了悠悠的一扇窗,他那些晃動、失焦、灰灰濛濛的反差,跟攝影前輩所講授的內容背道而馳。我不了解《美國人》的拍攝背景,但是好像喝了一杯很濃很苦的咖啡,精神為之一振。
美國朋友(節錄)
我是很意外地申請到芝加哥藝術學院的,當初陪我去吳先生那裡買唱片的女朋友已經在美國唸書了,她告訴我這所學校還不錯,鼓勵我申請看看,申請表寄過去以後,學校給我的回函是希望我從大學二年級或三年級開始讀起,主要是因為我沒有唸過電影的課程。開玩笑!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從大學開始唸起再到研究所,五六年的時光都耗盡了。學校的態度非常強硬,似乎完全沒有轉圜之地,後來也沒辦法,死馬當活馬醫,我寫了一封信給學校。
當然這封信不是我寫的,是女友幫我捉刀的。內容大概如下:
我覺得唸電影所憑藉的應該是概念或一個創作的想法,
絕對不是根據技術能力,
我很遺憾你們學校竟然是一個這麼保守、不知變通的地方……
很意外地,學校火速寄了一封信給我,他們竟然接受我的研究所申請,但是唯一的條件,就是要求我選修一堂大學部的基礎製作課程,叫做Production One。後來我聽系主任說,我是他們系上那麼多年以來,第一個研究所學生還去修Production One 的。
很快地,我行囊收一收,並提著一個很醜的大同電鍋赴美深造。
當初離開台灣的時候,爸爸把所有藏起來、埋起來的錢全部給我了,本來想用這筆錢唸到畢業,但是在第一學期結束的時候差不多快用光了,完全不解錢怎麼會用得那麼快。
我是從春季班開始唸,秋季班開課前,我算一算所有的存款連學費都付不了,那時候只有兩個選擇,死皮賴臉地回去跟家人要錢,我想爸爸可能也會死皮賴臉地跟我說沒錢,不然就是辦休學留在芝加哥伺機而動。暑假我還繼續留在學校做片子,有一次在系辦公室無意間遇到指導老師,我把情況講給她聽,她聳聳肩膀一副愛莫能助的樣子,記得要離開時,我跟她講了一句很不要臉的話。
「過了這個暑假,你可能再也看不到我這個優秀的學生了。」
不知道是我的可憐樣刺激了她,還是她真的覺得我是優秀的學生,開學前,我突然接到教務處的通知,叫我去學校找一位教務主管,教務主管是一位和藹的女士,她循循善誘地問了我很多問題,包括學校的學習、異地生活、還有關心家裡的狀況,大概的意思就是問我唸書的錢是不是家裡供應的,我把家裡的狀況稍微往慘的方向修正了百分之三十,也把父母親靠務農教育子女的苦處講給她聽,在我那有限的英文程度裡,她默默地聽著,後來她離開辦公室,把一個文件給我,她說,我的指導老師跟她講到我的狀況,她用很快的速度在學校裡面找到一筆錢,這筆錢應該可以供我一直唸到畢業。
當時我差點連媽都喊出來了,雖然我倆年紀相差沒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