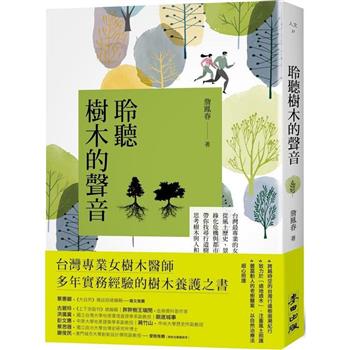台灣行道樹新典範
日治初期推動的行道樹計畫,在後期於各方面也面臨許多課題。尤其,面對養護管理卻顯示了專業認知度的不足。有鑒於此,田代氏又以革新為前提,提出行道樹改革方針。如劃分管理職權並設置行道樹主任掌管事務,訂立植栽技術、設計單位、導入外來行道樹文明特質等。植栽技術方面,提出樹種選擇及植栽距離之設計,並要求主管單位須具備行道樹及園藝相關分野的知識,以便於執行。對於歐美行道樹規畫導入,透過一種比較的方式,說明台灣行道樹事業的必要及設計方向性。如外來行道樹思想,說明各國行道樹植栽的技術特色,分為東洋、印度南洋、西洋類型。根據這三個不同環境所歸納出行道樹的特質,除了美化景觀也在空間上展現近代文明。同時也指出台灣屬亞熱帶氣候環境,參考南洋熱帶地區樹種,推廣行道樹為刻不容緩的事業。因此在計畫行道樹植栽同時,對於樹種選取更同時考量風土氣候,並透過近代科學技術來經營管理。
田代氏自鹿兒島再度回到台灣總督府殖產局任職時,提出台南鳳凰新道的行道樹規畫看法。台南為台灣最具歷史的都市,受到過去荷蘭等權力支配,行道樹僅於台南官田一帶展開。之後因市區改正展開道路計畫,接著台南廳舍的落成,並開通大道種植鳳凰木。鳳凰新道寬約二十公尺,全長約八百公尺,以單一樹種共一百五十三棵,植栽距離以每九公尺栽種一棵樹;平均樹齡以三年生、樹高約二、三公尺列植。田代認為植栽樣式為統治以來革新的作法,猶如歐美近代行道樹植栽樣式,可以說是台灣行道樹的新典範。
歐美外來行道樹思想
西歐行道樹的出現,早在十六世紀就出現於圓環。因戰亂導致許多圓環相繼毀壞,因此將圓環重新建設,擴大為三線的道路並種植行道樹,儼然成為市民休憩之場所。
法國
法國自十六世紀中期,國王亨利二世下令於國道種植歐洲榆樹。十七世紀以後,開始於塞納河周邊展開植樹計畫,號稱世界最美的街道景觀。除了法國,德國道路及行道樹規畫也毫不遜色。二十世紀初期,歐美各國開始採用石塊鋪裝道路,而德國柏林早已發展為柏油並在主要道路上種植行道樹。反觀英國,倫敦於十七世紀開始規畫散步道路,採用英桐大喬木配植以四列,成為著名的行道樹。此外國土處於低濕地的荷蘭,自古以來也採用榆樹、光蠟樹等作為行道樹。綜觀西歐自十六世紀開始,陸續展開行道樹規畫;首次出現以法令推動為十八世紀以後的法國,可以說為當時最先進計畫。
歐洲自十八世紀中期以後,工業化發展導致都市人口暴增、生活環境惡劣且擁擠不堪。隨著都市持續的發展,中古世紀的都市格局也早已不敷使用。因此各國相繼為都市的成長、改革提出解決方案。其中以法國塞納省省長奧斯曼的「巴黎大改造」最為成功,使巴黎的都市面貌煥然一新。巴黎自十二世紀開始人口不斷增加,十三世紀時人口已達二十萬。十九世紀後,面對百萬人口的擴展,城市街道路繁亂,而不得不採取撤廢城牆。大規模的拆毀以十九世紀中期所推動的「巴黎大改造」最為盛大。當時拿破崙三世為了誇示帝政,藉由舉行巴黎博覽會以提升國際競爭力,於是任命縣長奧斯曼負責博覽會,同時推動巴黎大改造。奧斯曼被任命為省長,重新規畫了巴黎的道路系統,拆毀了狹窄迂迴的市中心,進行了徹底的空間改造並塑造巴黎的都市性格。之後也委任造園技師阿爾方擔當巴黎綠地系統及行道樹整備局長。阿爾方因具備理工及土木背景,運用科學及技術於造園分野,使巴黎的林蔭大道成為後來世界各大都市競相模仿的楷模。
林蔭大道對於法國來說並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而把造園設計元素應用於都市計畫卻實為創新。巴黎的行道樹種植規範原則;第一必須篩選適合樹種,第二取適當植樹間隔的配植,第三熟知種植方法,第四專業養護管理。針對樹種的選擇還須具備八項條件,第一需強健,耐環境。第二樹幹直立,第三耐病蟲害,第四枝葉量適當,第五清潔不具惡臭,第六生長快速,第七壽命長,第八根系強健。阿爾方的規畫設計是利用綠蔭樹,將步車道分離。同時訂立行道樹保全、土壤環境、樹間距離以及設置苗圃栽培。因考慮巴黎行道樹保護問題,樹間距離以六至七公尺為距、植樹帶寬三公尺、長八公尺及土壤深度三.五公尺並配合排水溝設置。樹種以生長迅速、提供樹蔭且易於適應環境,同時配合樹穴蓋、支柱等避免風害及折損。此外,還啟動專門技術部門以管理行道樹。巴黎改造計畫至十九世紀末,行道樹數量高達十萬棵,規模浩大。著名的香榭大道,種植以歐洲七葉樹,之後部分改植以懸鈴木、槐樹等,整體行道樹規畫也帶給歐美各國很大影響。甚至十九世紀中期,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環城大道也導入椴樹、歐洲七葉樹、歐洲楓及岩槭等成為一種風潮。巴黎改造的成果,深深影響了遠在東方的日本。日本派遣使節團於一八七二年秋天到達巴黎,停留約兩個月之久。使節團歸國後,對於巴黎的都市公園及行道樹進行如此描述:「香榭大道直通凱旋門,寬廣大道種植四列行道樹,街道綠蔭盎然,深感壯觀與華麗。行道樹及廣場不僅提供休憩設施,也改善都市整體衛生環境。行道樹規畫如同網路覆蓋整體都市,公園與道路結為一體」。對於巴黎都市景觀的描述,也讓使節團的海外視察,受到強大的震撼與衝擊。因此在歸國後,隨即展開近代化的建設,導入西歐的都市計畫思想。連之後擔任台灣總督府技師的田代安定,也曾造訪法國並一睹巴黎行道樹光景。
德國
德國緊跟在法國之後,也開始展開行道樹的植栽計畫。十八世紀中期,德國萊比錫因七年戰爭(一七五四—一七六三)後,認為城牆防禦失去作用而計畫擺脫圍牆城市。在戰後著手拆毀東北要塞,並改建以圍繞市中心的綠色長廊,陸續規畫都市綠地以遊步道取代十六世紀的城牆遺跡。市長穆拉極力推動都市公園與行道樹植栽,並委請擔任市政廳城市園林管理部門的卡爾設計散步道,以此構成市區綠帶長廊的基本架構。十九世紀後,隨著都市發展以景觀為目的,行道樹的計畫又更為積極,並擴大散步道栽植華東椴及梧桐為綠帶長廊的典範。
美國
美國自十九世紀中期,以寬廣公園道結合公園綠地系統;著名代表如波士頓、堪薩斯州等展開的街路計畫。當時行道樹的設計,主要分為種植於兩側以及中央綠島。依據樹種規畫植栽帶寬度,而種植於中央綠島稱為公園道類型,也就是連結公園與公園的大道。如紐約布魯克林區,規畫東公園道以連結公園,設置寬約七十八公尺、中央為快速道約二十公尺,兩旁種植以六列榆樹,而靠近建物的人行步道寬約九公尺植一列行道樹。美國公園道路的展開為公園綠地系統的概念,而公園道一詞,來自於歐洲林蔭大道的轉換用語,構想出自於連結公園以誘導都市開發。進入二十世紀後,因道路美化運動而發布法令,明訂道路沿線種植樹木確保綠蔭為農務大臣及道路管理權責,行道樹保護也列為規範。當時密西根州推動道路計畫,規定必須僱用森林技師或風景技師提供植樹依據,陸續完成七萬株行道樹的規畫。其他地區,如紐約也以每年一萬棵的速度計畫植栽,採用榆樹、糖楓等高大喬木樹種。
公園道路導入
公園道路在二十世紀城市美化運動的推動之下,蔚為風潮。遠在亞洲的日本,也導入於「新東京計畫」。時任東京市長的後藤新平,配合都市計畫法而立案,是定位綠地系統的都市計畫。然而,戰後卻因考慮市區的經濟效益,東京內部的公園道路計畫遭到廢除。
在台灣,受到殖民政府的影響,陸續導入近代行道樹思想。特別是統治初期,將城壁跡地規畫為三線道路,並在各節點設置綠地圓環,以此為起點作為放射狀道路延伸至郊區。當時總督府計畫將三線道路導入法國香榭大道概念,但參考德國萊比錫之環城形勢,將來長遠之計畫為設置電車路線。因此採用萊比錫之散步道概念落實於三線道路。
之後在市區改正期計畫當中,說明以台北府城環之遺地作為計畫環狀公園,以中央為車道、兩側為步道,道路上設置三、四公尺寬的兩列綠樹帶,三線道路儼然成為台北林蔭大道象徵之一。然而隨著人口增加,台北地區人口已漸飽和,為了因應社會變化趨勢,殖民政府再度發布大台北市區計畫及都市計畫,並將防災思想導入公園道路安排。規畫公園道四條,寬度以六十至一百公尺作為公園道路連結公園綠地。因戰爭之迫近,僅完成公園道四號,寬四十公尺,並種植兩列的行道樹及特一號道路。其餘在戰後陸續建設及變更路線。
統治後期,深感人口增加與都市的擴大,殖民政府亟欲推動都市計畫。基於交通、休憩、都市美化及防災機能,將公園道與區域內的公園連結,說明公園道路設計為公園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公園道路不同於一般行道樹列於道路兩側,而是道路公園化。也就是將樹木配置於中央綠島與車道、步道相並行。公園道路的推動,持續擴大到地方都市如台中、台南、高雄等地區。因戰爭的爆發,無暇推動都市建設而無疾而終。儘管如此,公園道計畫於戰後也帶來很大的影響。戰後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後,高玉樹為首任市長。任期內,從事許多重大市政建設而公園道也為當中之一。為了建設台北市成為一個國際都會,將敦化南北路道路拓寬成七十公尺,其中仁愛路三段更達到一百公尺寬。高玉樹市長為建構近代林蔭大道,委託顏水龍教授擔任市政顧問規畫仁愛路、敦化北路等林蔭大道。顏水龍因過去留法期間,曾受巴黎香榭大道影響並將美術理念擴展至都市設計,落實南北貫穿大道與公園道路第四號相接,形成為L形的林蔭大道。之後高玉樹的回憶錄中也提到,仁愛路與巴黎的凱旋門圓環類比的說法,這也說明台北市的林蔭大道也有一段「巴黎化」的過程。
行道樹的轉變
戰後滿目瘡痍,政府著手推動復興建設計畫。都市行道樹依舊傳承過去行道樹種,相較於日治時期,外來樹種明顯減少。
日治初期的中山北路(敕使街道)於戰後,成為台北市最完善道路。道路寬度約四十公尺,綠島保留二.五公尺種植成列的樟樹;人行道上種植楓香。三線道路也承續日治時期的規畫,如愛國西路(南三線),左右綠島種植茄苳、金龜樹、榕樹、黃槐樹等,之後全線拓寬植以茄苳為台北市第一條標準之園林大道。中山南路(東三線)綠島種植以大王椰子為主,人行道上有榕樹、茄苳、白千層、楓樹、樟樹等樹種。戰後成為主要商場區域的中華路(西三線),人行道植榕樹、蒲葵,後換植以楓香樹種為主。而著名的交通要道,忠孝西路(北三線)隨著交通量增加,將日治時期北三線的之綠島拆除,改為六線快速道路。其他如公園道四號(仁愛路)也於戰後擴寬,遍植綠樹如樟樹、大葉桉、大王椰子、榕樹、菩提樹、白千層、木棉等近三千棵樹為台北林蔭大道之示範道路之一。另一方面,日治時期通往台北飛行場並無寬廣大道,戰後隨即成立台北航空站並著手開闢敦化路。因考慮國際要道,進而拓寬為七十公尺園林大道,於寬廣的綠地種植樟樹,而人行道植以榕樹、菩提樹、樟樹等。戰後,台北新闢的園林大道是採用樟樹、榕樹及台灣欒樹為主,不同於日治時期的椰科、豆科樹種。地方的行道樹也普遍種植以樟樹,其次為台灣欒樹、山櫻花、小葉欖仁、水黃皮等。戰後種植樟樹蔚為風潮,八 年代以後也開始廣泛種植黑板樹、小葉南洋杉等樹種。過去以來,行道樹選擇以生長迅速及耐修剪的樹種為主。因都市美化思潮,也考慮以觀賞花果或樹姿特質,同時能提供綠蔭效果及養護容易的樹種。
在日治時期,行道樹規畫主要以防災機能為出發點,戰後轉變為都市環境美化原則。而近年來,道路綠化以植栽設計、樹種選擇及維護管理等為基本原則,也開始關心生態機能的效果。面對當前都市熱島效應,行道樹的規畫不僅在於環境美化上,植栽的機能以及都市生態保育也賦予行道樹的公益機能。因此,隨著自然保育或環境保護意識日漸高漲的今日,除了適地適性的栽植外,後續的維護管理更是確保道路綠化系統之完整與永續性。
日治初期推動的行道樹計畫,在後期於各方面也面臨許多課題。尤其,面對養護管理卻顯示了專業認知度的不足。有鑒於此,田代氏又以革新為前提,提出行道樹改革方針。如劃分管理職權並設置行道樹主任掌管事務,訂立植栽技術、設計單位、導入外來行道樹文明特質等。植栽技術方面,提出樹種選擇及植栽距離之設計,並要求主管單位須具備行道樹及園藝相關分野的知識,以便於執行。對於歐美行道樹規畫導入,透過一種比較的方式,說明台灣行道樹事業的必要及設計方向性。如外來行道樹思想,說明各國行道樹植栽的技術特色,分為東洋、印度南洋、西洋類型。根據這三個不同環境所歸納出行道樹的特質,除了美化景觀也在空間上展現近代文明。同時也指出台灣屬亞熱帶氣候環境,參考南洋熱帶地區樹種,推廣行道樹為刻不容緩的事業。因此在計畫行道樹植栽同時,對於樹種選取更同時考量風土氣候,並透過近代科學技術來經營管理。
田代氏自鹿兒島再度回到台灣總督府殖產局任職時,提出台南鳳凰新道的行道樹規畫看法。台南為台灣最具歷史的都市,受到過去荷蘭等權力支配,行道樹僅於台南官田一帶展開。之後因市區改正展開道路計畫,接著台南廳舍的落成,並開通大道種植鳳凰木。鳳凰新道寬約二十公尺,全長約八百公尺,以單一樹種共一百五十三棵,植栽距離以每九公尺栽種一棵樹;平均樹齡以三年生、樹高約二、三公尺列植。田代認為植栽樣式為統治以來革新的作法,猶如歐美近代行道樹植栽樣式,可以說是台灣行道樹的新典範。
歐美外來行道樹思想
西歐行道樹的出現,早在十六世紀就出現於圓環。因戰亂導致許多圓環相繼毀壞,因此將圓環重新建設,擴大為三線的道路並種植行道樹,儼然成為市民休憩之場所。
法國
法國自十六世紀中期,國王亨利二世下令於國道種植歐洲榆樹。十七世紀以後,開始於塞納河周邊展開植樹計畫,號稱世界最美的街道景觀。除了法國,德國道路及行道樹規畫也毫不遜色。二十世紀初期,歐美各國開始採用石塊鋪裝道路,而德國柏林早已發展為柏油並在主要道路上種植行道樹。反觀英國,倫敦於十七世紀開始規畫散步道路,採用英桐大喬木配植以四列,成為著名的行道樹。此外國土處於低濕地的荷蘭,自古以來也採用榆樹、光蠟樹等作為行道樹。綜觀西歐自十六世紀開始,陸續展開行道樹規畫;首次出現以法令推動為十八世紀以後的法國,可以說為當時最先進計畫。
歐洲自十八世紀中期以後,工業化發展導致都市人口暴增、生活環境惡劣且擁擠不堪。隨著都市持續的發展,中古世紀的都市格局也早已不敷使用。因此各國相繼為都市的成長、改革提出解決方案。其中以法國塞納省省長奧斯曼的「巴黎大改造」最為成功,使巴黎的都市面貌煥然一新。巴黎自十二世紀開始人口不斷增加,十三世紀時人口已達二十萬。十九世紀後,面對百萬人口的擴展,城市街道路繁亂,而不得不採取撤廢城牆。大規模的拆毀以十九世紀中期所推動的「巴黎大改造」最為盛大。當時拿破崙三世為了誇示帝政,藉由舉行巴黎博覽會以提升國際競爭力,於是任命縣長奧斯曼負責博覽會,同時推動巴黎大改造。奧斯曼被任命為省長,重新規畫了巴黎的道路系統,拆毀了狹窄迂迴的市中心,進行了徹底的空間改造並塑造巴黎的都市性格。之後也委任造園技師阿爾方擔當巴黎綠地系統及行道樹整備局長。阿爾方因具備理工及土木背景,運用科學及技術於造園分野,使巴黎的林蔭大道成為後來世界各大都市競相模仿的楷模。
林蔭大道對於法國來說並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而把造園設計元素應用於都市計畫卻實為創新。巴黎的行道樹種植規範原則;第一必須篩選適合樹種,第二取適當植樹間隔的配植,第三熟知種植方法,第四專業養護管理。針對樹種的選擇還須具備八項條件,第一需強健,耐環境。第二樹幹直立,第三耐病蟲害,第四枝葉量適當,第五清潔不具惡臭,第六生長快速,第七壽命長,第八根系強健。阿爾方的規畫設計是利用綠蔭樹,將步車道分離。同時訂立行道樹保全、土壤環境、樹間距離以及設置苗圃栽培。因考慮巴黎行道樹保護問題,樹間距離以六至七公尺為距、植樹帶寬三公尺、長八公尺及土壤深度三.五公尺並配合排水溝設置。樹種以生長迅速、提供樹蔭且易於適應環境,同時配合樹穴蓋、支柱等避免風害及折損。此外,還啟動專門技術部門以管理行道樹。巴黎改造計畫至十九世紀末,行道樹數量高達十萬棵,規模浩大。著名的香榭大道,種植以歐洲七葉樹,之後部分改植以懸鈴木、槐樹等,整體行道樹規畫也帶給歐美各國很大影響。甚至十九世紀中期,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環城大道也導入椴樹、歐洲七葉樹、歐洲楓及岩槭等成為一種風潮。巴黎改造的成果,深深影響了遠在東方的日本。日本派遣使節團於一八七二年秋天到達巴黎,停留約兩個月之久。使節團歸國後,對於巴黎的都市公園及行道樹進行如此描述:「香榭大道直通凱旋門,寬廣大道種植四列行道樹,街道綠蔭盎然,深感壯觀與華麗。行道樹及廣場不僅提供休憩設施,也改善都市整體衛生環境。行道樹規畫如同網路覆蓋整體都市,公園與道路結為一體」。對於巴黎都市景觀的描述,也讓使節團的海外視察,受到強大的震撼與衝擊。因此在歸國後,隨即展開近代化的建設,導入西歐的都市計畫思想。連之後擔任台灣總督府技師的田代安定,也曾造訪法國並一睹巴黎行道樹光景。
德國
德國緊跟在法國之後,也開始展開行道樹的植栽計畫。十八世紀中期,德國萊比錫因七年戰爭(一七五四—一七六三)後,認為城牆防禦失去作用而計畫擺脫圍牆城市。在戰後著手拆毀東北要塞,並改建以圍繞市中心的綠色長廊,陸續規畫都市綠地以遊步道取代十六世紀的城牆遺跡。市長穆拉極力推動都市公園與行道樹植栽,並委請擔任市政廳城市園林管理部門的卡爾設計散步道,以此構成市區綠帶長廊的基本架構。十九世紀後,隨著都市發展以景觀為目的,行道樹的計畫又更為積極,並擴大散步道栽植華東椴及梧桐為綠帶長廊的典範。
美國
美國自十九世紀中期,以寬廣公園道結合公園綠地系統;著名代表如波士頓、堪薩斯州等展開的街路計畫。當時行道樹的設計,主要分為種植於兩側以及中央綠島。依據樹種規畫植栽帶寬度,而種植於中央綠島稱為公園道類型,也就是連結公園與公園的大道。如紐約布魯克林區,規畫東公園道以連結公園,設置寬約七十八公尺、中央為快速道約二十公尺,兩旁種植以六列榆樹,而靠近建物的人行步道寬約九公尺植一列行道樹。美國公園道路的展開為公園綠地系統的概念,而公園道一詞,來自於歐洲林蔭大道的轉換用語,構想出自於連結公園以誘導都市開發。進入二十世紀後,因道路美化運動而發布法令,明訂道路沿線種植樹木確保綠蔭為農務大臣及道路管理權責,行道樹保護也列為規範。當時密西根州推動道路計畫,規定必須僱用森林技師或風景技師提供植樹依據,陸續完成七萬株行道樹的規畫。其他地區,如紐約也以每年一萬棵的速度計畫植栽,採用榆樹、糖楓等高大喬木樹種。
公園道路導入
公園道路在二十世紀城市美化運動的推動之下,蔚為風潮。遠在亞洲的日本,也導入於「新東京計畫」。時任東京市長的後藤新平,配合都市計畫法而立案,是定位綠地系統的都市計畫。然而,戰後卻因考慮市區的經濟效益,東京內部的公園道路計畫遭到廢除。
在台灣,受到殖民政府的影響,陸續導入近代行道樹思想。特別是統治初期,將城壁跡地規畫為三線道路,並在各節點設置綠地圓環,以此為起點作為放射狀道路延伸至郊區。當時總督府計畫將三線道路導入法國香榭大道概念,但參考德國萊比錫之環城形勢,將來長遠之計畫為設置電車路線。因此採用萊比錫之散步道概念落實於三線道路。
之後在市區改正期計畫當中,說明以台北府城環之遺地作為計畫環狀公園,以中央為車道、兩側為步道,道路上設置三、四公尺寬的兩列綠樹帶,三線道路儼然成為台北林蔭大道象徵之一。然而隨著人口增加,台北地區人口已漸飽和,為了因應社會變化趨勢,殖民政府再度發布大台北市區計畫及都市計畫,並將防災思想導入公園道路安排。規畫公園道四條,寬度以六十至一百公尺作為公園道路連結公園綠地。因戰爭之迫近,僅完成公園道四號,寬四十公尺,並種植兩列的行道樹及特一號道路。其餘在戰後陸續建設及變更路線。
統治後期,深感人口增加與都市的擴大,殖民政府亟欲推動都市計畫。基於交通、休憩、都市美化及防災機能,將公園道與區域內的公園連結,說明公園道路設計為公園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公園道路不同於一般行道樹列於道路兩側,而是道路公園化。也就是將樹木配置於中央綠島與車道、步道相並行。公園道路的推動,持續擴大到地方都市如台中、台南、高雄等地區。因戰爭的爆發,無暇推動都市建設而無疾而終。儘管如此,公園道計畫於戰後也帶來很大的影響。戰後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後,高玉樹為首任市長。任期內,從事許多重大市政建設而公園道也為當中之一。為了建設台北市成為一個國際都會,將敦化南北路道路拓寬成七十公尺,其中仁愛路三段更達到一百公尺寬。高玉樹市長為建構近代林蔭大道,委託顏水龍教授擔任市政顧問規畫仁愛路、敦化北路等林蔭大道。顏水龍因過去留法期間,曾受巴黎香榭大道影響並將美術理念擴展至都市設計,落實南北貫穿大道與公園道路第四號相接,形成為L形的林蔭大道。之後高玉樹的回憶錄中也提到,仁愛路與巴黎的凱旋門圓環類比的說法,這也說明台北市的林蔭大道也有一段「巴黎化」的過程。
行道樹的轉變
戰後滿目瘡痍,政府著手推動復興建設計畫。都市行道樹依舊傳承過去行道樹種,相較於日治時期,外來樹種明顯減少。
日治初期的中山北路(敕使街道)於戰後,成為台北市最完善道路。道路寬度約四十公尺,綠島保留二.五公尺種植成列的樟樹;人行道上種植楓香。三線道路也承續日治時期的規畫,如愛國西路(南三線),左右綠島種植茄苳、金龜樹、榕樹、黃槐樹等,之後全線拓寬植以茄苳為台北市第一條標準之園林大道。中山南路(東三線)綠島種植以大王椰子為主,人行道上有榕樹、茄苳、白千層、楓樹、樟樹等樹種。戰後成為主要商場區域的中華路(西三線),人行道植榕樹、蒲葵,後換植以楓香樹種為主。而著名的交通要道,忠孝西路(北三線)隨著交通量增加,將日治時期北三線的之綠島拆除,改為六線快速道路。其他如公園道四號(仁愛路)也於戰後擴寬,遍植綠樹如樟樹、大葉桉、大王椰子、榕樹、菩提樹、白千層、木棉等近三千棵樹為台北林蔭大道之示範道路之一。另一方面,日治時期通往台北飛行場並無寬廣大道,戰後隨即成立台北航空站並著手開闢敦化路。因考慮國際要道,進而拓寬為七十公尺園林大道,於寬廣的綠地種植樟樹,而人行道植以榕樹、菩提樹、樟樹等。戰後,台北新闢的園林大道是採用樟樹、榕樹及台灣欒樹為主,不同於日治時期的椰科、豆科樹種。地方的行道樹也普遍種植以樟樹,其次為台灣欒樹、山櫻花、小葉欖仁、水黃皮等。戰後種植樟樹蔚為風潮,八 年代以後也開始廣泛種植黑板樹、小葉南洋杉等樹種。過去以來,行道樹選擇以生長迅速及耐修剪的樹種為主。因都市美化思潮,也考慮以觀賞花果或樹姿特質,同時能提供綠蔭效果及養護容易的樹種。
在日治時期,行道樹規畫主要以防災機能為出發點,戰後轉變為都市環境美化原則。而近年來,道路綠化以植栽設計、樹種選擇及維護管理等為基本原則,也開始關心生態機能的效果。面對當前都市熱島效應,行道樹的規畫不僅在於環境美化上,植栽的機能以及都市生態保育也賦予行道樹的公益機能。因此,隨著自然保育或環境保護意識日漸高漲的今日,除了適地適性的栽植外,後續的維護管理更是確保道路綠化系統之完整與永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