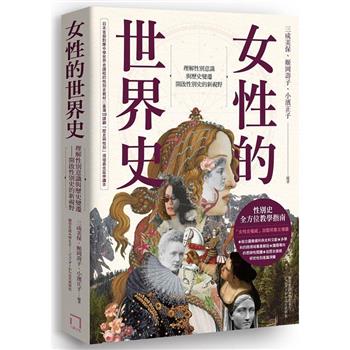〈女性與近代歐洲〉
◎8-1,概論⑧歐洲的擴張、危機與性別◎
◆從擴張走向危機
歐洲近代早期(近世)的變化走向為:「擴張」(16世紀)→「危機」(17世紀)→「成長」(18世紀)。而歐洲的「擴張」其實是透過侵略(屠殺)、殖民、通商、傳教、探險等各種方式推進,其與異文化的接觸更促進了人權思想之形成。只是就像洛克的「社會契約論」是以家父長制作為契約主體,而此時的女性並未被納入其中。接下來的「17世紀的危機」,同時也是「科學革命」的時代。由於當時進入小冰河期,氣候變得寒冷,導致瘟疫蔓延、遍地歉收、人口停滯成長。加上接連發生戰爭,人們飽受重稅所苦,因此常常發生動亂、農民暴動,甚至達到女巫審判的高峰期。在動亂中尋求人類理性的自然法則理念來取代神之所在,以及相信人類可以透過發展科學技術來控制自然,這兩件事可說互為表裡關係。最後,其實在歌頌人性的文藝復興時期,在藝術、科學領域均有許多活躍的女性,可惜大多都已被遺忘了。
◆政治與女性
歐洲近代早期女性參與政治的程度,因其身分、地區有所不同。越是自治性格強烈的共和制度都市、國家,在政治上越排斥女性(瑞士各州、德意志帝國都市等)。反之,在權力倚賴血統繼承,非以選舉、提名決定的王國,女性反而能夠登上王位。尤其在絕對專制王政下,只要朝廷越講求要由直系繼承王位,誕生女王的機會就越高。如英格蘭、蘇格蘭、西班牙、瑞典,皆在沒有直系男子繼承時改由女王即位(18世紀的俄國、奧地利亦同)。雖然法國依據14世紀的古老部族法典《薩利克法》,向來把女性排除在王位繼承者之外,但王太后(攝政)、王后、情婦等女性都有一定的政治發言權。
不管在哪一個宮廷,女性的角色都很重要,她們都可參與政治對話。然而參加政治的女性往往會讓男性知識分子心生警戒,所以女王、攝政太后總是費盡心思打造自己的形象。像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位期間1558~1603年)就扮演與聖母瑪麗亞形象重合的「童貞女王」,成功地塑造了自身形象;反之,積極仿效古代羅馬女神、扮演「母親」形象的攝政太后凱薩琳.德.麥地奇(Catherine de Medici,1519~1589年,左頁圖)卻被指控成一個堪比「暴政贊助者」的女巫,讓她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功績都被這個惡名給掩蓋了。
◆「家」
「家」是近代早期歐洲生活秩序的中心。無論生活、勞動、居住,都跟「家」連成一體。農民、公民的「家」會被納入城市或村落之共同體。家父長為共同體的正式成員,權利受到保障,對外可代表「家」、管理「家」的財產。「家」的成員包含家父長、家母、孩子、雇工(工匠、學徒)、親戚等同居人和退休老人,家父長對成員持有懲戒權力。「家」的規模不算很大,原因在於他們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平均壽命很低、常因無力抵抗瘟疫而死去,或者習慣把孩子送去別人家學習。此外,沒有繼承農地、沒有取得店主資格的人都不能結婚,因此初婚年齡頗高,單身男女很多。到了18世紀末,有一些雇工開始從「家」獨立出來,形成了近代的家族。
◎8-3,文藝復興藝術與女性──繪畫中的女性形象與女畫家◎
◆繪畫中的女性形象
在以義大利佛羅倫斯為中心、於15世紀時開花結果的文藝復興(指古典文化的新生)之中,人們重新採用了過去被中世紀基督教文化當成異教而忽略的古希臘羅馬神話,做為藝術的主題。其中愛與美的女神「維納斯」(此為羅馬神話之名,希臘神話中稱作「阿芙蘿黛蒂」[Aphrodite])更從視肉體為罪惡的基督教桎梏中解放出來,轉變成一個表現女性理想身體之美的主題形象。儘管維納斯繪畫表面上是在展現精神方面「天上之愛」的寓意,實際上卻帶有世俗肉身的裸體性感,正是現實女性的肖像。
◆畫家與贊助者
文藝復興文化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很大部分是有賴於那些靠工商業或金融業致富的城市貴族、同業公會、或教會的藝術贊助者(patron)。一般來說,相對於上流階層的贊助者(買家),畫家屬於收取訂製酬金來維持生計的工匠階層,因此當時藝術作品大幅反映了買家的興趣和意向。許多像維納斯之類的女性肖像都是由男性贊助者訂購、再由男性畫家繪製的。不過近年來保護藝術、訂購作品的女性贊助者漸漸浮上檯面,女性亦可扮演決定文化愛好的角色。
◆女性畫家
假如想成為一名職業畫家,首先得加入工作室,在師傅旗下累積學習經驗,等到可以獨當一面之後再加入同業公會──然則女性幾乎都沒有那些機會,除非她的父親就是畫家:例如義大利的阿特米西亞.真蒂萊希(Artemisia Gentileschi)一開始先在父親的工作室學習,而後留下一些以神話、聖經為題材的戲劇性繪畫傑作。其他還有繪製國王肖像的義大利畫家蘇菲妮絲貝.安古索拉(Sofonisba Anguissola,約1532~1625年)、以及擅長風俗畫的茱蒂絲.萊斯特(Judith Leyster,1609~1660年),只是她們長久以來皆被藝術史遺忘。在藝術以外,還有文藝復興前期的作家克莉絲汀.德.皮桑(約1365~1430年),她出身於威尼斯、主要在法國宮廷活動,以詩作、散文貫徹擁護女性的立場。她的作品《婦女城》便描寫了一個由女性美德治理的烏托邦。上述例子顯示,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文章中確實存在著「表現自我的女性」。
圖❶波提且利(Sandro Botticelli)《維納斯的誕生》(The Birth of Venus,約1485年)
這幅文藝復興時期最早的等身大全裸維納斯像,相傳是與佛羅倫斯梅迪西家族關係深厚的畫家波提且利,其受託繪製用來慶祝該家族婚禮的作品。畫中所繪愛與豐收的女神,不僅是象徵吉祥之兆的圖像,同時也保留了真實女性的身影。而模仿古希臘雕刻把雙手放在前面遮掩的「害羞維納斯」姿勢、與「橫臥維納斯」兩者均是裸女畫像的標準定型。
圖❷「我是藝術(家)」──阿特米西亞・真蒂萊希(1593~約1653年)的自畫像
阿特米西亞出生於羅馬,為畫家奧拉奇歐.真蒂萊希(Orazio Gentileschi)之女,她曾擔任父親助手參與工作室的製作,亦曾於1612年因為遭到師事的畫家強暴而站上審判法庭,最終她戰勝了那些痛苦經驗,躋身一流畫家,如今可在歐洲的美術館看到不少阿特米西亞畫作。從她把自己化為藝術擬人像的作品《自畫像做為繪畫藝術之寓言》(Self-Portrait as the Allegory of Painting,1630年代)上,就能看出她以畫家身分生活的強烈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