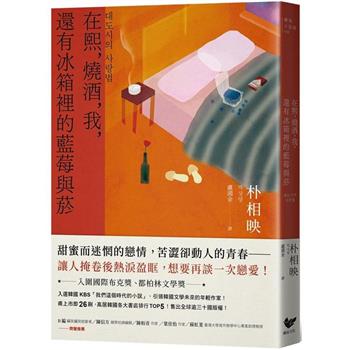●在熙
我走進酒店三樓的翡翠廳,聽說有四百名賓客。感覺上,現場的人似乎比這個數字還要多。我坐在禮台附近的一個指定座位上,看了看四處的餐桌。法文系同學們各自帶著老化速度不一的面孔坐著。究竟來了多少人啊?之前,在熙無論社團酒約或者系友會,只要有人通知,她絕對毫不猶豫參加,現在大概就是之前累積的結果吧。由此看來,在熙的親和力真是到了令人噁心的程度。我和至少時隔五到十年沒有見面的同學打了招呼。「聽說你成了作家,恭喜啊!」「多連絡吧!」「聽同學們之間傳出你死了的消息,還活得好好的嘛!」「你的小說在哪裡可以看到?在網上找了半天也沒找到。」「看來你寫東西也很辛苦吧,胖了這麽多。」「你還喝那麼多酒啊……」
我的書不久之後就要出版,我已經很少喝酒了,隨著年紀大身材自然變胖,你們不也一樣?你們如果老是這樣說,那可不能保證我以前發酒瘋的情況不會再次出現。雖然想這麽說,但身為三十多歲的社會人士,不得不有教養地一笑帶過。如果有人說看過我的小說,我會回答說那都是我編造出來的。對於根本沒有人詢問的問題,卻準備該如何回答的我真可笑。如果說自我意識過剩也是一種疾病,那我的情況實在是太嚴重了。
「婚禮馬上就要開始,請各位來賓就座。」
婚禮的司儀是即將成為在熙丈夫的朋友,下巴很尖,皮膚油光,完全不是我的菜。他的慶尚道方言口音很重,主持能力也不怎麼樣,聽説是電視台記者。我比他好太多了,為什麽要根據慣例,讓新郎的朋友擔任司儀?這實在讓我覺得不是滋味。
前方大螢幕上出現在熙和新郎的合照。看著手機拍攝出畫質低劣的兩名男女的照片,我連續喝了好幾杯紅酒。不久前跳槽到企業銀行的哲九碰了碰我的肩膀。
「你說實話,你和在熙到底是什麼關係?傳聞是事實嗎?」
傳聞雖然是事實,但是哲九啊,你這個跟在熙表白後被拒絕的傢伙,這好像不是你應該說的話吧?
*
二十歲的夏天,在熙和我迅速親近起來。在那個時期,只要有人請我喝酒,無論提出什麽要求我都會同意。那天也與平常差不多,我和不知道幾歲的男人在梨泰院漢密爾頓酒店的停車場接吻。也許是他在地下的俱樂部裡請我喝了六杯龍舌蘭酒,月光、路燈和全世界的霓虹燈似乎都照耀著我,耳朵裡不斷傳來凱莉・米洛的〈Electronic number〉。對方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我和某個人在黑暗城市街道上存在的事實。因此,我和身分不明的人用盡全力交纏彼此的舌頭。就在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在為我沸騰時,有人猛力撞擊我的背部。在醉醺醺的情況下,我還能判斷這分明是出於厭惡的攻擊行為。於是我離開對方的嘴唇,轉過身去。我下定決心,如果情況不妙,將不惜一切和對方幹上一架。於是我握緊拳頭,但站在我面前的卻是在熙。就跟往常一樣,她叼著一根濾嘴上沾著口紅的紅色萬寶路香菸。我的酒好像一下子就醒了,在熙看著露出驚訝表情的我,笑得喘不過氣來,然後用她特有的洪亮聲音大喊:
「乾脆把他吞到肚子裡去吧!」
我也不自覺地說出:「妳在講什麽啦?」之後大笑起來。這時,和我接吻的男人去了哪裡,甚至他是誰,現在都記不得了,只大略記得在熙和我在停車場說過的話。
「妳不會告訴學校其他人吧?」
「當然,我雖然沒什麽錢,但還是有道義的。」
「可是妳沒嚇一跳嗎?我和男人……」
「完全沒有。」
「妳什麽時候知道的?」
「看到你的第一眼。」
此類老套的話。
那時我還不太了解在熙,只記得她無論何時都穿著短褲,下課後比任何人都要更早一步跑到建築物外面抽煙而已。坦白說,在熙在系裡的評價幾乎是最差的。
大學時,我幾乎是系裡名副其實的異鄕人,但也不是從一入學開始就那樣的。當時只因為比別人高大一些,經常被男性學長邀去他們的租房聚會。他們的一起混的習慣非常固定,大概都是在撞球場或網咖結束第一輪後,聚集在學校前面的廉價餐廳,灌進燒酒配上非常鹹的下酒菜,然後去差別不大的租房中屋況最好的學長房間玩,聊聊女人後打呼入睡。 根本就不值一提的二十歲、二十一歲的男孩把自己當成什麼大人物一樣,說自己做愛有多厲害,讓誰如何滿足,系裡的女孩中誰最容易上床,在熙是經常被提及的對象之一。這種分明一半以上都是編造的謊言,我懷疑自己為什麽進到大學來還得聽這些垃圾。有一次喝醉後大喊「你們這些長得像傻屌的人少在那邊吹牛」,把酒桌給掀翻了,從那之後乾脆就不約我了。原本集體的屬性就很可笑,如果一度是該集體的一部分,一旦被排擠出來的人必然會成為更美味的祭品。他們對品評那些女孩失去新鮮感,就開始拿我當下酒菜,説怎麼看都像個同性戀、去梨泰院那裡玩什麼的……好像只有純真二十歲的人才會在意的那些消息傳得沸沸揚揚,那其中只有一半是對的(現實總是超出想像。)還沒過一個學期,當系裡幾乎沒有人不認識我的時候,那些傳聞才進了我的耳朵,我於是變成了笑話。我心想以後在系裡交不到朋友了,但又自嘲地合理化說那又怎麼樣,這些人都不太會喝酒,也沒有什麽意思。如此整理複雜的心情時,在熙突然出現在我的人生當中。
出乎意料地與在熙共享祕密的我,從那之後,就和她成了聊些索然無味男人的關係,事實上,在熙和我都沒有能聊這種話題的人,所以彼此的需求都非常迫切。
在熙和我的共同點是貞操觀念淡薄,不,不只是淡薄,簡直就是沒有,這方面在各自的世界裡都比較有名。在熙身高是一六七公分,五十一公斤,我則是一七七公分、七十八公斤,兩個人都只是比平均身高高了一點而已,雖然臉長得不是太好看,但也並不醜陋,還算帶得出場。(我獲得小説作家新人獎的時候,在評語中最常出現的句子就是『客觀的自我判斷能力』。) 世界已經做好了盡情利用二十歲貧窮但肆意揮霍的身體的準備,因此我們沒有什麼困難地隨便找個男人喝酒,早上聚在兩人中某個人的租房,在腫脹的臉部貼上面膜,共享一起過夜的男人的話題。
「他説自己在製作登山服的公司上班。老二比較小,但因為愛撫很厲害,所以想給他五十分。」
「那人說自己是延世大學統計系畢業的,好像是在說謊。他不但臉長得非常一般,一開口就讓人覺得他的腦袋裡面是空的,太可笑了。」
「他想偷拍影像,所以我把他的手機扔了出去,他説只是自己要看的,哼!以為我不懂?」
就這樣盡情地罵那些男人,不知不覺間閉上了眼睛,經常把乾巴巴的面膜貼在臉上,一起入眠。絕大部分的日子是早上比較早醒的我先起床,放任被子蓋住頭頂的在熙不管,烹煮速食明太魚湯或拉麵等,和聞到味道後起床的在熙一起用酸泡菜泡冷飯吃。 因此不知不覺間,在熙的房間擺放著我的髮膠和吉利刮鬍刀,我的房間裡擺放著在熙的眉筆和粉餅。我一個人的時候會拿起在熙的眼線筆填補眉毛上的空白處,或者拿出粉餅,毫無緣由地拍打臉頰或額頭三次,但是在熙不知道這件事。每當這時,我總會想在熙可能也會用我的刮鬍刀刮掉自己的腿毛或腋毛。
在熙與父母斷絕因緣是在二十一歲的春天。我們倆和父母的關係都不太好,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父母是壞人,他們只是平凡的中產階層家庭的保守父母。就像大部分平凡的父母一樣,他們雖然經常對子女說一些令人鬱悶的常識,但私底下卻是興奮地搞外遇或對宗教、股票、傳銷著迷的人。以我來説,因為討厭父母,所以有著『該吃的東西都要吃乾抹净』的孬夫心腸(所以長相越來越差了嗎?),看著眼色,每月向媽媽要幾十萬韓元的零用錢。但是在熙和父母大吵了一架後,乾脆斷了連絡,甚至拒絕了經濟上的援助,她果然是個有稜有角的女人。
在熙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社區的咖啡廳『Desthyne』打工。她說並不是因為招牌上寫著『命運』這一具有宏大意義的法語而選擇了那裡,只是因為那裡是社區裡為數不多可以自由吸煙的咖啡廳,所以一下子就喜歡上了。看著在熙一邊抽煙一邊煮咖啡的樣子,總是帶著二十出頭天真浪漫的可愛。每當我交到新伴侶時,都會把他們帶到Desthyne接受在熙的某種檢查(?)。在熙每次都會評價說他們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慾,性格像臭狗屎的傢伙。後來回首一看,在熙説的都沒錯。
在熙白天是Desthyne的店員,晚上做家教老師,凌晨還抽出時間喝酒。同時,她還聽學校的課,成績也還可以,總之無論做什麼都會超過平均水準的在熙,其他方面都不錯,唯獨在選擇好男人,以及在適當的時候向亂七八糟的男人告別這方面沒有什麽天分。所以我每次都會給在熙的男人們發拒絕或離別的短信,我在那個方面根本接近於達人,只要把我被別的男人甩掉時聽到的話原封不動地發給他們就可以了,所以沒有什麼困難。在那個時期,我認為自己是冷麵店的腳墊,隨便把脚抖一下就走過去的存在。(客觀的自我判斷能力!)
當Brown Eyed Girls的〈Abracadabra〉席捲全國時,我收到了入伍令。入伍前聽到因為以『親愛的哥哥』為開頭的同性愛人的信,被揭穿是同性戀後,在軍隊裡吃了很多苦頭的故事,所以在進入新兵訓練中心之前,我提醒當時交往的K以在熙的名義寫信。每當這個時候,在熙總是成為很好的煙霧彈。不僅是K,我還命令在熙每天寫好笑的故事寄給我,但是因為知道在熙討厭麻煩的性格,所以並沒有特別期待。
第二週訓練結束後,第一次收到信件時,我感到極度驚訝。因為在入伍前愛得死去活來的K在半個月的時間裡只寄來一封信(甚至連一張信紙都沒有寫完),但完全沒有期待的在熙卻寄來十二封信。剛開始是自己荒唐的日常生活(昨天在魷魚海邊喝酒的時候,把桌子掀翻了……)、胡亂寫下罵系裡人的髒話(哲九那瘋子想跟我睡覺,明明知道他在背後罵我,他這個表面和内心都十分噁心的狗崽子……)。隨著日期的推移,她開始表達對我們一起經歷的時光的感想和對我的思念。她甚至在最後一封信中寫道:「只有失去後才會明白的珍貴,你就是這樣。』這種不知道從哪裡抄來的句子,雖然知道這信一定是她喝酒之後寫下的,但還是有一點感動。因此,在公發的信紙上,我用力地寫下以「全世界最醜的在熙:」為起始的回信。
我剛被分配到部隊時,傳來在熙又開始和父母連絡的消息,在他們的資助下,去了澳洲當交換學生。另外,她還說K的苗頭不尋常,建議我找一天好好審問他。(用不了多久的時間,就證明她的直覺是正確的。)因意外事故以傷兵退伍共六個月的服役期間,在熙在軍隊裡是我公開的女朋友。
就像被趕出去一樣,當我重新回到社會的時候,在熙已經去澳洲了。這意味著直到復學為止,約有半年左右的時間,我的生活中沒有在熙,只能獨自堅持著。我沒有特別想做的事情,也沒有想見的人,一整天沒有離開過我房間裡的床,過著吃飯、睡覺的生活。媽媽對我這種懶惰的性格感到寒心,在聽膩了她的嘮叨之後,不到三個月,我就自己一個人住進學校門口的考試院裡。
*
過了一年,我和在熙在仁川機場重逢。她發現站在入境出口的我,趕忙扔下行李箱跑過來抱住我。聞到她頭髮上的煙味,我才真正感受到我們再次在一起的事實。
在熙回到韓國後,就以驚人的速度在學校正門前租了一間面積有十坪的全租單間公寓,並報名了英語補習班,拿到多益成績。復學後,她沒有再攻讀經濟學雙學位,而是進入市場營銷社團進行案例學習等,成為就業準備生。我對在熙那積極正面的樣子感到非常陌生,還好看到她一週喝七次酒,覺得還是我認識的那個在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