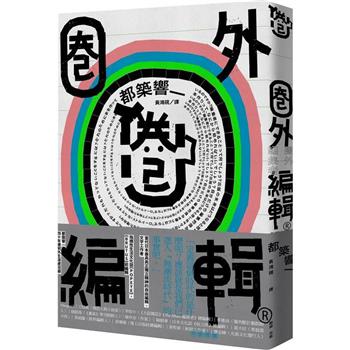問題1:做一本書要從何開始?(摘錄)
別看讀者臉色,觀照自己
這麼一想,我只能由衷感謝當時編輯部的環境,竟然允許我這種外行小鬼一意孤行。我會說:「這就是接下來的藝術趨勢!」然後跑去採訪沒人見過也沒人聽過的藝術家。面對其他媒體完全沒報導、沒人知道的題材,大多數的主管都會予以否決,但當時的總編給了我們最大限度的自由,讓我們做想做的事。
我們當然也挨罵過許多次。還記得我在《BRUTUS》時想出了「結婚特輯」,八成到今天仍是退書率最高的一期吧……。而且我還提出「在米蘭拍攝」的企畫,去找總編商量時說:「會很有趣喔~」結果又半抱怨地撇下一句:「但跟其他人的做法差太多了,不知道會不會賣。」總編大為震怒:「你是真的覺得有趣嗎?」我回答:「我認為成果一定會很有趣!」他便接著說:「那就不要看讀者臉色,全面做自己真心覺得有趣的主題。賣不好低頭謝罪是我的工作。」
我從那位總編身上學到很多,其中最身體力行的就是:「不要設定讀者群,絕對不要做市場調查。」不要追求「不認識的某人」的真實,而是要追求自己的真實。這教誨也許就是我編輯人生的起點。以製作女性雜誌為例。有人會設定讀者群,比方說:「本雜誌以二十五到三十歲單身女性為訴求對象,她們的收入大約多少多少……」一這麼設定的瞬間,雜誌就完蛋了。因為你自己就不是二十五歲到三十歲的單身女性。
明明是跟該族群無關的人,卻擅自認定「他們關心的事物是這些」。我認為那樣很怪,也很失禮。不該隨便認定,而是要想:我覺得有趣的事物,應該也有其他人會覺得有趣。這「其他人」有可能是二十歲的單身女性,也可能是六十五歲的大叔、十五歲的男孩子。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個讀者」,不是「讀者群」。
也許,最近雜誌會無聊的最大原因就在這裡。雜誌的狀況變得跟百貨公司一樣了。如今的百貨公司沒有個性,只是在比誰能引進最多知名品牌罷了,簡直變成了不動產業吧。雜誌的狀況會變得如此相似,正是因為市場調查做過頭了。時尚雜誌變得像化妝包等「特別附錄贈品」的包裝紙,以女性讀者為對象的性愛特輯則是男性編輯擅自妄想出來的,這樣的內容誰會想讀?再說,這些市場調查並不是出版社自己做的,大多是大型廣告代理商發表的。
我偶爾有機會和年輕編輯喝酒,發現會抱怨「企畫過不了」、「總編很廢」、「業務部多嘴」的人大多隸屬於大出版社(笑)。領高薪的人怨言特別多,而弱小出版社的色情雜誌編輯或八卦雜誌編輯絕對不會哀哀叫,我說真的。後者都說:「薪水少,工作辛苦,但我們是因為喜歡才做的。」
問題2:如何養成自己的編輯觀點?(摘錄)
沒錢才辦得到的事
在京都住兩年,認識各式各樣的人也和許多店家培養出感情後,我開始覺得「這樣下去不妙」(笑)。生活不奢侈的話花不到什麼錢,主攻學生、可自在入店的居酒屋也非常多。要是在那種店裡每晚跟朋友一起喝酒,把「真想做有趣的事」掛在嘴邊,十年轉眼就過了。實際上,在那裡落地生根的外國老嬉皮或自稱藝術家的大叔可多了。
因此我在第三年回到東京,幫《ArT RANDOM》系列收尾,也做一些零星的案子。漸漸地,我認識了許多年紀小我一輪的朋友。當時我在時尚業界的友人很多,交友圈是從那裡往外擴散的。不過在業界底層工作的年輕人,大多口袋空空(哎,我當時也才三十多歲就是了),和他們一起吃完飯,問起「要不要續攤」時,經常會演變成:「那就在住的地方喝吧。」因為比較不花錢。
就這樣,我開始會到這些年輕人的公寓去。他們住的房間當然很狹窄,就算裡頭放著時髦的衣物,內部裝潢也搆不著時髦的邊。但不知為何,我越來越覺得縮在這種地方喝酒非常舒暢。比待在雜誌會報導的那種奢華客廳還要舒暢許多。
接著我問起他們的生活狀況,回答不外乎是「每週打工兩天,剩下五天在練團室練習」、「稍微接點模特兒工作,其餘時間畫畫」之類的,令人非常感興趣。
這些年輕人也許是世俗眼光中的「輸家」,也許很讓父母擔心,但我越看越覺得就某個角度而言,他們的生活是非常「健康」的。收入沒多少,但不會去做
真的很討厭的事情,以此為生存之道。與其勉強去住租金較高的房子、搭客滿的電車通勤,還不如搬進租金不會造成負擔的狹窄房間,不管去玩或去工作都靠徒步或腳踏車解決。家裡沒有書房也沒有餐廳,但附近就有圖書館或喜歡的書店、朋友開的咖啡廳或酒吧,把街上當作房間的延伸就行了。
像那樣的房間、那樣的生活,如果只收集個十組寫成報導,大概只會被歸類為「邋遢房間趣聞」,但如果收集個一百組,也許就會產生不同的意義吧?這正是《日常東京 TOKYO STYLE》問世,以及我成為攝影家的契機。
這個計畫其實有前人打下的立足點。當時世界各地方非常流行命名為「某某Style」的時髦室內設計攝影集,例如《PARIS STYLE》、《MIAMI STYLE》之類的。這一系列「STYLE 攝影集」的作者是紐約知名記者蘇珊.斯萊辛(Suzanne Slesin),她完成幾本書後接著想出《JAPANESE STYLE》,於是和英國的美術總監、法國的攝影師一起飛過來,拜託我找可拍攝的住宅。她是我朋友的朋友,之前也在《BRUTUS》上報導過各種住宅。
於是我找了各式各樣他們看得上眼的時髦住宅,總之過程實在辛苦得不得了。光是豪宅還不行,因為沒有「SYTLE」就不能刊出來(笑)。
我接著只好利用各種關係,不斷向人鞠躬求情,過程中開始思考,為什麼做起來如此困難重重呢?我沒什麼大富大貴的朋友是其中一個原因,不過事實會不會是「家裡布置得這麼帥氣的人,比我們想的還要少上許多」呢?數量少,找起來才那麼辛苦。
「STYLE」若翻成日文,就是「風格」。帶有該風格的事物繁多,風格才能成立。如果數量很少,構成的就不是風格,而是「例外」了。因此我們不是在報導「日本的風格」,而是不自覺地在塑造「日本的例外」。
那麼,大多數人過的非例外生活是什麼樣子呢?如果舉我那陣子來往熱絡起來的東京年輕人為例,那就是「居住空間狹窄,但還是過得很開心」的生活風格。
在那之前,大家都說日本人住的房間是「兔子小屋」,視之為落後象徵,但我認識的年輕人都不以狹窄為苦。他們不會逼自己做不想做的工作,藉此住進較寬闊的房間,而是本能地選擇了不勉強自己的工作,生活在狹窄的房間裡。
我因此有了一個強烈的念頭:下次真想做一本書介紹真正的Japanese style !並逐一向認識的出版社提案。當時我根本無法想像自己拍照,主觀認定要是沒有哪家出版社提供預算,絕對不可能出版什麼攝影集。你想想,建築或室內設計的照片不是看起來都很專業、艱澀嗎?
後來,出版社一家一家拒絕了我,他們的看法都類似這樣:「只拍那些狹窄的房間是想怎樣?太壞心了吧。」
因此我一度放棄,心想,自己一個人是辦不到的吧。但我就算試圖喝酒忘了一切上床睡覺,忘不掉就是忘不掉。一旦開始在棉被裡頭想「這頁要是這樣做不知如何?收錄那人的房間也不錯吧?」就躺不住、睡不著了。
如此狀態持續兩、三天,我再也忍不住了,直奔友都八喜向店家說:「請給我外行人也能用的大型相機組。」就這樣買了下來,儘管完全沒有拍照的經驗。
總之先請攝影師朋友教我裝底片的方法,然後我就開始四處跑了。我沒有車,所以是把裝相機的袋子放在中古摩托車的踏墊上,三角架背在背上。一般室內攝影會使用的大型照明器材我買不下去,因為太貴了,再說根本無法放到機車踏墊上。我只買了一個燈,塞進相機包內。
當時還是底片機時代,它們根本不可能像這年頭的數位相機一樣,在高感光度條件下照樣拍出好看的照片。我也沒有閃光燈,只好在昏暗的狀態下拍,曝光時間就得長達三十秒到一分鐘,像在明治時代拍照似的(笑)。如果碰到實在太昏暗的狀況,我就會在曝光過程中默數五秒到十秒,然後緩慢揮動手上的燈,藉此補光。書出版後,也不少人的評語是:「沒拍攝房間主人,反而激發讀者的想像力。」但其實不是不想拍,是沒辦法拍(笑)。總不能叫人家一分鐘不要動。
就像那樣,我用專家看了會憋不住笑的器材和技巧拍了又拍。拍照方法完全自學,所以失敗的次數非常多,但失敗的話只要在再過去拍一次就行了。那陣子我不斷接案寫稿,拿到錢就去買底片。
就這樣拍了三年, 累積了將近一百個房間的照片後, 我硬是拜託《ArT RANDOM》的出版商京都書院幫我出版, 完成的書就是《日常東京 TOKYO STYLE》。我們按照最初的預謀(笑),採用跟《JAPANESE STYLE》等時髦室內設計攝影集完全相同的尺寸,也做成豪華感十足的硬殼精裝,讓書店誤以為是同一類書籍,放在同一區。似乎有不少外國觀光客真的買錯,整個傻眼(笑)。
問題5:你為誰做書?(摘錄)
藝術這種蛛絲
這些職人在封閉的世界內,忘我地進行專屬於自己的創作表現。看到他們,我就想起幾年前得知的「死刑犯的繪畫」。
前面稍微提過死刑犯吟詠的俳句。而在同樣封閉的極限狀況環境之中,當然也有囚犯是向繪畫尋求救贖。
某次碰巧看到的一小篇報導,成了我得以一次欣賞整批死刑犯繪畫的契機:廣島市郊外有個小劇場兼咖啡店「開放劇院咖啡」(Café teatro Abierto)預定舉辦死刑犯畫展。報導是在報紙還是網路上看到的,我已經忘了。當時我人在仙台工作,但對展覽內容非常有興趣,一查才知道仙台和廣島之間一天只有一班飛機直飛,於是我立刻預約了隔天的機票,決定去看看再說。
展間不過是在原本的舞台上以木板隔出來的,整體規模很小,DIY感十足,但每張畫都像是一記重拳,讓人動彈不得。
有的畫出自知名死刑犯之手,例如和歌山毒咖哩事件的林真須美之類的,也有非常厲害的素描、明天搞不好就會行刑卻悠悠哉哉畫出來的漫畫……我感動得一塌糊塗,但一想到這麼厲害的創作表現不知為何都沒有美術館或藝術媒體理會,又非常、非常地不甘心。於是我當場拜託主辦單位讓我拍照,在電郵雜誌上做了一個特輯。有個策展人讀了特輯,隔年在廣島縣福山市一個專推非主流藝術的小型美術館「鞆之津博物館」(鞆の津ミュージアム)舉辦展覽。開幕前似乎有相當多抗議和責難,但一開跑就引起莫大迴響,創下開館以來入場人數最多的紀錄。就算藝術雜誌不介紹,NHK的藝術節目不報導,會看的人就是會來細細品味。
在差不多同一時期,我另外在筑摩書房的網路雜誌上連載「東京右半邊」專欄,內容集結而成的書又是厚厚一大本。連載最後,我採訪了「東方工業」——全世界最高級矽膠娃娃的製造商。性愛娃娃以前叫「Dutch Wife」(這似乎不是日本人自創的英語,而是世界通用詞彙),指的是無法或不願與真人女性交往的男性當作性慾發洩對象的娃娃。東方工業在上野御徒町設有展售間,去那裡就能看到成排放置的娃娃,從美熟女到外觀年紀輕到有點危險的少女都有,現場還有顧問人員(或者說服務員)供客人徵詢意見,並提供一定程度的客製化服務。「我有這種喜好,有這種慾望,希望有這樣的女孩子」都能告訴他。最高級品一尊要價七十萬日元也是當然的,畢竟臉型、髮色、胸部大小、陰毛疏密都能指定。接單後就會向葛飾區的工廠下訂,成品再以宅急便寄到買主家,東方工業稱之為「出嫁」。順帶一提,因故送回原廠修理叫做「回娘家」。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會付那麼多錢買什麼娃娃,各位一定會好奇對吧?這可不是花幾千日元買玩具似的塑膠製充氣娃娃或令人懷念的「南極一號」,等級差多了。於是我又興沖沖地做了採訪。
購買者之中當然有戀物系的重度使用者,認為「比起活生生的女人,我說什麼都會乖乖聽的娃娃好多了」。但也有人是患有恐女症或臉紅症,沒辦法自然地面對女性;也有人有肢體障礙,無法與女性有肉體上的親密接觸。甚至還有這樣的例子:某精障男子到了一定年紀後開始有性慾,母親別無選擇只能用手幫他處理,但他的慾望越來越強烈,再這樣下去會演變成要命的狀況……母親煩惱到最後得知東方工業性愛娃娃的存在,感激地說:「它救了我們母子。」因此東方工業設有身心障礙者折扣制度,認真看待這件事。
每天都跟性愛娃娃一起生活,對某些人而言它當然會變成類似伴侶的存在,而不只是高價的自慰用工具。以前的人絕對不希望他人知道自己擁有性愛娃娃,但最近的使用者意識也開始產生改變,開始會舉辦線下聚會,或跟其他擁有者一起旅行。當然了,他們會讓自己喜歡的娃娃坐在副駕駛座,包下旅館,與娃娃比鄰開宴會。
和東方工業來往久了,有次突然接到他們的請求:「能不能請你當評審?」原來是要我評東方工業每隔幾年就會舉辦的「自豪的性愛娃娃攝影賽」。
說到性愛娃娃的照片,大多數人大概都會想像出一些變態的畫面吧?然而那類照片少之又少,真要說來,投稿作品都是「普通」照片居多。穿圍裙站在廚房做沙拉,穿睡衣打電腦,穿戴滑雪裝備置身滑雪場等等!如果不說它們是性愛娃娃,大家也許只會以為是普通的女友日常照。也因此,超越「娃娃」與「主人」的關係才會透過這些照片湧現。它在持有者眼中可能是戀人,可能是妹妹,可能是姐姐。這感情徹頭徹尾是「愛」,但世人只因為戀愛對象不是真正的女人而是娃娃,就視之為變態。
藝術有各種功能,從「提升教養」到「成名賺錢」都是。這些功能沒有好壞之別,但世界上最需要藝術的人,不就是被迫生活在封閉環境的人嗎?例如畫圖跟活著等義的非主流藝術家;明天也許就要接受死刑,卻把最後的時間奉獻給畫筆的死刑犯;以投稿獲得暴露照雜誌刊載為人生唯一樂趣的插畫職人;只將自己的真心獻給性愛娃娃的業餘攝影家等等。藝術對他們而言,難道不是最後的防護索嗎?知性探求型的藝術當然存在,也應當存在,但能夠救人一命的藝術也是存在的,重要順位比前者還要前面許多。我只是希望大家知道這點才做這些。這原本應是藝術新聞報導該扮演的角色,但沒人動手。
根本敬等人有個活動已經辦了三十年以上,叫「夢幻名盤解放同盟」,專門尋找、介紹沒人知道而且也沒人想知道的反常音樂。解放同盟展開活動時發表了一個宣言:「所有唱片,都該平等地獲得在唱盤上播放的權利。」藝術也完全一樣,所有藝術家畫出來的畫,都該平等地獲得掛在牆上的權利、受鑑賞的權利。喜好隨人,但連看都不看就貶低作品是不可原諒的。藝術品有評價高低、價格高低,但真正的優劣明明是不存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