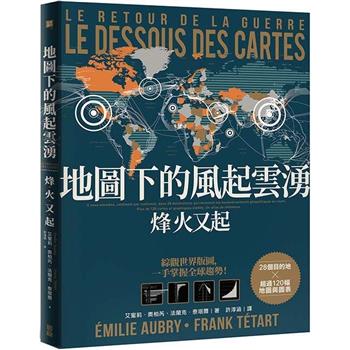目的地1
莫斯科
歡迎來到克里姆林宮。這裡從15世紀起動土興建,占地28公頃,包含大皇宮以及參議院,此即總統幕僚和弗拉狄米爾・普丁辦公的地方。關於克里姆林宮,這座護持沙皇和總統的堡壘,人們對那間出名的「超長桌」會議室並不陌生,因為自2022年2月起,那張桌子見證過多少歐洲領導人造訪流連,直到俄羅斯軍隊進犯烏克蘭邊境。除了Covid-19防疫所需的社交距離,不少觀察者發現,克里姆林宮的首腦對力量關係的展現情有獨鍾,也喜歡跟西方「保持距離」。
弗拉狄米爾・普丁意圖步步逼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計畫,合理化出兵烏克蘭的行動。根據俄羅斯的說法,在蘇聯解體和新國家嶄露頭角之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進逼俄羅斯聯邦的邊境,形成安全威脅(在2008年,這套說辭「正當化」了俄羅斯對喬治亞進行的軍事介入)。可是,俄羅斯的威權首腦會反而因為入侵烏克蘭的關係,而有利於北西洋同盟壯大陣容。如今,眼看普丁在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之後,還入侵烏克蘭領土,此舉究竟會不會是他的最後一場戰役,沒有人知道端倪——他的帝國主義大業是否已經走火入魔?他是不是高估了自己的軍事實力,而且不但小覷烏克蘭的反擊勁道,還低估了歐洲人跟美國人的反應?除非,他以為時間站在他這一邊⋯⋯。這場衝突(以及衝突造成的局勢分界,在世界上劃出一個拒絕選邊站的區塊)也有可能就此標誌權力集團兩極的分裂,使自由的西方與威權的東方勢不兩立。由於莫斯科與北京有可能彼此串通,形成威脅,此舉會讓世界進入新的政治力場,牽動經濟活動、軍事部署和文明角力。如此一來,沒有人能預測結局。
俄羅斯—烏克蘭
普丁的最後一戰?
有一天,普丁曾經表示,蘇聯解體是「上個世紀最慘烈的地緣政治災難」。從1999年以來,克里姆林宮的強人普丁矢志克服這個「災難」,並讓俄羅斯重拾強國威勢。蘇聯和美國並處冷戰時期的超級強權,是俄羅斯的前身;俄羅斯則是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之一,並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SC)擁有永久席次。不過,從2000年起,俄羅斯在普丁的推波助瀾之下,不但重振國力,而且對外政策更具侵略性,再度成為傲視全球的強權。其實,採取侵略性的對外政策達成的,是內政的目的,因為這樣才能讓人淡忘國內沒有實質的多元政治環境,讓反對的黨羽消音,並且鎮住俄羅斯人民日益飄搖的經濟民生。
俄羅斯幅員遼闊,接壤的國家有15個左右,其中的強國,包括美國隔著白令海峽(Bering Strait)和北冰洋(Arctic Ocean)與之相望,外加中國以及歐盟。這個地理位置當然形塑了俄羅斯觀看世界的方式,也會影響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立場。
近鄰國家
為了瞭解俄羅斯對外政策的邏輯,我們似乎有必要斟酌俄羅斯如何看待自己。俄羅斯將自己視為一大強國,承襲在1991年解體的蘇聯(Soviet Union)。同時,先前屬於蘇聯的共和國,則被俄羅斯視為直屬勢力範圍,不可侵犯。莫斯科將這些國家稱為「近鄰國家」(near abroad)。俄羅斯會在近鄰國家主張其經濟與戰略利益,例如位處哈薩克的拜克努爾(Baikonur)太空發射基地。俄羅斯也藉此和俄羅斯及俄語系人民維繫文化上的連結,在哈薩克,兩者加起來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這樣的影響力範圍中,莫斯科將分離主義運動化為己用,讓自己能持續掌控不同的國家,並在鞏固勢力時師出有名。聶斯特里亞(Transnistria)的案例便是如此,聶斯特里亞原是摩爾多瓦(Moldova)的俄語系地區。喬治亞共和國(Georgia)的兩塊領土阿布哈茲(Abkhazia)以及南奧塞提亞(South Ossetia)也是分離主義運動的案例。
2004年,西方陣營在喬治亞迎來「玫瑰革命」。在玫瑰革命中,親歐的米哈伊・薩卡希維利(Mikheïl Saakachvili)取得政權,加速該地區的民主運動。2008年夏天,薩卡希維利派遣軍隊進入阿布哈茲與南奧塞提亞兩地,此舉立即引發克里姆林宮強烈的武力反制,一度讓俄軍進逼喬治亞首都提比利斯(Tbilisi)。普丁的諸般武力展示,使他得以在南奧塞提亞與阿布哈茲保有俄軍基地,並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釋放清楚的訊息:讓喬治亞成為會員國,門兒都沒有。也因為這一連串的事件,歐盟在面對南高加索山地區並制定相關「睦鄰政策」(neighborhood policy)時,形成偏見。
對烏克蘭的執念
環顧這些「近鄰國家」,烏克蘭地位非凡。因為,對俄羅斯而言,烏克蘭是折衝要地,可以保護俄羅斯領土,同時還被視為俄羅斯的「歷史搖籃」。
有了這兩個原因,我們更能釐清2004年大事件的來龍去脈。當時民主派的示威人士在全國上下鼓譟,抗議總統選舉舞弊,造成親歐候選人落選,是為「橘色革命」。這場革命不對莫斯科的胃口,於是莫斯科逕行譴責西方勢力干預。為了讓烏克蘭重新向俄羅斯投誠,普丁在2006年1月透過國營企業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Gazprom),發動能源攻勢,掣肘烏克蘭。Gazprom藉著烏克蘭欠款未繳的理由,切斷輸往烏克蘭的天然氣。克里姆林宮順勢推行支援政策,扶持烏克蘭東部的俄語系民族。
併吞克里米亞
俄羅斯侵略色彩鮮明的對外政策,在2014年展開第一步。烏克蘭的親歐示威導致親俄的烏克蘭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Viktor Ianoukovitch)遭到廢黜,普丁於是出手併吞克里米亞。克里米亞是一座半島,大部分居民說俄語,而且港都塞凡堡(Sebastopol)握有俄羅斯海軍基地。然後,普丁派兵進入頓巴斯(Donbas)——頓巴斯居民主體也是俄語系人民——扶持烏克蘭境內的分離主義運動。
六年之內,第一起烏克蘭衝突造成兩方超過1萬4000人死亡。簽署於2014年9月的明斯克協議(Minsk Agreement),為進一步的和平協商畫下藍圖。明斯克協議將自治地位賦予受到親俄分離主義勢力控制的烏克蘭地區,可是,落實自治的路困難重重。其實,烏克蘭想重拾對邊境的掌握,根據澤倫斯基總統(Volodymyr Zelensky)的立場,這個原則是當務之急,而且沒有協商餘地。
俄羅斯面對歐盟與北約組織
如果併吞克里米亞讓俄羅斯總統人氣竄升,這是因為對俄羅斯人而言,此舉洗刷了蘇聯解體以及1990年代轉型期局面混亂所象徵的恥辱。對俄羅斯來說,併吞克里米亞師出有名,因為俄羅斯從2000年以來跟西方鄰國形成的局勢能因此別開生面。不管是歐盟東擴,或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範圍對俄羅斯邊境頻頻靠近,對俄羅斯當局來說,都是構釁之舉,畢竟北約的同盟勢力被視為美國軍事力量的觸角。
2004年,身為前蘇聯成員的波羅的海三小國加入了歐盟。俄羅斯聞之,有如骨鯁在喉,因為這代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上前叩門,也喚醒了冷戰時期的圍堵感受。在這樣的背景之下,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步上2008年喬治亞的後塵,使克里米亞遭到俄羅斯併吞。這在在顯示,俄羅斯拒絕讓自身的影響力在前蘇聯勢力範圍走下坡,為了制衡民主體制和西方價值,無所不用其極。自從蘇聯解體後,即使俄羅斯仰賴歐盟作為其首要貿易夥伴與外資來源,這個危機仍重創了俄羅斯與歐盟、美國的關係,引發西方的經濟制裁和俄羅斯的反制裁手段。2014年以後,莫斯科與布魯塞爾之間的經濟協商變得窒礙難行。
無論是在對外政策,或是在國內進行對西方影響力的抵制抗爭,普丁領導的俄羅斯與西方抗衡,成為政策的主軸。軍事上,莫斯科指控華盛頓當局在波蘭跟羅馬尼亞設置反飛彈防禦基地,此舉違反中短程核子武器公約的規範。在這段時期,俄羅斯和西方世界的關係十分艱困,促使克里姆林宮深化跟中國的連結。
莫斯科與北京:利斧新鑄?
自從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與中國便試圖建立良好的關係,從爬梳中俄邊境問題下手。2001年,中俄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並與中亞國家結盟,對抗伊斯蘭主義與分裂主義的勢力。2017年,印度與巴基斯塔加入了上海合作組織,讓上海合作組織海納超過一半的全球總人口。
中俄關係的緊密,也顯現在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一事之中。北京當局以不干預的原則之名,作壁上觀。軍火貿易和聯合軍事演習也讓兩個國家愈走愈近。不過,就算如此,中俄的兩相共謀,並未帶來均衡的同盟關係,也沒有讓中國成為盟友。中俄關係深度地不對等: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俄羅排名第12,國內生產毛額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左右。
為了和中國分庭抗禮,普丁在2016年提出了「大歐亞」(Greater Eurasia)計畫,和中國的絲路互通聲息。普丁希望能透過和北京合作,維持俄羅斯在國際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