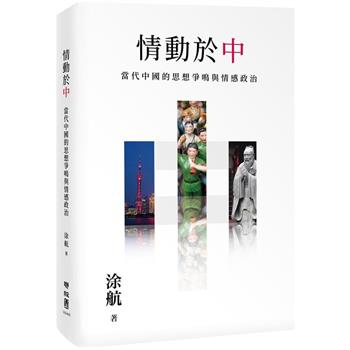第一章 「樂」與「罪」的隱秘對話
一、前言
1981年,李澤厚的《美的歷程》行世,隨即在校園和文化界掀起一陣「美學熱」。李著以迷人的筆觸描繪了中華文明起源之初的諸多美學意象:從遠古圖騰的「龍飛鳳舞」,到殷商青銅藝術中的抽象紋飾,再到百家爭鳴時期的理性與抒情,這幅綿長的歷史畫卷如暖流般撫慰著飽受創傷與離亂之苦的莘莘學子的心靈。李澤厚早先以其獨樹一幟的「回到康德」論述著稱,然而啟蒙思辨不僅關乎繁複的哲學論證,也得負起終極價值的使命。康德人性論的提綱掣領背後,是幾代中國美學家的關於審美與宗教的深思與求索。五四運動之初,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首倡用美學陶冶性靈以代宗教教化之說。相形之下,李著異彩紛呈的美學意象背後,隱約流動著其對儒學情感倫理學的重新闡釋。在李澤厚隨後描繪的「由巫到禮,釋禮歸仁」的儒學情理結構中,先秦儒學以此世之情為本體,孕育了與西方救贖文化截然不同的「樂感文化」。這種既具有民族本位主義又內含終極價值維度的審美主義試圖為文化轉型時期的中國提供一種安身立命的根基。
八十年代的啟蒙運動以美學的朦朧想像,重新啟動了五四時期的美育論,以感性詩意的方式呼喚文化和政治新命。面對新的政治想像,批評家劉再復以「文化反思」為出發點,將李著的啟蒙理念闡釋為一種高揚「文學主體」與「人性」的文藝理論,為重思現代中國文學打開了一個嶄新的視野。然而劉說並非僅僅局限於簡單的控訴暴政和直覺式的人道主義,更旨在叩問已發生的歷史浩劫中「我個人的道德責任」。換言之,文化反思並非以高揚個人主義為旨,而必須審判晦暗不明的個體在政治暴力中的共謀。受巴金《隨想錄》之啟發,劉再復以「懺悔」與「審判」為線索反思中國文學中罪感的缺失。劉著受到西洋啟示宗教的原罪意識啟發,卻並非意在推崇一種新的信仰體系。他希望另闢蹊徑,思考文學如何對證歷史,傷悼死者,追尋一種詩學的正義。罪感文學實質上是一種懺悔的倫理行為,通過勾勒靈魂深處的掙扎和彷徨來反思劫後餘生之後生者的職責。
本章以李澤厚的「樂感文化」和劉再復的「罪感文學」為題,通過重構兩者之間的隱秘對話,來勾勒新時期文化反思的兩種路徑。李澤厚在大力頌揚華夏美學的生存意趣和人間情懷的同時,毫不猶豫地拒斥神的恩寵以及救贖的可能。而劉再復則將現代中國文學對世俗政治的屈從歸咎於超越性宗教的缺失。二者凸顯的共同問題是: 新啟蒙運動為何需要以情感倫理的宗教維度為鑒來反思毛澤東革命的神聖性(sacrality)?簡而言之,對威權政治的批判,為何要以儒學之「樂」與基督教之「罪」這兩種道德—宗教情感為切入點?
在這裡,我需要引入「政治神學」(political theology)這一理論框架,來解釋政治神聖性(the sacralization of politics)與啟示宗教(revealed religion)之間的複雜張力。在其始作俑者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看來,理性化進程在驅逐宗教幻象的同時,也導致了「規範性價值的缺失」(normative deficit of modernity)。以技術理性為內驅力的自由民主制不僅無法掩飾其內在的道德缺失,而且在危急時刻不得不求助於高懸於政治程序之上的主權者以神裁之名降下決斷,以維護其根本存在。施密特的決斷論不乏將政治美學化的非理性衝動,然其學說要義並非推崇回歸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而在於借用神學要素來維護世俗政治之存有。由此可見,「政治神學」一詞內含無法調和的矛盾:它既喻指重新引入超越性的宗教價值來將現代政治「再魅化」,又意味著將神學「去魅化」為工具性的世俗政治。不同於施密特對政治「再魅化」的偏愛,二戰後的德國思想家往往以神學的政治化為出發點反思現代政治對宗教的濫用。在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等人的論述中,極權主義往往祭起宗教的術語、儀式、和情感來神聖化其世俗統治。現代政治權威不僅借用宗教的組織和符號,也從基督教的救贖理念和末世論中汲取靈感。在沃格林的筆下,現代全能政治源於靈知論(Gnosticism)對正統基督教救贖觀的顛覆:靈知主義者憑藉獲取一種超凡的真知在此岸世界建立完美的天國。洛維特則更進一步探討了共產主義理念和基督末世論的親和性:暴力革命的進步觀、烏托邦的理念和社會主義新人的三位一體均是基督救世思想的世俗形式。誠然,這種闡釋學的局限性顯而易見:現代政治進步觀與基督末世論之間的概念親和性(elective affinity)並不等同於歷史因果關係(historical causality),把神學理念直接推衍到對現代革命思想和社會運動的闡釋,其解釋效力值得懷疑。例如,中國政治學者雖然注意到毛澤東崇拜與宗教儀式之間的類似性,卻更傾向於強調世俗政治對於宗教符號的「策略性借用」(strategic deployment)。換言之,政治的神化僅僅是一種對宗教元素的功能主義利用。
我以為,這種功能主義的判斷無法解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宏大敘事賦予世俗政治的一種富於宗教情懷的「海洋性感覺」(oceanic feeling)。革命的神聖化本身蘊含了一種相互矛盾的雙向運動:在以世俗政治對宗教信仰的「去魅化」的同時,試圖將宗教的神聖性注入以「革命」、「社會主義」和「民族國家」為圖騰的世俗變革中。此文旨在以政治神學為切入點來重構李澤厚的「樂」與劉再復的「罪」之間的隱秘對話。我將論證,兩者的論述均以一種隱喻的方式構築宗教意識和政治專制的聯繫,並提出了相應的啟蒙路徑。李澤厚在大力頌揚華夏美學的生存意趣和人間情懷的同時,毫不猶豫地拒斥神的恩寵以及救贖的可能,而劉再復則將現代中國文學對世俗政治的屈從歸咎於宗教性的缺失。對於基督教超驗上帝(transcendental God)的文化想像導向了兩種看似截然不同卻隱隱相合的啟蒙路徑:以此岸世界的審美主義來消解共產革命的彼岸神話,或是以超驗世界的本真維度來放逐世俗國家對寫作的控制與奴役。
值得一提的是,我所指的「隱喻」並非狹義的修辭策略,而是以錯綜複雜的文辭、審美和想像力生成哲學論述的獨特路徑。不論是德里達等後結構主義者關於文字與思之「再現」(representation)的立論,還是Hans Blumenberg 以哲學人類學為出發點梳理概念性邏輯背後根深蒂固的「絕對性隱喻」(absolute metaphor)的嘗試,這些論述均將流動性的言說和星羅棋布的審美意象看做創生性哲學話語的源泉。更不必說,中國傳統中的「文」與「政」的相繫相依,早已超出了西學語境下的模仿論,而蘊含著道之「蔽」(concealment)與「現」(manifestation)的複雜律動。正因如此,單單從觀念史學或是從文學史的角度梳理李與劉的論述,都無法細緻地追蹤和指認政治—宗教批判與文學/文化批評之間看似毫無關聯,但卻以嬗變的「文」為媒介相互闡發的能動過程。因此,八十年代的啟蒙話語「荊軻刺孔子」式的隱喻政治正是我們闡釋李澤厚之「樂」與劉再復之「罪」的起點。
從另一方面來看,隱喻政治也凸顯「文」的歧義性:與狹義的(現代)文學之「文」不同,四處流串的「文」似乎缺乏有機統一,四處彌散,消解了「文化」、「文理」或「文統」本來具有的批判意義。在這裡,我關心的並不是是大而化之、無所不包的「文」的概念演化,而是重在討論新啟蒙知識分子如何以「文」—從李澤厚糅雜中西的美學、哲學實踐到劉再復天馬行空的文化批評—彰顯「情」的倫理教化之功。「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一詞源自十八世紀的西歐啟蒙運動。與高揚理性主體的康德不同,大衛‧休謨(David Hume)、亞當‧斯密(Adam Smith)等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極為強調感性教育的維度,提出培育「同情心」之必要。同一時期的法國啟蒙作家亦把小說作為熏陶情感、塑造道德激情、進而傳播啟蒙理念的重要媒介。與此類似,晚清以來的中國啟蒙知識分子將「文」視為情感教育、聯通啟蒙人性論的關鍵性媒介。例如,陳建華認為,《玉梨魂》這樣的「傷情—艷情」小說旨在「祛除暴力及其情感創傷」,通過「情教」來「重建一種現代國民主體與家庭倫理」。同理,在從「革命」到「啟蒙」的轉型語境中思考情感教育,意味著理解李澤厚與劉再復如何以文學和美學實踐批判毛時代的「階級仇恨」教育,為後革命時代提供普世人性的基礎,進而重塑後革命時代的公民主體性與感覺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