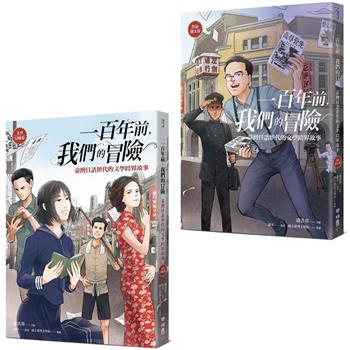夢之歌
蕭詒徽
能久親王的死法,一八九五
沒有人像日本的能久親王一樣,在臺灣史上死這麼多次。
一八九五年,明治天皇的舅舅、甲午戰後升任近衛師團攻臺司令官的能久親王,率軍接收剛成為殖民地的臺灣。五月二十九日軍隊於澳底登陸,六月七日進入臺北城,隨後開始了持續五個多月的乙未之戰──在臺灣各地烽起的抵抗,直到同年十月二十三日才受日軍控制,而在這不到半年的時間裡,能久親王在全臺各地死了十幾次:
八月初,他在新竹城外的牛埔山被義軍射殺。
八月底,他在王田崁被砲彈炸傷,抵達臺南後身亡;同一時間,他在灣里茄拔被割傷頸部,抵達臺南後傷重不治。
十月十一日,他在義竹受傷;十月十六日,他在大林受傷;十月十七日,他在回到雲林的路上病倒,但十月十八日又在嘉義附近受傷。日軍由北一路打到南,他在前往打狗的路上又被斬首。
有人說,這是因為臺灣人在戰敗之際不願接受被殖民的現實,在各地零星戰勝的捷報中,自然套上日軍司令的名字。有人說,其實八月初在新竹的那次,真正的能久親王就已經死了,但為了維護皇室形象與軍隊士氣,日本便讓剛好也率軍來臺的能久親王的弟弟──貞愛親王當替身,扮演出師未捷的哥哥,繼續在臺之役。
日本官方的說法則是這樣:
十月二十八日的清晨五點,能久親王因為患上瘧疾,連續多日高燒不退,在體溫飆到三九點六度後不省人事。隨行軍醫石黑忠悳從臺南拍了一通機密電報回日本──
「殿下今朝來衰弱大增,熱三十八度七分,脈百二十,呼吸三十,肺部水泡音全肺,咳痰不少,食慾乏,漸漸滋養物強進奉,三日來便祕,尿無異,但已晝夜不能分……」
清晨七點,石黑判斷能久親王已無脈搏。日本方面收到了死訊,但直到十一月五日才公布消息,為了避開十一月三日明治天皇的生日。
無論這通電報內容是真是假,有幾件事可以肯定:第一,能久親王畢竟是死了。第二,能久親王無論如何沒來得及等到十一月十八日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向天皇報告「全島悉予平定」的時刻,也不會曉得樺山資紀報告中所述的乙未戰爭情況:「五百多人負傷,一六四人戰死。另有數千人染疾而亡。」
樺山資紀所提的「數千人」,實際數字根據四十二年後井出季和太的《臺灣治績誌》統計,有四千六百四十二人──這還只是死亡人數。同一份統計中,光是乙未之役期間,在臺灣得到霍亂、痢疾等傳染病的人數高達兩萬六千○九十四人,是在戰場上負傷人數的五十倍。
能久親王打得贏臺灣戰士,但打不贏臺灣病毒──無論真相為何,日本官方公布的電報裡至少承認了這一點。
乙未戰役之後,日本迅速在臺灣開始擬定傳染病防治政策,改以無聲的方式繼續著他們平定這座島嶼的戰爭。有趣的是,在隨後由日軍大本營野戰衛生長官部編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戰役陸軍衛生紀事摘要》中,除了瘧疾、腳氣、霍亂、赤痢、傷寒之外,還提到了另外一種傳染病:愛憐病。
摘要中,得到愛憐病的士兵只有一千五百二十八人(同一份報告中瘧疾的患病人數是三萬五千九百一十一人)。患愛憐病後的死亡人數也只有少少七人,死亡率只有千分之四(霍亂的死亡率則高達七成);然而,摘要中卻以十分微妙的口吻述及此病「耗費戰時必要衛生物資,增添醫療搬運之煩瑣……徒費運輸至難之兵餉……」強調這病為日軍所帶來的困擾。
愛憐病就是性病。摘要中指出,縱然少有兵士因性病而死,但從治療到痊癒平均要花十六天,是霍亂的三倍。所以,摘要中那句話的潛臺詞是:得性病的傢伙最麻煩了,死不了還得吃飯,走不動還得搬運,去你的。
一八九七年七月,總督府頒布了「檢黴取締法」,前三條內容是這樣的:
一、
嚴加取締密賣淫者。
二、
密賣淫者需進行身體檢查,有毒者需入院或接受指定公醫之治療,患者治癒後在必要時間內仍需每週應訊接受身體檢查;無毒者亦然。
三、
無設置貸座敷之小市街,警察官署的特別監督下對認定為密賣淫者進行黴毒防治取締。
這些條文的潛臺詞則是:男人們會得性病,大抵都是娼妓的錯。
有趣的是,在檢黴取締法頒布隔年,總督府卻重新下令、廢除該法中的第二條與第三條。各地官廳也相繼廢除因之而生的「密賣淫取締規則」。這部法律最嚴格的部分,僅實行短短半年。
在檢黴取締法莫名刪修的四十四年後,五十四歲的臺灣詩人吳萱草來到了嘉義西門町三丁目大酒樓「西薈芳」。不為別的,他要帶西薈芳的當家藝旦彩雲外出,去見他正在當地旅居的老朋友、日治時期鹿港三大詩人之一,施梅樵。
拜訪(一),一九四一
吳萱草沒發現自己輕輕嘆了口氣。
那是昭和十六年,嘉義,伴他趕路的是一名美得像夢的女子。一回神,他看見她一雙探聽的眼睛,才意識到自己的心事無意間溢於言表。向她回以一笑,沒多說什麼。
前輩兼老友施梅樵下榻的旅舍就在不遠。為此他特地帶上這名女子,要讓她和施兄會一會。走著走著想起的卻是五年前《臺灣新文學》上刊的那則啟事:
島上優秀的白話詩人楊華,因過度的詩作和為生活苦鬥,約於兩個月前病倒在床,曾依靠私塾教師收入為生,今已斷絕,陷入苦境,企待諸位捐款救援,以助恢復元氣。
他當然記得楊華。十八年前參加高雄三友吟會、屏東礪社這兩詩社的擊缽聯吟活動,他在會上被奉為左詞宗,負責評比詩友們限時即興之作。缽聲一響時間到,人人交出作品,他一眼看見那充滿敬意的字跡:
詞林藝苑任滋繁,剪碧裁紅筆下翻。
著盡胸中文藻就,幾人佳句借君存。
他選這首詩為第一,詩的作者便是楊華了。那時,楊華才剛出道,《臺南新報》上刊載十數首他作的漢詩;一聊才曉得,楊華也曾與施梅樵師生相稱,寫漢詩時以「敬亭」為名,不用本名。
施兄這一生為了養家全島跑遍,哪裡有文塾請他教課他就去、教穩了請別人接手,自己又到下一個地方。不知是哪一年遇到的楊華吧。
不曉得施大哥聽說了沒有?
病倒的消息一刊出,月底楊華就在屏東老家上吊了。算算才三十歲?施大哥是寫漢詩的,也不知讀不讀《臺灣新文學》。
幸好她一起來了。吳萱草想,就算席間不意聊起楊華噩耗,有她在,施大哥也會開心的──
是彩雲吶,在《詩報》上以「薄情花」為題向全島徵詩、投詩應徵的作品來了一千一百多首的那位彩雲吶。
「彩雲乃嘉義西薈芳之妓女也,性耽風雅,喜學吟詠,者番感嘆身世飄零,欲向島內徵詩,望諸大雅勿吝珠玉,多惠佳作,以垂永遠紀念。」身為西薈芳當家藝旦的她親筆寫的這段徵詩啟事,施大哥就算沒讀到、也定然是聽說了的。
忽然,吳萱草想起了什麼,回頭叮囑彩雲:「等等妳詩唱應和,用針線繡活作喻可以,但別提襪線的典故。」
彩雲點點頭。吳萱草又對她笑,這回是嘉許的意思。他心想:等等見到面,一定要問施梅樵,堂堂鹿港大詩人怎麼沒有共襄詩壇盛事,寫首薄情花來讀讀?他們兩人年少時可都人稱風流啊──
想到這,他不禁又嘆了口氣,心道:是,我們都不年輕了。
彩雲的來歷,也許一九二○
吳萱草帶走的到底是哪一個彩雲?
一九三○年九月九日,漢詩詩社「臺南南社」與「春鶯吟社」的成員創辦了《三六九小報》,是日治時期臺灣第一份,也是最大的漢文期刊。每月三、六、九日發刊,自稱要與臺灣各地號稱大報的刊物有別,所以叫《三六九小報》。
在每一份《三六九小報》第四頁左下角長駐的,是連載藝旦軼事、通常名為「花叢小記」的專欄。
沒有人知道彩雲早年的出身。但如果她和大部分的藝旦經歷類似,那麼最一開始,她大概是被自己的家人賣掉的。
她可能像「花叢小記」所寫的藝旦小鳳一樣,先以數十元的價格被賣給某氏當「枝苗媳」──長大後要嫁給養家男丁的「媳婦仔」──但在婚配前被某氏以三百元轉賣給養母阿美,阿美訓練她唱曲賣藝。
然後,她可能像招仙閣的錦秀、小蓮芳一樣,從童年到少女的時光都在練習演奏樂器、吟詩、作曲、陪酒中度過。五歲,最晚十二、三歲開始,養母請曲師教這些藝旦囝仔唱北管、南管,練習琵琶彈唱,同時請漢文老師教授詩詞。
過程中她可能像淡水關渡的鳳嬌一樣,因不願學曲而被老鴇養母阿香鞭打虐待,或者被塾師用戒尺抽之。
養母會如此毫不吝惜地對待自己花幾百塊錢買來的養女,除了不是自己親生的,可能還因為她們懂得放眼未來:成功開業的尋常藝旦,每個月收入就有四、五百元。而製茶女工每個月的工資是二十五元。
教訓這些女孩們對她們而言,是一種投資。
直到一九三五年九月六日停刊為止,《三六九小報》僅停刊兩次,共發行四百七十九號;在所有花叢小記系列連載中,曾出現過兩個彩雲。而無論哪一個彩雲,都顯然是成功的投資。
第一個彩雲,是出現在第七十五期的「小彩雲」。她是藝旦「小寶桂」的鴇母,將小寶桂一手栽培成善唱北曲的淡水名妓。
而另一個,則是擅長與文人以漢詩唱和或吟詠、被尊稱為「彩雲女史」的名旦。在所有花叢小記中,總共只提到十九位藝旦擅長漢詩,彩雲就是其中之一。
所謂吟詩,有詠唱、歌唱的性質,是具有音樂性的。唱詩之間各有流派,曲調未必有別,但風格則各有所異,有人清越,有人悲怨。此外還有諸多「吟調」,如音調渾厚且帶情感的鹿港調、富高低抑揚之變化的天籟調等等。曾有人寫詩稱讚彩雲的琴藝,如果不是客套,那麼這位彩雲便是善文又善演的詩人歌手了。
兩個彩雲都在時稱羅山的嘉義地區活動,也都身負一藝之長。雖然真正陪吳萱草前往拜訪施梅樵的彩雲只有一個,但小彩雲與彩雲也不是完全沒有關聯──
當時藝旦在江湖走跳,取的是花名。其中,在花叢小記上出現過、花名上灌一個「小」字的,就有小雲英、小罔市、小王英、小寶桂、小彩鳳……之所以有這麼多小字輩的藝旦,是因為藝旦們習慣在曾走紅的藝旦舊名上冠字,當成自己的藝名。
搶前輩的彩頭,可又要與前輩區分,為了表示自己是「小」的、是「新」的──「彩雲」大概就是這樣被傳承沿用,成為了小彩雲。
根據吳萱草特地帶她拜訪老友的行動判斷,他身邊的彩雲,理應是善詩的(大)彩雲──雖然,文人們詩中所贈答的這位彩雲,也有可能並不是花叢小報上的那位彩雲──藝旦們有著相似的名字,相似的際遇,做著相似的工作,唱相似的歌,甚至在詩人歌詠她們的詩作中共享相似的處境和悲情。在那些作品裡,她們是她,她也是她們。
在他們眼中,她們與賣身為業的「趁食查某」或稱「婊」的娼妓們不同。她們是上流階層才消費的娛樂。她們不用本名,她們用詩和歌聲陪伴人客,賣的是靈魂和時間──「賣面不賣身」。
蕭詒徽
能久親王的死法,一八九五
沒有人像日本的能久親王一樣,在臺灣史上死這麼多次。
一八九五年,明治天皇的舅舅、甲午戰後升任近衛師團攻臺司令官的能久親王,率軍接收剛成為殖民地的臺灣。五月二十九日軍隊於澳底登陸,六月七日進入臺北城,隨後開始了持續五個多月的乙未之戰──在臺灣各地烽起的抵抗,直到同年十月二十三日才受日軍控制,而在這不到半年的時間裡,能久親王在全臺各地死了十幾次:
八月初,他在新竹城外的牛埔山被義軍射殺。
八月底,他在王田崁被砲彈炸傷,抵達臺南後身亡;同一時間,他在灣里茄拔被割傷頸部,抵達臺南後傷重不治。
十月十一日,他在義竹受傷;十月十六日,他在大林受傷;十月十七日,他在回到雲林的路上病倒,但十月十八日又在嘉義附近受傷。日軍由北一路打到南,他在前往打狗的路上又被斬首。
有人說,這是因為臺灣人在戰敗之際不願接受被殖民的現實,在各地零星戰勝的捷報中,自然套上日軍司令的名字。有人說,其實八月初在新竹的那次,真正的能久親王就已經死了,但為了維護皇室形象與軍隊士氣,日本便讓剛好也率軍來臺的能久親王的弟弟──貞愛親王當替身,扮演出師未捷的哥哥,繼續在臺之役。
日本官方的說法則是這樣:
十月二十八日的清晨五點,能久親王因為患上瘧疾,連續多日高燒不退,在體溫飆到三九點六度後不省人事。隨行軍醫石黑忠悳從臺南拍了一通機密電報回日本──
「殿下今朝來衰弱大增,熱三十八度七分,脈百二十,呼吸三十,肺部水泡音全肺,咳痰不少,食慾乏,漸漸滋養物強進奉,三日來便祕,尿無異,但已晝夜不能分……」
清晨七點,石黑判斷能久親王已無脈搏。日本方面收到了死訊,但直到十一月五日才公布消息,為了避開十一月三日明治天皇的生日。
無論這通電報內容是真是假,有幾件事可以肯定:第一,能久親王畢竟是死了。第二,能久親王無論如何沒來得及等到十一月十八日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向天皇報告「全島悉予平定」的時刻,也不會曉得樺山資紀報告中所述的乙未戰爭情況:「五百多人負傷,一六四人戰死。另有數千人染疾而亡。」
樺山資紀所提的「數千人」,實際數字根據四十二年後井出季和太的《臺灣治績誌》統計,有四千六百四十二人──這還只是死亡人數。同一份統計中,光是乙未之役期間,在臺灣得到霍亂、痢疾等傳染病的人數高達兩萬六千○九十四人,是在戰場上負傷人數的五十倍。
能久親王打得贏臺灣戰士,但打不贏臺灣病毒──無論真相為何,日本官方公布的電報裡至少承認了這一點。
乙未戰役之後,日本迅速在臺灣開始擬定傳染病防治政策,改以無聲的方式繼續著他們平定這座島嶼的戰爭。有趣的是,在隨後由日軍大本營野戰衛生長官部編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戰役陸軍衛生紀事摘要》中,除了瘧疾、腳氣、霍亂、赤痢、傷寒之外,還提到了另外一種傳染病:愛憐病。
摘要中,得到愛憐病的士兵只有一千五百二十八人(同一份報告中瘧疾的患病人數是三萬五千九百一十一人)。患愛憐病後的死亡人數也只有少少七人,死亡率只有千分之四(霍亂的死亡率則高達七成);然而,摘要中卻以十分微妙的口吻述及此病「耗費戰時必要衛生物資,增添醫療搬運之煩瑣……徒費運輸至難之兵餉……」強調這病為日軍所帶來的困擾。
愛憐病就是性病。摘要中指出,縱然少有兵士因性病而死,但從治療到痊癒平均要花十六天,是霍亂的三倍。所以,摘要中那句話的潛臺詞是:得性病的傢伙最麻煩了,死不了還得吃飯,走不動還得搬運,去你的。
一八九七年七月,總督府頒布了「檢黴取締法」,前三條內容是這樣的:
一、
嚴加取締密賣淫者。
二、
密賣淫者需進行身體檢查,有毒者需入院或接受指定公醫之治療,患者治癒後在必要時間內仍需每週應訊接受身體檢查;無毒者亦然。
三、
無設置貸座敷之小市街,警察官署的特別監督下對認定為密賣淫者進行黴毒防治取締。
這些條文的潛臺詞則是:男人們會得性病,大抵都是娼妓的錯。
有趣的是,在檢黴取締法頒布隔年,總督府卻重新下令、廢除該法中的第二條與第三條。各地官廳也相繼廢除因之而生的「密賣淫取締規則」。這部法律最嚴格的部分,僅實行短短半年。
在檢黴取締法莫名刪修的四十四年後,五十四歲的臺灣詩人吳萱草來到了嘉義西門町三丁目大酒樓「西薈芳」。不為別的,他要帶西薈芳的當家藝旦彩雲外出,去見他正在當地旅居的老朋友、日治時期鹿港三大詩人之一,施梅樵。
拜訪(一),一九四一
吳萱草沒發現自己輕輕嘆了口氣。
那是昭和十六年,嘉義,伴他趕路的是一名美得像夢的女子。一回神,他看見她一雙探聽的眼睛,才意識到自己的心事無意間溢於言表。向她回以一笑,沒多說什麼。
前輩兼老友施梅樵下榻的旅舍就在不遠。為此他特地帶上這名女子,要讓她和施兄會一會。走著走著想起的卻是五年前《臺灣新文學》上刊的那則啟事:
島上優秀的白話詩人楊華,因過度的詩作和為生活苦鬥,約於兩個月前病倒在床,曾依靠私塾教師收入為生,今已斷絕,陷入苦境,企待諸位捐款救援,以助恢復元氣。
他當然記得楊華。十八年前參加高雄三友吟會、屏東礪社這兩詩社的擊缽聯吟活動,他在會上被奉為左詞宗,負責評比詩友們限時即興之作。缽聲一響時間到,人人交出作品,他一眼看見那充滿敬意的字跡:
詞林藝苑任滋繁,剪碧裁紅筆下翻。
著盡胸中文藻就,幾人佳句借君存。
他選這首詩為第一,詩的作者便是楊華了。那時,楊華才剛出道,《臺南新報》上刊載十數首他作的漢詩;一聊才曉得,楊華也曾與施梅樵師生相稱,寫漢詩時以「敬亭」為名,不用本名。
施兄這一生為了養家全島跑遍,哪裡有文塾請他教課他就去、教穩了請別人接手,自己又到下一個地方。不知是哪一年遇到的楊華吧。
不曉得施大哥聽說了沒有?
病倒的消息一刊出,月底楊華就在屏東老家上吊了。算算才三十歲?施大哥是寫漢詩的,也不知讀不讀《臺灣新文學》。
幸好她一起來了。吳萱草想,就算席間不意聊起楊華噩耗,有她在,施大哥也會開心的──
是彩雲吶,在《詩報》上以「薄情花」為題向全島徵詩、投詩應徵的作品來了一千一百多首的那位彩雲吶。
「彩雲乃嘉義西薈芳之妓女也,性耽風雅,喜學吟詠,者番感嘆身世飄零,欲向島內徵詩,望諸大雅勿吝珠玉,多惠佳作,以垂永遠紀念。」身為西薈芳當家藝旦的她親筆寫的這段徵詩啟事,施大哥就算沒讀到、也定然是聽說了的。
忽然,吳萱草想起了什麼,回頭叮囑彩雲:「等等妳詩唱應和,用針線繡活作喻可以,但別提襪線的典故。」
彩雲點點頭。吳萱草又對她笑,這回是嘉許的意思。他心想:等等見到面,一定要問施梅樵,堂堂鹿港大詩人怎麼沒有共襄詩壇盛事,寫首薄情花來讀讀?他們兩人年少時可都人稱風流啊──
想到這,他不禁又嘆了口氣,心道:是,我們都不年輕了。
彩雲的來歷,也許一九二○
吳萱草帶走的到底是哪一個彩雲?
一九三○年九月九日,漢詩詩社「臺南南社」與「春鶯吟社」的成員創辦了《三六九小報》,是日治時期臺灣第一份,也是最大的漢文期刊。每月三、六、九日發刊,自稱要與臺灣各地號稱大報的刊物有別,所以叫《三六九小報》。
在每一份《三六九小報》第四頁左下角長駐的,是連載藝旦軼事、通常名為「花叢小記」的專欄。
沒有人知道彩雲早年的出身。但如果她和大部分的藝旦經歷類似,那麼最一開始,她大概是被自己的家人賣掉的。
她可能像「花叢小記」所寫的藝旦小鳳一樣,先以數十元的價格被賣給某氏當「枝苗媳」──長大後要嫁給養家男丁的「媳婦仔」──但在婚配前被某氏以三百元轉賣給養母阿美,阿美訓練她唱曲賣藝。
然後,她可能像招仙閣的錦秀、小蓮芳一樣,從童年到少女的時光都在練習演奏樂器、吟詩、作曲、陪酒中度過。五歲,最晚十二、三歲開始,養母請曲師教這些藝旦囝仔唱北管、南管,練習琵琶彈唱,同時請漢文老師教授詩詞。
過程中她可能像淡水關渡的鳳嬌一樣,因不願學曲而被老鴇養母阿香鞭打虐待,或者被塾師用戒尺抽之。
養母會如此毫不吝惜地對待自己花幾百塊錢買來的養女,除了不是自己親生的,可能還因為她們懂得放眼未來:成功開業的尋常藝旦,每個月收入就有四、五百元。而製茶女工每個月的工資是二十五元。
教訓這些女孩們對她們而言,是一種投資。
直到一九三五年九月六日停刊為止,《三六九小報》僅停刊兩次,共發行四百七十九號;在所有花叢小記系列連載中,曾出現過兩個彩雲。而無論哪一個彩雲,都顯然是成功的投資。
第一個彩雲,是出現在第七十五期的「小彩雲」。她是藝旦「小寶桂」的鴇母,將小寶桂一手栽培成善唱北曲的淡水名妓。
而另一個,則是擅長與文人以漢詩唱和或吟詠、被尊稱為「彩雲女史」的名旦。在所有花叢小記中,總共只提到十九位藝旦擅長漢詩,彩雲就是其中之一。
所謂吟詩,有詠唱、歌唱的性質,是具有音樂性的。唱詩之間各有流派,曲調未必有別,但風格則各有所異,有人清越,有人悲怨。此外還有諸多「吟調」,如音調渾厚且帶情感的鹿港調、富高低抑揚之變化的天籟調等等。曾有人寫詩稱讚彩雲的琴藝,如果不是客套,那麼這位彩雲便是善文又善演的詩人歌手了。
兩個彩雲都在時稱羅山的嘉義地區活動,也都身負一藝之長。雖然真正陪吳萱草前往拜訪施梅樵的彩雲只有一個,但小彩雲與彩雲也不是完全沒有關聯──
當時藝旦在江湖走跳,取的是花名。其中,在花叢小記上出現過、花名上灌一個「小」字的,就有小雲英、小罔市、小王英、小寶桂、小彩鳳……之所以有這麼多小字輩的藝旦,是因為藝旦們習慣在曾走紅的藝旦舊名上冠字,當成自己的藝名。
搶前輩的彩頭,可又要與前輩區分,為了表示自己是「小」的、是「新」的──「彩雲」大概就是這樣被傳承沿用,成為了小彩雲。
根據吳萱草特地帶她拜訪老友的行動判斷,他身邊的彩雲,理應是善詩的(大)彩雲──雖然,文人們詩中所贈答的這位彩雲,也有可能並不是花叢小報上的那位彩雲──藝旦們有著相似的名字,相似的際遇,做著相似的工作,唱相似的歌,甚至在詩人歌詠她們的詩作中共享相似的處境和悲情。在那些作品裡,她們是她,她也是她們。
在他們眼中,她們與賣身為業的「趁食查某」或稱「婊」的娼妓們不同。她們是上流階層才消費的娛樂。她們不用本名,她們用詩和歌聲陪伴人客,賣的是靈魂和時間──「賣面不賣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