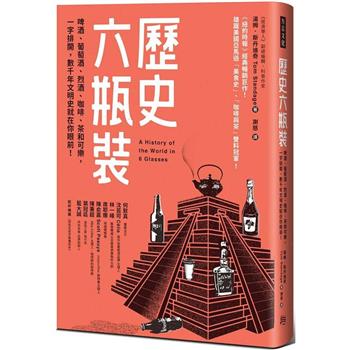▍共飲啤酒,展現信任
由於西元前9000~前4000年的新石器時代尚未出現文字,因此並未留下任何紀錄,顯示啤酒對於肥沃月彎聚落中的社會和宗教有多重要。然而,我們仍可從較晚期的紀錄推測,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人和古埃及人這些擁有文字的文明,究竟如何使用啤酒。
事實上,與啤酒相關的文化可說是歷久彌新,有些至今依然存在。打從一開始,啤酒這種飲料似乎就有重要的社會功能。蘇美人早在西元前四千年,就以象形文字描繪兩人用吸管從容器中共飲啤酒的畫面。然而,在蘇美人的時代,應該已有過濾啤酒中的穀類、穀殼和其他殘渣的技術,而陶藝技術的進步也足以輕鬆製作出個人的酒杯。圖中的飲酒者卻還是使用吸管,代表這樣的儀式在「吸管已非飲酒時的必要工具」之後,仍被延續了下去。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最可能的解釋就是飲品和食物不同,可真正地分享。由於當人們以同個容器分享啤酒時,喝的都是相同的液體,彼此沒有差異。但在切肉時,總會有某幾塊肉看起來特別誘人,分配時便容易引發爭端。因此,分享飲料在世界各地都是好客和友誼的象徵,提供者可藉此展示「內容物絕無下毒」或「此物適宜飲用」,代表自己值得信任;飲用者更可藉由暢飲表達自己的信賴。
最早期的啤酒以原始簡陋的容器釀造,個人杯具也還沒出現,當然必須眾人共享。雖然如今以吸管共享一大缸啤酒已不再是社會習俗,但茶和咖啡仍會盛裝在共享茶壺中;紅酒或烈酒也可能從相同的酒瓶中倒出。當我們在社交場合飲酒時,碰杯的動作也象徵性地讓個別的酒杯在那一瞬間結合成了共享的酒缸。上述這一切,皆源自於美索不達米亞的古老傳統。
▍死了都要喝
古埃及人也相信,他們來世的幸福與快樂,取決於能否取得充足的麵包和啤酒。標準的陪葬祭品包含麵包、啤酒、公牛、鵝、布料和淨化用的碳酸鈉。部分埃及的喪禮文件對死者允諾「啤酒永遠不會腐敗」,除了反映出永遠有啤酒可喝的渴望,也顯示了啤酒保存的困難。埃及的墳墓中,甚至可以看見釀酒和製作麵包的繪畫和模型,旁邊則放著一罐又一罐的啤酒(當然,裡頭的酒液早已完全蒸發殆盡)和釀酒器具。法老王圖坦卡門(Tutankhamun)約於西元前1315年過世,他的墓穴中就擺設釀酒專用的篩網。儘管一般人民僅能葬身於簡單的淺層墓穴中,但也會有小罐的啤酒陪葬。
從搖籃到墳墓,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人生命中的每個階段都與啤酒密不可分。這一切可說是天注定:隨著穀物生產過剩、社會結構越來越複雜,啤酒的用途廣泛,也需要文字的記錄。由於肥沃月彎的氣候條件最適合穀類生長,農耕也從此地興起,孕育出最古老的文明和文字,更生產出最大量的啤酒。
▍只有酒神可純飲葡萄酒
以雅典為首的希臘人認為,無論酒本身多麼高級,飲用時不摻水就是野蠻人的行為。他們相信,唯有酒神迪奧尼索斯能安全地直接喝純葡萄酒。(藝術作品中通常會描繪祂用特殊的酒瓶喝酒,代表裡頭不加半滴水。)與此相對,人類只能喝以水稀釋的酒,否則就會變得極度暴力,甚至失心瘋。
水會使酒變得安全,但酒也會讓水更安全。葡萄酒除了不含病原體外,發酵過程也會釋放出天然的抗菌成分。雖然希臘人並不知道這一點,但他們很清楚受汙染的水源有多麼危險;他們只會飲用泉水和深井裡的水,或是用水槽收集而來的雨水。他們也觀察到,和以水清洗的傷口相比,用葡萄酒治療的傷口較不易受感染(理由同樣是不含病原體,且含有天然抗菌成分)。因此,他們推論葡萄酒有清潔和淨化的力量。
有趣的是,希臘人認為,完全不喝酒就和只喝純酒一樣糟糕。羅馬時期的希臘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是這麼寫的:「酒鬼傲慢又無禮……但完全滴酒不沾也令人難以苟同。這樣的人比較適合照顧小孩,而不是參加飲酒宴會。」這兩種人都無法妥善運用酒神迪奧尼索斯賜予的禮物,而希臘人的理想是兩個極端間的中庸狀態;他們以水摻酒的習慣,正是使自己介於酗酒的野蠻人和滴酒不沾的粗鄙之間的最佳選擇。維持這種中庸狀態是「飲酒宴會國王」(symposiarch)的職責——擔任此職者可能是宴會主辦人,或是透過投票或擲骰子從與會者中挑選。「節制適度」是飲酒宴會的關鍵:飲酒宴會國王必須讓聚會者處於「清醒和酒醉的交界」,既能無憂無慮地暢所欲言,又不至於變得和蠻族一樣暴力。
▍突破天然酵母菌極限
歐洲第一位以蒸餾這項新技術進行相關實驗的,是十二世紀的義大利鍊金術師麥克.薩拉納斯(Michael Salernus)。他從阿拉伯書籍中習得此技術,並記錄以下發現:「將非常強烈的純葡萄酒與三份鹽混合,在一般容器中蒸餾,產生出的液體只要點火就會熊熊燃燒。」
當時的蒸餾技術顯然僅由極少數人獨占,因為薩拉納斯在寫作時,刻意將許多關鍵字以密碼代替(包含葡萄酒和鹽)。由於蒸餾的葡萄酒能點火燃燒,又被稱為aqua ardens,意即「燃燒的水」。
當然,「燃燒」這個字眼也可以用來描述嚥下蒸餾酒之後,喉嚨不舒服的感受。不過少量嘗試這種「燃燒的水」的人發現,雖然最初有些不適,緊接而來的活力和愉悅的感受,會讓一切都變得值得。由於葡萄酒在當時是廣泛使用的藥物,因此濃縮並純化的葡萄酒便具備了更強的治癒力,似乎也很符合邏輯。十三世紀晚期,歐洲各地的大學和醫學院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蒸餾葡萄酒在拉丁文的醫學專書中備受讚譽,被視為帶來奇蹟的新藥aqua vitae,即「生命之水」。
生命之水聽起來有點超自然的味道,某種程度上來說也的確如此。因為蒸餾過程帶來的葡萄酒,酒精濃度遠超過任何自然發酵的產物。即便最強大的酵母菌也無法釀出15%的酒精濃度,因此「15度」便成為發酵酒精飲料的天然極限。蒸餾技術使得鍊金術師得以突破這項數千年前發現發酵以來的自然限制。阿諾的學生拉蒙.陸里(Raymond Lully)宣稱生命之水是「人類最新發現的物質,在古代被隱匿,因為當時的人類太過年輕,不似現代的衰老,需要這種飲品來復甦。」阿諾和拉蒙都活到超過七十歲,在當時高齡得很不尋常,或許被歸功於生命之水的延年益壽之功。
▍過度稀釋可不行
除了奴隸之外,蘭姆酒在水手間也很搶手,從1655年起便就取代傳統啤酒,成為加勒比海上英國皇家海軍的薪酬。一個世紀內,蘭姆酒就成為英國海軍長途航行必備的飲品。傳統的啤酒既容易腐敗,酒精濃度又低,但若以半品脫的蘭姆酒代替往常一加侖的啤酒,對紀律和效率將造成重大的危害,為此,海軍上將艾德華.威農(Edward Vernon)下令配給的蘭姆酒必須摻入兩品脫的水。稀釋蘭姆酒並不影響喝下肚的酒精量,但至少能讓水手們比較願意去喝船上難以下嚥的飲用水。更重要的是,威農在稀釋的酒中加入糖和萊姆汁,讓這款飲料變得更好喝,此即最原始的雞尾酒,為表紀念而以他命名。由於威農的綽號是「老葛洛姆」(Old Grogram,他常穿一件絲毛混紡〔grogram〕的防水斗篷,這種布料纖維粗糙,會加入樹膠讓質料變硬),此飲料便被稱作「葛洛格」(grog)。
然而,酒精濃度差異甚大的問題,也存在於蘭姆酒上,而水手們看見自己的酒被摻水成「葛洛格」,難免會心生相對剝奪感。在十九世紀精準的比重計發明之前,沒有什麼輕易測量酒精濃度的方法。因此,負責分配蘭姆酒的海軍事務長,會透過以下(據說由皇家兵工廠發明)方法來測量稀釋前的濃度。他們在蘭姆酒中加少許水和黑色火藥粉,接著用放大鏡集中陽光以聚熱。假如火藥粉無法點燃,代表混合物的酒精濃度太低,得加入更多蘭姆酒,直到火藥粉幾乎可以燃燒,才代表濃度正確,據說大約是45%左右。(假如濃度過高,可能會引爆。不過根據傳統,事務長若喪失行動能力,水手就能自己取酒了。)
▍英國稱霸海洋的隱形關鍵
英國之所以能成為十八世紀的海上霸權,以葛洛格取代啤酒其實是隱形的關鍵因素。當時,壞血病是水手們的主要死因之一,會讓人日漸衰弱,而現在知道肇因是缺乏維生素C。最好的預防方式是固定攝取檸檬或萊姆汁,但這一點在十八世紀時不斷被發現又被淡忘。終於,到了1795年時,規定必須強迫在葛洛格中加入檸檬或萊姆汁,使得壞血症的發生率急遽降低。由於啤酒不含任何維生素C,以葛洛格取代之,自然大幅提升英國船員的整體健康狀態。而英國的死對頭法國則正好相反,船上的標準配給並非啤酒,而是四分之三公升的葡萄酒(約為現代的一瓶葡萄酒);較長的航程則配給十六分之三公升的生命之水(法語為eau-devie)。由於葡萄酒的維生素C含量低;生命之水則完全不含維生素C,法國海軍根本無法抵擋壞血症的侵襲。根據一位軍醫的說法,英國皇家海軍對壞血病無與倫比的抵抗力使戰力倍增,於1805年在特拉法加(Trafalgar)打敗法國和西班牙艦隊。(這也讓英國水手得到「英國佬」〔limey〕的暱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