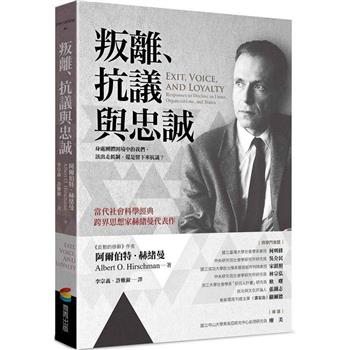導言及學說背景
在任何經濟、社會和政治體系中,個人、企業與組織一般都會背離有效率、理性、守法、高尚或正常的行為,而走向衰退。不論社會打下的基礎制度有多好,由於各種意外因素,有些行動者的行為達不到預期這是無可避免的,每個社會都必須學會和一些失序及不當的行為共存;但為了避免不當行為一再出現,進而導致全面的衰敗,社會必須能集結自身內部力量,盡可能使那些猶豫蹣跚的行動者回到系統,以維持正常運行所需。本書起初是為了探索這些內部力量在經濟體運行的狀況,但我發現,此處所發展出來的概念,不僅適用於企業之類的經濟行動者,也可廣泛應用到非經濟組織與情境。
雖然道德家和政治學家一直極為關切如何使個人免於墮落,如何使社會遠離腐敗,如何使政府免於衰退,但是經濟學家對於經濟行動者可以挽救的過失(repairable lapses)卻是不大關心。這有兩個理由。首先,經濟學預設經濟行動者即使不是採取中規中矩的理性行為,至少理性的程度也是固定不變。一間企業可能會因供給與需求情況的翻轉而表現惡化,但其利潤極大化(或成長率、或其他任何目標)的意願與能力並未減弱;但這可能也反映出,在供需要素不變的情況下,企業喪失了「利潤極大化的態度或能量」。如果採取後者的詮釋角度,就立即產生以下的問題:如何讓企業追求利潤極大化的能量回復到原先的水平?但一般來說,都是採取前者的詮釋;如此一來,客觀的供需條件能否反轉,也就更加令人存疑。換句話說,經濟學家基本上假定公司之所以會落後(或超前),都有著「充分的理由」;因此本書的核心概念,也就是隨機且多少可輕易「挽救的過失」,對那些經濟學家的推論來說,就有如天方夜譚了。
經濟學家不關心過失的第二個原因與第一個脫離不了關係。在競爭經濟的傳統模式中,從過失之中恢復元氣並非真的如此重要。當企業在競爭中敗陣下來,它的市占會由其他企業(包括新公司)補上,生產要素也會由其他企業接手,最終的結果有可能是全部的資源獲得更妥善的配置。由於有這樣的想法,比起道德主義者或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更能夠看待自己的任何一個病人(例如公司)犯錯;道德主義者深信自己每一個病人(個體)的內在價值,而政治學家則認為自己的病人(國家)獨一無二且無法取代。
我們釐清經濟學家對此毫不在意的原因之後,隨即可以挑戰這些說法的立據。諸如,設想經濟是一種完全競爭的體系,體系內個別公司財富的改變完全取決於比較優勢的基本轉移——這絕對無法代表真實世界的情況。首先,大家都知道真實的世界有獨占、寡占及獨占性競爭的大型王國。其中企業表現的惡化多少可能產生毫無效率且視而不見的死角(permanent pockets);就像政治學家認為政體內部的廉潔受內鬥、腐敗及死氣沉沉所威脅時,顯然就必須視其為即將來臨的警報。但是,即使在激烈競爭隨處可見之處,對於一時落後的企業是否有機會恢復雄風,經濟學家的漠不關心幾乎說不過去。精確地說,許多在相似條件下與對手相互競爭的企業,其個別企業的財富衰退,很可能只是因為一些隨機的、主觀的因素,這些因素在成本和需求條件的永久性不利變化中是可逆的或可補救的。在此情況下,恢復機制(mechanisms of recuperation)對於避免社會損失及人類困境,能夠發揮最實用的角色。
行文至此,我還要再插一句話,這種恢復的機制透過競爭本身就可輕易取得。競爭不就是應該要讓企業保持「戰戰兢兢」嗎?如果企業已經在走下坡,體會到營收日益下滑以及經歷競爭被淘汰出局的威脅,難道不會讓它的管理者鼓足幹勁、努力把企業拉回原本該有的表現嗎?
競爭無疑是一種重要的恢復機制。然而,本書要證明:(1)競爭這項特殊功能的意涵並未得到充分的闡述;(2)一旦競爭機制不可得,另一個主要的替代機制就會上場,或做為競爭機制的補充發揮作用。
進入「叛離」與「抗議」
本書提出的論點,是從生產可銷售物品給顧客的企業出發;但我們將會發現,這基本上——有時是原則上——可以適用於一些未直接收取金錢而向成員提供服務的組織,像是自願性團體、工會或政黨等等。人們假定,企業或組織的表現將因為一些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太持久的不明與隨機因素而面臨惡化;這些因素阻止企業或組織回復往昔的表現,並讓管理者將注意力與精力集中於此。表現的惡化最典型與最一般的是(也就是企業與其他組織都是如此)反映在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在品質上的絕對或相對惡化。然後,管理者將透過兩條路徑察覺自身的失敗:
(1)有些顧客不再購買企業的產品,或是有些成員退出組織。這是叛離選項(exit option)。因此,收益下降,組織的成員減少——不論導致退出的問題源自何處,管理者都必須設法加以修正。
(2)企業的顧客或組織成員,會直接向管理者或管理者所服從的上級表達自己的不滿,或向任何一位在乎且想聽的人表達自己的抗議。這是抗議選項(voice option)。因此,管理者必須再次想辦法探究顧客與成員不滿的原因,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法。
本書其餘的篇幅主要致力於比較分析這兩個選項,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我將探索以下幾個問題:什麼樣的情況下叛離的選項勝過抗議?反之,又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抗議的選項勝過叛離?叛離與抗議做為恢復機制,兩個選項的效率孰高孰低?在什麼情況下,兩種選項可以一起發揮作用?何種制度可以讓做為恢復機制的兩種選項充分運作?促使叛離選項充分運作的制度,能夠和設計改善抗議選項運作的制度相容嗎?
(略)
叛離與抗議:經濟和政治的化身(impersonations)
正如上文已經闡釋的,一旦檢視這些復甦內生力量的本質和力度,我們的探究將岔開兩路。它分為兩個相互對立(雖然並不互相排斥)的類別——叛離與抗議。即使沒能忠實地反映一種出更根本的區分(schism),這樣的二分法實在工整得出奇——叛離屬於經濟範疇,抗議則屬於政治範疇。當顧客對某一家企業的產品不滿意時,他可以改買另一家的產品,這是利用市場捍衛個人利益,或是改善自己的地位。顧者也可以啟動市場力量,讓相對表現日漸下滑的企業恢復元氣。這是使經濟蓬勃發展的機制:非常俐落——不是叛離,就是留下來抗議。這一切與個人無關——顧客與企業無須當面對質,避免企業難以評估或難以捉摸的元素,而且成敗完全可以藉由統計數據表示。這一切也以間接方式促成——衰退的企業走向復甦完全是受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所操控,乃是顧客決定跳槽所帶來的非預期結果。整體而言,抗議與叛離正好相反。抗議是個更加「混亂」的概念,因為它有可能逐步上升,由喃喃不平的嘀咕衍生為暴力的抗爭。它意味著表達一個人的批評意見,而不像超級市場裡私底下的「祕密」投票;抗議絕對是直接單刀直入而不迂迴。抗議是卓越的政治行動。
經濟學家往往自然而然地認定自己的機制有效率得多,而且也是唯一值得認真看待的機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一篇著名的論文中鼓吹將市場機制引入公共教育,就是這種經濟學家偏見的最佳說明。傅利曼所提方案的本質,是給學齡孩童的家長發放一種專用教育券;透過教育券,家長可以購買私人企業在競爭下提供的教育服務。傅利曼為自己的構想辯護如下:
家長把自己的子女從一所學校轉出再送進另一所學校,這樣比現在更能直接表達他們對學校的看法。一般來說,家長們目前要這樣做只能藉著搬家來達成。此外,他們就只能透過煩人的政治渠道表達個人意願。
我在此無意討論傅利曼的提案有何優點。我引用上面那段話,是為了充分說明經濟學家的偏見是偏向叛離勝過抗議。首先,傅利曼認為轉學或退出是個人表達對組織不滿的「直接」方式。沒有受過經濟學嚴謹訓練的人,可能會天真地建議表達觀點的直接方式是說出來。其次,表達個人看法及努力傳播觀點,還被傅利曼輕蔑地指稱這是訴諸「煩人的政治渠道」。但是,挖掘、利用並期待逐步改善這些管道,難道不就是政治、而且實際上是民主的過程嗎?
在整個人類制度中,從國家到家庭,不論抗議有多「煩人」,一般來說都是每位成員必須處理的問題。重要的是,假如問題仍舊肆虐,當前為了在大城市裡推動比較好的公立學校所做的主要努力,就是讓學校更去回應成員的需求。透過鼓吹並落實權力下放的手段,讓公立學校的成員與管理階層間的溝通迄今為止不再如此「煩人」。
但是,並不是只有經濟學家有盲點——(以范伯倫〔Veblen〕的話來說)一種「受過訓練卻沒有能力」(a trained incapacity)去理解我們此處提到兩種機制之一的有用性。事實上,叛離在政治領域的進展遠不及抗議在經濟領域的進展。除了被冠上無效率和「煩人」的標籤以外,政治上的叛離還要被冠上犯罪之名,因為叛離總是與遺棄、叛逃和叛變等負面標籤相連。
顯然,雙方對此事的激情與成見必須消除,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觀察一個典型的市場機制與一個典型的非市場機制(即政治機制)是如何共事;兩者或許是處於一種和諧且相互支持的狀態,也或許是相互擋道、破壞對方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
近距離觀察市場與非市場要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將顯示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對於理解政治現象很是管用,反之亦然。更重要的是,分析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要比單獨進行經濟或政治分析更能全面地理解社會過程。從這樣的角度來看,這本著作可以看成是把《經濟發展策略》一書所依據的論點應用到一個新領域:
傳統上似乎要求經濟學家得永遠論證以下問題:在任何非均衡的狀態下,單憑市場力量能否恢復均衡?這在現在肯定是個引人入勝的問題。但是,身為社會科學家,我們顯然要讓自己處理更宏觀的問題:不均衡的態勢可以單憑市場或非市場力量矯正嗎?還是要靠兩者共同發揮作用來矯正呢?我們認為,非市場的力量未必比市場力量還要更不「自動」。
我在這裡主要關注均衡擾動及恢復均衡的問題。阿羅(Kenneth Arrow)採用相同的分析方法,論證非最佳狀態走向最佳狀態的過程:
我在此處所提出的看法是,當市場未臻最佳狀態時,社會或多或少能看清此一缺口,非市場性的社會制度將出現並盡力彌補⋯⋯而這個過程未必會是有意識的進行。
但是,我和阿羅隨即補充,這些觀點並不表示市場和非市場力量的一些組合,就能剷除非均衡或非最佳的狀態。它們也不排除這兩股力量可以在不同目的下合作的可能性。但是,這畢竟為兩股力量的結合(也許結合得還不很合適)留下了空間,然而放任自由派(laissez-faire doctrine)和社會干預派(interventionist doctrine)皆以嚴格的摩尼教(Manichaean)觀點來看待市場和非市場兩種力量,兩派相互攻訐;放任自由派認為是好的力量,社會干預派就說那是邪惡之力,反之亦然。
最後一點。一直以來,叛離與抗議——也就是市場與非市場力量、經濟與政治機制——做為兩個主要的行動者,無論是位階或重要性皆難分軒輊。因此,當我在此基礎上構思自己的劇本時,我希望向政治學家證明經濟學概念有其用處,也想讓經濟學家相信政治學概念有其用處。近來,當經濟學家宣稱為分析稀缺現象與資源配置之目的而發展的概念,可成功用於解釋權力、民主與國族主義等多樣化的政治現象時,這種互惠性在最近的跨學科工作一直欠缺。因此,經濟學家已成功占領了相鄰學科的很大一部分;而政治學家——相對於工具豐富的經濟學家而言,他們的自卑情結恰好等同於經濟學家面對物理學家的自卑感——也已經顯示本身非常渴望被殖民化,並經常主動應和侵略者。也許,我們需要一個經濟學家在我們被壓迫的同事中重新喚醒身分認同與榮耀的感受,讓他們有一種自信,認為自己的概念不僅雄偉壯觀(grandeur),還散發著人造光芒(rayonnement)。我希望這可以是本文的副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