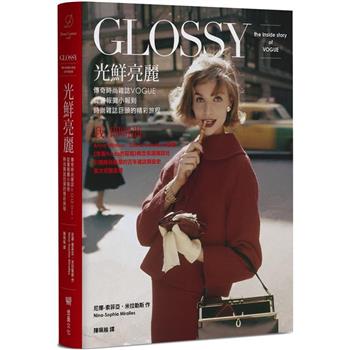第十一章:安娜.溫圖來了《VOGUE》代表性人物的早年生活
安娜‧溫圖與英國版《VOGUE》
在時尚業界,沒有一個名字能與安娜‧溫圖相提並論。即使是我們當中最不注重時尚的人,也會對她心生恐懼、感到迷戀、情緒緊張激動,由此證明她的個人崇拜力量。但即使是安娜‧溫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這位英國時尚編輯究竟是如何成功爭取到亞歷山大‧利柏曼和士毅‧紐豪斯的支持,我們永遠無從得知。格蕾絲‧米瑞貝拉還記得她突然出現在美版《VOGUE》時,是個骨瘦如柴、捉摸不透的人。據時尚界傳聞,溫圖曾因職缺被推薦給米瑞貝拉。當米瑞貝拉問她想要哪份工作時,溫圖戴著黑色太陽眼鏡,漫不經心地回答:「妳的。」
溫圖一九四九年出生於倫敦,是家裡五個孩子之一,不過早年她最大的哥哥因為一場自行車意外不幸去世,年僅十歲。她父親是不屈不撓的查爾斯‧溫圖,長期擔任倫敦《標準晚報》的編輯。溫圖遺傳到的特點不只是新聞工作者的氣質,連冰冷的態度也肯定來自她的父親──他在艦隊街被稱為「冰霜查爾斯」(Chilly Charles)。一位前員工說過:「見到查爾斯‧溫圖時,你會先被他冷冰冰的外表嚇到,但進一步了解他以後,你會發現,這只是冰山一角。」安娜‧溫圖在街道綠意盎然的聖約翰森林區長大,後來被送去一系列倫敦北部的女子學校就讀,這些學校非常豪華,學生都坐專車到校。她的性情頑強而複雜,顯然對於任何學術科目都不感興趣。她不會努力與同學相處,一有機會就翹課。
據傳聞,安娜‧溫圖年僅十四歲時,從英版《VOGUE》撕下一頁關於短髮造型的內容,跑到梅菲爾一家美髮沙龍店剪掉她的頭髮。從那時起,她就一直留著招牌的鮑伯頭。在傑瑞‧歐本海默未經授權的揭密傳記(二〇〇五年出版)中,人們記得她冷酷無情和挑釁,取笑胖子、嘲弄單身或守寡的老師。她一直著魔般地觀察自己的身材,每週到貝克街一家私人診所做臉部按摩。她肯定是他們診所幾十年來最年輕的顧客。雖然溫圖家的價值觀保守,但他們似乎給這位衣服狂的女兒極大的自由。到十五歲的時候,她可以愛去哪就去哪,過著相當自主的生活,晚上可以泡夜店、跳舞、出風頭。那些記得她的人,對她的記憶大多是瘦到難以置信、沉默寡言、明顯的羞澀、以及她與老男人不斷的調情。十六歲時,溫圖因為校服問題與學校發生最後一次的爭執,她認為校服很難看。拒絕遵從規定的她,走出校門,再也沒有回來。
沒有任何線索顯示溫圖在十幾歲或成年初期對雜誌有任何特別的興趣,但她確實在什麼東西適合自己和穿什麼能引起迴響這方面具有天生的理解力。當她父母在薩伏伊飯店為她舉辦二十一歲生日派對時,她已經從海外遠親那裡繼承了兩大筆遺產,這些錢足以讓她住進豪華公寓,購買昂貴轎車。更重要的是,這讓她擁有了設計師品牌的衣服,每季都可以不假思索地更新一輪。
在迪斯可的七〇年代初,溫圖找到了她在出版業的第一個角色。端莊的《哈潑時尚》與叛逆的《女王》合併,他們正在尋找員工。溫圖沒有任何經驗,但她憑自己一身服裝獲錄取。薪水很低,但這點當然不重要。她不需要薪水,她想要的是與一群很酷炫的人在一起。雖然她堅稱自己沒有特別的目標,但在一九七一年準備《哈潑斯女王》十二月號刊時,每個員工都必須寫下自己理想的聖誕禮物。據傳,溫圖的是想成為《VOGUE》編輯。但她的老闆們認為這個內容不適合發表。
身為《哈潑斯女王》的時裝助理,溫圖的成功苦樂參半。在拍攝方面,她有獨到的見解。她能夠組織龐大而不靈活的團隊,也知道如何管理乖僻的攝影師。她開始戴上墨鏡,似乎在打磨自己的個性,只是還沒奏效:別人覺得她傲慢無禮,有點不可理喻,因為她拒絕在工作時間以外與團隊的人交談或往來。有報導指稱,一些基層員工受不了溫圖一貫的惡劣作風,辭職走人。雖然溫圖能幹且專注,但她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在那個年代,編輯部的時裝工作人員只負責實際的攝影工作,不管文字,可是她無法好好與撰稿者溝通自己的想法,經常使複雜的情況變得更困難。儘管如此,公司還是提拔她擔任助理時尚編輯,不禁讓人懷疑,關於對她那些過去的描述究竟可信度有多少。
剖析新近的歷史困難,畢竟他人有不滿要宣洩。然而,有一項事實似乎無可辯駁:溫圖野心十足。《哈潑斯女王》的時尚編輯準備撤換時,溫圖已經躍躍欲試。經理正在尋找一位具寫作經驗的人才,而溫圖幾乎沒有任何經驗──她才工作幾年而已──但她仍努力爭取成為這個職位的角逐者之一。後來由資深記者明‧霍格得到這個位置,溫圖難以接受。她不斷試圖破壞霍格,爭執一再發生,後來一九七五年溫圖離開,搬到了紐約。
二十五歲來到大蘋果,溫圖自然而然地融入相當於她倫敦社交圈的紐約社交圈。以前週末去漂亮的莊園,晚上去名流聚集的安娜貝爾私人俱樂部。現在雖然住在上東區,但她還是參加了在市中心時髦新潮的閣樓和屋頂雞尾酒會,過著藝術家和英國僑民備受仰慕的生活。不久,她獲得《哈潑時尚》初級時尚編輯的職位。溫圖再次展現出訓練有素、創新以及不妥協的精神,但也再次激怒她的同事們。她不願意改變時裝拍攝來搭配編輯簡報,讓不習慣受質疑的前輩們大感驚訝。她覺得自己懂得更多,《哈潑時尚》則認為他們大可省去這些麻煩。她九個月內就遭解雇。
遭解雇雖然大受打擊,但並沒有改變她的方式。在她幾名男友的幫助下,溫圖進入了《Viva》雜誌,由鮑勃‧古橋內和他妻子凱西‧基頓所發行的刊物。古橋內是《閣樓》雜誌的創辦人兼編輯,這款是比較隱晦的男性成人雜誌,而《Viva》則是作為女性雜誌推出的──針對女性的情色刊物。溫圖每天都要穿過古橋內春光四溢的帝國走廊,兩側牆都是女人半裸海報,才能到達她的辦公室。後來問到她的工作經驗,她會省略在「閣樓新寵」的資歷。儘管如此,由此也證明溫圖的性格,她堅持在這個不太光彩的崗位上、與老闆關係日益緊張的情況下製作時尚單元,直到雜誌停刊。再度失業。
她的職業生涯繼續起起伏伏。一九八〇年,一家新雜誌《Savvy》以自由撰稿人聘請她,薪水低到連雜誌總監都感到尷尬。不過她要求為她的版面提供更多空間,以換取接受這種屈辱,並希望藉此她的作品能夠吸引到別家出版社給予更好的工作機會。整整一年沒有進展後,到了一九八一年,她透過人脈關係的協助,爭取到另一個時尚編輯職位,這次是在《紐約》雜誌。她在這裡終於可以大展身手。她追求高級時尚、性感的方式在新一代高薪、熱愛消費的雅痞夫妻當中引起了共鳴。《紐約》雜誌的讀者群比她任職過的其它雜誌還要廣泛,所以溫圖的作品現在打開了知名度。而且很快吸引到廣告商,渴望在民眾購買時進行推銷。
溫圖風格的攝影照片充滿了瘦削、黝黑、肌肉發達的女性,以摩天大樓為背景,穿著男性襯衫,裡面什麼都不穿,拎著公事包。除了這種極端八〇年代的女強人美學,她也會不時閃現創意靈感;在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全版廣告中,她委託包含尚・米榭・巴斯基亞在內的紐約當代藝術家,畫出他們對於最新時裝系列的詮釋。這種藝術與時尚的特別融合產生了溫圖夢寐以求的效果:它吸引到康泰納仕集團的後裔亞歷山大‧利柏曼的注意,並邀她出席一場會議。
康泰納仕的高層們還沒準備好提供安娜‧溫圖任何像是出版編輯這樣的具體職位,反倒發明了一種中間角色;一九八三年,她以「創意總監」出現在出版資訊欄,以前沒人用過這個頭銜。時任美版《VOGUE》總編輯的格蕾絲‧米瑞貝拉怒火中燒,尤其是當溫圖開始在編輯會議上批評她時。後來溫圖接受產業雜誌《廣告週刊》採訪,該雜誌發表一篇過分煽情的人物介紹,盛讚她是出版界的創新者,更讓米瑞貝拉的怒氣衝天。任何尷尬的事實都恰好遺漏,尤其是她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部分……,這篇吹捧文章卻只有輕描淡寫提到她對英國文學的熱愛。
既然安娜‧溫圖是時尚界的代言人,別人自然很容易批評她的每一個過錯,無論是多麼微小的失誤。不過,雖然溫圖已習慣因冷漠和磨人而招惹同事們的反感,卻還是不習慣處理後續結果。她的一意孤行在之前的工作裡可以得到想要的結果,但康泰納仕是家大公司,裡面都是大人物。來自四面八方的敵意強烈,每一位資深編輯、總監、經理和出版商,都在緊張得瑟瑟顫抖的權力之爭中左推右擠。競爭激烈,每個人都想從中分一杯羹。米瑞貝拉也許對溫圖的干涉感到憤恨,但那也不是溫圖的理想安排。利柏曼給她一個不太明確的職位,溫圖顯然不屬於任何部門。她可以阻礙別人的想法,但別人也可以削弱她。
溫圖習慣在規模相對小的時尚部門工作,所以傾向接管製作,但《VOGUE》是暢銷雜誌企業,拍攝是他們的專業。他們擁有龐大的團隊,而溫圖根本沒有管理這種規模的經驗。她自己的不合作態度讓事情變得更糟。最喜歡的伎倆是公然無視米瑞貝拉,巴結利柏曼。成功惹惱米瑞貝拉後,反過來米瑞貝拉又給利柏曼找麻煩。這種無窮無盡的爭鬥錯綜複雜,令人費解,而且持續不休。外界不禁納悶這裡究竟是不是有成效的工作環境。
到最後,因為敵意不斷升級,利柏曼不得不禁止溫圖再碰時裝單元。要溫圖遠離自己最愛的主題服裝,對她造成很大的壓力。當時《VOGUE》雜誌多名員工表示,看過她淚流滿面,或者發現她坐在辦公桌前,對著話筒另一端的未來丈夫大衛‧夏佛啜泣。夏佛是兒童精神科醫生,這點至少讓他成為很好傾聽者;儘管大多數專家認為他的貢獻遠不只這些,暗指他比起情人,更像是她的私人生活教練。在夏佛的鼓勵下,溫圖非常努力向同事們表明她是認真的。而同時期的另一篇矛盾報導卻稱,溫圖不但沒哭,反而是位暴君,把所有辦公室的牆壁換成透明玻璃,因為她無法忍受屬下關起門來竊竊私語。這個版本的報導刊登在《紐約時報雜誌》,內容引述她的話說,她不喜歡任何隱藏起來的東西──似乎除了她自己藏在瀏海和墨鏡後面的臉。
不管有沒有牆,溫圖都渴望努力得到回報。毫無疑問,她在等待米瑞貝拉被趕走,把總編輯職位移交出去。甚至在康泰納仕內部,人們也開始認為她遲早會成為美版《VOGUE》的下一位總編輯。然而,萬萬沒想到是英版《VOGUE》先落到她手中。當時任布洛克雜誌總編輯碧雅翠絲‧米勒宣布退休計畫時,利柏曼看到了機會,可以在不損失人才的情況下,把這位針鋒相對的「門生」調走。由於不受同事歡迎,溫圖不得不接受康泰納仕替她安排的新計畫,但抉擇很難。現在是她配偶的夏佛必須留在紐約工作,但幾個月前剛出生的小兒子不得不隨她一起去。許多第一次當母親的人可能會放棄,但堅持是溫圖性格的關鍵成分。她擔任該職位的短暫期間,將以蹂躪英版《VOGUE》的「核武溫圖」形象印在人們記憶中,從某些方面來看並不公允。
黛安娜‧佛里蘭的異想世界
在祕魯安地斯山脈中部,海拔約兩萬英呎的高度,聚集了一群特殊的小團體。這裡是世界最長和世界第二高的山脈,由青苔如茵的高原,高到融入墨藍陰影中的山峰,冰川融化後形成的明淨潟湖所構成。連綿起伏的雲層把整個景貌刷成白色。想在這裡找到英國攝影師約翰‧考恩,替美版《VOGUE》拍攝時尚大片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一九六〇年代後期,他卻試圖讓幾位穿著貂皮大衣的模特兒歡欣雀躍的身影永存不朽。和他一起參加這次凍傷冒險之行還有著名的髮型師艾拉‧嘉蘭特,以及有嚴重眩暈的時尚編輯巴布斯‧辛普森。
考恩一直在計畫拍攝一個盛大氣派的廣告,結合積雪覆蓋的山脈、鬱鬱蔥蔥的草木和印加遺址,讓穿著各式各樣服裝──麂皮、圍巾、背心和巴伐利亞傳統服飾,以及採用大量皮草,從栗鼠類到山貓的皮草大衣──的模特兒看起來像騰空而起,飄浮在雲霧瀰漫的景致中。送他們到那裡的直升機飛行員警告過,最晚到下午五點,再晚就得等別人來救他們了。結果規定的時間一再延後,飛行員都離開了,夜幕低垂。最後這群人不得不爬下山,模特兒們還穿著細跟鞋,後來他們找到一處洞穴,設法升火。他們在那裡過夜,窩在皮草大衣裡取暖。第二天醒來,迎接他們的是怒火中燒的祕魯軍隊,藏身處周圍都是美洲獅留下的足跡。馬上被驅逐出境。
照片印出來後,刊登在一九六八年美版《VOGUE》十月號雜誌上,不過還有其它很多的「昂貴小毛病」──由最新的總編輯黛安娜‧佛里蘭提供──沒有公諸於世。這種超現實派、達利風格的祕魯冒險絕對不會只有一次。佛里蘭曾派大衛‧貝利遠赴印度拍攝白老虎,但後來再也沒有刊登過這些照片。模特兒佩奈洛普‧特里拍攝另一系列照片被佛里蘭否決,因為她抱怨「嘴唇沒有慵懶感」。重新拍攝經常列入待辦事項。發脾氣也是如此。異國情調的拍攝地點雖然耀眼動人,但需要數月的準備時間。簽證必須得到國務院的批准。為了通關,工作人員必須將旅行中的每一件單品,甚至是極小配飾,都整理成一份海關文件,以確保離開這個國家的東西都能順利回來。一位編輯想起某次在伊朗的旅行,她花了幾個晚上的時間來解開數百個用於「裝飾」的法國古董窗簾流蘇。還有一次,佛里蘭突然決定在喜馬拉雅山拍攝的一組照片裡要有一頂大帽子。要送到已經出發前往亞洲的團隊,他們將這頂帽子裝在帽盒裡,必須透過汽車、吉普車、駱駝、最後靠驢子運上山,才能送到那個偏遠的地方。熨斗、燙衣板和縫紉工具必須和衣物放在一起。這些昂貴的服裝經常需要當場修補和修改。
要創造讓佛里蘭滿意的「造型」非常困難。布料樣本必須訂購、運送、挑選、送回;然後衣服委製、修改、丟棄、重新訂購;髮型師、彩妝師、模特兒、編輯、助理、造型師、攝影師都必須經過試用、聘僱、解聘。每一步都必須用拍立得寶麗來(Polaroid)記錄下來,這樣團隊中的每個人都可以追蹤變化。光是相機底片的沖印費用就高得離譜。所以,史上照片拍攝花費最高的紀錄保持者自然是佛里蘭。一九九六年秋天,雜誌發表一組名為「The Great Fur Caravan」時尚大片,篇幅足足有二十六頁。這支拍攝團隊(成員中還有一位兩百多公分高的相撲選手)在日本待了五個星期,拖著十五箱衣服爬上積雪覆蓋的高山。他們穿貂皮長靴、戴著白色貂皮頭巾、套上美栗鼠和俄羅斯山貓的連指手套擺姿勢,這個年代明顯是在善待動物組織(PETA)出現以前。由傳奇攝影師理查德‧艾維登拍攝,時尚編輯波利‧梅倫監督,由超模薇露希卡擔綱拍攝主角,據說這組時尚大片耗資一百萬美元。以現今幣值計算,大約是七百五十萬美元。
「The Great Fur Caravan」時尚大片被稱為一場「時尚冒險」,其幕後團隊是一群「角色陣容」。當時把照片拍攝稱為「記事」也是很常見。這些詞彙某程度解釋了佛里蘭領導下的《VOGUE》是怎麼看待時尚的。佛里蘭生於世紀之交,談起一九〇〇年代初期巴黎貴婦們所穿的華麗衣服,語帶留戀。佛里蘭在咆哮的二〇年代渡過了青春歲月,親身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變化,她是站在第一線目睹時尚界驚人轉變的見證人。她將自己定位成最後一位真正的美學家和時尚學者,在《VOGUE》的專欄版面上結合夢想與歷史。
佛里蘭摒棄當時女性雜誌常見的食譜和居家小秘訣,認為俄羅斯和中國的浪漫主義更重要。她明白是什麼轉瞬即逝的特質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正是這種直覺帶來魔力,調和了讓她顯得難相處和不夠通情達理的性格。佛里蘭的夢想,總是伴隨著非常實際的價格問題。最後由誰來買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