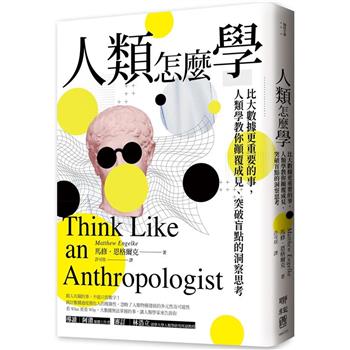第七章 權威
「女人的問題」
初步蘭群島的布料生產只是故事的開始。正如韋納所指出的,我們在民族誌紀錄中發現,從部落首領的斗篷和席子、皇室的長袍、神職人員的祭服到死者的神聖裹屍布,通常都是政治權威和權力的重要象徵。總的來說,是女人創造了這一切。初步蘭群島的案例事實上相對微不足道。在玻里尼西亞和太平洋的許多地方,布料都是權力、聲望或權威的主要象徵。莫斯認為每個禮物都因其「精神」(在著名的毛利人範例中,這種精神即是「豪」)要求回報。韋納提出要理解這個觀點,我們必須理解毛利人斗篷的政治重要性,就像庫拉珍寶本身也有某種人格和能動性。
然而,撇開所謂片面觀點不說,我們目前看到的許多民族誌確實迴避了父權占主導地位的問題。是的,馬凌諾斯基在他的分析中忽略了女性,但即使是韋納也指出,相較於男性,女性透過布料生產過程享有的權威和主體性依然受限。或是想想榮譽和恥辱,這通常有明顯的性別面向:男人贏得榮譽,而女人失去榮譽。像是巴蘇托族牛的奧祕,女人在這方面便不那麼重要。巴蘇托族男人利用牛的神祕性伸張他們在家戶及社群裡的權威。有人可能想起聘禮的概念,牛的奧祕有很大一部分就在聘禮之上。從維多利亞時代的傳教士到近代女性主義運動中的許多批評者都將這比作視女人為可以買賣的商品。但母系親屬制度呢?這無疑是由女性定義的權威形式。不過在你閱讀有關母系社會的政治關係論述之後,也可以認為這其實是在承認不同的男性在掌權:不是女人的丈夫,而是他們的兄弟。那麼更一般的「血液」呢?我們已經討論過血液是生命力和生命的強大象徵,它也和女性汙染、危險及死亡有關。「現代」瓦西馬婆羅門女性重新定義了經期隔離及禁忌的程度和範圍,但隔離的行為還是保留了下來。而且,許多女性也堅持這麼做。
那麼,文化最終總是會成為父權制度嗎?女性只是第二性嗎?
簡單來說,不;較長一點的回答是:這些是錯誤的問題。這兩個答案都無意否認或淡化男性用許多方式掩蓋女性的社會角色和地位—更不用說女性本身。它也不是在掩飾權力經常存在的醜陋面。關於「不」這個簡單的回答,是為了表明我們不能將性別關係自然化;憑著人類學的良知,並且基於民族誌證據,我們不能說庫拉圈或牛的奧祕,甚至是推動《唐頓莊園》劇情的習俗和繼承法都表明一項事實,即男人總是已經處於或最終總會處於優勢。
至於「這些是錯誤的問題」這個答案,我們要考慮兩點。一是簡單的觀點問題,價值政治
如何形塑我們對權威、聲望和權力的評估。如果我們把布料生產放在論述的中心會如何呢?或是撫養孩子?或者就此而言,大多數地方的大多數小學老師都是女性呢?如果某個地方存在「父權體系」,或者在我們心裡,它反映出類似於前幾章所說在歐洲傳教士和非洲人的相遇時所產生的事情:意識的殖民化。
第二點比較不那麼直接,但可能更重要。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它不是觀點問題,而是是否真實存在任何可感知的固定事物的問題。對某些人類學家而言,假設「男」和「女」是棋盤上的人物,他們和我們一樣在玩同一個遊戲,或者被困在同一個鬥爭之中,便是錯誤所在。
許多人類學家都提出了這個論點,其中瑪麗蓮.史翠山的作品影響深遠。她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作品《禮物的性別:美拉尼西亞的女性問題和社會問題》(The Gender of the Gift: Problems with Women and Problems with Society in Melanesia)將這個論點具體化。史翠山在副標題所說的「問題」與西方分析家對美拉尼西亞性別關係所做的假設有關。這些分析家包括人類學家、女性主義者,還有最重要的女性主義人類學家。對史翠山來說,許多西方對性別關係及男性對女性的支配的批評並沒有考慮到土著觀點,無論是男或女。事實上,史翠山希望我們擺脫這個立場的隱喻,因為它假設我們能分類的所有差異都基於相同的基礎。
在接下來大部分內容中,我想專注討論觀點問題。在兩個例子中(對埃及伊斯蘭教令〔fatwa〕的研究,以及對仄翁〔Chewong〕採集狩獵群體的研究)我們能發現呼應史翠山看法的觀點。那麼,我們先回到聘禮的行為上,因為這一定會引起某種與「女性問題」相對的權威問題。
性別與世代
聘禮(bride wealth)是一方(通常是男性家長或親屬)在結婚時給予另一方(通常是女性家長或親屬)的特定物品(通常不只是日常意義上的商品或金錢,也包括特殊物品)。正如我說過的,「聘禮」這個詞或許會讓某些當代讀者覺得這是一個對事實上是把女性當作商品的政治正確委婉說法。在早期,這確實偶爾會被稱為「聘金」(bride price),似乎是一個更加誠實的標籤。然而,早在一九三一年,知名人類學者伊凡—普里查就建議不再採用「聘金」這個詞,因為它帶有很大的誤導性。他的建議的脈絡來自一本重要期刊中進行了兩年多的辯論,其中提出了幾個可能的詞語,有一些非常奇怪。伊凡—普里查認為「聘禮」是最好的詞彙,他也很高興在任何情況下,「聘金」這個說法都沒什麼支持者:
至少在某一點上,專家之間似乎相當一致,即不希望保留「聘金」一詞。把這個名詞從民族學文獻中刪除有著充分的理由,因為它頂多只能強調這種財富在經濟上的功能,卻排除了其他重要的社會功能。而且在最糟的情況下,它讓外行人認為這個脈絡中使用的「金額」和常見英語說法的「購買」是同義詞,也因此相信非洲的妻子像歐洲市場上的商品一樣可以買賣。這種無知對非洲人造成的傷害筆墨難以形容。
伊凡—普里查是對的。正如後來的研究強調的那樣,我們不能假設西方對交換、性別關係及社會人格的理解是普世皆然的。必須對每一點都有具體的了解,才能夠知道聘禮是女性從屬地位、次要地位或商品化的明確象徵。
但這個主題不只如此。因為涉及到權威問題時,聘禮最主要標示出的不是性別差異,而是世代差異。對新娘的關注在幾個方面都具誤導性,尤其是在大多數情況下,聘禮不會留給新娘,而是送給她的父母。事實上,如果我們想找到人類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我們應該要思考年紀,而非性別。年長者似乎總是有話語權。此外,在有些情況下,聘禮是賦予女性權力的來源。
以中國的聘禮為例。過去三十年,閻雲翔一直在研究中國東北村莊社會及文化生活的轉變。從廣義上講,這些可以用他所說的「中國社會的個人化」來描述。許多轉變都發生在一九八○年代,當時中國開始將其經濟往市場路線調整。這種調整日益受到全球化動態的影響,包括想法的流動和個人主義的修辭。閻雲翔也強調,自一九四九年起,中國共產黨實施的政策促成這些轉變,但這往往很諷刺,因為這些政策是基於社群主義和相互關係的社會主義原則。
其中一項政策涉及廢除聘禮。共產黨在一九五○年代禁止婚姻裡的金錢往來。對共產黨員而言,聘禮是種落後的傳統做法,阻擋了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共產黨希望將社會連結從大家庭轉為理想的核心家庭,國家在其中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另一個因素是「孝順」的傳統。在中國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地方,孝道的理想尤為重要,要求人們服從父母。這意味著不僅要尊重他們的意願,在他們年老時照顧他們,人生中的決定(例如嫁娶的對象)也要能反映他們的利益(也就是說,世系的利益)和欲望。然而在強大的主導性國家下,這種價值觀顯然可能分裂忠誠度。事實上,對共產黨而言,他們的目標是用人類學家所稱的「孝道民族主義」取代孝順。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政治領導人經常鼓勵以親屬的角度來思考國家。
聘禮在中國並沒有消亡。一九五○年代,聘禮被宣布為非法之後,當地人想出新的婚姻交易範疇來迴避正式的禁令。但共產黨的宣傳活動發揮了影響力。在文革期間,這種做法的結構被迫發生了重要的轉變。為了減輕政治壓力和審查監督,一九七○年代的家庭開始把聘禮轉移給新娘本人,這種從新娘家族轉至新娘個人的改變,因日後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影響而日益增加。到了一九九○年代,閻雲翔研究的村莊裡,年輕女性已經有來自自由、選擇和權利的修辭的新詞彙來表明她們的立場。支持她們的還有共產黨四十年來挑戰傳統家庭正當性以及曾經無庸置疑的孝道思想的努力。
透過共產主義和資本原則的奇異結合——毛主席和米爾頓.傅利曼的影響似乎是一致的——聘禮成為一種工具,年輕女性可以透過它主張並行使真正的權力。首先,年輕人對婚嫁對象有更大的發言權。這項統計很驚人。在一九五○年代,閻雲翔所研究的村莊裡有百分之七十三的婚姻是長輩安排的;到了一九九○年代,沒有一個是如此。但根據閻雲翔的說法,新娘的複雜程式中有一個新面向更值得注意。在一九九○年代和二○○○年代的不同時期,閻雲翔觀察到準新娘與未來的婆家針對聘禮討價還價,更不用說家庭支持的流動方向了。孝道沒有消失,但它被「父母之心」的理念抵銷——父母及另一半的家長在某些情況下屈從於孩子的欲望及要求。
在閻雲翔的研究中,有個二十二歲的女性案例特別突出。她無禮地和公婆談判,以至於村裡的人認為她很自私,但她不在乎。她告訴閻雲翔:「走著瞧。我有個可愛的兒子,兩頭乳牛,家裡的現代化家電,還有個會聽我話的老公!我公婆尊重我,經常幫我做家事,如果我沒有個性,我不可能擁有這一切。我們村裡的女孩都崇拜我。」
這是「自私」嗎?這是觀點問題。一方面,雖然我們沒有聽到這個表現特別良好的丈夫怎麼說,但新郎通常完全支持新娘的強硬策略,因為他也能因此受惠。這些新的婚姻形式變化是為了支持夫婦,而非個人。不同的團體單位—核心家庭—已經和古老的父系氏族一起變化。此外,這種夫妻在生兒子的問題上經常不會辜負非常「傳統」的期望,其中最主要的期望是認為丈夫和父親(及他的父母)都是父系的延續。
閻雲翔本人也對這種新世代的出現表達出一種失落感和類似遺憾的情緒。但另一種詮釋認為,面對經濟和政治重大變化時,這種權威的轉變是為了努力過著有道德的生活。然而,這也再次表現出現代化的努力經常以看似違反直覺預期的方式,持續依賴傳統帶來的一切。
「女人的問題」
初步蘭群島的布料生產只是故事的開始。正如韋納所指出的,我們在民族誌紀錄中發現,從部落首領的斗篷和席子、皇室的長袍、神職人員的祭服到死者的神聖裹屍布,通常都是政治權威和權力的重要象徵。總的來說,是女人創造了這一切。初步蘭群島的案例事實上相對微不足道。在玻里尼西亞和太平洋的許多地方,布料都是權力、聲望或權威的主要象徵。莫斯認為每個禮物都因其「精神」(在著名的毛利人範例中,這種精神即是「豪」)要求回報。韋納提出要理解這個觀點,我們必須理解毛利人斗篷的政治重要性,就像庫拉珍寶本身也有某種人格和能動性。
然而,撇開所謂片面觀點不說,我們目前看到的許多民族誌確實迴避了父權占主導地位的問題。是的,馬凌諾斯基在他的分析中忽略了女性,但即使是韋納也指出,相較於男性,女性透過布料生產過程享有的權威和主體性依然受限。或是想想榮譽和恥辱,這通常有明顯的性別面向:男人贏得榮譽,而女人失去榮譽。像是巴蘇托族牛的奧祕,女人在這方面便不那麼重要。巴蘇托族男人利用牛的神祕性伸張他們在家戶及社群裡的權威。有人可能想起聘禮的概念,牛的奧祕有很大一部分就在聘禮之上。從維多利亞時代的傳教士到近代女性主義運動中的許多批評者都將這比作視女人為可以買賣的商品。但母系親屬制度呢?這無疑是由女性定義的權威形式。不過在你閱讀有關母系社會的政治關係論述之後,也可以認為這其實是在承認不同的男性在掌權:不是女人的丈夫,而是他們的兄弟。那麼更一般的「血液」呢?我們已經討論過血液是生命力和生命的強大象徵,它也和女性汙染、危險及死亡有關。「現代」瓦西馬婆羅門女性重新定義了經期隔離及禁忌的程度和範圍,但隔離的行為還是保留了下來。而且,許多女性也堅持這麼做。
那麼,文化最終總是會成為父權制度嗎?女性只是第二性嗎?
簡單來說,不;較長一點的回答是:這些是錯誤的問題。這兩個答案都無意否認或淡化男性用許多方式掩蓋女性的社會角色和地位—更不用說女性本身。它也不是在掩飾權力經常存在的醜陋面。關於「不」這個簡單的回答,是為了表明我們不能將性別關係自然化;憑著人類學的良知,並且基於民族誌證據,我們不能說庫拉圈或牛的奧祕,甚至是推動《唐頓莊園》劇情的習俗和繼承法都表明一項事實,即男人總是已經處於或最終總會處於優勢。
至於「這些是錯誤的問題」這個答案,我們要考慮兩點。一是簡單的觀點問題,價值政治
如何形塑我們對權威、聲望和權力的評估。如果我們把布料生產放在論述的中心會如何呢?或是撫養孩子?或者就此而言,大多數地方的大多數小學老師都是女性呢?如果某個地方存在「父權體系」,或者在我們心裡,它反映出類似於前幾章所說在歐洲傳教士和非洲人的相遇時所產生的事情:意識的殖民化。
第二點比較不那麼直接,但可能更重要。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它不是觀點問題,而是是否真實存在任何可感知的固定事物的問題。對某些人類學家而言,假設「男」和「女」是棋盤上的人物,他們和我們一樣在玩同一個遊戲,或者被困在同一個鬥爭之中,便是錯誤所在。
許多人類學家都提出了這個論點,其中瑪麗蓮.史翠山的作品影響深遠。她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作品《禮物的性別:美拉尼西亞的女性問題和社會問題》(The Gender of the Gift: Problems with Women and Problems with Society in Melanesia)將這個論點具體化。史翠山在副標題所說的「問題」與西方分析家對美拉尼西亞性別關係所做的假設有關。這些分析家包括人類學家、女性主義者,還有最重要的女性主義人類學家。對史翠山來說,許多西方對性別關係及男性對女性的支配的批評並沒有考慮到土著觀點,無論是男或女。事實上,史翠山希望我們擺脫這個立場的隱喻,因為它假設我們能分類的所有差異都基於相同的基礎。
在接下來大部分內容中,我想專注討論觀點問題。在兩個例子中(對埃及伊斯蘭教令〔fatwa〕的研究,以及對仄翁〔Chewong〕採集狩獵群體的研究)我們能發現呼應史翠山看法的觀點。那麼,我們先回到聘禮的行為上,因為這一定會引起某種與「女性問題」相對的權威問題。
性別與世代
聘禮(bride wealth)是一方(通常是男性家長或親屬)在結婚時給予另一方(通常是女性家長或親屬)的特定物品(通常不只是日常意義上的商品或金錢,也包括特殊物品)。正如我說過的,「聘禮」這個詞或許會讓某些當代讀者覺得這是一個對事實上是把女性當作商品的政治正確委婉說法。在早期,這確實偶爾會被稱為「聘金」(bride price),似乎是一個更加誠實的標籤。然而,早在一九三一年,知名人類學者伊凡—普里查就建議不再採用「聘金」這個詞,因為它帶有很大的誤導性。他的建議的脈絡來自一本重要期刊中進行了兩年多的辯論,其中提出了幾個可能的詞語,有一些非常奇怪。伊凡—普里查認為「聘禮」是最好的詞彙,他也很高興在任何情況下,「聘金」這個說法都沒什麼支持者:
至少在某一點上,專家之間似乎相當一致,即不希望保留「聘金」一詞。把這個名詞從民族學文獻中刪除有著充分的理由,因為它頂多只能強調這種財富在經濟上的功能,卻排除了其他重要的社會功能。而且在最糟的情況下,它讓外行人認為這個脈絡中使用的「金額」和常見英語說法的「購買」是同義詞,也因此相信非洲的妻子像歐洲市場上的商品一樣可以買賣。這種無知對非洲人造成的傷害筆墨難以形容。
伊凡—普里查是對的。正如後來的研究強調的那樣,我們不能假設西方對交換、性別關係及社會人格的理解是普世皆然的。必須對每一點都有具體的了解,才能夠知道聘禮是女性從屬地位、次要地位或商品化的明確象徵。
但這個主題不只如此。因為涉及到權威問題時,聘禮最主要標示出的不是性別差異,而是世代差異。對新娘的關注在幾個方面都具誤導性,尤其是在大多數情況下,聘禮不會留給新娘,而是送給她的父母。事實上,如果我們想找到人類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我們應該要思考年紀,而非性別。年長者似乎總是有話語權。此外,在有些情況下,聘禮是賦予女性權力的來源。
以中國的聘禮為例。過去三十年,閻雲翔一直在研究中國東北村莊社會及文化生活的轉變。從廣義上講,這些可以用他所說的「中國社會的個人化」來描述。許多轉變都發生在一九八○年代,當時中國開始將其經濟往市場路線調整。這種調整日益受到全球化動態的影響,包括想法的流動和個人主義的修辭。閻雲翔也強調,自一九四九年起,中國共產黨實施的政策促成這些轉變,但這往往很諷刺,因為這些政策是基於社群主義和相互關係的社會主義原則。
其中一項政策涉及廢除聘禮。共產黨在一九五○年代禁止婚姻裡的金錢往來。對共產黨員而言,聘禮是種落後的傳統做法,阻擋了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共產黨希望將社會連結從大家庭轉為理想的核心家庭,國家在其中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另一個因素是「孝順」的傳統。在中國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地方,孝道的理想尤為重要,要求人們服從父母。這意味著不僅要尊重他們的意願,在他們年老時照顧他們,人生中的決定(例如嫁娶的對象)也要能反映他們的利益(也就是說,世系的利益)和欲望。然而在強大的主導性國家下,這種價值觀顯然可能分裂忠誠度。事實上,對共產黨而言,他們的目標是用人類學家所稱的「孝道民族主義」取代孝順。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政治領導人經常鼓勵以親屬的角度來思考國家。
聘禮在中國並沒有消亡。一九五○年代,聘禮被宣布為非法之後,當地人想出新的婚姻交易範疇來迴避正式的禁令。但共產黨的宣傳活動發揮了影響力。在文革期間,這種做法的結構被迫發生了重要的轉變。為了減輕政治壓力和審查監督,一九七○年代的家庭開始把聘禮轉移給新娘本人,這種從新娘家族轉至新娘個人的改變,因日後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影響而日益增加。到了一九九○年代,閻雲翔研究的村莊裡,年輕女性已經有來自自由、選擇和權利的修辭的新詞彙來表明她們的立場。支持她們的還有共產黨四十年來挑戰傳統家庭正當性以及曾經無庸置疑的孝道思想的努力。
透過共產主義和資本原則的奇異結合——毛主席和米爾頓.傅利曼的影響似乎是一致的——聘禮成為一種工具,年輕女性可以透過它主張並行使真正的權力。首先,年輕人對婚嫁對象有更大的發言權。這項統計很驚人。在一九五○年代,閻雲翔所研究的村莊裡有百分之七十三的婚姻是長輩安排的;到了一九九○年代,沒有一個是如此。但根據閻雲翔的說法,新娘的複雜程式中有一個新面向更值得注意。在一九九○年代和二○○○年代的不同時期,閻雲翔觀察到準新娘與未來的婆家針對聘禮討價還價,更不用說家庭支持的流動方向了。孝道沒有消失,但它被「父母之心」的理念抵銷——父母及另一半的家長在某些情況下屈從於孩子的欲望及要求。
在閻雲翔的研究中,有個二十二歲的女性案例特別突出。她無禮地和公婆談判,以至於村裡的人認為她很自私,但她不在乎。她告訴閻雲翔:「走著瞧。我有個可愛的兒子,兩頭乳牛,家裡的現代化家電,還有個會聽我話的老公!我公婆尊重我,經常幫我做家事,如果我沒有個性,我不可能擁有這一切。我們村裡的女孩都崇拜我。」
這是「自私」嗎?這是觀點問題。一方面,雖然我們沒有聽到這個表現特別良好的丈夫怎麼說,但新郎通常完全支持新娘的強硬策略,因為他也能因此受惠。這些新的婚姻形式變化是為了支持夫婦,而非個人。不同的團體單位—核心家庭—已經和古老的父系氏族一起變化。此外,這種夫妻在生兒子的問題上經常不會辜負非常「傳統」的期望,其中最主要的期望是認為丈夫和父親(及他的父母)都是父系的延續。
閻雲翔本人也對這種新世代的出現表達出一種失落感和類似遺憾的情緒。但另一種詮釋認為,面對經濟和政治重大變化時,這種權威的轉變是為了努力過著有道德的生活。然而,這也再次表現出現代化的努力經常以看似違反直覺預期的方式,持續依賴傳統帶來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