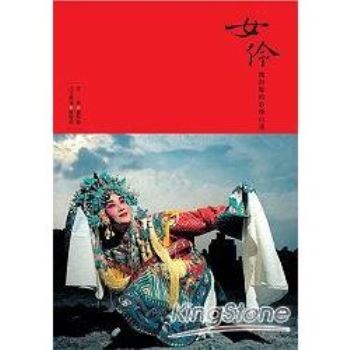從青衣到壞女人
「正月裡,梅花粉又白,大姑娘房裡繡鴛鴦……」
少女懷春的曹七巧,在閨房裡哼著小調,心中想著對街藥房裡的小劉,幻想自己有一天與他成家,兒女成群……
然而,夢想就只能是夢想。這不是曹七巧的人生,她沒有如此這般平凡幸福的機會;她注定要過的,是充滿狡詐、心機,華麗而蒼涼的一生。
遲暮晚年,曹七巧臥在鴉片床上抽大煙,這一生總想留住些什麼,卻也終究都是留不住的啊。鴉片床翻轉,突然讓她憶起了什麼,用已然沙啞蒼老的聲音,哼起了歌。
「正月裡,梅花粉又白,大姑娘房裡繡鴛鴦……」
幕要落下了,一陣掌聲中,我深深吸了一口氣。
還好,我不是曹七巧,我是魏海敏。
我是誰?曹七巧!
「金鎖記」是我從事表演工作30餘年,挑戰性最高的一齣戲。張愛玲筆下塑造的人物,都沒有絕對的好、也不是絕頂的壞;她彷彿在蓋樓房,用一層又一層的際遇與情緒,引領人物走到一個孤絕的境地。
演出張愛玲筆下的人物,已經是一件難事;因為所有張迷都在等著看,看演員落入文字無法轉換的陷阱裡。再加上,曹七巧更是張愛玲筆下所有人物中,性格最複雜的一個。她以低下出身的女性,對抗性別的、階級的不平等,終於學到爭奪的本領;至於那些人生中曾有過的美好與欲求,她逼迫自己遺忘或麻木,只有錢,只有永遠留在身邊的一雙兒女,才能牢牢鞏固她的世界。
剛開始排「金鎖記」時,我很難進入曹七巧的角色。這是我演過反差最大的角色,她是朵土裡開出來的花,太生活化、也太自然了,跟京劇中的角色有極大的差別;再者,她的個性太扭曲,和京劇中的青衣美學背道而馳。
因此,我花了極大的氣力進入這個角色。我必須要說,曹七巧這個女人真是太利害了,她讓我從排戲到演出,一刻不得閒地揣摩她的個性、她的行事風格----在那樣的時代、那樣不友善的環境,曹七巧如何自處?如何掙得一切?又如何將一切毀去?
在那段排戲的日子裡,我常常想像自己就是曹七巧,那句話用什麼語氣?那個動作該怎麼轉身?眼神該虛該實?抬頭該抬到什麼角度?末了,在睡前,腦海中所背頌著,還是那幾句唱腔。
眼尖的觀眾或許能發現,我設計了一個「華麗而蒼涼」的手勢----右手從左手掌中將絲巾抽開,只剩下半空中,一個什麼都握不住的左手。用這樣的隱喻,呼應張愛玲的原著,也表現曹七巧什麼都想留、卻又什麼都留不住的命運。
雖然「金鎖記」的演出十分成功,票房更是告捷,我卻在演出後不斷反省自己的表演方式,覺得還有未臻完美的地方。
曹七巧是「可憐、可愛、可惡、可恨」的女人,我覺得自己掌握了「可憐、可愛」的她,卻依然不夠「可惡、可恨」。
不過,這齣戲一定是會留下來的,將來再有機會再次演出曹七巧,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掌握得更多。
這就是京劇程式化表演方式的可貴之處----藉著一次又一次的演出,讓一個角色更細緻、更紮實,也更立體。
「正月裡,梅花粉又白,大姑娘房裡繡鴛鴦……」
少女懷春的曹七巧,在閨房裡哼著小調,心中想著對街藥房裡的小劉,幻想自己有一天與他成家,兒女成群……
然而,夢想就只能是夢想。這不是曹七巧的人生,她沒有如此這般平凡幸福的機會;她注定要過的,是充滿狡詐、心機,華麗而蒼涼的一生。
遲暮晚年,曹七巧臥在鴉片床上抽大煙,這一生總想留住些什麼,卻也終究都是留不住的啊。鴉片床翻轉,突然讓她憶起了什麼,用已然沙啞蒼老的聲音,哼起了歌。
「正月裡,梅花粉又白,大姑娘房裡繡鴛鴦……」
幕要落下了,一陣掌聲中,我深深吸了一口氣。
還好,我不是曹七巧,我是魏海敏。
我是誰?曹七巧!
「金鎖記」是我從事表演工作30餘年,挑戰性最高的一齣戲。張愛玲筆下塑造的人物,都沒有絕對的好、也不是絕頂的壞;她彷彿在蓋樓房,用一層又一層的際遇與情緒,引領人物走到一個孤絕的境地。
演出張愛玲筆下的人物,已經是一件難事;因為所有張迷都在等著看,看演員落入文字無法轉換的陷阱裡。再加上,曹七巧更是張愛玲筆下所有人物中,性格最複雜的一個。她以低下出身的女性,對抗性別的、階級的不平等,終於學到爭奪的本領;至於那些人生中曾有過的美好與欲求,她逼迫自己遺忘或麻木,只有錢,只有永遠留在身邊的一雙兒女,才能牢牢鞏固她的世界。
剛開始排「金鎖記」時,我很難進入曹七巧的角色。這是我演過反差最大的角色,她是朵土裡開出來的花,太生活化、也太自然了,跟京劇中的角色有極大的差別;再者,她的個性太扭曲,和京劇中的青衣美學背道而馳。
因此,我花了極大的氣力進入這個角色。我必須要說,曹七巧這個女人真是太利害了,她讓我從排戲到演出,一刻不得閒地揣摩她的個性、她的行事風格----在那樣的時代、那樣不友善的環境,曹七巧如何自處?如何掙得一切?又如何將一切毀去?
在那段排戲的日子裡,我常常想像自己就是曹七巧,那句話用什麼語氣?那個動作該怎麼轉身?眼神該虛該實?抬頭該抬到什麼角度?末了,在睡前,腦海中所背頌著,還是那幾句唱腔。
眼尖的觀眾或許能發現,我設計了一個「華麗而蒼涼」的手勢----右手從左手掌中將絲巾抽開,只剩下半空中,一個什麼都握不住的左手。用這樣的隱喻,呼應張愛玲的原著,也表現曹七巧什麼都想留、卻又什麼都留不住的命運。
雖然「金鎖記」的演出十分成功,票房更是告捷,我卻在演出後不斷反省自己的表演方式,覺得還有未臻完美的地方。
曹七巧是「可憐、可愛、可惡、可恨」的女人,我覺得自己掌握了「可憐、可愛」的她,卻依然不夠「可惡、可恨」。
不過,這齣戲一定是會留下來的,將來再有機會再次演出曹七巧,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掌握得更多。
這就是京劇程式化表演方式的可貴之處----藉著一次又一次的演出,讓一個角色更細緻、更紮實,也更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