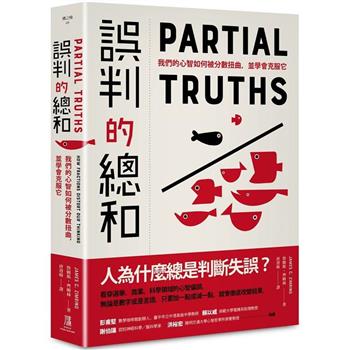第三章 確認偏誤
我們的心智如何根據既有信念來評估證據
死刑是意見兩極的政治議題。因為人犯了罪而把那人殺掉,有著長久深遠的歷史。在至今仍行使的一套最古老的法制系統──英國法的脈絡中,處決一度極為普遍。1800年代的人會因為超過兩百種不同的犯行而遭處決,包括擅闖他人土地時穿著偽裝,或有強力證據顯示孩童有犯意(你沒讀錯,不是對孩童有犯意,而是孩童有犯意)這類雞毛蒜皮小事。自從那高峰過後,能處決人的犯行就日漸減少。當前除了美國以外,沒有哪個工業化國家會處決囚犯;該國五十州裡有二十七州有死刑法律。從全世界來看,一百九十五個國家中有五十六個有死罪並實際執行死刑。
關於死刑的爭論,一般包括能否嚇阻犯罪的問題。換言之,死刑能否降低適用死刑的犯行之犯罪率?想一想你目前對這議題的看法。相關資料很複雜。
就美國死刑來說,克隆諾(Kroner)和菲力普(Phillips)的研究,比對了其中十四州在採用死刑前後一年之間謀殺率是否有差異。十四州當中,有十一州的謀殺率在採用死刑後降低。因此,該研究支持死刑的嚇阻效應。由帕瑪(Palmer)和克蘭達爾(Crandall)進行的另一個研究,則比對了十對有著不同死刑法律的相鄰州。而在十對相鄰州中,有八對出現死刑州謀殺率較高的情況。這個研究反駁了死刑的嚇阻效應。考量這些研究結果後,你現在怎麼看?這些資料如何影響你對於「死刑是否有嚇阻力」的信念,又為何影響了你?花點時間來想想吧。
這個練習源自於1970年代晚期在史丹佛大學進行的一個心理實驗。該研究是對兩組研究生進行,而在幾周前就已根據課堂上針對既有信念的問卷,將這兩組人識別出來。第一組人支持死刑,並覺得死刑有嚇阻作用;第二組人則持相反看法。來自這兩組的一些受試者,混同研究人員一起圍著大桌子坐下,執行實驗的人不知道哪個受試者屬於哪組。每位受試者都被告知,他們會拿到兩張隨機選出的索引卡,標示著二十項有關死刑嚇阻效果的研究。卡上會顯示其中一項研究的結果。受試者被指示要讀第一份研究,以此評估他們的想法是否被改變,以及如果有的話是如何造成的;接著再讀第二份研究,再次評估想法是否被改變,若有的話又是如何造成(受試者在計分量表上替自己的信念評分)。
但其實所有受試者閱讀的是同樣兩份研究的描述,而這兩份研究皆為虛構,但刻意寫成具有「會在司法判決引用的當前文獻中找到的那種研究之特徵」。實驗結果是,兩組人馬在閱讀了索引卡之後,都增進了對自己最初立場的信念。換言之,以完全一樣的方式呈現出同樣資訊,可同時強化大相逕庭的兩種對立看法。重要的是,這不是研究的內在性質(亦即某一份比另一份嚴謹)所造成的,因為當研究者把虛構研究的研究結果互調之後,還是會出現一樣的效應。這也不是受試者閱讀研究的順序所致;研究者也控制了這部分。
同一份資料怎麼有辦法同時支持相反互斥的看法?受試者對閱讀過的研究寫下評估,而他們的回應揭露了一個清楚的效應,那就是:每一組人馬都把支持自己先入為主看法的研究評分為高品質,而把反對的研究評為低品質。此外,這還不只是陳述偏好的問題而已。受試者給出了非常具體的理由,說明他們為何偏好某些研究勝過其他研究,也評論了實驗設計、研究時間長度、接受比對團體的隨機化,以及自變項的數量。這些都是研究中應考量的適當科學問題;然而,它卻提出一個疑難問題。受試者並沒有把研究的優缺點認定為研究本身造成的結果,而是當成研究結論是否合乎受試者既有信念造成的差異。
我們正在描述的效應有別於前兩章提出的效應。在這種情況下,人人接觸的是一樣的資料,但卻會根據接觸資訊前的想法而以不同的方式評估。這種下意識的程序稱作「確認偏誤」,被描述為「以偏袒既有信念、期望或手上某個假說的方式,來尋求或詮釋證據」。人們面對遇到的證據時,並不是客觀的觀察者;我們觀察世界的方式,反而受到我們早已相信的東西所影響。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並不是「眼見為憑」,而是「眼見所信」。
如果你覺得你的看法受到現有證據的強力支持,而反對的證據沒有,那麼你最好重新思考。情況或許真是如此,但不管真實情況是否如此,你可能都會這麼覺得。那些反對你看法的人,可能也一樣深信既有證據證明他們的看法沒錯,而你的沒有。
儘管「確認偏誤」這個詞要到1960年代才由瓦森(Peter Cathcart Wason)發明,但人們早就發覺到人有確認偏誤的傾向。早在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西元前431~404年)時,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寫道:「人有種習慣,就是把渴望的事物寄託於粗率的希望上,並使用獨斷的理由來把不想要的事物推到一邊。」二千二百年後,我們身上還是有這個傾向,就如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談起在森林中尋找特定某類植物時所言:「我們在擁有某個想法並開始相信這想法以前,是沒辦法看到任何事物的――而那之後,我們就很難再看見其他事物了。」
確認偏誤的正式實驗研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開始。尼克森(Raymond S. Nickerson)於1998年對這主題寫下一份傑出而詳盡的評論,雖然在那之後人們於確認偏誤的認識一直都有所進展,但沒有人比他更能刻劃該問題的深度和廣度。[8] 確認偏誤的一個特點是:在人心中,支持某信念之證據的分量,會高過反駁某信念的證據分量――人並不會公平地權衡所有證據。用尼克森的話來說,就是「一旦某人對某議題採取了一個立場,他的首要目標就變成替該立場辯護,或者為該立場賦予正當理由。也就是說,不論一個人在採取立場之前對待證據有多公正無私,在採取立場之後,便會變得十分偏頗。」比這更極端的是,當人遇到反對其信念的證據時,人可能不只會忽視該證據,甚至有可能會用該證據來增強他們對於「該證據駁斥的事物」的信念。
舉凡注意美國激烈政爭辯論的人,都免不了看見確認偏誤即時在眼前開展。梅西耶(Hugo Mercier)和斯珀伯(Dan Sperber)特別指出,人不是只會對任何碰巧出現在腦中的想法尋求肯定而已。他們也很擅長替違反自身既有信念的想法尋找否定證據。出於這個理由,梅西耶和斯珀伯偏好使用「我方偏誤」(myside bias)一詞,而它似乎很適合當今世界。你可以在同一晚花上一小時,看看政治傾向不同的新聞(在美國,可能是福斯新聞[Fox News]、CNN和MSNBC)。你一定很難相信這些新聞是在報導同一起事件。任何國家都能觀察到這種關於不同資訊來源的現象。用尼克森的話來說,
許多人已經寫過這種偏誤,而且這種偏誤看來夠強大也無所不在,以至於人們會去想說,能不能光憑這種偏誤來說明大部分發生在個人、團體和國家之間的爭論、爭吵和誤會。[12]
人們可能會有更憤世嫉俗的看法,認為有些新聞出處是刻意偏誤,是幕後有特定意圖的操縱者的宣傳工具。當然,情況有可能確實如此。然而,因為有確認偏誤的存在,所以在解釋意見的差異時,情況也未必就是如此。當然,這些選項並非互斥的;兩種因素都有可能正在運作。
確認偏誤是無心之過,對於自利一無所知
對人類行為和思考的分析揭露了各式各樣的偏誤。我們的一般對話,常包含許多對於種族、宗教、年齡、性別、族群和性偏好(以及其他多種)偏誤的擔心。偏見和歧視這類用詞,常用來指涉這類偏誤。然而,確認偏誤的本質打從根本就不一樣。確認偏誤並非一種信念。確認偏誤是種程序,我們藉著這種程序來強化我們的信念――任何信念都行,而不去管那信念的源由或正確性。
我們最初的信念來自幾個不同源頭(我們觀察到的事物、我們閱讀的內容、別人跟我們說的事、我們夢到的事物、我們推理的事物、直覺以及心念一動)。我們活著就會有持續不斷的經驗,而它們有可能會符合我們的信念(也可能不會)。人可能會以為人類會根據持續不斷的經驗來調整自己的信念,但有了確認偏誤,我們反而會根據我們的信念來調整我們的經驗。因此,不論信念的起源為何,確認偏誤幾乎是所有信念能夠維持下去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