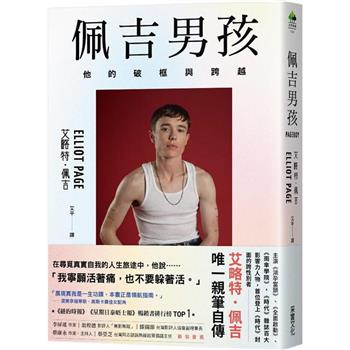2. 性向猜猜樂
艾倫.佩姬性向猜猜樂——我掃過標題,臉上失去血色。這是《鴻孕當頭》人氣正旺時,《村聲》(Village Voice)雜誌登出的一篇文章,作者是麥可.穆斯托(Michael Musto)。我迅速掃過文章內容。麥可對一位二十歲少女的性向大加臆測,並做出總結:「早就該爆出來了,她到底是不是?就是那個,你知道的,蕾絲邊嘛!她的穿著打扮的確很……你懂的,很T……讓我們來把這些臭女同志的線索串起來吧。朱諾到底是不是『那個』?」
一夕之間,我成了眾所矚目的焦點,但早在我還住加拿大的時候,「臭女同志」這個稱號便屢屢在成長過程中出現。上了高中後,霸凌招數翻新,從班上人氣女孩的冷嘲熱諷,變成強押我進男生廁所這種相對戲劇化的舉動。我被推進去,陌生而刺鼻的尿味撲來,我豎耳等待,等他們的笑聲散去、越盪越遠——離開時卻迎面撞上板著一張臉的英文老師,嚴肅地盯著我說:「去我辦公室!」我道歉,沒說我是被逼的。
霸凌升溫的不久前,為了參加足球比賽,我和一位名叫費歐娜的女孩成了室友,一起住在聖法蘭西斯薩維爾大學(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的宿舍裡。該所大學位於安蒂崗尼希市(Antigonish),就在加拿大新斯科細亞省(Nova Scotia)的西北端,距離布雷頓角(Cape Breton)只有幾步之遙。學校會定期舉辦蘇格蘭境外現行最久的蘇格蘭高地運動會(Highland Games)。
我至今仍記得費歐娜的笑聲。我能從一片噪音中辨認出來,她的笑聲會穿過所有雜訊,鑽入我的雙耳,在我身體裡膨脹。我很想靠近她,想要她渴望我。我是隊上的右翼中場,速度快,個頭矮小但拚勁十足。她則是清道夫,我們隊的最後一道防線,同時也跟踢中路中場的球員一起擔任雙隊長。她是天生的領導者,有威望,但為人親切。她很罩。我愛看她踢球——強勁、流暢,而且帶著一股令我羨慕的自信。我深深著迷。
我們躺在硬邦邦的床上,各自占據房間的一側,牆面覆著一層廉價的深色木材。我盯著天花板,深吸一口氣,不確定要憋著,還是吐出來好?這種感受相當奇妙,彷彿在偷看一種未來的可能性。
「我覺得我可能是雙性戀。」我沒頭沒腦地說,從來沒對任何人吐露過類似的話。
「不,你才不是。」她立刻回應,是個下意識的反射動作,並且咯咯笑了起來。
這一次,她的笑聲既無情又刺耳,但我還是想和她一起笑。同性戀真是可笑又糟糕,不是嗎?光是在健康教育課上出現「同性戀」這個詞,就會引發一陣竊笑,放學後回家看的那些情境喜劇更是雪上加霜。每次別人或我自己拿同志開玩笑,那個玩笑都會堵在那裡,像是卡在鞋底上的屎。聚光燈從舞台右側移到舞台左側,我會圍著它跳踢踏舞,像條落水狗,急著想甩掉它,把它甩出去。
我想不起來之後我們又聊了什麼,只記得迴盪的笑聲,還有硬邦邦的床面。
我睡不著,凌晨五點左右溜到亮著日光燈的走廊上,坐在地上看起書。美國小說家馮內果(Kurt Vonnegut)是我這輩子第一位真正喜歡的作家。我正在讀《夜母》(Mother Night),一本談論道德灰色地帶的小說,馮內果寫道:「我們是我們所假扮的樣子,所以我們得小心選擇要假扮什麼。」我獨自坐在走廊,咀嚼著這些字句。恥辱感以穩定搖擺的頻率在我體內震盪。有什麼東西正在從我的指縫間流失,不可能抓得住。我靜靜等待太陽升起。
所有人都會在公共區域一起吃早餐。菜色有提姆霍頓咖啡店的貝果,以及一大袋某位家長送來的柳橙。大人會在一旁看著我們,邊享用著他們的咖啡。我安靜地用餐,不知道該怎麼面對費歐娜,覺得還是先避開比較好。我抓起護脛,打算早點去球場為比賽暖身。
「臭女同志。」從某處傳來的詞彙賞了我一記耳光,還搭配上某種我日後會相當熟悉的惡劣嘲諷表情,彷彿在幸災樂禍:哈,我跟你才不一樣。說話的人是費歐娜一位人緣好的朋友。真的很傷人。那是種被孤立的痛,一句看似無心的話,實則難以抹滅。
生活在那之後就變了調。某些東西被斬斷。我能察覺那些交頭接耳,那些能量的轉變,還有流言蜚語。也許是好事?搖搖欲墜的牙總得拔掉。
如果艾倫是女同志怎麼辦?
幾個月之後,爸爸和我回新斯科細亞省的洛克港(Lockeport)拜訪奶奶,那是個位於南岸區的小漁村,人口只有五百多人。一艘艘漁船停在港邊,沿著長長的碼頭排成一列,船身顏色彷彿聖誕節的彩燈。磨舊的黃,褪色的紅,各種不同色調的藍。一張新斯科細亞的明信片。
我還小的時候,每年的七月一日,爸爸都會帶我回洛克港。這是個在我家鄉被稱為「加拿大日」的節日,和美國的獨立紀念日很像,但少了一點從皇室獨立出來的味道,更像是「加拿大的生日」。身為一個從小在新斯科細亞長大的白人小孩,我對我們的歷史和定位一無所知。無論是過往犯下種族清洗的嚴重程度、系統性的種族歧視,或是種族隔離制度,都沒有人教過我。
我以為加拿大日不過是放放煙火、走走遊行、在教堂地下室吃吃草莓海綿蛋糕的日子,加上我最喜歡的活動「爬油柱」──一根又長又細的圓木平放在碼頭上,一端朝海港突出,離水面有一大段距離。堅硬的木頭上塗滿厚厚一層豬油。伸向大海那側的圓木末端放著另一大塊豬油,底下壓著一堆現金,讓參賽者去搶。說穿了,只有兩種方法能做到:第一種,趴著過去,速度要慢,小幅度地向前移動,然後再慢下來,但這種方法通常都以失敗收場。第二種,成功的關鍵似乎是盡可能用最快的速度滑行出去,盡可能地把錢掃下去,然後投奔大西洋的冰冷懷抱。浮上水面後,在酷寒的海水中撿拾那些掉下的鈔票。海鷗會在上方盤旋,朝漂浮在海面上的豬油俯衝。不,我從來沒試過。
奶奶還住在爸爸從小長大的那棟房子。那是一棟兩層樓的矮房,有三間臥室和白色的牆板。房子的後方是森林,一望無際的森林。對街則是我爺爺的雜貨店,佩吉商店。這家店至今還在,雖然我不確定店名現在叫什麼。他們裝了一台加油機。
二樓的臥室之間有一座長型的衣帽間,可以從一間通往另一間。我還小的時候常常躲進裡頭,想像自己舞進一處異想世界,門是那麼的小,彷彿為我量身打造。我會拉扯燈泡上的鍊條開關,讓裸露在外的燈泡照亮我的寶物收藏。這一幕非常有演電影的感覺。我會察看一箱箱子彈,仔細檢視,眼睛瞇得像位珠寶商,對於如此小的物品竟能殺死穿梭於森林的雄鹿而感到著迷。牠們健壯的身軀高速奔馳,看起來雄偉至極,不可能被這麼迷你的物品擊潰。
「丹尼斯,如果艾倫是女同志怎麼辦?」奶奶趁我們都坐在她的陽光玻璃房時問我爸爸。她的語氣和平時發表種族歧視言論時一樣尖銳。倘若套用艾拉妮絲.莫莉塞特(Alanis Morissette)版本的諷刺來做總結,說這句話的奶奶,與我剛出生時,送一隻爪子和耳朵上印著彩虹的熊玩偶給我的奶奶,是同一個人。那時的我十六歲,剛為一部接演的電影剃頭。電視轉播著多倫多藍鳥隊的比賽,棒球是奶奶最喜歡的運動,而她最支持的球隊是多倫多。還是波士頓?那次是她過世前我最後幾次見到她。我很好奇,假如她現在還活著,會對她的孫子有什麼看法?我不覺得她還會挑彩虹的款式。有些人確實是會變的。
在好萊塢,被藏起來的小酷兒
《鴻孕當頭》大紅時,恰好是諸多同業告誡我千萬別對外張揚同性戀身分的時候。他們說那樣做對我不利,該為自己留後路,要相信這麼做對我最好。所以我穿上禮服,化好妝,給攝影師拍照,將寶拉藏起來。
我受憂鬱症所苦,恐慌症發作得厲害,劇烈到快要崩潰的程度。我幾乎無法正常生活。麻木、沉默,胃裡彷彿有根釘子,我無法開口訴說自己有多痛苦,畢竟「我的夢想成真了」,至少別人是這樣說的。我打發自己的感受,嫌自己小題大作,譴責自己不知感激。我太過愧疚而不敢承認自己受傷了、失能了,不敢承認我看不見未來。
讀完穆斯托的文章後,我打給經紀人,但最後,我們只獲得一篇後續的部落格文章,裡面詳細記載了他們的談話內容:「『懷疑一個人是不是同性戀,又不是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我氣得大喊。」說得沒錯,揣測他人是不是同性戀,既不傷天,也不害理,但此舉之所以輕率又危險,是因為寫作者忽視了被議論的那位年幼酷兒究竟經歷過什麼。
《鴻孕當頭》在多倫多國際影展首映上獲得相當熱烈的迴響。當時的我並沒有聘請私人公關,這是因為先前發生過一件事,讓我決定自己來。有名純真的青少年問:「你看過《西娜公主》(Xena)嗎?」卻獲得公關這樣的回答:「沒有,因為我不是女同性戀。」我很高興不必再和那位公關共事,她的回答完全體現了好萊塢為人詬病之處──虛假、空洞、恐同。話雖如此,我還是沒有準備好,也沒有足夠的經驗能獨自駕馭這突如其來的人氣。
在加拿大以演員身分長大的感覺很不一樣,尤其是我小時候那個年代。加拿大並沒有凡事追求光鮮亮麗的文化,也沒那麼迷戀閃閃發亮的東西。那些不得不包裝自己的要求,是在《鴻孕當頭》之後才出現的。
我原本打算穿牛仔褲和一件「類」西式的襯衫去參加《鴻孕當頭》的全球首映會。我覺得這樣搭配很不賴,而且有領子。不錯看吧?我心想。福斯探照燈影業(Fox Searchlight Pictures)的公關團隊得知我的造型後,緊急把我抓去布魯亞街(Bloor Street)上的霍爾特倫弗魯精品百貨公司,搞得一陣雞飛狗跳,完全是標準的好萊塢作風。我建議穿西裝,但他們說我應該穿禮服配高跟鞋。他們和導演討論了一陣後,我接到導演的電話。他同意他們的看法,堅持要我乖乖配合。另一明主演麥可.塞拉(Michael Cera)身穿運動鞋、休閒長褲和有領襯衫亮麗登場。我覺得他這樣穿很時髦。我很想知道,他們為什麼不帶他去百貨公司?我猜,他大概沒什麼需要遮遮掩掩的吧。他獲得認可,他做得很好。
被迫覺得自己不夠好、不正確,是一個需要被藏起來的小酷兒,同時,卻因為如此否定自己而受到大眾喜愛,這整個狀況成了一道滑坡,我記不得自己是從何時開始一直向下滑落。它就像一層黏在肌膚上的薄膜,怎麼洗都洗不掉。一股衝動湧現,想要把身上的肉給撕下來,這股衝動像是一種斥責——我變得跟身上的肉一樣令人生厭。
我待在洛杉磯的時間越來越長,參加《鴻孕當頭》記者會、會議,以及實際上整整為期兩季的「頒獎季」。在新斯科細亞,另一家媒體深入調查了我的性向,也許是想要打敗穆斯托的那篇「性向猜猜樂」。《法蘭克》(Frank)是一本總部位於哈利法克斯(Halifax),自一九八七年起發行的「雜誌」。他們視自己為時事諷刺型雜誌,其實更像是八卦小報。當時我人正在聖塔莫尼卡(Santa Monica),接到爸爸打來的電話,說我登上了封面。那是一張我在日舞影展的照片,上頭壓著大大的標題,寫著——艾倫.佩姬是同性戀嗎?
我當場崩潰。坐在朋友開的民宿的床上,我緊閉哭溼的雙眼,臉上沾滿淚水。拜託,請讓這一切只是場夢。求你了。
回到哈利法克斯後,我發現這本雜誌無處不在,雜貨店、加油站、街角商店……到處都是它的蹤影,無不站在架上問著同一個問題——艾倫.佩姬是同性戀嗎?寶拉會把它們翻到背面,藏在其他雜誌後面。有一次她還偷走了南岸區一間加油站的整落庫存。
那個夏天,我和寶拉在一起所嘗到的自由滋味,即將劃下句點。
寶拉的身影出現在報導的某張照片中,那是我們幾個人在一場派對上的合照。我至今依然記得那晚,我們聚在哈利法克斯其中一棟大樓公寓裡,那是一棟路上越來越常見、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大樓。該篇報導針對我們兩個是否正在交往有諸多臆測,仔細羅列各方流言。寶拉那時還沒向家人出櫃。我盯著那張照片,頓悟了一件事:照片一定是某個朋友流出的。我至今仍不知道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