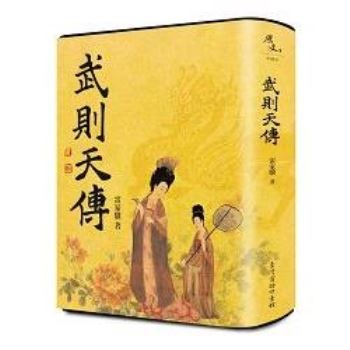第一章 武氏家世
文水武氏的家世
平林漠漠煙如織,長安京城籠罩於黃昏冥色之中,使者一行來至應國公宅。應國夫人楊氏率其家人拜舞接旨。使者展開詔書宣讀:
「於戲!惟爾武士鑊第二女,幼習禮訓,夙表幽閑,冑出鼎族,譽聞華閫,宜遵舊章,授以內職,是用命爾為才人。往欽哉,其光膺徽命,可不慎歟!」
這年是大唐貞觀十二年(638),武士鑊第二女明空,行年十四歲。她奉詔入宮,使大唐國祚改寫的命運,正悄悄地步上了歷史的舞臺,中國歷史也展開了空前絕後的一頁。唯一的女皇帝-是開國皇帝,同時也是亡國皇帝,而且是一個迄今仍有爭議的女皇帝,將從此揭開她自己乃至國史的新里程。
大唐開國至今已經二十一年,王室婚姻,皆取當世勳貴名臣的子女為對象。武明空的父親故利州都督.應國公武士彠是十六位「太原元謀勳效功臣」-唐朝開國功臣-之一。武士彠於隋朝煬帝大業十三年(617)追隨太原留守李淵起兵反隋,一路攻入關中,佔領西京長安,建立了唐朝,年號武德。武德元年(618)八月六日,皇帝論功行賞,分太原起義幹部為兩等功臣,均賜以「太原元謀勳效功臣」的勳號。其中第一等功臣只有兩人,第二等功臣則有十四人,武士彠名列二等功臣,當時他的職官是中央最高行政機關尚書省兵部的庫部郎-亦即兵部四司之一庫部司的司長。庫部司職掌全國武器軍備設施的政令,司長位列正五品,屬於政府的清要官。當時國家初建,群雄并列,戰爭方殷,士彠掌管全國的武器軍備設施,位任可謂重要。
武士彠是功臣,當然有「勳」;但是庫部郎位任縱然重要,卻也還算不上是「貴」。直至武德三年(620),士彠昇為正三品部長級的工部尚書,同年武德皇帝將軍隊作了一次調整,把關中的主力部隊劃分為十二軍,各給予軍號,原駐在醴泉道的改稱為井鉞軍。武士彠大約在這時曾經一度兼統此軍為軍將,稍後又以本官檢校右廂宿衛的禁軍。唐朝官僚制度,三品以上就是國之大臣,掌握大權的行政中樞是尚書省,由尚書令、僕射和六部尚書組成權力核心,世稱八座,而工部尚書即是尚書八座之一,可見武士彠已經躋身政府高層。十二軍是唐朝政權的核心武力,士彠兼統其中一軍,甚至又指揮右廂禁軍,更見武德皇帝對他的信任與重用。也就是說,從武德三年以後,武士彠已經名符其實的是「當世勳貴」,所以其女日後被召納入宮,應不至於意外。
不僅如此,武氏在太原附近的文水縣聚族而居,士彠的兄弟和宗人對唐朝的開國也有一定的功勞,而成為「太原元從」。
他的長兄武士稜原來務農,追隨起義,官至司農少卿,封宣城縣公,武德皇帝利用他的專長,令他常居苑中,主持農囿之事。士稜之子君雅襲爵,官至鎧曹參軍,其子希玄後亦襲爵,為貞觀皇帝的右勳衛。次兄士逸也有戰功,武德初為齊王府戶曹,封安陸縣公,後來累授益州行臺左丞。又有文水宗人武恭,也是唐朝元從,制授諫議大夫。
可見文水武氏可能有一批人,因為武士彠之故,追隨武德皇帝李淵太原起義,立有大小不等的功勳,至此都已做官。是則文水武氏在唐初政壇,應有一定的份量。後來李敬業起兵反武,駱賓王為他撰寫〈討武氏檄〉,聲討當時臨朝武太后之罪,竟至說她「地實寒微」,實際上是政治文宣的因素居多。不過就社會的角度看,駱賓王的說法事實上也頗有他的根據,不至於完全誣蔑武家。中國從魏晉南北朝以來,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階級,他們世代做官,依照他們世代官位的高低,高的形成了大士族,或者稱為世族、大姓、高門,次者成為小姓,先世沒有做官的則是寒素。世族高門掌握,甚至壟斷了社會和政治的資源,即使到了南北朝後期和唐朝前期,他們的家人已經很久沒有做官,但是其社會地位也還沒有消失,僅只是政治上的衰敗門戶而已,一般人仍然不惜花大錢和他們的子女結婚,攀附他們的門第。這種現象世稱「賣婚」-就是買賣婚姻。中國人好面子重身份,只要能力所及,對婚喪二事大都極盡奢華舖張,自古已然。唐朝人選擇婚姻有三個標準-門第、財富和功名,而以門第為第一優先。如今為了抬高自己身份,不惜慕人祖宗,攀附他人門戶,所以武德皇帝之子貞觀皇帝-也就是著名的唐太宗-在即位後對此風氣極為痛惡,予以嚴厲批評,說是無禮和無恥,下詔修《氏族志》,必須以尊「崇我唐朝人物衣冠」作為評定門第的標準,書成頒行於天下;然而社會觀念植根已深,風尚依舊,也沒有為之改變。這一年正是明空奉詔入宮之年。
依照這種社會觀念與標準,武家的確不是高門大姓。
根據後來李嶠奉大周女皇敕令所寫的〈攀龍臺碑〉和《新唐書》卷七四上的〈宰相世系表〉所述,武氏係并州太原郡文水縣人,出自姬姓,是周平王少子之後。因為周平王少子生時手上紋理有一「武」字,後代遂以武為姓氏。降至武明空第八代祖武念,官拜北魏洛州刺史.歸義侯。七代祖武洽,官至北魏平北將軍、五兵尚書、晉陽公,別封大陵縣。此下五代祖武克己、高祖武居常,皆曾襲繼壽陽公之爵。大陵在隋朝改稱為文水,故成為文水縣人。
又據〈宰相世系表〉,武明空從七代祖武洽已下,直系均有任官的記錄:
六代祖神龜為祭酒,
五代祖克己為本州大中正、司徒.越王長史,
高祖居常為北齊鎮遠將軍,
曾祖儉為北周永昌王諮議參軍,
祖父華為隋東都丞,
父士彠為唐工部尚書,封應國公。
基本上,除其父親以外,即使所載是真的,武明空自第五代祖已降,所任都是幕佐之官,算不上是顯宦之家,因此也算不上是閥閱高門。不過,除非有史料可以推翻〈宰相世系表〉的記載,否則文水武氏儘管不屬於高門大姓,但是也不至於如〈討武氏檄〉所說的「地實寒微」。武明空「革命」當了大周皇帝後,曾於聖歷元年(698)八月,命令姪孫武延秀入突厥和親,突厥可汗默啜告訴來使說:「我世受李氏恩,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並且移書說:「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小姓,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外國元首罵武周王室為「小姓」。小姓的社會門第不及大姓,但卻也不至於寒素,或者可以反映文水武氏當時社會地位的真相。無論如何,文水武氏在當時傳統社會中,僅能屬於小姓等級的門第;但是在她入宮之年以後,則因是新貴而屬於甲族,不過猶未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可。武士彠傳奇性的發跡和發展
武士彠是武華的第四子,鄉里民間傳說他是一個經營林業的木材商人;不過〈攀龍臺碑〉卻說他出生時就有帝王之象,才兼文武,人格如何高,學識如何優,材幹如何好,這麼多優點令他名動當世朝,使到隋文帝屢加辟召,司徒楊雄、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宏、兵部尚書柳述等公卿大臣,爭相向他抗禮求教。李嶠奉命寫〈攀龍臺碑〉之時已經是大周王朝的時代,此碑是女皇為頌揚其父武士彠-這時已追尊為「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帝」-人格功德之碑,後來唐朝史臣修撰國史之時,懷疑它和舊史有「過為褒詞」和「虛美」之嫌,不足予以深究,不免對武士彠的事跡大加刪削,以至也有過為刪削之嫌。
事實上,文水武氏是地方上的小姓,子弟們也不一定都出仕做官。根據史書的記錄,南、北朝以降門第子弟窮哈哈或無仕者,所在多有,不算稀奇。青年時期的武士彠,經營木材很可能即是他的生意之一,所以史書說他「家富於材,頗好交結」。近世有些學者據此推論武士彠以鬻賣木材為業,是木材商人,值隋朝屢興鉅大土木工程,因而致富,因此判斷他是投機善賈之流。經商致富之說,大抵可信。筆者以為,投機是善賈之能事,好交結應酬也是商場的常習,根據士彠的發跡事跡看,他的確是能觀時通變之人,這也正是他的長處所在,使他所以能成為唐朝的開國功臣。
武士彠經商致富與隋煬帝即位後大興土木以事建設有關,其中重大工程之一是營建洛陽為東京。大業元年(605)營建東京既是重大的工程建設,遂由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兩位宰相分別擔任營建的正、副使-楊達後來就是武明空的外祖父。大約明空之父武士彠販賣木材入東京,利用關係與財富,常與權貴交結,一時傾動當朝。其間,他曾招致楊素的猜忌,想構以禍端,幸虧他經商的優點適時發揮作用,因為交結廣、神通大,得到楊雄、牛宏等權貴的營護而免於禍,從此深自隱匿,以求自保。無獨有偶,後來女皇的情夫張易之兄弟,也曾利用他們的權勢販賣木材及其他買賣,為時人所側目與批評,給女皇帶來了危機。
楊素向來負冒財貨,營求產業,在東、西二京和諸方都會處,置有物業以千百數,素為時議所鄙。是則士彠因為經商應酬而得罪了楊素,應有可能。總之,武士彠曾經得罪楊素而逃隱,極可能是一個事實,因為女皇革命之後,曾下制禁錮楊素及其兄弟的子孫,不許他們擔任京官和侍衛,也許與此事有關。
士彠逃隱後開始注意局勢的變化,及至隋煬帝大業七年(611)對高麗用兵失敗後,國內亂局開始擴大,反隋起義逐漸蜂起。在這種環境氣氛之下,士彠遂想到要出山,決定往事功方面發展。不論他的真正動機究竟如何,這時煬帝實行廣募驍勇、掃地為兵的政策,士彠參與隋軍,可見他是有志從軍立功,以求仕宦的。
士彠在此之前沒有任何資歷,出山後當上了鷹揚府隊正。隊正統領五十人,是府兵制的最低常制長官。〈攀龍臺碑〉對武士彠在隋末的軍事表現著墨極重,用以表彰父親的軍功,其目的是透過頌揚先人的積德累功,作為武周早有天命的論述依據,遂使此碑所述有過為褒詞和虛美偽冒之事。碑誌在中國一向是用以諛美死人的,只要不過份相信,也就無傷大雅。
鷹揚府隊正只是一個小軍官,而太原留守李淵則系出隴西李氏,是今上(隋煬帝)的表弟,身份官爵俱高,武士彠怎樣結交上他,以致成為唐朝開國功臣?根據〈攀龍臺碑〉的說法,士彠要出山時,諸兄素聞李密-當時反隋群雄之最有實力者-之名,乃勸他前去投靠。「李密雖有才氣,未能經遠,欲圖功業,終恐無成」,士彠告訴他們。顯然他的出山不是要自立山頭,而是要投靠明主,以「圖功業」。適逢此時(大業十一年,615),李淵奉詔往山西討捕起事人民,撫慰地方。他行軍於汾、晉之間,休止於士彠之家,因蒙士彠顧接,乃得以結交。至十三年(617),李淵奉詔坐鎮太原為留守,於是引用士彠為行軍司鎧,成為留守府主管軍事裝備的幕僚。所以後來攻入長安,他就順理成章地官拜庫部郎,掌管全國的武器軍備設施。
士彠雖為留守李淵所引用,卻是副留守王威之黨,不是李淵的心膂之託。士彠觀察李淵,以為此人「雄傑簡易,聰明神武,此可從事矣」,於是攀附不遺餘力;李淵也常往武宅「樂飲經宿,恩情逾重」。長官與部屬之間有信任和默契,有遊樂和享受,應是常有之事;只是士彠與李淵兩人身份地位懸殊,結交也不久,關係卻如此快速的發展,應是士彠刻意奉迎的結果,所以後來李淵對武士彠說,「嘗禮我,故酬汝以官」,正是指此而言。這時的李淵,對武士彠來說可能只是可居的奇貨,全力投資以期日後獲得鉅大的報酬。反之,李淵一方面因為得人款待,另一方面又鑑於他曾是成功的商人,想借用他的經營長才以協助處理軍事裝備,所以也就引用士彠為行軍司鎧。事實上,李淵在太原廣結豪傑,史載當鄉長的晉陽(即太原)富人劉世龍就曾因人引見於他,李淵「雖知其細微亦接待之,以招客」。
由於武士彠原非李淵的心膂之託,因此李淵沒有讓他參與起兵及進攻關中的任何重大決策。不過,武士彠對大唐的「太原起義」另有貢獻。
大業十三年,李淵鑑於群雄競逐之局已成,隋室終不可挽救,於是也想策馬參與逐鹿。猶豫之間,一時不能遽定。武士彠某晚夜行,聽到空中「有稱唐公(李淵)為天子者」;又夢到「從高祖(李淵)乘馬登天,俱以手捫日月」,於是具狀告訴李淵。這事雖事涉迷信,但在相信天命的當時,無異是勸李淵起義,可以增強其信心,所以「高祖大歡,益以自負」。另外又呈獻所撰兵書給李淵,等於教李淵用兵作戰。李淵請他幸勿多言,許以將來成功之後,「當同富貴耳」。
除此以外,當李淵祕密進行起兵部署時,武士彠還有以下兩件功勞。
第一件是當李淵以另一起事集團劉武周進據汾陽宮為借口,命令二郎李世民和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集結之時,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對此懷疑,尤其因長孫順德、劉弘基二人原是逃兵,故欲予以逮捕審判。武士彠勸告兩位副留守,說二人是唐公之客,逮捕審判他們則必與唐公大起糾紛,使王威等不敢行動。其次是留守司兵田德平想建議王威等審按募兵的狀況,士彠又勸止他說:「討捕兵馬的兵權總隸於唐公,王威、高君雅等不過只是寄主罷了,他們又能怎樣?」所以田德平也停止了行動。這兩件事的擺平,使李淵能順利進行募兵和集結,尋即舉兵起事。
十三年五月李淵起兵,逮斬王威和高君雅,建大將軍府,用士彠為鎧曹參軍。接著隨軍進攻關中,期間以功拜壽陽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從平京師,遷光祿大夫,賜宅一區於長安。同年十一月,李淵扶立隋恭帝後,又錄前後功效改封為義原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翌年-隋恭帝義寧二年,唐武德元年(618)-五月,煬帝死訊傳至,李淵廢恭帝自立,開建唐朝,此即武德皇帝,後來的唐高祖。武士彠稍後被任為庫部郎,賜以「太原元謀勳效功臣」銜。至武德三年更遷拜工部尚書,躋身「當世勳貴」之列。不僅如此,武德皇帝除了履行「當同富貴」的諾言之外,為了答謝當年受到武士彠的盛待,更另封其兩兄為郡公,聲言「欲使卿一門三公」云云。唐朝史臣說武士彠「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
也就是說他只是因為從龍首義,故依例封為功臣而已,這評價就武士彠上述的表現來說,顯然甚不公平。縱使不論武士彠在李淵起兵前夕所立的功效,單從他在《大唐創業起居注》的確名列於少數幕僚的名單中,一直為李淵管理和供應軍備之事來看,顯然也是甚為稱職的,因此也就不能說他當時不重要。如果缺少他在軍備後勤的有效策劃和支援,李淵的部隊能如此順利攻進關中嗎?中國人論戰一向著重戰場表現,「戡難之勞」指的是指揮若定的統帥,和衝鋒陷陣的將士,後勤支援常遭忽視,就如同看打球只注視前鋒攻進一樣;不知有效的後勤支援,也常是致勝的關鍵。武士彠勝任鎧曹參軍之職,可以從李淵平定京師後,即起用他為兵部庫部郎一職看得出來,三年後昇遷他為工部尚書,應當也與借重此才幹有關。就是說李淵始終借重武士彠的經營管理長才,這也是他所以成為開國功臣的原因之一。
武士彠從武德三年至八年左右擔任工部尚書,中間曾因參與令典的編修,因此進爵為從一品的應國公。唐初慣例上常用武人為都督、刺史,是則位為尚書、曾任軍將的武士彠,外放為都督而出掌方面,應是遲早之事。
隋末佔有淮南地區的是杜伏威.輔公祏集團,武德二年(619)杜伏威請降入朝,所部由輔公祏統領。公祏於武德六年(623)八月反唐,武德皇帝命趙郡王李孝恭為行軍元帥,李靖為副,率領李勣等七總管往討,至翌年三月平定,遂授孝恭為東南行臺左僕射,李靖為行臺兵部尚書。其年行臺廢,孝恭轉為揚州大都督,李靖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凋弊,李靖鎮撫之,吳、楚以安。不過,尋因突厥入侵,李靖於武德八年(625)八月改任安州都督,奉命率軍北上抵抗,遺缺由武士彠接任。士彠在八月以後以權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的官銜,赴任接替李靖。所謂「權檢校」就是暫時代理的意思,〈攀龍臺碑〉說皇帝約武士彠「期以半年」,即指此而言。不料士彠此去,就再也沒有回任中央的機會了。
士彠的留任揚州,和他在任上的政績有關,碑文說他「降北海之渠,未踰期月;盡南山之盜,詎假旬時。然後商旅安行,農桑野次,化被三吳之俗,威行百越之境」,使管區日漸安定、經濟日漸恢復。因此,當武德九年半年約期屆滿之時,調回中央的不是武士彠而是李孝恭,揚州大都督則由襄邑郡王李神通繼任。原因是因為有當地「父老數百人,詣闕上表,乞更留一年」,所以璽書褒美,讓士彠留任。同年下半年,武士彠協助李神通遷移州府及居民自丹陽遷於江北,使廣陵從此成為州治,得以專揚州之名,這也是武士彠的一種政績。士彠的經營長才,也應由此作觀察。就在同一年-武德九年(626)-六月,天策上將.尚書令.秦王李世民發動玄武門兵變,逼其父皇交出政權。至八月,世民以皇太子身份即位,是為唐太宗。世民以太子執政期間,中樞高層換了一批人,主要由秦府人馬出任要職。所以此時徵召武士彠入朝,對他僅是止於寵賜頻繁,事以殊禮,以安撫父皇舊部罷了;尋而卻另以鎮守戰略要地的理由,將他改授為豫州都督。
翌年-貞觀元年(627)-十二月,因利州都督李孝常謀反伏誅,督區政情不穩,乃改授武士彠為利州都督。士彠赴任後迅速將餘黨撫平,故又得璽書褒美,增邑五百戶。也就是說,貞觀皇帝實際上亦是看重他的經營長才。貞觀五年(631)底,士彠以利州朝集使的身份回京述職,並在十二月領銜上表,奏請封禪泰山而不獲允許,可見他在政壇仍然相當活躍。武士彠的奏請雖然不獲許,不料卻在三十五年後,由他的二女兒—大唐天后—推動並完成了此盛舉,真是天意!是月稍後,武士彠改任為荊州都督,直至九年(635)五月,太上皇(李淵)死訊傳至荊府,武士彠悲慟萬分,乃嘔血而死。士彠死狀馳奏朝廷,貞觀皇帝聞之,嗟悼說:「可謂忠孝之士!」乃追贈為禮部尚書,諡號為「定」。
武德九年秦王世民兵變逆父,改朝換代之際,秦府班底當道,這是他不能回任中央官的原因。不過,事有焉知非福者,他一再外放為都督,而且都是有危機或戰略之地,所以纔有機會發揮他的經營管理之才,大抵以維持社會治安為主,恢復經濟為次,政績不錯。依照唐朝諡法:「大慮安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追補前過曰定,安民大慮約定,純行不爽曰定。」可見士彠因為歷任都督,有安民之功,所以被有司建議諡為定。如果不因人廢言,武士彠不失為一個幹材。他的發跡雖然頗富傳奇性,但是絕非僅因從龍首義而例封功臣,一個平庸的馬屁精而已。
貞觀皇帝對武士彠並無特別的恩遇,贈官不是最高級的三公官,也不列他入「凌煙閣功臣」名單之內。武士彠後來一再被追尊,與其女武明空被貞觀皇帝之子-後來的唐高宗-寵愛有關。追贈并州都督是在明空為昭儀之時,追贈司空、司徒.周國定公是在明空為皇后之後。及至武后與高宗並稱「二聖」,更被追崇為太原郡王,食邑五千戶,以文水縣三百戶充奉陵邑,置令、丞已下諸官,他的廟諱和祖先名諱皆禁止冒犯。武后以太后身份臨朝以後,又追崇其父為魏王,食邑一萬戶。降至大周革命前夕,更追尊為忠孝太皇。革命後,於天授元年(690)尊為孝明高皇帝,廟號太祖,陵墓稱為昊陵,聖歷二年(699)改昊陵署為攀龍臺,即是〈攀龍臺碑〉的由來。
文水武氏的家世
平林漠漠煙如織,長安京城籠罩於黃昏冥色之中,使者一行來至應國公宅。應國夫人楊氏率其家人拜舞接旨。使者展開詔書宣讀:
「於戲!惟爾武士鑊第二女,幼習禮訓,夙表幽閑,冑出鼎族,譽聞華閫,宜遵舊章,授以內職,是用命爾為才人。往欽哉,其光膺徽命,可不慎歟!」
這年是大唐貞觀十二年(638),武士鑊第二女明空,行年十四歲。她奉詔入宮,使大唐國祚改寫的命運,正悄悄地步上了歷史的舞臺,中國歷史也展開了空前絕後的一頁。唯一的女皇帝-是開國皇帝,同時也是亡國皇帝,而且是一個迄今仍有爭議的女皇帝,將從此揭開她自己乃至國史的新里程。
大唐開國至今已經二十一年,王室婚姻,皆取當世勳貴名臣的子女為對象。武明空的父親故利州都督.應國公武士彠是十六位「太原元謀勳效功臣」-唐朝開國功臣-之一。武士彠於隋朝煬帝大業十三年(617)追隨太原留守李淵起兵反隋,一路攻入關中,佔領西京長安,建立了唐朝,年號武德。武德元年(618)八月六日,皇帝論功行賞,分太原起義幹部為兩等功臣,均賜以「太原元謀勳效功臣」的勳號。其中第一等功臣只有兩人,第二等功臣則有十四人,武士彠名列二等功臣,當時他的職官是中央最高行政機關尚書省兵部的庫部郎-亦即兵部四司之一庫部司的司長。庫部司職掌全國武器軍備設施的政令,司長位列正五品,屬於政府的清要官。當時國家初建,群雄并列,戰爭方殷,士彠掌管全國的武器軍備設施,位任可謂重要。
武士彠是功臣,當然有「勳」;但是庫部郎位任縱然重要,卻也還算不上是「貴」。直至武德三年(620),士彠昇為正三品部長級的工部尚書,同年武德皇帝將軍隊作了一次調整,把關中的主力部隊劃分為十二軍,各給予軍號,原駐在醴泉道的改稱為井鉞軍。武士彠大約在這時曾經一度兼統此軍為軍將,稍後又以本官檢校右廂宿衛的禁軍。唐朝官僚制度,三品以上就是國之大臣,掌握大權的行政中樞是尚書省,由尚書令、僕射和六部尚書組成權力核心,世稱八座,而工部尚書即是尚書八座之一,可見武士彠已經躋身政府高層。十二軍是唐朝政權的核心武力,士彠兼統其中一軍,甚至又指揮右廂禁軍,更見武德皇帝對他的信任與重用。也就是說,從武德三年以後,武士彠已經名符其實的是「當世勳貴」,所以其女日後被召納入宮,應不至於意外。
不僅如此,武氏在太原附近的文水縣聚族而居,士彠的兄弟和宗人對唐朝的開國也有一定的功勞,而成為「太原元從」。
他的長兄武士稜原來務農,追隨起義,官至司農少卿,封宣城縣公,武德皇帝利用他的專長,令他常居苑中,主持農囿之事。士稜之子君雅襲爵,官至鎧曹參軍,其子希玄後亦襲爵,為貞觀皇帝的右勳衛。次兄士逸也有戰功,武德初為齊王府戶曹,封安陸縣公,後來累授益州行臺左丞。又有文水宗人武恭,也是唐朝元從,制授諫議大夫。
可見文水武氏可能有一批人,因為武士彠之故,追隨武德皇帝李淵太原起義,立有大小不等的功勳,至此都已做官。是則文水武氏在唐初政壇,應有一定的份量。後來李敬業起兵反武,駱賓王為他撰寫〈討武氏檄〉,聲討當時臨朝武太后之罪,竟至說她「地實寒微」,實際上是政治文宣的因素居多。不過就社會的角度看,駱賓王的說法事實上也頗有他的根據,不至於完全誣蔑武家。中國從魏晉南北朝以來,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階級,他們世代做官,依照他們世代官位的高低,高的形成了大士族,或者稱為世族、大姓、高門,次者成為小姓,先世沒有做官的則是寒素。世族高門掌握,甚至壟斷了社會和政治的資源,即使到了南北朝後期和唐朝前期,他們的家人已經很久沒有做官,但是其社會地位也還沒有消失,僅只是政治上的衰敗門戶而已,一般人仍然不惜花大錢和他們的子女結婚,攀附他們的門第。這種現象世稱「賣婚」-就是買賣婚姻。中國人好面子重身份,只要能力所及,對婚喪二事大都極盡奢華舖張,自古已然。唐朝人選擇婚姻有三個標準-門第、財富和功名,而以門第為第一優先。如今為了抬高自己身份,不惜慕人祖宗,攀附他人門戶,所以武德皇帝之子貞觀皇帝-也就是著名的唐太宗-在即位後對此風氣極為痛惡,予以嚴厲批評,說是無禮和無恥,下詔修《氏族志》,必須以尊「崇我唐朝人物衣冠」作為評定門第的標準,書成頒行於天下;然而社會觀念植根已深,風尚依舊,也沒有為之改變。這一年正是明空奉詔入宮之年。
依照這種社會觀念與標準,武家的確不是高門大姓。
根據後來李嶠奉大周女皇敕令所寫的〈攀龍臺碑〉和《新唐書》卷七四上的〈宰相世系表〉所述,武氏係并州太原郡文水縣人,出自姬姓,是周平王少子之後。因為周平王少子生時手上紋理有一「武」字,後代遂以武為姓氏。降至武明空第八代祖武念,官拜北魏洛州刺史.歸義侯。七代祖武洽,官至北魏平北將軍、五兵尚書、晉陽公,別封大陵縣。此下五代祖武克己、高祖武居常,皆曾襲繼壽陽公之爵。大陵在隋朝改稱為文水,故成為文水縣人。
又據〈宰相世系表〉,武明空從七代祖武洽已下,直系均有任官的記錄:
六代祖神龜為祭酒,
五代祖克己為本州大中正、司徒.越王長史,
高祖居常為北齊鎮遠將軍,
曾祖儉為北周永昌王諮議參軍,
祖父華為隋東都丞,
父士彠為唐工部尚書,封應國公。
基本上,除其父親以外,即使所載是真的,武明空自第五代祖已降,所任都是幕佐之官,算不上是顯宦之家,因此也算不上是閥閱高門。不過,除非有史料可以推翻〈宰相世系表〉的記載,否則文水武氏儘管不屬於高門大姓,但是也不至於如〈討武氏檄〉所說的「地實寒微」。武明空「革命」當了大周皇帝後,曾於聖歷元年(698)八月,命令姪孫武延秀入突厥和親,突厥可汗默啜告訴來使說:「我世受李氏恩,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並且移書說:「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小姓,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外國元首罵武周王室為「小姓」。小姓的社會門第不及大姓,但卻也不至於寒素,或者可以反映文水武氏當時社會地位的真相。無論如何,文水武氏在當時傳統社會中,僅能屬於小姓等級的門第;但是在她入宮之年以後,則因是新貴而屬於甲族,不過猶未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可。武士彠傳奇性的發跡和發展
武士彠是武華的第四子,鄉里民間傳說他是一個經營林業的木材商人;不過〈攀龍臺碑〉卻說他出生時就有帝王之象,才兼文武,人格如何高,學識如何優,材幹如何好,這麼多優點令他名動當世朝,使到隋文帝屢加辟召,司徒楊雄、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宏、兵部尚書柳述等公卿大臣,爭相向他抗禮求教。李嶠奉命寫〈攀龍臺碑〉之時已經是大周王朝的時代,此碑是女皇為頌揚其父武士彠-這時已追尊為「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帝」-人格功德之碑,後來唐朝史臣修撰國史之時,懷疑它和舊史有「過為褒詞」和「虛美」之嫌,不足予以深究,不免對武士彠的事跡大加刪削,以至也有過為刪削之嫌。
事實上,文水武氏是地方上的小姓,子弟們也不一定都出仕做官。根據史書的記錄,南、北朝以降門第子弟窮哈哈或無仕者,所在多有,不算稀奇。青年時期的武士彠,經營木材很可能即是他的生意之一,所以史書說他「家富於材,頗好交結」。近世有些學者據此推論武士彠以鬻賣木材為業,是木材商人,值隋朝屢興鉅大土木工程,因而致富,因此判斷他是投機善賈之流。經商致富之說,大抵可信。筆者以為,投機是善賈之能事,好交結應酬也是商場的常習,根據士彠的發跡事跡看,他的確是能觀時通變之人,這也正是他的長處所在,使他所以能成為唐朝的開國功臣。
武士彠經商致富與隋煬帝即位後大興土木以事建設有關,其中重大工程之一是營建洛陽為東京。大業元年(605)營建東京既是重大的工程建設,遂由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兩位宰相分別擔任營建的正、副使-楊達後來就是武明空的外祖父。大約明空之父武士彠販賣木材入東京,利用關係與財富,常與權貴交結,一時傾動當朝。其間,他曾招致楊素的猜忌,想構以禍端,幸虧他經商的優點適時發揮作用,因為交結廣、神通大,得到楊雄、牛宏等權貴的營護而免於禍,從此深自隱匿,以求自保。無獨有偶,後來女皇的情夫張易之兄弟,也曾利用他們的權勢販賣木材及其他買賣,為時人所側目與批評,給女皇帶來了危機。
楊素向來負冒財貨,營求產業,在東、西二京和諸方都會處,置有物業以千百數,素為時議所鄙。是則士彠因為經商應酬而得罪了楊素,應有可能。總之,武士彠曾經得罪楊素而逃隱,極可能是一個事實,因為女皇革命之後,曾下制禁錮楊素及其兄弟的子孫,不許他們擔任京官和侍衛,也許與此事有關。
士彠逃隱後開始注意局勢的變化,及至隋煬帝大業七年(611)對高麗用兵失敗後,國內亂局開始擴大,反隋起義逐漸蜂起。在這種環境氣氛之下,士彠遂想到要出山,決定往事功方面發展。不論他的真正動機究竟如何,這時煬帝實行廣募驍勇、掃地為兵的政策,士彠參與隋軍,可見他是有志從軍立功,以求仕宦的。
士彠在此之前沒有任何資歷,出山後當上了鷹揚府隊正。隊正統領五十人,是府兵制的最低常制長官。〈攀龍臺碑〉對武士彠在隋末的軍事表現著墨極重,用以表彰父親的軍功,其目的是透過頌揚先人的積德累功,作為武周早有天命的論述依據,遂使此碑所述有過為褒詞和虛美偽冒之事。碑誌在中國一向是用以諛美死人的,只要不過份相信,也就無傷大雅。
鷹揚府隊正只是一個小軍官,而太原留守李淵則系出隴西李氏,是今上(隋煬帝)的表弟,身份官爵俱高,武士彠怎樣結交上他,以致成為唐朝開國功臣?根據〈攀龍臺碑〉的說法,士彠要出山時,諸兄素聞李密-當時反隋群雄之最有實力者-之名,乃勸他前去投靠。「李密雖有才氣,未能經遠,欲圖功業,終恐無成」,士彠告訴他們。顯然他的出山不是要自立山頭,而是要投靠明主,以「圖功業」。適逢此時(大業十一年,615),李淵奉詔往山西討捕起事人民,撫慰地方。他行軍於汾、晉之間,休止於士彠之家,因蒙士彠顧接,乃得以結交。至十三年(617),李淵奉詔坐鎮太原為留守,於是引用士彠為行軍司鎧,成為留守府主管軍事裝備的幕僚。所以後來攻入長安,他就順理成章地官拜庫部郎,掌管全國的武器軍備設施。
士彠雖為留守李淵所引用,卻是副留守王威之黨,不是李淵的心膂之託。士彠觀察李淵,以為此人「雄傑簡易,聰明神武,此可從事矣」,於是攀附不遺餘力;李淵也常往武宅「樂飲經宿,恩情逾重」。長官與部屬之間有信任和默契,有遊樂和享受,應是常有之事;只是士彠與李淵兩人身份地位懸殊,結交也不久,關係卻如此快速的發展,應是士彠刻意奉迎的結果,所以後來李淵對武士彠說,「嘗禮我,故酬汝以官」,正是指此而言。這時的李淵,對武士彠來說可能只是可居的奇貨,全力投資以期日後獲得鉅大的報酬。反之,李淵一方面因為得人款待,另一方面又鑑於他曾是成功的商人,想借用他的經營長才以協助處理軍事裝備,所以也就引用士彠為行軍司鎧。事實上,李淵在太原廣結豪傑,史載當鄉長的晉陽(即太原)富人劉世龍就曾因人引見於他,李淵「雖知其細微亦接待之,以招客」。
由於武士彠原非李淵的心膂之託,因此李淵沒有讓他參與起兵及進攻關中的任何重大決策。不過,武士彠對大唐的「太原起義」另有貢獻。
大業十三年,李淵鑑於群雄競逐之局已成,隋室終不可挽救,於是也想策馬參與逐鹿。猶豫之間,一時不能遽定。武士彠某晚夜行,聽到空中「有稱唐公(李淵)為天子者」;又夢到「從高祖(李淵)乘馬登天,俱以手捫日月」,於是具狀告訴李淵。這事雖事涉迷信,但在相信天命的當時,無異是勸李淵起義,可以增強其信心,所以「高祖大歡,益以自負」。另外又呈獻所撰兵書給李淵,等於教李淵用兵作戰。李淵請他幸勿多言,許以將來成功之後,「當同富貴耳」。
除此以外,當李淵祕密進行起兵部署時,武士彠還有以下兩件功勞。
第一件是當李淵以另一起事集團劉武周進據汾陽宮為借口,命令二郎李世民和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集結之時,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對此懷疑,尤其因長孫順德、劉弘基二人原是逃兵,故欲予以逮捕審判。武士彠勸告兩位副留守,說二人是唐公之客,逮捕審判他們則必與唐公大起糾紛,使王威等不敢行動。其次是留守司兵田德平想建議王威等審按募兵的狀況,士彠又勸止他說:「討捕兵馬的兵權總隸於唐公,王威、高君雅等不過只是寄主罷了,他們又能怎樣?」所以田德平也停止了行動。這兩件事的擺平,使李淵能順利進行募兵和集結,尋即舉兵起事。
十三年五月李淵起兵,逮斬王威和高君雅,建大將軍府,用士彠為鎧曹參軍。接著隨軍進攻關中,期間以功拜壽陽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從平京師,遷光祿大夫,賜宅一區於長安。同年十一月,李淵扶立隋恭帝後,又錄前後功效改封為義原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翌年-隋恭帝義寧二年,唐武德元年(618)-五月,煬帝死訊傳至,李淵廢恭帝自立,開建唐朝,此即武德皇帝,後來的唐高祖。武士彠稍後被任為庫部郎,賜以「太原元謀勳效功臣」銜。至武德三年更遷拜工部尚書,躋身「當世勳貴」之列。不僅如此,武德皇帝除了履行「當同富貴」的諾言之外,為了答謝當年受到武士彠的盛待,更另封其兩兄為郡公,聲言「欲使卿一門三公」云云。唐朝史臣說武士彠「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
也就是說他只是因為從龍首義,故依例封為功臣而已,這評價就武士彠上述的表現來說,顯然甚不公平。縱使不論武士彠在李淵起兵前夕所立的功效,單從他在《大唐創業起居注》的確名列於少數幕僚的名單中,一直為李淵管理和供應軍備之事來看,顯然也是甚為稱職的,因此也就不能說他當時不重要。如果缺少他在軍備後勤的有效策劃和支援,李淵的部隊能如此順利攻進關中嗎?中國人論戰一向著重戰場表現,「戡難之勞」指的是指揮若定的統帥,和衝鋒陷陣的將士,後勤支援常遭忽視,就如同看打球只注視前鋒攻進一樣;不知有效的後勤支援,也常是致勝的關鍵。武士彠勝任鎧曹參軍之職,可以從李淵平定京師後,即起用他為兵部庫部郎一職看得出來,三年後昇遷他為工部尚書,應當也與借重此才幹有關。就是說李淵始終借重武士彠的經營管理長才,這也是他所以成為開國功臣的原因之一。
武士彠從武德三年至八年左右擔任工部尚書,中間曾因參與令典的編修,因此進爵為從一品的應國公。唐初慣例上常用武人為都督、刺史,是則位為尚書、曾任軍將的武士彠,外放為都督而出掌方面,應是遲早之事。
隋末佔有淮南地區的是杜伏威.輔公祏集團,武德二年(619)杜伏威請降入朝,所部由輔公祏統領。公祏於武德六年(623)八月反唐,武德皇帝命趙郡王李孝恭為行軍元帥,李靖為副,率領李勣等七總管往討,至翌年三月平定,遂授孝恭為東南行臺左僕射,李靖為行臺兵部尚書。其年行臺廢,孝恭轉為揚州大都督,李靖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凋弊,李靖鎮撫之,吳、楚以安。不過,尋因突厥入侵,李靖於武德八年(625)八月改任安州都督,奉命率軍北上抵抗,遺缺由武士彠接任。士彠在八月以後以權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的官銜,赴任接替李靖。所謂「權檢校」就是暫時代理的意思,〈攀龍臺碑〉說皇帝約武士彠「期以半年」,即指此而言。不料士彠此去,就再也沒有回任中央的機會了。
士彠的留任揚州,和他在任上的政績有關,碑文說他「降北海之渠,未踰期月;盡南山之盜,詎假旬時。然後商旅安行,農桑野次,化被三吳之俗,威行百越之境」,使管區日漸安定、經濟日漸恢復。因此,當武德九年半年約期屆滿之時,調回中央的不是武士彠而是李孝恭,揚州大都督則由襄邑郡王李神通繼任。原因是因為有當地「父老數百人,詣闕上表,乞更留一年」,所以璽書褒美,讓士彠留任。同年下半年,武士彠協助李神通遷移州府及居民自丹陽遷於江北,使廣陵從此成為州治,得以專揚州之名,這也是武士彠的一種政績。士彠的經營長才,也應由此作觀察。就在同一年-武德九年(626)-六月,天策上將.尚書令.秦王李世民發動玄武門兵變,逼其父皇交出政權。至八月,世民以皇太子身份即位,是為唐太宗。世民以太子執政期間,中樞高層換了一批人,主要由秦府人馬出任要職。所以此時徵召武士彠入朝,對他僅是止於寵賜頻繁,事以殊禮,以安撫父皇舊部罷了;尋而卻另以鎮守戰略要地的理由,將他改授為豫州都督。
翌年-貞觀元年(627)-十二月,因利州都督李孝常謀反伏誅,督區政情不穩,乃改授武士彠為利州都督。士彠赴任後迅速將餘黨撫平,故又得璽書褒美,增邑五百戶。也就是說,貞觀皇帝實際上亦是看重他的經營長才。貞觀五年(631)底,士彠以利州朝集使的身份回京述職,並在十二月領銜上表,奏請封禪泰山而不獲允許,可見他在政壇仍然相當活躍。武士彠的奏請雖然不獲許,不料卻在三十五年後,由他的二女兒—大唐天后—推動並完成了此盛舉,真是天意!是月稍後,武士彠改任為荊州都督,直至九年(635)五月,太上皇(李淵)死訊傳至荊府,武士彠悲慟萬分,乃嘔血而死。士彠死狀馳奏朝廷,貞觀皇帝聞之,嗟悼說:「可謂忠孝之士!」乃追贈為禮部尚書,諡號為「定」。
武德九年秦王世民兵變逆父,改朝換代之際,秦府班底當道,這是他不能回任中央官的原因。不過,事有焉知非福者,他一再外放為都督,而且都是有危機或戰略之地,所以纔有機會發揮他的經營管理之才,大抵以維持社會治安為主,恢復經濟為次,政績不錯。依照唐朝諡法:「大慮安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追補前過曰定,安民大慮約定,純行不爽曰定。」可見士彠因為歷任都督,有安民之功,所以被有司建議諡為定。如果不因人廢言,武士彠不失為一個幹材。他的發跡雖然頗富傳奇性,但是絕非僅因從龍首義而例封功臣,一個平庸的馬屁精而已。
貞觀皇帝對武士彠並無特別的恩遇,贈官不是最高級的三公官,也不列他入「凌煙閣功臣」名單之內。武士彠後來一再被追尊,與其女武明空被貞觀皇帝之子-後來的唐高宗-寵愛有關。追贈并州都督是在明空為昭儀之時,追贈司空、司徒.周國定公是在明空為皇后之後。及至武后與高宗並稱「二聖」,更被追崇為太原郡王,食邑五千戶,以文水縣三百戶充奉陵邑,置令、丞已下諸官,他的廟諱和祖先名諱皆禁止冒犯。武后以太后身份臨朝以後,又追崇其父為魏王,食邑一萬戶。降至大周革命前夕,更追尊為忠孝太皇。革命後,於天授元年(690)尊為孝明高皇帝,廟號太祖,陵墓稱為昊陵,聖歷二年(699)改昊陵署為攀龍臺,即是〈攀龍臺碑〉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