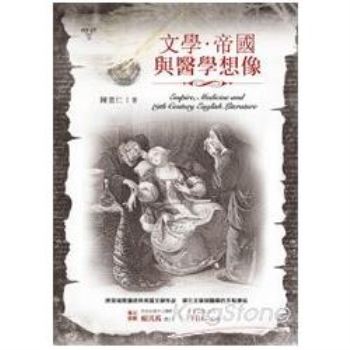第一章
科學與禁忌──人體解剖、盜墓奇聞與《科學怪人》
西方醫學的進步相當倚重解剖學的發展,就某個程度上來說,解剖學確認許多肉眼所不能及的病理細節,介入病人身體表層下的身體紋理,我們因此得以跨越生死的界線,推測生命的存在樣態,也得以追蹤疾病在人體肆虐的痕跡。因為解剖學在檢驗的過程所採用的方法和態度,都富含科學的精神,所以醫學被視為是一門科學,也就不足為奇。科學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在於能夠被重複驗證,科學化的醫學也當如此。不僅僅是同一個案例所得出的解剖報告應該一致,面對相同死因的不同案例,解剖學也有能力抽絲剝繭,找出症狀和疾病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應用科學的方法和態度,我們也可以在更大的人口樣本中歸納總體的健康與疾病趨勢,提供一套對於總體人口檢驗、預測與管理的依據。
然而在醫學史中,病理解剖作為現代醫學知識體系的重要支柱,也不過是十九世紀開始的事情。儘管解剖學的技術發展從未真正停止過,但就民眾感知與輿論氣氛的角度而言,解剖學的專業形象遲遲無法建立,和基督教信仰以及政治勢力的箝制有很大的關係。除此之外,在任何文化中,死亡都是人類理性認知無法充分理解的範疇,既然無法理解,就只能任由禁忌與迷信大量繁殖,也因此,解剖學也往往和死亡禁忌緊密連結。職是之故,在西方醫學中,解剖一直是最具神秘色彩也最受爭議的一門學問,而在所有文學或是文化的想像與再現中,解剖也一直是最具爭議性、最具禁忌色彩、但也是最令人好奇的熱門話題。
這個章節所要討論的,是人體解剖禁忌和盜屍奇聞之間的關係,從而延伸到文學中對於死亡與解剖的想像,並以此比對十九世紀外科手術與醫學技術的進展,企圖理解奠基在人體解剖之上的醫學,是如何遊走在禁忌與理性的邊緣。一方面,解剖強調理性、冷靜、精準,是醫學的科學基礎,該要恪遵理性、客觀、抽離等理性科學的價值;另一方面,解剖是連結死亡與身體禁忌最直接的醫學操作,在所有醫療診斷與臨床教育的範疇中,執行解剖的手是唯一探觸身體深處的手,也是唯一直接碰觸死亡的手,這樣的手自然成為最令人感到恐懼與著迷的手。執行解剖的醫師的手同時碰觸象徵毀滅與誕生的衝突現象,在面對死亡軀體的過程中,釐清生命延續的秘密;在切割死亡軀體的過程中,見證死亡的尊嚴與恐懼。解剖同時連結生與死的矛盾特質,召喚十九世紀初才女瑪莉‧雪萊(Mary Shelley)的創作靈感,寫下《科學怪人》(Frankenstein)這部膾炙人口的科幻奇想。
《科學怪人》的故事與形象
無論你有沒有讀過小說原著,你一定都聽過「科學怪人」這個名號。你或許看過小說改編的電影,或許在科幻片看到以科學怪人為主調的改編版本,或許你曾在卡通或是漫畫看到科學怪人的Q版造型,頭上還明顯看得到長長的縫合痕跡以及突起的螺絲帽。在化妝派對或是在小朋友的萬聖節裝扮中,科學怪人都有一定的支持者。大家都聽過科學怪人,但是只要一追問身邊的人「誰是科學怪人?」,相信會有許多人答不上來,能夠開口回話的人當中,也必定會有不少人誤認科學怪人就是這位造型怪異的怪獸,而非創造此一怪獸的科學家。這現象當然反映出幾個值得注意的文化面向,首先,因為翻譯過程的失誤或是以訛傳訛的關係,在流行文化的傳播中,往往將科學怪人誤導為被複製生命的妖怪猛獸,而不是創造生命的科學家。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看過或聽過科學怪人,樂見科學怪人持續在科幻題材中不斷融合新元素重現,這足以顯現科學怪人在一般民眾心中受到歡迎的程度,也足以顯見這一個看似通俗的角色設定有其矛盾曖昧之處:科學家所創造出來的怪物同時代表恐懼與希望、暴力與生命,但是這帶來毀滅力量的怪獸卻也是眾人投注同情的焦點所在。
科學與禁忌
貫穿《科學怪人》全書的,是關於何而為人的省思。科學家由屍塊拼湊的人造人,與自然天生的正常人,究竟有什麼樣的差異?小說對此似乎抱持著僅存的樂觀,認定兩者在天生情感上並無差異,兩者同樣具有感情,兩者同樣都具有優異的語言學習能力,同樣對孤立無援的處境感到哀傷,同樣為同伴的辭世感到哀痛,也同樣需要伙伴的慰藉。然而,不同的是,富蘭肯斯坦為母胎所親生,而怪物則是挖掘公墓的死刑屍首拼湊而成。藉此,《科學怪人》成功地將小說的議題設定導向為對人的關懷。人的基本價值為何?如果是屍塊拼湊而成的人造人,究竟是否可以視為人?
《科學怪人》故事中由屍塊拼湊成人體的驚悚劇情,以及富蘭肯斯坦在隱密的實驗室內大量以屍體進行實驗的描述,儘管並非小說的重點,但卻因情節具有發揮空間,經常是改編成電影時刻意渲染放大的橋段。如果比對同時期的醫學發展,這些情節足
以令人聯想到1783年義大利解剖學家賈法尼(Luigi Galvani)以通過電流的金屬片啟動青蛙肌肉的收縮現象。賈法尼藉此實驗結果宣稱生物的神經存有生物電,電流由動物的組織產生,透過連接金屬的傳導使得實驗的青蛙成為電流導體,這種存在於生物體身上的電流被後人廣泛稱為賈法尼電流(Galvanic current)。同樣的,也有許多學者認為《科學怪人》受到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藉由風箏發現自然界電流的影響,或者是受到同時期英國科學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發明發電機的感召。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發現,科學領域中震撼世人的電學實驗成為小說家書寫未來世界的靈感泉源。由此當可確信,儘管科幻小說構築非現實的想像世界,但幻想往往源自現實生活的啟發,無論是賈法尼的電流實驗或是富蘭克林、法拉第的電學研究,在當時都是舉世震撼的新發現,足以納編為幻想元素,構造令讀者眼睛為之一亮的未來世界。也就是說,儘管科幻小說勾勒的是一個虛構不存在的世界,但是引發想像的觸媒以及提供想像連結的構成元素,其實是來自於現實世界的所見所聞。
但是這樣的說法無法充分解釋小說觸碰的道德禁忌。雖然科學經常是啟發想像世界的觸媒,但卻未必直接與小說企圖召喚的恐懼想像產生連結,也就是說,科學的發展並不會導向死屍藉由電流復活的推論;再者,無論是富蘭克林、賈法尼或是法拉第,他們所代表的多半是積極、理性而客觀的科學精神,而非虛構幻想的意涵。相較之下我們發現,《科學怪人》所玩弄的,卻是外表看似理性冷靜實則瘋狂失心的面向。作為一個科學家的原型,富蘭肯斯坦所顯現出來的,是對於科學迷信般的執著,以及隨著執著而來的狂妄、僭越、驕傲等非理性的態度,富蘭肯斯坦無異是瘋狂科學家的代名詞。這些負面的聯想,恐怕都不是富蘭克林、賈法尼或是法拉第等科學家帶給當時社會的主流觀感。
《科學怪人》之所以驚世駭俗,是因為它直接挑戰當時社會對於死亡以及屍體的禁忌,更精確地說,是因為它呈現了當時社會上因供應解剖用屍體的嚴重不足而普遍產生盜墓賣屍的社會現象。
根據理查森(Ruth Richardson)的說法,在瑪莉‧雪萊的童年直至她長大成人的這段期間,盜墓取屍(bodysnatching)的行為相當氾濫。理查森研究瑪莉‧雪萊以及雪萊的傳記,發現他們兩人在瑪莉‧沃史東克拉芙辭世後經常造訪她於倫敦聖潘卡拉斯(St. Pancras)的墓園,兩人密集的造訪,除了表達對於死者的思念之外,就當時盜墓猖獗的氣氛而言,更隱含有保衛死者屍體免於遭竊轉賣淪落解剖實驗台的實際用意。根據醫學史與倫敦歷史的記載,當時倫敦聖潘卡拉斯附近的墓園,也就是約莫今日的國王十字(King’s Cross)一帶,正好是盜墓竊屍最為猖獗的地帶。有關英國盜墓竊屍的報導在1832年左右嘎然而止,彷彿一個流行於社會底層的敗壞風氣一夕之間獲得導正。儘管如此,流傳於社會各界有關盜墓竊屍的各式傳言已然為社會普遍認知,這樣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對社會大眾的效應更是無從估算。醫學史學者大多同意這樣的看法:十九世紀之初因為醫學教學與研究的實際需求遠高於合法取得的屍體,竊取甫下葬的屍體轉賣圖利,已經是普遍流傳市井間的都會傳奇。當時合法屍體的來源多為公開執行死刑的重大刑犯或是客死街頭而無人招領的無名屍,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民眾親友下葬的屍體突遭挖掘轉賣,淪於醫學院與民間研究室解剖之用,其意義不僅是對於死者的冒犯與侵擾,對於心痛的家人而言,親友屍首遭受盜賣解剖無異於是讓親友和死刑犯一般接受死後凌遲。無論盜墓竊屍是否具有提昇醫療研究水平等光明正大的藉口,民眾對於醫界竊取屍體普遍感到憎恨厭惡,這種集體負面情緒的產生,經常與解剖的研究與教學有關。也就是說,《科學怪人》之所以在出版之初具有驚世駭俗的強大效應,不只是因為小說創造了多麼恐怖的怪獸,更因為是小說中理應呈現理性與紀律的醫師/科學家卻恰恰呈現人性中最為陰暗瘋狂的行徑,對於當代的讀者來說,這樣的錯置反應當時社會感受最深切的恐懼與禁忌。
科學與禁忌──人體解剖、盜墓奇聞與《科學怪人》
西方醫學的進步相當倚重解剖學的發展,就某個程度上來說,解剖學確認許多肉眼所不能及的病理細節,介入病人身體表層下的身體紋理,我們因此得以跨越生死的界線,推測生命的存在樣態,也得以追蹤疾病在人體肆虐的痕跡。因為解剖學在檢驗的過程所採用的方法和態度,都富含科學的精神,所以醫學被視為是一門科學,也就不足為奇。科學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在於能夠被重複驗證,科學化的醫學也當如此。不僅僅是同一個案例所得出的解剖報告應該一致,面對相同死因的不同案例,解剖學也有能力抽絲剝繭,找出症狀和疾病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應用科學的方法和態度,我們也可以在更大的人口樣本中歸納總體的健康與疾病趨勢,提供一套對於總體人口檢驗、預測與管理的依據。
然而在醫學史中,病理解剖作為現代醫學知識體系的重要支柱,也不過是十九世紀開始的事情。儘管解剖學的技術發展從未真正停止過,但就民眾感知與輿論氣氛的角度而言,解剖學的專業形象遲遲無法建立,和基督教信仰以及政治勢力的箝制有很大的關係。除此之外,在任何文化中,死亡都是人類理性認知無法充分理解的範疇,既然無法理解,就只能任由禁忌與迷信大量繁殖,也因此,解剖學也往往和死亡禁忌緊密連結。職是之故,在西方醫學中,解剖一直是最具神秘色彩也最受爭議的一門學問,而在所有文學或是文化的想像與再現中,解剖也一直是最具爭議性、最具禁忌色彩、但也是最令人好奇的熱門話題。
這個章節所要討論的,是人體解剖禁忌和盜屍奇聞之間的關係,從而延伸到文學中對於死亡與解剖的想像,並以此比對十九世紀外科手術與醫學技術的進展,企圖理解奠基在人體解剖之上的醫學,是如何遊走在禁忌與理性的邊緣。一方面,解剖強調理性、冷靜、精準,是醫學的科學基礎,該要恪遵理性、客觀、抽離等理性科學的價值;另一方面,解剖是連結死亡與身體禁忌最直接的醫學操作,在所有醫療診斷與臨床教育的範疇中,執行解剖的手是唯一探觸身體深處的手,也是唯一直接碰觸死亡的手,這樣的手自然成為最令人感到恐懼與著迷的手。執行解剖的醫師的手同時碰觸象徵毀滅與誕生的衝突現象,在面對死亡軀體的過程中,釐清生命延續的秘密;在切割死亡軀體的過程中,見證死亡的尊嚴與恐懼。解剖同時連結生與死的矛盾特質,召喚十九世紀初才女瑪莉‧雪萊(Mary Shelley)的創作靈感,寫下《科學怪人》(Frankenstein)這部膾炙人口的科幻奇想。
《科學怪人》的故事與形象
無論你有沒有讀過小說原著,你一定都聽過「科學怪人」這個名號。你或許看過小說改編的電影,或許在科幻片看到以科學怪人為主調的改編版本,或許你曾在卡通或是漫畫看到科學怪人的Q版造型,頭上還明顯看得到長長的縫合痕跡以及突起的螺絲帽。在化妝派對或是在小朋友的萬聖節裝扮中,科學怪人都有一定的支持者。大家都聽過科學怪人,但是只要一追問身邊的人「誰是科學怪人?」,相信會有許多人答不上來,能夠開口回話的人當中,也必定會有不少人誤認科學怪人就是這位造型怪異的怪獸,而非創造此一怪獸的科學家。這現象當然反映出幾個值得注意的文化面向,首先,因為翻譯過程的失誤或是以訛傳訛的關係,在流行文化的傳播中,往往將科學怪人誤導為被複製生命的妖怪猛獸,而不是創造生命的科學家。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看過或聽過科學怪人,樂見科學怪人持續在科幻題材中不斷融合新元素重現,這足以顯現科學怪人在一般民眾心中受到歡迎的程度,也足以顯見這一個看似通俗的角色設定有其矛盾曖昧之處:科學家所創造出來的怪物同時代表恐懼與希望、暴力與生命,但是這帶來毀滅力量的怪獸卻也是眾人投注同情的焦點所在。
科學與禁忌
貫穿《科學怪人》全書的,是關於何而為人的省思。科學家由屍塊拼湊的人造人,與自然天生的正常人,究竟有什麼樣的差異?小說對此似乎抱持著僅存的樂觀,認定兩者在天生情感上並無差異,兩者同樣具有感情,兩者同樣都具有優異的語言學習能力,同樣對孤立無援的處境感到哀傷,同樣為同伴的辭世感到哀痛,也同樣需要伙伴的慰藉。然而,不同的是,富蘭肯斯坦為母胎所親生,而怪物則是挖掘公墓的死刑屍首拼湊而成。藉此,《科學怪人》成功地將小說的議題設定導向為對人的關懷。人的基本價值為何?如果是屍塊拼湊而成的人造人,究竟是否可以視為人?
《科學怪人》故事中由屍塊拼湊成人體的驚悚劇情,以及富蘭肯斯坦在隱密的實驗室內大量以屍體進行實驗的描述,儘管並非小說的重點,但卻因情節具有發揮空間,經常是改編成電影時刻意渲染放大的橋段。如果比對同時期的醫學發展,這些情節足
以令人聯想到1783年義大利解剖學家賈法尼(Luigi Galvani)以通過電流的金屬片啟動青蛙肌肉的收縮現象。賈法尼藉此實驗結果宣稱生物的神經存有生物電,電流由動物的組織產生,透過連接金屬的傳導使得實驗的青蛙成為電流導體,這種存在於生物體身上的電流被後人廣泛稱為賈法尼電流(Galvanic current)。同樣的,也有許多學者認為《科學怪人》受到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藉由風箏發現自然界電流的影響,或者是受到同時期英國科學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發明發電機的感召。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發現,科學領域中震撼世人的電學實驗成為小說家書寫未來世界的靈感泉源。由此當可確信,儘管科幻小說構築非現實的想像世界,但幻想往往源自現實生活的啟發,無論是賈法尼的電流實驗或是富蘭克林、法拉第的電學研究,在當時都是舉世震撼的新發現,足以納編為幻想元素,構造令讀者眼睛為之一亮的未來世界。也就是說,儘管科幻小說勾勒的是一個虛構不存在的世界,但是引發想像的觸媒以及提供想像連結的構成元素,其實是來自於現實世界的所見所聞。
但是這樣的說法無法充分解釋小說觸碰的道德禁忌。雖然科學經常是啟發想像世界的觸媒,但卻未必直接與小說企圖召喚的恐懼想像產生連結,也就是說,科學的發展並不會導向死屍藉由電流復活的推論;再者,無論是富蘭克林、賈法尼或是法拉第,他們所代表的多半是積極、理性而客觀的科學精神,而非虛構幻想的意涵。相較之下我們發現,《科學怪人》所玩弄的,卻是外表看似理性冷靜實則瘋狂失心的面向。作為一個科學家的原型,富蘭肯斯坦所顯現出來的,是對於科學迷信般的執著,以及隨著執著而來的狂妄、僭越、驕傲等非理性的態度,富蘭肯斯坦無異是瘋狂科學家的代名詞。這些負面的聯想,恐怕都不是富蘭克林、賈法尼或是法拉第等科學家帶給當時社會的主流觀感。
《科學怪人》之所以驚世駭俗,是因為它直接挑戰當時社會對於死亡以及屍體的禁忌,更精確地說,是因為它呈現了當時社會上因供應解剖用屍體的嚴重不足而普遍產生盜墓賣屍的社會現象。
根據理查森(Ruth Richardson)的說法,在瑪莉‧雪萊的童年直至她長大成人的這段期間,盜墓取屍(bodysnatching)的行為相當氾濫。理查森研究瑪莉‧雪萊以及雪萊的傳記,發現他們兩人在瑪莉‧沃史東克拉芙辭世後經常造訪她於倫敦聖潘卡拉斯(St. Pancras)的墓園,兩人密集的造訪,除了表達對於死者的思念之外,就當時盜墓猖獗的氣氛而言,更隱含有保衛死者屍體免於遭竊轉賣淪落解剖實驗台的實際用意。根據醫學史與倫敦歷史的記載,當時倫敦聖潘卡拉斯附近的墓園,也就是約莫今日的國王十字(King’s Cross)一帶,正好是盜墓竊屍最為猖獗的地帶。有關英國盜墓竊屍的報導在1832年左右嘎然而止,彷彿一個流行於社會底層的敗壞風氣一夕之間獲得導正。儘管如此,流傳於社會各界有關盜墓竊屍的各式傳言已然為社會普遍認知,這樣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對社會大眾的效應更是無從估算。醫學史學者大多同意這樣的看法:十九世紀之初因為醫學教學與研究的實際需求遠高於合法取得的屍體,竊取甫下葬的屍體轉賣圖利,已經是普遍流傳市井間的都會傳奇。當時合法屍體的來源多為公開執行死刑的重大刑犯或是客死街頭而無人招領的無名屍,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民眾親友下葬的屍體突遭挖掘轉賣,淪於醫學院與民間研究室解剖之用,其意義不僅是對於死者的冒犯與侵擾,對於心痛的家人而言,親友屍首遭受盜賣解剖無異於是讓親友和死刑犯一般接受死後凌遲。無論盜墓竊屍是否具有提昇醫療研究水平等光明正大的藉口,民眾對於醫界竊取屍體普遍感到憎恨厭惡,這種集體負面情緒的產生,經常與解剖的研究與教學有關。也就是說,《科學怪人》之所以在出版之初具有驚世駭俗的強大效應,不只是因為小說創造了多麼恐怖的怪獸,更因為是小說中理應呈現理性與紀律的醫師/科學家卻恰恰呈現人性中最為陰暗瘋狂的行徑,對於當代的讀者來說,這樣的錯置反應當時社會感受最深切的恐懼與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