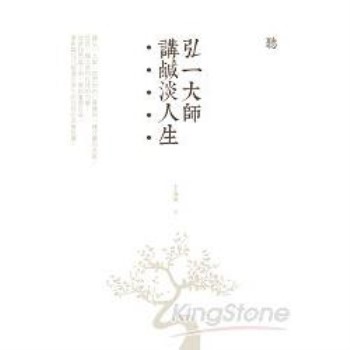二、清澈似水,利世而不爭
余秋雨在《都江堰》中寫道:「水,看似柔順無骨,卻能變得氣勢滾滾,波湧浪疊,無比強大;看似無色無味,卻能揮灑出茫茫綠野,累累碩果,萬紫千紅;看似自處低下,卻能蒸騰九霄,為雲為雨,為虹為霞;看似沒有造型,卻能作為滋潤萬物的救星而被殷殷期盼……」水如此,那似水的人呢?己身清澈,利世而不爭。紅了野花,綠了小草,喜了山雀,美了天空,李叔同只做一條靜靜流淌於山腳的小溪。
最難得浪子回頭
佛說:「以恨對恨,恨永遠存在;以愛對恨,恨自然消失。」
弘一大師勸誡信眾:「人褊急我受之以寬容,人險仄我待之以坦蕩。」
或許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種說教,或許很多人會對此不以為然、嗤之以鼻。然而,一個真正心胸寬廣的人,必定能理解這些話語,因為他領略過心如碧海的境界。那是遠離憤恨、惱怒、不甘、怨尤等種種負面情緒的地方,那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陽光、快樂、鮮花、彩霞等美好的辭彙紛紛湧入心間。
一個人因為犯罪而進了監獄,隨著出獄日子的臨近,他越來越焦躁不安。因為他害怕!他不敢回家,不敢面對妻子和兒女。他想:「我的妻子見到我,會怎麼樣呢?她會不會憤怒地罵我呢?指責我給家庭蒙羞,使親人抬不起頭呢?肯定會的!我讓她一個人承受生活的重擔,她一定不會原諒我了,不會再愛我了。」他不停地想,簡直要絕望了。最後,他給妻子寫了一封信:「如果你願意讓我回家的話,在我們家房前的樹上繫一條黃絲帶;如果你不願意,就不用繫了。」出獄的日子到了,他忐忑不安地向家的方向走去。快走到家的時候,他遠遠地望見自家房前的樹上繫滿了黃絲帶,正隨風飄蕩,而他的妻子,正帶著兒女在樹下朝他微笑……
即使是神,也不是只對不錯的。少多少怨恨便會增加多少快樂。使人從狹隘自私中解脫的是寬容。對家人寬容,收穫的是團聚、圓滿的親情;對他人寬容,收穫的是輕鬆、快慰的心情。一顆不肯寬容的心,只會使事情變得更糟糕,心情變得更壞,只會使自己陷入痛苦中不能自拔;寬容不在,很多不幸的事便不可避免,使人追悔莫及。
朝陽升起之前,廟前山門外凝滿露珠的春草裡,跪著一個人:「師父,請原諒我。」
他是某城風流的浪子。二十年前他曾是廟裡的小和尚,極得方丈寵愛。方丈將畢生所學全數教授,希望他能成為出色的佛門弟子。他卻在一夜間動了凡心,偷偷下了山;色彩繽紛的城市,迷住了他的眼目,從此花街柳巷,他只管放浪形骸。夜夜都是春,卻夜夜不是春。二十年後的一個深夜,他陡然驚醒,窗外月色如洗,澄清明澈地灑在他的掌心。他忽然懺悔了,披衣而起,快馬加鞭趕往寺裡。
「師父,您肯饒恕我,再收我做徒弟嗎?」方丈深深厭惡他的放蕩,只是搖頭說:「不,你罪孽深重,必墮阿鼻地獄,要想佛祖饒恕,除非連桌子也會開花。」浪子失望地離開了。
第二天早上,方丈踏進佛堂的時候,驚呆了:一夜間,佛桌上開滿了大簇大簇的花朵,紅的,白的,每一朵都芳香逼人,佛堂裡一絲風也沒有,那些盛開的花朵卻簌簌急搖,彷彿在焦灼地召喚著誰。方丈頓大徹大悟,他連忙下山尋找浪子,卻已經來不及了,心灰意冷的浪子,又重新墮入他過去的荒唐生活。
而佛桌上開出的那些花朵,只開放了短短的一天。是夜,方丈圓寂,臨終遺言:「這世上,沒有什麼歧途不可以回頭,沒有什麼錯誤不可以改正。」
「浪子回頭金不換」,一顆真誠向善的心,是最罕有的奇蹟,好像佛桌上開出的花朵。讓奇蹟隕滅的不是錯誤,而是一顆冰冷、不肯原諒、不肯相信的心。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人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工作,就難免會犯錯誤,錯了並沒有什麼,知錯能改才是最重要的。當別人犯了錯誤的時候,以寬容的心態來對待他們,給他們反省的機會。寬容是一種無聲的教育。一個寬容的人,可收穫和諧圓滿,笑對人生。
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
武器可以殺死人,卻不能征服人心。
真正能征服人心的,不是武器,而是道德。
道理能征服人,主要靠真理的力量;道德能征服人,主要靠人格的力量。人格和德行作為一種非智力因素,儘管不是道理,但往往勝於道理。從某種意義上說,德行是形象的道理,道理是抽象的德行。
弘一大師未出家前,曾給學生講解了他對「先器識而後文藝」的理解。在他看來,要首重人格修養,次重文藝學習,具體地說,要想做一個好的文藝家,必須先做一個好人。這是李叔同的文藝觀,也是他的人生觀。出家後的李叔同,也是先做一個好和尚後,研究佛法的。正是由於他的人格魅力,受其感召而皈依佛門者不計其數。
佛教是一個非常講究以品德去感召他人的宗教,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就真正做到了以德服人。他曾自己掃地、自己修葺房屋、為弟子裁衣、為老人穿針、照顧生病的弟子等。他的每一個行為都可作為他人的模範,展現出了內在高尚的品德,正是他的這種品德,最終讓佛法發揚光大。
有位青年脾氣很暴躁,經常和別人打架,大家都不喜歡他。
有一天,這位青年無意中遊蕩到了大德寺,碰巧聽到一位禪師在說法。他聽完後發誓痛改前非,於是對禪師說:「師父,我以後再也不跟人家打架、鬥口角了,免得人見人煩,就算是別人朝我臉上吐口水,我也只是忍耐地擦去,默默地承受!」
禪師聽了青年的話,笑著說:「哎,何必呢?就讓口水自己乾了吧,何必擦掉呢?」
青年聽後,有些驚訝,於是問禪師:「那怎麼可能呢?為什麼要這樣忍受呢?」
禪師說:「這沒有什麼能不能忍受的,你就把它當做蚊蟲之類的停在臉上,不值得與它打架或者罵它。雖然被吐了口水,但並不是什麼侮辱,就微笑著接受吧!」
青年又問:「如果對方不是吐口水,而是用拳頭打過來,那可怎麼辦呢?」
禪師回答:「這不一樣嗎?不要太在意!這只不過一拳而已。」
青年聽了,認為禪師實在是豈有此理,終於忍耐不住了,舉起拳頭,向禪師的頭上打去,並問:「和尚,現在怎麼辦呢?」
禪師非常關切地說:「我的頭硬得像石頭,並沒有什麼感覺,但是你的手大概打疼了吧?」青年愣在那裡,已是無話可說。
禪師告訴青年的是「德」,「德」不是空口的說教,而是實際的行動。正是如此,才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裡的「人和」,便是一種高尚的品德。這種品德具有巨大的力量,使人心悅誠服,有時甚至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不戰而百國來朝。
戰國時,齊宣王想做霸主,便向孟子請教。孟子說他不講霸道,只講王道,希望齊宣王行仁政,用道德的力量來統一天下。並說,對於國君來說,是否這樣做,只存在肯為不肯為的問題,不存在能做不能做的問題。
接著,孟子舉了一個有名的例子,他說:「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把泰山夾在胳膊底下跳過北海,告訴人說:「這個我辦不到。」這真是不能。替老年人折取樹枝,告訴人說:「這個我辦不到。」這是不肯做,不是不能做。大王您的不行仁政,不是屬於把泰山夾在胳膊底下跳過北海一類,而是屬於替老年折取樹枝一類。孟子所舉的這個例子是很有說服力的。對於我們來說,是否做社會道德的實踐者,也是一個肯為不肯為的問題,而不是能做不能做的問題。
對於一個國家,尚且可以用道德的王道來加以征服,那麼,對於個人而言則更是如此。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不但能夠使自己成就不凡的人生,而且可以感化周圍的人,使善的力量遍及人間。因此,我們生活中的每個人,即使從來沒有了解過佛法,只要能夠培養自己的品德,做道德的踐行者,並造福周圍的人,那就離佛的境界不遠了。
千教萬教,言傳身教
李叔同未出家前,曾從事很長時間的教育工作。陶行知曾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李叔同堪稱一位極其優秀的教師,他的一言一行,都很好地為這句話做了註解。我們可以用陶行知的一句話,來形容李叔同對教學工作的理解:「先生不應該專教書,他的責任是教人做人;學生不應該專讀書,他的責任是學習人生之道。」
教人做人,李叔同從來不是照本宣科地呆板講解,而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打動學生。
一次,李叔同給學生們上音樂課,一個學生在下面偷偷摸摸看別的書,李叔同發現後並沒有說什麼。只是等到下課後,把那位學生叫到自己面前,也不斥責,只說:「下次上課不要看別的書。」然後深深鞠了一躬。
還有一次,剛下課,一位學生便猛地推開門,李叔同只聽得「啪」的一聲,那位學生留給他一個背影,很快便不見人影了。後來,李叔同把那位學生叫到自己身邊,對他說:「下次走出教室,輕輕關門。」然後深深鞠了一躬。
向學生鞠躬的李叔同是令人感動的!在學校中,有幾個老師肯向學生鞠躬啊?教育是神聖的,只有視教育為神聖使命的人,才會在學生面前鞠躬。很多沒沒無聞的教育者,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向學生傳達人生的道理。
一位走出大學校門的學生,曾這樣回憶他的一位大學老師:
我們新生報到後不久,一天上文學課,上課鈴聲響起,我快步跑向教室門口,正巧一個樸素的男孩子也來到門口,他看到我,將身體側了側,說:「女士先請。」我沒多想,刺溜一下躥到自己的座位上。再抬頭一看,只見那名男生走到講台前,緩緩開口:「大家好,我是你們的古文老師……」
這位古文老師每次上完課,都會親自把黑板擦得乾乾淨淨。他的衣著總是樸素而簡潔,他待人總是真誠有禮,他的課也總是意趣橫生,很快,他便成了全班同學崇拜的對象。那時候,因為趙本山的小品中,一句「小樣的,穿馬甲我就不認識你啦」,導致全中國馬甲滯銷。我們的古文老師卻常穿一件藍色的馬甲。班裡的男同學於是都紛紛效仿,在那個馬甲蕭條的年代,因為古文老師,它在我們班蔚然成風……
國外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曾說過:「世界上沒有不好的學生,只有不好的老師。」上文那位同學記憶中的老師,之所以如此讓人難以忘懷,是因為老師生活上的寬厚和樸素,工作上的認真和自律,深深吸引了學生們,這是他人格上的魅力。
現在是一個越來越重視教育、教育者越來越多的時代,教育者,影響的是一代人、數代人,他們的自身素質是教育的重中之重。
千教萬教,不如言傳身教!
因為多情而出家
無情無性的不是佛,而是魔。
弘一大師割捨了妻兒子女,在世人眼中是無情的。然而,這種對親人的無情,恰恰反映出了他對世人的有情。
人們常說:「自古忠孝不能兩全。」弘一大師對人生終極意義的追求,與他的世俗家庭生活是矛盾的。他曾說:「在我二十三到二十六歲之間,是最幸福的。後來的一切都充滿了悲傷與哀痛,直到出家前。」他因為現實的痛苦無法擺脫而出家,但這不是逃避的出家,而是為了尋找答案,尋找解除世人心靈苦楚的答案而出家!
人們說:「情到深處轉無情。」或許,他對人生的感情太深,所以才不肯將就,所以才非要徹底地清楚明白,這種堅決的態度,使他決絕地出家。但他不是無情的,而是多情的,正如佛祖釋迦牟尼一樣,因為多情,才出家。
釋迦牟尼佛原是喜馬拉雅山山麓和恆河之間釋迦部落的太子,原名悉達多。
一次,他和父王郊遊,看見田中的農人,赤體裸背在烈日之下耕作;老牛拖著犁不得休息,還被鞭打得皮破血流;又見農田中被犁翻出的小蟲、蚯蚓,被鳥雀競相啄食,慘痛萬分。看到這樣一幅活生生的生存鬥爭圖,他心中感到無限的哀痛。他就在閻浮樹下,端坐沉思。淨飯王找到他,問他為何如此,他說:「看見世間眾生互相吞食,心中感到萬分難過,所以坐在這裡沉思。」
某天,他乘車到了東門,於人群中看見一個老人,髮白面皺,骨瘦如柴,手持柺杖,行動極其困難。車經南門,又看見一個病者,身瘦腹大,喘息呻吟,痛苦萬狀地在道旁掙扎。後來到了西門,遇到一族人抬著一具屍體。那屍體膿血流溢,惡臭難聞,隨行的親屬,痛哭流涕,使睹者心酸。悉達多看到此等情狀,感慨萬分。想到世人不拘富貴貧賤,都逃不過老病死的大關,乃歎道:「日月易過,少年不常,老至如電,身形不支,氣力衰虛,坐起苦極,我雖富貴,豈能獨免,念及將來,甚可畏驚。」
悉達多的所見所聞,使他思考:為什麼大多數人過著艱難困苦的生活呢?為什麼人生常常遭受挫折和不幸呢?為什麼每個人最後都難以逃脫死亡的命運呢?……為了得到人生諸多問題的答案,悉達多離開了王宮,離開了自己的父母、妻兒,出家修行。他三十五歲時,獨自坐在尼連禪河邊佛陀伽耶附近一棵菩提樹下,努力探索人生問題。經過七天七夜的苦思冥想,戰勝了種種煩惱魔障,終於在黎明時豁然開朗,徹悟了人生無盡苦惱的根源和解脫輪迴的方法。
弘一大師的出家,和釋迦牟尼佛類似,他同情當時社會中眾多受苦受難的民眾,對生老病死、一切無常生起了厭離心。有句話說:「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若想尋求人生真諦,又何必出家呢?可能對於弘一大師而言,選擇了出家的形式,便可以使他脫離人世間的各種無用的關係和煩惱事,專心致志地思考。況且,宗教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在探索的過程中,實踐了各種各樣的修行方法,如果不出家,他是沒有辦法那麼做的。
余秋雨在《都江堰》中寫道:「水,看似柔順無骨,卻能變得氣勢滾滾,波湧浪疊,無比強大;看似無色無味,卻能揮灑出茫茫綠野,累累碩果,萬紫千紅;看似自處低下,卻能蒸騰九霄,為雲為雨,為虹為霞;看似沒有造型,卻能作為滋潤萬物的救星而被殷殷期盼……」水如此,那似水的人呢?己身清澈,利世而不爭。紅了野花,綠了小草,喜了山雀,美了天空,李叔同只做一條靜靜流淌於山腳的小溪。
最難得浪子回頭
佛說:「以恨對恨,恨永遠存在;以愛對恨,恨自然消失。」
弘一大師勸誡信眾:「人褊急我受之以寬容,人險仄我待之以坦蕩。」
或許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種說教,或許很多人會對此不以為然、嗤之以鼻。然而,一個真正心胸寬廣的人,必定能理解這些話語,因為他領略過心如碧海的境界。那是遠離憤恨、惱怒、不甘、怨尤等種種負面情緒的地方,那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陽光、快樂、鮮花、彩霞等美好的辭彙紛紛湧入心間。
一個人因為犯罪而進了監獄,隨著出獄日子的臨近,他越來越焦躁不安。因為他害怕!他不敢回家,不敢面對妻子和兒女。他想:「我的妻子見到我,會怎麼樣呢?她會不會憤怒地罵我呢?指責我給家庭蒙羞,使親人抬不起頭呢?肯定會的!我讓她一個人承受生活的重擔,她一定不會原諒我了,不會再愛我了。」他不停地想,簡直要絕望了。最後,他給妻子寫了一封信:「如果你願意讓我回家的話,在我們家房前的樹上繫一條黃絲帶;如果你不願意,就不用繫了。」出獄的日子到了,他忐忑不安地向家的方向走去。快走到家的時候,他遠遠地望見自家房前的樹上繫滿了黃絲帶,正隨風飄蕩,而他的妻子,正帶著兒女在樹下朝他微笑……
即使是神,也不是只對不錯的。少多少怨恨便會增加多少快樂。使人從狹隘自私中解脫的是寬容。對家人寬容,收穫的是團聚、圓滿的親情;對他人寬容,收穫的是輕鬆、快慰的心情。一顆不肯寬容的心,只會使事情變得更糟糕,心情變得更壞,只會使自己陷入痛苦中不能自拔;寬容不在,很多不幸的事便不可避免,使人追悔莫及。
朝陽升起之前,廟前山門外凝滿露珠的春草裡,跪著一個人:「師父,請原諒我。」
他是某城風流的浪子。二十年前他曾是廟裡的小和尚,極得方丈寵愛。方丈將畢生所學全數教授,希望他能成為出色的佛門弟子。他卻在一夜間動了凡心,偷偷下了山;色彩繽紛的城市,迷住了他的眼目,從此花街柳巷,他只管放浪形骸。夜夜都是春,卻夜夜不是春。二十年後的一個深夜,他陡然驚醒,窗外月色如洗,澄清明澈地灑在他的掌心。他忽然懺悔了,披衣而起,快馬加鞭趕往寺裡。
「師父,您肯饒恕我,再收我做徒弟嗎?」方丈深深厭惡他的放蕩,只是搖頭說:「不,你罪孽深重,必墮阿鼻地獄,要想佛祖饒恕,除非連桌子也會開花。」浪子失望地離開了。
第二天早上,方丈踏進佛堂的時候,驚呆了:一夜間,佛桌上開滿了大簇大簇的花朵,紅的,白的,每一朵都芳香逼人,佛堂裡一絲風也沒有,那些盛開的花朵卻簌簌急搖,彷彿在焦灼地召喚著誰。方丈頓大徹大悟,他連忙下山尋找浪子,卻已經來不及了,心灰意冷的浪子,又重新墮入他過去的荒唐生活。
而佛桌上開出的那些花朵,只開放了短短的一天。是夜,方丈圓寂,臨終遺言:「這世上,沒有什麼歧途不可以回頭,沒有什麼錯誤不可以改正。」
「浪子回頭金不換」,一顆真誠向善的心,是最罕有的奇蹟,好像佛桌上開出的花朵。讓奇蹟隕滅的不是錯誤,而是一顆冰冷、不肯原諒、不肯相信的心。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人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工作,就難免會犯錯誤,錯了並沒有什麼,知錯能改才是最重要的。當別人犯了錯誤的時候,以寬容的心態來對待他們,給他們反省的機會。寬容是一種無聲的教育。一個寬容的人,可收穫和諧圓滿,笑對人生。
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
武器可以殺死人,卻不能征服人心。
真正能征服人心的,不是武器,而是道德。
道理能征服人,主要靠真理的力量;道德能征服人,主要靠人格的力量。人格和德行作為一種非智力因素,儘管不是道理,但往往勝於道理。從某種意義上說,德行是形象的道理,道理是抽象的德行。
弘一大師未出家前,曾給學生講解了他對「先器識而後文藝」的理解。在他看來,要首重人格修養,次重文藝學習,具體地說,要想做一個好的文藝家,必須先做一個好人。這是李叔同的文藝觀,也是他的人生觀。出家後的李叔同,也是先做一個好和尚後,研究佛法的。正是由於他的人格魅力,受其感召而皈依佛門者不計其數。
佛教是一個非常講究以品德去感召他人的宗教,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就真正做到了以德服人。他曾自己掃地、自己修葺房屋、為弟子裁衣、為老人穿針、照顧生病的弟子等。他的每一個行為都可作為他人的模範,展現出了內在高尚的品德,正是他的這種品德,最終讓佛法發揚光大。
有位青年脾氣很暴躁,經常和別人打架,大家都不喜歡他。
有一天,這位青年無意中遊蕩到了大德寺,碰巧聽到一位禪師在說法。他聽完後發誓痛改前非,於是對禪師說:「師父,我以後再也不跟人家打架、鬥口角了,免得人見人煩,就算是別人朝我臉上吐口水,我也只是忍耐地擦去,默默地承受!」
禪師聽了青年的話,笑著說:「哎,何必呢?就讓口水自己乾了吧,何必擦掉呢?」
青年聽後,有些驚訝,於是問禪師:「那怎麼可能呢?為什麼要這樣忍受呢?」
禪師說:「這沒有什麼能不能忍受的,你就把它當做蚊蟲之類的停在臉上,不值得與它打架或者罵它。雖然被吐了口水,但並不是什麼侮辱,就微笑著接受吧!」
青年又問:「如果對方不是吐口水,而是用拳頭打過來,那可怎麼辦呢?」
禪師回答:「這不一樣嗎?不要太在意!這只不過一拳而已。」
青年聽了,認為禪師實在是豈有此理,終於忍耐不住了,舉起拳頭,向禪師的頭上打去,並問:「和尚,現在怎麼辦呢?」
禪師非常關切地說:「我的頭硬得像石頭,並沒有什麼感覺,但是你的手大概打疼了吧?」青年愣在那裡,已是無話可說。
禪師告訴青年的是「德」,「德」不是空口的說教,而是實際的行動。正是如此,才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裡的「人和」,便是一種高尚的品德。這種品德具有巨大的力量,使人心悅誠服,有時甚至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不戰而百國來朝。
戰國時,齊宣王想做霸主,便向孟子請教。孟子說他不講霸道,只講王道,希望齊宣王行仁政,用道德的力量來統一天下。並說,對於國君來說,是否這樣做,只存在肯為不肯為的問題,不存在能做不能做的問題。
接著,孟子舉了一個有名的例子,他說:「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把泰山夾在胳膊底下跳過北海,告訴人說:「這個我辦不到。」這真是不能。替老年人折取樹枝,告訴人說:「這個我辦不到。」這是不肯做,不是不能做。大王您的不行仁政,不是屬於把泰山夾在胳膊底下跳過北海一類,而是屬於替老年折取樹枝一類。孟子所舉的這個例子是很有說服力的。對於我們來說,是否做社會道德的實踐者,也是一個肯為不肯為的問題,而不是能做不能做的問題。
對於一個國家,尚且可以用道德的王道來加以征服,那麼,對於個人而言則更是如此。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不但能夠使自己成就不凡的人生,而且可以感化周圍的人,使善的力量遍及人間。因此,我們生活中的每個人,即使從來沒有了解過佛法,只要能夠培養自己的品德,做道德的踐行者,並造福周圍的人,那就離佛的境界不遠了。
千教萬教,言傳身教
李叔同未出家前,曾從事很長時間的教育工作。陶行知曾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李叔同堪稱一位極其優秀的教師,他的一言一行,都很好地為這句話做了註解。我們可以用陶行知的一句話,來形容李叔同對教學工作的理解:「先生不應該專教書,他的責任是教人做人;學生不應該專讀書,他的責任是學習人生之道。」
教人做人,李叔同從來不是照本宣科地呆板講解,而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打動學生。
一次,李叔同給學生們上音樂課,一個學生在下面偷偷摸摸看別的書,李叔同發現後並沒有說什麼。只是等到下課後,把那位學生叫到自己面前,也不斥責,只說:「下次上課不要看別的書。」然後深深鞠了一躬。
還有一次,剛下課,一位學生便猛地推開門,李叔同只聽得「啪」的一聲,那位學生留給他一個背影,很快便不見人影了。後來,李叔同把那位學生叫到自己身邊,對他說:「下次走出教室,輕輕關門。」然後深深鞠了一躬。
向學生鞠躬的李叔同是令人感動的!在學校中,有幾個老師肯向學生鞠躬啊?教育是神聖的,只有視教育為神聖使命的人,才會在學生面前鞠躬。很多沒沒無聞的教育者,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向學生傳達人生的道理。
一位走出大學校門的學生,曾這樣回憶他的一位大學老師:
我們新生報到後不久,一天上文學課,上課鈴聲響起,我快步跑向教室門口,正巧一個樸素的男孩子也來到門口,他看到我,將身體側了側,說:「女士先請。」我沒多想,刺溜一下躥到自己的座位上。再抬頭一看,只見那名男生走到講台前,緩緩開口:「大家好,我是你們的古文老師……」
這位古文老師每次上完課,都會親自把黑板擦得乾乾淨淨。他的衣著總是樸素而簡潔,他待人總是真誠有禮,他的課也總是意趣橫生,很快,他便成了全班同學崇拜的對象。那時候,因為趙本山的小品中,一句「小樣的,穿馬甲我就不認識你啦」,導致全中國馬甲滯銷。我們的古文老師卻常穿一件藍色的馬甲。班裡的男同學於是都紛紛效仿,在那個馬甲蕭條的年代,因為古文老師,它在我們班蔚然成風……
國外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曾說過:「世界上沒有不好的學生,只有不好的老師。」上文那位同學記憶中的老師,之所以如此讓人難以忘懷,是因為老師生活上的寬厚和樸素,工作上的認真和自律,深深吸引了學生們,這是他人格上的魅力。
現在是一個越來越重視教育、教育者越來越多的時代,教育者,影響的是一代人、數代人,他們的自身素質是教育的重中之重。
千教萬教,不如言傳身教!
因為多情而出家
無情無性的不是佛,而是魔。
弘一大師割捨了妻兒子女,在世人眼中是無情的。然而,這種對親人的無情,恰恰反映出了他對世人的有情。
人們常說:「自古忠孝不能兩全。」弘一大師對人生終極意義的追求,與他的世俗家庭生活是矛盾的。他曾說:「在我二十三到二十六歲之間,是最幸福的。後來的一切都充滿了悲傷與哀痛,直到出家前。」他因為現實的痛苦無法擺脫而出家,但這不是逃避的出家,而是為了尋找答案,尋找解除世人心靈苦楚的答案而出家!
人們說:「情到深處轉無情。」或許,他對人生的感情太深,所以才不肯將就,所以才非要徹底地清楚明白,這種堅決的態度,使他決絕地出家。但他不是無情的,而是多情的,正如佛祖釋迦牟尼一樣,因為多情,才出家。
釋迦牟尼佛原是喜馬拉雅山山麓和恆河之間釋迦部落的太子,原名悉達多。
一次,他和父王郊遊,看見田中的農人,赤體裸背在烈日之下耕作;老牛拖著犁不得休息,還被鞭打得皮破血流;又見農田中被犁翻出的小蟲、蚯蚓,被鳥雀競相啄食,慘痛萬分。看到這樣一幅活生生的生存鬥爭圖,他心中感到無限的哀痛。他就在閻浮樹下,端坐沉思。淨飯王找到他,問他為何如此,他說:「看見世間眾生互相吞食,心中感到萬分難過,所以坐在這裡沉思。」
某天,他乘車到了東門,於人群中看見一個老人,髮白面皺,骨瘦如柴,手持柺杖,行動極其困難。車經南門,又看見一個病者,身瘦腹大,喘息呻吟,痛苦萬狀地在道旁掙扎。後來到了西門,遇到一族人抬著一具屍體。那屍體膿血流溢,惡臭難聞,隨行的親屬,痛哭流涕,使睹者心酸。悉達多看到此等情狀,感慨萬分。想到世人不拘富貴貧賤,都逃不過老病死的大關,乃歎道:「日月易過,少年不常,老至如電,身形不支,氣力衰虛,坐起苦極,我雖富貴,豈能獨免,念及將來,甚可畏驚。」
悉達多的所見所聞,使他思考:為什麼大多數人過著艱難困苦的生活呢?為什麼人生常常遭受挫折和不幸呢?為什麼每個人最後都難以逃脫死亡的命運呢?……為了得到人生諸多問題的答案,悉達多離開了王宮,離開了自己的父母、妻兒,出家修行。他三十五歲時,獨自坐在尼連禪河邊佛陀伽耶附近一棵菩提樹下,努力探索人生問題。經過七天七夜的苦思冥想,戰勝了種種煩惱魔障,終於在黎明時豁然開朗,徹悟了人生無盡苦惱的根源和解脫輪迴的方法。
弘一大師的出家,和釋迦牟尼佛類似,他同情當時社會中眾多受苦受難的民眾,對生老病死、一切無常生起了厭離心。有句話說:「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若想尋求人生真諦,又何必出家呢?可能對於弘一大師而言,選擇了出家的形式,便可以使他脫離人世間的各種無用的關係和煩惱事,專心致志地思考。況且,宗教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在探索的過程中,實踐了各種各樣的修行方法,如果不出家,他是沒有辦法那麼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