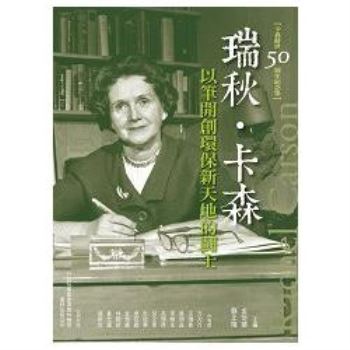瑞秋.卡森──以筆開創環保新天地的鬪士
王瑞香
瑞秋.卡森一生寫作不輟,她的筆耕生涯始於對海洋的愛,而終於對正義的追求。「卡森」這名字總使人想到《無聲的春天》一書,但,除了這本掀起現代環保運動的名著之外,卡森女士還留給世人別的寶貴遺產。終其一生,卡森熱愛兩樣事物:一是海洋,一是寫作。完成於她生命最後階段的《無聲的春天》其實是責無旁貸的良心之作,而她膾炙人口的人稱「海洋三部曲」的三本海洋書寫則真正結合了她的兩項最愛。回顧她緊湊的一生,讓人不禁想:若有選擇,卡森寫於她生命最脆弱時刻的最後一本著作,該不是這樣一本使她捲入一場與化工業之大戰的暮鼓晨鐘之作,而會是另一本揉合科學與詩意的自然書寫吧。
海洋三部曲
卡森因《無聲的春天》一書而舉世聞名,但這本書必須放在她較早作品的脈絡裡才能加以充分領會,才能了解它的衝擊力;也可以說,是她之前的海洋系列書寫為《無聲的春天》鋪了路。
卡森於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出生於美國賓州匹茲堡附近的一個小鎮,上有一姊一兄,從小喜歡閱讀;童年的一張照片捕捉到無憂無慮的卡森坐在草地上唸書給她的狗聽,這個令人會心一笑的畫面非常具有代表性。卡森也喜歡寫作,而且極有天分,十一歲即有作品發表。因為從小嚮往當作家,卡森大學時主修英文,但在大二時因受到生物老師史金克的啟發而轉攻生物學。這個重要的轉折為她日後的生涯鋪了路。
一九二九年夏天自大學畢業後,卡森在麻州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待了六個禮拜,當一名新手調查員。這年年底就開始了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和絕大多數的美國民眾一樣,卡森一家陷入經濟困境,她因而必須在課餘兼職。是年秋季她開始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讀,接下來幾個夏天都到伍茲霍爾作調查研究。
卡森在一九三二年完成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碩士學位。她亟想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無奈她幾乎沒有錢讀書,更何況家庭責任也不允許她繼續求學――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七年父親和姊姊相繼過世,她責無旁貸地挑起了撫養母親和兩個學齡甥女的擔子。一九三五年,二十八歲的卡森接受一項指派,為廣播電台撰寫一個名為「海底羅曼史」之節目的講稿,這份工作是個轉捩點,它結合了卡森的兩個特長:寫作才華與海洋科學學識。她的表現相當稱職,使得該廣播節目十分成功。為了家計,卡森同時也為《巴爾的摩太陽報》和《大西洋月刊》撰寫有關自然史的文章。從此,卡森便穩穩走在海洋書寫的道路上。次年,卡森在巴爾的摩市的美國漁業局謀了一份差事,頭銜為水生生物學家,成為該局所雇用的第二位女性全職專業雇員。
***
《無聲的春天》
卡森原本無意寫一本有關農藥的書,更無意當英雄,或和化工業搏鬪,而毋寧是那個時代的一些不尋常的事件將她扯進了那場戰爭。卡森無心插柳,但時代需要她――而她一切都準備好了,她便這樣走進了風暴裡。個性使然,她不能容許自己看見不公正而坐視不管,另一方面,她所具備的一切讓她認為自己責無旁貸――在專業上她是科學家,在個人方面她深愛自然,而身為暢銷作家她也知道她的筆所能發揮的力量。
從海洋轉向農藥
殺蟲劑和除草劑等化學物是如何進入人們的生活的?要探討這個問題必須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期間,生物學家、化學家、物理學家都被徵召去協助軍隊,新科技因而蓬勃發展。戰後,科學家和企業家利用這個成果發展出商品,俾以改善國民的生活品質,一九三九年發展出來的「二氯二苯三氯乙烷」(縮寫為DDT)便是其中一例。DDT 是強效殺蟲劑,能有效制止傷寒、瘧疾及其他由昆蟲傳染之疾病的擴散,在大戰期間拯救了無數的性命因而聲名大噪;它替美軍消滅了南太平洋島嶼上傳播瘧疾的昆蟲,而在歐洲,它被用來消滅頭蝨。戰後,美國農業部和企業推銷DDT 及其他強效化學物來對抗各種疾病,增加國內生產力。美國的DDT 產量在一九四四到一九六三年不到十年的期間便增加了將近二十倍,而DDT 的使用從一九四五年起用量遽增,已成為一般人唾手可得的農藥。當時,只有少數人對DDT 這個新的神奇化合物表達保留的看法,其中包括卡森和自然寫作名家提爾。提爾曾警告:「像DDT 這樣不分青紅皂白的農藥噴灑對自然界經濟所造成的擾亂,就像革命對社會經濟所帶來的干擾一樣。所有的昆蟲有百分之九十是有益的,若殺死了牠們,一切就立刻失去平衡。」卡森接二連三得知因為濫用DDT 這類氯化碳氫化合物而造成田地汙染、殃及許多無辜鳥獸的事件。她認為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曾向《讀者文摘》提出一篇有關DDT 危害環境之證明的文章,但遭退稿。當時她的主要關注仍在於海洋與海岸環境,還在撰寫這些議題的相關書籍。
一九四八年,美國醫藥協會警告,包括DDT 在內的大部分新出品的農藥對人類所帶來的長期毒力「是完全未經探查的」。不過,像這樣的警告鮮少為科學圈以外的公眾所知。一九五○、一九五一年當DDT 在食物裡的殘留成為大家所關心的議題時,國會也曾就食品添加物之安全的議題舉行聽證會,而制定有關化學物必須註冊、檢測的一些新法規。但無論如何,DDT 和其他農藥仍繼續為人們所使用。
一九五八年,一封信函重新觸動卡森撰寫有關DDT 之危險的念頭。她的友人娥嘉.哈金斯寫信向她透露,DDT 的噴灑造成大量鳥隻死在她位於麻州的一座私人鳥類禁獵區裡。該地區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曾進行空中噴灑農藥的滅蚊計畫,哈金斯希望卡森能透過華府相關人士的協助以停止這項噴灑行動。
卡森得知,各種針對掠食動物與獵物的控制計畫將農藥大量散佈到環境裡,毫不顧慮農藥對標的害物以外的生物所造成的後果。卡森再次向雜誌社提議派她撰寫有關DDT 效應的報導,但再度失敗。在一九五八年,卡森已是暢銷作家,卻仍無法說動雜誌社派她報導DDT 事件,這事實說明了卡森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在當時顯得多麼異端和具爭議性。然而,她仍決定深入了解,並詳盡蒐集、記錄有關農藥濫用的科學證據。當手頭掌握了相當的相關研究資料時,卡森決心撰寫一本有關DDT 的書,如她後來所說的:「我越了解農藥,就越感到震驚。我知道我有足夠的材料來寫一本書。我發現,身為自然學家的我最重要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脅,而這就是我能力所及最重要的任務。」卡森在最適恰的時刻成為最適恰的信使;她能見樹又見林,看見相同的情況在許多不同的環境的角落發生,並且知道要如何運用她所蒐集的科學資訊,以及用甚麼方式來呈現這整件事。決定寫書後卡森便更加積極蒐集資料:她和一些正在蒐集有關農藥影響環境之證據的科學家通訊、會晤;和某些官方科學家的往來有時讓她得到機密情報;她也前往聯邦機構以及國家研究圖書館,例如國家衛生研究院的醫學圖書館,挖掘資料。
卡森花了將近五年的時間將書寫成。
沒有不具詩意的海洋──關於瑞秋.卡森的「海洋三部曲」
吳明益
如果我談海洋的書裡有詩意,那不是因為我刻意注入詩情,而是因為真實地描寫海洋時,沒有人能夠排除詩意。(瑞秋.卡森)
一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我在光華商場地下樓的一家舊書店邂逅了一本外表看來頗為質樸的書――瑞秋.卡森的《海風下》。書的封面已然破損,舊書店的老板因而使用紙張將書包起來,用簽字筆寫上書名。彼時開始對自然書寫感興趣的我,打開書的那一刻,就被海風帶離了小小的書店空間,再下一刻清醒時,發現自己已經在書架前站了一下午,把書讀完大半了。
《海風下》是一九四一年,卡森三十五歲的作品,也正是日本偷襲珍珠港那一年。這本描述海岸生態,並且以海洋生物視野構思的作品,僅僅賣出兩千餘本。我以為這也暗示了,文學性格強的自然書寫,未必有像直接關涉即時議題的「環境啟示錄」一樣容易引起讀者關注;相對地,它們就像有恆久耐心的海浪,逐步為海岸塑型。
這本書也打開了我認識卡森女士真正的開始。她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個決意對抗龐大勢力的環境鬪士,而是因為從心智上、科學上累積的對海洋的情感,終究使得她在大地受傷時挺身而出,在這過程中,她的信念就如同文學在她體內的作用,是一種平靜、複沓、頑強如海浪的力量。也因此,我以為要真正認識卡森女士,不能只看她的環境啟示錄,也要看她柔軟、深刻的文學性自然書寫。
二
瑞秋從小就對動物故事深感興趣,她最喜歡的作家是赫爾曼•梅爾維爾、約瑟夫•康拉德、羅伯特•路易士•史蒂文生。這裡頭似乎有著寓言式的宿命――這幾位作家的重要作品,都離不開海洋。
卡森在就讀賓夕法尼亞女子學院時,原本以文學為主修,卻在聽了一門生物課程後激起了熱烈的興趣,並且覺得自己在寫作上缺乏想像力,於是決定轉修生物學,最後在霍普金斯大學獲動物學碩士學位,並且在畢業後任職於麻薩諸塞州的伍玆霍爾海洋生物實驗室。那是一個「不論從那個方向走不了多遠,就會遇到海」的地方,也是瑞秋走入海洋的開始。然而因為父親驟逝,家中經濟負擔落在她身上,她只得在漁業管理局找份兼職工作,並且替電台專有頻道廣播撰寫科技文章來換取收入。由於當時行政部門對女性仍有很深的就業歧視,卡森是漁業管理局第二位受聘的女性,這印證了她具有優秀的專業能力。
在廣播節目結束後,她的部門主管艾默.希金斯希望以廣播的內容為漁業局製作一系列介紹海洋生物的小冊子,並且要她寫一篇導言。瑞秋完成了這篇大約有二十五頁的長導言,寫作時她刻意避免了文學性筆法,希望能拋開「人為偏見」,並且叮嚀自己「說故事的人不能進入故事」。然而,瑞秋或許也因此發現自己體內的文學欲望並未死去,因為稿子交到希金斯的手上後,他仍舊認為這篇文章太具有文學性,不適合當作一本介紹海洋生物手冊的導言。然而文章又寫得太迷人,他因而建議她投到《大西洋月刊》。
這篇文章就是《海風下》寫作的開始。
***
三
我有時候會想,如果瑞秋.卡森只是一個卓越的、負有聲望的女科學家,那麼《無聲的春天》還會不會引起那麼巨大的社會迴響?我對這個問題是有預想答案的,那就是卡森女士在「海洋三部曲」已經匯聚了一批讀者:有科學讀者、文學讀者,還有更多的愛聽故事的人。過去沒有人講海洋的科學故事給他們聽,而現在有一個了。
也因此,卡森累積了她的科學信用、文學信用,還有對自然環境的情感信用。
在早期的《海風下》,敏銳的讀者當可以讀到卡森向亨利.威廉森取法的敘事技巧:卡森讓黑剪嘴鷗「靈巧」,三趾鷸「黑腳兄」、「銀條」,旅鼠「伍文嘉」,魚鷹「潘東」,鯖魚「史康波」,鰻魚「安貴臘」,海鱒「席諾雄」,帶出動物「主觀鏡頭」的敘事。比方說,在寫到鯖魚的迴游時,卡森說:「鯖魚並不順著海的層次翻山過谷。離開冬眠地後,牠們好像急著立刻來到陽光照耀的上層,從百噚深處直直攀上水表。在深海的幽冥中待了四個月,鯖魚興奮地竄上明亮的水層,鼻頭伸出水面,看一眼鑲嵌在蒼穹下的浩渺海洋。」(1994:100) 而寫到三趾鷸,她描述:「海水在柔美的月色下泛著銀光,許多魷魚受光的吸引,心醉神搖地浮出表面,面向月光,在海上載浮載沉。牠們輕輕打水,凝視著月光後退,那麼專注,竟不知自己已漂入危險的灘頭,直待沙粒磨身,才驚覺過來。倒楣的魷魚受困淺灘,拚命打水只把自己推進更淺、水退只餘沙之處。早晨,三趾鷸一見天光便往退潮線覓食,發現海口灘頭散布著魷魚的屍體。」(1994:35)這樣的筆法正是被質疑為「太過文學」之處,畢竟說鯖魚「好像急著」、「興奮地」;魷魚「心醉神搖」,都是非科學性描寫的主觀感受。
但在這樣的描述底下,卡森要藉生物視野的變換表現的,是帶領讀者認識潮間帶、極地之海、海底、河口……流轉變動的環境,解釋海濱生態、海中生態以及海底生態的複雜面貌。
比方說,寫到剪嘴鷗的覓食,和潮水漲落是有深刻關係的:「潮水是日落時分退去的,現在重新漲起,淹沒了剪嘴鷗下午棲息的地盤,更沿海口而入,盈滿沼澤。剪嘴鷗大半夜都在覓食,輕振細長的雙翼,尋找隨潮水而來,躲藏在水草間的小魚。就因為牠們趁潮覓食,人家又管牠們叫『潮鷗』。」(1994:3) 而在魚群游過的洋流底下:「是海溝,海的太古之床,大西洋最深的地方。海溝之中無日月,百萬年的流逝都無意義,遑論季節的急遽變換。太陽在此深處毫無勢力,這裡的黑暗無始無終,亦無程度可言。熱帶的陽光再熾烈,也絲毫不能緩解海溝中水冬夏不分的冰寒。年月凝成世紀,世紀凝成地質年代,大洋盆底的水流總是沉緩嚴寒,從容不迫而又堅定不移,恰似時間之流本身。」(1994:235-6)有些科學家認為,這種將海洋知識順著帶點虛構文學的敘事角度表現出來的手法是危險的。即使是現在,如果一個自然書寫者運用這樣的技巧來寫作(內容並由專家校訂過),也一定會遭受部分人士的質疑與批判。但時過境遷,這部作品在世界上的流傳,完全展現了她做為一個文學作者的高度與天份。請讀讀以下的段落,不禁讓我想起她所說的,描寫海洋,沒有人能排除詩意:
鰻魚安桂臘埋首水中,隨著忙忙奔進溢洪道的池水而行。憑著敏銳的感覺,她嚐出水中特異的氣和味:是雨濕秋葉的苦澀,是林中苔蘚、地衣、腐植質的味道。含著這樣氣味的水,匆忙流過鰻魚身邊,往大海去。( 1994:1-2)
除了潮聲和鳥鳴,這晚全然寂靜。風沉睡著,海口有碎浪上灘的聲音,但遠方大海的鼓搗則淡成近乎嘆息,是一種有韻律的吐氣聲,彷彿海,也在峽灣的門戶外睡著了。
只有最靈敏的耳朵,才聽得見一隻寄居蟹拖著牠的殼屋,在水線上方沙灘上行走的聲音;也才辨別得出一隻小蝦被魚群追趕,匆忙上岸時抖落一身小水珠,在水面跌出的叮咚聲。但在這小島的夜晚,在海與海的邊緣,這些聲音是細微不可得聞的。(1994:10)
明春之前,這些鳥不會回返陸地。牠們要在海上過冬,共享海上的白晝與黑夜、暴風與寧靜、霰與雪、陽光與迷霧。(1994:157)
但做為一個科學家,卡森女士可能也知道她這樣的寫作方式不會獲得科學界的肯定。在寫作《周遭之海》時,開始大量引用研究者的論文、航海日誌,以及關於海的相關材料(如達爾文與康拉德的筆記與書),更強調信而有徵的自然史敘事。卡森在一九六○年新版的序裡強調她試著把一九五一年以前人類對海洋「最重要的新資訊」,都寫在這本書裡了。書中從海洋的形成、深海生態寫到海底火山、島嶼生態以及波浪與洋流的形成,最終談到海洋與人類的關係,卡森的筆下博學、睿智,而且還很「迷人」。比方說,卡森從地球生成寫起,寫到月球的誕生,與地球潮汐的關係,在當時科學界的推測:「下一次你在夜晚駐足於海灘,凝望著映照於海面的月華,覺察到月球所牽引的潮汐起伏時,請記得月球之所以形成,很可能是因為地球在某一次的大陸潮中,將地球物質拋入了太空。此外,也不要忘了,如果月球真的是以這種方式生成,這個事件也可能和我們所知的海盆與大陸的形成極有關聯。」(2006:23)
而海洋的形成,在卡森的筆下如同馬奎斯《百年孤寂》那場落不盡的雨一樣魔幻且詩意:「在地殼溫度冷卻到一定程度後,地表便開始降雨,從那時到現在,地球上再也不曾出現這種降雨情形,大雨日以繼夜不斷落下,連下了數天、數月、數年甚至數百年,雨水澆灌著空無一物的海盆,或落在大陸陸塊上,最後匯積成大海。」(2006:25) 這樣的海洋孕育了萬物,以致於「即使離開海洋而上岸生活,體內仍然帶著一部分的海洋,且這項特徵代代相傳,時至今日,仍能顯示所有陸生動物與牠們遠古時代海中先祖的關聯――無論是魚類、兩棲動物、爬蟲類、溫血鳥類還是哺乳動物,每一種生物血管內所流的血液,都和海水一樣帶有鹹味,甚至連鈉、鉀、鈣等元素的含量比例都幾乎相同。在數百萬年以前,生物的遠古始祖由單細胞進化成多細胞,而後更發展出循環系統,雖然當時在這些生物體內所循環的,不過只是海水,然而從那一天起,循環系統就成為我們代代相傳的特徵。」(2006:31)
王瑞香
瑞秋.卡森一生寫作不輟,她的筆耕生涯始於對海洋的愛,而終於對正義的追求。「卡森」這名字總使人想到《無聲的春天》一書,但,除了這本掀起現代環保運動的名著之外,卡森女士還留給世人別的寶貴遺產。終其一生,卡森熱愛兩樣事物:一是海洋,一是寫作。完成於她生命最後階段的《無聲的春天》其實是責無旁貸的良心之作,而她膾炙人口的人稱「海洋三部曲」的三本海洋書寫則真正結合了她的兩項最愛。回顧她緊湊的一生,讓人不禁想:若有選擇,卡森寫於她生命最脆弱時刻的最後一本著作,該不是這樣一本使她捲入一場與化工業之大戰的暮鼓晨鐘之作,而會是另一本揉合科學與詩意的自然書寫吧。
海洋三部曲
卡森因《無聲的春天》一書而舉世聞名,但這本書必須放在她較早作品的脈絡裡才能加以充分領會,才能了解它的衝擊力;也可以說,是她之前的海洋系列書寫為《無聲的春天》鋪了路。
卡森於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出生於美國賓州匹茲堡附近的一個小鎮,上有一姊一兄,從小喜歡閱讀;童年的一張照片捕捉到無憂無慮的卡森坐在草地上唸書給她的狗聽,這個令人會心一笑的畫面非常具有代表性。卡森也喜歡寫作,而且極有天分,十一歲即有作品發表。因為從小嚮往當作家,卡森大學時主修英文,但在大二時因受到生物老師史金克的啟發而轉攻生物學。這個重要的轉折為她日後的生涯鋪了路。
一九二九年夏天自大學畢業後,卡森在麻州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待了六個禮拜,當一名新手調查員。這年年底就開始了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和絕大多數的美國民眾一樣,卡森一家陷入經濟困境,她因而必須在課餘兼職。是年秋季她開始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讀,接下來幾個夏天都到伍茲霍爾作調查研究。
卡森在一九三二年完成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碩士學位。她亟想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無奈她幾乎沒有錢讀書,更何況家庭責任也不允許她繼續求學――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七年父親和姊姊相繼過世,她責無旁貸地挑起了撫養母親和兩個學齡甥女的擔子。一九三五年,二十八歲的卡森接受一項指派,為廣播電台撰寫一個名為「海底羅曼史」之節目的講稿,這份工作是個轉捩點,它結合了卡森的兩個特長:寫作才華與海洋科學學識。她的表現相當稱職,使得該廣播節目十分成功。為了家計,卡森同時也為《巴爾的摩太陽報》和《大西洋月刊》撰寫有關自然史的文章。從此,卡森便穩穩走在海洋書寫的道路上。次年,卡森在巴爾的摩市的美國漁業局謀了一份差事,頭銜為水生生物學家,成為該局所雇用的第二位女性全職專業雇員。
***
《無聲的春天》
卡森原本無意寫一本有關農藥的書,更無意當英雄,或和化工業搏鬪,而毋寧是那個時代的一些不尋常的事件將她扯進了那場戰爭。卡森無心插柳,但時代需要她――而她一切都準備好了,她便這樣走進了風暴裡。個性使然,她不能容許自己看見不公正而坐視不管,另一方面,她所具備的一切讓她認為自己責無旁貸――在專業上她是科學家,在個人方面她深愛自然,而身為暢銷作家她也知道她的筆所能發揮的力量。
從海洋轉向農藥
殺蟲劑和除草劑等化學物是如何進入人們的生活的?要探討這個問題必須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期間,生物學家、化學家、物理學家都被徵召去協助軍隊,新科技因而蓬勃發展。戰後,科學家和企業家利用這個成果發展出商品,俾以改善國民的生活品質,一九三九年發展出來的「二氯二苯三氯乙烷」(縮寫為DDT)便是其中一例。DDT 是強效殺蟲劑,能有效制止傷寒、瘧疾及其他由昆蟲傳染之疾病的擴散,在大戰期間拯救了無數的性命因而聲名大噪;它替美軍消滅了南太平洋島嶼上傳播瘧疾的昆蟲,而在歐洲,它被用來消滅頭蝨。戰後,美國農業部和企業推銷DDT 及其他強效化學物來對抗各種疾病,增加國內生產力。美國的DDT 產量在一九四四到一九六三年不到十年的期間便增加了將近二十倍,而DDT 的使用從一九四五年起用量遽增,已成為一般人唾手可得的農藥。當時,只有少數人對DDT 這個新的神奇化合物表達保留的看法,其中包括卡森和自然寫作名家提爾。提爾曾警告:「像DDT 這樣不分青紅皂白的農藥噴灑對自然界經濟所造成的擾亂,就像革命對社會經濟所帶來的干擾一樣。所有的昆蟲有百分之九十是有益的,若殺死了牠們,一切就立刻失去平衡。」卡森接二連三得知因為濫用DDT 這類氯化碳氫化合物而造成田地汙染、殃及許多無辜鳥獸的事件。她認為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曾向《讀者文摘》提出一篇有關DDT 危害環境之證明的文章,但遭退稿。當時她的主要關注仍在於海洋與海岸環境,還在撰寫這些議題的相關書籍。
一九四八年,美國醫藥協會警告,包括DDT 在內的大部分新出品的農藥對人類所帶來的長期毒力「是完全未經探查的」。不過,像這樣的警告鮮少為科學圈以外的公眾所知。一九五○、一九五一年當DDT 在食物裡的殘留成為大家所關心的議題時,國會也曾就食品添加物之安全的議題舉行聽證會,而制定有關化學物必須註冊、檢測的一些新法規。但無論如何,DDT 和其他農藥仍繼續為人們所使用。
一九五八年,一封信函重新觸動卡森撰寫有關DDT 之危險的念頭。她的友人娥嘉.哈金斯寫信向她透露,DDT 的噴灑造成大量鳥隻死在她位於麻州的一座私人鳥類禁獵區裡。該地區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曾進行空中噴灑農藥的滅蚊計畫,哈金斯希望卡森能透過華府相關人士的協助以停止這項噴灑行動。
卡森得知,各種針對掠食動物與獵物的控制計畫將農藥大量散佈到環境裡,毫不顧慮農藥對標的害物以外的生物所造成的後果。卡森再次向雜誌社提議派她撰寫有關DDT 效應的報導,但再度失敗。在一九五八年,卡森已是暢銷作家,卻仍無法說動雜誌社派她報導DDT 事件,這事實說明了卡森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在當時顯得多麼異端和具爭議性。然而,她仍決定深入了解,並詳盡蒐集、記錄有關農藥濫用的科學證據。當手頭掌握了相當的相關研究資料時,卡森決心撰寫一本有關DDT 的書,如她後來所說的:「我越了解農藥,就越感到震驚。我知道我有足夠的材料來寫一本書。我發現,身為自然學家的我最重要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脅,而這就是我能力所及最重要的任務。」卡森在最適恰的時刻成為最適恰的信使;她能見樹又見林,看見相同的情況在許多不同的環境的角落發生,並且知道要如何運用她所蒐集的科學資訊,以及用甚麼方式來呈現這整件事。決定寫書後卡森便更加積極蒐集資料:她和一些正在蒐集有關農藥影響環境之證據的科學家通訊、會晤;和某些官方科學家的往來有時讓她得到機密情報;她也前往聯邦機構以及國家研究圖書館,例如國家衛生研究院的醫學圖書館,挖掘資料。
卡森花了將近五年的時間將書寫成。
沒有不具詩意的海洋──關於瑞秋.卡森的「海洋三部曲」
吳明益
如果我談海洋的書裡有詩意,那不是因為我刻意注入詩情,而是因為真實地描寫海洋時,沒有人能夠排除詩意。(瑞秋.卡森)
一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我在光華商場地下樓的一家舊書店邂逅了一本外表看來頗為質樸的書――瑞秋.卡森的《海風下》。書的封面已然破損,舊書店的老板因而使用紙張將書包起來,用簽字筆寫上書名。彼時開始對自然書寫感興趣的我,打開書的那一刻,就被海風帶離了小小的書店空間,再下一刻清醒時,發現自己已經在書架前站了一下午,把書讀完大半了。
《海風下》是一九四一年,卡森三十五歲的作品,也正是日本偷襲珍珠港那一年。這本描述海岸生態,並且以海洋生物視野構思的作品,僅僅賣出兩千餘本。我以為這也暗示了,文學性格強的自然書寫,未必有像直接關涉即時議題的「環境啟示錄」一樣容易引起讀者關注;相對地,它們就像有恆久耐心的海浪,逐步為海岸塑型。
這本書也打開了我認識卡森女士真正的開始。她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個決意對抗龐大勢力的環境鬪士,而是因為從心智上、科學上累積的對海洋的情感,終究使得她在大地受傷時挺身而出,在這過程中,她的信念就如同文學在她體內的作用,是一種平靜、複沓、頑強如海浪的力量。也因此,我以為要真正認識卡森女士,不能只看她的環境啟示錄,也要看她柔軟、深刻的文學性自然書寫。
二
瑞秋從小就對動物故事深感興趣,她最喜歡的作家是赫爾曼•梅爾維爾、約瑟夫•康拉德、羅伯特•路易士•史蒂文生。這裡頭似乎有著寓言式的宿命――這幾位作家的重要作品,都離不開海洋。
卡森在就讀賓夕法尼亞女子學院時,原本以文學為主修,卻在聽了一門生物課程後激起了熱烈的興趣,並且覺得自己在寫作上缺乏想像力,於是決定轉修生物學,最後在霍普金斯大學獲動物學碩士學位,並且在畢業後任職於麻薩諸塞州的伍玆霍爾海洋生物實驗室。那是一個「不論從那個方向走不了多遠,就會遇到海」的地方,也是瑞秋走入海洋的開始。然而因為父親驟逝,家中經濟負擔落在她身上,她只得在漁業管理局找份兼職工作,並且替電台專有頻道廣播撰寫科技文章來換取收入。由於當時行政部門對女性仍有很深的就業歧視,卡森是漁業管理局第二位受聘的女性,這印證了她具有優秀的專業能力。
在廣播節目結束後,她的部門主管艾默.希金斯希望以廣播的內容為漁業局製作一系列介紹海洋生物的小冊子,並且要她寫一篇導言。瑞秋完成了這篇大約有二十五頁的長導言,寫作時她刻意避免了文學性筆法,希望能拋開「人為偏見」,並且叮嚀自己「說故事的人不能進入故事」。然而,瑞秋或許也因此發現自己體內的文學欲望並未死去,因為稿子交到希金斯的手上後,他仍舊認為這篇文章太具有文學性,不適合當作一本介紹海洋生物手冊的導言。然而文章又寫得太迷人,他因而建議她投到《大西洋月刊》。
這篇文章就是《海風下》寫作的開始。
***
三
我有時候會想,如果瑞秋.卡森只是一個卓越的、負有聲望的女科學家,那麼《無聲的春天》還會不會引起那麼巨大的社會迴響?我對這個問題是有預想答案的,那就是卡森女士在「海洋三部曲」已經匯聚了一批讀者:有科學讀者、文學讀者,還有更多的愛聽故事的人。過去沒有人講海洋的科學故事給他們聽,而現在有一個了。
也因此,卡森累積了她的科學信用、文學信用,還有對自然環境的情感信用。
在早期的《海風下》,敏銳的讀者當可以讀到卡森向亨利.威廉森取法的敘事技巧:卡森讓黑剪嘴鷗「靈巧」,三趾鷸「黑腳兄」、「銀條」,旅鼠「伍文嘉」,魚鷹「潘東」,鯖魚「史康波」,鰻魚「安貴臘」,海鱒「席諾雄」,帶出動物「主觀鏡頭」的敘事。比方說,在寫到鯖魚的迴游時,卡森說:「鯖魚並不順著海的層次翻山過谷。離開冬眠地後,牠們好像急著立刻來到陽光照耀的上層,從百噚深處直直攀上水表。在深海的幽冥中待了四個月,鯖魚興奮地竄上明亮的水層,鼻頭伸出水面,看一眼鑲嵌在蒼穹下的浩渺海洋。」(1994:100) 而寫到三趾鷸,她描述:「海水在柔美的月色下泛著銀光,許多魷魚受光的吸引,心醉神搖地浮出表面,面向月光,在海上載浮載沉。牠們輕輕打水,凝視著月光後退,那麼專注,竟不知自己已漂入危險的灘頭,直待沙粒磨身,才驚覺過來。倒楣的魷魚受困淺灘,拚命打水只把自己推進更淺、水退只餘沙之處。早晨,三趾鷸一見天光便往退潮線覓食,發現海口灘頭散布著魷魚的屍體。」(1994:35)這樣的筆法正是被質疑為「太過文學」之處,畢竟說鯖魚「好像急著」、「興奮地」;魷魚「心醉神搖」,都是非科學性描寫的主觀感受。
但在這樣的描述底下,卡森要藉生物視野的變換表現的,是帶領讀者認識潮間帶、極地之海、海底、河口……流轉變動的環境,解釋海濱生態、海中生態以及海底生態的複雜面貌。
比方說,寫到剪嘴鷗的覓食,和潮水漲落是有深刻關係的:「潮水是日落時分退去的,現在重新漲起,淹沒了剪嘴鷗下午棲息的地盤,更沿海口而入,盈滿沼澤。剪嘴鷗大半夜都在覓食,輕振細長的雙翼,尋找隨潮水而來,躲藏在水草間的小魚。就因為牠們趁潮覓食,人家又管牠們叫『潮鷗』。」(1994:3) 而在魚群游過的洋流底下:「是海溝,海的太古之床,大西洋最深的地方。海溝之中無日月,百萬年的流逝都無意義,遑論季節的急遽變換。太陽在此深處毫無勢力,這裡的黑暗無始無終,亦無程度可言。熱帶的陽光再熾烈,也絲毫不能緩解海溝中水冬夏不分的冰寒。年月凝成世紀,世紀凝成地質年代,大洋盆底的水流總是沉緩嚴寒,從容不迫而又堅定不移,恰似時間之流本身。」(1994:235-6)有些科學家認為,這種將海洋知識順著帶點虛構文學的敘事角度表現出來的手法是危險的。即使是現在,如果一個自然書寫者運用這樣的技巧來寫作(內容並由專家校訂過),也一定會遭受部分人士的質疑與批判。但時過境遷,這部作品在世界上的流傳,完全展現了她做為一個文學作者的高度與天份。請讀讀以下的段落,不禁讓我想起她所說的,描寫海洋,沒有人能排除詩意:
鰻魚安桂臘埋首水中,隨著忙忙奔進溢洪道的池水而行。憑著敏銳的感覺,她嚐出水中特異的氣和味:是雨濕秋葉的苦澀,是林中苔蘚、地衣、腐植質的味道。含著這樣氣味的水,匆忙流過鰻魚身邊,往大海去。( 1994:1-2)
除了潮聲和鳥鳴,這晚全然寂靜。風沉睡著,海口有碎浪上灘的聲音,但遠方大海的鼓搗則淡成近乎嘆息,是一種有韻律的吐氣聲,彷彿海,也在峽灣的門戶外睡著了。
只有最靈敏的耳朵,才聽得見一隻寄居蟹拖著牠的殼屋,在水線上方沙灘上行走的聲音;也才辨別得出一隻小蝦被魚群追趕,匆忙上岸時抖落一身小水珠,在水面跌出的叮咚聲。但在這小島的夜晚,在海與海的邊緣,這些聲音是細微不可得聞的。(1994:10)
明春之前,這些鳥不會回返陸地。牠們要在海上過冬,共享海上的白晝與黑夜、暴風與寧靜、霰與雪、陽光與迷霧。(1994:157)
但做為一個科學家,卡森女士可能也知道她這樣的寫作方式不會獲得科學界的肯定。在寫作《周遭之海》時,開始大量引用研究者的論文、航海日誌,以及關於海的相關材料(如達爾文與康拉德的筆記與書),更強調信而有徵的自然史敘事。卡森在一九六○年新版的序裡強調她試著把一九五一年以前人類對海洋「最重要的新資訊」,都寫在這本書裡了。書中從海洋的形成、深海生態寫到海底火山、島嶼生態以及波浪與洋流的形成,最終談到海洋與人類的關係,卡森的筆下博學、睿智,而且還很「迷人」。比方說,卡森從地球生成寫起,寫到月球的誕生,與地球潮汐的關係,在當時科學界的推測:「下一次你在夜晚駐足於海灘,凝望著映照於海面的月華,覺察到月球所牽引的潮汐起伏時,請記得月球之所以形成,很可能是因為地球在某一次的大陸潮中,將地球物質拋入了太空。此外,也不要忘了,如果月球真的是以這種方式生成,這個事件也可能和我們所知的海盆與大陸的形成極有關聯。」(2006:23)
而海洋的形成,在卡森的筆下如同馬奎斯《百年孤寂》那場落不盡的雨一樣魔幻且詩意:「在地殼溫度冷卻到一定程度後,地表便開始降雨,從那時到現在,地球上再也不曾出現這種降雨情形,大雨日以繼夜不斷落下,連下了數天、數月、數年甚至數百年,雨水澆灌著空無一物的海盆,或落在大陸陸塊上,最後匯積成大海。」(2006:25) 這樣的海洋孕育了萬物,以致於「即使離開海洋而上岸生活,體內仍然帶著一部分的海洋,且這項特徵代代相傳,時至今日,仍能顯示所有陸生動物與牠們遠古時代海中先祖的關聯――無論是魚類、兩棲動物、爬蟲類、溫血鳥類還是哺乳動物,每一種生物血管內所流的血液,都和海水一樣帶有鹹味,甚至連鈉、鉀、鈣等元素的含量比例都幾乎相同。在數百萬年以前,生物的遠古始祖由單細胞進化成多細胞,而後更發展出循環系統,雖然當時在這些生物體內所循環的,不過只是海水,然而從那一天起,循環系統就成為我們代代相傳的特徵。」(20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