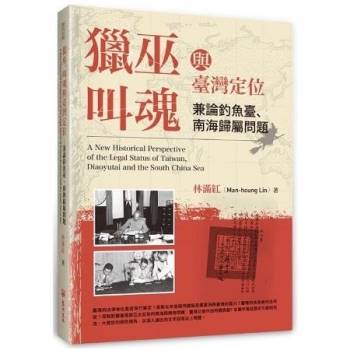一、世界史中的社會恐懼─從獵巫、叫魂,到臺灣的「認同」危機
在世界歷史當中,在某些特定的時空,會產生某種特殊的社會恐懼。對某個問題,社會當中很多人視以為禁忌,明哲保身者更避而不談,但社會很多的不安、偏見、猜忌、仇恨與對立又不斷環繞著這個問題在堆疊發展。既然是普遍的社會恐懼,社會中的每一種人對這個問題都會有某種心理想像。雖然人人心中的想像不一定相同,但卻可以疊合拓展而為一種普遍的危機。由於整個危機來自不同人的心理想像,整個危機其實並非來自真實,但針對這樣一個危機在沒有真實基礎下的想像與疊合拓展的分析,卻可以勾勒該特定時空歷史的特殊發展。
獵巫與叫魂
16、7 世紀英國普遍展開的女巫獵殺行動(witch hunt)即為此種社會恐懼的樣例。在Boston 北邊Salem 港的Witch Museum,可以看到當年女巫被追捕、刑求、處刑的恐怖蠟像。就像在臺北的坪林會設立茶業博物館一樣,特殊博物館的存在通常是用來紀錄某一特定時空的顯著歷史。在西洋當代史學領域中,有關16、7 世紀英國以及歐陸普遍展開的女巫獵殺行動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這些研究中一本整合性作品─ Keith Thomas的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 1971) 一書指出這個社會恐懼的背景如下:在16、7 世紀中,有成千上萬的巫師(多為女性),常因為隔壁家發生的不幸(如小孩猝死、突然失火、或只是芝麻小事如奶油無法凝固),被告到法庭說這些生活中的不順或不幸是女巫耍弄巫術所造成。在一半以上的疾病沒法解釋與醫治,沒有良好的防火設備,以及現代科學知識不普及的時代,這些聯想都是可能的。但這種生命、財產欠缺保障的情況在16、7 世紀以前也是有的,何以大規模獵殺女巫的現象只顯著存在於16、7 世紀? Keith 由控訴者和起訴者雙方思維的湊合來加以解釋。在這個時代之前,鄰里間相互濟弱扶貧,是一種公共道德,在16、7世紀間,只許教區濟貧,不許沿門施捨。被控耍弄巫術的老婦多半孤貧,村民不想伸出援手,又於心難安,其特別成為村民遭逢不幸時的代罪羔羊,多少是因為村民藉以紓解其因新舊道德不一所引起的內心衝突。相對之前之後,這個時代的神學理論特別流行魔鬼附身行惡的觀念,而負責審判者又多為神職人員,他們認為這些老婦很可能原來道德即有所欠缺,得不到天主的眷顧,使魔鬼有可乘之機,既然是魔鬼附身,當然是要將她們燒死來為民除惡,但究竟哪些人會突然間被說是魔鬼附身,也就成為這個時代的社會恐懼。
清代中國也曾發生社會恐懼的案例,哈佛大學教授孔復禮(Philip A. Kuhn) 所著的《叫魂》(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86, 1990)指出,乾隆33 年(1768),很多道士、乞丐、泥水匠被指控偷偷剪斷別人辮子而奪走那人魂魄,此種案件蔓延江南乃至北方數省,案子審理期間長達10個月左右,很多被控者在逼供過程中冤死。孔教授由皇帝、官僚、百姓三者心理恐懼的湊合來勾劃此一案件之所由始。
乾隆年間大量增加的人口造就了許多的流民。就百姓而言,他們對社會中新增加的許多流民感到不安。他們或是乞丐,或是變相的乞丐─道士,或是與能夠呼風喚雨的道士相似而可以左右風水的泥水匠。這些人對本地人而言,既非同鄉,又非同族;對他們的求助委實不願伸出援手,但這又與社會有無相通的傳統道
德相衝突,而增加本地人的心理惶恐。
清乾隆朝的皇帝官僚關係,說是專制統治,又有很多方面皇帝無法控制,官吏的上下敷衍早已使皇帝心中忐忑。漢人文化的中心─江南,聽說出了剪辮的案子,辮子是滿族統治漢族的文化象徵,這樣一樁叛逆行為竟然沒有大臣上報,更使皇帝氣極敗壞。
皇帝由情報系統得知這個消息的事很快傳到地方官吏耳中,儘管地方官吏慣於敷衍,但是皇威依然顯赫,如果不認真查辦此事,可能危及身家。在此情況下,那些平常令村民感到不安的道士、乞丐、泥水匠成為被指控的對象。即使他們不承認剪過別人的辮子、招人魂魄─叫魂,官吏也要他們承認。什麼人突然間會被戴上「剪辮」的帽子,便成為18 世紀中國存在一段時間的社會恐懼。
臺灣認同危機背後的迷思
在當前臺灣,「藍」與「綠」成為人與人之間互貼標籤、互相撕裂的一道心牆。作者自1990 年起迄今一直進行的「亞太商貿網絡與臺商, 1860-1961」研究計畫,附帶地讓作者得知整個臺灣的認同危機,也是不同人群的心理想像湊合而出的一個莫須有的社會恐懼,而這回最大的犧牲者不是女巫,不是乞丐、道士或泥水匠,而是整個臺灣兩千三百萬人民或是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和平。今天臺灣的認同問題,與各個族群都欠缺面對共同問題的基本概念、及不同族群有互相抵觸的歷史記憶有關。這些迷思(myth)大抵可抽離出以下三方面:
1. 忽略identity 的法律身分含意
學界所指的「認同」是「identity」一字的翻譯。如果將identity 說成是「認同」,指的是個人的心理感受,可能人人不同,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也會有所不同。1997 年哈佛燕京學社召開「Culture China and Taiwan Conciousness」會議,作者從杜維明與李歐梵兩位教授的對談中學到「identity」事實上有另外一層意思,那就是「身分」,像「身分證」的英文是「identification card」。這個「身分」指的是一種法律地位,例如我們要有身分證才能享受健保資源或參加投票。相對「認同」意涵的不確定性,「身分或法律地位」意涵,有或沒有,必須非常確定。外文系出身的杜教授還說他是極早將identity 翻譯成「認同」而未翻譯成「身分」引進臺灣的人,因為這樣一個翻譯可能產生的誤導作用,他還說對臺灣當前的認同危機要負相當的責任。可以注意的是日文即未將「identity」翻譯成「認同」,而直接用" 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晚近有關國族建構的論述多半偏重心理感受的identity,而作者的「亞太商貿網絡與臺商」計畫研究到的identity 很多是法律地位的identity。晚近有關國族建構的論述與作者的「亞太商貿網絡與臺商」研究計畫有關identity 切入角度之別,可用Parsenjit Duara 在2003 年出版的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與作者在1995 年發表的〈臺灣與東北間的貿易,1932-1941〉來加以對照。相對滿洲國是偽政權的說法,Duara 用博物館的強調東北文化特性的展示,東北歷史、民俗的研究,鄉土文學的撰寫,民間社團的配合政府動員等等,來表達東北人建構國家認同之真意;拙作在確定臺灣與滿洲國間的貿易是否為國際貿易時,用的指標則是:臺灣商人到滿洲國這片領土時,還是要繳納這個國家規定的關稅,也要將臺灣以金本位發行的貨幣換成滿洲國以銀本位發行的貨幣。我們常說一到機場的海關,就是返抵國門;我們用的錢,我們說是國幣;關稅、貨幣常是象徵國家主權的制度。滿州國人的國家國民身分也因此是法律性的,而與心理建構性的有所區隔。
臺灣於1895 年割讓日本之後,其商船需比照外國船進入中國的「海關」,而不能進入只准中國船進入的「中國常關」,因為在這個時期臺灣人並非中國的國民。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外務部檔案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外交檔案所藏1902 年福州將軍、總稅務司、外務部等與日本外務省的往返文件,指出隨著《馬關條約》簽訂,臺灣與清朝中國主權、國籍關係的顯著變化。日本籍的臺灣船因與大陸民帆不易分辨,常混進外國船不能進入的中國常關,中國官方根據《馬關條約》要求日方政府,臺灣船要比照外國船進入海關,要確定臺灣船懸掛日本旗,臺灣船隻格式、顏色要與大陸民船有所區隔,甚至希望臺灣船隻上的人員不要著華服而改穿洋服,以確保中國主權。
目前臺商在中國大陸的企業也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內投資」,而是「外商投資」。無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與地方法規,臺商適用其「涉外法規」。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公布之法規而言,1986 年的《鼓勵外商投資規定》適用於臺商,1990 年的《關於鼓勵華僑和香港澳門同胞投資的規定》,臺商也可「參照執行國家有關涉外經濟法律、法規之規定,享受相應的外商投資企業待遇」。地方性法規對臺商地位之界定,亦是將臺商等同外商處理,例如《寧夏回族自治區鼓勵外商投資規定》第2 條清楚寫明:本條例適用於「臺灣的公司企業、經濟組織和個人在本自治區境內投資設立的⋯⋯企業」;又如《天津市鼓勵外商投資高新技術研究開發和產業化項目暫行規定》第三條亦闡明此規定適用於「臺灣的金融機構、基金、公司等經濟組織或個人」。因此就法律身分而言,當前的臺灣人顯然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
2. 欠缺近代國家主權的觀念
談論臺灣的主權定位,常有人說到根深蒂固的大中國觀念難以抗拒。作者近年的兩大研究,意料之外地都告訴作者:中國人非常不知道什麼是國家主權。作者在寫China Upside Down 一書時,發現大清王朝相對東亞各國欠缺貨幣主權,使其在十九世紀上半葉世界銀荒中首當其衝,並促成其經濟、社會、政治、思想、乃至在東亞中地位的全盤變化。作者所進行的「亞太商貿網絡與臺商」的研究計畫,由國籍、關稅、貨幣制度,很清楚地看到1895 年及1952 年臺灣兩度主權移轉,但臺灣當前社會,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臺灣是否擁有主權並不清楚。「主權」概念自1648 年之《西發利亞條約》後,成為近代西方政治與國際法的重要思想。「主權」指的是某一領土範圍內的人與物歸哪個國家所有,「所有權」和「處分權」或「支配權」是一體的兩面,主權與統治權也是互為表裡。國家是行使主權的政治實體,政府是行使國家主權的行政單位。以主權概念為核心的民族國家建構是近代世界歷史的重要主題。
說大家欠缺主權觀念可以一百元新臺幣為例來加以說明。目前一百元新臺幣上印有「中華民國」和孫中山先生遺像,有些人也許會不喜歡,但過年時紅包袋裡如果單純裝著一張紙,小孩拿到之後,一定不如裡面裝著百元臺幣高興,因為後者可以讓小孩換取他想要的東西。為什麼同樣是一張紙,後者的偏好較高?因為百元臺幣有國家主權支撐,也就是以臺澎金馬及其附屬島嶼擔保它的購買力。這個主權還不只是對內的,還是對外的:外國人到臺灣生活要換臺幣使用,臺幣目前依然可以折換成外幣,購買其他國家物品。半個多世紀以來,明明大家收到面額無論多少的臺幣,都很開心;但一說到臺灣的主權問題,不是很害怕,就是準備要吵架,我們欠缺主權觀念的情形由此可略窺一二。
研究中國外交史的植田捷雄教授指出,在鴉片戰爭之後,W.A. P. Martin 由西文中譯了一部國際公法,日本人很快將這個譯本又譯成日文而廣泛閱讀。除此之外,日本還引進其他的國際公法或有關主權的討論。到了《馬關條約》簽訂時,中國人深刻體察到日本人比中國人懂得國際公法。《馬關條約》的三個語文版本,有關臺澎領土主權永遠割讓日本的部分,英文版是:「China cedes to Japan in perpetuity and full sovereignty」,日文版對應「full sovereignty」的語詞是「主權」,中文版則是「權」,多少呈顯中國人對「主權」概念的陌生。
主權行使範圍一定是有效統治的領土範圍。在《中日和約》談判過程中雙方最大的爭議是:日方極力堅持將和約適用範圍限於「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及將來在其控制下之領土」,此立場亦獲得美國之諒解,但是中華民國卻堅持領有中國全部領土。中華民國對日媾和之基本原則有三:(1)維持與各盟國平等之地位,(2)中日雙邊和約應與《舊金山和約》大體相同,(3)日本必須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國全部領土之主權。最後,《中日和約》第3 條、第10 條及第一號照會都表達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以有效統治範圍為限。
主權行使對象的領土不只是土地,它包括土地及其上之所有人或物,人又包括自然人與法人。1895 到1945 年間產生而存留在臺灣的人如李登輝先生,或機關如臺灣銀行,甚至1945 到1952 年間由中國大陸移遷臺灣的人如蔣經國先生,或機關如中央銀行,都構成1952 年《中日和約》中日本向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宣布放棄的臺澎領土的一部分。但今日社會還經常出現故宮是不是我們的,外省人是否應該離去這種言論,一而再,再而三地呈顯我們對主權、領土概念的陌生。
一般人不瞭解臺灣主權移轉的歷史,與中日戰爭後大陸人與臺灣人有關日本極為對立的歷史記憶也有所關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