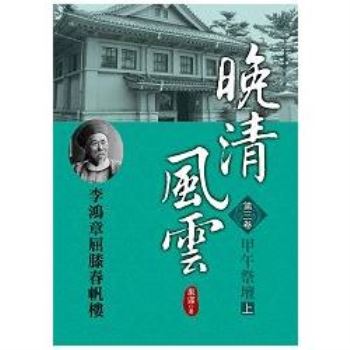第一章 「墨絰從戎」
中法戰起
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六月。這真是一個蝦荒蟹亂的兵戈之年,尚是初伏,就熱得不行。上海虹口公和祥碼頭至廣肇公所的大馬路上,原本是極繁華熱鬧的街市,此時因天氣太熱,至上午十點後便顯得有些蕭條了,頭上那一盆火似的驕陽烤得人頭皮發麻眼發花,地上熱浪滾滾、暑氣蒸人,行人多避走兩邊的樹蔭及店堂的屋簷下,除了鈴聲叮叮噹的馬車、人力車,馬路中間極少行人,連一向拼死拼活叫喊的小販、乞丐也多躲到弄堂口或石庫門洞邊,享受穿堂風的涼爽滋潤去了,馬路中間空蕩蕩的,只有近年才出現的報童不辭辛勞,此刻猶抱一摞摞散發著油墨香的報紙,閃在路口滿頭大汗地向行人兜售。那叫喊聲特別誇張,聲嘶力竭,令行人不時駐足圍觀,也引得臨街的茶樓酒館裡的客人推窗觀望。
「賣報賣報!《申報》《滬報》《時報》,還有洋文的《字林西報》,看法蘭西戰艦鼓浪東來,看李中堂奉旨巡海!」
多事之秋,危機四伏呵!去年朝鮮發生了政變--以國王生父大院君李罡應為首的保守派,唆使士兵譁變,反對王妃閔氏為首的閔氏家族,亂兵還焚日本使館、殺死日本僑民。日本天皇派兵前去問罪,幸虧中國事先獲得消息,北洋派出三千慶軍趕赴仁川,統領吳長慶採用袁世凱之謀,誘擒李罡應,迅速平定了暴亂,才使日本人無所藉口。
東鄰的事尚未完結,法國人又在越南打起來了。為此,朝廷不得不下詔,令因母喪丁憂在籍的李鴻章迅速回任北洋籌備戰守--今天的報紙,載的就是這事。
小百姓關心柴米油鹽往往超過國家大事--法國兵艦要來,說不定便要攻打上海,一旦港口被封鎖,物資運不進來,那米麵油鹽豈不要斷了供應?
「快走快走,公和泰米價怕又往上躥了!」這是布衣短褐赤腳草鞋的路人在喊叫。
「不急不急,只要李中堂出山,天下就太平了。李中堂百戰勳名,所向無敵,就憑了他老人家這塊牌子也足以嚇退洋人!」茶樓上的清客,見識又高了一層。
好像為了印證茶客們的猜測似的,十點半左右,大街的西頭突然出現了大隊手持大刀和背毛瑟槍的兵丁,他們成兩路縱隊從大街兩邊穿過,直達黃浦江邊,然後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地拉開距離,背向大街開始警戒,這中間另有大隊佩三橫槓臂章的印度巡捕,他們把住各通衢道口開始設卡攔阻行人。
接著,手持大令巡街的道標都司領一隊馬隊從那邊過來了,這是一隊雄赳赳氣昂昂的道標兵,一個個虎視眈眈地注視著兩邊的百姓。在公共租界出現大隊武裝華兵是不多見的事,官方事先顯然有過交涉,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猜疑:「好威風啊,接欽差啦!」
「還有洋人捧場啊!」
「去年兩江總督左宗棠巡視吳淞口要塞也沒這麼氣派!」
「嘿嘿,此人只怕比左爵相來頭還要大一些!」
「誰?」
「誰,李中堂唄,他老人家不是已到滬多時了嗎?」
果然,就在第三撥巡街道標兵走過,人們隱約望見從街西頭走過來一溜官轎,約幾十頂,打頭的是一頂平頂的、用藍布幔子遮護的四人小轎,抬轎的兵勇穿著白色無胸號背褡子,前後左右沒有儀仗執事、旗羅傘蓋,沒有誇耀主人功名爵祿、勳名職銜的高腳牌,更沒有鼓樂,冷冷清清,透出一股冷峻肅殺之氣,讓人好費猜疑。
更奇怪的是左右護兵及扶著轎槓的中軍雖也全副武裝,穿的卻是素服,連頭上的紅纓子也摘了,換了一根白綾子在打漂漂。過了這頂四人小轎,才是一色的綠呢頂八抬大轎,他們顯然是來送行的上海地方文武官員。
「咦,走頭的難道是李中堂?」
「怎麼像出殯似的,親兵護衛都穿孝呢?」
「這還不明白,李中堂還熱孝在身,照理是只能在家守靈。眼下雖奉旨出山,移孝作忠,可怎麼能不顧禮法去擺街抖威風呢?」茶客們的議論有典謨有訓誥,
「眼下中法大戰在即,人家這是效法老師曾文正公的故事,金革毋避,墨絰從戎!」
果然,待轎子走近,人們看見,小轎門簾掀起,李鴻章端坐轎中,一身重孝,目光呆滯,面帶戚容,分明一個「哀毀骨立、風吹即倒」的孝子模樣。
轎子到了公和祥碼頭,下到接官亭,此時接官亭已臨時搭起了一長溜天篷,直接到躉船上。只見北洋公署幕僚薛福成、馬建忠、于式枚、羅豐祿等文官,丁汝昌、葉志超等武將及李經方、李經述等李氏子侄早已等候在碼頭上,他們全是一身素服,李鴻章剛下轎,眾人馬上圍上來請安,緊隨其後的上海道劉瑞芬、織布局總辦盛宣懷、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等一齊擁上來要與中堂話別,李鴻章一見,僅回身向送行的拱了拱手,道聲「各位請回」,便繞開前面一幫子人直往躉船。
下到江邊,只見狹窄的黃浦江上已擺滿了上飄各國旗幟的輪船,緊靠公和祥碼頭的是北洋水師「康濟號」練船,眼下艙門大開,船上官佐皆在甲板上雁陣兩行為中堂站班。李鴻章再次轉身拱手讓堅持送上躉船的官員留步,然後在長子經方次子經述左右攙扶下跨上「康濟號」左舷甲板。隨著一聲長長的汽笛,岸上也響起了送行官員一片祝誦聲:「中堂一帆風順!」
「康濟號」第二次拉響汽笛後便啟動了,隨著艦尾白色水花翻起,緩緩掉頭駛向吳淞口。
李鴻章今年六十二歲了,與五短身材、面團團如滿月的左宗棠不同,他生得長身鶴立,面目清癯,尤其是花甲過後,鬢邊白髮、顎下銀鬚,面飄然如玉樹臨風,人謂此為「仙鶴」之姿。此刻「仙鶴」高昂著頭,對列隊鵠立在甲板上的官佐僅點點頭,便旁若無人地緩緩走向後艄,憑欄向漸行漸遠的大上海眺望--在烈日的照耀下,十里洋場熱氣蒸騰,高樓大廈鱗次櫛比,遠遠望去,像用巨石壘起一道道逶迤起伏的城牆,城牆上飄著旌旗,排列著劍戟。
上海,二十一年前是他李鴻章的發跡之地,在這裡,他以赫赫威名、煌煌戰績,使自己由一名不見於經傳的書生,成為一個雄圖霸舉、舉世矚目的人物,今天,時局孔艱,他又在眾人注目下,由這裡再度出山,去迎接更大的機遇與挑戰……
康濟號
滔滔黃海,遠接天際。「康濟號」,正加足馬力劈波斬浪朝北急駛……
一覺醒來的李鴻章披衣漫步在甲板上,縱情地眺望著大海。天公造物,煞是怪異--前天還碧波蕩漾、宛如平湖的大海,一覺醒來卻黃湯滾滾,濁浪翻騰,而代替蒸人暑氣的是一絲絲北風,拂衣而過,涼意沁人心脾。
不是才一覺的工夫麼?東海與黃海差異竟如此之大,才一千三百噸、航速不過九海浬的「康濟號」航行在這洪濤巨浪之間,有如一匹羸馬艱難地跋涉在沙漠戈壁中。
然而,大海不比沙漠,水性隨勢而流,漂浮不定,看似柔媚卻不時掀起排空濁浪,潛伏著殺機……
由此,他不由想到「雲譎波詭」一詞,再進一層,又想到人們常用的比喻:官場--宦海。今天,他這個宦海弄潮兒奉旨奪情復出,雖有「奉旨」二字打頭,但於一個標榜「孝行第一」的孔聖門徒,父母之喪未能盡禮,究竟是臨危受命移孝作忠還是貪戀祿位不惜羽毛呢?
然而,他卻實在是有說不出的苦衷--自他丁憂出缺,朝廷派張樹聲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張樹聲雖為淮系舊人,自己一手提拔上來的,竟然也生鵲巢鳩佔之心,為迎合輿論,竟與京師那一班主戰派桴鼓相應,甚至上疏奏調清流幹將張佩綸幫辦北洋軍務。
這不是成心假戲真做,為擴充羽翼而拉攏方方面面的人物嗎?當御史楊崇伊把這消息寫信告訴他時,李鴻章不由在心裡冷笑了。
張佩綸少年科第,玉堂金馬中人,一向自視甚高,怎在乎一赳赳武夫的薦引呢?何況張父印塘是李鴻章舊友,張佩綸和他這個「老世叔」政見儘管不同,私交卻是不薄,哪怕就在李鴻章居喪期間,二人也不斷魚傳尺素、驛寄梅花,此番的「墨絰從戎」便是在張佩綸一再奏請下促成的。真是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啊!
想到此,他真想開懷大笑,道行淺薄的張樹聲,張網看不清三尺深的水,燒香竟然拜錯了廟!
「大人,前面快到渤海口了,水師的艦船已結隊來迎了呢!」李鴻章正倚欄回想聯翩,丁汝昌從艦橋上下來,匆匆走到他身後向他稟報。
他從容回頭望了丁汝昌一眼,又順著他的手勢往左前方看去,只見沿大陸一線,島嶼星羅棋布,有幾個比島更小的黑點成直線漂浮在海中間,如隱在雲霧中的星星,渺彌相望,若隱若現。
他接過丁汝昌手中的單筒望遠鏡細看--前面果然來了一長溜艦船,為首一艘船頭高高翹起,看那輪廓真有些像前年從英國購回的「揚威號」巡洋艦,他不由笑著點了點頭。
四年前,日本從英國沙木大造船廠購得一艘千噸級巡洋艦,號「扶桑」,駛回日本後,引起朝野轟動。次年,海軍中將西鄉從道率「扶桑號」訪華,拜訪了李鴻章,交談中西鄉從道得意之色溢於言表。
李鴻章將詳情奏聞朝廷,朝廷這才對海防有了緊迫感,「揚威」與「超勇」就是在這時從英國購進的,這是一對姊妹船,排水量與「康濟號」差不多,都是一千三百噸,馬力卻比「康濟」大了三倍--「康濟」馬力才七百五十匹,「揚威」、「超勇」卻都是二千四百匹,航速達十五海浬。這以前北洋只幾艘馬尾船廠造的木殼炮船,幾個大的海浪也能掀翻它,直到「揚威」、「超勇」駛回,北洋才算擁有具有遠航能力的巡洋艦。
上午九時,南下相迎的水師各艦終於在山東成山角海面與「康濟號」相遇。「揚威」、「超勇」為首,「威遠」、「泰安」、「鎮海」、「操江」四艘炮艦及「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邊」、「鎮中」六艘炮艇成一字縱隊迎上來,各艦艇上將弁一齊在甲板列隊,遠遠向著立在「康濟」艦橋上的李鴻章打千請安,各艦一齊放響了禮炮,一時之間,硝煙四起,霹靂山崩,李鴻章雖一身素服,但在眾幕僚簇擁下,仍遠遠地向將弁們微笑著揮手致意……
「康濟」駛過後,艦隊立刻變換隊形,由一字縱隊一分為二,跟在「康濟」後邊轉過成山角,由東向西緩緩向水師的第一大軍港威海進發……
威鎮海疆
應該說渤海灣地勢,渾然天成--自大陸線艮維左轉,三千里河山斜伸入海,將中國北部與日本隔開,是為朝鮮,這是一道天然屏障。接下來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如兩條巨臂,控扼渤海灣,兩大半島最近距離不過兩百多里,這又是第二道屏障,京津就如在巨臂的拱衛中。
前明時代,倭寇猖獗,為保衛京師,明廷曾下令於威海、天津兩地設衛所,煙台便因戚繼光建烽火台而得名。
兩年前,李鴻章和他的幕僚們及洋顧問參照前明史料,通過測量、繪圖、篩選後確認,如果在威海、旅順擺上一支新式水師,則如給兩臂配上了兩把利劍,進可馳騁黃海、西朝鮮灣,退可在渤海灣周旋,神京當無恙矣!謀定而發,乃奏明朝廷,在威海和旅順建北洋水師總埠,在旅順設水師提督行轅,在威海劉公島上設提督公署。
今天,他先去看威海。
短短四天行程,從東海到黃海,不但海水變色,氣候也似乎由夏而秋--眼下的威海港灣陽光明媚,海風涼爽宜人。
「康濟號」進入港內停泊後,李鴻章走出官艙,立刻被眼前熱火朝天的施工場面吸引住了。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水師提督衙門,它座落在劉公島半山腰上。以前這一帶只一小小漁村,數十戶人家在山下結茅而居,十分簡陋;山上榛莽叢生、山石掩沒,一片荒涼,有幸的是它被李鴻章選中,做了北洋水師的基地。
自威海建港後,劉公島一下熱鬧起來,島上大道縱橫,人來人往,金碧輝煌的水師提督衙門巍然聳立,在它的周圍幾乎拓平了半邊山,依次而建的是水師營房、學堂、發電廠、倉庫、電報局、修械所、醫院及外籍雇員娛樂場。這些建築先後開工,目前都在建設中,但見屋架林立,吆喝之聲此起彼伏,很是壯觀。
在這一片公房下面,有很長一溜木屋,這是一條買賣街,房屋雖簡陋,但從剃頭擔子縫紉店到酒樓妓院應有盡有。
水師提督衙門已快竣工,出碼頭沿石階拾級而上,先是一個大草坪,有點將台、守望樓及兩座小炮樓,衙署基宇宏開,分前後三進、東西花廳、左右廂房;紅牆碧瓦,很是氣派。
站在前面草坪放眼四顧,島內風光盡收眼底。李鴻章在眾幕僚簇擁下,用望遠鏡仔細觀察著一切,臉上不由泛起了滿意的微笑,他喚著丁汝昌的字說:「禹廷,威海衛為你的建牙開府之地,也是水師根本所在,如何萬無一失、固若金湯,你們可要考慮周全!」
一句話開了個頭,丁汝昌乃從腋下夾著的羊皮護書中取出一張圖。此圖出自德國步兵工程師漢納根之手,為威海衛防禦總圖,島內碼頭、海堤及各工廨眾人皆看在眼中,唯兵力部署、火力分布不清楚,此圖則標識分明,一看全知。
丁汝昌將圖展開在草地上,向眾人講述威海防務--因是前明衛所,故也稱「威海衛」,它在煙台與成山角之間,其海灣成一箕形--依山有兩臂向東北斜伸入海,如半月形,而在口外橫有兩島,若泥丸塞海,即劉公島和日島。為保衛港灣,眼下已依地形構築了南北幫兩組永久性炮台,共配有大炮數十門,炮口一律伸向外海,火力強弱、遠近搭配得當,可組成一面密集的火網,而且,測量員又參照地形地物測準了距離,敵人若從海上來犯,無論是艦艇列陣而攻還是用步兵登陸,只要在有效射程之內,都能準確無誤地命中目標,使之葬身海底。
眾幕僚聽了丁汝昌的介紹,一個個無不點頭稱讚。
不想在旁邊看熱鬧的,有一記名守備,叫孫無忌,為人行事與名字吻合,說話不看場合,愛和人頂牛,夥伴們於是給他排了個渾名叫「老鴰嘴」。
「老鴰嘴」因一直未補上實缺,被丁汝昌派到工程處,在提督衙門工地當監工。他對威海防務一無所知,今天見這麼多人來到他的工地,面對海灣指指點點,因都穿著便服,「老鴰嘴」不認得中堂,便當一般場合也擠進來看熱鬧,當眾人說好時,竟突然插話說:「炮口皆向著大海,萬一敵人從背後進攻呢?」
眾人一下怔住了,丁汝昌深覺掃興,乃瞪他一眼,斥道:「你是何人,竟敢插嘴,滾!」
一聲斷喝,嚇得此人屁滾尿流而退。李鴻章也覺掃興,忙解嘲說:「此說不無道理,不過此人不知威海既為總埠,能不水陸依倚、前防後護?眼下榮成至煙台一線,為張朗齋中丞的嵩武軍防區,那可是一支百戰之師喲!」
張朗齋即山東巡撫張曜,他所率嵩武軍是左宗棠征西的主力,為百戰奇勳的戰將。用這支部隊守護後路,自是無虞。回到船上,李鴻章興致很高,丁汝昌看在眼中,提議道:「提督衙門竣工在即,老師何不留一匾額以資紀念?」
李鴻章欣然相諾,走至案前,提筆揮毫寫下四個大字:威震海疆。
與湘陰若何
看過威海看旅順。旅順的工地也熱火朝天,李鴻章十分滿意。回到船上特將丁汝昌留下,指陳方略,面授機宜,因無外人,乃坦陳心腹。
「禹廷,我們眼下是家大業大了!」李鴻章盤腿坐在銅床上,背靠枕頭雙目微閉面帶微笑,很是躊躇滿志怡然自得。
「是!水師有今天,乃老師嘔心瀝血之結果!」丁汝昌的恭維不露痕跡。
「這個嘛,說句粗話叫寡婦養崽,全靠眾人!」
李鴻章說罷哈哈大笑,將丁汝昌拉到身邊坐下,深有感歎地說:「同治初年,曾文正公讓徐壽父子試造『黃鵠號』,此為大清自造輪船之始。其時萬里海疆無防,是我們淮甸子弟篳路藍縷,白手起家,才有今天的局面。眼下北洋,閩江水師不能比,南洋粵海更不能比,這可是本錢!」
李鴻章最後於「本錢」二字加重了語氣,門生丁汝昌自然心領神會,師生二人都有些陶醉……
同治元年,李秀成攻上海,滬紳錢鼎鉻趕赴曾國藩大營,效申包胥秦庭一哭,始有李鴻章組軍援滬,此為淮軍之發軔。賴洋人洋槍洋炮之功,淮軍打出了威風,才月餘,李鴻章即由一記名道直升江蘇巡撫。
李鴻章由此對洋人的堅船利炮有了切身體驗。這以後老師曾國藩持盈保泰,急流勇退,處處讓淮軍佔先,淮軍成為天下勁旅,但督撫擁兵自重,兵為將有,餉由自籌,朝廷政令不能暢通,於以異族入主中原的愛新覺羅氏有礙,李鴻章有時想到兔死狗烹,不由毛骨悚然。
又是老師曾國藩一言解惑:淮軍利閣下安;淮軍鈍閣下危--短短十二個字,交與門生一個總訣:處此形勢,要麼韜光養晦,不做出頭檁子;要麼便樹大根深,讓人奈何不得。老師已選中前者,終於以「千古完人」而終;自己既已走了險棋,自應以雄圖霸舉而彪炳史冊……
沉默少許,李鴻章突然問道:「禹廷,你隨我幾十年,經歷不少,我想考考你!」
丁汝昌以為是問時事,乃說:「老師是問對法之軍事?」
老師不屑地一笑說:「法蘭西?關我鳥事?他們在越南打,距北洋遠著呢?我是想問問你--鄙人一生功業,與湘陰若何?」
「湘陰」自然指的是左宗棠,眼下載譽東歸,晉二等恪靖侯,這比李鴻章的一等肅毅伯要高一層;後又奉旨入值軍機,這等於享有宰相的名與實,這又比李鴻章僅有大學士的虛銜強;左宗棠一向對洋人強硬,輿論一直揚左抑李,這又是讓李鴻章氣餒的。眼下老師欲與左宗棠比本錢,丁汝昌心中躊躇,口裡卻說:「湘陰怎能比得上您!」
「何以見得?」
丁汝昌說:「湘陰以乙榜起家,居然也封侯拜相,區區一舉人,怎及您兩榜及第、金殿傳臚風光?所以,他入閣便遲了您好幾年,後來算是皇上賞了臉;另外,您這文華殿大學士為首輔,遠勝他那東閣;再說,他眼下出督兩江,兩江權重,可直督位尊……」
「俗了俗了,我又未讓你舉高腳牌!」李鴻章不讓他說完,頭連連在枕上擺道,「我不看表面文章!」
「這個--」丁汝昌不由語塞。
李鴻章嘲笑道:「你是鄉里人看戲,只重行頭不重功夫,唱做念打才是關鍵,何謂手眼身法步,何謂千斤韻白四兩皮,你全一竅不通!」
「門生還未弄通題意。」丁汝昌紅著臉自辯,「才說做官,怎麼又唱戲?」
李鴻章笑道:「戲臺小天地,天地大戲臺。我所謂本錢,便是指實力、人才、地盤及個人聲望之謂也?」
經如此一點撥,丁汝昌豁然開朗,忙說:「那湘陰無法望您項背!」
接下來他滔滔不絕,如數家珍,「第一,論手下才俊,湘陰以同鄉之地利,卻招不走曾文正身後的帳下文武,反而統統為您網羅,聽說他從新疆返京,除了衛士無一人追隨,出督兩江,只得重組幕府;第二,麾下戰將,除了劉錦棠和張曜,餘皆碌碌,但劉錦棠是曾文正公舊將,張曜屬淮軍系列,與主帥之淵源又豈能與您手下劉省三(銘傳)、潘琴軒(鼎新)及我輩比?再說地盤,此公起家於閩浙,後又出督陝甘,眼下又去兩江,從東南到西北再又東南,居無定所,哪能比您在北洋幾十年,勢如藩封,一省官員無不唯您馬首是瞻,這是他想也想不到的!」
「哈哈!」李鴻章坐直身子,指著丁汝昌說,「總算沾了邊--王壬秋(闓運)論他們湖南人物,謂胡詠芝能用人不能識人;左季高能識人不能容人;只有曾文正既能識人又能容人,此言真是不刊之論。左季高東征西討幾十年,帳下僅楊昌濬碩果僅存。如此刻薄寡恩之人,能不自歎帳下凋零?」
李鴻章說到這裡,一雙眼上下打量丁汝昌,丁汝昌明白老師的未盡之言--自己一個長毛降將,賴老師超擢拔識,一步一個臺階,眼下銜為武職正一品,職為實缺水師提督。想到這一層不由感激涕零,紅著臉說:「老師是有福大家享,有光大家沾,不像左湘陰,孤家寡人一個。」
李鴻章擺擺手說:「這還不算,他不及我的還不在這!」
丁汝昌一怔:「還有什麼?」
李鴻章伸個懶腰,趿著鞋,在艙房踱了一圈,洋洋自得地說:「他真正不如我的是洋務!」
丁汝昌說:「是啊,門生怎麼就丟了一大頭呢!湘陰在蘭州也辦了個機器局,可哪能比江南機器局?辦了個蘭州織呢局,又哪能比上海織布局?」
李鴻章又連連擺手說:「洋務之道,不外兩途,一為強兵富國,一為外交。眼下列強環伺,外交糾紛層出不窮,辦外交和輯列強,湘陰名望遠不及我。所以,凡發生交涉,要談判,洋人往往點名要我,這可是湘陰無可奈何的。」
中法大戰在即,諭旨命李鴻章速赴戎機,丁汝昌很想就此請纓,不料老師「指陳方略」盡扯些閒事。但畢竟追隨了二十餘年,他摸清了老師路數,此時細細品味,竟也悟出了一些不可言傳的東西……
中法戰起
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六月。這真是一個蝦荒蟹亂的兵戈之年,尚是初伏,就熱得不行。上海虹口公和祥碼頭至廣肇公所的大馬路上,原本是極繁華熱鬧的街市,此時因天氣太熱,至上午十點後便顯得有些蕭條了,頭上那一盆火似的驕陽烤得人頭皮發麻眼發花,地上熱浪滾滾、暑氣蒸人,行人多避走兩邊的樹蔭及店堂的屋簷下,除了鈴聲叮叮噹的馬車、人力車,馬路中間極少行人,連一向拼死拼活叫喊的小販、乞丐也多躲到弄堂口或石庫門洞邊,享受穿堂風的涼爽滋潤去了,馬路中間空蕩蕩的,只有近年才出現的報童不辭辛勞,此刻猶抱一摞摞散發著油墨香的報紙,閃在路口滿頭大汗地向行人兜售。那叫喊聲特別誇張,聲嘶力竭,令行人不時駐足圍觀,也引得臨街的茶樓酒館裡的客人推窗觀望。
「賣報賣報!《申報》《滬報》《時報》,還有洋文的《字林西報》,看法蘭西戰艦鼓浪東來,看李中堂奉旨巡海!」
多事之秋,危機四伏呵!去年朝鮮發生了政變--以國王生父大院君李罡應為首的保守派,唆使士兵譁變,反對王妃閔氏為首的閔氏家族,亂兵還焚日本使館、殺死日本僑民。日本天皇派兵前去問罪,幸虧中國事先獲得消息,北洋派出三千慶軍趕赴仁川,統領吳長慶採用袁世凱之謀,誘擒李罡應,迅速平定了暴亂,才使日本人無所藉口。
東鄰的事尚未完結,法國人又在越南打起來了。為此,朝廷不得不下詔,令因母喪丁憂在籍的李鴻章迅速回任北洋籌備戰守--今天的報紙,載的就是這事。
小百姓關心柴米油鹽往往超過國家大事--法國兵艦要來,說不定便要攻打上海,一旦港口被封鎖,物資運不進來,那米麵油鹽豈不要斷了供應?
「快走快走,公和泰米價怕又往上躥了!」這是布衣短褐赤腳草鞋的路人在喊叫。
「不急不急,只要李中堂出山,天下就太平了。李中堂百戰勳名,所向無敵,就憑了他老人家這塊牌子也足以嚇退洋人!」茶樓上的清客,見識又高了一層。
好像為了印證茶客們的猜測似的,十點半左右,大街的西頭突然出現了大隊手持大刀和背毛瑟槍的兵丁,他們成兩路縱隊從大街兩邊穿過,直達黃浦江邊,然後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地拉開距離,背向大街開始警戒,這中間另有大隊佩三橫槓臂章的印度巡捕,他們把住各通衢道口開始設卡攔阻行人。
接著,手持大令巡街的道標都司領一隊馬隊從那邊過來了,這是一隊雄赳赳氣昂昂的道標兵,一個個虎視眈眈地注視著兩邊的百姓。在公共租界出現大隊武裝華兵是不多見的事,官方事先顯然有過交涉,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猜疑:「好威風啊,接欽差啦!」
「還有洋人捧場啊!」
「去年兩江總督左宗棠巡視吳淞口要塞也沒這麼氣派!」
「嘿嘿,此人只怕比左爵相來頭還要大一些!」
「誰?」
「誰,李中堂唄,他老人家不是已到滬多時了嗎?」
果然,就在第三撥巡街道標兵走過,人們隱約望見從街西頭走過來一溜官轎,約幾十頂,打頭的是一頂平頂的、用藍布幔子遮護的四人小轎,抬轎的兵勇穿著白色無胸號背褡子,前後左右沒有儀仗執事、旗羅傘蓋,沒有誇耀主人功名爵祿、勳名職銜的高腳牌,更沒有鼓樂,冷冷清清,透出一股冷峻肅殺之氣,讓人好費猜疑。
更奇怪的是左右護兵及扶著轎槓的中軍雖也全副武裝,穿的卻是素服,連頭上的紅纓子也摘了,換了一根白綾子在打漂漂。過了這頂四人小轎,才是一色的綠呢頂八抬大轎,他們顯然是來送行的上海地方文武官員。
「咦,走頭的難道是李中堂?」
「怎麼像出殯似的,親兵護衛都穿孝呢?」
「這還不明白,李中堂還熱孝在身,照理是只能在家守靈。眼下雖奉旨出山,移孝作忠,可怎麼能不顧禮法去擺街抖威風呢?」茶客們的議論有典謨有訓誥,
「眼下中法大戰在即,人家這是效法老師曾文正公的故事,金革毋避,墨絰從戎!」
果然,待轎子走近,人們看見,小轎門簾掀起,李鴻章端坐轎中,一身重孝,目光呆滯,面帶戚容,分明一個「哀毀骨立、風吹即倒」的孝子模樣。
轎子到了公和祥碼頭,下到接官亭,此時接官亭已臨時搭起了一長溜天篷,直接到躉船上。只見北洋公署幕僚薛福成、馬建忠、于式枚、羅豐祿等文官,丁汝昌、葉志超等武將及李經方、李經述等李氏子侄早已等候在碼頭上,他們全是一身素服,李鴻章剛下轎,眾人馬上圍上來請安,緊隨其後的上海道劉瑞芬、織布局總辦盛宣懷、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等一齊擁上來要與中堂話別,李鴻章一見,僅回身向送行的拱了拱手,道聲「各位請回」,便繞開前面一幫子人直往躉船。
下到江邊,只見狹窄的黃浦江上已擺滿了上飄各國旗幟的輪船,緊靠公和祥碼頭的是北洋水師「康濟號」練船,眼下艙門大開,船上官佐皆在甲板上雁陣兩行為中堂站班。李鴻章再次轉身拱手讓堅持送上躉船的官員留步,然後在長子經方次子經述左右攙扶下跨上「康濟號」左舷甲板。隨著一聲長長的汽笛,岸上也響起了送行官員一片祝誦聲:「中堂一帆風順!」
「康濟號」第二次拉響汽笛後便啟動了,隨著艦尾白色水花翻起,緩緩掉頭駛向吳淞口。
李鴻章今年六十二歲了,與五短身材、面團團如滿月的左宗棠不同,他生得長身鶴立,面目清癯,尤其是花甲過後,鬢邊白髮、顎下銀鬚,面飄然如玉樹臨風,人謂此為「仙鶴」之姿。此刻「仙鶴」高昂著頭,對列隊鵠立在甲板上的官佐僅點點頭,便旁若無人地緩緩走向後艄,憑欄向漸行漸遠的大上海眺望--在烈日的照耀下,十里洋場熱氣蒸騰,高樓大廈鱗次櫛比,遠遠望去,像用巨石壘起一道道逶迤起伏的城牆,城牆上飄著旌旗,排列著劍戟。
上海,二十一年前是他李鴻章的發跡之地,在這裡,他以赫赫威名、煌煌戰績,使自己由一名不見於經傳的書生,成為一個雄圖霸舉、舉世矚目的人物,今天,時局孔艱,他又在眾人注目下,由這裡再度出山,去迎接更大的機遇與挑戰……
康濟號
滔滔黃海,遠接天際。「康濟號」,正加足馬力劈波斬浪朝北急駛……
一覺醒來的李鴻章披衣漫步在甲板上,縱情地眺望著大海。天公造物,煞是怪異--前天還碧波蕩漾、宛如平湖的大海,一覺醒來卻黃湯滾滾,濁浪翻騰,而代替蒸人暑氣的是一絲絲北風,拂衣而過,涼意沁人心脾。
不是才一覺的工夫麼?東海與黃海差異竟如此之大,才一千三百噸、航速不過九海浬的「康濟號」航行在這洪濤巨浪之間,有如一匹羸馬艱難地跋涉在沙漠戈壁中。
然而,大海不比沙漠,水性隨勢而流,漂浮不定,看似柔媚卻不時掀起排空濁浪,潛伏著殺機……
由此,他不由想到「雲譎波詭」一詞,再進一層,又想到人們常用的比喻:官場--宦海。今天,他這個宦海弄潮兒奉旨奪情復出,雖有「奉旨」二字打頭,但於一個標榜「孝行第一」的孔聖門徒,父母之喪未能盡禮,究竟是臨危受命移孝作忠還是貪戀祿位不惜羽毛呢?
然而,他卻實在是有說不出的苦衷--自他丁憂出缺,朝廷派張樹聲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張樹聲雖為淮系舊人,自己一手提拔上來的,竟然也生鵲巢鳩佔之心,為迎合輿論,竟與京師那一班主戰派桴鼓相應,甚至上疏奏調清流幹將張佩綸幫辦北洋軍務。
這不是成心假戲真做,為擴充羽翼而拉攏方方面面的人物嗎?當御史楊崇伊把這消息寫信告訴他時,李鴻章不由在心裡冷笑了。
張佩綸少年科第,玉堂金馬中人,一向自視甚高,怎在乎一赳赳武夫的薦引呢?何況張父印塘是李鴻章舊友,張佩綸和他這個「老世叔」政見儘管不同,私交卻是不薄,哪怕就在李鴻章居喪期間,二人也不斷魚傳尺素、驛寄梅花,此番的「墨絰從戎」便是在張佩綸一再奏請下促成的。真是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啊!
想到此,他真想開懷大笑,道行淺薄的張樹聲,張網看不清三尺深的水,燒香竟然拜錯了廟!
「大人,前面快到渤海口了,水師的艦船已結隊來迎了呢!」李鴻章正倚欄回想聯翩,丁汝昌從艦橋上下來,匆匆走到他身後向他稟報。
他從容回頭望了丁汝昌一眼,又順著他的手勢往左前方看去,只見沿大陸一線,島嶼星羅棋布,有幾個比島更小的黑點成直線漂浮在海中間,如隱在雲霧中的星星,渺彌相望,若隱若現。
他接過丁汝昌手中的單筒望遠鏡細看--前面果然來了一長溜艦船,為首一艘船頭高高翹起,看那輪廓真有些像前年從英國購回的「揚威號」巡洋艦,他不由笑著點了點頭。
四年前,日本從英國沙木大造船廠購得一艘千噸級巡洋艦,號「扶桑」,駛回日本後,引起朝野轟動。次年,海軍中將西鄉從道率「扶桑號」訪華,拜訪了李鴻章,交談中西鄉從道得意之色溢於言表。
李鴻章將詳情奏聞朝廷,朝廷這才對海防有了緊迫感,「揚威」與「超勇」就是在這時從英國購進的,這是一對姊妹船,排水量與「康濟號」差不多,都是一千三百噸,馬力卻比「康濟」大了三倍--「康濟」馬力才七百五十匹,「揚威」、「超勇」卻都是二千四百匹,航速達十五海浬。這以前北洋只幾艘馬尾船廠造的木殼炮船,幾個大的海浪也能掀翻它,直到「揚威」、「超勇」駛回,北洋才算擁有具有遠航能力的巡洋艦。
上午九時,南下相迎的水師各艦終於在山東成山角海面與「康濟號」相遇。「揚威」、「超勇」為首,「威遠」、「泰安」、「鎮海」、「操江」四艘炮艦及「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邊」、「鎮中」六艘炮艇成一字縱隊迎上來,各艦艇上將弁一齊在甲板列隊,遠遠向著立在「康濟」艦橋上的李鴻章打千請安,各艦一齊放響了禮炮,一時之間,硝煙四起,霹靂山崩,李鴻章雖一身素服,但在眾幕僚簇擁下,仍遠遠地向將弁們微笑著揮手致意……
「康濟」駛過後,艦隊立刻變換隊形,由一字縱隊一分為二,跟在「康濟」後邊轉過成山角,由東向西緩緩向水師的第一大軍港威海進發……
威鎮海疆
應該說渤海灣地勢,渾然天成--自大陸線艮維左轉,三千里河山斜伸入海,將中國北部與日本隔開,是為朝鮮,這是一道天然屏障。接下來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如兩條巨臂,控扼渤海灣,兩大半島最近距離不過兩百多里,這又是第二道屏障,京津就如在巨臂的拱衛中。
前明時代,倭寇猖獗,為保衛京師,明廷曾下令於威海、天津兩地設衛所,煙台便因戚繼光建烽火台而得名。
兩年前,李鴻章和他的幕僚們及洋顧問參照前明史料,通過測量、繪圖、篩選後確認,如果在威海、旅順擺上一支新式水師,則如給兩臂配上了兩把利劍,進可馳騁黃海、西朝鮮灣,退可在渤海灣周旋,神京當無恙矣!謀定而發,乃奏明朝廷,在威海和旅順建北洋水師總埠,在旅順設水師提督行轅,在威海劉公島上設提督公署。
今天,他先去看威海。
短短四天行程,從東海到黃海,不但海水變色,氣候也似乎由夏而秋--眼下的威海港灣陽光明媚,海風涼爽宜人。
「康濟號」進入港內停泊後,李鴻章走出官艙,立刻被眼前熱火朝天的施工場面吸引住了。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水師提督衙門,它座落在劉公島半山腰上。以前這一帶只一小小漁村,數十戶人家在山下結茅而居,十分簡陋;山上榛莽叢生、山石掩沒,一片荒涼,有幸的是它被李鴻章選中,做了北洋水師的基地。
自威海建港後,劉公島一下熱鬧起來,島上大道縱橫,人來人往,金碧輝煌的水師提督衙門巍然聳立,在它的周圍幾乎拓平了半邊山,依次而建的是水師營房、學堂、發電廠、倉庫、電報局、修械所、醫院及外籍雇員娛樂場。這些建築先後開工,目前都在建設中,但見屋架林立,吆喝之聲此起彼伏,很是壯觀。
在這一片公房下面,有很長一溜木屋,這是一條買賣街,房屋雖簡陋,但從剃頭擔子縫紉店到酒樓妓院應有盡有。
水師提督衙門已快竣工,出碼頭沿石階拾級而上,先是一個大草坪,有點將台、守望樓及兩座小炮樓,衙署基宇宏開,分前後三進、東西花廳、左右廂房;紅牆碧瓦,很是氣派。
站在前面草坪放眼四顧,島內風光盡收眼底。李鴻章在眾幕僚簇擁下,用望遠鏡仔細觀察著一切,臉上不由泛起了滿意的微笑,他喚著丁汝昌的字說:「禹廷,威海衛為你的建牙開府之地,也是水師根本所在,如何萬無一失、固若金湯,你們可要考慮周全!」
一句話開了個頭,丁汝昌乃從腋下夾著的羊皮護書中取出一張圖。此圖出自德國步兵工程師漢納根之手,為威海衛防禦總圖,島內碼頭、海堤及各工廨眾人皆看在眼中,唯兵力部署、火力分布不清楚,此圖則標識分明,一看全知。
丁汝昌將圖展開在草地上,向眾人講述威海防務--因是前明衛所,故也稱「威海衛」,它在煙台與成山角之間,其海灣成一箕形--依山有兩臂向東北斜伸入海,如半月形,而在口外橫有兩島,若泥丸塞海,即劉公島和日島。為保衛港灣,眼下已依地形構築了南北幫兩組永久性炮台,共配有大炮數十門,炮口一律伸向外海,火力強弱、遠近搭配得當,可組成一面密集的火網,而且,測量員又參照地形地物測準了距離,敵人若從海上來犯,無論是艦艇列陣而攻還是用步兵登陸,只要在有效射程之內,都能準確無誤地命中目標,使之葬身海底。
眾幕僚聽了丁汝昌的介紹,一個個無不點頭稱讚。
不想在旁邊看熱鬧的,有一記名守備,叫孫無忌,為人行事與名字吻合,說話不看場合,愛和人頂牛,夥伴們於是給他排了個渾名叫「老鴰嘴」。
「老鴰嘴」因一直未補上實缺,被丁汝昌派到工程處,在提督衙門工地當監工。他對威海防務一無所知,今天見這麼多人來到他的工地,面對海灣指指點點,因都穿著便服,「老鴰嘴」不認得中堂,便當一般場合也擠進來看熱鬧,當眾人說好時,竟突然插話說:「炮口皆向著大海,萬一敵人從背後進攻呢?」
眾人一下怔住了,丁汝昌深覺掃興,乃瞪他一眼,斥道:「你是何人,竟敢插嘴,滾!」
一聲斷喝,嚇得此人屁滾尿流而退。李鴻章也覺掃興,忙解嘲說:「此說不無道理,不過此人不知威海既為總埠,能不水陸依倚、前防後護?眼下榮成至煙台一線,為張朗齋中丞的嵩武軍防區,那可是一支百戰之師喲!」
張朗齋即山東巡撫張曜,他所率嵩武軍是左宗棠征西的主力,為百戰奇勳的戰將。用這支部隊守護後路,自是無虞。回到船上,李鴻章興致很高,丁汝昌看在眼中,提議道:「提督衙門竣工在即,老師何不留一匾額以資紀念?」
李鴻章欣然相諾,走至案前,提筆揮毫寫下四個大字:威震海疆。
與湘陰若何
看過威海看旅順。旅順的工地也熱火朝天,李鴻章十分滿意。回到船上特將丁汝昌留下,指陳方略,面授機宜,因無外人,乃坦陳心腹。
「禹廷,我們眼下是家大業大了!」李鴻章盤腿坐在銅床上,背靠枕頭雙目微閉面帶微笑,很是躊躇滿志怡然自得。
「是!水師有今天,乃老師嘔心瀝血之結果!」丁汝昌的恭維不露痕跡。
「這個嘛,說句粗話叫寡婦養崽,全靠眾人!」
李鴻章說罷哈哈大笑,將丁汝昌拉到身邊坐下,深有感歎地說:「同治初年,曾文正公讓徐壽父子試造『黃鵠號』,此為大清自造輪船之始。其時萬里海疆無防,是我們淮甸子弟篳路藍縷,白手起家,才有今天的局面。眼下北洋,閩江水師不能比,南洋粵海更不能比,這可是本錢!」
李鴻章最後於「本錢」二字加重了語氣,門生丁汝昌自然心領神會,師生二人都有些陶醉……
同治元年,李秀成攻上海,滬紳錢鼎鉻趕赴曾國藩大營,效申包胥秦庭一哭,始有李鴻章組軍援滬,此為淮軍之發軔。賴洋人洋槍洋炮之功,淮軍打出了威風,才月餘,李鴻章即由一記名道直升江蘇巡撫。
李鴻章由此對洋人的堅船利炮有了切身體驗。這以後老師曾國藩持盈保泰,急流勇退,處處讓淮軍佔先,淮軍成為天下勁旅,但督撫擁兵自重,兵為將有,餉由自籌,朝廷政令不能暢通,於以異族入主中原的愛新覺羅氏有礙,李鴻章有時想到兔死狗烹,不由毛骨悚然。
又是老師曾國藩一言解惑:淮軍利閣下安;淮軍鈍閣下危--短短十二個字,交與門生一個總訣:處此形勢,要麼韜光養晦,不做出頭檁子;要麼便樹大根深,讓人奈何不得。老師已選中前者,終於以「千古完人」而終;自己既已走了險棋,自應以雄圖霸舉而彪炳史冊……
沉默少許,李鴻章突然問道:「禹廷,你隨我幾十年,經歷不少,我想考考你!」
丁汝昌以為是問時事,乃說:「老師是問對法之軍事?」
老師不屑地一笑說:「法蘭西?關我鳥事?他們在越南打,距北洋遠著呢?我是想問問你--鄙人一生功業,與湘陰若何?」
「湘陰」自然指的是左宗棠,眼下載譽東歸,晉二等恪靖侯,這比李鴻章的一等肅毅伯要高一層;後又奉旨入值軍機,這等於享有宰相的名與實,這又比李鴻章僅有大學士的虛銜強;左宗棠一向對洋人強硬,輿論一直揚左抑李,這又是讓李鴻章氣餒的。眼下老師欲與左宗棠比本錢,丁汝昌心中躊躇,口裡卻說:「湘陰怎能比得上您!」
「何以見得?」
丁汝昌說:「湘陰以乙榜起家,居然也封侯拜相,區區一舉人,怎及您兩榜及第、金殿傳臚風光?所以,他入閣便遲了您好幾年,後來算是皇上賞了臉;另外,您這文華殿大學士為首輔,遠勝他那東閣;再說,他眼下出督兩江,兩江權重,可直督位尊……」
「俗了俗了,我又未讓你舉高腳牌!」李鴻章不讓他說完,頭連連在枕上擺道,「我不看表面文章!」
「這個--」丁汝昌不由語塞。
李鴻章嘲笑道:「你是鄉里人看戲,只重行頭不重功夫,唱做念打才是關鍵,何謂手眼身法步,何謂千斤韻白四兩皮,你全一竅不通!」
「門生還未弄通題意。」丁汝昌紅著臉自辯,「才說做官,怎麼又唱戲?」
李鴻章笑道:「戲臺小天地,天地大戲臺。我所謂本錢,便是指實力、人才、地盤及個人聲望之謂也?」
經如此一點撥,丁汝昌豁然開朗,忙說:「那湘陰無法望您項背!」
接下來他滔滔不絕,如數家珍,「第一,論手下才俊,湘陰以同鄉之地利,卻招不走曾文正身後的帳下文武,反而統統為您網羅,聽說他從新疆返京,除了衛士無一人追隨,出督兩江,只得重組幕府;第二,麾下戰將,除了劉錦棠和張曜,餘皆碌碌,但劉錦棠是曾文正公舊將,張曜屬淮軍系列,與主帥之淵源又豈能與您手下劉省三(銘傳)、潘琴軒(鼎新)及我輩比?再說地盤,此公起家於閩浙,後又出督陝甘,眼下又去兩江,從東南到西北再又東南,居無定所,哪能比您在北洋幾十年,勢如藩封,一省官員無不唯您馬首是瞻,這是他想也想不到的!」
「哈哈!」李鴻章坐直身子,指著丁汝昌說,「總算沾了邊--王壬秋(闓運)論他們湖南人物,謂胡詠芝能用人不能識人;左季高能識人不能容人;只有曾文正既能識人又能容人,此言真是不刊之論。左季高東征西討幾十年,帳下僅楊昌濬碩果僅存。如此刻薄寡恩之人,能不自歎帳下凋零?」
李鴻章說到這裡,一雙眼上下打量丁汝昌,丁汝昌明白老師的未盡之言--自己一個長毛降將,賴老師超擢拔識,一步一個臺階,眼下銜為武職正一品,職為實缺水師提督。想到這一層不由感激涕零,紅著臉說:「老師是有福大家享,有光大家沾,不像左湘陰,孤家寡人一個。」
李鴻章擺擺手說:「這還不算,他不及我的還不在這!」
丁汝昌一怔:「還有什麼?」
李鴻章伸個懶腰,趿著鞋,在艙房踱了一圈,洋洋自得地說:「他真正不如我的是洋務!」
丁汝昌說:「是啊,門生怎麼就丟了一大頭呢!湘陰在蘭州也辦了個機器局,可哪能比江南機器局?辦了個蘭州織呢局,又哪能比上海織布局?」
李鴻章又連連擺手說:「洋務之道,不外兩途,一為強兵富國,一為外交。眼下列強環伺,外交糾紛層出不窮,辦外交和輯列強,湘陰名望遠不及我。所以,凡發生交涉,要談判,洋人往往點名要我,這可是湘陰無可奈何的。」
中法大戰在即,諭旨命李鴻章速赴戎機,丁汝昌很想就此請纓,不料老師「指陳方略」盡扯些閒事。但畢竟追隨了二十餘年,他摸清了老師路數,此時細細品味,竟也悟出了一些不可言傳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