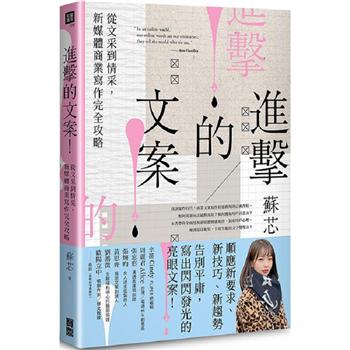第2 章 用戶的新喜好和小心思
2.1 網路毒化了用戶的大腦嗎?
在本書第一章中,我們分析了新媒體時代媒介形勢的變化和資訊在不同類型平臺上的流動規則,這對創作者創作出高傳播度的作品至關重要。在傳播學領域,有一句著名警句,叫作「媒介即訊息」,它由媒介理論家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提出,意在提醒人們媒介形式的重要性。麥克魯漢在其著作《認識媒體: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中曾寫過一個有力的比喻:媒介是竊賊,我們是看門狗,媒介內容是一塊美味的肉,竊賊為了轉移看門狗的注意,將肉扔給了我們,因此我們只注重媒介的內容,而忽略了媒介的形式。麥克魯漢認為,拋開媒介傳遞的內容不談,媒介形式本身的出現和發展,就會導致尺度變化、速度變化和模式變化。他在這裡又打了一個比方:
鐵路的作用並不是把運動、運輸、輪子或道路引入人類社會,而是加速並擴大人們過去的功能,創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和新型的閒暇。無論鐵路是在熱帶還是在北方寒冷的環境中運轉,都發生了這樣的變化。這樣的變化與鐵路媒介所運輸的貨物或內容是毫無關係的。
從紙質媒體時代,到電子媒體時代,再到數字化媒體時代,媒介形式的變化讓人們產生了哪些變化?它們又是怎樣改變、重塑著人們的閱讀習慣、思維方式甚至行為模式的?美國作家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G. Carr)在《淺薄》(The Shallows)一書中,比較了網路誕生前後,不同媒介形式對人們思維方式的影響。卡爾認為,由於人的大腦是高度可塑的,網路的出現,正在讓全神貫注的「線性思維」被一種新的、更「淺薄」的思維模式取代,新的思維模式習慣於用簡短、雜亂、爆炸性的方式收發資訊,遵循的原則是愈快愈好。
他在書中寫道:
正如麥克魯漢所說,媒體不僅僅是資訊通道。媒體提供思考的素材,同時它們也在影響思考的過程。網路所做的似乎就是把我們的專注和思考能力撕成碎片,拋到一邊。無論是上網還是不上網,我現在獲取資訊的方式都是網路傳播資訊的方式,即透過快速移動的粒子流來傳播資訊。以前,我戴著潛水呼吸器,在文字的海洋中緩緩前進。現在,我就像一個摩托快艇手,貼著水面呼嘯而過。
隨著人們閱讀的載體從紙面發展到螢幕,發生變化的不僅是人們的閱讀方式,還有人們閱讀的專注程度和深入程度。網路時代的閱讀是一種「超連結」式閱讀,我們在網頁上的許多文章中都能看到超連結,點擊這些超連結,我們就可以從一篇文章連接到另一篇文章,從一個觀點跳到另一個觀點。在數字文件的連結之間跳躍,顯然比在紙質印刷品之間來回翻閱要便捷和高效許多。
然而,超連結在充當高效導航工具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用戶精力的分散。與此同時,用戶的閱讀方式也會發生很大的變化。過去,用戶可以捧著一本書沉浸式地、從頭至尾地將它讀完,現在,用戶在讀某一篇文章時就可能被其中的某個超連結吸引,整個閱讀路線可能會呈現樹枝那樣的枝椏狀。也就是說,用戶的閱讀方式正在由「線性閱讀」往「非線性閱讀」轉變。
網路的閱讀環境鼓勵淺度、非線性、多任務式的閱讀,它還設計了一個高效反饋的機制來鼓勵大家這樣做。比如,我們每點開一個連結,就可以看到一堆新鮮的內容;我們每刷一次朋友圈,讓人心癢難耐的「小紅點」就會消失;我們在搜尋引擎上每搜尋一次內容,就會看到相關資訊的列表。
相信許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當你在新聞網站上閱讀資訊時,LINE提示音忽然響了起來,同事在群組中向你發送了一個工作文件,你不得不點開查看;幾秒鐘後,你的電子郵件信箱又跳出一個彈出式視窗,告訴你剛收到一封郵件,於是你點開郵件標題查看內容並寫了一封回覆郵件;接著,你的電話響了,是快遞人員打來告訴你,你購買的快遞放在了社區收發室,你掛了電話,忍不住打開LINE TODAY滑了滑熱門搜尋,卻看到了某個明星離婚的消息,於是你在這個話題下看了一陣子熱鬧⋯⋯就這樣,一兩個小時稍縱即逝,你最開始打開的那個新聞網站還在孤零零地等著你把文章讀完,但你早就忘了它的存在了。
演員阿茲・安薩里(Aziz Ansari)曾指出,當人們去查看Instagram的新回覆或《紐約時報》又更新了什麽內容的時候,其實他們在意的根本不是獲取內容,而是沉迷於那種看到新事物的感覺。
在尼古拉斯・卡爾看來,網路毒化了用戶的大腦,讓人們變得愈來愈「淺薄」,這裡的「淺薄」或許不是一個貶義詞,它代表著用戶的閱讀習慣乃至思維模式都正在喪失「深潛」的能力。在新媒體時代,創作者必須知曉用戶閱讀習慣和思維模式的變化,並在內容品質與用戶喜好之間尋找平衡,才有更大的機率創作出受人歡迎的作品。
2.2 賭場機制與甜甜圈效應
在憂心忡忡的學者們眼裡,用戶的大腦正遭遇網路的「毒化」,他們的注意力被五光十色的電子產品與數字化內容撕扯成支離破碎的碎片,他們正失去深度思考的能力。那麽,在這個變化發生的時候,網路的各個產品又起到了哪些推波助瀾的作用呢?
據美國《告示牌》(Billboard)榜單數據顯示,流行歌曲的長度正變得愈來愈短。2000年,《告示牌》單曲榜單中,時長中位數為4分6秒;2010年,這個數字減少到3分40秒;到了2018年,則進一步下降到3分31秒。不僅流行歌曲的整體長度變短了,歌曲的前奏也變得愈來愈短,而且前奏變短的目的,正是儘快抓住用戶的注意力,否則等待它們的命運就是被用戶迅速地「跳過」。
當注意力成為一種稀缺資源時,當前眾多的網路產品,無論是圖文、影片還是音檔,就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去獲取用戶的注意力、黏住用戶的注意力。當用戶在Instagram、抖音等App上播放一段搞笑影片,看完一個之後,系統會自動為他們播放下一支短片,而且播放的內容都是搞笑類的短片,符合用戶當時內容消費的「胃口」。這樣的產品機制太瞭解當代用戶容易分心的特質,於是製造了連續不斷的觀賞體驗,讓用戶不用動手指就能看到自己感興趣的內容。
以抖音這款短片App為例,從它剛剛上線到日活躍用戶(Daily Active User)突破2億5000萬人,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抖音之所以能收獲數量這麽龐大的高黏著度用戶群體,和它的產品設計機制密不可分。
曾經有人將抖音的產品界面比作「賭場」。當用戶進入抖音App界面之後,原本出現在手機頂部的信號、時間、電量等資訊統統都被短片界面覆蓋了,用戶一旦開始觀看抖音短片,就看不到現在幾點幾分,也無法精確地知悉自己已經看了多久的短片。抖音的產品設計刻意模糊了用戶對時間的判斷,因此會有「抖音5分鐘,人間1小時」的戲謔說法。
這樣的產品機制和賭場的裝潢很類似,賭場都會安裝電子天幕,無論賭場外是淩晨幾點,賭場內看到的都是一片藍天白雲,這容易讓賭徒們產生一種「天色還早,還能再玩一會兒」的心理;此外,賭場都是無窗的,至少在裡面很難看到透明的玻璃窗,這也是為了將賭徒與外界充分地隔離開來,讓他們產生沉浸式的體驗。
滑抖音時,用戶被源源不斷地推薦感興趣的內容,這個過程就像在不斷地接收演算法遞過來的「甜甜圈」,用戶並不知道下一個「甜甜圈」是草莓味還是巧克力味的,但無論是什麽口味的,它都會是一個美味的「甜甜圈」,在這樣未知又充滿期待的心理下,用戶就會感到難以自拔。
資訊流開發者阿薩・拉斯金(Aza Raskin)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你的手機螢幕背後,有上千名工程師正試圖使軟體最大限度地讓你上癮。在各網路產品以「日活躍用戶」和「用戶使用時長」作為衡量產品價值的最重要層面時,以使用戶「上癮」為目的的產品機制的出現,就變得不那麽難以理解了。
Facebook的產品經理葛瑞格・馬拉(Greg Marra)就曾把網路產品中常見的資訊流比作「甜甜圈」——一種營養價值不高但讓人喜愛的甜食。眾所周知,甜食能使人分泌快樂的多巴胺。也許有時用戶想喝一杯清爽健康的羽衣甘藍汁,但網路產品從「點擊率」出發,依然不斷遞給用戶一個個「甜甜圈」,用戶又難以抗拒,因此形成循環。從短期來看,滿足了用戶內容消費的需求,但從長期來看,卻並沒有為用戶提供足夠的「營養」。對此,技術作家湯瑪斯・戈茨(Thomas Goetz)曾提出了一項「甜甜圈」測試,呼籲網路公司推出的每一個新產品都應該通過這項測試。這個「甜甜圈」測試包含以下五個問題:
1.它是否減少了人們獨自使用的時間?
2.它可以幫助人們多運動嗎?
3.它對你和你的家人、朋友或社區有益嗎?
4.使用它之後,會讓人感覺更好嗎?
5.人們使用它愈多,就能收益愈多嗎?
甜甜圈測試的目的是釐清一款產品給用戶帶來的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如果以它為標準,目前盛行的網路產品中,有幾個能順利通過測試呢?
2.3 數字時代用戶的「病症」
數字時代的居民是雙面的、矛盾的,他們一面興致勃勃、精力充沛,眼神追逐著一條條滑過資訊流的內容,一面又疲憊不堪、精神渙散,眼睛下掛著濃厚的黑眼圈;他們一面渴望著更多新鮮的內容與刺激,一面又因為資訊過載而感到焦慮不已。歸納起來,數字時代的用戶在資訊消費領域具有以下五種病症。
病症一:注意力渙散症
注意力渙散症,或許是資訊過載的數字時代最為常見的一種大眾病症了。韓裔瑞士籍哲學家韓炳哲在其著作《倦怠社會》中提出了「超注意力」的概念,認為人們的深度注意力正在日益邊緣化、渙散化,並在不間斷的多個資訊源之間來回切換,他這樣描述道:
過度的刺激、資訊和資訊,從根本上改變了注意力的結構和運作方式,感知因此變得分散、碎片化。深度注意力日益邊緣化,讓位於另一種注意力——超注意力。這種渙散的注意力體現為不斷地在多個任務、資訊來源和工作日程之間轉換焦點。
不得不承認,如今讓人分散注意力的事物可謂密集地分布在用戶周圍,電子郵件、朋友的簡訊、新聞桌面彈出視窗、股市資訊、明星八卦等,只要有螢幕在的地方,就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訊。人們通常不停地重複著相似的動作:拖動滑鼠並點擊游標按鈕,敲擊電腦鍵盤,在一個個網頁間切換、手指在狹小的手機鍵盤上迅速跳躍,拇指向下以拖動資訊流,點擊消除一個個因為更新資訊而出現的小紅點⋯⋯。
我們在做出這些行為的同時,我們的眼睛、耳朵、指尖都會收到相應的反饋,我們大腦的視覺皮層、觸覺皮層和聽覺皮層也會隨之收到穩定的刺激,我們的大腦也變得愈來愈習慣如此頻繁切換與多任務並行的模式。也就是說,我們的大腦已經接受了導致注意力分散的各類刺激,並默認它們為正常模式了。
過去,當人們接收資訊時,比如當我們讀一本書、讀一份報紙時,我們的注意力就像在進行一次「深潛」,紙質讀物給我們提供了潛水所需的足夠的「氧氣」;而數字時代,當我們消費內容時,我們的注意力就好像在進行一次次的「浮潛」,我們需要不時地浮出水面進行「緩氣」,而在這個過程中,注意力的連貫性與深度就隨之失去了。
這種現象也被稱作「注意力殘留症」(Attention Residue),也是多任務、多線條並行的工作模式所導致的一種「病症」。注意力殘留是指當人們從任務A轉向任務B時,我們的注意力並沒有即時轉移,殘留的一部分注意力依然在思考任務A。如果在轉移之前,我們對任務A缺乏控制或關注度較低,這種殘留就會更加嚴重。即使在轉移之前我們已經完成了任務A,我們的注意力依然會有一段殘留的時間。任務的間斷會導致工作效率降低,在多個任務、多件事項疊加時就會產生注意力殘留。
當代用戶的工作、生活、娛樂環境,都是一種允許注意力殘留出現的環境。在職場中,人們在多個會議中穿梭,在電腦前伏案時,會不時地收到不得不查看並及時回覆的電子郵件;在生活中、娛樂中,在發達的消費社會和應接不暇的商品面前,用戶的注意力也很容易發生轉移。注意力殘留現象不利於人們養成深度工作、深度思考的習慣,也會導致效率的降低。
病症二:錯失恐懼症
隨著技術的發展,人們的社交行為已經全面「線上化」了。智慧型手機變成了人類隨身攜帶的「新器官」,LINE、Facebook等平臺讓人們隨時隨地可以與他人保持溝通,人類只要睜著眼,就一直處於心理上的上線狀態,對網路的依賴正在持續增強。這就導致當一個人不在線上、未連線時,往往會感受到一種悵然若失的焦慮感,這樣的焦慮會讓人們產生負面情緒和抑鬱感受,這被稱為「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
一般而言,當用戶錯過了某個社交事件、社交經歷、社交互動,或是對它們既沒參與也不知情時,就會引發錯失恐懼症。比如,人們總是擔心錯過朋友圈的動態,每個小紅點出現時都要及時消滅;自己所在的LINE群組裡就算有100條未讀訊息,也要爬回頂部一條條讀完;出門要是忘記帶手機,那感覺簡直比坐牢還難熬;要是在朋友圈刷到了幾個好友在聚會時發的照片而你對此毫不知情,那一刻真的會產生被世界遺棄的恐懼。
不過,一些飽受錯失恐懼症困擾的人也反向滋生出另一種心態,那就是JOMO(joy of missing out)心理,即「享受錯過」。關閉Facebook朋友圈、不帶手機出門一天等行為都屬於JOMO的範疇,這樣的行為在資訊過載的傳播環境下,往往能給當事人帶來放空般的治癒作用。
病症三:社交焦慮症
社群媒體在給人們帶來豐富的資訊與娛樂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小的社交焦慮。在社群媒體上,人們展示自己的生活、表達自我的觀點並在虛擬世界進行社交,但是這種展示與表達比線下的社交更容易進行粉飾與偽裝——人們往往傾向於在社群媒體上展示自己生活的精采時刻,有選擇性地展示生活的酸甜苦辣,社群媒體上大部分人的生活看上去都是光彩熠熠的,這樣的特點,就很容易讓平臺上的用戶因攀比而產生壓力與失落感。
據調研機構Origin數據顯示,有超過一半的Z世代成年人表示他們「正減少對社群媒體使用」,甚至有1/3的人表示會永久關閉社群媒體帳戶。可以看出,與日俱增的社交壓力已經讓不少年輕人開始重新審視甚至階段性放棄社群媒體。在國內年輕人中,也有不少人正在使用 「關閉朋友圈」或「只顯示三天朋友圈」的微信功能。不少中國用戶認為,社群媒體使得他們的個人資訊安全及隱私缺乏保障,減少了他們的睡眠時間,使他們的注意力變得不夠集中甚至讓他們的視力變差。
「發一條朋友群組動態」或「發推」成了許多人在生活中遇到開心、驚喜、意外時第一時間的反應。甚至有的人在遭遇車禍、地震等危險事件後所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在社群媒體上更新狀態。除了這些較為極端的案例,愈來愈多的人也開始意識到,社群媒體占用了他們太多時間,讓他們錯過了生活中更多真實的瞬間。就連著名歌手瑪丹娜(Madonna)也在接受媒體採訪談到社群媒體時表示「它們只會讓你們感覺更不好」。瑪丹娜在社群媒體上是名副其實的「大V」,擁有的粉絲數量超過3000萬人,她認為社群媒體會讓人不自覺地和其他人比較,而這種比較只會讓人更不喜歡自己,並使人成為獲得他人肯定的奴隸。瑪丹娜的觀點也道出了人們對經營自己社交帳戶,以及維護自己社交面孔、希望獲得他人肯定的壓力。
2.1 網路毒化了用戶的大腦嗎?
在本書第一章中,我們分析了新媒體時代媒介形勢的變化和資訊在不同類型平臺上的流動規則,這對創作者創作出高傳播度的作品至關重要。在傳播學領域,有一句著名警句,叫作「媒介即訊息」,它由媒介理論家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提出,意在提醒人們媒介形式的重要性。麥克魯漢在其著作《認識媒體: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中曾寫過一個有力的比喻:媒介是竊賊,我們是看門狗,媒介內容是一塊美味的肉,竊賊為了轉移看門狗的注意,將肉扔給了我們,因此我們只注重媒介的內容,而忽略了媒介的形式。麥克魯漢認為,拋開媒介傳遞的內容不談,媒介形式本身的出現和發展,就會導致尺度變化、速度變化和模式變化。他在這裡又打了一個比方:
鐵路的作用並不是把運動、運輸、輪子或道路引入人類社會,而是加速並擴大人們過去的功能,創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和新型的閒暇。無論鐵路是在熱帶還是在北方寒冷的環境中運轉,都發生了這樣的變化。這樣的變化與鐵路媒介所運輸的貨物或內容是毫無關係的。
從紙質媒體時代,到電子媒體時代,再到數字化媒體時代,媒介形式的變化讓人們產生了哪些變化?它們又是怎樣改變、重塑著人們的閱讀習慣、思維方式甚至行為模式的?美國作家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G. Carr)在《淺薄》(The Shallows)一書中,比較了網路誕生前後,不同媒介形式對人們思維方式的影響。卡爾認為,由於人的大腦是高度可塑的,網路的出現,正在讓全神貫注的「線性思維」被一種新的、更「淺薄」的思維模式取代,新的思維模式習慣於用簡短、雜亂、爆炸性的方式收發資訊,遵循的原則是愈快愈好。
他在書中寫道:
正如麥克魯漢所說,媒體不僅僅是資訊通道。媒體提供思考的素材,同時它們也在影響思考的過程。網路所做的似乎就是把我們的專注和思考能力撕成碎片,拋到一邊。無論是上網還是不上網,我現在獲取資訊的方式都是網路傳播資訊的方式,即透過快速移動的粒子流來傳播資訊。以前,我戴著潛水呼吸器,在文字的海洋中緩緩前進。現在,我就像一個摩托快艇手,貼著水面呼嘯而過。
隨著人們閱讀的載體從紙面發展到螢幕,發生變化的不僅是人們的閱讀方式,還有人們閱讀的專注程度和深入程度。網路時代的閱讀是一種「超連結」式閱讀,我們在網頁上的許多文章中都能看到超連結,點擊這些超連結,我們就可以從一篇文章連接到另一篇文章,從一個觀點跳到另一個觀點。在數字文件的連結之間跳躍,顯然比在紙質印刷品之間來回翻閱要便捷和高效許多。
然而,超連結在充當高效導航工具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用戶精力的分散。與此同時,用戶的閱讀方式也會發生很大的變化。過去,用戶可以捧著一本書沉浸式地、從頭至尾地將它讀完,現在,用戶在讀某一篇文章時就可能被其中的某個超連結吸引,整個閱讀路線可能會呈現樹枝那樣的枝椏狀。也就是說,用戶的閱讀方式正在由「線性閱讀」往「非線性閱讀」轉變。
網路的閱讀環境鼓勵淺度、非線性、多任務式的閱讀,它還設計了一個高效反饋的機制來鼓勵大家這樣做。比如,我們每點開一個連結,就可以看到一堆新鮮的內容;我們每刷一次朋友圈,讓人心癢難耐的「小紅點」就會消失;我們在搜尋引擎上每搜尋一次內容,就會看到相關資訊的列表。
相信許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當你在新聞網站上閱讀資訊時,LINE提示音忽然響了起來,同事在群組中向你發送了一個工作文件,你不得不點開查看;幾秒鐘後,你的電子郵件信箱又跳出一個彈出式視窗,告訴你剛收到一封郵件,於是你點開郵件標題查看內容並寫了一封回覆郵件;接著,你的電話響了,是快遞人員打來告訴你,你購買的快遞放在了社區收發室,你掛了電話,忍不住打開LINE TODAY滑了滑熱門搜尋,卻看到了某個明星離婚的消息,於是你在這個話題下看了一陣子熱鬧⋯⋯就這樣,一兩個小時稍縱即逝,你最開始打開的那個新聞網站還在孤零零地等著你把文章讀完,但你早就忘了它的存在了。
演員阿茲・安薩里(Aziz Ansari)曾指出,當人們去查看Instagram的新回覆或《紐約時報》又更新了什麽內容的時候,其實他們在意的根本不是獲取內容,而是沉迷於那種看到新事物的感覺。
在尼古拉斯・卡爾看來,網路毒化了用戶的大腦,讓人們變得愈來愈「淺薄」,這裡的「淺薄」或許不是一個貶義詞,它代表著用戶的閱讀習慣乃至思維模式都正在喪失「深潛」的能力。在新媒體時代,創作者必須知曉用戶閱讀習慣和思維模式的變化,並在內容品質與用戶喜好之間尋找平衡,才有更大的機率創作出受人歡迎的作品。
2.2 賭場機制與甜甜圈效應
在憂心忡忡的學者們眼裡,用戶的大腦正遭遇網路的「毒化」,他們的注意力被五光十色的電子產品與數字化內容撕扯成支離破碎的碎片,他們正失去深度思考的能力。那麽,在這個變化發生的時候,網路的各個產品又起到了哪些推波助瀾的作用呢?
據美國《告示牌》(Billboard)榜單數據顯示,流行歌曲的長度正變得愈來愈短。2000年,《告示牌》單曲榜單中,時長中位數為4分6秒;2010年,這個數字減少到3分40秒;到了2018年,則進一步下降到3分31秒。不僅流行歌曲的整體長度變短了,歌曲的前奏也變得愈來愈短,而且前奏變短的目的,正是儘快抓住用戶的注意力,否則等待它們的命運就是被用戶迅速地「跳過」。
當注意力成為一種稀缺資源時,當前眾多的網路產品,無論是圖文、影片還是音檔,就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去獲取用戶的注意力、黏住用戶的注意力。當用戶在Instagram、抖音等App上播放一段搞笑影片,看完一個之後,系統會自動為他們播放下一支短片,而且播放的內容都是搞笑類的短片,符合用戶當時內容消費的「胃口」。這樣的產品機制太瞭解當代用戶容易分心的特質,於是製造了連續不斷的觀賞體驗,讓用戶不用動手指就能看到自己感興趣的內容。
以抖音這款短片App為例,從它剛剛上線到日活躍用戶(Daily Active User)突破2億5000萬人,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抖音之所以能收獲數量這麽龐大的高黏著度用戶群體,和它的產品設計機制密不可分。
曾經有人將抖音的產品界面比作「賭場」。當用戶進入抖音App界面之後,原本出現在手機頂部的信號、時間、電量等資訊統統都被短片界面覆蓋了,用戶一旦開始觀看抖音短片,就看不到現在幾點幾分,也無法精確地知悉自己已經看了多久的短片。抖音的產品設計刻意模糊了用戶對時間的判斷,因此會有「抖音5分鐘,人間1小時」的戲謔說法。
這樣的產品機制和賭場的裝潢很類似,賭場都會安裝電子天幕,無論賭場外是淩晨幾點,賭場內看到的都是一片藍天白雲,這容易讓賭徒們產生一種「天色還早,還能再玩一會兒」的心理;此外,賭場都是無窗的,至少在裡面很難看到透明的玻璃窗,這也是為了將賭徒與外界充分地隔離開來,讓他們產生沉浸式的體驗。
滑抖音時,用戶被源源不斷地推薦感興趣的內容,這個過程就像在不斷地接收演算法遞過來的「甜甜圈」,用戶並不知道下一個「甜甜圈」是草莓味還是巧克力味的,但無論是什麽口味的,它都會是一個美味的「甜甜圈」,在這樣未知又充滿期待的心理下,用戶就會感到難以自拔。
資訊流開發者阿薩・拉斯金(Aza Raskin)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你的手機螢幕背後,有上千名工程師正試圖使軟體最大限度地讓你上癮。在各網路產品以「日活躍用戶」和「用戶使用時長」作為衡量產品價值的最重要層面時,以使用戶「上癮」為目的的產品機制的出現,就變得不那麽難以理解了。
Facebook的產品經理葛瑞格・馬拉(Greg Marra)就曾把網路產品中常見的資訊流比作「甜甜圈」——一種營養價值不高但讓人喜愛的甜食。眾所周知,甜食能使人分泌快樂的多巴胺。也許有時用戶想喝一杯清爽健康的羽衣甘藍汁,但網路產品從「點擊率」出發,依然不斷遞給用戶一個個「甜甜圈」,用戶又難以抗拒,因此形成循環。從短期來看,滿足了用戶內容消費的需求,但從長期來看,卻並沒有為用戶提供足夠的「營養」。對此,技術作家湯瑪斯・戈茨(Thomas Goetz)曾提出了一項「甜甜圈」測試,呼籲網路公司推出的每一個新產品都應該通過這項測試。這個「甜甜圈」測試包含以下五個問題:
1.它是否減少了人們獨自使用的時間?
2.它可以幫助人們多運動嗎?
3.它對你和你的家人、朋友或社區有益嗎?
4.使用它之後,會讓人感覺更好嗎?
5.人們使用它愈多,就能收益愈多嗎?
甜甜圈測試的目的是釐清一款產品給用戶帶來的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如果以它為標準,目前盛行的網路產品中,有幾個能順利通過測試呢?
2.3 數字時代用戶的「病症」
數字時代的居民是雙面的、矛盾的,他們一面興致勃勃、精力充沛,眼神追逐著一條條滑過資訊流的內容,一面又疲憊不堪、精神渙散,眼睛下掛著濃厚的黑眼圈;他們一面渴望著更多新鮮的內容與刺激,一面又因為資訊過載而感到焦慮不已。歸納起來,數字時代的用戶在資訊消費領域具有以下五種病症。
病症一:注意力渙散症
注意力渙散症,或許是資訊過載的數字時代最為常見的一種大眾病症了。韓裔瑞士籍哲學家韓炳哲在其著作《倦怠社會》中提出了「超注意力」的概念,認為人們的深度注意力正在日益邊緣化、渙散化,並在不間斷的多個資訊源之間來回切換,他這樣描述道:
過度的刺激、資訊和資訊,從根本上改變了注意力的結構和運作方式,感知因此變得分散、碎片化。深度注意力日益邊緣化,讓位於另一種注意力——超注意力。這種渙散的注意力體現為不斷地在多個任務、資訊來源和工作日程之間轉換焦點。
不得不承認,如今讓人分散注意力的事物可謂密集地分布在用戶周圍,電子郵件、朋友的簡訊、新聞桌面彈出視窗、股市資訊、明星八卦等,只要有螢幕在的地方,就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訊。人們通常不停地重複著相似的動作:拖動滑鼠並點擊游標按鈕,敲擊電腦鍵盤,在一個個網頁間切換、手指在狹小的手機鍵盤上迅速跳躍,拇指向下以拖動資訊流,點擊消除一個個因為更新資訊而出現的小紅點⋯⋯。
我們在做出這些行為的同時,我們的眼睛、耳朵、指尖都會收到相應的反饋,我們大腦的視覺皮層、觸覺皮層和聽覺皮層也會隨之收到穩定的刺激,我們的大腦也變得愈來愈習慣如此頻繁切換與多任務並行的模式。也就是說,我們的大腦已經接受了導致注意力分散的各類刺激,並默認它們為正常模式了。
過去,當人們接收資訊時,比如當我們讀一本書、讀一份報紙時,我們的注意力就像在進行一次「深潛」,紙質讀物給我們提供了潛水所需的足夠的「氧氣」;而數字時代,當我們消費內容時,我們的注意力就好像在進行一次次的「浮潛」,我們需要不時地浮出水面進行「緩氣」,而在這個過程中,注意力的連貫性與深度就隨之失去了。
這種現象也被稱作「注意力殘留症」(Attention Residue),也是多任務、多線條並行的工作模式所導致的一種「病症」。注意力殘留是指當人們從任務A轉向任務B時,我們的注意力並沒有即時轉移,殘留的一部分注意力依然在思考任務A。如果在轉移之前,我們對任務A缺乏控制或關注度較低,這種殘留就會更加嚴重。即使在轉移之前我們已經完成了任務A,我們的注意力依然會有一段殘留的時間。任務的間斷會導致工作效率降低,在多個任務、多件事項疊加時就會產生注意力殘留。
當代用戶的工作、生活、娛樂環境,都是一種允許注意力殘留出現的環境。在職場中,人們在多個會議中穿梭,在電腦前伏案時,會不時地收到不得不查看並及時回覆的電子郵件;在生活中、娛樂中,在發達的消費社會和應接不暇的商品面前,用戶的注意力也很容易發生轉移。注意力殘留現象不利於人們養成深度工作、深度思考的習慣,也會導致效率的降低。
病症二:錯失恐懼症
隨著技術的發展,人們的社交行為已經全面「線上化」了。智慧型手機變成了人類隨身攜帶的「新器官」,LINE、Facebook等平臺讓人們隨時隨地可以與他人保持溝通,人類只要睜著眼,就一直處於心理上的上線狀態,對網路的依賴正在持續增強。這就導致當一個人不在線上、未連線時,往往會感受到一種悵然若失的焦慮感,這樣的焦慮會讓人們產生負面情緒和抑鬱感受,這被稱為「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
一般而言,當用戶錯過了某個社交事件、社交經歷、社交互動,或是對它們既沒參與也不知情時,就會引發錯失恐懼症。比如,人們總是擔心錯過朋友圈的動態,每個小紅點出現時都要及時消滅;自己所在的LINE群組裡就算有100條未讀訊息,也要爬回頂部一條條讀完;出門要是忘記帶手機,那感覺簡直比坐牢還難熬;要是在朋友圈刷到了幾個好友在聚會時發的照片而你對此毫不知情,那一刻真的會產生被世界遺棄的恐懼。
不過,一些飽受錯失恐懼症困擾的人也反向滋生出另一種心態,那就是JOMO(joy of missing out)心理,即「享受錯過」。關閉Facebook朋友圈、不帶手機出門一天等行為都屬於JOMO的範疇,這樣的行為在資訊過載的傳播環境下,往往能給當事人帶來放空般的治癒作用。
病症三:社交焦慮症
社群媒體在給人們帶來豐富的資訊與娛樂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小的社交焦慮。在社群媒體上,人們展示自己的生活、表達自我的觀點並在虛擬世界進行社交,但是這種展示與表達比線下的社交更容易進行粉飾與偽裝——人們往往傾向於在社群媒體上展示自己生活的精采時刻,有選擇性地展示生活的酸甜苦辣,社群媒體上大部分人的生活看上去都是光彩熠熠的,這樣的特點,就很容易讓平臺上的用戶因攀比而產生壓力與失落感。
據調研機構Origin數據顯示,有超過一半的Z世代成年人表示他們「正減少對社群媒體使用」,甚至有1/3的人表示會永久關閉社群媒體帳戶。可以看出,與日俱增的社交壓力已經讓不少年輕人開始重新審視甚至階段性放棄社群媒體。在國內年輕人中,也有不少人正在使用 「關閉朋友圈」或「只顯示三天朋友圈」的微信功能。不少中國用戶認為,社群媒體使得他們的個人資訊安全及隱私缺乏保障,減少了他們的睡眠時間,使他們的注意力變得不夠集中甚至讓他們的視力變差。
「發一條朋友群組動態」或「發推」成了許多人在生活中遇到開心、驚喜、意外時第一時間的反應。甚至有的人在遭遇車禍、地震等危險事件後所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在社群媒體上更新狀態。除了這些較為極端的案例,愈來愈多的人也開始意識到,社群媒體占用了他們太多時間,讓他們錯過了生活中更多真實的瞬間。就連著名歌手瑪丹娜(Madonna)也在接受媒體採訪談到社群媒體時表示「它們只會讓你們感覺更不好」。瑪丹娜在社群媒體上是名副其實的「大V」,擁有的粉絲數量超過3000萬人,她認為社群媒體會讓人不自覺地和其他人比較,而這種比較只會讓人更不喜歡自己,並使人成為獲得他人肯定的奴隸。瑪丹娜的觀點也道出了人們對經營自己社交帳戶,以及維護自己社交面孔、希望獲得他人肯定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