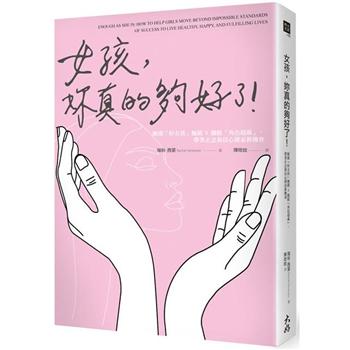Chapter 4 克服自我懷疑,勇敢踏出舒適圈
──打破「固定型心態」,冒有益身心健康的風險
每次我成功地做到我原先害怕或緊張的事情時,都會使我更加自信。
──潔西,十九歲
◆如果我做不到怎麼辦?學習設定務實的目標
有「固定型心態」的女孩用一種奇怪的邏輯在面對挑戰:她們越害怕失敗,就越期待失敗。過大的目標很少等於成功;事實上,它們通常會導致挫敗。完美主義的人,在面對挑戰時容易設定不切實際的期望。
你的女兒如何追求目標與這些目標是什麼一樣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好消息是,她可以透過改變對成功的看法,來學習面對自我懷疑。
你的女兒需要了解現實生活中的成功,通常是透過一點一滴的累積而來的,而不是突然出現在某個史詩般的光榮時刻。我會在我的工作坊上建議女孩,「每天做一些讓妳稍微緊張的事情。」例如,潔西會練習「微勇氣」,在生活周遭找些小機會,練習她想獲得的重要技能。她會去一家咖啡廳,然後一家又一家。李決定在教授們的辦公時間去找他們,並努力不跳過任何一餐。這些女孩每天採取一個小步驟。
在實踐上,我使用一個「三階段」的系統來規畫目標:舒適區、低風險區和高風險區。哈迪亞是一名大一學生,她的目標是能夠在課堂上發言。她的舒適區──現在對她來說很容易的事──是在課堂上保持安靜。她告訴我,她偶爾會自願朗讀。
我問她的低風險區是什麼:一個可以朝向她上課發言目標邁進的小步驟。低風險區──應該讓妳感到緊張但不會把妳嚇壞。換句話說,它牽涉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面對的風險。
哈迪亞決定在每一堂課上發言三次。這是一個在課堂上幾乎不說話的女孩!不,我說,再試一次,再採取小一點的步驟。
哈迪亞對我翻了個白眼,但想了又想。她說她可以發電子郵件給教授,表達她對發言感到的焦慮,並希望能和他見面討論。
她的高風險區是什麼?這會是她可以邁向目標的一個步驟,只是現在感覺起來還有點太可怕。對哈迪亞來說,這個步驟是在班上選座位時,坐在前排,讓發言這件事變得不可避免,而教授更有可能點到她。伴隨著這項練習,會發生兩件很棒的事:首先,隨著女孩做到低風險區的步驟,並變得更有勇氣,高風險區的步驟看起來也不會那麼可怕。隨著時間過去,練習會轉化成習慣。在她們的書《信心密碼》(The Confidence Code)中,凱蒂.凱(Katty Kay)和克萊爾.史普曼(Claire Shipman)寫道,「你從擅長的事情中獲得的信心是具有傳染性的,它會蔓延。你擅長什麼甚至不重要:對一個孩子來說,它可以是像綁鞋帶一樣簡單的事。重要的是,擅長一件事會讓你有信心嘗試別的東西。」所以當女孩意識到她們想變換朋友圈,或為戲劇表演進行試鏡時,她們不會再將這些挑戰視為一個令人畏懼且需要被克服的單一時刻,而是一道她們可以逐漸攀升的階梯,並在最後達到目標。
這對十七歲的喬安娜來說特別真實。在參加「勇氣訓練營」時,她的目標是讓自己變成肢體更靈活的舞者。在參加我們的工作坊之前,她告訴我,她會毫不猶豫地給自己設定一週五天、每天伸展一小時的目標。這也是為什麼她會坐在我們的教室裡,在前幾堂課給我白眼的原因。
隨著時間過去,她開始發現把標準設得太高,只會讓她感到挫敗,讓她完全停止伸展。她決定只在做功課的空檔或在學校課間休息時隨機做點伸展。不,這並不理想。「這是一種妥協,」她說,在一開始就覺得很奇怪。
在實施她的新計畫幾天後,喬安娜意識到,她喜歡生活沒有那種「我永遠無法滿足的期望」的心理負擔。她了解設定每天伸展一小時的目標,然後沒辦法做到,只會讓她感覺很差勁。「當妳能以更小的步驟做事時,妳對自己的感覺會更好。妳知道妳在完成某些東西……這就像,當妳從一份清單上劃掉一些完成事項時,會得到的那種快樂。」但是,她說:「當妳有這些高標準時,就不容易將焦點放在妳從學習和生活過程中所獲得的喜悅上,因為妳投入的目的只是想得到最好的表現結果。」凱和史普曼寫道,「信心與行動有關。」也許對女孩信心最大的威脅不是失敗,而是不行動、不做、不練習。這就是女孩傾向做的:低頭將手放在大腿上而不是舉起來,提出異議,而不是潛入水中。
一遍又一遍地,當我與女孩調整她們設定目標的方式時,我會給那些擁有偉大夢想,追求高成就的學生一個建議:降低妳的標準。她們每次都會笑,但我很認真,而她們也很快地就發現這是多麼有效。
我使用一個小技巧:在她們選擇去冒一個較小的風險後,我會問她們對它的看法。如果她們翻白眼,嘀咕著這個挑戰幾乎不算什麼,或是說這「感覺起來很蠢」,那就對了!她們找到了一個合適的目標,而且她們準備採取行動。
Chapter 5 妳不是往壞處想,就是想太多
──「心理跑步機」讓妳焦慮和轉不停的腦袋疲累不堪
「我是那種,當我上床睡覺時,會重新回顧我在白天說的每句話,然後對超過一半的話責怪自己的人。」──哈珀,十六歲
◆負面思考推著妳前進:防禦性悲觀
在考試前與一群女孩坐在一起,妳會聽到各種各樣的聲音此起彼落地預測最壞的情況:
「我一定會考不及格。」
「這會毀了我的學業成績平均點數。」
「我永遠畢不了業。」
心理學家稱之為「防禦性悲觀」(Defensive Pessimism),或「計畫失敗」。它運作的原理是這樣的:當你在面對挑戰時,預先設想一個負面的結果。如果事情如你所願,你會感到驚喜;如果沒有,那麼你也為失望的結果做好了心理準備。這與準備「緊急避難包」是一樣的心理,是你為了以防萬一而做的準備。
「我一直告訴自己最壞的情況就是那樣,所以即使我做得不那麼好,我的感覺會好一點。」十六歲的阿維莎告訴我。摩根是一位二十二歲的大學畢業生,她對我描述她在申請工作時按下「發送」按鈕的心情。「我說,『好吧,有這麼多人申請,大多數的人都比妳更有資格,而妳只做了這個和那個,所以妳不會得到這份工作。』」「妳參加考試,然後對自己說,『我會失敗,這堂課我不會過』」,二十一歲的米菲比說,「或是『我可能必須採用不會顯示分數的通過/不通過的選項』,或『我畢不了業或找不到工作。我必須讓自己準備好面對失敗。』」她補充說,預期被拒絕,讓她能提前對任何可能發生的痛苦感到麻木。
威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的朱莉.諾瑞姆(Julie Norem)教授在研究中發現,約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會運用「防禦性悲觀」,主要為了排解焦慮的情緒,而防禦性悲觀者在工作上的表現往往更有效率。十六歲的哈珀說得更簡潔:「負面觀點推動我前進。」換句話說,這不一定是壞事。
然而,每當我聽到女孩大聲宣布她們會失敗得多慘,我都對這個說法抱持懷疑的態度。「防禦性悲觀」意味著你將負能量邀請進你的生活中,這樣你才能應付挑戰。心理學家認為這是一種管理焦慮的有效方式;但研究證明,防禦性悲觀者經常對自己產生負面的想法。緊接在「我將會失敗」之後的是「我可能沒那麼聰明」,或是「如果我失敗了,沒有進入我想就讀的學校,讓我的父母失望怎麼辦?」
這種消極的思維模式降低一個人的自尊心,並提高發生抑鬱症狀的機率。低落的自尊心可能會使一個女孩更加倍努力──也許她還會把它當作一種自我懲罰。所以她努力了、成功了,並快速提高了她的自尊心;但如果她預測自己會失敗,那麼,她就會因為對自己的缺失做出正確判斷,而獲得小小的勝利。她會告訴自己,「我不是說過了嗎?」當下一個挑戰來臨時,這個循環又重新開始──就像你每天洗澡往身上抹肥皂又沖掉一般,日復一日。
這是我們希望女孩學習的方式嗎?是基於對失敗的恐懼而不是對成功的希望所驅動?思考她們不想要什麼,而不是對她們想要的懷抱更大的夢想?研究顯示,被「逃避表現目標」──避免比別人表現更差的渴望──激勵的人,更有可能努力實現目標。他們不太會有內在動力,比起學習並享受它,他們更擔心形象受損。二〇〇三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大學女生明顯比男生更擔心表現得比別人差。由於多種原因,女孩更容易有「防禦性悲觀」。女孩將失敗看得特別重,並將失敗解釋為自己缺乏能力的標誌──她們實際上感受到的焦慮比男孩嚴重得多。當女孩比男孩成功時,她會貶低自己的才能,這表示成功並不能使她們變得更有自信(對男孩來說,成功則會讓他們變得更有自信)。如果女孩感覺自己面臨失敗的威脅越來越大,她們更可能採取自我保護的立場,而不是侵略性──我做得到──的態度。
我們不要忘記,女孩的世界喜歡防禦性悲觀者。她們預想最糟的結果,是在實踐社會認可的謙虛。「我把那個考試考砸了」也是女孩在說「我不是那麼聰明、成功、精通」的代名詞。女孩的謙卑,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同儕朋友和成年人的獎勵。
女孩關於「我很醜-不-我最醜」的對話,是很接近「防禦性悲觀」的表現。一個女孩大聲地表達她擔心自己的職業夢想不會成真,她的朋友會安慰她:「妳在開玩笑吧,我相信妳一定沒問題,我表現得比妳差多了!」兩個女孩都獲得同儕的認可和壓力釋放。她們可以透過將自己的恐懼外放來停止再想它。因為她們通過了女孩世界的「謙虛測試」,她們彼此馬上會更喜歡對方。
「這是種扭曲的社群感,」十七歲的喬安娜告訴我,「知道妳並不孤單,令人感到放心。妳們一起完成了所有事情,也一起做好了準備,並一起經歷了這一切,之後它很自然地變成共享失敗的同溫層。」
但是,當你深入一點探究,你會看到表面下潛藏著不那麼具有姐妹情誼的東西。隨著女孩分享她們的恐懼,競爭的種子也開始萌芽。「妳拿自己與其他人做比較,」喬安娜說:
即使當妳聽到別人說「我搞砸了」,妳會說些讓她們放心的話,但妳可能在心裡面會說,「哦,她把這個搞砸了,但我沒有。」這讓我站在更高的位置上。有一點點像是……貶低別人來抬高自己。
女孩悄悄地從盟友變成競爭對手。一直在說她們的缺點,會讓女孩感到自己不夠好和有所缺乏。這是一個「比較」的有害配方。為了真正感到放心,她們可能需要知道另一個人已經失敗了。如同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說過的,「成功還不夠,其他人必須失敗。」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這種行為會成為一種習慣,讓女孩每次面臨未知且結果可能會令人失望的挑戰時,都傾向於依賴這種心態。如果女孩不是真的期待會成功,她們如何對新的可能性保持完全開放的心態?「防禦性悲觀」可能會讓女孩感覺更好、更確定,但它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好奇心和成長的可能。這不是對她們成功機會所進行的深思熟慮,只是用「反正我可能會失敗」來面對每一個重大問題。它也可能會影響信心;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當女性低估自己的能力時,她們不太可能冒險並探索新的機會。
女孩在學習成長上能感受到的喜悅很少,尤其是表現最好的人。太多人似乎認為苦難等於成功。如果它沒有傷害你、嚇唬你、給你關於失敗的噩夢,或是讓你壓力大到瀕臨極限,你一定是不夠努力,這樣你也不配成功。
「防禦性悲觀」是這種痛苦次文化的一部分。這是一種大幅減低焦慮並將謙卑最大化的工具,但它犧牲的卻是女孩的勇氣。畢竟,女孩無法在面對風險時,透過快速拉上她們思想和靈魂的窗戶,並祈禱免於遭受甚至還沒發生的失敗,來變得更強大。不,當她們能確實地思考失敗可能意味著什麼和看起來是什麼樣子,而不是轉向她們想像中那些不真實的災難畫面,她們才會變得更強大。
幫助女孩不僅想像挫折,也想像她們對挫折的反應,會是取代防禦性悲觀並增加其信心的方法。幾十年來,運動心理學家透過在競賽前將賽事具象化的方法來培養菁英運動員。運動員對賽事進行「意象」(Imaging)是一種訓練工具,讓參賽者在不可預測的情況發生前,制定應對策略。
如果你的女兒擔心可能被拒絕,無論是工作上或在學校裡,和她一起討論聽到「不」的感受。她想像自己會有什麼感受?她會想到什麼?她在接到被拒絕的消息後,如何關照自己?她接下來還能做什麼來推動自己前進?
現在和她一起想像,她在聽到「是」的時候會有什麼感受。她會感覺什麼和想到什麼?為什麼這個勝利對她來說是重要的?她會如何慶祝?擁有這兩種情境將有助於提醒她,為什麼她起初會關心這件事(或者,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不關心)。這可以幫助她記得,對於如何處理發生在她身上的事,她是有所選擇的,同時你也可以向她保證,無論如何,你都會在身邊支持她。在我開始教導女孩有關「防禦性悲觀」之前,預期最壞的情況也是我的祕密策略,而我從未對它多做思考。然後,我開始在學生的話語裡聽到自己。聽著這些聰明勤奮、未來正在等著她們的女孩告訴我,她們將會輸得多慘,給我帶來很大的刺激──它讓我很生氣。
我開始面對自己的壞習慣。每隔幾個月的時間,我會向《紐約時報》提交一份社論。每次我按下「發送」按鈕時,我會對自己竊竊私語:「他們會拒絕它。」 我確實被拒絕過:一次、兩次、三次、四次。當然,它令人失望。然後,有件奇怪的事發生了。有個影像突然進入我的腦海中:影像中的人是我,手上拿著《紐約時報》,並看到我的名字印在上面。
想像成功對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經驗。但是,我已經被拒絕了很多次,因此聽到「不」的經驗,對我而言已經不再陌生──我不僅知道它,還知道它不會把我殺了。
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我揭露了「奧茲大帝」(Great and Powerful Oz)的真面目(我要聲明,我以此比喻「失敗」,而不是《紐約時報》),並且發現「失敗」就如同電影中的奧斯卡,不是奧茲王國預言中的奧茲大帝,而只是一個在馬戲團耍小手段的騙子魔術師。
練習面對「失敗」、「不」、「拒絕」、「失望」的心態:這是放棄「防禦性悲觀」心態的關鍵。一旦我害怕失敗的感覺消退,我就沒有什麼理由需要保護自己;我可以更專注於冒險帶來的樂趣,而不是建立認知障礙來保護自己免受風險。
讓我再說一遍:我可以真的享受自己在做的事。我可以抓住機會,享受樂趣,並從挑戰中學習。
如果你是個防禦性悲觀者,你可能已經向女兒傳達過一些類似的觀念。我們很容易幫孩子和學生寫好面對風險的劇本,正如一位大學生告訴研究人員:「我的父母總是說,『不要將目標設得太高,因為妳只會感到失望。』……他們總是小心地不想提高我的希望,這樣我就不會感到失望。」在與女兒談她的習慣之前,花一些時間反思自己的習慣。諾瑞姆設計了一份調查問卷,目的就在於衡量「防禦性悲觀」。其中的問題包括:儘管我應該會做得很好,但我經常在一開始就預期最壞的情況。
我花了很多時間想像可能會出現什麼問題。
我會在這些情況下,小心不要變得過度自信。
在這些情況下,有時我更擔心自己看起來會不會像個傻瓜,而不是擔心是否做得好。
考量可能出錯的情況,有助於我做好準備。
我們大多數的人不會為了打擊孩子,告訴他去預期最壞的情況。我們在建議女孩不要對目標感到太興奮時,我們認為自己是在保護她們。但是,我可以確定地說,社會已經在那個部分做很多了,女孩需要從父母那裡得到的是,幫助她們設想從失敗中恢復和成功的能力。
──打破「固定型心態」,冒有益身心健康的風險
每次我成功地做到我原先害怕或緊張的事情時,都會使我更加自信。
──潔西,十九歲
◆如果我做不到怎麼辦?學習設定務實的目標
有「固定型心態」的女孩用一種奇怪的邏輯在面對挑戰:她們越害怕失敗,就越期待失敗。過大的目標很少等於成功;事實上,它們通常會導致挫敗。完美主義的人,在面對挑戰時容易設定不切實際的期望。
你的女兒如何追求目標與這些目標是什麼一樣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好消息是,她可以透過改變對成功的看法,來學習面對自我懷疑。
你的女兒需要了解現實生活中的成功,通常是透過一點一滴的累積而來的,而不是突然出現在某個史詩般的光榮時刻。我會在我的工作坊上建議女孩,「每天做一些讓妳稍微緊張的事情。」例如,潔西會練習「微勇氣」,在生活周遭找些小機會,練習她想獲得的重要技能。她會去一家咖啡廳,然後一家又一家。李決定在教授們的辦公時間去找他們,並努力不跳過任何一餐。這些女孩每天採取一個小步驟。
在實踐上,我使用一個「三階段」的系統來規畫目標:舒適區、低風險區和高風險區。哈迪亞是一名大一學生,她的目標是能夠在課堂上發言。她的舒適區──現在對她來說很容易的事──是在課堂上保持安靜。她告訴我,她偶爾會自願朗讀。
我問她的低風險區是什麼:一個可以朝向她上課發言目標邁進的小步驟。低風險區──應該讓妳感到緊張但不會把妳嚇壞。換句話說,它牽涉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面對的風險。
哈迪亞決定在每一堂課上發言三次。這是一個在課堂上幾乎不說話的女孩!不,我說,再試一次,再採取小一點的步驟。
哈迪亞對我翻了個白眼,但想了又想。她說她可以發電子郵件給教授,表達她對發言感到的焦慮,並希望能和他見面討論。
她的高風險區是什麼?這會是她可以邁向目標的一個步驟,只是現在感覺起來還有點太可怕。對哈迪亞來說,這個步驟是在班上選座位時,坐在前排,讓發言這件事變得不可避免,而教授更有可能點到她。伴隨著這項練習,會發生兩件很棒的事:首先,隨著女孩做到低風險區的步驟,並變得更有勇氣,高風險區的步驟看起來也不會那麼可怕。隨著時間過去,練習會轉化成習慣。在她們的書《信心密碼》(The Confidence Code)中,凱蒂.凱(Katty Kay)和克萊爾.史普曼(Claire Shipman)寫道,「你從擅長的事情中獲得的信心是具有傳染性的,它會蔓延。你擅長什麼甚至不重要:對一個孩子來說,它可以是像綁鞋帶一樣簡單的事。重要的是,擅長一件事會讓你有信心嘗試別的東西。」所以當女孩意識到她們想變換朋友圈,或為戲劇表演進行試鏡時,她們不會再將這些挑戰視為一個令人畏懼且需要被克服的單一時刻,而是一道她們可以逐漸攀升的階梯,並在最後達到目標。
這對十七歲的喬安娜來說特別真實。在參加「勇氣訓練營」時,她的目標是讓自己變成肢體更靈活的舞者。在參加我們的工作坊之前,她告訴我,她會毫不猶豫地給自己設定一週五天、每天伸展一小時的目標。這也是為什麼她會坐在我們的教室裡,在前幾堂課給我白眼的原因。
隨著時間過去,她開始發現把標準設得太高,只會讓她感到挫敗,讓她完全停止伸展。她決定只在做功課的空檔或在學校課間休息時隨機做點伸展。不,這並不理想。「這是一種妥協,」她說,在一開始就覺得很奇怪。
在實施她的新計畫幾天後,喬安娜意識到,她喜歡生活沒有那種「我永遠無法滿足的期望」的心理負擔。她了解設定每天伸展一小時的目標,然後沒辦法做到,只會讓她感覺很差勁。「當妳能以更小的步驟做事時,妳對自己的感覺會更好。妳知道妳在完成某些東西……這就像,當妳從一份清單上劃掉一些完成事項時,會得到的那種快樂。」但是,她說:「當妳有這些高標準時,就不容易將焦點放在妳從學習和生活過程中所獲得的喜悅上,因為妳投入的目的只是想得到最好的表現結果。」凱和史普曼寫道,「信心與行動有關。」也許對女孩信心最大的威脅不是失敗,而是不行動、不做、不練習。這就是女孩傾向做的:低頭將手放在大腿上而不是舉起來,提出異議,而不是潛入水中。
一遍又一遍地,當我與女孩調整她們設定目標的方式時,我會給那些擁有偉大夢想,追求高成就的學生一個建議:降低妳的標準。她們每次都會笑,但我很認真,而她們也很快地就發現這是多麼有效。
我使用一個小技巧:在她們選擇去冒一個較小的風險後,我會問她們對它的看法。如果她們翻白眼,嘀咕著這個挑戰幾乎不算什麼,或是說這「感覺起來很蠢」,那就對了!她們找到了一個合適的目標,而且她們準備採取行動。
Chapter 5 妳不是往壞處想,就是想太多
──「心理跑步機」讓妳焦慮和轉不停的腦袋疲累不堪
「我是那種,當我上床睡覺時,會重新回顧我在白天說的每句話,然後對超過一半的話責怪自己的人。」──哈珀,十六歲
◆負面思考推著妳前進:防禦性悲觀
在考試前與一群女孩坐在一起,妳會聽到各種各樣的聲音此起彼落地預測最壞的情況:
「我一定會考不及格。」
「這會毀了我的學業成績平均點數。」
「我永遠畢不了業。」
心理學家稱之為「防禦性悲觀」(Defensive Pessimism),或「計畫失敗」。它運作的原理是這樣的:當你在面對挑戰時,預先設想一個負面的結果。如果事情如你所願,你會感到驚喜;如果沒有,那麼你也為失望的結果做好了心理準備。這與準備「緊急避難包」是一樣的心理,是你為了以防萬一而做的準備。
「我一直告訴自己最壞的情況就是那樣,所以即使我做得不那麼好,我的感覺會好一點。」十六歲的阿維莎告訴我。摩根是一位二十二歲的大學畢業生,她對我描述她在申請工作時按下「發送」按鈕的心情。「我說,『好吧,有這麼多人申請,大多數的人都比妳更有資格,而妳只做了這個和那個,所以妳不會得到這份工作。』」「妳參加考試,然後對自己說,『我會失敗,這堂課我不會過』」,二十一歲的米菲比說,「或是『我可能必須採用不會顯示分數的通過/不通過的選項』,或『我畢不了業或找不到工作。我必須讓自己準備好面對失敗。』」她補充說,預期被拒絕,讓她能提前對任何可能發生的痛苦感到麻木。
威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的朱莉.諾瑞姆(Julie Norem)教授在研究中發現,約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會運用「防禦性悲觀」,主要為了排解焦慮的情緒,而防禦性悲觀者在工作上的表現往往更有效率。十六歲的哈珀說得更簡潔:「負面觀點推動我前進。」換句話說,這不一定是壞事。
然而,每當我聽到女孩大聲宣布她們會失敗得多慘,我都對這個說法抱持懷疑的態度。「防禦性悲觀」意味著你將負能量邀請進你的生活中,這樣你才能應付挑戰。心理學家認為這是一種管理焦慮的有效方式;但研究證明,防禦性悲觀者經常對自己產生負面的想法。緊接在「我將會失敗」之後的是「我可能沒那麼聰明」,或是「如果我失敗了,沒有進入我想就讀的學校,讓我的父母失望怎麼辦?」
這種消極的思維模式降低一個人的自尊心,並提高發生抑鬱症狀的機率。低落的自尊心可能會使一個女孩更加倍努力──也許她還會把它當作一種自我懲罰。所以她努力了、成功了,並快速提高了她的自尊心;但如果她預測自己會失敗,那麼,她就會因為對自己的缺失做出正確判斷,而獲得小小的勝利。她會告訴自己,「我不是說過了嗎?」當下一個挑戰來臨時,這個循環又重新開始──就像你每天洗澡往身上抹肥皂又沖掉一般,日復一日。
這是我們希望女孩學習的方式嗎?是基於對失敗的恐懼而不是對成功的希望所驅動?思考她們不想要什麼,而不是對她們想要的懷抱更大的夢想?研究顯示,被「逃避表現目標」──避免比別人表現更差的渴望──激勵的人,更有可能努力實現目標。他們不太會有內在動力,比起學習並享受它,他們更擔心形象受損。二〇〇三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大學女生明顯比男生更擔心表現得比別人差。由於多種原因,女孩更容易有「防禦性悲觀」。女孩將失敗看得特別重,並將失敗解釋為自己缺乏能力的標誌──她們實際上感受到的焦慮比男孩嚴重得多。當女孩比男孩成功時,她會貶低自己的才能,這表示成功並不能使她們變得更有自信(對男孩來說,成功則會讓他們變得更有自信)。如果女孩感覺自己面臨失敗的威脅越來越大,她們更可能採取自我保護的立場,而不是侵略性──我做得到──的態度。
我們不要忘記,女孩的世界喜歡防禦性悲觀者。她們預想最糟的結果,是在實踐社會認可的謙虛。「我把那個考試考砸了」也是女孩在說「我不是那麼聰明、成功、精通」的代名詞。女孩的謙卑,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同儕朋友和成年人的獎勵。
女孩關於「我很醜-不-我最醜」的對話,是很接近「防禦性悲觀」的表現。一個女孩大聲地表達她擔心自己的職業夢想不會成真,她的朋友會安慰她:「妳在開玩笑吧,我相信妳一定沒問題,我表現得比妳差多了!」兩個女孩都獲得同儕的認可和壓力釋放。她們可以透過將自己的恐懼外放來停止再想它。因為她們通過了女孩世界的「謙虛測試」,她們彼此馬上會更喜歡對方。
「這是種扭曲的社群感,」十七歲的喬安娜告訴我,「知道妳並不孤單,令人感到放心。妳們一起完成了所有事情,也一起做好了準備,並一起經歷了這一切,之後它很自然地變成共享失敗的同溫層。」
但是,當你深入一點探究,你會看到表面下潛藏著不那麼具有姐妹情誼的東西。隨著女孩分享她們的恐懼,競爭的種子也開始萌芽。「妳拿自己與其他人做比較,」喬安娜說:
即使當妳聽到別人說「我搞砸了」,妳會說些讓她們放心的話,但妳可能在心裡面會說,「哦,她把這個搞砸了,但我沒有。」這讓我站在更高的位置上。有一點點像是……貶低別人來抬高自己。
女孩悄悄地從盟友變成競爭對手。一直在說她們的缺點,會讓女孩感到自己不夠好和有所缺乏。這是一個「比較」的有害配方。為了真正感到放心,她們可能需要知道另一個人已經失敗了。如同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說過的,「成功還不夠,其他人必須失敗。」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這種行為會成為一種習慣,讓女孩每次面臨未知且結果可能會令人失望的挑戰時,都傾向於依賴這種心態。如果女孩不是真的期待會成功,她們如何對新的可能性保持完全開放的心態?「防禦性悲觀」可能會讓女孩感覺更好、更確定,但它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好奇心和成長的可能。這不是對她們成功機會所進行的深思熟慮,只是用「反正我可能會失敗」來面對每一個重大問題。它也可能會影響信心;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當女性低估自己的能力時,她們不太可能冒險並探索新的機會。
女孩在學習成長上能感受到的喜悅很少,尤其是表現最好的人。太多人似乎認為苦難等於成功。如果它沒有傷害你、嚇唬你、給你關於失敗的噩夢,或是讓你壓力大到瀕臨極限,你一定是不夠努力,這樣你也不配成功。
「防禦性悲觀」是這種痛苦次文化的一部分。這是一種大幅減低焦慮並將謙卑最大化的工具,但它犧牲的卻是女孩的勇氣。畢竟,女孩無法在面對風險時,透過快速拉上她們思想和靈魂的窗戶,並祈禱免於遭受甚至還沒發生的失敗,來變得更強大。不,當她們能確實地思考失敗可能意味著什麼和看起來是什麼樣子,而不是轉向她們想像中那些不真實的災難畫面,她們才會變得更強大。
幫助女孩不僅想像挫折,也想像她們對挫折的反應,會是取代防禦性悲觀並增加其信心的方法。幾十年來,運動心理學家透過在競賽前將賽事具象化的方法來培養菁英運動員。運動員對賽事進行「意象」(Imaging)是一種訓練工具,讓參賽者在不可預測的情況發生前,制定應對策略。
如果你的女兒擔心可能被拒絕,無論是工作上或在學校裡,和她一起討論聽到「不」的感受。她想像自己會有什麼感受?她會想到什麼?她在接到被拒絕的消息後,如何關照自己?她接下來還能做什麼來推動自己前進?
現在和她一起想像,她在聽到「是」的時候會有什麼感受。她會感覺什麼和想到什麼?為什麼這個勝利對她來說是重要的?她會如何慶祝?擁有這兩種情境將有助於提醒她,為什麼她起初會關心這件事(或者,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不關心)。這可以幫助她記得,對於如何處理發生在她身上的事,她是有所選擇的,同時你也可以向她保證,無論如何,你都會在身邊支持她。在我開始教導女孩有關「防禦性悲觀」之前,預期最壞的情況也是我的祕密策略,而我從未對它多做思考。然後,我開始在學生的話語裡聽到自己。聽著這些聰明勤奮、未來正在等著她們的女孩告訴我,她們將會輸得多慘,給我帶來很大的刺激──它讓我很生氣。
我開始面對自己的壞習慣。每隔幾個月的時間,我會向《紐約時報》提交一份社論。每次我按下「發送」按鈕時,我會對自己竊竊私語:「他們會拒絕它。」 我確實被拒絕過:一次、兩次、三次、四次。當然,它令人失望。然後,有件奇怪的事發生了。有個影像突然進入我的腦海中:影像中的人是我,手上拿著《紐約時報》,並看到我的名字印在上面。
想像成功對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經驗。但是,我已經被拒絕了很多次,因此聽到「不」的經驗,對我而言已經不再陌生──我不僅知道它,還知道它不會把我殺了。
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我揭露了「奧茲大帝」(Great and Powerful Oz)的真面目(我要聲明,我以此比喻「失敗」,而不是《紐約時報》),並且發現「失敗」就如同電影中的奧斯卡,不是奧茲王國預言中的奧茲大帝,而只是一個在馬戲團耍小手段的騙子魔術師。
練習面對「失敗」、「不」、「拒絕」、「失望」的心態:這是放棄「防禦性悲觀」心態的關鍵。一旦我害怕失敗的感覺消退,我就沒有什麼理由需要保護自己;我可以更專注於冒險帶來的樂趣,而不是建立認知障礙來保護自己免受風險。
讓我再說一遍:我可以真的享受自己在做的事。我可以抓住機會,享受樂趣,並從挑戰中學習。
如果你是個防禦性悲觀者,你可能已經向女兒傳達過一些類似的觀念。我們很容易幫孩子和學生寫好面對風險的劇本,正如一位大學生告訴研究人員:「我的父母總是說,『不要將目標設得太高,因為妳只會感到失望。』……他們總是小心地不想提高我的希望,這樣我就不會感到失望。」在與女兒談她的習慣之前,花一些時間反思自己的習慣。諾瑞姆設計了一份調查問卷,目的就在於衡量「防禦性悲觀」。其中的問題包括:儘管我應該會做得很好,但我經常在一開始就預期最壞的情況。
我花了很多時間想像可能會出現什麼問題。
我會在這些情況下,小心不要變得過度自信。
在這些情況下,有時我更擔心自己看起來會不會像個傻瓜,而不是擔心是否做得好。
考量可能出錯的情況,有助於我做好準備。
我們大多數的人不會為了打擊孩子,告訴他去預期最壞的情況。我們在建議女孩不要對目標感到太興奮時,我們認為自己是在保護她們。但是,我可以確定地說,社會已經在那個部分做很多了,女孩需要從父母那裡得到的是,幫助她們設想從失敗中恢復和成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