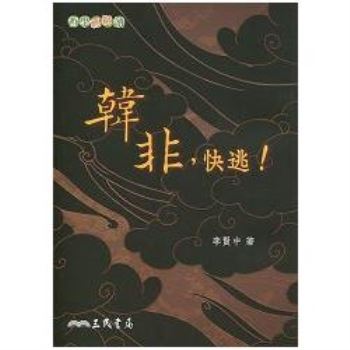壹、韓非,快逃!
一、韓非生平
韓非,滿腔的抱負與理想,可惜懷才不遇、不被韓王所重用。他年輕的時候,曾經到齊國稷下學宮,拜荀子為師。荀子是儒家的大儒,他當時的地位就相當於現在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在齊國稷下學宮,各國的知識份子都齊聚到他這個地方來,成百上千人在那個地方研究學問與治國方略。韓非的師兄李斯,比韓非早到稷下向荀子學習。
李斯在他家鄉楚國上蔡,做個當差的,在他工作場所附近的廁所中,他觀察到一些老鼠吃著骯髒的東西,當人或狗經過的時候就嚇得躲起來,又瘦又乾。可是李斯經過米倉時他發現到,倉庫裡面的老鼠,又肥又壯;在大倉庫中也沒有人或狗的騷擾。他看到這些景象之後,想想自己的處境,不禁悲從中來;他想到自己不就像廁所裡的那些老鼠嗎,又瘦又乾、又窮又困,只能做一個小小公務員……後來沒多久,他就下定決心,跑回家告別他的老母與妻小,一個人直奔到齊國稷下,拜荀子為師。
經過了一段時間,有這麼一天,李斯突然間聽到馬蹄聲,由遠而近,他遠眺窗外,見到一位翩翩美少年,那少年身穿白色的貴族服飾,騎乘於白馬上,由一個馬僮牽引著緩緩走進學宮大門。沒想到學宮的祭酒荀子,居然還到門口去迎接他。李斯的心裡很不是滋味,心想「是什麼人物,居然連我們老師都親自到門口來迎接他?」李斯心中正嘀咕著,只見那白馬少年優雅地下了馬,向荀子打躬作揖說道:「拜拜拜……拜拜拜,拜見老師。」哎呀,這個時候,李斯心裡一陣舒坦,他不再那麼嫉妒那白馬少年了,因為「原來他不過是一個口吃、結巴的小子罷了。」李斯暗暗譏笑著。
沒錯,來者正是韓非,他的確是一個結巴的人,言談口吃,講話講得不太清楚,可是他文章寫得很好,是很有思想的一個韓國貴族公子,他見韓國積弱不振,聽聞荀子在齊國收徒授課,於是他不辭路途遙遠,到齊國來拜在荀子的門下,向荀子學習經世治國的大學問,當然,也就與李斯成了同門師兄弟,同窗數載。
匆匆幾年過去,李斯學成之後離開了齊國,輾轉任職於秦國,受到秦王的重用,就在那兒平步青雲,升上高官;而韓非呢,學成了之後,回到自己的國家不斷地上書韓王,苦心勸韓王要怎麼樣厲精圖治,怎麼樣才能讓韓國富強起來,但上書始終石沉大海,未受重視。韓國,在春秋時代,原來不過是晉國的一部分,後來三家分晉,從晉國分出了韓、趙、魏三個國家,只有在申不害做韓國宰相的十幾年之間,韓國國勢穩定,之後則始終受到大國的威脅。因那韓國正好是處在秦國、楚國、魏國等列強間的一個小國,安危堪虞,所以韓非就常常上書韓王,指出國君如果無法識人用才,國家必定亂亡。在《韓非子‧顯學》篇中,韓非列舉了韓國一些與法治理念相悖的現象,他說:「假定一國的君主,他所欣賞的是那種堅決不進入危險地區,不參軍打仗,不願拿天下的大利來換自己小腿上的一根毫毛;看重這種人的見識,讚揚這種人的行為,並且認為他們是輕視財物、愛惜生命的高人,值得尊重。可是,在法治賞罰的標準下,君主所以把良田和豪宅拿出來作為賞賜,又設置官爵和俸祿,為的就是希望民眾為國家去拼死效命;現在君主既然尊重那些輕視財物、愛惜生命的人,再想要求民眾出生入死,為國事作出犧牲,那就根本不可能了。」
韓非繼續闡述,另一種常被君主欣賞的人是:「收藏書冊,講究辯說,聚徒講學,從事文章學術事業,又喜高談闊論的人,君主認為這些遊說之人是賢士。然而,官吏們徵稅的對象是種田的人,而君主供養的卻是那些著書立說的學士。如此,對於種田的人徵收重稅,對於學士卻給予厚賞;這樣,再想督責民眾努力耕作而少說空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還有君主欣賞一種講求氣節的人,「他們一副堅持操守而不容侵犯的樣子,自以為高明,聽到別人對他的批評,立刻拔劍而起;君主卻禮遇這樣的人,以為這是愛惜自我的表現。然而,對那些在戰場勇敢殺敵立功的人卻不予獎賞,對那些逞凶鬥狠、喜報私仇的人,反要使他們尊貴;這樣要想求得民眾奮勇殺敵而不去私鬥,根本也是不可能的。國君如果在國家太平時供養儒生和俠客,等到國家危難到來時,卻需要用戰士來打仗。由於所供養的人卻不是真正要用的人,真正需要使用的人卻又不是平日所供養的人,這就是國家發生禍亂的原因。」
韓非指出韓王所用的那些人是「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根本沒有辦法在國家危急的時候,來幫忙解決問題。
可是呢,韓王根本就不理會韓非這個家室沒落的貴族與他的上書,韓非有志難伸,只好拼命寫書,寫出了〈孤憤〉、〈五蠹〉、〈說難〉、〈難勢〉、〈姦劫弒臣〉等這些文章,探討君臣的關係,以及怎麼樣來治理國家,才能使國家富強;指出國家的衰弱、混亂、敗亡,又是由哪些因素所造成。
這些文章寫成之後,輾轉流傳到秦王的手中,秦王一看,愛不釋手。秦王嬴政曾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他到處找這些文章的作者,想當面向他討教富國強兵之道。他說:「我如果能夠見到此人,就算我死了都沒有遺憾。」
李斯知道了此事,趕緊稟告秦王,他說:「這是我的同學韓非,他現在人在韓國。」
「是韓非嘛!好啊,你把這個人給我找來。」這個時候,秦國強盛,秦王他想要統一六國,正準備要發兵。「好,那我們就先打韓國,讓我見見韓非這個人。」秦王順勢下令。
韓王聽到消息,迫於無奈,趕快召韓非進宮,「現在國家就要亡了,我派你出使秦國,千萬要把我們國家保住,韓國的安危就靠你了。」
這時,韓非終於有機會受韓王重用,出使秦國,可是他的命運實在是不好,到了秦國,禮貌上與秦王匆匆見過一面,但卻沒有機會好好和秦王深談。就被安排住進秦國的雲陽宮候命。此時,李斯開始憂慮韓非的才幹為秦王所欣賞,進而取代他在秦王心目中的地位,於是就不斷地在秦王面前講韓非的壞話,他說:「韓非是韓國人,他畢竟還是為他自己的國家著想,絕不可能為我們秦國效力,所以即使您今天重用他,他也不可能為我們秦國牟利;若不用他,將來讓他回去韓國,那豈不是縱虎歸山,他反而會是我們一統天下的阻礙,不如找個藉口把他給殺了吧。」當時秦國大臣姚賈,也隨聲應和,他們兩個互相勾結,積極遊說秦王,後來,秦王真被他們說動了。
「好吧,那就以間諜之罪,賜韓非一死。」李斯接到命令之後,馬上就拿毒藥到雲陽宮給韓非,要韓非速速自我了斷。李斯走進軟禁韓非的雲陽宮中,正欲開口,韓非有點興奮,結結巴巴地說:「你……來……接……我見……秦王嗎?」
李斯:「當年我們一起在老師門下治學的時候,我就曾經想過可能會有今天。如今,你看看這天下,各國擁兵自重,若無你我來運籌帷幄,他們不過是一群螻蟻、草芥,沒有任何作用。」
韓非:「聲……東擊西,遠……交近攻,你……的策論一向學得……很……好。」
李斯:「你是我的同門,應明白這天下之道,一山不容二虎。」
韓非:「所……以,你……要……我消失?」韓非已看出李斯的意圖。
李斯奸笑著說:「你我算是同門,輸在師兄的謀略之下,並不可恥。」
韓非:「以……前我……太相信你,現……在我……誰都不再相信,老……師曾說過我……們這些人是……為戰……爭而生的,有時我……也會問,如果沒了戰……爭,我們的存……在又有……何意義?我……只希望你……看在我……們曾經同……門的份上,最……後再讓……我見一……次嬴……政就好。」
李斯臉色浮現一股肅殺之氣:「你才說不再相信任何人,現在就算我答應你,你想你見得到嗎?」
韓非絕望地搖搖頭說:「六尺黃土之下,我看你又能活多久。」說完狂笑幾聲,拿起李斯帶來的毒酒,一飲而盡,結束了他這充滿抱負與遺憾的一生。
其實,後來秦王反悔,想要免除韓非死刑,再見他一面,但卻已經來不及了。韓非生於西元前二八○年,於秦王政十四年,西元前二三三年過世。韓非的一生,就是在這樣一種很無奈的情況之下結束。
他所留下來的文章,集結成冊,稱《韓非子》,共有五十五篇。其中有:〈孤憤〉、〈五蠹〉兩篇是秦始皇親自閱讀過的文章,〈孤憤〉篇論及君主如何受到大臣的蒙蔽,敗壞法紀,當權大臣又為何仇視像韓非一樣的法術之士,法術之士孤掌難鳴,眼見國家危難,心急如焚,與權臣競爭又不能取勝、不被重用,充滿有志難伸的憤慨。〈五蠹〉篇談的是五種傷害國家的人,像木頭裡的蠹蟲一般,包括:儒者、縱橫家或說客、帶劍的遊俠、君主寵信的近臣以及商工之民。二、韓非與荀子談人性
話說韓非在稷下向荀子學習,三年後的某一天,師徒二人走在河邊,柳絮紛飛;遠處麥田人車走動,正忙著收成。
荀子緩緩說道:「人的本性為惡,社會之所以會有良善的行為,乃是依靠後天教育去改變氣質;今日所呈現的人性,生來就有好利之心,順其心發展,人與人之間相互爭奪,哪裡會有辭讓之禮?生來就有嫉恨嫌惡之心,順其心發展,殘忍賊害他人的行為層出不窮,哪裡還有忠貞信實的品格?人一生下來就有耳目感官的欲望,喜好美色、淫聲,順其心發展,荒淫暴亂就不可避免,哪裡還有禮義文化可言?因此,若從人之心性,順人之情欲,必然會有爭奪,觸犯理分,而使社會秩序紊亂;因此,必須透過後天禮義、師長的教化,才能使人有辭讓的行為,合乎社會的規範,導引人心為善。」
韓非說:「老師說得極是,但禮義、師法如何導人為善?如果人人自私自利,禮義、師法又有何吸引力,使人願意學習?人的內心又如何可能接受禮義師法的教育?」
荀子說:「人是可以被環境影響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就算是平民百姓,走在路上的每一個人,就其潛能而言,都可能成為像禹一般的聖人。」
韓非說:「弟子以為放眼今日天下,影響人的大環境中,充滿著人人競逐名利的風氣,就像田裡工作的工人,他們不過是為了希望雇主多給一點工錢,才在那裡賣力工作,若是沒有錢拿,無利可圖,又有誰會願意賣力工作呢?又像那雇主,準備了豐盛的點心給那些工人享用,看起來主奴之間好像父子一般親熱,其實雇主打的如意算盤是希望工人認真工作,快點將麥子收完好賣錢,其實還是為著自己的利益。」
荀子說:「雖然好利是人的本性,滿足人自己的欲望也是人的本能,不過,人的心還是有選擇的能力。」
韓非問:「人心有什麼能力呢?」
荀子答:「人心有自主的能力。你可以將一個人的手腳綁起來不讓他動,把他的口捂起來,不讓他說話,但是你卻無法改變他的意念、心志。」
韓非問:「心志如何選定它所要追求的方向呢?」
荀子說:「心志可以認識世界上的事物,透過不同經驗的比較,而選擇對自己長期有利的事去做。」
韓非繼續問:「什麼是不同經驗呢?」
荀子回答:「就是在不同時間、不同階段、管理人民、統治國家的成效經驗相比較啊!你說說看,是一個沒有秩序的社會對大家有利,還是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對大家有利呢?」韓非回答:「當然是有秩序的社會比較有利啊!」
荀子說:「沒錯,古代聖人就是透過這樣的認知與比較,而制定了禮義制度來施行教化,讓百姓獲得最大的利益,因此,好利的人民必須接受禮義、師法的教育,化性起偽;也就是轉化他們原本的惡性,透過後天的禮義、師法來改造本性,這就是人為的導惡為善。」
韓非問:「聖人的心如何認知?一般老百姓又為何認知不到?如果百姓人人短視近利,根本無法瞭解聖人制禮作樂的用心,以致禮義的教育效果不彰,那又該如何是好呢?」
荀子說:「聖人的心能夠虛壹而靜。」
韓非問:「何謂虛?」
荀子回答:「虛,就是不以所藏害所將受。也就是原有的知識不會佔滿人的內心,心總可容受新的知識。」
韓非問:「何謂壹?」
荀子回答:「人的內心中容受了不同的知識,但不會因為先前的知識干擾了後學的知識;心可以專注於其壹,不受影響。」
韓非又問:「何謂靜?」
荀子回答:「人心浮動,受外物幻夢影響,但它有能力安靜篤定。」
韓非問:「老師所說的虛壹而靜,固然有其道理,但一般老百姓卻不容易做到,僅有極少數的聖人可能,並且內心修養人人各異,虛玄而無益於治。我認為根本不必探究心性的內涵、作用,只要從絕大多數人那種趨利避害的傾向,予以對治即可。既然人人好利,因此賞罰可用,禮義已經過時,根本無法發揮管理上的功效,因此弟子主張:應該要採取嚴刑峻罰,以更具權威與效率的法律來治國,在重賞重罰之下,建立信賞必罰之威;如此才能富國強兵,完成一統天下的霸業。」
荀子聽到此,長歎一口氣,對著韓非說:「嚴刑峻罰,治標不治本,非長治久安之計;你既有這種想法,就算天下有你容身之處,也會危機四伏,你還是自求多福吧!」
韓非悵悵然,不久之後,他拜別了老師,返回韓國。三、韓非評慎到、儒者,論任賢與任勢
在韓非時代之前,有主張尚賢的儒者,質疑慎到強調權勢的說法。慎到是趙國邯鄲人,年代約稍晚於孟子,為戰國中期的思想家,齊宣王時曾在齊國稷下學宮講學,頗負盛名。《莊子•天下》篇把他與田駢同歸一派,後成為從道家分化出來的法家,主張「尚法」和「重勢」。
在稷下學宮所舉辦的一場早期論辯大會中,慎到說:「飛龍騰雲而行,遊蛇駕霧而動,然而一旦雲開霧散,牠們就跟蚯蚓、螞蟻一樣了,因為牠們失去了騰雲駕霧飛行的憑藉。賢人之所以屈服於不肖的人,是因為賢人權力小、地位低。不肖的人之所以能被賢人制服,是因為賢人的權力大、地位高。可見治理的成效,其關鍵在於勢位權力的大小,而不在於治理者個人的道德操守如何。」
接著,慎到舉例說:「古代聖王堯如果是一個平民,就算只有三個人,他也管不住;要是古代暴王桀作為天子,卻能搞得天下大亂。由此得知,管理國家要靠權勢,而不是靠那些有道德或有智慧的人。射箭時,弓弩力弱而箭頭卻飛得很高,這是因為有風力的推動;管理者本身雖然未必有賢德,但是他的命令卻得以推行,這是因為得到了眾人的幫助,大家都認可他的權力。堯若非天子,他在平民百姓中施行教化,平民百姓不會聽他的;等他南面稱王統治天下的時候,就能令出必行,有禁必止。由此看來,賢德智能並不足以制服民眾,而勢位卻可以使賢人屈服的。」
此時,主張尚賢的儒者反問慎到,說:「龍飛在天,蛇騰林間,我們並不認為龍蛇不需要依託雲霧這種外在的勢力。雖然如此,但捨棄賢才而專靠外在權勢,難道就可以治理好國家嗎?不見得如此吧。有了雲霧的依託,就能騰雲駕霧飛行,是因為龍、蛇天生資質好;現在同樣是濃厚的雲層,蚯蚓並不能騰雲而上,同樣是濃厚的霧氣,螞蟻並不能依附而飄起。雖有厚雲濃霧的依託,而不能騰雲駕霧飛行,是因為蚯蚓、螞蟻天生資質低下,無法掌握、運用這些外在的勢力。」
儒者進一步分析歷史上朝代興亡的道理:「夏桀、商紂南面稱王統治天下時,他們把天子的權勢像龍蛇以雲霧作為依託一般,而天下仍然不免於大亂,正說明夏桀、商紂的資質低下,不懂得如何善用權勢。再說,慎到認為堯憑權勢來治理天下,而堯的權勢和桀的權勢沒有什麼不同,結果桀的治理卻導致天下大亂。權勢這東西是被動的,既不能讓賢人用它,也不能讓不肖的人不用它。賢人用它天下就太平,不肖的人用它天下就混亂。按人的本性來看,賢能的人少而不肖的人多,如果威勢的作用常被多數不肖的人利用,那權勢就變成擾亂天下的亂因,而權勢被賢能者運用而治理好天下的情況就少了。權勢這東西,既便於治理天下,也可能會擾亂天下。所以《周書》上說:『不要給老虎添上翅膀,否則牠將飛進城邑,任意吃人。』統治者就像那老虎,要是讓不肖的人憑藉權勢,這好比給老虎添上了翅膀。夏桀、商紂造高臺、挖深池來耗盡民力,用炮格的酷刑來傷害民眾的生命。桀、紂能夠胡作非為,是因為天子的威勢成了他們的翅膀。假使桀、紂只是普通的人,他敢開始幹一件壞事,就遭受刑罰了。可見權勢是滋長虎狼之心、造成暴亂事件的東西,也就是天下的大禍害。」
一、韓非生平
韓非,滿腔的抱負與理想,可惜懷才不遇、不被韓王所重用。他年輕的時候,曾經到齊國稷下學宮,拜荀子為師。荀子是儒家的大儒,他當時的地位就相當於現在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在齊國稷下學宮,各國的知識份子都齊聚到他這個地方來,成百上千人在那個地方研究學問與治國方略。韓非的師兄李斯,比韓非早到稷下向荀子學習。
李斯在他家鄉楚國上蔡,做個當差的,在他工作場所附近的廁所中,他觀察到一些老鼠吃著骯髒的東西,當人或狗經過的時候就嚇得躲起來,又瘦又乾。可是李斯經過米倉時他發現到,倉庫裡面的老鼠,又肥又壯;在大倉庫中也沒有人或狗的騷擾。他看到這些景象之後,想想自己的處境,不禁悲從中來;他想到自己不就像廁所裡的那些老鼠嗎,又瘦又乾、又窮又困,只能做一個小小公務員……後來沒多久,他就下定決心,跑回家告別他的老母與妻小,一個人直奔到齊國稷下,拜荀子為師。
經過了一段時間,有這麼一天,李斯突然間聽到馬蹄聲,由遠而近,他遠眺窗外,見到一位翩翩美少年,那少年身穿白色的貴族服飾,騎乘於白馬上,由一個馬僮牽引著緩緩走進學宮大門。沒想到學宮的祭酒荀子,居然還到門口去迎接他。李斯的心裡很不是滋味,心想「是什麼人物,居然連我們老師都親自到門口來迎接他?」李斯心中正嘀咕著,只見那白馬少年優雅地下了馬,向荀子打躬作揖說道:「拜拜拜……拜拜拜,拜見老師。」哎呀,這個時候,李斯心裡一陣舒坦,他不再那麼嫉妒那白馬少年了,因為「原來他不過是一個口吃、結巴的小子罷了。」李斯暗暗譏笑著。
沒錯,來者正是韓非,他的確是一個結巴的人,言談口吃,講話講得不太清楚,可是他文章寫得很好,是很有思想的一個韓國貴族公子,他見韓國積弱不振,聽聞荀子在齊國收徒授課,於是他不辭路途遙遠,到齊國來拜在荀子的門下,向荀子學習經世治國的大學問,當然,也就與李斯成了同門師兄弟,同窗數載。
匆匆幾年過去,李斯學成之後離開了齊國,輾轉任職於秦國,受到秦王的重用,就在那兒平步青雲,升上高官;而韓非呢,學成了之後,回到自己的國家不斷地上書韓王,苦心勸韓王要怎麼樣厲精圖治,怎麼樣才能讓韓國富強起來,但上書始終石沉大海,未受重視。韓國,在春秋時代,原來不過是晉國的一部分,後來三家分晉,從晉國分出了韓、趙、魏三個國家,只有在申不害做韓國宰相的十幾年之間,韓國國勢穩定,之後則始終受到大國的威脅。因那韓國正好是處在秦國、楚國、魏國等列強間的一個小國,安危堪虞,所以韓非就常常上書韓王,指出國君如果無法識人用才,國家必定亂亡。在《韓非子‧顯學》篇中,韓非列舉了韓國一些與法治理念相悖的現象,他說:「假定一國的君主,他所欣賞的是那種堅決不進入危險地區,不參軍打仗,不願拿天下的大利來換自己小腿上的一根毫毛;看重這種人的見識,讚揚這種人的行為,並且認為他們是輕視財物、愛惜生命的高人,值得尊重。可是,在法治賞罰的標準下,君主所以把良田和豪宅拿出來作為賞賜,又設置官爵和俸祿,為的就是希望民眾為國家去拼死效命;現在君主既然尊重那些輕視財物、愛惜生命的人,再想要求民眾出生入死,為國事作出犧牲,那就根本不可能了。」
韓非繼續闡述,另一種常被君主欣賞的人是:「收藏書冊,講究辯說,聚徒講學,從事文章學術事業,又喜高談闊論的人,君主認為這些遊說之人是賢士。然而,官吏們徵稅的對象是種田的人,而君主供養的卻是那些著書立說的學士。如此,對於種田的人徵收重稅,對於學士卻給予厚賞;這樣,再想督責民眾努力耕作而少說空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還有君主欣賞一種講求氣節的人,「他們一副堅持操守而不容侵犯的樣子,自以為高明,聽到別人對他的批評,立刻拔劍而起;君主卻禮遇這樣的人,以為這是愛惜自我的表現。然而,對那些在戰場勇敢殺敵立功的人卻不予獎賞,對那些逞凶鬥狠、喜報私仇的人,反要使他們尊貴;這樣要想求得民眾奮勇殺敵而不去私鬥,根本也是不可能的。國君如果在國家太平時供養儒生和俠客,等到國家危難到來時,卻需要用戰士來打仗。由於所供養的人卻不是真正要用的人,真正需要使用的人卻又不是平日所供養的人,這就是國家發生禍亂的原因。」
韓非指出韓王所用的那些人是「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根本沒有辦法在國家危急的時候,來幫忙解決問題。
可是呢,韓王根本就不理會韓非這個家室沒落的貴族與他的上書,韓非有志難伸,只好拼命寫書,寫出了〈孤憤〉、〈五蠹〉、〈說難〉、〈難勢〉、〈姦劫弒臣〉等這些文章,探討君臣的關係,以及怎麼樣來治理國家,才能使國家富強;指出國家的衰弱、混亂、敗亡,又是由哪些因素所造成。
這些文章寫成之後,輾轉流傳到秦王的手中,秦王一看,愛不釋手。秦王嬴政曾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他到處找這些文章的作者,想當面向他討教富國強兵之道。他說:「我如果能夠見到此人,就算我死了都沒有遺憾。」
李斯知道了此事,趕緊稟告秦王,他說:「這是我的同學韓非,他現在人在韓國。」
「是韓非嘛!好啊,你把這個人給我找來。」這個時候,秦國強盛,秦王他想要統一六國,正準備要發兵。「好,那我們就先打韓國,讓我見見韓非這個人。」秦王順勢下令。
韓王聽到消息,迫於無奈,趕快召韓非進宮,「現在國家就要亡了,我派你出使秦國,千萬要把我們國家保住,韓國的安危就靠你了。」
這時,韓非終於有機會受韓王重用,出使秦國,可是他的命運實在是不好,到了秦國,禮貌上與秦王匆匆見過一面,但卻沒有機會好好和秦王深談。就被安排住進秦國的雲陽宮候命。此時,李斯開始憂慮韓非的才幹為秦王所欣賞,進而取代他在秦王心目中的地位,於是就不斷地在秦王面前講韓非的壞話,他說:「韓非是韓國人,他畢竟還是為他自己的國家著想,絕不可能為我們秦國效力,所以即使您今天重用他,他也不可能為我們秦國牟利;若不用他,將來讓他回去韓國,那豈不是縱虎歸山,他反而會是我們一統天下的阻礙,不如找個藉口把他給殺了吧。」當時秦國大臣姚賈,也隨聲應和,他們兩個互相勾結,積極遊說秦王,後來,秦王真被他們說動了。
「好吧,那就以間諜之罪,賜韓非一死。」李斯接到命令之後,馬上就拿毒藥到雲陽宮給韓非,要韓非速速自我了斷。李斯走進軟禁韓非的雲陽宮中,正欲開口,韓非有點興奮,結結巴巴地說:「你……來……接……我見……秦王嗎?」
李斯:「當年我們一起在老師門下治學的時候,我就曾經想過可能會有今天。如今,你看看這天下,各國擁兵自重,若無你我來運籌帷幄,他們不過是一群螻蟻、草芥,沒有任何作用。」
韓非:「聲……東擊西,遠……交近攻,你……的策論一向學得……很……好。」
李斯:「你是我的同門,應明白這天下之道,一山不容二虎。」
韓非:「所……以,你……要……我消失?」韓非已看出李斯的意圖。
李斯奸笑著說:「你我算是同門,輸在師兄的謀略之下,並不可恥。」
韓非:「以……前我……太相信你,現……在我……誰都不再相信,老……師曾說過我……們這些人是……為戰……爭而生的,有時我……也會問,如果沒了戰……爭,我們的存……在又有……何意義?我……只希望你……看在我……們曾經同……門的份上,最……後再讓……我見一……次嬴……政就好。」
李斯臉色浮現一股肅殺之氣:「你才說不再相信任何人,現在就算我答應你,你想你見得到嗎?」
韓非絕望地搖搖頭說:「六尺黃土之下,我看你又能活多久。」說完狂笑幾聲,拿起李斯帶來的毒酒,一飲而盡,結束了他這充滿抱負與遺憾的一生。
其實,後來秦王反悔,想要免除韓非死刑,再見他一面,但卻已經來不及了。韓非生於西元前二八○年,於秦王政十四年,西元前二三三年過世。韓非的一生,就是在這樣一種很無奈的情況之下結束。
他所留下來的文章,集結成冊,稱《韓非子》,共有五十五篇。其中有:〈孤憤〉、〈五蠹〉兩篇是秦始皇親自閱讀過的文章,〈孤憤〉篇論及君主如何受到大臣的蒙蔽,敗壞法紀,當權大臣又為何仇視像韓非一樣的法術之士,法術之士孤掌難鳴,眼見國家危難,心急如焚,與權臣競爭又不能取勝、不被重用,充滿有志難伸的憤慨。〈五蠹〉篇談的是五種傷害國家的人,像木頭裡的蠹蟲一般,包括:儒者、縱橫家或說客、帶劍的遊俠、君主寵信的近臣以及商工之民。二、韓非與荀子談人性
話說韓非在稷下向荀子學習,三年後的某一天,師徒二人走在河邊,柳絮紛飛;遠處麥田人車走動,正忙著收成。
荀子緩緩說道:「人的本性為惡,社會之所以會有良善的行為,乃是依靠後天教育去改變氣質;今日所呈現的人性,生來就有好利之心,順其心發展,人與人之間相互爭奪,哪裡會有辭讓之禮?生來就有嫉恨嫌惡之心,順其心發展,殘忍賊害他人的行為層出不窮,哪裡還有忠貞信實的品格?人一生下來就有耳目感官的欲望,喜好美色、淫聲,順其心發展,荒淫暴亂就不可避免,哪裡還有禮義文化可言?因此,若從人之心性,順人之情欲,必然會有爭奪,觸犯理分,而使社會秩序紊亂;因此,必須透過後天禮義、師長的教化,才能使人有辭讓的行為,合乎社會的規範,導引人心為善。」
韓非說:「老師說得極是,但禮義、師法如何導人為善?如果人人自私自利,禮義、師法又有何吸引力,使人願意學習?人的內心又如何可能接受禮義師法的教育?」
荀子說:「人是可以被環境影響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就算是平民百姓,走在路上的每一個人,就其潛能而言,都可能成為像禹一般的聖人。」
韓非說:「弟子以為放眼今日天下,影響人的大環境中,充滿著人人競逐名利的風氣,就像田裡工作的工人,他們不過是為了希望雇主多給一點工錢,才在那裡賣力工作,若是沒有錢拿,無利可圖,又有誰會願意賣力工作呢?又像那雇主,準備了豐盛的點心給那些工人享用,看起來主奴之間好像父子一般親熱,其實雇主打的如意算盤是希望工人認真工作,快點將麥子收完好賣錢,其實還是為著自己的利益。」
荀子說:「雖然好利是人的本性,滿足人自己的欲望也是人的本能,不過,人的心還是有選擇的能力。」
韓非問:「人心有什麼能力呢?」
荀子答:「人心有自主的能力。你可以將一個人的手腳綁起來不讓他動,把他的口捂起來,不讓他說話,但是你卻無法改變他的意念、心志。」
韓非問:「心志如何選定它所要追求的方向呢?」
荀子說:「心志可以認識世界上的事物,透過不同經驗的比較,而選擇對自己長期有利的事去做。」
韓非繼續問:「什麼是不同經驗呢?」
荀子回答:「就是在不同時間、不同階段、管理人民、統治國家的成效經驗相比較啊!你說說看,是一個沒有秩序的社會對大家有利,還是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對大家有利呢?」韓非回答:「當然是有秩序的社會比較有利啊!」
荀子說:「沒錯,古代聖人就是透過這樣的認知與比較,而制定了禮義制度來施行教化,讓百姓獲得最大的利益,因此,好利的人民必須接受禮義、師法的教育,化性起偽;也就是轉化他們原本的惡性,透過後天的禮義、師法來改造本性,這就是人為的導惡為善。」
韓非問:「聖人的心如何認知?一般老百姓又為何認知不到?如果百姓人人短視近利,根本無法瞭解聖人制禮作樂的用心,以致禮義的教育效果不彰,那又該如何是好呢?」
荀子說:「聖人的心能夠虛壹而靜。」
韓非問:「何謂虛?」
荀子回答:「虛,就是不以所藏害所將受。也就是原有的知識不會佔滿人的內心,心總可容受新的知識。」
韓非問:「何謂壹?」
荀子回答:「人的內心中容受了不同的知識,但不會因為先前的知識干擾了後學的知識;心可以專注於其壹,不受影響。」
韓非又問:「何謂靜?」
荀子回答:「人心浮動,受外物幻夢影響,但它有能力安靜篤定。」
韓非問:「老師所說的虛壹而靜,固然有其道理,但一般老百姓卻不容易做到,僅有極少數的聖人可能,並且內心修養人人各異,虛玄而無益於治。我認為根本不必探究心性的內涵、作用,只要從絕大多數人那種趨利避害的傾向,予以對治即可。既然人人好利,因此賞罰可用,禮義已經過時,根本無法發揮管理上的功效,因此弟子主張:應該要採取嚴刑峻罰,以更具權威與效率的法律來治國,在重賞重罰之下,建立信賞必罰之威;如此才能富國強兵,完成一統天下的霸業。」
荀子聽到此,長歎一口氣,對著韓非說:「嚴刑峻罰,治標不治本,非長治久安之計;你既有這種想法,就算天下有你容身之處,也會危機四伏,你還是自求多福吧!」
韓非悵悵然,不久之後,他拜別了老師,返回韓國。三、韓非評慎到、儒者,論任賢與任勢
在韓非時代之前,有主張尚賢的儒者,質疑慎到強調權勢的說法。慎到是趙國邯鄲人,年代約稍晚於孟子,為戰國中期的思想家,齊宣王時曾在齊國稷下學宮講學,頗負盛名。《莊子•天下》篇把他與田駢同歸一派,後成為從道家分化出來的法家,主張「尚法」和「重勢」。
在稷下學宮所舉辦的一場早期論辯大會中,慎到說:「飛龍騰雲而行,遊蛇駕霧而動,然而一旦雲開霧散,牠們就跟蚯蚓、螞蟻一樣了,因為牠們失去了騰雲駕霧飛行的憑藉。賢人之所以屈服於不肖的人,是因為賢人權力小、地位低。不肖的人之所以能被賢人制服,是因為賢人的權力大、地位高。可見治理的成效,其關鍵在於勢位權力的大小,而不在於治理者個人的道德操守如何。」
接著,慎到舉例說:「古代聖王堯如果是一個平民,就算只有三個人,他也管不住;要是古代暴王桀作為天子,卻能搞得天下大亂。由此得知,管理國家要靠權勢,而不是靠那些有道德或有智慧的人。射箭時,弓弩力弱而箭頭卻飛得很高,這是因為有風力的推動;管理者本身雖然未必有賢德,但是他的命令卻得以推行,這是因為得到了眾人的幫助,大家都認可他的權力。堯若非天子,他在平民百姓中施行教化,平民百姓不會聽他的;等他南面稱王統治天下的時候,就能令出必行,有禁必止。由此看來,賢德智能並不足以制服民眾,而勢位卻可以使賢人屈服的。」
此時,主張尚賢的儒者反問慎到,說:「龍飛在天,蛇騰林間,我們並不認為龍蛇不需要依託雲霧這種外在的勢力。雖然如此,但捨棄賢才而專靠外在權勢,難道就可以治理好國家嗎?不見得如此吧。有了雲霧的依託,就能騰雲駕霧飛行,是因為龍、蛇天生資質好;現在同樣是濃厚的雲層,蚯蚓並不能騰雲而上,同樣是濃厚的霧氣,螞蟻並不能依附而飄起。雖有厚雲濃霧的依託,而不能騰雲駕霧飛行,是因為蚯蚓、螞蟻天生資質低下,無法掌握、運用這些外在的勢力。」
儒者進一步分析歷史上朝代興亡的道理:「夏桀、商紂南面稱王統治天下時,他們把天子的權勢像龍蛇以雲霧作為依託一般,而天下仍然不免於大亂,正說明夏桀、商紂的資質低下,不懂得如何善用權勢。再說,慎到認為堯憑權勢來治理天下,而堯的權勢和桀的權勢沒有什麼不同,結果桀的治理卻導致天下大亂。權勢這東西是被動的,既不能讓賢人用它,也不能讓不肖的人不用它。賢人用它天下就太平,不肖的人用它天下就混亂。按人的本性來看,賢能的人少而不肖的人多,如果威勢的作用常被多數不肖的人利用,那權勢就變成擾亂天下的亂因,而權勢被賢能者運用而治理好天下的情況就少了。權勢這東西,既便於治理天下,也可能會擾亂天下。所以《周書》上說:『不要給老虎添上翅膀,否則牠將飛進城邑,任意吃人。』統治者就像那老虎,要是讓不肖的人憑藉權勢,這好比給老虎添上了翅膀。夏桀、商紂造高臺、挖深池來耗盡民力,用炮格的酷刑來傷害民眾的生命。桀、紂能夠胡作非為,是因為天子的威勢成了他們的翅膀。假使桀、紂只是普通的人,他敢開始幹一件壞事,就遭受刑罰了。可見權勢是滋長虎狼之心、造成暴亂事件的東西,也就是天下的大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