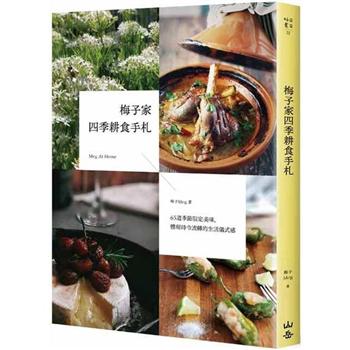Part1 時序,夏末
迎接韭菜開花,變成刻畫著季節的分界,告別夏季的儀式。
大熱天裡最好能不要煮食,我有信心能靠吃剉冰度過整個夏季。
但非要下廚,我寧願開烤箱和計時器後,遠遠逃離戰場,也不要顧在火爐邊上。
●夏末,盼秋涼
下午兩點多,我坐立難安。
站起來,開冰箱,把頭伸進去看了一圈。嘆口氣,關上冰箱。
接著,拉開旁邊的乾貨櫃,眼睛掃過了罐頭、醬料、乾麵區、穀米區,就這樣呆站了三十秒,再次關上門。
這套動作我今天至少做了五次。
牆上時鐘滴答地響著。
再過不久,老的小的,放學下班。而主婦,對於晚餐仍然沒有靈感,腦海一片空白。心情低落,沮喪極了。
這樣的場景對我來說並不尋常,但每年都會發生幾次,而且通常都發生在七月中到八月底。
鬼門開?才不是。
盛夏的太陽炙熱猛烈,連續數星期攝氏四十五度上下的氣溫,才是罪魁禍首。我心愛的小菜園正被沙漠無情的夏季煎著、熬著,除了少數耐熱的植物,滿眼焦黃。
無意識地將落地窗打開一條縫,樹上此起彼落的蟬鳴立刻穿透到屋內。
外頭熱氣緊接著撲面而來,像是開了烤箱。
出不去,感覺像困獸。「好想去剪蔥!摘香草!拔蘿蔔!挖馬鈴薯!」
整天心裡都這樣吶喊著。
料理人缺了自家的好食材,我像是被廢了武功的劍客,坐以待斃。
這是在南加州沙漠地區居住所要付上的代價。務農的人依附時節作息,而盛夏七、八月,正是沙漠最苦悶的時候。
休耕月份的空白,數算著日子盼著韭菜花開,已經成為每年的常態……
●隨著韭菜開花,蔥圃也開始茂盛了起來
院子裡幾圃從廚餘回收長成的蔥叢,足夠全家日常煮食的消耗。
一整年當中,我大概只需要從市場買五、六次蔥,除了天氣過於炎熱或寒冷、生長怠滯的那幾週之外,我們家的蔥錢真是省了不少。
回想第一圃自耕蔥,源自於我跟任職餐廳的廚房討要回來的一大包廚餘蔥頭,在乾燥涼爽的月份胡亂插入土裡,一發不可收拾,自此就連續供應了家裡兩年半的青蔥之需。這段時間,蔥圃開花結籽了兩次,蔥籽掉入土中又兀自長出小蔥苗,於是我又將新苗移植分種成了幾圃。如此一來,即使日照方向和時數隨著季節改變,幾圃分置在園中不同區域的蔥叢,也能夠輪替供給自家廚房所需。
而後,菜園內就固定有蔥圃。整理菜圃時,看不順眼就整叢挖起、換植別處,有時也整株連根拔出使用,而後同樣留下蔥頭再重新植回…… 總之,我覺得蔥這種作物十分粗勇,一年到頭進出土壤也並無大礙,一樣年年繁茂。盛產時,根本來不及吃,只能任由它老化的外葉攤垂一地,看不下去就整圃一口氣剪下來料理;而蔥頭,當然是重新插回土裡,由它生生不息。
進入夏季尾聲,自家菜園裡大部分都還是剛插的幼苗,因為暑熱尚未真正消退,附近市場的蔬菜也是乏善可陳。這時候,院子裡那幾圃茂盛的韭與蔥,還有一年四季都可購得的洋蔥,也可以充當蔬菜料理,添補餐桌菜色的不足。
Part 2 時序,深秋
秋季最讓人開心的,還是自家菜園的蔬菜在接下來幾個月中可以陸續銜接上了。
打開冰箱盤點食材時,總是忍不住嘴角上揚,
料理的靈感也會因著這些美好的蔬材而源源不絕。
我又重新忘情地投入菜園的農活,翻土、除草、播入秋耕的種子。
●風涼,秋耕起
隨著韭菜花季的離去,日照漸短,氣候明顯降溫,吹來的風也是涼涼的,終於開始有秋意了!
當地小農市集開幕的月份,走一趟總是收穫滿滿,這是我每年入秋後最期待的事情之一。我喜歡冰箱裡塞滿各式農產品的感覺,打開冰箱盤點食材時,總是忍不住嘴角上揚,料理的靈感也會因著這些美好的蔬材而源源不絕。
但秋季最讓人開心的,還是自家菜園的蔬菜在接下來幾個月中可以陸續銜接上了。
這對在高溫酷暑裡活活煎熬數月的我們來說,實在是很快樂的事情,我又重新忘情地投入菜園的農活,翻土、除草、播入秋耕的種子。
我每年會選植十幾種不同的葉菜,還有好幾款蘿蔔、馬鈴薯、胡蘿蔔等根莖,固定要種的四季豆、豌豆,以及各種香草。除此之外,也輪耕不同的瓜類、辣椒、茄科等果實類蔬菜。接續整個冬季一直到來年春末,足以供給一家人百分之七十的蔬菜之需,其餘的,就從小農市集補足。
太喜歡這樣的生活方式,吃時令、吃在地,這實在是件讓人快樂的事情。
●秋梨,熱食
雖說美國的夏季也產梨,但秋季的品種更適合料理。當市場出現漂亮緊實的秋梨,我就會一口氣買上許多回家「烤了放著慢慢吃」。
對,就是「烤梨」沒錯!
再好吃的梨,若讓我直接當成水果啃著吃,一次只有淺嚐一個的胃口,但加了楓糖漿及香草莢焗烤後,梨肉變得柔軟迷人,香氣撲鼻,我可以一口氣吃下三個,臉不紅氣不喘。
烤過的梨肉,搭配早餐鬆餅或燕麥也是絕配。秋季的早晨已經可以感覺到涼意,比起冰涼的水果,溫熱的烤梨更加健胃暖心。
不同於烤葡萄,跟華人朋友們聊到「洋梨熱食」的概念,似乎就沒什麼文化衝擊了。
就好比我們熟悉的冰糖燉水梨、小吊梨湯、水梨銀耳等;西式料理也常將洋梨拿來焗烤或是燉煮。如果在烹梨同時添加像是葡萄酒、香草、玫瑰、楓糖、堅果等食材,所有的香氣便會盡數被吸收到梨肉裡,在本身的果香之外更增添層次。
經營餐廳的那幾年,每星期必須做好幾次酒燉洋梨。
當時我們餐廳有道「洋梨溫沙拉」非常受歡迎:將事先燉好的洋梨切片,於小鍋內用奶油快速煎出焦香氣,放在綜合沙拉嫩葉上,搭配羊奶軟酪,以及覆盆子芥香沙拉醬汁…… 為了這道熱銷菜品,我們常常削梨削到手軟。
餐廳的廚房燉梨是這樣的:挑結實的梨種,選外觀蒂頭完整的產品,耐心地一個個削皮、再小心地把籽核挖除。加入葡萄酒、原蔗糖、少許海鹽,蓋過梨身,大火滾開後,再以中小火煨煮二十分鐘,直接於鍋內放涼,冷藏浸泡至少隔夜,二、三天後更美味。
記得自己曾經說過,夏天白酒燉梨、冬季紅酒燉梨,當年餐廳菜色設計也如此依照季節變更。不過,近年來我更愛白葡萄酒,常常寒冬裡開瓶的也是冰冰涼涼的白酒,自己定下的不成文「燉梨原則」也只好調整。
還有,燉梨固然美味,但我最愛的其實是最後剩下的酒漬梨汁,即使是簡單調以蘇打水都非常好喝啊!
●拆解一隻全鴨之後
天氣涼爽,是時候做些花功夫的菜餚了。比起全雞,我更喜歡拆解全鴨。
在美國買到的脫毛全鴨,一般會把鴨脖、胗肝一起附上,包裝好,塞在骨架中空處。將內臟包裝從鴨腹中取出,然後用利刀將兩片鴨胸割下,翻轉過來,沿著脊骨肋條邊上找到腿骨關節,仔細切下帶皮鴨腿,最後是鴨翅。
一口氣處理兩隻全鴨,得到鴨胸、鴨腿各四片,淨鴨架兩付,另外鴨翅、鴨脖、鴨胗、肝等下水邊角料一大盤,足夠我們一家人吃好幾餐,非常實惠。
淨鴨架可以用來煲湯,多餘的鴨皮煉出整罐鴨油,之後用以炒菜做滷,都是美味。鴨腿適合油封, 脆皮鴨胸則和黃瓜、大蔥搭配得天衣無縫,用燙麵餅捲著吃,這在我家常被用來偽裝北京烤鴨。鴨胸還可用來自製臘肉,然後拿來做煲仔飯;而料理胸、腿的同時,用煸炸出的多餘油脂來烤馬鈴薯或是炒四季豆,就可以連同蔬菜一起搞定當日餐食。
經營餐廳的時候,油封鴨腿是最受歡迎的菜色之一。
雖然經過低溫慢火悉心油封的鴨腿,本身酥而不膩、入口即化,已經饒富滋味,然而這道幾乎多數法式餐廳都會供應的經典料理,最終如何在餐盤上呈現,才是真正體現各個廚房不同烹調特色之關鍵。
餐廳裡,我們隨著時令更換配菜菜色。例如夏季,你或許會看見金酥的鴨腿搭配炙烤杏桃和酸櫻桃巴沙米克(Balsamic)醬,而秋冬則換成煎得焦香的酒燉洋梨和紅酒醬。我喜歡配菜裡帶有少許甜和酸的元素,總覺得這樣的味覺背景更能詮釋鴨腿本身的細緻馨香、濃郁微鹹。
在家中復刻油封鴨腿,我仍會悉心搭配當季蔬果,如自家秋收的胡蘿蔔、番茄、馬鈴薯等,淋拌鴨油,焗烤至金黃,與酥脆鹹香的鴨腿極為合拍。全食物,純手工,順時令,這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健康飲食」。
Part3 時序,入冬
摘橙子成了我們家不成文的年度家庭活動。忙碌一下午,以豐收的歡愉結束感恩節假期,迎接冬季。
我的原則是「冬季缸醃、夏天鹽漬」。
趁天涼,整缸酸菜泡菜盡情吃個夠;
至於做成老鹹菜、梅乾菜,那是春天以後的事了。
●冬季才見梅爾檸檬
檸檬在美國雖說四季不缺,但梅爾檸檬(Meyer Lemon)卻只在冬日裡的短短數星期會出現於市面上。梅爾是檸檬與柳橙的混種,皮薄而汁水多、不苦不澀、酸度適中,還帶有淡淡如花似蜜的香氣。朋友家也有種植,逢產季多到自用吃不完,搬了幾袋到公司四處求爺告奶,拜託大家幫忙消耗,我們當然也助人為樂、當仁不讓,每年冬季照例領一大袋回家。
在這裡生活久了,會發現美國人很喜歡用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當生命給了你檸檬) 的開頭來造句。家裡有檸檬樹的人都知道,產季那一樹的檸檬吃到胃泛酸都用不完;送鄰居,左鄰右舍也多半都有檸檬樹,避之不及。所以原句「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 」(當生命用檸檬砸向你,把它們做成檸檬汁),是鼓勵人們換角度思考,化危機為轉機、化困境為福氣的意思。
我不想只做檸檬汁,倒是把檸檬用鹽醃起來,做出比檸檬汁更實惠的鹹檸檬。
回想起人生醃製的第一罐鹹檸檬是在婚前,當時是跟著一位姐妹從越南朋友那兒學來的。原出處無可考,反正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古法,聽說在中國南部省份及東南亞地區都很常見。
對當時年少又沒什麼耐心的我們而言,製作「一年以後才能品嚐」的成品,真是非常考驗耐力的事。還記得第一罐鹹檸檬剛泡起來的時候,接連好幾個星期,幾乎每天對著瓶子晨昏定省,反覆撫摸著瓶身,一邊觀察裡面的動靜。那時我跟當時還是男友的先生已交往近六年時間,姐妹們常開玩笑,戲稱我在幫自己釀製「女兒紅」。
求婚發生在檸檬醃起的幾個月後,匆忙準備婚禮之餘,已經把那罐鹹檸檬忘得乾乾淨淨;婚後一年左右,又購得新屋,每天到工地查看進度,哪還記得有鹹檸檬這檔子事兒。就這樣,那罐鹹檸檬跟著我從小公寓搬到新家,從這個角落換到那個角落,兩、三年的時間,都不曾真正地想起它來。
女兒出生後幾年,某一天我感冒得厲害,鼻子、嗓子、眼睛、喉嚨,無一處舒服。忽然想起了這罐多年以前的「女兒紅」,放膽切取一塊,泡了一杯熱蜂蜜水,宛如陳皮的中藥香氣伴隨著熱氣灌下去,感冒馬上就好了一半。後來,那罐鹹檸檬又陸續被使用了幾年。最後剩餘的幾顆,使用時,已經是存放七年之久的XO等級。
繼越式鹹檸檬之後,我又愛上摩洛哥式的鹽漬檸檬。
不同於越南朋友教的鹹檸檬用鹽水泡製,摩洛哥式的鹽漬檸檬,是用鹽、各種香料及檸檬本身的汁水醃漬的,可依喜好做得又香又辣,製作時程短,醃漬的過程可以在冰箱內冷藏進行,非常方便。這款檸檬的風味,除了鹹味之外,也「鹹感」十足……意思是,比起越式鹹檸檬可以調成飲料的甘醇,摩洛哥鹽漬檸檬更適合應用在料理中,即使搭配大魚大肉也清香撲鼻,化油解膩。
因此,每逢冬季當朋友送上大把檸檬,小廚房的工作就會開始很耗鹽,幾罐檸檬醃起,可以享用到翌年冬檸檬又黃之時。
【後記】
自耕自給,過日子的智慧
二○二○年三月,我們傻站在家附近常去的超市裡,眼前狼藉一片,簡直讓人無法置信。
所有日常用品被掃購一空,衛生紙、清潔劑、護理用品、罐頭以及新鮮蔬果……原本陳列這些商品的貨架上空蕩蕩。
疫情延燒,作為世界第一強國國民的美國人買不到麵包,買不到麵粉,買不到牛奶雞蛋、米飯麵條。
這是我們一個多星期以來第一次出門購物。
兩週前先生工作時收到一罐病人的肺液,而後確診為新冠肺炎患者。那是我們當地的第一例。醫院為了安全起見,居家隔離或有風險的一線人員及家屬。
是的,我們被隔離了!
雖然接續的病毒檢測為陰性,隔離解除回前線上班,但緊接著學校停課,加州也進入半封城狀態,人仰馬翻,待回過神來衝到市場補貨,已經什麼都買不到了。
──
冷凍櫃前走來兩位男士,拉出最後一條冷凍的包裝麵包,而且還是無麩質的,索價七美元。
其中一人拿著冰涼的麵包喃喃低語:「這可以嗎?」然後看看標價,驚呼:「七美元!!」
另一位滿臉為難:「或許我們可以嘗試自己做?」
轉頭看著同樣空空如也的烘焙貨架。上面除了兩包全麥麵粉,其餘無論麵粉、酵母、糖,或是泡打粉等,皆所剩無幾。想必他們從未自己做過麵包,而如今是想做卻也備不齊材料,兩人捧著冷凍麵包糾結了許久,就連站在附近的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他們心中的凝重與擔心。
──
書記錄到了一半的此時,疫情讓我看到生活與食物源頭連結的必要性。
在疫情剛開始的兵荒馬亂中,面對接下來還不知會持續多久的封城及無米之炊,我完全沒有慌亂,腦海裡很快地盤點出家中冰箱及乾貨櫃裡的存貨,細數一遍當下菜圃裡出產的品種,包括那些天生自來的野菜,再迅速地挑揀些尚未搶光的商品,心裡馬上有了可以熬過一個月的底氣。
自耕自給,其實是一種機動性極高的生活方式,要學會順天,隨季節調整變化,即使手邊的食材有限,也可以創造料理。這原是一種生存的本能,是過日子的智慧,可惜現代生活的便利將之逐漸消磨殆盡。
以往,常有朋友在聽到我的生活後不可置信:「什麼?你連這些都自己做?」
我則回答得淡然:「是啊,買不到只好自己做了……」理所應當一般,並不多做解釋。
「自己做」這件事在持續了近二十年後,卻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了。當我執拗地把自己也種進了土裡,生了根,大地連接著我的血脈,它生機蓬勃,我也源源不絕。這種穩紮的踏實感,就是我人生的安定。
──
所以,之後一連串的防疫封城,對我們家來說並沒什麼不同。
小伊甸依舊滿園春景,遍地花開,宅家拈花,蹲菜園、窩廚房,讀書、寫稿、照相,過得渾然忘我。期間,嘗試著將紅亞麻花壓入麵片,用蒲公英花瓣來揉牛奶饅頭,趁著鼠麴草遍地趕快做粿,拿出之前曬好的自家菜脯米(蘿蔔絲乾),炒香肉末紅蔥,順應節氣的鼠麴粿綠得發亮,甜糯Q彈……每天光是採集滿地的野菜花卉,趕著將它們做成時令料理,就忙得樂不可支。
於是,我的居家防疫時光沒有苦悶,只有一如既往平靜的節奏感。
不去想過了幾日、還有幾日,就專心地把每天活得豐富,用享受的心情把手邊每件事情細細做好。
「日子過著過著,就越來越好了。」
我一直是這樣相信著。
迎接韭菜開花,變成刻畫著季節的分界,告別夏季的儀式。
大熱天裡最好能不要煮食,我有信心能靠吃剉冰度過整個夏季。
但非要下廚,我寧願開烤箱和計時器後,遠遠逃離戰場,也不要顧在火爐邊上。
●夏末,盼秋涼
下午兩點多,我坐立難安。
站起來,開冰箱,把頭伸進去看了一圈。嘆口氣,關上冰箱。
接著,拉開旁邊的乾貨櫃,眼睛掃過了罐頭、醬料、乾麵區、穀米區,就這樣呆站了三十秒,再次關上門。
這套動作我今天至少做了五次。
牆上時鐘滴答地響著。
再過不久,老的小的,放學下班。而主婦,對於晚餐仍然沒有靈感,腦海一片空白。心情低落,沮喪極了。
這樣的場景對我來說並不尋常,但每年都會發生幾次,而且通常都發生在七月中到八月底。
鬼門開?才不是。
盛夏的太陽炙熱猛烈,連續數星期攝氏四十五度上下的氣溫,才是罪魁禍首。我心愛的小菜園正被沙漠無情的夏季煎著、熬著,除了少數耐熱的植物,滿眼焦黃。
無意識地將落地窗打開一條縫,樹上此起彼落的蟬鳴立刻穿透到屋內。
外頭熱氣緊接著撲面而來,像是開了烤箱。
出不去,感覺像困獸。「好想去剪蔥!摘香草!拔蘿蔔!挖馬鈴薯!」
整天心裡都這樣吶喊著。
料理人缺了自家的好食材,我像是被廢了武功的劍客,坐以待斃。
這是在南加州沙漠地區居住所要付上的代價。務農的人依附時節作息,而盛夏七、八月,正是沙漠最苦悶的時候。
休耕月份的空白,數算著日子盼著韭菜花開,已經成為每年的常態……
●隨著韭菜開花,蔥圃也開始茂盛了起來
院子裡幾圃從廚餘回收長成的蔥叢,足夠全家日常煮食的消耗。
一整年當中,我大概只需要從市場買五、六次蔥,除了天氣過於炎熱或寒冷、生長怠滯的那幾週之外,我們家的蔥錢真是省了不少。
回想第一圃自耕蔥,源自於我跟任職餐廳的廚房討要回來的一大包廚餘蔥頭,在乾燥涼爽的月份胡亂插入土裡,一發不可收拾,自此就連續供應了家裡兩年半的青蔥之需。這段時間,蔥圃開花結籽了兩次,蔥籽掉入土中又兀自長出小蔥苗,於是我又將新苗移植分種成了幾圃。如此一來,即使日照方向和時數隨著季節改變,幾圃分置在園中不同區域的蔥叢,也能夠輪替供給自家廚房所需。
而後,菜園內就固定有蔥圃。整理菜圃時,看不順眼就整叢挖起、換植別處,有時也整株連根拔出使用,而後同樣留下蔥頭再重新植回…… 總之,我覺得蔥這種作物十分粗勇,一年到頭進出土壤也並無大礙,一樣年年繁茂。盛產時,根本來不及吃,只能任由它老化的外葉攤垂一地,看不下去就整圃一口氣剪下來料理;而蔥頭,當然是重新插回土裡,由它生生不息。
進入夏季尾聲,自家菜園裡大部分都還是剛插的幼苗,因為暑熱尚未真正消退,附近市場的蔬菜也是乏善可陳。這時候,院子裡那幾圃茂盛的韭與蔥,還有一年四季都可購得的洋蔥,也可以充當蔬菜料理,添補餐桌菜色的不足。
Part 2 時序,深秋
秋季最讓人開心的,還是自家菜園的蔬菜在接下來幾個月中可以陸續銜接上了。
打開冰箱盤點食材時,總是忍不住嘴角上揚,
料理的靈感也會因著這些美好的蔬材而源源不絕。
我又重新忘情地投入菜園的農活,翻土、除草、播入秋耕的種子。
●風涼,秋耕起
隨著韭菜花季的離去,日照漸短,氣候明顯降溫,吹來的風也是涼涼的,終於開始有秋意了!
當地小農市集開幕的月份,走一趟總是收穫滿滿,這是我每年入秋後最期待的事情之一。我喜歡冰箱裡塞滿各式農產品的感覺,打開冰箱盤點食材時,總是忍不住嘴角上揚,料理的靈感也會因著這些美好的蔬材而源源不絕。
但秋季最讓人開心的,還是自家菜園的蔬菜在接下來幾個月中可以陸續銜接上了。
這對在高溫酷暑裡活活煎熬數月的我們來說,實在是很快樂的事情,我又重新忘情地投入菜園的農活,翻土、除草、播入秋耕的種子。
我每年會選植十幾種不同的葉菜,還有好幾款蘿蔔、馬鈴薯、胡蘿蔔等根莖,固定要種的四季豆、豌豆,以及各種香草。除此之外,也輪耕不同的瓜類、辣椒、茄科等果實類蔬菜。接續整個冬季一直到來年春末,足以供給一家人百分之七十的蔬菜之需,其餘的,就從小農市集補足。
太喜歡這樣的生活方式,吃時令、吃在地,這實在是件讓人快樂的事情。
●秋梨,熱食
雖說美國的夏季也產梨,但秋季的品種更適合料理。當市場出現漂亮緊實的秋梨,我就會一口氣買上許多回家「烤了放著慢慢吃」。
對,就是「烤梨」沒錯!
再好吃的梨,若讓我直接當成水果啃著吃,一次只有淺嚐一個的胃口,但加了楓糖漿及香草莢焗烤後,梨肉變得柔軟迷人,香氣撲鼻,我可以一口氣吃下三個,臉不紅氣不喘。
烤過的梨肉,搭配早餐鬆餅或燕麥也是絕配。秋季的早晨已經可以感覺到涼意,比起冰涼的水果,溫熱的烤梨更加健胃暖心。
不同於烤葡萄,跟華人朋友們聊到「洋梨熱食」的概念,似乎就沒什麼文化衝擊了。
就好比我們熟悉的冰糖燉水梨、小吊梨湯、水梨銀耳等;西式料理也常將洋梨拿來焗烤或是燉煮。如果在烹梨同時添加像是葡萄酒、香草、玫瑰、楓糖、堅果等食材,所有的香氣便會盡數被吸收到梨肉裡,在本身的果香之外更增添層次。
經營餐廳的那幾年,每星期必須做好幾次酒燉洋梨。
當時我們餐廳有道「洋梨溫沙拉」非常受歡迎:將事先燉好的洋梨切片,於小鍋內用奶油快速煎出焦香氣,放在綜合沙拉嫩葉上,搭配羊奶軟酪,以及覆盆子芥香沙拉醬汁…… 為了這道熱銷菜品,我們常常削梨削到手軟。
餐廳的廚房燉梨是這樣的:挑結實的梨種,選外觀蒂頭完整的產品,耐心地一個個削皮、再小心地把籽核挖除。加入葡萄酒、原蔗糖、少許海鹽,蓋過梨身,大火滾開後,再以中小火煨煮二十分鐘,直接於鍋內放涼,冷藏浸泡至少隔夜,二、三天後更美味。
記得自己曾經說過,夏天白酒燉梨、冬季紅酒燉梨,當年餐廳菜色設計也如此依照季節變更。不過,近年來我更愛白葡萄酒,常常寒冬裡開瓶的也是冰冰涼涼的白酒,自己定下的不成文「燉梨原則」也只好調整。
還有,燉梨固然美味,但我最愛的其實是最後剩下的酒漬梨汁,即使是簡單調以蘇打水都非常好喝啊!
●拆解一隻全鴨之後
天氣涼爽,是時候做些花功夫的菜餚了。比起全雞,我更喜歡拆解全鴨。
在美國買到的脫毛全鴨,一般會把鴨脖、胗肝一起附上,包裝好,塞在骨架中空處。將內臟包裝從鴨腹中取出,然後用利刀將兩片鴨胸割下,翻轉過來,沿著脊骨肋條邊上找到腿骨關節,仔細切下帶皮鴨腿,最後是鴨翅。
一口氣處理兩隻全鴨,得到鴨胸、鴨腿各四片,淨鴨架兩付,另外鴨翅、鴨脖、鴨胗、肝等下水邊角料一大盤,足夠我們一家人吃好幾餐,非常實惠。
淨鴨架可以用來煲湯,多餘的鴨皮煉出整罐鴨油,之後用以炒菜做滷,都是美味。鴨腿適合油封, 脆皮鴨胸則和黃瓜、大蔥搭配得天衣無縫,用燙麵餅捲著吃,這在我家常被用來偽裝北京烤鴨。鴨胸還可用來自製臘肉,然後拿來做煲仔飯;而料理胸、腿的同時,用煸炸出的多餘油脂來烤馬鈴薯或是炒四季豆,就可以連同蔬菜一起搞定當日餐食。
經營餐廳的時候,油封鴨腿是最受歡迎的菜色之一。
雖然經過低溫慢火悉心油封的鴨腿,本身酥而不膩、入口即化,已經饒富滋味,然而這道幾乎多數法式餐廳都會供應的經典料理,最終如何在餐盤上呈現,才是真正體現各個廚房不同烹調特色之關鍵。
餐廳裡,我們隨著時令更換配菜菜色。例如夏季,你或許會看見金酥的鴨腿搭配炙烤杏桃和酸櫻桃巴沙米克(Balsamic)醬,而秋冬則換成煎得焦香的酒燉洋梨和紅酒醬。我喜歡配菜裡帶有少許甜和酸的元素,總覺得這樣的味覺背景更能詮釋鴨腿本身的細緻馨香、濃郁微鹹。
在家中復刻油封鴨腿,我仍會悉心搭配當季蔬果,如自家秋收的胡蘿蔔、番茄、馬鈴薯等,淋拌鴨油,焗烤至金黃,與酥脆鹹香的鴨腿極為合拍。全食物,純手工,順時令,這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健康飲食」。
Part3 時序,入冬
摘橙子成了我們家不成文的年度家庭活動。忙碌一下午,以豐收的歡愉結束感恩節假期,迎接冬季。
我的原則是「冬季缸醃、夏天鹽漬」。
趁天涼,整缸酸菜泡菜盡情吃個夠;
至於做成老鹹菜、梅乾菜,那是春天以後的事了。
●冬季才見梅爾檸檬
檸檬在美國雖說四季不缺,但梅爾檸檬(Meyer Lemon)卻只在冬日裡的短短數星期會出現於市面上。梅爾是檸檬與柳橙的混種,皮薄而汁水多、不苦不澀、酸度適中,還帶有淡淡如花似蜜的香氣。朋友家也有種植,逢產季多到自用吃不完,搬了幾袋到公司四處求爺告奶,拜託大家幫忙消耗,我們當然也助人為樂、當仁不讓,每年冬季照例領一大袋回家。
在這裡生活久了,會發現美國人很喜歡用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當生命給了你檸檬) 的開頭來造句。家裡有檸檬樹的人都知道,產季那一樹的檸檬吃到胃泛酸都用不完;送鄰居,左鄰右舍也多半都有檸檬樹,避之不及。所以原句「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 」(當生命用檸檬砸向你,把它們做成檸檬汁),是鼓勵人們換角度思考,化危機為轉機、化困境為福氣的意思。
我不想只做檸檬汁,倒是把檸檬用鹽醃起來,做出比檸檬汁更實惠的鹹檸檬。
回想起人生醃製的第一罐鹹檸檬是在婚前,當時是跟著一位姐妹從越南朋友那兒學來的。原出處無可考,反正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古法,聽說在中國南部省份及東南亞地區都很常見。
對當時年少又沒什麼耐心的我們而言,製作「一年以後才能品嚐」的成品,真是非常考驗耐力的事。還記得第一罐鹹檸檬剛泡起來的時候,接連好幾個星期,幾乎每天對著瓶子晨昏定省,反覆撫摸著瓶身,一邊觀察裡面的動靜。那時我跟當時還是男友的先生已交往近六年時間,姐妹們常開玩笑,戲稱我在幫自己釀製「女兒紅」。
求婚發生在檸檬醃起的幾個月後,匆忙準備婚禮之餘,已經把那罐鹹檸檬忘得乾乾淨淨;婚後一年左右,又購得新屋,每天到工地查看進度,哪還記得有鹹檸檬這檔子事兒。就這樣,那罐鹹檸檬跟著我從小公寓搬到新家,從這個角落換到那個角落,兩、三年的時間,都不曾真正地想起它來。
女兒出生後幾年,某一天我感冒得厲害,鼻子、嗓子、眼睛、喉嚨,無一處舒服。忽然想起了這罐多年以前的「女兒紅」,放膽切取一塊,泡了一杯熱蜂蜜水,宛如陳皮的中藥香氣伴隨著熱氣灌下去,感冒馬上就好了一半。後來,那罐鹹檸檬又陸續被使用了幾年。最後剩餘的幾顆,使用時,已經是存放七年之久的XO等級。
繼越式鹹檸檬之後,我又愛上摩洛哥式的鹽漬檸檬。
不同於越南朋友教的鹹檸檬用鹽水泡製,摩洛哥式的鹽漬檸檬,是用鹽、各種香料及檸檬本身的汁水醃漬的,可依喜好做得又香又辣,製作時程短,醃漬的過程可以在冰箱內冷藏進行,非常方便。這款檸檬的風味,除了鹹味之外,也「鹹感」十足……意思是,比起越式鹹檸檬可以調成飲料的甘醇,摩洛哥鹽漬檸檬更適合應用在料理中,即使搭配大魚大肉也清香撲鼻,化油解膩。
因此,每逢冬季當朋友送上大把檸檬,小廚房的工作就會開始很耗鹽,幾罐檸檬醃起,可以享用到翌年冬檸檬又黃之時。
【後記】
自耕自給,過日子的智慧
二○二○年三月,我們傻站在家附近常去的超市裡,眼前狼藉一片,簡直讓人無法置信。
所有日常用品被掃購一空,衛生紙、清潔劑、護理用品、罐頭以及新鮮蔬果……原本陳列這些商品的貨架上空蕩蕩。
疫情延燒,作為世界第一強國國民的美國人買不到麵包,買不到麵粉,買不到牛奶雞蛋、米飯麵條。
這是我們一個多星期以來第一次出門購物。
兩週前先生工作時收到一罐病人的肺液,而後確診為新冠肺炎患者。那是我們當地的第一例。醫院為了安全起見,居家隔離或有風險的一線人員及家屬。
是的,我們被隔離了!
雖然接續的病毒檢測為陰性,隔離解除回前線上班,但緊接著學校停課,加州也進入半封城狀態,人仰馬翻,待回過神來衝到市場補貨,已經什麼都買不到了。
──
冷凍櫃前走來兩位男士,拉出最後一條冷凍的包裝麵包,而且還是無麩質的,索價七美元。
其中一人拿著冰涼的麵包喃喃低語:「這可以嗎?」然後看看標價,驚呼:「七美元!!」
另一位滿臉為難:「或許我們可以嘗試自己做?」
轉頭看著同樣空空如也的烘焙貨架。上面除了兩包全麥麵粉,其餘無論麵粉、酵母、糖,或是泡打粉等,皆所剩無幾。想必他們從未自己做過麵包,而如今是想做卻也備不齊材料,兩人捧著冷凍麵包糾結了許久,就連站在附近的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他們心中的凝重與擔心。
──
書記錄到了一半的此時,疫情讓我看到生活與食物源頭連結的必要性。
在疫情剛開始的兵荒馬亂中,面對接下來還不知會持續多久的封城及無米之炊,我完全沒有慌亂,腦海裡很快地盤點出家中冰箱及乾貨櫃裡的存貨,細數一遍當下菜圃裡出產的品種,包括那些天生自來的野菜,再迅速地挑揀些尚未搶光的商品,心裡馬上有了可以熬過一個月的底氣。
自耕自給,其實是一種機動性極高的生活方式,要學會順天,隨季節調整變化,即使手邊的食材有限,也可以創造料理。這原是一種生存的本能,是過日子的智慧,可惜現代生活的便利將之逐漸消磨殆盡。
以往,常有朋友在聽到我的生活後不可置信:「什麼?你連這些都自己做?」
我則回答得淡然:「是啊,買不到只好自己做了……」理所應當一般,並不多做解釋。
「自己做」這件事在持續了近二十年後,卻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了。當我執拗地把自己也種進了土裡,生了根,大地連接著我的血脈,它生機蓬勃,我也源源不絕。這種穩紮的踏實感,就是我人生的安定。
──
所以,之後一連串的防疫封城,對我們家來說並沒什麼不同。
小伊甸依舊滿園春景,遍地花開,宅家拈花,蹲菜園、窩廚房,讀書、寫稿、照相,過得渾然忘我。期間,嘗試著將紅亞麻花壓入麵片,用蒲公英花瓣來揉牛奶饅頭,趁著鼠麴草遍地趕快做粿,拿出之前曬好的自家菜脯米(蘿蔔絲乾),炒香肉末紅蔥,順應節氣的鼠麴粿綠得發亮,甜糯Q彈……每天光是採集滿地的野菜花卉,趕著將它們做成時令料理,就忙得樂不可支。
於是,我的居家防疫時光沒有苦悶,只有一如既往平靜的節奏感。
不去想過了幾日、還有幾日,就專心地把每天活得豐富,用享受的心情把手邊每件事情細細做好。
「日子過著過著,就越來越好了。」
我一直是這樣相信著。